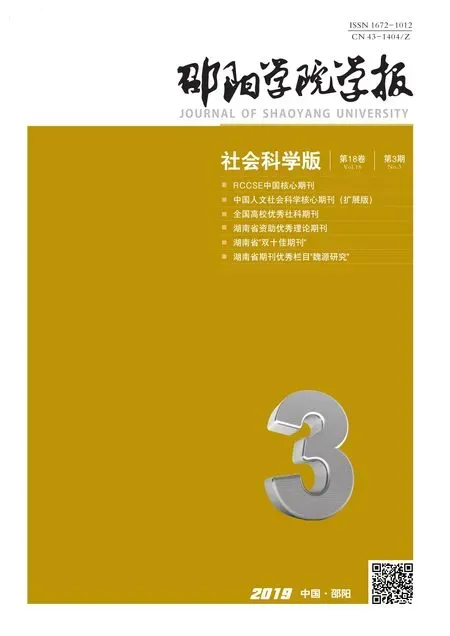从“Virtue”的中译本看亚里士多德与朱熹思想的融通
2019-06-26陈永宝
陈永宝
(1.台湾辅仁大学 哲学系, 台湾 新北 24205; 2.三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三明 365004)
朱熹理学中是否蕴含着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注本文采用廖申白的译注版的《尼可马可伦理学》,以下同此版本。亚里士多德,因翻译不同又称亚里斯多德,以下称“亚氏”。里所规定的伦理意涵,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从流传较广的廖申白的中文译本及周辅成所作的书序中,我们不难发现两位学者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了融合这两种思想的倾向。这里特别指出的是,周辅成所做的序言中,大量引用中国古典文献来回应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如其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大家知道以‘中庸’为原则。……亚里士多德所谓‘中’,虽然有调和妥协的意义,可被乡愿利用;但更重要的,是面向一个高远的目的,坚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去接近它,恰如其分地取得它”[1]Ⅷ。同时,他还引用了《中庸》的原文“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免而中,不思而得;从容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2]38来阐述他的想法。
《中庸》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这个版本。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周辅成在这里试图借《中庸》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朱熹理学搭建一个桥梁,有融合二者的趋向。在此基础上,谢晓东借助他的引导,在二者的结合上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指出,“亚里士多德对至善问题的思考在西方古典时代很具有代表性。而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朱熹对至善的研究是比较系统和完整的。故而,对中西两位哲学大家的至善观予以比较就具有了一定的价值和意义”[3]51。这里,谢晓东将“Virtue”理解为“德性”,因此将两者结合的切入点定位为“至善思想”。于是,对亚氏德行论的理解便被放置在了一个静态的框架中。相反,潘小慧指出,将Virtue这个词由“德性”翻译成“德行”更为合适[4]16,这样或许更能反映亚氏的原意。她指出,“关于‘Virtue’的中文译名,远东英汉辞典、牛津高级英英、英汉双解辞典、世界英汉四用辞典等三部辞典均翻译成‘德行’。在伦理学及伦理教育的学术圈里,最通行的译名也是‘德行’,如沈青松、黄藿、蔡信安。大陆则多见‘德性’和‘美德’二种译名,如龚群、戴扬毅等译Alasdair Maclntyre所著之AfterVitue为《德性之后》;另如王海明。台湾教育学者也有力主应译为‘美德’者,如但昭伟,另见林逢祺。笔者在此,采用‘德行’和‘德行伦理学’的译名,除了通行之外还有二个理由:第一,《论语·先进11.2》里提到孔子的四科教育,分别为‘德行’、‘言语’、‘政事’及‘文学’,‘德行’居首,‘德行’是中国早有的语汇;第二,‘Virtue’意指一种选择的好习惯,因此可译为‘德行’,而‘Virtue Ethics’则为求一致故可译为‘德行伦理学’”。[4]16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并非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对“德”的追求上,而是在“活动”中寻找人存在的意义。
于是,我们将以上学者的观点综合起来,便可提出这样的问题:朱熹理学是否存在亚氏“行”或“实践”的部分?朱熹的“内圣”之“行”,是否等同于或近似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理智德行”的含义?这成为本文讨论的核心。
一、两种思维概念的辨析
(一)亚氏“Virtue”的“德行”与“德性”
朱熹理学中存在“行”的部分,与亚氏“Virtue”概念的动态诠释部分较为相近。亚氏说:“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其他研究不同,不是思辨的,而有一种实践目的(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解德性,而是为了使自己有德,否则这种研究就毫无用处),我们就必须研究实践的性质,研究我们应当怎样实践。”[1]37这也就是说,亚氏的德性的重点在于“做”,或在于“行”。于是,我们这里可以得出,理解亚氏“善理念”的动态状态,需要我们将“Virtue”这个词采取进一步的阐释与梳理。“德行”相较于“德性”更加接近亚氏伦理学的原意。也就是说,亚氏的幸福观不是知识论式的解释,也不是柏拉图的静态式的固守,而在于进入到社会现实之中或人的实践之中去探索。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出现的众多概念中,如获得、称赞、适度、选择、考虑、希望、勇敢、节制、放纵、理解、友爱……,我们明显可以发现,动态角度分析才是理解亚氏解决幸福问题的最主要方式。也就是说,如果借用中国哲学的概念系统,亚氏的伦理学是一种以工夫论为主体的伦理学。因此,将“Virtue”翻译成“德行”而不是“德性”或“美德”,是更为符合亚氏原意的。
此外,在语源学上,“Virtue”译为“德行”也较为精确。“从语源来看,‘德行’(virtue)一词来自希腊文的ρετ(arete),本义是‘卓越’(excellence),泛指事物美善的卓越(the excellence of perfection of a thing);与‘恶’(vice)作为‘事物美善的阙如’(a defect or absence of perfection due to a thing)正好相反。‘德行’(virtue)的拉丁文是virtus,与拉丁文的‘男人’(vir〔man〕)及‘能力’(vis〔power〕)有相同的根源,原意是男人的力量,而男人的主要力量在于‘坚毅’或‘勇敢’;此词的拉丁文也泛指完成某些合乎人性行为的能力和倾向。”[4]65即使我们不纠结于“卓越”“坚毅”“勇敢”在当时运用时的词性(即形容词、动词或名词),但就其通常的用法来看,它至少蕴含着大量的动态意涵。因此,“行”相对于“性”,在中文的语境中,更加符合亚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原意。当然,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virtue有静态成分,也不是说将virtue翻译成“德性”或“美德”就是错误的。对于将西方概念翻译为中文概念时的差异,我们不能过于苛责,只能基于研究现状,选择学者们认为较为合理的一种翻译结果。同时,翻译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就要求我们在对待西方文献的中文译本时,要有一种相对的包容态度。
从这一点上看,亚氏的“以善作为目的”的伦理学建构,主要是以一种动态的方式进行的“德行”伦理学。那么,关于“行”或“实践”,我们能否在朱熹理学的概念范畴架构中寻找出相似的概念呢?
(二)朱熹理学的“至、止”之行
谢晓东在论证朱熹与亚氏“至善”思想时,指出:“朱熹主要通过对《大学》三纲领中的‘止于至善’一语的诠释来切入对至善问题的思考。‘至善’一词是由‘至’和‘善’二字组合而成,对于朱子来说,‘善’字轻,‘至’字重。因此,应该先搞清‘至’字的含义。”[3]52谢晓东此引文中的材料来源于《朱子语类》。[6]270也就是说,在论证朱熹理学与亚氏伦理学的时候,谢晓东敏锐地观察到“至”这个概念对于沟通朱熹与亚氏的桥梁作用。只不过,由于他将关注点集中于“至”上,如“在对‘道盛德至善’予以解释时,朱子认为‘盛也,至也,皆无以复加之词。’也就是说,‘至’具有‘无以复加’的特性,它是一个形容词。……就性质而言,‘至善’是指‘极好’。‘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是极好处。必到极处,便是道理十分尽头,无一毫不尽,故曰至善。’(《朱子语类》卷十四,第267页)至善是极好处。……就数量而言,‘至善’是指‘最好’。……因此,至善具有‘最高善’和‘最完整的善’的意思。从字面意义而言,朱熹的观点同于亚里士多德”[3]52。在将“Virtue”翻译成“德性”的情况下,谢晓东将朱熹与亚氏的联合点定位于“至”的阐述是合理的。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商榷:
一是谢晓东认为朱熹的“至”是一个形容词,如“‘至’具有‘无以复加’的特性,它是一个形容词”,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朱熹在诠释“至”的概念时,并不只把“至”诠释为形容词,“至”在朱熹的语词运用中,也有动词的含义。如其在解释“格物致知”时,他将“格”诠释为“至也”[2]5。这里的“至”至少有“达到”之意,而非只是形容词的“最”或“最完善”。
二是只将“至善”理解为“最高善”和“最完整的善”,也是一种静态的诠释。这种静态的诠释同样值得商榷。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如果将“Virtue”翻译成“德行”,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朱熹对于“止于至善”这四个字的侧重程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工夫论的角度来诠释朱熹理学的这段话,应该将重点放置于“止”而不是“至”。那么,朱熹的“止”是什么含义呢?朱熹在解释“止于至善”时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2]5。在诠释“知止而后有定”时,说“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2]5。从《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出现的这个释中,我们可以看到,“止”至少有“达到至善过程”的这个含义,朱熹在这里主要是要强调“致知在格物”。
综上所述,朱熹理学中确实存在“行”的部分,而这与亚氏强调“活动”“实践”是殊途同归。因此,从动态的“行”的角度来看,朱熹和亚氏的“德行”观念似乎是相同的。
二、朱熹的“内圣之行”
(一)朱熹“内圣之学”之“实践”
以“心性之学”对抗佛老对南宋士大夫的影响,这应该是朱熹着重谈心性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朱熹的“心性之学”,被当今学者解读较多的一个角度就是工夫论。它结合朱熹的“内圣之学”与后世学者研究工夫论的视角,可得出朱熹理学中存在着“内圣之行”这个结论。至少在“已发未发”或“发而中节”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上,可做动态的诠释。同时,也可以从朱熹反对李延平只做“静心工夫”这一点上得到更为确凿的证据。朱熹认为,“今人皆不肯于根本上理会。如‘敬’字,只是将来说,更不做将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无凑泊处。明道延平皆教人静坐。看来须是静坐”[6]210。又如,朱熹说:“敬非是块然兀坐,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而后谓之敬。只是有所畏谨,不敢放纵,如此则身心收敛,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气象自别。存得此心乃可为学。”[6]211阐述朱熹理学由“内圣之学”转为“内圣之行”,是对朱熹理学由知识论转向工夫论的肯定,而工夫论又是儒家入世思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这一点来看,朱熹的“内圣之行”的这种说法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这种说法也面临着挑战,如杨祖汉总结牟宗三对朱子的定论时指出,“自从牟宗三先生《心体与性体》写成,对朱子的思想形态,几已论定。即朱子是以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之理论架构,展开其本体论、工夫论之种种说法。在宇宙论上之理气二分,决定了在心性论、工夫论上之心、性(理)为二,性理不活动,活动者是气,而心是活动,故心是气。心虽是虚灵知觉,但因其为活动,故心只能是气,不能是理。心可藉其虚灵知觉之能以知理,依理而活动,使情感之活动亦依性理而行,此为‘心统性情’”[7]195。
可以说,依据这种阐述,呈现“动态的”不是心本身,而是“气”。杨祖汉在注解中指出:“牟先生判朱子系统的关键在于心不即理,理成了存有而不活动,因此反对者往往特别强调朱子言心的意义,如钱穆先生以为朱子未尝外心言理及言性,心之重要性更胜于理,但对于心与理或性之异,却无明白剖析。金春峰教授亦将中和旧说与新说中所言之心都视为‘道德的本心’,故两者并非不同的系统,但并未就朱子文献一一作仔细说明,故其说缺乏说服力。至于唐君毅先生,较能根据朱子文献作有深度异议,其认为朱子言心于宇宙论或泛论工夫论时,跟心性论与直接相应心性论的工夫论上实有不同,如此则朱子在宇宙论上视心为气,在心性论上心又不是气,便造成朱子理论的不一致。另外,陈来先生对于朱子言心,也能紧扣文献作讨论,认为知觉之心不属于形而下者,不可言气,但并未针对牟先生说作响应。”[7]197
针对上面出现的矛盾,杨祖汉主张“从朱子重敬的角度,重新省察朱子的中和新旧说,由此对朱子论心,及心性的关系,试图作一不同于牟先生及近时学人的诠释”[7]198。在这里可以看出,朱熹的伦理学应该是一种以“敬”为工夫的伦理学。朱熹本人对“敬”也颇为重视,如其认为,“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济之以义,辨其是非,则不活。若熟后,敬便有义,义便有敬。静则察其敬与不敬,动则察其义与不义。‘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6]216因此,正如杨祖汉所关注的“持敬”,这个“持”字至少可以明白朱熹的内圣之学有一种“实践德行”的成份。
(二)“正心诚意”与“格物致知”
那么,这种实践是“意动”还是“行动”?如果朱熹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只是一种“意动”,那对朱熹理学的理解就陷入与佛教纠缠不清的状态中,无非给出的区隔标准是“入世”还是“出世”。那如果朱熹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是一种“行动”,那这种行动的主体是心的已发未发,还是气的阴阳流变,又需要加以解释。我们至少可以认为,朱熹理学在内圣方面没有那么“纯粹”,或者说他的理论本来就在反对“意动”或“行动”这两个极端而主张兼而有之。因此,“正心诚意”和“格物致知”并非是平常理解的“先后”关系。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2]4。这里的先后,正如讨论朱子的“理先气后”的“先后”一样,存在着时间的先后、逻辑的先后、形而上的先后,还是理论上的先后等争议性讨论。[9]84-89朱熹对“先后”问题的理解,不是从“时间”的标准去衡量,而是将其理解为二者同时共在,或至多理解为“理论次序”的先后关系,这样似乎更为合理。这种打破常识中关于“先后”的理解,也应该适用于“格物致知”一定在“正心诚意”之先的思路。
基于此,我们基本上把朱熹理学中的“正心诚意”和“格物致知”两个最重要的伦理学部分给阐述出来,并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诠释。其目的就在于说明,朱熹的“正心诚意”与亚氏的“理论德行”、朱熹的“格物致知”与亚氏的“实践德行”,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关联。
三、亚氏的“理智之行”与“实践之行”
亚氏将灵魂的德行分为“道德德行”和“理智德行”[1]165。对于这一点,廖申白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人的德性(行)在亚里士多德以及许多其他哲学家那里通常是指相应于灵魂的非逻各斯的即欲望的部分的德性(行)。人的灵魂有一个有逻各斯的部分和一个没有逻各斯的部分。相应地,人的德性(行)可以分行道德的德性(行)和理智的德性(行)两部分。理智德性(行)可以由教导生成,道德德性(行)则需要通过练习来养成。理智德性(行)又可以分为理论德性(行)和实践理性(行)的”[1]ⅩⅩⅥ。
廖申白指出,“智慧(Philosophic wisdom/Margites)是理论理性的德行,是人的最高等的德性。明智(Practical wisdom)是实践的德行,一方面作为理智德性可以由教导而生成;另一方面由于与道德不可分离其育成又离不开习惯”[1]ⅩⅩⅥ。那么,这里的智慧是否可以看成是朱熹理学中的“理”或“性”,这里的“明智”是否可以被理解为朱熹理学中的“气”或“阴阳”在伦理学视角中的运行状态。如果我们可以找到相关的证据,是否就可以说明,虽然亚氏与朱熹处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宗教背景观,但其“伦理学”的视角具有一致性。于是,我们必须进一步对亚氏的智慧和明智进行诠释。
亚氏的“智慧”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即所谓的“物理学之后”。廖申白在翻译亚氏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7部分时,给这一部分附加上“智慧”的标题,指出了这部分包含了亚氏对智慧一词的界定。亚氏认为,“智慧这个词,我们在技艺上用于述说那些技艺最完善的大师。……在这种用法上,智慧仅仅是指技艺上的德性”[1]174-175。但是,他随后又指出“某些人总体上有智慧,而不是某些方面,……所以,智慧显然是各种科学中最为完善者。有智慧的人不仅知道从始点推出的结论,而且真切地知晓那些始点。所以,智慧……必定是关于最高等的题材的、居首位的科学。”[1]175这里的“最高善”与“最高等的题材、居首位的科学”,与朱熹理学中的“性”观念十分相似。朱熹的“性”观念分为“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与亚氏前面提到“技艺上的德性”十分相似。朱熹认为,“人物性本同,只气禀异”[6]58。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人物性本同”可以看成是亚氏“技艺上的德性”。朱熹认为人与人是不同的,这不是“性”的不同,而是“气禀的差异”。这个差异就导致了每个人无法达到自己在道德上“技艺的德性”。如果“气禀之性”足够优良,那么“气禀之性”就构成了朱熹所提出的“天地之性”,如朱熹所说,“人物之生,天赋之以此理,未尝不同,但人物之禀受自有异耳”[6]58。于是“气禀之性”与“天地之性”达成合和,也就可以说“气质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6]68。而这个“天地之性”十分近似于亚氏伦理学中“最为完善者”的智慧。于是,我们的第一个疑问得到了相应的解答。

笔者在这里比较赞同多玛斯的诠释,这种诠释更加接近于亚氏关于“实践”的内涵。因此,将其译于“明智”或“智德”,均可说得通。也就是说,亚氏的phronesis是一种动态的践行伦理的行为,而不该只局限在分析式的静态思维模式中。那么,从这一角度来看,他的明智与朱熹理学中的“气”“阴阳”或是“心统性情”的“心”,具有一定相似性。
四、结语
朱熹理学的伦理学思想,与亚氏的伦理学思想,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二者在面对“善”“德”的思考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二者毕竟相隔时间较远,中西地理空间位置差异较大,思想沟通也较为不便。因此,二者思想中表现出来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从某种角度上说,朱熹的伦理学思想更接近于多玛斯(Thomas Aquinas)解读下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我们也可以将其看成是多玛斯的思想。如多玛斯提出的四德之说,即智德、义德、勇德和节德[8]Ⅲ,与朱熹理学中的止于至善、正心诚意、心统性情、发而中节等核心观念更为相近。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朱熹理学中确实蕴含着亚氏的伦理学观念,二者的关注点均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问题。但由于空间、时间、宗教背景、现实问题等因素的差异,二者是不可能完全等同的。中西语词概念意义的完全等同,不是中国学者研究此类问题的出发点和目标,也不是做比较研究的正确之路。因此,我们要做的工作是,通过后世学者对二者的研究,揭示出二者在伦理学方面的异同点,进而对二者的理论加以完善。无论是以中国哲学诠释西方哲学,还是以西方思维诠释中国思想,这都是当今学者必须面对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