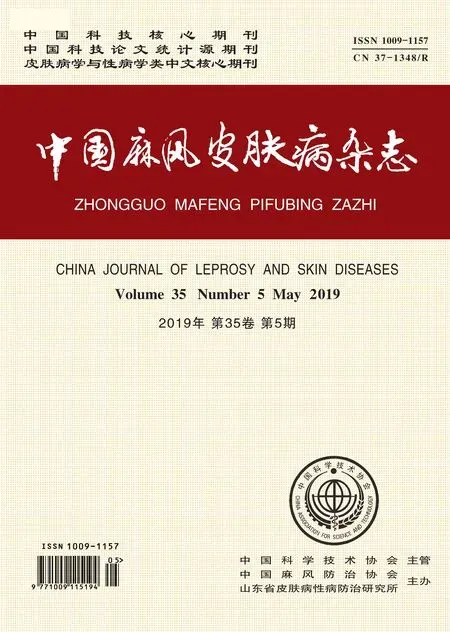现代化背景下的侗族麻风习俗与文化变迁
——以黎平县麻风村为例
2019-06-01周仕阳石庆菊王景权
周仕阳 石庆菊 王景权
侗族是我国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分布以黔湘桂交界区为主,总人口约280万,语言为侗语,民族习俗与文化特征浓厚。长久以来,侗族地区同样深受麻风危害,了解侗族地区有关麻风的习俗与文化认知,对于更好解决侗族地区麻风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黎平县,总人口55万,其中侗族人口38.5万,约占全县总人口70%,有“侗乡之都”的称号。全县从1949年至2017年累计发现麻风781例,其中602例为侗族。2017年,全县仅有现症病人2例。本文以黎平县麻风村(朝阳医院)为例,探讨侗族习俗与文化中对麻风的传统认知以及在现代化背景下的变迁,以期增进对麻风历史与现状的认识,推进侗族地区消除麻风危害的进程。
1 麻风村:形成历史与现状
在侗族居民历史中,何时出现麻风病患,无考证,最早据《黎平县志》[1]载:
“清,光绪年间,已有银朝村吴公黑、吴婢黑祖孙俩人患麻风。被众驱至村东南五华里山腰居住,后死于山上(侗语名高雷)。从此,人们不敢进入此山。
民国六年(1917),又有该村吴补好、吴补囡二人亦患麻风,又被驱进此山。麻风病人在外讨饭期间,经过互相认识,结识了本县的平天、肇兴、水口、洪州、以及毗邻广西三江等地的麻风病人,得知那里有座麻风山,为求得一个共同棲身之地,就逐渐集中来高雷。
民国三十三年(1944)时,先后有20余个麻风患者到高雷来搭棚居住。”
20世纪50年代,响应国家隔离政策与自身需要。1955年,黎平县政府对麻风病人集中隔离管理。1958年,黎平县委员会在晚清、民国时期麻风病人自由组合聚集地(黎平县口江乡银朝村雷岭坡脚)建立麻风病医院。同年底,黎平县麻风防治委员会成立[2],开始全面实施收治麻风病人(1968年更名为黎平县朝阳医院)。与全国麻风村历程相似,麻风村的发展,经历了麻风病人在解放前自由组合的互助或自生自灭的萌芽时期,解放和大跃进前的初创时期;1958年至1980年代强制收容隔离的扩大时期,1976年黎平县朝阳医院人数达记录以来的顶峰时期,在册麻风病人468人[3],这一时期也是当地收容措施最严厉时期;以及1980年代以后联合化疗全面实施后的萎缩时期。此后,朝阳医院渐退出麻风防治管理角色,只收容无家可归,无人照料的老弱病残麻风病人,成为麻风病人康复疗养机构(图1、2)。从1949-2017年,一共收治了613例麻风病患者。

图1 远眺朝阳康复村

图2 朝阳康复村村民用餐
2017年麻风村有麻风治愈村民79人,男43人,女36人,年龄46~87岁,平均年龄68.9岁。侗族人口75人,其它民族4人。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残疾标准》[4]鉴定(2级以上):1、视力残疾:盲一级2人;2、言语残疾:一级1人,二级1人;3、精神残疾:二级1人;4、肢体残疾:一级4人,二级3人;以肢体残疾为主,多数为多重残疾。残疾人占总全村麻风人口的96.2%(76/79)。个人人生活费根据残疾轻重为每月423至533元。医院目前有医务人员5名,志愿者 3名,主要负责麻风防治、医疗、康复及管理工作。2017年,政府财政除工作人员工资与康复村民保障金外,另拨有6万元办公经费,同年投资108.87万元,用于改造1.542公里的通村水泥路。
2 “口碑与中医的融合”:侗族医药对麻风病的认识
麻风在侗语中称“鲵”、“剥裸”等,为歧视词语(即麻风、虫、腹中虫)。侗族认为麻风病的认识与发展,是与不道德、遗传、野蛮、传染的综合。侗族在麻风的获得与诊断上,往往也只是一些传说,就笔者访谈的数位80岁以上侗族老人口述,相似的一致,如吴某,89岁:“侗族医仙玛麻妹(女性神医,侗族崇拜的天界,与汉族的‘天刑’类似)的一天,在各寨施善,一户人家长得非常动人的‘辣乜’(未嫁的女子)在自己的厢房侧身午休,恰巧一位来自外寨四处游荡,好吃懒做的‘辣办’(男人)从其窗前经过,兽性大发,并欲翻窗对其进行侮辱,刚好被路过的玛麻妹看到,便伸手将窗户突破,‘辣乜’腹中虫即刻从破损处,飞进‘辣办’的身体内。并且向窗外山林、田野等四处飞窜,若干年后,男子出现了手脚畸形,嘴角歪斜,眉毛脱漏等症状”。也正是这样的传说原因,侗族地区对但凡出现不治之症的畸残,大都考虑这一疾病。在治疗麻风病中,侗族以扶正、却邪为主的辨病施治来治疗“麻风病”。如《侗族医药探秘》[5]《中国侗族医药》[6]所记录的“麻风病”方为:元参、漂苍术、熟地、苍耳、苡仁、茯苓、前仁、甘草、白芥子各100克,银花700克,蒲公英200克,先将熟地研烂,余药焙干研成细末,加蜂蜜调匀为丸,每次服50克,开水冲服,每日2次,连服18天为一疗程。但是从有关有记录以来,包括民间草医,麻风的治疗效果均无良好疗效。出自笔者一份20世纪60年代的文字记录:“1956年10月,黎平县卫生科聘请榕江县草医向和兴来麻风山为病人治病,当时在村患者有60余人,分住在半山腰的13个草棚内。县民政科为向医生在村内建造了两间木板房,作为住宿及制药室。病人每天服用向医生用中、草药煎制的膏丸。治一年后,未见病情有多大好转,再加上服药后,不准吃生水和少吃盐巴,故病人拒服,向和兴也于1957年3月离村。”对于疗效好坏,更多时候不会怪罪于施救者,患者及家人往往也只能是命运与安排。
3 “不道德与传染”:侗族习俗与文化中的污名
在侗族的文化中,人们对麻风的歧视与排斥,源于人们认为患麻风病的途径、方式是不道德的,表现在遗传的看法,重大事项中不得参与或限制性参与,和死后的处理方法上。
麻风在遗传上的说法,由来已久的,侗族在传统的观念中得了麻风是因为自己或祖宗行为恶劣“不洁”,这似乎同样印证了前述侗族医仙玛麻妹的故事,但患麻风也与遗传有关,他们家庭或者族人一定有麻风的“根”。主要是体现在婚姻的基础上,年轻人谈婚论嫁时,有麻风病史的家庭,绝不开亲。即便这一代人没有发现麻风病,可能隐藏于体,死亡之前没有发病。
对于女性麻风患者治疗方法,侗族遗留的传说中,最普遍的疗法应该是将自身的疾病传染给男性,侗语为“搭”(即“过”“过癩”)。即女性麻风病患者或尚处于潜伏期的时候,通过交媾传染给无辜的男人,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好色男性容易患上麻风,男多于女的原因。这一说法,给患上麻风的人扣上了个人生活作风不端正等不道德的帽子。黎平及周围地区的侗族社会里,凡五官不端,特指患有麻风病者,生前是不能够过问、参与任何有关祭“萨”(侗族女神,译为主母)和出席重大仪式与活动的,如是这样就表示对“萨”的不尊、诋毁,是会遭到“寨老”“款首”(侗族村寨自治组织领导者)严厉处理的。即便是村寨举行娶嫁殇等多不得拢,这都是神、祖先、人际等的基本关系。
麻风蛊是最盛行放蛊的一种。在侗族社会文化中,特别在一些交通闭塞村,流传盛广。从“蛊”的原意往往又有腹中“虫”的意思,而侗语又将“麻风病”称之为“鲵”(直译为“虫”),当然还指包括如肺结核、肝炎等疑难杂症,使得他们只能求助于巫术、迷信,加之晚期的恐怖外形,就直接被说成蛊,人云亦云,以至越说越感恐怖。时常,麻风病人因自身地位等级低下或排斥,往往背上“放蛊”的“替罪羊”。就笔者了解,蛊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不管认为是法术,是毒药,是疾病,对于半开化的西南少数民族而言,只是观念上的存在。巫蛊指控,其产生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基础,致使“放蛊”长期存在。
麻风患者死后,灵魂归属也是不能返回与祖先埋葬在一起的,只能变成孤魂野鬼,这主要表现在尸体处理上。侗族在麻风病人死亡后,不能按照侗族的习俗进行隆重的土葬仪式,在去世当天立即对其尸体进行火葬,地点选择在 “乱葬组”或当地人称“麻风山”的山上上进行,并沿用至今。遗体处理人员为贫困潦倒、好吃懒做人员或是自身患有麻风者来处理,“房族”(同姓氏)人员立即远离、不靠近,不参与,同时村寨中 “寨老”对周围路途进行把守,其他人员不得过往。
4 “誓不两立与野蛮”:侗族社会与家庭的排斥
对于麻风病人所有指控或迫害,或麻风病人对社会的报复。很多时候也表现在公众与麻风病患之间的冲突,偶尔出现野蛮行径,甚至誓不两立的状态。李金莲[7]《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麻风病》记述:“民国三十三年(1944)腊月的一天,保安团大队长阎文昭,率保安兵百余人,以产出鸦片烟苗为名,窜入病村,任意机枪扫射,当场打死麻风病人龙台花、吴公相二人。口江吴奶锦,因麻风病人到她家去讨饭,她不给,反而上楼去吐口水给病人,平时对麻风病人刻薄,在1949年的一天,吴奶锦同几个妇女到新寨对面便婢坡上砍柴,被十余个麻风病人围住,拉去进行强奸,并用脓血涂她身上,吴奶锦回家后,数月不敢出门,不久就病死了。这件事也激起了人们对麻风病人的仇视。1949年银朝村的保长吴昭和,为驱赶麻风病人,趁病人外出讨饭之时,再次放火烧掉麻风村的全部茅棚和财产,又使得洪州区黑洞村的麻风病人,吴香焕、吴胜焕二人被冻死于病村。”
家庭作为个体初级的关系网络,这种家庭排斥表现为对麻风病患的离弃、否认、冷淡和感情疏淡。曾在麻风病院接受隔离治疗的患者治愈回家,在家已经几年甚至几十年了,无残疾或残疾较轻,身强力壮,早年能干活,社会与家庭还需要他们。随着的年纪增大或合并其它疾病的,公众害怕麻风患者死亡,可能连累家庭或者房族,赶到麻风村,无法在家继续生活。患麻风者,即便是自己所生健康子女,一旦诊断患有麻风,很多需要将其“过继”给其他人,认其他人为父母。在笔者保存的月份麻风患者赠送子女的协约,大意为:“赠送字,我吴**送小儿女给吴**,欧**二人。长大成人,由吴**,欧**二人怎样办,一切事情,我吴**不管。赠送字,经手人,吴**。1989年正月十九日(农历),历史合同,今后双方没有返悔”《黎平县卫生志》8载:“麻风患者,X其亮。1980年2月27日,X其亮病危,房族侄X克明,在外界的舆论下,又怕死于家里无人敢来帮忙,就出钱请人抬至坡上将其烧死,时年81岁”。笔者曾经历:“2004年,黎平县DS乡DQ村,吴X,因患麻风曾在本院进行隔离治疗,痊愈后返家,在家死亡后,全村即刻跑走,远离死者周围房屋。‘房族’、‘寨老’、村两委立马报告乡、县两级政府,一小时内,全寨个人自愿集资到2万人民币的尸体处理经费,后经乡、县两级政府协调,朝阳医院带领‘麻风病人’将尸体拉回麻风村,以火葬习俗进行遗体处理。”以上例子,表面措施都是防止传染,深层次的习俗是不让死者的灵魂回来,永远不给村寨带来疾病与污染。这使得社会与家庭归属感强烈的麻风病患的个人,永远失去了人生的意义。
5 “消除与后麻风时代”:麻风村的未来
麻风作为一个古老的疾病,目前仍然缺乏有效的一级预防措施,麻风村作为历史的产物,尽管侗族习俗与文化对于现代麻风认知具有一定抵抗性,但随着麻风康复村里面康复老人的相继离逝,麻风村的历史任务终将终结。这一机构,为我国麻风的消除,做出了巨大贡献,彰显出国家对于麻风控制技术在侗族地区的成就,现代麻风科学认知,必将占据侗族文化的主流。现阶段,当地居民对麻风病人的了解、同情、关心与日俱增,麻风病人处境也渐渐得以改善,他们更加有信心战胜疾病本身,逐渐适应社会。2016年1月在东京发布的《麻风历史与人类遗产国际研讨会决议》[9]中,倡导麻风医院可作为麻风诊断、培训、康复、研究中心、麻风博物馆等,这些对于侗族地区麻风村转归等有参考意义。现今,随着科学的进步与社会发展,侗族地区麻风形势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甚至已经看不到一家完整的麻风医院(村)了,作为麻风疾病史的主要载体,单就侗族学疾病史而言,黎平朝阳医院等侗族文化色彩浓郁的麻风村继续存在或保留有着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