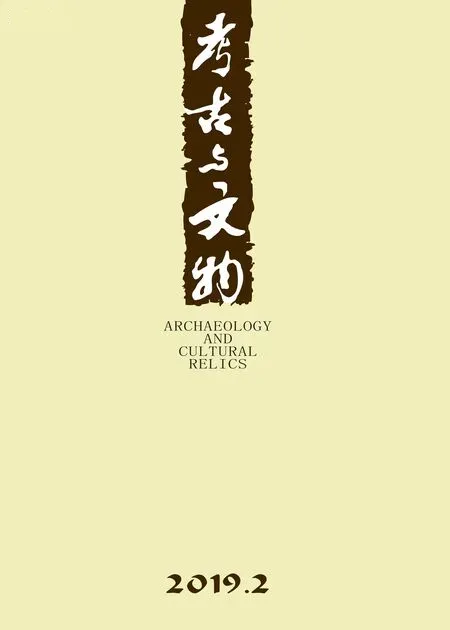大河口西周墓地M6043出土釉砂珠饰的科学分析研究
2019-05-30王颖竹陈坤龙梅建军马泓蛟李存信谢尧亭
刘 勇 王颖竹 陈坤龙 梅建军 马泓蛟李存信 朱 磊 谢尧亭
(1.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3.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 4.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 )
中国境内西周时期的墓葬常会出土一种以石英颗粒为主体、其隙间存在玻璃相的管饰和珠饰,这种制品被称为“料珠”[1]、“琉璃珠”[2]、“玻璃珠”[3]、“多晶石英珠”[4]、“费昂斯(Faience)”[5]、“石英珠”[6]、“釉砂(Faience)和玻砂(Frit)”[7]等,本文以“釉砂”一词来表示这种制品。釉砂的原料由石英砂、助熔剂、着色剂构成,加热后在石英颗粒隙间形成玻璃相,大部分石英颗粒保持晶体形态。1959年,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使用光谱分析法鉴定了河南洛阳西周墓出土的“料珠”[8],拉开了我国采用科技手段研究釉砂制品的序幕。随后针对釉砂制品的科学分析主要集中在物相结构、化学成分等方面,讨论助熔剂、着色剂和制作工艺,并涉及中西文化交流。
山西翼城县大河口墓地M6043属于西周时期墓葬[9],实验室考古发掘中在墓主颈部出土了一组项链,其由4串穿孔珠饰和管饰组成,自墓主颅骨向胸骨端沿颈骨将该组项链依次编号为A、B、C、D[10]。其中A串50、B串61、C串66、D串63枚,共240枚,其中B、C串各含管饰1枚,D串含连体珠饰1枚。珠饰颜色呈蓝色、浅绿色和白色等。分析大河口M6043出土釉砂珠饰的结构和成分特征,对研究西周时期釉砂制作技术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分析方法
样品制备:从A、B、C、D中各取3枚,共12枚相对完整的穿孔珠饰,其直径0.47~0.66、孔径 0.26~0.40、高 0.40~0.62厘米,顺序编号为SYDF001至SYDF012(图一),用无水乙醇清洗,去除表面附着物,保证测试准确度。用手术刀垂直于珠饰穿孔切取12件样品的新鲜断面,用环氧树脂包埋并打磨、抛光、喷碳。
分析仪器及工作条件:Hitachi S-3600N扫描电子显微镜;美国 EDAX公司 Genesis 2000XMS型 X射线能谱仪,工作电压 20KV,激发时间100s,采用ZAF定量方法。
二、分析结果
大河口墓地M6043出土的12件珠饰样品胎体成分显示其皆为高SiO2低熔剂特征,胎体SiO2含量在92%以上,是典型的釉砂成分特征,结合显微观察到的大量石英颗粒与其隙间玻璃相分布情况,断定这12件珠饰样品皆为釉砂制品。釉砂珠饰胎体隙间玻璃相中K2O含量有所不 同, 样 品 SYDF002、SYDF006、SYDF008、SYDF010、SYDF011这5件样品的玻璃相中K2O含量在9.9~12.8%之间,同时皆含有1.9~4.8%的Na2O;其余7件样品玻璃相中K2O含量在0.1~1.5%之间,Na2O含量低于检测下限(表一)。玻璃相中皆含有Cu,Cu作为釉砂珠饰的着色剂使釉砂呈现蓝色或浅绿色。
三、相关问题讨论
(一)成型工艺
目前研究认为我国釉砂是以石英粉末(或粘土)混合一定量的含铜物质和草木灰,一次塑形后进行烧制的,采用无范成型的方式[11]。通常认为我国釉砂是通过内芯法成型的,即在内芯材料上将调配好的原料捏塑成所需要的形状,而后入炉焙烧。芯撑材质可能为黏土[12],也可能为木棒[13]。经观察,样品SYDF003和SYDF009穿孔内壁有与穿孔方向一致的线状凸起(图二、三),应为釉砂珠饰成型时穿孔内的棒状或管状支撑物所留痕迹。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釉砂管内壁曾发现过与穿孔方向一致的凹凸相见的条纹,推测成型过程很可能是中间裹有麦秆类草本植物泥捏而成[14]。推断大河口釉砂成型使用了木质芯撑。
样品SYDF009穿孔一侧边缘圆滑,另一侧边缘半圆滑、半有毛茬,推测该样品为先烧造成连体珠,再将两枚珠饰分开(图四、五);大河口M6043出土釉砂中,有一枚由两个珠饰组成的连体珠饰,两个珠饰连接处部分连接,未连接处边缘圆滑、未见毛茬,应为烧制后原貌(图六)。形成这种连体珠饰有两种可能:第一,珠饰成型时就是两枚连接在一起,穿在木质芯撑上烧制;第二,两枚成型时是分开的,烧制时同穿在一根木质芯撑上,因距离较近烧制过程中连接在一起。就所见到的连体珠饰和样品SYDF009的半边毛茬现象可知,釉砂珠饰存在至少两个串在一起进行烧制的情况。本文分析的珠饰一般穿孔较圆而胎体多为不规则穿孔球体,样品SYDF011穿孔横截面呈圆形,但胎体横截面呈椭圆形,穿孔不在珠饰中间部位,而是偏向一侧(图七);电镜下观察显示,胎体较厚的一侧没有玻璃相富集情况,表明不是烧制过程中“流釉”造成的胎体变形,而是成型时胎体便如此。同时样品表面未发现明显凸起的范线和打磨痕迹,表明釉砂成型使用范的可能性较小,其成型工艺是在木质芯撑上直接塑形。夏鼐曾经根据古埃及釉砂提出,连珠饰可能是釉砂在芯撑上成型后,借助工具将胎体平滑的表面按压出凹凸不平的效果,从而形成连珠饰[15]。大河口墓地所出的连珠饰可能也采用了类似工艺制成。
(二)施釉工艺
M. S. Tite[16、17]将釉砂施釉工艺分为三种:直接施釉、包埋施釉和风干施釉,不同的施釉方式会导致釉砂具有不同的显微结构。直接施釉和包埋施釉制作过程类似,均是在已成型的胎体上涂覆釉料,直接施釉的釉料为浆状,而包埋施釉的釉料则为干粉。风干施釉则是混合石英和釉料,掺和少量的水或黏合剂,捏塑成型后阴干。釉层、反应层和胎体的厚度、界限形态、玻璃成分变化趋势,是判断釉砂施釉工艺的重要依据。采用直接施釉或包埋施釉方法制成的釉砂,往往具有明显的胎釉分界线;而风干施釉法制成的釉砂胎体无明显分层,存在有大量的隙间玻璃相。经分析的甘肃崇信于家湾墓地出土釉砂珠既有风干施釉,也有包埋施釉[18];经分析的山西横水倗国墓地一个釉砂样品为直接施釉[19]。釉砂的主要原料石英没有黏性,通常会在石英中添加一定量熔剂[20]或黏合剂[21]帮助胎体成型,或事先对胎体进行烧结[22]。烧结后的胎体具有较致密的外层,如果另行涂覆釉料后再加热焙烧,那么胎釉之间理应存在一条较为清晰的分界线。然而本文分析的12件釉砂均没有清晰平滑的胎釉分界线,胎体经事先烧结的可能性较小。
样品SYDF001的两个截面具有不同的胎体疏密程度:一面胎体中部孔洞较多、胎体外侧和内侧穿孔部位较为致密(图八),体现出分层现象;另一个截面胎体表面和中部致密程度相当(图九),没有明显分层现象。如果根据胎体疏密程度分层情况将釉砂施釉工艺分为直接施釉和风干施釉,则针对样品SYDF001不同面会做出直接施釉和风干施釉两种施釉工艺的判断。而实际上这是同一个釉砂珠饰,不可能同时采取不同的施釉工艺。所以胎体疏密程度不能作为釉砂施釉工艺的判定标准。
本文分析的12件釉砂珠饰胎体内部皆存在隙间玻璃相,根据珠饰表面是否存在由石英颗粒与玻璃相组成连续的釉层,将12件样品分为2组:第一组表面有釉层,包括SYDF001、003、004、005、007、009、012七个(图一〇),宏观表现为珠饰表面光滑有光泽,有不规则龟裂纹,可见明显圆形凹陷(图一一);第二组表面无釉层,包 括 SYDF002、006、008、010、011五个(图一二),宏观表现为珠饰表面粗糙无光泽(图一三)。有釉层的一组中样品SYDF012胎体结构松散、机械强度不高,无釉层的一组中样品SYDF011胎体结构紧密、机械强度较高。
电镜观察显示,经分析的12件釉砂珠饰玻璃相在胎体中的分布没有从表面到中间逐步减少的趋势,玻璃相分布较为均匀,表明作为助熔剂主要成分的K2O在胎体成型时已较均匀地分布在胎体内,由此推断大河口这12个釉砂样品使用了风干施釉工艺。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组釉砂珠饰表面玻璃相富集形成釉层,出现这种现象有两种可能:1.表层可能再次经历了施釉并再次烧制;2.烧制时温度高而导致釉砂表面玻璃相程度高而形成釉层。第二组无釉层釉砂样品中,胎体内部存在大量隙间玻璃相,表明其烧制时的温度足以使釉砂表面玻璃化形成釉层,但事实是该组釉砂表面没有釉层。所以第二种烧制温度高使釉砂表面形成釉层的假设不成立。以此推断第一组表面有釉层的釉砂应经历了风干施釉烧制成型后再次对其表面进行了直接施釉或包埋施釉程序。直接施釉具有“流釉”的特征,包埋施釉形成的釉层较为均匀[23]。本文分析的有釉层釉砂样品中,电镜观察显示釉层较为均匀,所以第一组表面有釉层的釉砂先后使用了风干施釉和包埋施釉工艺。
(三)助熔剂特征
本文分析的12件釉砂皆为钾基釉砂,根据各自玻璃相中K2O含量将其分为两组。
第一组包括SYDF002、006、008、010、011五个样品,SiO2含量在77%左右波动,K2O含量为9~13%,Na2O含量为1~5%,是典型的K2O-Na2O-SiO2釉砂。西周中期及稍晚时期,陕西宝鸡国墓地[24]、山西天马——曲村墓地[25]、山西横水倗国墓地[26]、山西羊舌晋侯墓地[27]、陕西韩城芮国墓地[28]出土的釉砂珠,K2O含量在9~15%之间,Na2O含量在1~7%之间,大河口墓地M6043的大部分钾基釉砂珠的熔剂含量与之相近。约同一时期,甘肃崇信于家湾墓地和山西天马——曲村墓地的一部分釉砂珠,熔剂中的K2O(2~5%)含量低于Na2O(7~17%),与埃及釉砂相近。埃及釉砂使用富钠草木灰、天然泡碱或混合碱做熔剂,制成的釉砂具有较高的氧化钠和氧化钾,Na2O/K2O>1[29]。通常根据Na2O/K2O的比值可初步判断釉砂珠的大致来源,Na2O/K2O>1可能说明西周时期的中国与埃及或受埃及影响的地区之间存在物质或技术往来;Na2O/K2O<1则显示出中国本土自制的特征[30]。山西大河口墓地M6043的K2O-Na2O-SiO2釉砂珠Na2O/K2O<1,显示出中国本土自制的特征。
第二组包括SYDF001、003、004、005、007、009、012七个样品,SiO2含量为82~93%,K2O含量为0.1~1.5%,Na2O含量低于检测下限。其中SYDF001、005、007、009含有CaO,含量为0.3~5.3%。该组釉砂玻璃相中K2O含量较低,未检测出Na2O,部分含有CaO,与第一组K2O-Na2O-SiO2釉砂成分及含量具有明显 区 别。SYDF001、005、007、009为K22O-CaO-SiO2釉 砂,SYDF003、004、012为 K2O-SiO2釉砂。第一组釉砂玻璃相中K2O、Na2O含量高且皆不含CaO,第二组釉砂玻璃相中K2O含量低且未检测到N2O,同时部分含有CaO,表明这两组釉砂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助溶剂。前文施釉工艺中论及,根据珠饰表面是否存在釉层,将12件样品分为了表面光滑有釉层(SYDF001、003、004、005、007、009、012七个样品)和粗糙无釉层(SYDF002、006、008、010、011五个样品)两组,结合助溶剂特征可知,光滑有釉层的一组助溶剂具有低含量K2O(0.1~1.5%)特征,粗糙无釉层的一组助溶剂具有高含量K2O(9~13%)特征。这不是一个巧合,K2O含量与釉砂表面是否有釉层具有对应关系,这是以往研究中未引起关注的一点。
(四)着色剂及其他
中国釉砂的化学成分表现出富含CuO的特征,与西方釉砂存在明显差异,显示中国自主制造的特点[31]。大河口釉砂样品玻璃相中CuO含量在2.2~12.5%之间,表现出富含CuO的特征,表明其为中国本土自制。釉砂中蓝色分布较为均匀,表明Cu分布较为均匀,同时未发现富铜颗粒,表明Cu很可能是作为助熔剂的一部分以离子形式添加到釉砂中的。
样品SYDF007和样品SYDF012胎体外侧存在粘连其他珠饰残片的现象,在烧制时与其他珠饰烧结在一起,表明釉砂珠饰制作时同时烧制若干枚(图一四)。
四、结语
经分析大河口M6043出土釉砂样品的成型工艺是在木质芯撑上直接塑形;其皆采用了风干施釉工艺,其中SYDF001、003、004、005、007、009、012七个样品在风干施釉基础上又进行了包埋施釉程序;其K2O含量高于Na2O的助溶剂特征及以Cu作为着色剂的特征显示了这些釉砂皆为中国本土自制。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发现与综合研究”(17ZDA218)的阶段性成果。陈坤龙为本文通讯作者。样品采集得到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写作过程中得到山东大学马清林教授、北京大学崔剑锋副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技优秀青年研究计划课题”(2014220)、英国学术院牛顿国际奖学金(NF160456)给予了资助。特此致谢!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四号·洛阳中州路(西工段)[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59-60.
[2]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队.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6(4).
[3]杨伯达.西周玻璃的初步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2):14-24.
[4]张福康,程朱海,张志刚.中国古琉璃的研究[J].硅酸盐学报,1983(1):67-76.
[5]安家瑶.玻璃器史话[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7-8.
[6]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J].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7]李青会,张斌,干福熹等.一批中国南方出土古玻璃的化学成分的PIXE分析结果[C]//中国南方古玻璃研究——2002年南宁中国南方古玻璃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76-84.
[8]同[1].
[9]谢尧亭,王金平,杨及耘等.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J].考古,2011(7).
[10]朱磊,刘勇,李存信等.山西翼城大河口M5010、M6043实验室考古简报[J].江汉考古,2019(2).
[11]李青会,董俊卿,干福熹.中国早期釉砂和玻璃制品的化学成分和工艺特点探讨[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4):31-41.
[12]干福熹等.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13]谷舟.中国釉砂与早期玻璃关系的探讨[D].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2015.
[14]同[3].
[15]Xia Nai. Ancient Egyptian Beads, Berlin, Heidelberg:Springer, 2014:38.
[16]Tite M S, Freestone I C, Bimson M. Egyptian Faienc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Methods of Production[J]. Archaeometry,1983(25):17-27.
[17]Tite M S, Bimson M. Faienc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Microstructures Associated with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Glazing [J]. Archaeometry, 1986(28):69-78.
[18]张治国,马清林.崇信于家湾出土西周中期费昂斯珠研究[M]//崇信于家湾周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168-179.
[19]谷舟,谢尧亭,杨益民等.显微CT在早期釉砂研究中的应用:以西周倗国出土釉砂珠为例[J].核技术,2012(4):265-269.
[20]Vandiver P. B. A review and proposal of new criteria for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of Egyptian faience// La couleur dans la peinture et l'emaillage de l'Egypte ancienne (Colinart S.Menu M., eds), Bari: Edipuglia, 121-139.
[21]董俊卿,后德俊,干福熹.中国古代釉砂的科学研究[M]//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51.
[22]秦颍,陈茜,李小莉,陈千万.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石英珠”(釉砂)的测试分析及制作工艺模拟实验分析[J].硅酸盐学报,2012(4):567-576.
[23]同[13].
[24]Yong Lei, Yin Xia. Study on Production Techniques and Provenance of Faience Beads Excavated in China [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5(53):32-42.
[25]同[24].
[26]同[19].
[27]同[24].
[28]同[24].
[29]Vandiver P B. Raw Materials and Fabrication Methods Used in The Production of Faience [M]//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Faience and Related Early Vitreous Materials. Ox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Archaeology, 2008.
[30]同[24].
[31]干福熹,胡永庆,董俊卿,等.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料珠和料管的分析[J].硅酸盐学报,2009(6):1005-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