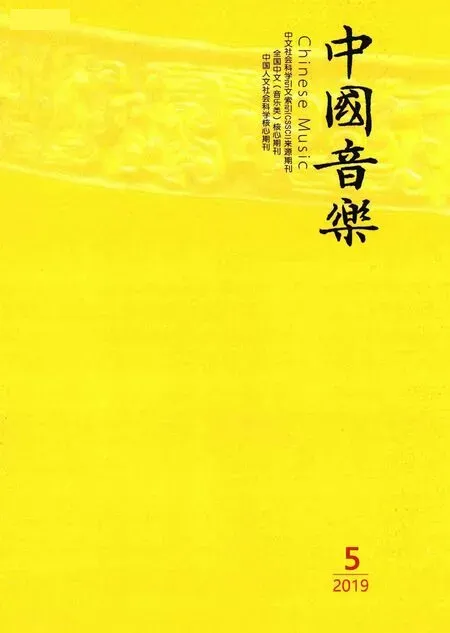一个乡村乐社的音乐民族志
——评钟思第《采风:新旧中国的民间艺人生活》
2019-05-23张黎黎
○ 张黎黎
自198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第一次去屈家营到薛艺兵写出了《屈家营音乐会的调查与研究》以来,改革开放后的冀中乐社研究在中国音乐学界逐步兴盛,至今方兴未艾,成为中外学者关注中国民间笙管乐社,尤其是北方笙管乐社的一个重要门户。20世纪80年代初冀中乐社的调查与普查活动和现如今追求民族志写作范式的田野考察研究都对这一地区民间音乐的挖掘与整理工作意义深远。前者对冀中乐社的律、调、谱、器进行了数年的搜集与整理,后者对拥有这些古老乐器和掌握这些古老乐曲的民间艺人进行了时间(历史)与空间(场域)的立体关照,为丰富北方笙管乐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英国学者钟思第(Stephen Jones)对冀中、京津地区民间乐社的调查与普查活动和对南高洛音乐会的深入研究值得关注。
钟思第于1986年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是当时为数不多研究中国民间音乐(尤其是北方农村音乐)的留学生之一。在研究南高洛音乐会的十多年时间里(1989—2003),他一直同中国学者薛艺兵和张振涛一起前往田野进行考察,此外,还有乔建中、萧梅等音乐学家也曾同他去过南高洛。《采风:新旧中国的民间艺人生活》(以下简称《采风》)是其在冀中、京津地区研究中国民间音乐所出版的第二部作品,是其专项研究中国民间乐社的第一部作品。
一、写作背景和内容结构
1989年,英国学者钟思第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学者薛艺兵第一次来到河北省涞水县南高洛村,参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河北地区民间音乐的考察活动(1989—1992)①1989年2月,钟思第(Stephen Jones)获得了一笔来自英国学术委员会的考察津贴,开启了为期一年与薛艺兵一同考察冀中、天津一带笙管乐的经历。之后的几年时间里,直到1992年,他们又通过其他经费,去了北京周边及其他省份做了民间器乐和仪式音乐的普查工作。具体的地区有:1989年新年期间在冀中地区;1990年和薛在闽南及广东东部;1991年和薛在廊坊(军芦村,周各庄),后来和陈克秀第一次去了山西阳高;1992年夏天和薛艺兵及景蔚岗去了山西多地,同年和薛艺兵去了辽宁。,随后出版了其第一本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专著《中国民间乐社》②Stephen Jones.Folk Music of China: living instrumental traditions.Oxford: Clarendon Press (paperback edition with CD), 1995.。1993年,在钟思第及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英中友好协会资助一笔费用,使他们得以在冀中、京津地区开展民间乐社的普查活动(1993—1995)。普查中,在中国学者的建议下,钟思第萌生了专项研究南高洛的想法,在进行了十多年的田野考察后,于2004年出版了《采风:新旧中国的民间艺人生活》③Stephen Jones.Plucking the Winds: 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Leiden: CHIME Foundation (with CD), 2004.。
《采风》一书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重构南高洛的历史;第二部分是作者“自己”置身事内的考察,主要针对的是涞水县义安镇的南高洛村。作者旨在通过重构南高洛的历史和现代生活来理解农村的现代性。他将具体的民间艺人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起点和终点,显示出不同于中国学者在对待民间音乐研究时执着于文本分析的态度,在他看来,音乐只是仪式整体的一部分。在书中,他把南高洛音乐会放在历史语境和社会政治语境中加以叙述,通过其著作可以看出,作者时而站在边缘的立场梳理南高洛的历史,时而身处其中,力争成为局内人的一份子,感受当地的文化氛围。
这本书的名称从英文直译过来是《采风—新旧中国的民间艺人生活》,顾名思义讲述的主要是一群生活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努力维持民间乐社的农村艺人。事实上,不能称他们为艺人,原因是他们不以演奏音乐为生,这与民间以“红白喜事”为主的吹打班在职能上有着本质区别。具体来说,这本书围绕着不同时代下,与南高洛音乐会有关的一个个具体的“人”来进行层层描述,很像一幅微缩的近现代中国乡村史,或者是一部与南高洛音乐会有关的民间艺人的民族志。文内没有艰深晦涩的理论束缚,没有一以贯之的对音乐文本的曲式分析,行文朴素。笔者不敢妄自界定这是一部人类学的著作,但是可以断言这不是经验想象中的民族音乐学著作,或者说不是国人概念中音乐学传统范式上的写作模式。正如书中开篇写到的:“这本书描述了一群生活在中国北京南部村庄的音乐家们,记录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在20世纪中动荡的生活经历……对这本书的阅读主要是以人们的生活为主要内容。”④Stephen Jones.Plucking the Winds: 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Leiden: CHIME Foundation (with CD), 2004, p.1.该书的序言部分在对全书做了一个简单介绍后,便从村里葬礼活动的场景设置开始娓娓道来。
因此,《采风》主要讲述的是河北省涞水县南高洛音乐会中一群农民的故事,确切地说是一群以务农为主,在特定时间扮演民间音乐家身份的,并且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数代民间艺人的故事。全书共分为十二章,从目录上看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致谢;文中术语;序;年表;地图。第二部分正文:缔造历史,共有七章,时间跨度是1400年到1980年代。第三部分正文:鲜活的音乐,共有五章,时间跨度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第四个部分:结尾;家谱;附录;谱例;注释;参考书目;术语索引;CD的注释;CD的目录。
可以看出该书的主旨与出发点是藉由南高洛民间仪式音乐的活动来一窥这一地区的社会演变,从而勾勒出新旧中国交替时民间艺人的整体社会生活和整个中国社会生活的农村缩影。可以说对南高洛音乐会的考察、学习是这一整体研究的一个引子,它的作用是通过这一个引子来引出新旧中国民间社会生活的演化进程,从血缘关系、人口迁徙到村庄历史、村民互动来描摹出一个中国村庄社会的历史与秩序。
这本书的时间跨越从1400年到1990年代,“本书第一部分的叙述从15世纪村庄的建立开始到1989年,主要集中在1949年解放之前和1966年之后。第二部分的故事从1989年以来开始更像是作者与村民的互动和讨论;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概述了他们的音乐和宗教仪式,第十二章回归到描述新近的戏剧性发展”⑤Stephen Jones.Plucking the Winds: 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Leiden: CHIME Foundation (with CD), 2004, p.1.。序言的结尾部分作者指出接下来的写作任务是:追溯村庄的历史和历史里的音乐家,通过典型历史事件来概括中国近现代史。本书大致时间脉络为:15世纪初村庄成立→18世纪仪式音乐产生→1900年义和团大屠杀→1911年清王朝统治的终结→1930—1931年的一系列仪式→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内战→1949年解放→解放初的相关社会背景→1980年废除公社制度到自由化→“我”对村庄文化的侵入。书中各个章节基本上是按照上述顺序开始写起,但时间上有重合的部分,并不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发展,而是跳跃进行,也就是说本书整体上还是在现代的时间语境里回溯之前发生的历史事件。
二、写作特点与脉络解析
《采风》将国家的大历史与传统和南高洛本地的历史与传统并置起来关照新旧中国农村音乐家的生活。就结构而言,本书有两条主线贯穿前后,一是国家的大历史和南高洛地区的小历史;二是音乐会会员的生命轨迹。故事的主要开端要越过序言从第一章开始。第一章,作者“通过零星但重要的日期来了解村庄及其仪式的早期历史及20世纪初期的历史”⑥Stephen Jones.Plucking the Winds: 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Leiden: CHIME Foundation (with CD), 2004, p.29.,这部分历史信息主要是通过一个叫单福义的老人提供。单福义是村里有名的文人,至今健在,解放前上过私塾,舞文弄墨,画画写字,样样在行,写过《村名探源》《南高洛纪事》⑦《村名探源》是南高洛的村史,目前南高洛没有完整版本,只有前半部分。,还写过一部描写拒马河畔农村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春归梦》。书中有关高洛地区早期的历史、个人史或趣事基本上来自《村名探源》《南高洛纪事》,或是单福义老人的口述。
书中行文的关键在于透过封建帝国和新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解放后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解读这些事件对农村会社中音乐家生活的影响。本书从1403年村庄的诞生说起,到文末的最终时间2001年,中间经历的典型历史时期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在这里面与会社相关的各种人物的各种活动,瓦解着又重构着地方文化的传统。两条主线(历史与个人)一直紧密的平行发展。需要再次说明的是,作者的写作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一一地呈现事件,而是会时不时地跳跃到当前的时间里再折回到历史现场进行描述。这是其写作上的一大特点。
全书正文的两大部分正如上文所说历史事件中的人物与社会生活中的人物共同发展,立体地呈现出时间与空间的叙述模式,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桩桩普通的琐事,共同再造高洛地区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习俗。
该书第二部分“鲜活的音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写起,正如作者所说,“这部分是我1989年在高洛观察的大量一手资料的描述以及我与音乐家的关系”。⑧Stephen Jones.Plucking the Winds: 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Leiden: CHIME Foundation (with CD), 2004, p.189.这部分内容是作者在现实中大量参与观察和置身事内体验的结果,里面经常提及的音乐家有何清、蔡安、单玉田、单福义、蔡然、蔡玉润、单伶等,提到这些人物时作者会在人名前加上自己对他们的理解,如令人敬畏的何清(Formidable He Qing),有个性的蔡然(Eccentric Cai Ran),村历史专家单福义(Village historian Shan Fuyi),聪明的音乐家蔡玉润(Talented musician Cai Yurun)等,这种评价不仅仅是人名前加上一个形容词,而是显示了作者长久以来与他们相处所产生的了解。
书中提供的信息量很大,作者通过不同人物的社会行为观察到文化变迁的偶然性,认为“有些人可能会发现‘重新的发明’都在这, 但它是一个有机的改造细节,而不是一个转型的内容”⑨Stephen Jones.Plucking the Winds: 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Leiden: CHIME Foundation (with CD), 2004, p.318.等,类似有价值的观点在文中还有很多。对于作者而言,他认为“我的大多数同学对解放初期的中国文化更感兴趣,而我固执地坚持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抗拒学习现代语言,我大约成了和高洛村民一样的抵抗者。遗憾的是那时我仍然不知道中国民间音乐的存在,对何清的尝试和其他高洛的音乐家在整个历史时期保持他们的传统还没有注意到”⑩Stephen Jones.Plucking the Winds: 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Leiden: CHIME Foundation (with CD), 2004, p.169.。当意识到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农村就会有数以千计的民间乐社之后,他便开启了中国民间音乐的研究之旅,他认为“这次(1989)的访问是我自己生命的里程碑”⑪Stephen Jones.Plucking the Winds: 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Leiden: CHIME Foundation (with CD), 2004, p.189.,也是“协会生命中的另一个里程碑”⑫Stephen Jones.Plucking the Winds: 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Leiden: CHIME Foundation (with CD), 2004, p.229.。而南高洛也成了他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重要节点,作者更是坦言“我把自己长征的第一步(更像是悠闲的散步)给了中国音乐和高洛”⑬Stephen Jones.Plucking the Winds: 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Leiden: CHIME Foundation (with CD), 2004, p.168.。
三、该书的贡献和意义
钟思第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其重点不在“音乐”,而在“民间”,在于民间叙事;而音乐,只是一个窗口。同其他有关民间仪式音乐和乐社的研究相比,他的贡献和特点在于:
第一,在有限的篇幅内将研究对象—农村乐人的生存背景上溯到村庄的起源处,简要讲述了早期外来的移民故事和仪式文化,交代清楚了这一地区的血缘关系与宗族组织。越过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较少部分书写,书中接着出现的典型历史节点都是我们熟悉和亲历的当代生活。在这一系列的历史环境里作者通过高洛地区音乐会中个别人物的命运、家族遭遇、当局态度以及音乐会或其他民间社团经历的沉寂、复兴、竞争等事件,反映了国家政治制度笼罩下,小地方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作者将建国前后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浓缩在了南高洛,使得生活在其中的农村艺人只有招架的精力,没有思考的余地和能力。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钟思第笔下的南高洛音乐会从还没有确凿证据的15世纪开始一直延存到今日,背负它的就是作者所说的这些乐社的一代代音乐家们,书中人的主体作用被毫无疑问地彰显。在钟思第眼里,田野并不仅仅是呈现与搜集资料的去处,而是将历史、人物、材料合而为一进行研究的地方与空间,换句话说,他的田野不仅仅是考察眼前的场景,而是研究贯穿场景的历史和人物(特指20世纪80年代)。
作者认为,老人的去世对乐社的打击是致命的。张振涛曾说,我们在田野考察中,倾向于发现年代久远的宝卷、乐器,而钟思第关注的则是村子里坐在大树底下翻阅宝卷的人。“然而喜欢古代文献的固化模式,让我看不到当下,没有把目光落在大树下的那位农民身上,而是落在了那本流传了千年的乐谱上面。”⑭张振涛:《咬定管子不放松:钟思第与冀中乡村考察》,《音乐研究》,2015年,第12期,第15页。在南高洛,最让钟思第感到惋惜的是老会头何清的去世,他认为何清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何清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是一位保守型的人物,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音乐会的关键人物,也是音乐会说一不二的领导者。可见,年代久远的谱本、宝卷、乐器固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但是没有实践这些的民间艺人,那么一切则缺乏实际意义。就像林中树之于屈家营音乐会,虽则他不是乐手,但他却是推动屈家营前行的重要力量,代表了屈家营的一个时代。他的离世,也正如钟思第所说,意味着屈家营一个时代的结束。因此,“改变,是由个人引起”⑮Stephen Jones.Plucking the Winds: 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Leiden: CHIME Foundation (with CD), 2004, p.227.。
第二,作者打破身份边界,国籍界限,说汉语,与南高洛村民穿相似的服装,同吃同住,一起开坛、坐坛、收坛。在决定专项研究这里的历史风俗之后,长时间往返于南高洛和他处,试图重建新旧中国交替下的民间艺人生活。他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视界,一种在国家秩序、社会规范的更迭视域中,全新看待中国民间乐社的生存历史、演化过程和现实处境的新视角,并且将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倒灌在乡村中,映照在乐社里不同年代音乐家们的人生史中。从音乐家们的人生史中,我们又看到了国家层面历史的种种态势与跌宕起伏。二者互为倒影,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乡土中国已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历史与文明。
第三,更进一步说,作者将国家历史的宏观叙事与地方进程的微观讲述并行地放在了一起。国家层面通过典型的历史事件呈现,地方层面通过具体的个人经历呈现,这接近典型的人类学对宗族、礼仪与神明的研究方法。⑯〔美〕萧凤霞,包弼德等:《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文史》,2007年,第5期。这已经不只是典型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式,已然是对音乐家个体的民族志书写。书中对音乐会中的音乐家、仪式和神均有一个整体关照,让时间与空间并存,立体地与音乐会中的人与物一起前行,看似简单的铺叙,实则是在高超的写作手法下隐藏了对研究对象的深深关怀与爱护。
第四,文章第二部分的时间是作者介入的时间段,这一部分作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夹叙夹议,通过他的视角,我们看到了1989年到2002年南高洛音乐会一波三折的经历,以及在这个跌宕背景下音乐家们的所作所为。通过他的描述我们能够看到音乐家们努力地将这些零碎的传统困难地拼接起来,以继续生活在自己编制的文化之网中,让自己成为传统的接续者、仪式的承载者和音乐的继承者,让村民们得以继续沐浴在想象中的“神”的庇佑下以安心度日,因为“以前老一辈人就是这样的”。这是他通过自己的体验让我们认识到的民间乐社的功能与意义。
四、他者眼中的他者观
由于《采风》的中文版还没有面世,因此有关《采风》的中文评价并不多,在一两篇对比式书评中,明显可以看出,其评价的内容稍显简单。在国内为数不多的相关评述中,张振涛以及晋克俭的两篇论文都有专门开辟小节评述《采风》这本书。由于写作重点不同,二人对这本书在文中的描述角度也略有不同,前者较为宏观,后者较为具体。
张文在“中国学者眼中的外国学者”一节中,对《采风》进行了高度概括。其中,第一部分通过对钟思第在意大利教会找到的南高洛20世纪初的教堂照片,窥视出南高洛音乐会与外来文化融合的期限能够推至20世纪初,而“照片则让人对乡村的‘西方化’进程和区域宗教环境有了真切了解”⑰张振涛:《咬定管子不放松:钟思第与冀中乡村考察》,《音乐研究》,2015年,第21期,第11页。。对书中连接各个时代民间艺人生活的音乐会社,作者从书中观察到这种“音乐艺术”组织是“以‘音乐’为名誉实际上起着沟通整个村落参与社区事物的多元功能的乐社”⑱张振涛:《咬定管子不放松:钟思第与冀中乡村考察》,《音乐研究》,2015年,第21期,第11页。,并且这个乐社在区域群体的生活环境中起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事实上,这也是作者自己对冀中地区民间乐社的价值观念与角色定位,尤其是像音乐会这种“善会”。第二部分通过几个关键词和特殊历史时期,以点带面素描文本,指出钟思第能够跳出“生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观察局限,能够产生另一种看待中国音乐的视角。相对于其他对中国实际音乐生活没有认识的外国音乐学家而言,钟思第的这部著作也打破了他们对中国乡村音乐已经没有历史深度的偏见,而这种偏见会因为像钟思第这种学者的努力而化解。⑲张振涛:《咬定管子不放松:钟思第与冀中乡村考察》,《音乐研究》,2015年,第21期,第11页。
晋克俭一文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整体介绍了河北地区音乐会的职能、价值、活动及现有的主要研究成果(仅限于薛艺兵、张振涛和钟思第三人)。文章的最后一段作者回到对《采风》的评价中,总结性地评估了这本书的价值和贡献,认为钟思第的写作特点与中国传统志书的写作手法、与熟读典坟的中国文人不同。钟思第的研究结合了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的优长,这种研究视野能够补足正史和其他官方文献的局限,因为“正史不可能提供民间社会组织的传承和沿革历史,更不可能提供村落历史编年、乐师的人生细节”⑳晋克俭:《民间音乐会田野研究的一个范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64-65页、第65页。,并指出“他的工作也为中国学者现阶段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一个范例”㉑晋克俭:《民间音乐会田野研究的一个范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64-65页、第65页。,同时,也是民间音乐会田野研究中的一个典型范例。
五、结 语
钟思第写这本书断断续续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这使得他有机会长时间观察社会变化带给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这种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会社生存状态,也改变了周围的一切关系。作者一直认为无论是对道教仪式还是对民间音乐的研究都要在背景—场景中考察研究对象的生活及相关活动,而不能仅仅通过文本或其他历史材料来重建研究对象的结构。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它构成了事物瞬息万变的场景之一,人们经历过的年代,能够回忆起的往事,构成了研究对象目前生存状态的背景和条件。因此,将研究对象搁置在人们都了解的社会背景中进行描述,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作者认为信仰的意义在于村民通过向神请愿来解决自己的现世困难:“今天村民们最重要的神灵崇拜是后土的送子观音和财神爷,以及地藏菩萨和地狱的十王,简单地说村民们的普遍担忧需要去通过向神来寻求帮助。”㉒Stephen Jones.Plucking the Winds: 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Leiden: CHIME Foundation (with CD), 2004, p.278.对于信仰的流变与淡化,作者认为信仰在之前一代的仪式专家㉓指的是何清等老一辈的仪式专家。那里已经有所改变,并且在今天继续变化。同时作者也观察到村民对待神的态度虽然不如以前投入,但是虔诚的观念依然存在。
洋洋洒洒三十几万字的著作中,有意义的论点还有很多,在这里不一一例举。钟思第的这些观察与思考,给我们回过头来研究南高洛音乐会,带来了很多灵感与启发。这部著作出版已有十多年,现在看来,里面的诸多问题意识与考察资料仍然与目前民间乐社的现实处境相契合,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从中能体会到作者对乡村文化变迁的敏锐性把握,而这种乡土社会的研究风格,在实地考察与个人口述中构建出的历史进程,对我们通过音乐会和音乐家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互助与关系提供了一个别样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