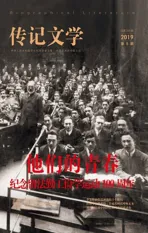巴黎城的中国农民
——王守义的故事
2019-05-17一格
一 格
河北省高阳县文化馆
传奇人生拉开序幕
1920年11月,波涛汹涌的印度洋上,一艘法国邮船“博尔多斯”号正在波峰浪谷中穿行。有名的“华工之乡”高阳县有数位青年乘船赴法,开始他们的“淘金梦”。西田果庄村一个小业主的儿子王守义也在其中。王守义家道小康,几十亩薄田、几张织布机维持着一家大小的生活。王守义是个聪明的农家青年,很早就学会了耕耩锄耪,犁杖杆子耙都能侍弄得服服贴贴。一心想早抱孙子的父亲早早地为王守义娶了一门亲,隔年就有了儿子王欣蒲。要不是那年洋纱大量在家乡倾销,王守义家的织布机再也织不出养活全家的活命钱;要不是家乡高阳出了个名人李石曾大力号召赴法勤工俭学,提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王守义就会和村里的许多年轻人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终老家乡了。读过高小的王守义粗通文墨,萌生了去法国闯荡世界、挣钱养家、投身实业、大干一场的想法,他瞒着家里人偷偷地在布里留法工艺学校报了名,学法语、学技术,一年之后,准备赴法。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王守义在妻子的帮助下,趁天黑偷偷打开窗户,跑了出来,一口气跑到洛阳,找到在洛阳开布线庄的舅父,借了盘缠,又赶到上海,终于登上了这艘七千吨级的法国邮轮“博尔多斯”号。
在轮船上,大多数勤工俭学生因为剧烈晕船,不能随意走动。但对于布里留法工艺学校的毕业生王守义来说,晕船却不是问题。王守义家里开着织布厂,从小就经常和父亲一起坐着船从家乡的潴龙河北上白洋淀卖布,他还跟着父亲乘船到过保定府,下过天津卫。所以,王守义每天都按时走到位于三等舱的餐厅用餐。他发现三等舱的乘客中有两位漂亮的女乘客,也经常在一个浓眉大眼、面目英俊的男青年的陪伴下来餐厅吃饭。这两人一看就是新潮的女学生:都剪着短发,过越南和新加坡时还穿上了白衣青裙。更令王守义吃惊的是,其中一位女生还操着和自己同样的保定口音。
一番交谈后得知这位漂亮的女学生就是从直隶女子师范赴法的勤工俭学生张若名,她的女伴就是她的同学、直隶大名府的郭隆真。而陪伴在她们两人身边的男子就是日后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
张若名的老家清苑县温仁村离王守义的老家不过几十里地,王守义经常跟他的父亲、兄弟去赶温仁大集卖他们家织的土布。这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大洋邂逅,令三个直隶人和久居天津的周恩来顿感亲切。
在随后的日子里,三个直隶同乡和周恩来饭后的小谈,为他们的旅途消除了太多的烦闷和疲劳。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了法兰西,保持到了里昂的协和饭店。正是由于王守义的介绍,高阳老乡段秉鲁和段秉午把自己长期经营的饭店二楼让给张若名和郭隆真居住,也使协和饭店成为了在法华人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有一天,张若名说:“王大哥,这船上顿顿米饭海带汤,有什么办法能找点面食解解馋呀?”
王守义神秘地从兜里掏出一把豆饼说:“来,先给二位贤妹解解馋吧!”
张若名惊讶地问:“哪来的豆饼?”
王守义说:“我们住的统舱里,隔壁就是活牛和活猪,喂牲口的饲料山堆大垛的。那天,我找到了一口袋豆饼,这不是天赐美食吗?听一个同学说,过几天还要喂它们黑豆。我一定给三位留点黑豆,咱们也在船上过过年。”
不几天,王守义真的从喂牛的饲料里弄到了许多黑豆,他们用几个苹果贿赂了厨师,为他们炒熟。这种在保定、高阳一带非常流行的小吃伴随了他们剩下的海上行程。
一天,王守义吃多了黑豆闹肚子,一路小跑着去厕所。巧的是,有一个法国水兵蹲在那里不出来,害得王守义用力拍打着厕所的门板,用蹩脚的法语嚷着叫着。法国水兵好半天才缓缓地走出来,对着王守义喊道:“Cochon,Chinois(中国猪)!”并重重地给了矮小的王守义一个直拳。王守义被打得眼冒金星,也顾不得与他理论,先进厕所解决问题去了。
回到统舱,王守义找到周恩来,抚摸着受伤的下巴诉说刚才的遭遇。周恩来拉上他就要去找船长。王守义叹了一口气说:“算了吧,‘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就叫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你还记得咱们过越南的时候,西贡的华人纳税要比当地人多一倍,这真是个叫人没法活下去的世界呀!”
王守义说:“要不是洋纱在我们老家倾销,我家的织布厂开不下去了,我是死也不会离开结发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上法国受这个洋罪的呀!”
周恩来说:“总有一天,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和这些欺负人的阶级斗上一斗,灭掉他们的威风!”
王守义问:“看你每天都在甲板上看书、写字,没有空闲的时候。李福景学采矿,若名学文学,孙树增学机械,你到法国去学什么呀?”
周恩来回答说:“学革命,为天下人谋永福。”

沙洛瓦劳动大学图书室,右二为聂荣臻
无论在远赴法国的轮船上,还是目的地法兰西,王守义无意之中和一批日后影响中国当代史的巨人成为了朋友。除了周恩来,还有邓小平、聂荣臻、李立三、赵世炎等。
在巴黎中国豆腐公司,王守义曾和邓小平一起磨过豆腐,和聂荣臻住过一间工房。他下过煤窑,拾过洋人的面包渣,为法国妇女当过洗衣工。而这几样工作,同样也是初到法国的邓小平、赵世炎、李立三们常打的工种。
1975年,邓小平访问法国,在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他暂时离开陪同的法国政府总理雅克·希拉克,与一位前来接机的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热烈地相拥在一起,嘴里脱口说出一句令人不解的话:高阳的“马老五”哇。
这位老人就是王守义,“马老五”即法文临时工“马勒儿伍”的汉化发音。这张照片后来被王守义悬挂在巴黎华侨俱乐部的大厅里。
邓颖超访法期间,四次约见王守义,了解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时的生活和经历。1978年,王守义回国参加国庆观礼,老同学聂荣臻在中南海设宴款待。曾经受王守义资助的留法学生钱三强、程茂兰等科学家出席作陪。席间,谈到青年时期在法国的难忘岁月,几位老人都动了情。王守义,这个当年巴黎弗朗哥地区东方饭店的小老板,几度哽咽失声。
当年在法国,周恩来曾派他的得力助手、高阳老乡马志远、周世昌问过王守义,参加不参加共产党。王守义认真地说:“我文化低,多做工挣钱,资助你们救国吧。”
王守义,这个当年为周恩来理过发,经常请聂荣臻、邓小平吃饭,和他们掰腕子的高阳农民,成为了一段重要革命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王守义晚年与邓颖超合影
“活关公”与“女梵高”
中国农民的儿子王守义在法国,几乎做遍了所有的工种,他甚至学会了汽车修理、飞机驾驶,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法国通”。
王守义急公好义,他用自己的劳动所得资助了程茂兰、张德禄、王毓糊、王书堂等一大批中国勤工俭学生,使他们学有所成,博士、硕士、工程师的名头得了一大堆,而他本人却没能进入高等学府进修,只是心平气和地在法国经营他的天地,拓展着华人社会的生存空间。说不清有多少在法华人的后事是王守义帮助办理的,说不清王守义为多少穷困潦倒的穷乡亲争回了属于自己的遗产,王守义在法国巴黎的华人世界里,得了一个“活关公”的称号。
最后,王守义荣任“巴黎旅法华人俱乐部”副主席,可谓实至名归。
王守义的传奇故事上演了一生,他的命运被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光环照耀,他是真正的燕赵慷慨悲歌之士。他的爱情故事,发生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高潮后很长一段时间,那是勤工俭学运动的余波荡漾,是中国青年在法国浪漫爱情生活的最后绝响。
仿佛是命中注定,“活关公”必然要与“女梵高”相遇、相识、相知。
那是一次在法华人难忘的午餐会,王守义在饭店里邂逅了穷困潦倒的中国女画家潘玉良。她正在大杯大杯地喝酒,有些沙哑的类似男人的发音颇为另类。酒过三巡之后,潘玉良为大家表演节目,这个女子居然唱起了京剧中的黑头:“将酒宴摆置在分金堂上……”王守义问一个同乡那是谁,同乡回答他:“一个画画的女疯子,穷到了家,却不肯卖画换饭吃。”接下来同乡又神秘地说:“她的画可是值钱,法国政府都不准她的画作出国呢。”
王守义盯着潘玉良的面孔,一个神秘的爱的音符在王守义的心中轰然奏响:这个女子不寻常!
王守义紧接着潘玉良的尾音站了起来,说:“我是河北高阳人,我给大家唱一段高阳昆曲《关大王单刀会》吧。”接着,王守义走到潘玉良身边,唱起了:“趁西风驾着那小舟一叶,早离了九重龙观阙,来探他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
接下来的故事尽人皆知,一部黄蜀芹导演、巩俐主演的传奇电影《画魂》,不仅让潘玉良名声大噪,也让王守义这个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小人物”在历史的长焦镜头里曝了光。
很快,潘玉良就被王守义接到了专门为她租住的高级公寓里,开始了她作为一个“专业画家”的优裕生活。一幅幅在法国画坛的惊世之作新鲜出炉,法国政府、美术家协会的各种奖章和巨大荣誉也如期而至,高贵的法国艺术殿堂对潘玉良打开了它神圣的大门。
这个在世界画坛上有“女梵高”之称的现代艺术大师在王守义的全力扶持、倾囊相助下,像一株迟开的桂花在艺术之都、时尚之都巴黎大放异彩。而对王守义和潘玉良这对饱经沧桑的华夏儿女来说,收获了一份相濡以沫的爱情,一份厮守终生的承诺,才是真正沉甸甸的果实。潘玉良形貌平庸,衣装简朴,王守义绝不是拜倒在石榴裙下的轻狂之徒。此后,王守义和潘玉良成为了没有名分的夫妻,更是心心相印的朋友,他们相扶相携,直到生命的终点。
20世纪70年代,一代才女潘玉良在法国病逝。作为潘玉良监护人的王守义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生前寂寞、一生苦难屈辱的潘玉良晚年相逢王守义,是这个多灾多难、才华盖世的中国女性生命中不多的亮色,弥足珍贵。临终时,潘玉良把她和大量画作托付给王守义,还托他把潘赞化赠予自己的一块怀表转交给潘氏后人。后来王守义一一实现了潘玉良的遗愿:画作回归祖国,怀表转交潘氏后人——那是潘玉良心灵上的认祖归宗吧。

潘玉良为王守义做雕塑
一尊潘玉良手塑的王守义塑像,若没有心灵的相知、生命的托付,绝对不会那么栩栩如生。
王守义拍摄的用来反映潘玉良创作和生活的纪录片被他保存得完好无损,多年之后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创作会议上放映并引起轩然大波,比起当年刘海粟聘请潘玉良当教授引起的反响毫不逊色。珍珠究竟是珍珠,潘玉良画作的艺术价值是由时间、历史和美共同缔造的。无疑,王守义,这个潘玉良身后的普通的勤工俭学生,一个中国农民,也是这个艺术殿堂的奠基者之一。
潘玉良的葬礼在一场连绵不断的春雨中举行。王守义,早已不是那个俊逸潇洒的留学生,而成为了一个皓首皱脸、佝偻瘦小的老者。他站在雨中,目送和他同样受尽人间冷暖的潘玉良回归泥土。那是他亲自选定的墓穴——双人墓穴,一旁的空位是留给自己的。
王守义晚年回国探亲,特地请家乡最为有名的书法家赵锡庄先生,为潘玉良书写了墓志铭。那是一幅遒劲的隶书,就像他早年在布里留法工艺学校读书时,学校门楣上那美观的校名一样。在潘玉良长眠的法国公墓中,一块精致的墓碑格外惹人瞩目:艺术家潘玉良之墓。这几个字要比一旁后加上去的“王守义之墓”几个字大一号,它似乎做出这样一个暗示:王守义甘心情愿地躲在潘玉良身后,为这个旷世奇才作伴。就像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换持中国护照;就像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亲驾飞机送近百名科学家回归祖国,始终是一个躲在幕后的“配角”。
王守义颁给潘玉良的奖章:金皇后
潘玉良的画出了名,王守义先后投资为她在法国、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西方主流国家举办了别开生面的画展,花去了王守义几十年辛勤经营挣得的真金白银,他的心血和金钱换来了潘玉良充满生命力度和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画作风靡欧洲。法国国家美术馆美术沙龙大奖、法国国家艺术奖、比利时皇家艺术金奖,一顶顶桂冠戴在了这个曾被一些画界精英判处“死刑”的另类画家的头上。潘玉良去世后,她的《自画像》卖到了1021万港币,她的《非洲裸妇》拍出了900多万的天价,她的数以千计的画作、雕塑被收藏界人士疯狂追捧。然而这些,曾经穷困潦倒的潘玉良永远不知道了,为了保存这些艺术珍品九死一生千金散尽的王守义也永远不知道了。这样的经历和荷兰画家梵高何其相似。“女梵高”的称号,潘玉良实至名归。当年,梵高的身边有一个真正的知己,他亲爱的兄弟温森特·提奥;而潘玉良的身边也有一个白发知己,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民——王守义。
1972年,王守义曾短暂地告别巴黎,告别潘玉良,回到中国,回到故乡高阳。那一年距离他离开家乡赴法勤工俭学整整过去了52年。这一次回乡,他恰好也在家乡待了52天,历史就是这样的巧合和相似。
在家乡高阳,他选了几样无法替代的纪念品带回法国,一样是家乡出产的家纺丝织品,一样是用袋子装了满满一袋家乡的黄土。最奇特的是,他选了几穗家乡刚刚收获的玉米,全须全尾地带回了法国。回到巴黎他们租住的市政府公寓,王守义激动地大喊:“玉良,这是我颁给你的金奖。比利时政府不是奖给你一个皇家艺术大奖吗?我带回的这几穗玉米,是我们老家的土特产,品种叫‘金皇后’,我颁给你中国家乡的‘金皇后’奖!你是我心里永远的金皇后!”
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的一代画魂潘玉良热泪盈眶,喃喃地说:“这个金皇后奖,比你当年给我的红玫瑰还要珍贵。”
那几穗被称为“金皇后”的玉米,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几年,就悬挂在他们的房间里,而后连同那袋家乡的黄土,也按照遗嘱都撒在了他们的坟墓里。
潘玉良当然是浪漫的天才,是艺术之神缪斯钟爱的天使,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和法兰西浪漫的土地上书写着绚烂的艺术传奇;而王守义也是天才,他是生活的天才,他的所作所为,是生命之舟在时间的河流上荡漾开去的美丽涟漪。王守义的一生,也许就是一个行为艺术家浪漫一生的真实写照,那是一种真正的浪漫,以生命为舞台的大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