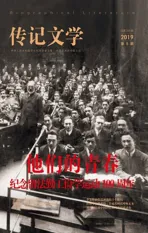蔡和森: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急先锋
2019-05-17史克己
史克己
河北省高阳县文化馆
蔡和森(1895—1931),复姓蔡林,名和仙,字润寰,号泽膺,学名彬,别名和森,湖南双峰人。1918年与毛泽东等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随即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担任著名的《向导》周报主编。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是中共中央早期领导人的核心人物之一。1925年,参与组织领导五卅运动。同年10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届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后当选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7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代理秘书长。1931年因叛徒出卖被捕,8月在广州牺牲。
朗吟飞过洞庭湖
1918年6月,一艘客船从湖南长沙扬帆启航,穿过洞庭湖,直趋武昌。在船过洞庭湖的时候,一个长发凌乱、目光犀利的青年站在船帆下吟哦:
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
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
世乱吾自治,为学志转坚。
从师万里外,访友人文渊。
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
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
虽无鲁阳戈,庶几挽狂澜。
凭舟衡国变,意志鼓黎元。
潭州蔚人望,洞庭证源泉。
这个心事重重的青年就是来自湖南长沙的师范毕业生蔡林彬。后来,蔡林彬以“和森”之名著称,他的原名倒不常被人提起了。
蔡和森这次远赴北京可谓重任在肩。
一个多月前,蔡和森和毛泽东、萧子升、张昆弟、罗学瓒、陈绍休、欧阳泽、邹鼎承、周世钊等热血青年成立了一个秘密青年团体:新民学会。此次,他就是奉全体会员的委托,“专司其事”,远赴北京,找他们的恩师杨昌济联系留法勤工俭学事宜。
从此,这个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领袖人物,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袖里青蛇胆气粗”“朗吟飞过洞庭湖”。在北京,蔡和森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北京大学、豆腐池胡同杨昌济宅第和东城遂安伯胡同李石曾(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的住所,很快了解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程序、所费川资和学生条件。他敏锐地嗅到了一股生动之气在遥远的异国之邦召唤着他,这是在沉朽、垂绝的湖南教育圈子内闻所未闻的。他一面写信给毛泽东、萧子升,让他们联系更多的湖南青年响应赴法留学的号召,一面与湖南在北京的高官士绅磋商,筹措湖南学生留法经费。
“多人打水,始有饱鱼吃!”在他的倡导下,湖南在京的名流都行动起来了,这其中包括他的恩师、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著名教育家胡子靖,北京政府河工督办、前财政部长熊希龄,众议员王子刚,司法部典狱司长王文豹等,大家都积极为留法勤工俭学生筹措经费,华法教育会也答应将湖南学生赴法贷款的名额从25人增加到70人。
当然,蔡和森最关心的还是新民学会,他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壮怀激烈地说:“必使我辈团体,几年后成为世界的中心!”
三月不知肉味
那时的中国,国穷、家穷、人穷,而年轻的学子更穷,要谋求一份职业,着实不易。或许就是这种贫穷困厄,才激发了他们奋起图强的大志。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言:“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10月6日,蔡和森得到了他的第一份职业:在布里留法工艺学校教授国文。月薪是从学生们的学费中挤出来的,每月20块大洋,这是留法勤工俭学会给这位湖南学生的特殊优待。
蔡和森非常看重这份工作,因为他的家里太穷了。在家时,他已经把每天的一日三餐简化为一日两餐或一餐,爱晚亭畔的苦读也拯救不了他的“饿乡惊梦”。从家乡出发时,母亲变卖了首饰,他又从萧子升那里借了4块大洋才凑齐了盘缠,而现在一下子每月可以挣20块大洋。一想到能用这些钱换成在湖南不曾见到读到的书籍报刊,怎不令他喜上眉梢。
10月10日,蔡和森在保定告别了毛泽东、萧子升,带着湖南预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初级班学员,分水路、陆路,分别乘坐6舱小船和蓝篷布马车,踏上了赴布里留法工艺学校的路途。
几天的奔波劳累,蔡和森的腿扭伤了,他拄着一根柳木棍,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开着玩笑。来自湖南益阳的孙发力,手里拿着一本《留法勤工俭学会说明书》问蔡和森:“蔡老师,布里村处在高阳和蠡县之间,这“蠡”字怎么解释?”
蔡和森回答说:“‘蠡’,就是蚌壳的意思。这说明,布里村一带过去是烟波浩渺之处。此地离沧州不远,据当地传说,蠡县附近就是过去的野猪林所在。”蔡和森看来已对布里村做了一番认真的梳理,这与他的同学毛泽东的习惯一样——去哪里工作,先对那里的风土人情了然于心。
孙发力、唐铎、颜昌颐喊了起来:“这么说,我们就是林冲发配了?”
蔡和森说:“林冲不过一介武夫,而我们是要出国勤工俭学,去‘世界文明第一国’法兰西寻求真理,振兴中国教育,十个林冲也比不得我们这班莘莘学子。”
蔡和森在布里村度过了4个多月的艰难时光,北方的严寒“洞穿”了他年轻的胸膛。他是一个真正的利他主义者:20块大洋,多数救济更为穷困的学弟们。他托毛泽东在北京买了20多条毛围巾,送给了这些湖南同学,他还央求华工段秉鲁的媳妇做了一件皮袍子作为“公共礼服”:谁有事谁穿,谁有病谁用它抵挡风寒。而蔡和森付给段秉鲁媳妇的1块银元,则被她珍藏多年,至死也不肯花掉。多年以后,熊信吾谈起蔡和森对他们这一帮小同学的关照和爱护时,依然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当年,湖南学生熊信吾只有13岁,还是一个半大的孩子。刚到布里村时,还是中秋时节,他就整天喊冷,好几次,一个人躲在宿舍里哭鼻子。蔡和森走过来,摸着他的头说:“小熊原来就是这个熊样子啊,这么点苦就吃不得,那日后怎么去法国勤工俭学?走,咱们今天放假一天,到高阳城里赶集买棉衣、吃切糕去。”
北方人的饭食以面食居多,更何况是在偏僻的乡村,窝头、咸菜就是他们连月不易的伙食。而黄米切糕,更是难得的美食。
啖蛇胆,明大志
不过,他们还是吃过肉的。
是蛇肉。那是北方最常见的蛇——蚺蛇。
颜昌颐、孙发力、唐铎、侯昌国等一班湖南同学,捉住了几条即将冬眠的大蛇。
颜昌颐对孙发力和侯昌国几人说:“这几天蔡先生的哮喘病又犯了,咱们把蛇胆送给蔡先生吃,让他补补中气吧。”
当冒着热气的蛇胆放在蔡和森面前的时候,蔡和森被学生们感动了。他向嗜饮的国文教员李宝华讨来了白酒,和着蛇胆一饮而尽。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蔡和森边饮边吟。
布里留法工艺学校的法文教员齐连登、国文教员李宝华、几何教员沈宜甲等都被他的名士风采惊住了。
“昔有汉高祖拔剑斩蛇定天下,今有湖南蔡和森君生啖蛇胆赴法留学,蔡君定有经天纬地之才干!”
国文教员李宝华的评判几年后就在蔡和森的身上得到了验证。
布里村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每天晨起散步的“湖南蛮子”: 在村路上,无论碰到拾粪的老人,还是放学的儿童,他都会笑脸相迎,拉呱几句。在北方严冬的夜里,蔡和森头缠白毛巾,向法语教员齐连登求教法文,浓重的湖南发音令他的法语学得非常艰涩,但他从未有一天停止过。他可以忍受几个月不吃肉的苦,但听说有的湖南学生偶去附近的集市上买“马”(一种彩票),却是大发雷霆:“我们赴法勤工俭学,是大者远者重者之业,耽于儿戏,岂可有成?我友毛润之,与朋友言从不及私事小事。一次他的腿摔坏了,卧床一个月,他就用躺在床上的一个月,通读了一遍《资治通鉴》。我们来这里学法语,学技工,是为了赴法留学救国救民,己身之修养万不可靡费!”
“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这是蔡和森在北方写给毛泽东的信。这个装了一兜子墨子的书来到布里村苦学法语、苦练内功的湖南师范生,在贫困的中国北方农村,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做“地主”和“剥削”——有的村子成百上千顷的土地归一个人所有,半个村庄的房子也是地主一家的。地主出门乘坐的大车一式的三大套,没有一匹杂毛牲口,而大多数穷人冬天为取暖却不分老幼去搂拾田野里的枯草败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4个多月的见识,无疑为蔡和森的思想奠定了一个充满实践意味的根基。临告别布里村的时候,他已经拿着载有十月革命消息的报纸对颜昌颐、孙发力等人说:“劳农专政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
离开布里村后,蔡和森的行李中墨子的书已经换成《新青年》《旅欧周刊》,他带着满脑子的“列宁”“马克思”“劳农专政”等新名词,赶赴北京,去找毛泽东、萧子升,继续他们留法勤工俭学的寻梦之旅。
那是1919年的除夕,唐铎、熊信吾送蔡和森到保定火车站,鞭炮声和锣鼓声不绝于耳。车厢里空荡荡的,没有几个旅客,也没有年夜饭的热气腾腾,只有冰凉的座椅和漫漫长途等待着这个远方的游子。
“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长剑走天涯。”
小“威尼斯”里的“夫妻档”
蔡和森终于在1919年年末,踏上了法兰西的国土——马赛港。大型邮轮“盎特莱蓬”号靠岸后的第五天,蔡和森终于到了巴黎,在华侨协社等待分配学习法文的学校。他迫不及待地对向警予说:“咱们最该去的地方就是豆腐公司。应该说,我们是在布里留法工艺学校开始留法生活的,我们一定要去那里看一看,布里村的乡亲们还托我给豆腐公司的亲人们捎好呢。”
见到蔡和森,李石曾异常兴奋,感慨地说:“蔡君,两年前在北京初会的时候,想不到我们的留法勤工俭学发展到这种地步吧?”蔡和森说:“石曾先生心地澄明,发乎其衷襄助勤工俭学生,中国的教育史上会铭记先生的功德的。”李石曾说:“和森先生已到,与子升兵合一处,将成一家,只差一个毛润之了,你们‘湘中三杰’如若相会在法兰西,当是多么美妙的故事噢。”
此时的李石曾,沉醉在自己创造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貌似繁荣的假象里,殊不知他那套无政府主义的管理模式正在一步步走向衰亡。
初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往往根据川资的多少,由李石曾分配到法国的各个中学先补习法文。钱多的,李石曾分配他们到巴黎、里昂等大城市的中学;其次者则被分配到小城市,如著名的风景区枫丹白露;再次者分到麦南市;更次者分到蒙达尼。囊中羞涩的学生暂时在华侨协社里食宿,等候华法教育会为他们觅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历史老人再一次在法兰西留下这样的经验之谈:改变中国命运的风云人物大都出自那些川资较少、偏居小城或真正勤工俭学的青年中间。
蔡和森、蔡畅、葛健豪一家和向警予、李富春、唐铎、颜昌颐、陈绍休、贺果、陈毅、李维汉、聂荣臻等都被分配到离巴黎几个小时车程的小城,如麦南、枫丹白露和有“法国威尼斯”之称的蒙达尼。他们先是在中学补习法文,而后,资金不足再去做工。从此,蒙达尼,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法国小城因为一批中国历史名人而声扬四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著名的蒙达尼派迅即成为留学生的核心,而蔡和森就是这个核心里的中心人物。中国革命史中令人称道的伟大爱情“向蔡同盟”亦在这里缔结,蔡和森、向警予在这座水光潋滟、酷似意大利威尼斯的小城里,开了一家“夫妻档”,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点燃了一大批热血青年心中的热情。
刚到法国,大家都吃不惯法国饭食,面对烤得干焦的面包和每顿必饮的冷水冲生红酒,蔡和森和一大群中国学生怎么也咽不下去。蒙达尼公学好心的副校长、法国社会党党员沙伯一个一个地给中国学生做工作:喝红酒活血又可以御寒。但大家还是难以下咽,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把大馒头一样的面包里面较软的部分抠出来吃——看外表还完整,但里面却空空如也。蔡和森和向警予给校方提了建议:烧一大锅滚开的水,把面包泡到开水里煮软后再吃。于是乎大家甘之如饴,每人一顿吃两大盆。
伙食还好办,难以抵挡的是法国的寒冬,大雪飘飘,滴水成冰,又因为连年战争,煤价暴涨,连壁炉也免了。来自中国南方的留学生大半没有经历过零下十摄氏度的严寒,而他们在上海所做的出国服装又都是廉价的西服,有的连个毛背心都没有,冷风吹来,就像刀子挖骨一般疼痛难忍。留学生们也顾不得礼仪了,穿上从国内带来的绸缎棉袍、短袄等衣物来御寒,一时花团锦簇,色彩缤纷,杂陈于法国各处住有中国学生的学校里,引得法国学生指指点点。
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就读于蒙达尼女子公学,她的三寸金莲更令法国人惊诧不已,纷纷前来围观。
蔡和森的哮喘病因为严寒再一次复发,他上不得课,出不得门,只有躲在租来的房子里,靠着一本《法华字典》读报看书。他对向警予说:“这里的冬天比布里村的冬天更难熬,那里还有街坊邻居们给扫树叶、拾树枝烧火炕,可这里连个壁炉都没有。”向警予说:“不怕,有让你点燃心火的东西。”边说边从怀里掏出一本小册子向他晃了晃:“你看,这是什么?”
蔡和森抢过来一看,是一本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这本被无数工人和无产者奉为“圣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光辉著作,就这样完整地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
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蔡和森靠着一本《法华字典》,“囚首垢面,猛看蛮译”了十几部马列专著,《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都经蔡和森之手传到胸怀四海志、改造旧世界的中国青年学生的心中。在蒙达尼男子公学的宿舍里,蔡和森给毛泽东和陈独秀等写了大量的信件,提出了建立共产党、实行社会革命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从而奠定了他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重要地位。

沙洛瓦劳动大学实习工厂
吉利数和“撒尿说”

萧子升说:“我们刚到法国,这里世界著名的文豪雨果说过:‘对罪恶的毒瘤,要开刀,但主刀的外科大夫必须格外冷静,而不是激烈。’我们的团体最好还是以石曾先生的‘自由、互助、工读’为主旨,采取无政府、无强权,如浦鲁东式之新式革命的好。”
蔡和森说:“这还是无政府主义的老一套。无政府主义行得通吗?自由主义是灵丹妙药吗?譬如说我们正在这间教室里开会,有人想在这时撒尿——这可以说是自己的自由,但是能不能在这时撒尿呢?当然不能。一个人的行为要受到周围环境的制约,受到社会、纪律的限制,不受纪律限制、不受社会制约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这是一个多么野心勃勃的“工读计划”!
不久,毛泽东回信:“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字)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但蔡和森始终没有加入工学励进会和工学世界社。“我为什么不加入工学世界社呢?我就是烦它的这‘工学’两个字。”蔡和森甚至在工学世界社决定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后,还不肯加入该社。
1920年12月,工学世界社再次召开大会,李维汉主张以个性为出发点,将社会建设在健全分子上面。蔡和森说:“你这是‘偏方’,治不了中国社会的痼疾。在病入膏肓的中国,非严正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大革命不可。”
数月之后,当留法勤工俭学生在被陈箓、吴稚晖等政客和法国当局、中国北洋政府耍弄得走投无路,蔡和森率领“先发队”准备出发进占里昂中法大学时,李维汉痛心疾首地对蔡和森说:“和森,我的‘偏方’真是无用,要求生存,救中国,非得像你所主张的那样,对军阀和旧世界,对帝国主义,均应一概扑杀之!”
而湖南留法学生欧阳泽当初对安徽学生尹宽说得颇为准确的一句话就是:“我看中国革命未来的领袖不是陈独秀,而是蔡和森。”后来,也成为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的尹宽从蔡和森处得到了第一本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如获至宝,读后到处宣讲。他说:“这本书,有学问的人读了不见得亲切,但工人们读了,一定会觉得讲到了他们的心里。”

1920年12月底,工学世界社在法国蒙达尼举行年会,图为与会者合影。第一排左四为蔡和森;第三排右五为李维汉;第四排右八为李富春
勤工俭学的那个年代,真是多事之秋。这边刚刚打破了军阀政客们的“大饭碗”——拒款运动算是大大地长了勤工俭学生们的志气,但接踵而至的这个消息就再坏也没有了——以勤工俭学名义成立的里昂中法大学对所有勤工俭学生们彻底地关上了大门。无论是法国当局、中国驻法公使馆,还是华法教育会,都统一了口径:里昂中法大学与勤工俭学生毫无关系。
勤工俭学生们赖以求学的希望霎时破灭。
1921年9月3日,法国政府宣布,从9月15日起停发留法勤工俭学生们的维持费。
9月25日,里昂中法大学将按时开学,而新任校长吴稚晖正在国内招收新学生,不日将前往法国。
困居在法国各地的近两千名勤工俭学生被彻底抛弃了!
所幸的是,这时的勤工俭学生再也不是一盘散沙,蒙达尼派与劳动学会两股最大的力量勇敢地走到了一起,迎接这次对于年轻的勤工俭学生们来说还显得过于险恶过于复杂的斗争。
9月5日,“克鲁邹工厂勤工俭学生争回里、比两大学运动团”成立,陈毅起草了争回里、比两大学的《宣言》和《通告》;
9月6日,以蔡和森为首的蒙达尼勤工俭学生,在巴黎华侨协社召开会议,各地代表二百余人应邀参加,确定以争回里、比大学为近期斗争主要目标;
9月17日,两派学生在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的主持下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一致决定“谋求勤工俭学生全体的根本解决,以开放里昂中法大学为唯一目标”,并确定了三个信条:一、誓死争回里大;二、绝对不承认部分解决;三、绝对不承认考试。
这里的“信条”,条条都有很大的“来头”,尤其是最后一条——绝对不承认考试,更有深意。不承认考试,不是他们考不上,而是向当时的中国政府、法国政府和世界表明:这是我们的政治态度,是向政治对手的叫板,是一个政治团体最初的主张和行动萌芽。很显然,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共产党员在信条的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赤色,共产党人最心仪的色彩,鲜血一样的红色信仰已经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成为了最富吸引力的流行色。而蔡和森壮烈的一生,无疑就是那抹红色中最耀眼的一束。
十几年后,蔡和森临危受命,远赴香港指导处于低潮的工人运动,被军阀逮捕。牢狱之中,他一定回忆起了他在法兰西的土地上,最先接触到的那抹鲜艳的红色,他也一定回忆起了他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来到中国北方布里小村的那个寒冷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