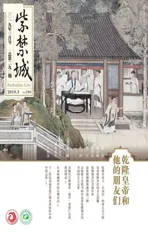怀抱观古今 深心托豪素浅谈乾隆皇帝的文人意趣
2019-04-30郝炎峰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
郝炎峰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
乾隆皇帝自身的文人意趣,是乾隆一朝在皇帝周围出现一大批以诗词书画见长的词臣、画家的根本原因。乾隆皇帝的这种文人意趣并非骨中带来,而是源自其自身的文学、艺术修养,又通过书法、绘画、诗词,甚至是文房器物的创作表现得淋漓尽致……
乾隆皇帝,姓爱新觉罗,名弘历,庙号高宗,是清代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他的一生基本贯穿了整个十八世纪。在位期间,他励精图治,巩固边疆,社会总体安定,经济较为繁荣。在其统治晚期,西方世界发生了剧烈变革。乾隆盛世之下,社会潜伏着重重危机,但乾隆皇帝仍可称为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之一,乾隆一朝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高峰。
乾隆皇帝自幼得满汉名师教导,接受了系统而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加之聪颖好学,即位后于万机余暇游艺翰墨,留下了数量庞大的诗文和书画作品。造办处和江南三织造等机构在他的指导下还制作了大量的具有文人雅趣的文房用品。通过对这些文物的考察,我们可以对乾隆皇帝的个性、审美和文人情趣有更多的了解,同时也有助我们于艺术一道,全面地理解和评价乾隆皇帝。
文人意趣的养成
满人入关以后,充分认识到儒家思想在治理国家上的不可替代性,因此十分重视皇子和宗室子弟的教育。据《清太宗实录》记载,清太宗皇太极曾下令:「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赵翼(一七二七年~一八一四年)回忆他所见到的皇子读书情景,讲道:「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依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并感叹道:「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檐曝杂记》卷一「皇子读书」)吴振棫(一七九〇年~一八七〇年)也曾记载过清代皇子的教育情况:「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退迟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惟元旦免入直,除夕及前一日,巳刻准散直。」(《养吉斋丛录》卷四)
雍正皇帝非常重视对皇子的教育,他为弘历延请了多位老师,这些老师不是朝廷重臣便是当世大儒。其中福敏、朱轼和蔡世远三位对其影响最大,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年),六十九岁的乾隆皇帝作《怀旧诗·三先生三首》回忆起这三位老师时仍满怀深情。
福敏(一六七三年~一七五六年),字龙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以知县待铨。时世宗(雍正皇帝)在藩邸,高宗(乾隆皇帝)初就傅,命福敏侍读。」(《清史稿·列传九十·福敏传》)从乾隆皇帝的诗作中可知,福敏自弘历六岁即被聘为老师,直至雍正初年出任浙江巡抚,前后近十年。乾隆皇帝在《怀旧诗·三先生三首·龙翰福先生》中怀念说,福敏「能多方诱迪,于课读为长。余初就外傅,始基之立,实有以成之」,并称从福敏处「得学之基」。(《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五十八)
朱轼(一六六五年~一七三五年),字若瞻,一字伯苏,号可亭。雍正初年被选为弘历老师。乾隆皇帝在《怀旧诗·三先生三首·可亭朱先生》诗中说:「皇考选朝臣,授业我兄弟。四人胥宿儒,徐(元梦)、朱(轼)及张(廷玉)、嵇(曾筠)。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并自注云:「我朝成例,皇子初就学,见师傅,彼此皆长揖。皇考择此四人为余兄弟之师,命在懋勤殿行拜见之礼,示尊重也。」朱轼工古文,「究心经学,著有《周易注解》、《仪礼节略》及《历代名臣名儒循吏传》诸书」。乾隆皇帝「从学十余年,深得讲贯之益,学之全体,于先生窥津逮焉」。(《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五十八)
蔡世远(一六八二年~一七三三年),字闻之,号梁村。雍正二年至九年任弘历老师。乾隆皇帝在《怀旧诗·三先生三首·闻之蔡先生》中说:「所从之师虽多,而得力于读书之用,莫如闻之先生。」蔡世远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学识渊博,尤精于性理之学。他继承「二程」和朱子之学,又深研周敦颐、张载的学说,是清代闽学派的骨干。乾隆皇帝说他于蔡世远「得学之用」,其为学对乾隆皇帝的影响可谓深远。
除此三位先生外,雍正皇帝为弘历挑选的老师还有徐元梦、张廷玉、嵇曾筠、鄂尔泰、蒋廷锡、邵基、胡煦、顾成天等多人。雍正八年,弘历奉父亲之命将自己之前所作的诗文结集为《乐善堂集》,作为自己二十岁的一个总结。他在《乐善堂集》的序文中说:「余生九年始读书,十有四岁学属文,今年二十矣。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讲论至再至三。」这些老师为年轻的弘历讲解儒家经典,教授作文方法,可以说弘历的启蒙教育已经站在了极高的起点上,这也为他以后的诗文创作开启了兴趣之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弘历在接受儒家教育的同时,还受到了严格的书法训练。清代至迟自顺治时起,就开始有意识地训练皇子的汉文书法。顺治时,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便向皇帝建议:「皇上承太祖、太宗之大统,聪明天纵,前代未有,今满书俱已熟习,但帝王修身治人之道,尽备之于经,一日之间,万机待理,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伏祈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则治化亦光矣。」王士禛曾记载:「上(顺治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万几之余,游艺翰墨,时以奎藻颁赐部院大臣,而胸中丘壑又有荆、关、倪、黄辈所不到者,真天纵也。」(《池北偶谈》卷十二「谈艺二·世祖御笔」)故宫博物院目前还保留有顺治皇帝学习汉文书法的习作及书画作品多件。
乾隆皇帝最敬重的皇祖康熙皇帝也十分钟情于翰墨。康熙皇帝一生临池不辍,他曾说「自幼习书,豪素在侧,寒暑靡间」(《懋勤殿法帖序》,《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三十二),「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和珅、梁国治《钦定热河志》卷十四),「耽好笔墨,有翰林沈荃,素学明时董其昌字体,曾教我书法。张、林二内侍,俱及见明时善于书法之人,亦常指示,故联之书法有异于寻常人者以此」。(《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此外,康熙皇帝还刊刻了《懋勤殿法帖》,编修了《佩文斋书画谱》,都是当时重大的内府书画整理工程。
雍正皇帝在书法上亦颇有心得,他雅好临池,「留心书法最久,所见历代法帖最多」。(《跋淳化阁帖后》,《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十二)此外他还非常重视文人意趣的表达。他命人创作多幅行乐图,在画中体验文人的生活情境。将自东汉至明代「令人心旷神怡,天机畅适」(《悦心集序》,《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八)的佳章妙句选编成《悦心集》,显示出对文人意趣的追慕。此外他还亲自参与到文房用具、瓷器、漆器、木器等工艺品的设计、制作中,对材料、形式、技巧、色彩都有品评判断,反复强调要「文雅」、「秀气」、「素静」、「精细」,以符合文人的审美要求。
顺治、康熙、雍正几位皇帝,均在政务之余寄情翰墨,留下了大量的书画作品,这些都对乾隆皇帝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弘历在登基称帝前的十三年间,每天坚持练习书法,除节日和特殊情况外极少间断。如此高强度的训练和超乎常人的勤奋,使得弘历的书法功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使得书法成为伴随他一生的兴趣爱好,并成为日后出现一大批以书画见长的词臣和画家围绕在他周围的根本原因。在诗文、书法之外,弘历继承其父对文人意趣、文人审美的重视,登基之后,开始了规模更大、影响更为广泛的带有文人意涵的活动,终其一生,显现出这位帝王在文人意趣方面的浓厚兴趣。
文人意趣的表现
乾隆皇帝自身所带有的文人意趣是多方面的,从诗文的创作到书画的实践,从文房用具的制作到园林的营造,几乎涵盖文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肖像行乐
乾隆皇帝命人绘制了多幅行乐图画像,这些画像中,他被描绘成一位文士,身着传统服饰,或拈须深思,或提笔凝神。在《弘历古装像》轴中,乾隆皇帝端坐于书房之内,一手拈须,一手执笔。书桌上,已铺开一张良纸,似乎正等待着他落笔书写。书桌旁的几上放置着精致的觚、盆和瓶,觚、瓶中插着盛开的梅枝和兰花,正与窗外的古梅和青翠的竹子交相辉映。春天已到,皇帝的眼神坚毅而有神,似乎已然成竹在胸,只差将胸中丘壑落在纸上了。这幅图营造了祥和的氛围,精致的陈设为典雅的书斋平添了几分清幽与高逸,共同烘托着画面的主人公 一位自信的文士。
乾隆皇帝还命人创作了多幅具有哲学意味的《是一是二图》。这几幅绘画构图大同小异:乾隆皇帝身着古代服饰,一腿半趺坐于床榻之上,右手执笔,左手持纸卷,脸扭向右侧,一副文士装扮。床榻后面的屏风上,或绘山水,或绘花卉,清逸高雅。屏风上,悬挂着一轴乾隆皇帝的半身像,体貌、着装与坐榻上的皇帝相同。挂轴中的皇帝头扭向左侧,正与坐榻上的皇帝遥遥相对,似乎有着默契的交流。床榻右前方书桌后,一名童子正手持花瓶,往书桌上的杯中注水。皇帝两侧的家具上,摆满了青铜嘉量、觚、炉、鼎、玉璧、青花罐、瓶、壶、册页、手卷等物,它们不仅充实了画面,令构图更为饱满,而且映衬出乾隆皇帝儒雅的生活情趣和他对传统文化的赏识与重视。
其实这些《是一是二图》是有母题的,即源于宋代的《人物图》页。类似体现乾隆皇帝文人雅意的仿古行乐图在乾隆时期还绘有不少。如金廷标所绘的《弘历宫中行乐图》和佚名宫廷画家所绘的《弘历赏雪图》、《薰风琴韵图》等,画面中的乾隆皇帝均身着汉族文人的服饰,神情淡然,从中可见他对汉族文人乐天自在的生活状态的向往之情。其中,《宫中行乐图》临仿自刘松年的《宫中图》,《薰风琴韵图》临仿于刘松年款《琴书乐志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皇帝在其御制诗《题宫中行乐图一韵四首》中,有「松年粉本东山趣」之语,「东山」的典故来源于东晋文人谢安携丝竹隐居于东山的故事。诗的小注中,说明了仿制此画的理由:「《石渠宝笈》藏刘松年此幅,喜其结构古雅,因命金廷标摹为《宫中行乐图》。」可以推测,其他的几幅临仿之作也应该都有相似的理由,即文人意趣、结构古雅。
天章海溢
乾隆皇帝登基后,承继父、祖勤政的作风,处理政务、批阅奏章,数十年如一日,显示出超强的意志。同时在万机之余暇,于诗文上也取得了很多成就。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保留诗作最多的人,他爱诗成癖,一生作诗不辍,据统计,他的《乐善堂全集》、《清高宗御制诗初集》至《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再加上太上皇期间的《清高宗御制诗余集》,共收诗作总数达四万三千六百八十九首。他称自己「平生结习最于诗」(《题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二十五),倘若几天不吟咏便「辄恍恍如有所失」。(《清高宗御制诗初集》跋)。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年),面对数以千计的诗作,他曾写诗道:「赋诗何必多,杜老言诚正。况乎居九五,所贵行实政。」(《尚书蒋溥奏进所刻御制诗集书此志怀》,《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十九)然而自此之后,他还是一直维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除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因崇庆皇太后病世,「简行幸,疏吟咏」,诗作数量明显锐减,全年仅二百九十二首外,其他年份,诗作数量年均都在七百首以上,其中最多的是乾隆三十七年,有一千零六十七首之多。
写诗的爱好一直持续到乾隆晚年。和珅曾这样描述乾隆皇帝:「每日万几之暇,读书无间,寒暑吟咏,日十数篇有余。」(《五福五代堂联句》,《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十九)他的诗情与中国古代传统文人如出一辙。而御制诗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感,为我们还原了乾隆皇帝有喜有悲、有情有义的多重面相。
在乾隆皇帝的御制诗中,吟咏书画、青铜、玉器、陶瓷、砚台等艺术品的诗作约有三千四百余首。对于他喜爱的艺术品,他反复题咏来表明他的态度和喜好,如《题赵孟頫水村图手卷》、《赵昌写生蛱蝶》、《咏周牺匜》、《咏痕都斯坦玉壶》、《咏砚墨》等。
御笔风飞
书法是陶冶情操、抒发性情的有效载体,为历代文人所重视。乾隆皇帝自幼就受到系统的书法训练,而这一爱好在他成为皇帝之后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乾隆皇帝一生创作过大量的书法作品。故宫博物院现在庋藏有乾隆皇帝的书法作品上万件,足以说明他的勤奋和用功。
乾隆时期,内府收藏盛极一时,典藏了大量历代名家法帖,为乾隆皇帝观摩、临习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乾隆皇帝对历代法书名帖无不临摹,甚至一摹再摹,如钟繇、索靖、陆柬之、欧阳询、颜真卿、怀素、柳公权、虞世南、褚遂良、杨凝式、张即之、「宋四家」、文徵明、董其昌等,都在他的临摹范围之内。乾隆皇帝对王羲之书法尤为偏好,搜检《石渠宝笈》,可以看出在他所临习的古代各家法书中,王羲之所占的比重最大,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法帖。对王羲之的得意作品,乾隆皇帝表现的近乎痴狂,他曾提到「逸少兰亭帖,学摹自幼龄」,甚至一生都在不断临写《兰亭序》。至今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多件乾隆皇帝与《兰亭序》或《兰亭诗》相关的墨迹。对于与《兰亭序》相关的书法作品的保藏、流传,乾隆皇帝也十分重视。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年)春,乾隆皇帝将收集到的历代书法名家兰亭墨迹六帧(唐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摹《兰亭序》,唐柳公权《兰亭诗》,明董其昌《临柳公权兰亭诗》,《戏鸿堂刻柳公权兰亭诗》原本),再加上大学士于敏中《补戏鸿堂刻柳公权兰亭诗阙笔》,及乾隆皇帝自己临写的董其昌《临柳公权兰亭诗》,合为「兰亭八柱」。为了「一永其传」,乾隆皇帝将圆明园坐石临流亭改建成八方重檐亭,并易以石柱,每柱刻一本,即著名的「兰亭八柱」。
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乾隆皇帝收藏到了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他特辟养心殿西暖阁为「三希堂」,用来贮藏这三件稀世珍宝。对「三希」之首的《快雪时晴帖》,乾隆皇帝更是多次题跋,并在帖前写下「天下无双,古今鲜对」、「神乎其技」的溢美之词,又评价其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此后,他不断地临摹这三件法书,名之以《三希文翰》,以此来表达对它们的珍爱和推崇。
此插屏为乾隆四十四年,乾隆皇帝为贮藏《兰亭序》真迹摹本,令造办处所造。插屏面板刻会稽兰亭聚会场面,取下抽拉式面板,里面两侧边框刻乾隆皇帝御笔:“叙诗荟美由今昔,临写存真在晋唐。”中间是存放兰亭摹本的八个屉匣,十分隐蔽,合上面板即是一件可作装饰摆设的家具。
抛开艺术水平不论,乾隆皇帝对自己的书法是有要求的。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乾隆皇帝《行书习字诗》卷上,原字明显被人刮擦处理过,之后乾隆皇帝又重新题写习字诗于其上。在后面的跋中,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此诗书于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乾隆皇帝认为,之前自己的书法水平不够,因此命造办处的去旧字高手张恺将原字刮除。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年)十一月,乾隆皇帝曾下旨要求臣下回缴乾隆二十年之前颁赐的各类御笔书法,即使已经制作成匾额、对联或勒在石材上的赐字,也要将墨迹原本缴回。原因是他认为自己往昔的阅历和实践不足,笔力有所欠缺。在这道谕旨中,为了说明自己在书法上的苦心修习,他还举了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练字书写过十万麻笺的例子来类比。
丹青披泽
乾隆皇帝接触绘画的时间比书法要晚,受到的教育也不太系统,但其绘画起点很高。乾隆时期,内府汇集了大量的历代绘画珍品,为他临摹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乾隆皇帝的周围始终活跃着一批擅长绘事者,如宗室允禧、允禄,大量宫廷画家如蒋廷锡、董邦达,以及西洋画家如郎世宁、王致诚等。皇子时期,弘历就时常与这些人交往,向他们请教画学,与他们探讨画理、切磋画艺,得到了高水准的艺术指点。乾隆皇帝与这些工于绘事的臣子们相处,不仅可以对他们的绘画技巧进行近距离的观察与了解,也激发了他浓厚的创作兴趣。
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在圆明园逗留时,经常到西洋画家王致诚的画室看他画画。为此王致诚在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十一月四日给布鲁瓦西亚侯爵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平时作画的地方,正是我向您讲过的那些小殿堂之一。皇帝几乎每天都前往那里观看我的工作,以至于使我无法缺席不到。」
根据《石渠宝笈》和《盛京故宫书画录》的记载,乾隆皇帝一生至少创作了一千四百多幅绘画作品,涵盖了人物、花鸟、走兽、山水、楼阁等各类题材。如《寿星图》、《仿赵孟頫沙渚双鸳图》、《瓶莲图》、《临文徵明五君子图》、《多禄图》、《避暑山庄烟雨楼图》、《西湖图》等。这些画的共同特点是:介于工笔与大写意之间,笔墨简练,着重表现物象的意态神韵和精神内涵,构图简括,主题突出,画面具有平和淡雅的文人气。
文房萃珍
乾隆皇帝雅好书画,着意于文人意趣,对文房用具的品质和样式要求也十分苛刻。乾隆时期的宫廷文房用具品类丰富,形式多样。除笔、墨、纸、砚「四友」外,还有笔架、笔筒、笔洗、镇纸等。这些文房用具,一部分出自内务府造办处,或按照内廷要求交由杭州、苏州、江宁三织造承办制作;一部分则来自于地方进贡。文房用具不仅有实用价值,也是融书法、绘画、雕刻、装饰等各种艺术为一体的艺术品。
根据档案记载和对目前留存实物的观察,乾隆皇帝御用笔无不用材讲究、制作精良。材质方面,金银玉瓷、木竹牙骨,无所不有。装饰技艺方面,集各种工艺技法,极尽工巧。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中记载内府用笔:「供御文房四事,别类称名,不可胜纪……笔之属则以书福笔为万撰珍用之管,所谓赐福苍生也。御书常用者,有斑竹管、大提笔、髹漆、文檀各种提笔。其寻常供用朱书、墨书之用者,则有万年青管、经天纬地、万年枝、云中鹤、惟精惟一、云汉为章,及竹管、檀管、钿管,皆由外省供进。」乾隆时期,仍以浙江湖州制笔最负盛名,每年地方例贡文房用具中以湖笔数量最多。
乾隆皇帝喜欢在笔管四围刻以名言佳句或御制诗文,营造清雅的文人氛围,如「管城无处不生花」、「无思不入奇」、「珠圆玉润」、「宇宙经纶」等,还有御笔「兰亭真赏」、御制「牡丹花诗」等,无不构思巧妙,雕刻精细。
乾隆时期,造办处专设墨作,负责御用墨的制作,生产了很多「内廷恭造之式」的御制墨,它们大多署「御墨」字样或「乾隆年制」款,制作精良,装潢考究,极具时代特点和皇家品味。乾隆御制墨中,有以皇帝书斋或宫殿命名的墨品,如「敬胜斋珍法墨」、「遂初堂藏墨」、「御制淳化轩墨」等;有仿古集锦墨,由各种形式墨锭组合成套,有的一套中墨锭多达数十种,如乾隆四十年重装所制博古墨,由四十种墨式组合而成,包括螭佩、玉彘、青圭、昭文、国宝、七香图、鱼佩等,并特制红雕漆龙纹墨匣盛装。
还有一套乾隆御题画诗墨,质地优良,墨模雕刻精细,是套墨中的稀世珍品。这套墨共九锭,从右至左、自上而下分别为:沈周画茄菜诗墨、吴历画山水诗墨、王蒙画林壑云泉诗墨、王蒙画竹趣图画诗墨、黄筌杏花文禽图画诗墨、文徵明画松石画诗墨、王宠画山水诗墨、王绂画山水画诗墨、方壶画叶菜图画诗墨,每锭正面为名画,背面是乾隆御题诗。墨的形状、大小各不相同,有花瓣形、长方形、圆形、正八边形等。其中年代最早的画是五代后蜀黄筌(九〇三年~九六五年)的《杏花文禽图》,还有「元四家」之一王蒙的两幅画《林壑云泉图》和《竹趣图》,以及元代方壶,明代王绂、沈周、文徵明、王宠,清代吴历的作品。乾隆皇帝的题诗或以诗论画,或借题发挥。题诗有五言、七言,有律诗、绝句,诗后分别钤以「乾隆」、「几暇怡情」、「几暇临池」、「得佳趣」、「乾隆宸翰」等玺印。乾隆时期,内府收藏了大量历代名画,这套墨是从乾隆皇帝题诗的名画中精选出八位画家的九幅佳作,由雕墨家依照数尺长的画卷,微缩雕刻在几寸长的墨模上再制成墨,以纯熟的技艺表现出原画的意境。
乾隆皇帝钟情翰墨,对纸张的要求可谓精益求精。在皇帝需求的直接推动下,乾隆时期,除在纸张的传统制作技艺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外,还出现了许多品质优良、工艺精湛、不同质地、不同图案、用途各异的纸张,中国古代造纸迎来了黄金年代和制作高峰。
具体而言,乾隆皇帝御用书画纸有各色粉蜡笺纸、洒金纸、罗文纸、宣纸、金粟山藏经纸、侧理纸、明仁殿纸、梅花玉版笺、澄心堂纸等,均是当时纸张中的精品。如乾隆皇帝十分喜爱的梅花玉版笺,其纸面涂以粉蜡,光滑匀称,质地坚厚结实,银白色的纸面上为纵横交错的冰纹及金色或银色的梅花图案,右下角钤盖花边隶书小印「梅华(花)玉版笺」。
同时,为了满足内廷源源不断的纸张需求,在乾隆皇帝的命令下,还仿制出了大量的传世名纸,如仿侧理纸、仿金粟山藏经纸、仿澄心堂纸、仿明仁殿纸、仿梅花玉版笺、仿高丽纸等。
砚作为文房四宝之一,自古就受到文人的重视。它不仅作为创作书画不可或缺的实用物品,更是一种可以怡情悦性的艺术品,故从选材、雕刻工艺、形制设计上都十分讲究。乾隆皇帝更是如此,他命廷臣于敏中等人收集内府所藏古砚精品二百四十方,于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编纂成《钦定西清砚谱》,图文并茂,钩摹精美,记载详细,考证充分,体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
乾隆时期的御用砚,大部分出自造办处砚作。除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四大名砚」及瓦砚、砖砚等传统砚台之外,更有被清代视为砚台之首的松花石砚。
「松花石出混同江边砥石山,绿色、光润、细腻,品埒端歙。自明以前无有取为砚材者,故砚谱皆未之载。我朝发祥东土,扶舆磅礴之气,应候而显,故地不爱宝,以翊文明之运。自康熙年至今,取为砚材,以进御者。」(《钦定西清砚谱》卷二十二「松花石双凤砚说」)松花石在清代被认定为是王朝龙兴发祥之地的圣物,故此类砚台专供皇室所用,对于产地也进行封锁,秘而不宣。
除笔墨纸砚外,乾隆时期还有形式各异的辅助用具,如臂搁、笔架、笔筒、笔床、笔洗、砚滴、水丞、水注、镇尺等,它们增加了书写的便利,逐渐被视为不可或缺的文房用具。乾隆皇帝喜赋诗题咏,仅御题文房用具即多达数百首。他还命工匠将这些诗文镌刻于笔、墨、砚、笔筒、笔洗、文具匣等用具之上,使之蕴含了文化内涵和文人意趣,呈现出独特的宫廷艺术风格。
乾隆时期社会总体安定,经济发展,国库充盈,为乾隆皇帝增修园林、制作文玩、从事他喜欢的文人活动提供了物质保证。同时,乾隆皇帝在皇子时期接受了严格、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为其诗文和书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乾隆皇帝在勤政之余,醉心于诗词,一生书法、绘画创作不辍。他对文房用具要求极高,有时会亲自参与设计和修改,促进了这些艺术品类的创新和高水平的制作工艺。他对这些文人意趣之事、之物显示出超乎寻常的喜好,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相关文物,让我们在其帝王身份之外,对乾隆皇帝有更全面的评价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