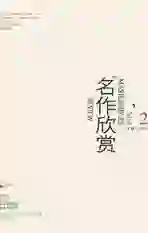从“有我之思”到“无我之境”看“物境诗”的审美价值
2019-04-10王运涛
王运涛
摘要:在中国传统诗学中,相比于“有我”的备受推崇,“无我”作为主体长期以来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许久以来,尽管万水干山能够独自徜徉于人类“文明”之外,然而作为“山水诗”中触物感“兴”之体的“山水”,却很少会被理解为具有“独立之精神”的“无情之物类”。及至王国维“无我之境”的审美建构,方始打破了传统诗学浓郁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将传统的“有我之思”压倒“无我之境”的状况加以扭转,因此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
关键词:山水诗 “有我之思” “无我之境” 以物观物
孟子有言:“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由是可知,孔子虽不是道家学派的代表,却能以一种“道观”的方式观天地万物之理,察鸟兽动植之文,诚所谓“观物有方,技近乎道”。“‘一阴一阳谓之道,儒道之别,在于斯。前者为道家所察,看阴;后者乃儒家之所重,推阳。前者看小,后者事大。”传为唐王昌龄所著的《诗格》有言“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其中自然形象的物境是面对自然的观物取象,心理形象的情境是感悟自然的澄怀味象,形象之外的意境是追求意境的象外之象,三者构成了意境的三个层次。然而,由于在传统文化中,“观乎人文”的时刻远远超过“观乎天文”的时刻,使得“物境”在传统中国文学批评中并没有像“人境”(人的生命等)那样得到足够的重视。
一、传统诗学中的“有我之思”与“有我之境”
中国古典诗歌以关涉山水自然或吟风弄月而著名,这种类型的诗歌被笼统地称为“山水诗”“田园诗”和“山水田园诗”。在大多数情况下,山水诗的内容确实是与诗人的写作技巧、文法知识、身体经验和精神状态(或者人格)等有着复杂的联系。譬如,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当诗人无法摆脱命运的纠缠时,往往会“寄情山水”,借助“江山之助”,在诗人与山水、主体与客体、人类与物境的暂时“两忘”中得以解脱,于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诗人的“有我之思”逐渐弥漫山水之间,由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关涉山水自然(吟风弄月)的“山水诗”佳作迭出。无论是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还是苏轼的“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抑或辛弃疾的“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物境”在诗人眼中总能对人类的悲喜有所感受。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甚至各领风骚三五年)相比,“国破山河在”,大自然的不易损坏,“城春草木深”,大自然春去春又回的时常更新,特别是它欣欣向荣的春色,往往更容易使人想起人的脆弱和痛苦。“往来人自老,今古月常新”,这种自然与人之间的无情对比是中国诗歌的永恒主题。由此而来,传统的中国山水诗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就是探讨山水与诗人人格之间的关系。
“有我之境”就是“我”出现在诗境中,即“诗境”中留有“我”的影子。如欧阳修的《蝶恋花》中“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如果说“乱红”的意象恰能描述主人公的内心活动,那么它就是主人公烦乱心绪的写照。在这首词中,花只是诗境中的客体,充当配角,人是主角,是主体,其中“我”不但出现了,而且是作为抒情主体出现的,明写“我”的心境状态。该词隐喻了“我”与“物”(“花”)之间的“同病相怜”:二者都是柔弱、多愁善感的,也经历着被遗弃的类似遭遇。“章台路”这一意象表明,女主人公对离青楼而去的情人满腹幽怨:如果说词中的女主人公是一朵娇艳的花儿,那么她的情郎就是一只翩然飞走的蝴蝶。然而,如果我们认真阅读这首词,这种“对号入座”的解读是不是有些牵强呢?我们之于花儿对于它用花蕊滋养的蝴蝶离去的感受的体验需要怎样的想象力呢?经此一番将“物”视为潜在的能“观”其他实体的“观者”的發问,我们认为“物”不仅仅是“人间之事”的“代言者”,它更是独立于“我”之外的“能思”的自为存在者。
二、王国维“无我之境”的审美建构
“无我之境”就是“我”从“诗境”中退隐。在王国维的“无我之境”中,由于审美主体放弃了人类万物灵长的惯性思维,“我”的自我意识便在此“山水之间”隐藏了行迹。“我”的隐退反而促使“物境诗”得以再现“物”的“真实”,或者说“直接性”地言说“物境”。如陶渊明《饮酒(其五)》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人把视线从“我”身上转移开来,注重的是“无意中的见”,写的是一种“无我之境”。在这里,远处的群山既是自然的风景,也是人世繁华的象征。诗人无意间与群山相遇,在这种邂逅中,他事先并无欣赏山景的“观光计划”,因此“见山”完全是被动的,不期然而然的。此处用“见”却不用“望”的妙处向来为人所激赏:“望”是一种有意识的“观看”,具有较多的“自我意识”,望到的只能是“有我之境”;“见”则是一种无意间的“邂逅”,主体意识在此行迹全无,见出的是“无我之境”。在“无我之境”中,就在诗人无意间抬头的一刹那,远处青山就映入眼帘,好像群山有在人面前显现自身的能力,甚至也把“我”的“主观意识”完全消解了。这无疑有助于唤醒世人认真地对待“物的主体”:“物”不仅仅是“人间之事”的“代言者”,更是独立于“我”之外的“能思”的自为存在者。
从“有我”到“无我”的“言说主体”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我”完全消失,而是“真义”存在于无言的“物境”中。如叔本华所言:“天才的性能就是立于纯粹直观地位的本领,在直观中遗忘自己……即是说完全不在自己的兴趣、意欲和目的上着眼,从而一时完全撤销了自己的人格,以便(在撤销人格后刷了为认识着的纯粹主体,明亮的世界眼。”当“我”从“物境”中退隐,主动放弃由来已久主观认识中的人类对于“物境”的优越性,此时的“无我”并不是“没有了自我”或者“忘记自我”,更不是“麻木无情”,恰恰是“我”并不把“物境”仅仅视为感知对象与格致之“物”。如此一来,反而更容易实现邵雍“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的修心学说的境界。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由于创构“物境诗”的“感兴”需要“诗人虚静空明的心态与特定物象不期而遇”,并且“经由诗人的审美取舍、艺术重构和艺术传达,就成了心物浑融的‘无我之境”。因此,这种意义上的“无我”才是“无私的”,它是以“物境”为其导向,而不是以“我”为“独尊”,以“我”为评判“物境”之高下的准绳。由是可知,“无我之境”是把“我”从“唯我”的“审美泥淖”中超拔出来(而不否定“我”),为“物境”预留出独立于人类感知之外的“审美空间”。因此,“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无我之境”不仅是“我”对于“物境”的承认,更是一种“情感状态”的标示。
三、一流大诗人的“以物观物”与“物境诗”
在传统的诗学观点看来,“以物观物”也是诗人“观物”的一种方法。因为“物”是不能作为观的主体的,“观者”是属于人类的“我”,只不过要尽可能地贴近属于“物境”的“物”的视角来呈现,因而“无我之境”其实仍是以“我”而非“物”为“境”的中心。这自然是合乎日常经验的,但问题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属于人类的“我”怎能“以物观物”呢?如果“以物观物”可以被理解为“观”并不限于“我”(人类),它也可以是“物”,即任何能够感觉其他主体的“主体”,那么这种解释便使得“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的难题变得清晰起来。无论是苏轼的“空固纳万物,静固了群动”,还是程颢的“万物静观皆自得”,无不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所有的实体都有成为“观者”(“观”的主体)和“被观者”(“观”的客体)的潜在质素。当诗人在艺术呈现过程中,更多地遵从“物”的“物性”,而不是代“物”言说的时候,“物境诗”由此摆脱了语言和文明的羁绊,使审美主体更能接近原生态的“物境”,体验到“物境”的“自然美”。如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时的“物境诗”更像是作为“艺术作品”而不是作为属于“自然”的“派生物”而存在的。
随着人类自由的“表达”不应以牺牲“物”的自由表达为代价的认识日益深入人心,“物境诗”的艺术技法也不是相对于其“目的”而言的“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因此,越来越多的诗人尝试着不再一味地把“物的主体”仅仅具体化为种种“意象”。“物境诗”的境界高下,并不追求对“自然”的逼真“再现”或“模仿”,也不以其所造之境在“经验世界”中是否可见为标准。这时的“以物观物”更像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自觉应用。又如庄子在《齐物论》中所言:“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日:彼出于是,是亦因彼。”与之相对应,“在叔本华的哲学中,观我与观物,方式与顺序固是不同,然皆须视‘我为万物中之一物,如此才能使观者和被观者,得莹彻之呈现”。
以传统的观点来看,不能被“物境”的具身体验证实的审美经验就是“不真实”的,诗人对于“物境”的具身体认影响着“物境诗”的创作。事实上,“物的主体”只能通过想象而存在,人类可以自由地想象任何仅仅存在于意识中而在现实中不存在的主体。例如,作者描绘原始森林中的动物世界,那些个性鲜明的动物或许是不存在的,也不需要考虑是否有人能证实“我”的想象。艺术作品之所以具有生命,恰恰是因为它们用人类的方式去再现不属于人类的语言,以自然和人类不能言说的方式在言说。如王国维建构的“无我之境”,便是竭力使曾经被“我”压制以“肯定自我”的“物境”重新“显现”,标示“物”的在场和“自然美”的可能。因此,不妨把“物境”诗看作是在“生产”自身的审美经验,而非从他处“复制”灵感。如此一来,我们就不用在“物境”诗的审美经验或者“我”對于“物”的具身经验之间预先做出“谁是主体”的“审美判断”。
总之,一流的大诗人多能以自然展示其自身的方式观之。传统诗学观将“无我”理解为“忘身于自然”的做法,有着浓郁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这种观点妨碍着我们以更有意义的方式理解“物的主体”,同时它也剥夺了我们置身于“物境”中体验“以物观物”的“自然美”的“机会”。王国维“无我之境”的美学思想给审美主体带来的启发是,我们应该认真地对待“物的主体”,包括重估它在被“以物观物”的美感经验称之为“物境诗”中的“主体”地位。而作者意想中的“主体”在可见或不可见的“经验世界”中是可以独立存在的。“物境诗”的“意象”也有其审美价值,其原因就在于该“意象”与“经验世界”中的“物象”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不管二者的相似度有多高,“意象”就因此而具有了“真实性”,因而也自有其“审美价值”。其所追求“自然美”并不以艺术与“经验世界”中的客体的相似程度为衡量标准,而是它能否唤起审美主体对于经验世界之外的物作为其自身的美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