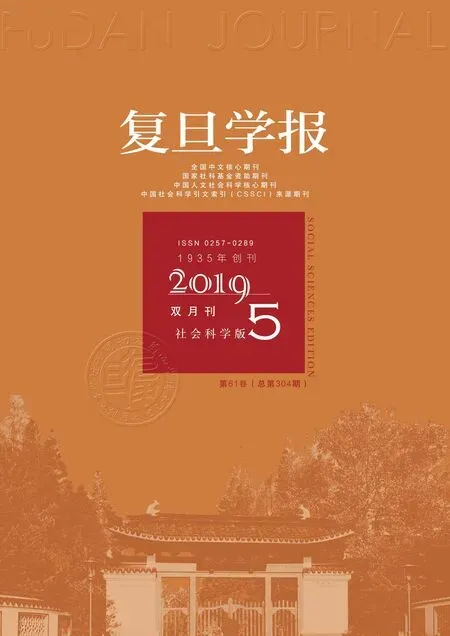“兴味派”文人与小说话关系探论
2019-03-24朱泽宝
朱泽宝
(湖南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长沙 410082)
小说话,滥觞于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经过三百余年不绝如缕的嬗变,最终于1903年在梁启超等人主持的《新小说》“小说丛话”栏目中正式定名。由此,小说话借着小说跃居文坛中心的时代背景,也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据不完全统计,小说话的存世数量已有千余种之多,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小说批评不可或缺的一翼。无论就文本数量还是批评实绩而言,经过这不到半个世纪的积累,小说话已可与诗话、词话、文话等并肩立于话体文学批评之林而无愧色。在这其中,民国“兴味派”①本文的“兴味派”,大致指民国初年追求“兴味”的一批小说家。学界或称其为“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民国旧派”、“通俗文学派”等,因其含义多偏负面或不完全,本文不取。“兴味派”小说家以其丰硕的创作实绩堪称民国初年小说界的主流,其影响波及整个民国时期。详见孙超:《“兴味派”:辛亥革命前后的主流小说家》,《文学遗产》2013年第3期。文人的功绩不可忽略。他们积极投入到小说话的创作,以丰硕的创作业绩巩固着小说话的批评史地位,并将小说话锻造成其流派建构的重要工具。可以说,“兴味派”文人赋予着小说话更为完整的话体文学批评体性,而得益于小说话不同于其他批评样式的灵活形式,“兴味派”文人鲜活的文坛形象与批评姿态也得以更为突显,小说话遂成为保存其理论发声与群体认同的一份宝贵档案。本文即着力探寻“兴味派”文人与小说话间呈现出的双向塑造之关系。
一、“正名”:小说话批评地位的确立与宣扬
话体文学批评之产生,本缘于文人的从容闲谈。“话”之对象的选取,实际上是文人喜好与趣味的体现。小说话的长期缺席与小说的倍受欢迎间构成的强烈反差,客观地展现出小说在雅俗文化中截然不同的地位。到了20世纪初,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在内忧外患的国家局势刺激下,梁启超等人始极力推崇小说的无上地位,赋予其“新民”的意义。在此背景下,小说话这一概念的提出,本就带着推尊小说文化地位的意义。正如梁启超在其《小说丛话》中说:“诗话、文话、词话等,更汗牛充栋矣。乃至四六话、制义话、楹联话,亦有作者。……惟小说尚阙如,虽由学士大夫鄙弃不道,抑亦此学幼稚之征证也。”②梁启超:《小说丛话》,《新小说》,1903年,第1卷第7期。这既交待出小说话出现的必要性,更能从其中看出梁启超为小说争取与诗、词、文,甚至四六、制义、楹联等同等地位的急迫之心。此后,吴趼人在《月月小说》上连载的《说小说》、黄人在《小说林》上发表的《小说小话》等有影响的小说话接踵而至。这些晚清名人对小说话的呼唤与理论实践,在小说批评领域固然极有价值,但纵观当时的知识界,小说话在事实上并没有赢得与诗话、词话等同等的地位。如清末民初卓有影响的《民权素》《庸言》等刊物上都有“诗话”等专栏,小说话则往往只能屈身于“文苑”“评论”等栏目下,尚未有独立之资格。因此,为小说话“正名”甚至“争名”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到了“兴味派”文人的肩上。大致说来,“兴味派”文人做了以下几种尝试:
第一,从梁启超那里“接着说”,重申小说话的存在价值是文学批评演进历程中的必然结果。其论说策略与梁启超基本相似,即以诗话、词话等为参照,将小说话的缺失视为文学批评领域的不正常现象。如胡寄尘就在《小说管见》中直言小说话存在的必要:“小说自是一种文艺,诗有话,文有谈,小说亦不妨有论。”①寄尘:《小说管见》,《民国日报》1919年2月20日。此处虽提到的是“论”,但从其前后语境来看,实与现代性的学术专论不同,其含义应与“话”“谈”等相当,指的就是话体文学批评样式。经过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宣传与近二十年的实践,小说作为文艺之一种的观念已为大众所认同。在这种情形下,还没有小说话,自然是不合时宜的。而发表于《珊瑚》、署名说话人的《说话》对此现象谈得更为透彻:“诗有话,称诗话;词有话,称词话;曲有话,称曲话;谜有话,称迷话……小说也应该有话,说小说的话,应称‘说话’。”②说话人:《说话》,《珊瑚》,1933年,第13号。“说话”虽与“小说话”字面有所歧异,但两者内涵与外延却并无二致。这段话看似老调重弹,只是将梁启超三十余年前的话再说一遍,却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三十年代各文体之分布格局已与梁启超的时代有了天壤之别,当年诗歌等尚是文坛之正宗,而此时无论新文学家还是旧派文人,都主要致力于小说创作。若此时小说话还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无疑就是传统话体文学批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丧失活力的表现。故而对于尚有传统批评思维的学者而言,小说话的有无,关系着小说与话体文学批评的双重颜面。因此,“兴味派”文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梁启超的话语重新演绎一遍,自有其新鲜的意味,而其为小说话正名的努力也由此显得更为迫切与有力。
第二,“兴味派”文人创作的大量小说话被直接命名为“小说话”,从直观层面上直接扩大着小说话的影响力。小说话的接受度不如诗话、词话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标识度不够明显。在小说话产生之初,基本上没有小说话被直接称为“某某小说话”,而往往标作“小说丛话”“小说杂话”“小说闲评”等名目,虽然点明了其话体批评之实质,却也在客观上削弱了小说话这一新生事物的知名度与传播度。至“兴味派”文人手中,方开始径称这一批评文体为“小说话”,如解弢《小说话》、何海鸣《求幸福斋小说话》、补庵《铃斋小说话》、范烟桥《小说话》、吕君豪《小说话》、龙友《小说话》、陈元品《小说话》、织孙《小说话》、虎啸《小说话》等,或出之“兴味派”文人之手,或刊载于其主持的刊物上。此外,还有上文提到的《说话》及《息庐小说谈》《民国小说谈》等,其命名也与“小说话”极其相似,而内涵完全相同,也推进着小说话这一名目的传播。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命名为“小说话”的小说话,虽然篇幅或有长短,最初发表的载体各有不同,但都是严格以散谈的形式来闲评各种小说现象,严格地恪守着话体文学批评的规范,对于后来的小说话都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尤其是解弢的《小说话》,其语言之典雅、视野之广阔、评论之精当,乃至方法之邃密,都在整个民国话体文学批评中堪称上乘之作,足为小说话史上的典范之作。小说话的文体规范在这一系列“小说话”的引导下也逐渐定型。
第三,“兴味派”文人利用掌握的媒体资源,采取各种策略,推动小说话的规模化发表,直接扩大小说话的影响。最明显的举措就是设置专门用于发表小说话的专栏。其实,小说话从其定名之初即与报刊有着莫大的关联,梁启超主持的《小说丛话》就在《新小说》的“论说”栏连载,前后持续一年之久。当然,这里的“论说”远不限于小说话,更有许多政论性文字存乎其间。民国初年,上海等地的通俗文化刊物多掌握在“兴味派”文人手里,为他们宣传、发表小说话都提供了足够的平台。“兴味派”文人则更进一步,常在其主持的报刊上开辟专栏,专门用于小说话的发表。如《小说日报》就曾专辟“小说话”专栏,专门刊载小说话文字,前后有许廑父、徐枕亚、何海鸣、徐卓呆、秋月柳影、听潮生、灨一、郑逸梅,俞天愤、冯霭如、董巽观、梁寿卿、张乙庐、金智周等五十余人在其中发表对于各种小说现象的看法。其间参与的人数、话题的广度以及理论的深度比起《新小说》中的《小说丛话》,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如《星期》曾先后创立“小说杂谈”“谈话会”等两个专栏,琴楼、马二、无虚生、琴倩、伊凉、以刚、赓夔、灵蛇、鹃魂、董希白、吴兴、转陶、郑逸梅、无诤、吟秋、戴梦鸥、醉绿、镜水生等数十人,先后在其中谈论其对小说的感想,随写随载,语言活泼,内容广泛,涉及到新旧小说之对比、小说的社会功用、古代小说的研究等当时小说评论领域的时髦话题。还有的刊物则开辟小说话栏目,用以专门讨论某一类型的小说。如《半月》从第一卷第六号至第四卷第一号就开辟“侦探小说杂谈”“侦探小说琐话”等栏目,先后登载了张舍我、王天恨、朱、鲍眕、程小青、范菊高、郑逸梅等人的小说话,专门谈论侦探小说的创作、阅读诸问题。这在推动小说话形态多元化与功能多样化方面起着良好的作用。
与开辟专栏以成规模地发表小说话相映成趣的是,“兴味派”文人还常编选若干种小说话,汇为一集,予以出版。这种“选本”式的小说话结集,实体现出“兴味派”文人在小说话批评特性上的深度自觉,有着将小说话经典化的意味。如周瘦鹃、骆无涯曾编选一部小说集,名曰《小说丛谭》,1926年10月在大东书局出版。该书共收程瞻庐《望云居小说话》、范烟桥《小说话》、张舍我《侦探小说谈》、胡寄尘《说海感旧录》、郑逸梅《小说杂志丛话》、黄厚生《说林嚼蔗录》、周瘦鹃《说觚》等十三种。这些小说话都出自当时文坛名人之手,且颇有理论价值,其中蕴含的引领示范意义自不待言。不管是小说话专栏的开辟,还是小说话的结集出版,本质上都是小说话的规模化发表,以成批出现的集群效应来拓展小说话的知名度与接受度。
第四,“兴味派”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叙述小说话“史”。这种“史”的描述或有不够准确之处,但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其凸显出小说话的产生有其常理意义,并已形成客观的演变谱系,其中呈现出为小说话正名并巩固其地位的强烈意图。如对小说批评素有研究的胡寄尘就说过:“小说之有评论,始于民国元年之《太平洋报》,但所论多不确当,无足取者,自后六七年来,小说盛行,而评论独付阙如。今小凤首先提倡,著《小说杂论》,继者踵起,《日报》小说栏中,时见有此项言论。《小说新报》且又预告另添论坛一类矣。不可谓不盛也。惟有一事,须预防其流弊者,即不可各分门户、自立党派是也。”①寄尘:《小说管见》,《民国日报》1919年2月20日。这里提到的“小说之有评论”,实特指小说话而言,从下文提到的叶小凤的《小说杂著》即可印证此点。再者,习见意义上的小说评论渊源久远,以胡寄尘之学养,不可能仅将其追溯至“民国元年”,更可说明此段是指“小说话”。此段评论言简而意远,既有对小说话起源的追溯,也有对其演变趋势的前瞻。他明确提出的小说话始于“《太平洋报》”,实则指的是无名氏于1912年8月8日至9月25日在《太平洋报》上连载的无名氏的《小说闲评》,每则文字从数十字到数百字不等,分别讨论《官场现形记》《孽海花》《九尾龟》等白话小说、《右台仙馆笔记》等文言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等外国小说以及小说作法、小说评点等小说现象,完全没有混入传奇、弹词等其他文体,堪称标准的小说话体裁。胡寄尘将小说话的起源追溯至此,或因其体例规范使然。更可贵的是,其在当时小说话著作趋于繁盛的时代,表现出极强的洞察力与预见性,警惕着小说话中可能出现的门户之见。这一切都预示着小说话具有充分的创作积累与阐释空间。
二、“辨体”:小说话批评体性的扩充与完善
话体文学批评最初由诗话发其端。由于诗歌在中国文体中的正宗地位以及诗话最初创作者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巨大的示范效应,诗话一举奠定中国话体文学批评样式的写作规范。诗话“集以资闲谈”②欧阳修:《六一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4页。的创作意趣、“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③许觊:《彦周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第378页。的话题选择,以及“即目散评”式的写作形式等,都为词话、文话、曲话等继承。小说话作为话体文学批评的后起之秀,能否具备前代诗话、词话等呈现出的批评体式与精神内涵,是其是否有资格被称为“话”的根本要素。
20世纪初的时代背景已与涵孕出诗词、词话的传统社会相差甚大。当时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生于其间的文人们大多没有当年诗话作家们从容闲谈的闲情与余裕。①宋人优裕、闲适的晚年生活,是诗话产生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见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改革与救国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主流追求,相应的文学批评也自然要为这一目标服务,就连小说话的定名者梁启超本人即是当时功利主义小说思想的代表人物。即使以《新小说》上连载的“小说丛话”而论,也是理论批评者过多,而闲谈故事者偏少,话体文学批评“资闲谈”②有学者认为“资闲谈”是诗话的基本写作方式。见祝尚书:《论宋诗话》,《文学遗产》2016年第1期。的精魂在小说话的诞生之初,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缺位。
此外,话体文学批评的基本文本形式必须是由若干条内容组成,“一条一条内容互不相关”③蔡镇楚:《中国诗话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7、18页。。在西方学术规范强势涌入的20世纪初,追求论著的体系性与逻辑性成为潮流,小说话这个刚诞生不久的新批评样式不可避免地受到此种风气的影响。仅仅在小说话正式定名的十年后,小说话已开始偏离传统话体批评的轨道,甚至还表现出明显的与小说专论合流的倾向。如常被视为小说话代表作的成之的《小说丛话》与管达如的《说小说》,然细读之下,可发现二者均呈现出严谨细密的写作逻辑与构建完整的小说知识体系的雄心④如黄霖先生即认为“《说小说》将晚清一些主要的小说观点条理化,显得颇有系统。”“(《小说丛话》)对晚清的小说理论做了一次归纳。”分别见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51、403页。,二者都是徒有小说话之名,其形制与内容已不是“话体”所能囊括的。
不管是早期的梁启超还是诚之、管达如等人,其笔下的小说话都承担着反省中国小说传统以及建构完整的小说知识体系的严肃任务,客观上说是对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的一次理论回应。至于其本应具有的批评特质,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如此,话体文学批评样式中“资闲谈”的内核在小说话中荡然无存,此时的小说话徒然具有话体批评的形式,还远没有继承其应有的精神特质。迎接着现代曙光诞生的小说话,饱受着紧张的文人心态与西方学术论著形式影响的双重干扰,是否能兼备千百年来话体批评沉淀下来的所有必要特质,在当时的条件下,确是个未知数。
这一困局在“兴味派”文人那里得到了根本的扭转。可以说,在“兴味派”文人的小说话写作中,文人的写作风格与批评样式的根本特质达成了浑融的契合。有学者曾提出“宋诗话的本质特征是‘消费’诗歌”⑤祝尚书:《论宋诗话》,《文学遗产》2016年第1期。,更准确地说,消费诗人与消费诗歌在诗话的理论话语中充当了同等重要的功能。其后,不管话体批评样式如何变异、增添何种新的功能,这种以消费作品与消费作家为特质的闲谈始终是其稳固不变的内核。梁启超等人没有赋予小说话的“闲谈”属性,在“兴味派”文人那里充分完成了。“兴味派”文人多活跃在上海等现代消费主义盛行的大都市,其主办的报刊也大多以消遣为基调,肆意地消费流行小说。消费小说名家,也成了“兴味派”小说话的重要话题。早期话体批评中展露出的轻松闲适的氛围,在“兴味派”文人所作的小说话里得以复现。
首先,从小说话的命名上看,“兴味派”文人着力彰显其“闲谈”的本质属性。“名定而实辨”⑥王先谦:《荀子集解》,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275页。,通过对一项事物的命名,往往能呈现出命名者的态度倾向。欧阳修开辟了“以资闲谈”的诗话写作风格,有学者指出“从诗话之体的首创者、体式、性质、风格特征诸方面来考察,欧派诗话应当是中国诗话之坛上的正宗”。⑦蔡镇楚:《中国诗话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7、18页。由于诗话的典范效应,“闲谈”遂成为传统话体批评中的主导风格与规定性特征,内容选择的丛杂性与写作倾向的谐趣性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不同于诗话、词话等,小说话在最初发表时,基本上不在小说话前冠以作者的姓名、字号、室名等个人化信息。“兴味派”文人笔下的小说话多以“小说某话”来命名。当然,这里的“小说”可置换为“说部”“稗乘”“稗官”或具体的小说名等,“话”常由“评”“谈”“谭”“说”“言”等代替。重点在于,“兴味派”文人对于作为联结言说形式的“话”与言说对象的“小说”的“某”字的选择,往往能准确地体现话体批评应有的神韵。一般来说,“杂”与“闲”二字是小说话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字眼。举例而言,含“杂”的有叶小凤《小说杂谈》、周瘦鹃《小说杂谈》、李薰风《小说杂谈》、民哀《稗官琐谈》、寄尘《小说拉杂谈》等,含“闲”字的有马二先生《我之闲谈》、眷秋《小说闲评》、姚民哀《小说闲话》、藏拙斋主人《小说闲语》等。其他与此语意相近的“琐”“漫”“丛”“屑”等,也都是“兴味派”文人命名小说话的常用字。此类文字所指示的作者态度看上去“并不严肃”①郭绍虞评价宋人诗话时说“其性质之并不严肃”。见郭绍虞:《宋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页。,却精准地传递出小说话的批评精髓,契合着传统话体文学批评随性而发、散漫而谈的文本特质。正是这一篇篇“小说杂话”“小说闲评”,在专题论著成为学术主流著述方式的20世纪上半期,延续着话体批评最后的光辉,小说话的话体批评特征也因此变得无可置疑。
其次,从小说话的内容选择上看,重“论事”而轻“论辞”,小说家的言行成为其最为关注的话题。在以消遣为底色的都市文化环境中,传统话体批评“资闲谈”功能在“兴味派”文人的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现。“闲谈”的对象多半是当时最活跃的那批小说家。无论是说坛名家,还是无名读者,都习惯将其所熟知的小说家秘闻作为独家新闻而公之于世。其“闲谈”的内容则五花八门,涉及小说家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生活琐事到文学活动,几乎无所不包。有的记录小说家的生活习惯,王天恨《说海周旋录》提到施济群时说:“济群写的信很潦草,和我一样,提起笔来,只管有一事写一事,所以常常写上几张信笺,字却一点不考究。”②王天恨:《说海周旋录》,《半月》,1925年,第4卷第23号。有的推崇小说家的性情品德,如金智周《说海珍闻》表彰许廑父慷慨资助贫寒学生的豪举。有的复述小说家对文坛风气的看法,如黄转陶《说林忆旧录》记尤玄甫以为“现在的小说界,有了‘小说阀’了,人家说旺盛是好现象,吾倒说现象不好。所以吾殊不愿再以有用的笔墨,贡献给小说阀”。③黄转陶:《说林忆旧录》,《半月》,1924年,第3卷第15号。有的则披露小说家的创作秘辛,郑逸梅笔下的小说话多能及此,如其称孙漱石写《海上繁华梦》时说:“犹虑曲苑中有秘不告人之处,万难出于意想,他就把天香院主娶了回来,金屋藏娇,玉楼偎影,在温柔乡中消受艳福。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著书时才得鞭辟入里,大之如院中之一切弊害,小之则一切忌讳、一切规例,都从天香院主那里得来。”④郑逸梅:《说林掌故录》,《上海生活》,1940年,第4卷第2期。更有的指出小说家团体形成及其风格传承,如姚民哀的《说林濡染谈》就认为于右任、钱芥尘、周少衡、包天笑及严独鹤等人,分别通过办报、办学等途径,造就了一大批小说家。由于谈者与被谈者间普遍存在的亲密关系,小说话中贡献的“谈资”足以成为研究“兴味派”文人生平甚至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三、小说话中的“兴味派”群体建构策略
小说话与“兴味派”文人间呈现出双向塑造的关系,“兴味派”文人完善着小说话作为话体批评的应有属性,而小说话也成为“兴味派”文人群体意识建构的重要武器。如果说在20世纪二十年代曾出现过一场激烈的“新”“旧”文学观念之争的话,那么论争的双方并不是势均力敌的,以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一派大张挞伐,而“旧派”的声音却极为微弱,甚至存在严重的“失语”现象。其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形象也显得模糊不清,甚至长期作为一个被攻击而无法反击的沉默的负面形象而存在。“作为一个群体,它是一个由建构、想象而生成的动态群体。”⑤胡安定:《鸳鸯蝴蝶派的形象谱系与自我认同》,《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从后世对其纷杂的称呼中就可见一斑。事实上,“兴味派”小说家们具有鲜明的群体观念,小说话正是其构建群体意识的重要武器,只是由于小说话长期以来的被遮蔽而显得不为人知。当我们开始钩沉那沉埋已久的小说话文献时,“兴味派”文人在其中寄寓的特殊的群体建构策略也应一并表明。
第一,规范“小说”边界,摒除新小说家。⑥为论述方便,本文提到的“新小说家”均沿习称,指“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派的小说家。实则相对古典小说而言,“兴味派”文人也自称为“新小说家”。如周瘦鹃《小说杂谈》就曾说“吾国古时小说,未有作日记体者,惟新小说始有斯体,……其最先见者,有包天笑《馨儿就学记》,后有徐枕亚《雪鸿泪史》,均日记体之长篇小说,颇脍炙一时人口。”对于“新”“旧”文学观念之争,“兴味派”文人看似采取守势,面对新文学家们咄咄逼人的批判,只能发出调和性的声音,如“各有所长,不相掩没;各有所短,亦不能强为辩护”①绮缘:《小说琐话》,《小说新报》1919年第12期。,绝少见其能针锋相对地对新文学一派从思想主旨到遣词造句作系统性的理论批判。这并不意味着“兴味派”文人们对新小说家的主张完全认同。在小说话中,“兴味派”文人常常将新小说家不纳入讨论之范围,就很能说明问题。小说话,顾名思义,当是批评各种小说现象之作。易言之,但凡是小说,无论新旧古今,都可纳入小说话的讨论范围。而详察“兴味派”诸人各种类型小说话,提及新文学的寥寥无几。特别是专门讨论“当代”小说家的小说话,完全没有新小说家的一席之地。如民哀的《民国小说谈》,仅“谈”杨尘因、王大觉、叶小凤三人的小说创作面貌,无一语及新派文人。孙绮芬的《小说闲话》,也只是闲话吴双热、天虚我生、周瘦鹃等“旧派”文人的小说。再如署名“可怜虫”的调侃之作《小说界的十二金钗》,所列也全是“旧”文人。这种近乎将“小说”等同于“兴味派”小说的观念几乎笼罩着“兴味派”文人笔下的所有小说话,如郑逸梅的《小说杂志丛话》,也未话及任何一种“新派”小说杂志。
署名大胆书生的《小说点将录》最能说明问题。大胆书生以点将录的体例,将“兴味派”诸人类比为《水浒》英雄,每人下加以按语,评论极高,兼及其文坛地位或文学成就。如将李涵秋比拟为林冲,赞曰:“禁军教头(涵秋为师范学校教师有年),冠绝时流。见摈王伦,有志莫酬(涵秋曾有纪事自述昔年初作小说时,有稿投某书局未录)。怒潮澎湃起英雄(涵秋以《广陵潮》得名),匹马单枪孰与俦。”②大胆书生:《小说点将录》,《红杂志》1922年第1期。以“点将录”之方式开展文学批评的第一人舒位,曾谈过其旨趣所在:“爰效东林姓氏之录,演为江西宗派之图。”③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序》,《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页。所谓“江西宗派图”,就是吕本中所作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江西诗派”这一诗人群体的概念也正是发源于此。有学者指出,“《点将录》确实是《宗派图》的延续”。④龚鹏程:《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5页。《小说点将录》正起到了强烈的群体确认的作用。既名曰“小说点将录”,那么就理当将当时小说家全部“点”过一遍。事实上被其“点”者有七十余人,全是“兴味派”小说家,如包天笔、陈冷血、王钝根、李涵秋、周瘦鹃等,而当时的新文学小说名家如鲁迅、郁达夫等皆未被列入。大胆书生的《小说点将录》问世后,陆澹庵(署名“莽书生”)鉴于其“所点只七十余人”,“戏为大胆书生补成全璧,易其名曰《文坛点将录》,示范围之较广也”。⑤莽书生:《文坛点将录》,《金钢钻报》1925年7月30日。其派别意识更为强化,所评亦皆为“兴味派”文人,于“新派”小说家中仅列入茅盾一人,将其比附为“地兽星紫髯伯皇甫端”,并不怀好意地下了这样的赞语:“勾角磔格,蛮夷之语,犬羊之属,君与为侣。”按语更为恶毒:“雁冰善蟹行文,编《小说月报》,提倡新文学,新文学家大多主张非孝主义,乃禽兽之属也。”⑥莽书生:《文坛点将录》,《金钢钻报》1925年9月27日。于是,在对本派文人的褒扬与对新文学家的攻击间,“兴味派”文人的优越感顿生,其派别意识也在此比较中得以强化。
第二,重建经典小说谱系,完成自我经典化。孰为小说之正宗,是新旧两派论争的必争之地。“兴味派”文人在理论话语的建构上稍逊新文学家,但也曾做出过相关尝试,如范烟桥撰《中国小说史》,就将“最近十五年”的“兴味派”文人的小说创作誉为千年来的“小说全盛时期”,包天笑、徐枕亚、李涵秋、叶小凤等人独领风骚,而新小说家在其中无一席之地。对于其间的缘由,包天笑在该书的《弁言》中说得很清楚:“吾国之小说,自有其悠远之历史,讵稗贩舶来之品,摹拟蟹行之文,以为斯业之足传?”⑦包天笑:《弁言》,范烟桥:《中国小说史》,苏州:苏州秋叶社,1927年,第1页。而出自“兴味派”文人之手的小说话者不约而同地体现出这一精神,在建构中国小说谱系时,极力凸显“兴味派”小说与古典小说的传承关系,而将“新”小说摒之于外。如大觉的《稗屑》,杂论古今小说,在民国部分仅论及苏曼殊、叶小凤等人;周瘦鹃《小说杂谈》纵论中外小说,于当时的小说家也仅提到包天笑、天虚我生、刘醉蝶等人。任情《小说漫谈》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详论《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七侠五义》等作品后,转入对“近十余年来”小说界状况的描述,其结论为:“旧小说虽种类繁多,不乏名作,而厌故喜新,乃人之恒情、有求则必有供,新小说家遂应时而出,遍于大江南北,南方小说家如李涵秋、徐枕亚、周瘦鹃、张春帆、徐卓呆、不肖生等,皆享名一时。北方小说家如张恨水、刘云若、李薰风、赵焕亭等,亦为人所盛道。”①任情:《小说漫谈》,《盛京时报》1937年6月4日。这里谈到的“新小说家”,指的就是如李涵秋、徐枕亚、张恨水这一班“兴味派”文人。在任情的叙述中,“兴味派”小说自然接续上中国古典小说的演变脉络,是悠长的小说传统在新时代的当然继承者,其在小说界的正统地位不容置疑。有意思的是,任情在《小说漫谈》的最后也提到了“所谓新文艺小说家”,除鲁迅、茅盾外大多数皆不置可否,根本就在于新小说家“今但谋其毛皮而忽略其实学,则文字虽作到如何华丽,骨子里则终不免空虚也”。②任情:《小说漫谈》,《盛京时报》1937年6月4日。在其看来,大多数新小说家旧学根底的缺乏,使其小说不足以跻身经典小说序列。同时,重视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是“兴味派”文人与新派文学观念的又一个重要分野,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其小说经典建构谱系中。张恨水曾作一篇小说话曰《今小说家与古文人孰似》,特意强调“兴味派”文人学习前代文学的功力,将当时主要“兴味派”文人与古代著名文人一一作类比,如认为陈蝶仙父子似“苏氏父子”,恽铁樵“似柳柳州”,李涵秋“似陆剑南”③张恨水:《今小说家与古文人孰似》,《申报》1921年2月12日。,又“仿佛袁随园”,如此等等,皆意在将“兴味派”文人视为古代文学传统在当时的传承者。总而言之,“兴味派”小说话构建的经典小说谱系,透露出一条崭新的小说从古至今的演变路径,已颇具自我经典化的意味。
第三,渲染文人轶事,强化群体认同。如上文所述,“兴味派”小说话中最常见的内容就是“闲谈”,“兴味派”文人的生平事迹更是闲谈的主要对象。在这看似无聊且无关紧要的闲谈中,“兴味派”文人的群体意识正在不断被树立与强化。在这看似无关紧要的闲谈中,往往具有浓厚的社会意义。“所有这些故事,都会创造出一种群体感,是这种感觉把有着共同世界观的人编织到了同一个社会网络之中。重要的是,故事还能使我们明白,生活在旁边那条峡谷里的人们是否属于自己人,是否可以和我们同属一个群体。”④[英]罗宾·邓巴:《人类的演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74页。《红杂志》上《文坛趣话》的发起与跟进,就完整地呈现出以故事聚拢团体的镜像。发起者施济群在交待写作缘由时说:“比年以编辑杂志故,时得与文坛诸子握手言欢,而诙谐笑乐之性,初未稍改。积久趣事弥多,因摭记忆所及,录刊《红杂志》,名曰《文坛趣话》,盖皆纪实也。”⑤施济群:《文坛趣话》,《红杂志》,1923年,第2卷第1期。《文坛趣话》在当时就起到了很强的聚合同仁的作用,黄转陶、严独鹤、枫隐等人先后参与到这一创作行列,并持续不断地发掘与贡献新的趣话,就是明显的表征。《文坛趣话》共连载四十余期,先后谈及严独鹤、尤半狂、程瞻庐、姚民哀、顾明道、许指严、周瘦鹃、赵苕狂等数十人的趣事。这其中披露的许多“趣事”甚至极其琐屑无聊,如嘲笑赵眠云头太小,爆料程小青欢喜吃五香豆,取笑郑逸梅吃西瓜子没有黄雀快。这些信息本在充作谈资或聊以考证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文学批评价值。但当其以小说话的面貌出现在公开发表的杂志上时,却有了特别的意味。其最初也只在朋友之间流传,现在将其堂而皇之地将其刊载于杂志上,公之于众,除了博读者一笑,满足其对这些名闻一时的小说家生活的好奇心外,还无形中具备了建构群体认同的作用。《文坛趣话》中出现的谈者与被谈者的人数共有五十多人,基本上聚拢了当时“兴味派”的主要人物,可谓“兴味派”的一次集体亮相。其中没有出现任何一个新小说家,清楚地显示了彼此的界限。而且,这些趣事的发表,在他们看来,不过就是将寻常的闲谈取笑从客厅搬到了报刊上,多了一些听众或观众而已。这些看似仅可称为八卦的故事,被翻着花样地不断讲述,拉进了小说家与普通读者的距离,使其追求趣味的文风更为深入人心。其他如郑逸梅的《著作家之嗜好》《文坛清话》、王天恨的《说海周旋录》、潘祖贤的《谈谈几位小说家》等等,都是以同样的轻松笔调描写“兴味派”文人的逸闻趣事。通过反复的言说,在这些“插科打诨”的趣话中,“兴味派”文人和群体风格变得前所未有的鲜明,塑造文学群体意识这一严肃的活动也正在徐徐展开。
第四,运用类比,确定格调。话体批评中普遍存在的类比思维,最初发源于《周易》。①《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种思维方式“常常凭着对事物可以感知的特征为依据,通过感觉与联想,以隐喻的方式进行系联”。②葛兆光:《七世纪以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类比之物的选取,往往能反映其人对社会的感知角度,进而折射出其审美意趣与思想倾向。“兴味派”文人常常在小说话中将其派中之文人类比成当时社会流行之事物,正好与其迎合都市民众心理的消遣主义倾向相契合,而“兴味派”的主流风格也从此可窥。最常见的就是常将文人比作名花。如郑逸梅的《稗苑花神》将严独鹤、周瘦鹃、徐卓呆等二十余位“兴味派”文人比附为各种花神,其理由多五花八门。如严独鹤为“玫瑰神”,因其“近辑《红玫瑰》杂志”;徐卓呆为“梅花神”,因“卓呆一署半梅、逸梅,愿为梅花神执鞭”。③郑逸梅:《稗苑花神》,《半月》,1925年,第4卷第4号。此外还有慕芳的《文苑群芳谱》等,沿袭着此种路数,将包天笑等小说家比拟为花,而在论述上更为细致,如分析包天笑何以为莲花时说“天笑作品,清芬悠远,喻以莲花,最为相宜。他有时写得很秾艳,有时却出诸白描,又可拿红白莲花来比仿”。④慕芳:《文苑群芳谱》,《红玫瑰》,1925年,第1卷第32期。可见,将“兴味派”文人比作花是当时的潮流。署名“可怜虫”的《小说界的十二金钗》,特意列举当时颇有盛名的字号中有女性色彩的“兴味派”文人,一一加以调侃。将小说家类比为名花美人,并不纯为追求谐趣使然,也不全然是对“男子作闺音”的文化传统的切身实践,实是与民国初年出版界喜以名妓、名花充作杂志封面的风气相契合。“兴味派”文人又曾自命为“社会之花”,潮流杂志《社会之花》的主编王钝根就有这样的豪迈宣言:“今吾侪以优美之文艺为社会之花,此花长好而不萎,爱花者皆可得之,无一人快意众人羡妒之弊。得之者欢喜把玩,无爱哂烦恼丧志贼命之虞。”⑤王钝根:《〈社会之花〉发刊词》,《社会之花》,1924年1月创刊号。他们将本派文人比喻为名花,寄寓着服务社会的意愿。
更重要的是,在以轻松的笔调迎合都市中产阶级心理的过程中,也宣告了这一群体文人的主流风格。“兴味派”文人对自身形象的比附,远不限于名花美人。粗粗翻阅当时的小说话,就会发现,凡是当时都市普通人群热爱的事物,如“雀牌”“戏子”“影戏演员”“酒”等,都会被拿来作为本派文人形象的对照物。⑥分别见新庵《小说家与雀牌》(《小说日报》1923年2月4日)、洲钱金智周《小说家与影戏演员》(《小说日报》1923年3月4日)、章抱桐《小说家与戏子》(《小说日报》1922年12月17日)、洲钱金一仙《小说家与酒》(《小说日报》1923年3月12日)。其比附之方式有出于风格相似者,更多的则纯是无谓有噱头,如称“毕倚虹,是红酒”,恐怕就是因“虹”“红”二字谐音而已;更有甚者,有的根本没有指出比附的理由。其合理性已不再重要,热衷于将“兴味派”文人比附为流行之物本就能释放出重要的信号,即这类小说家是与消费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存在,本质上就是巨大的消费生产体系的一部分。
四、余 论
“兴味派”构成了20世纪前半期文坛的半壁江山,小说话也是当时小说批评的重要一翼。二者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其身后的命运又是如此相似。“兴味派”文人长期面临着污名化的困境,以至于其追求“兴味”的文学宣言都被漠视、被置换;小说话这一批评样式则长期被遗忘,即使偶有人提起,也仅能见其只鳞片爪。小说话少人问津事实上更加重着“兴味派”的应有风采被堙没。这是现代学术规范嬗变中必然会出现的悲剧。
“兴味派”文人喜以话体批评来传达其批评理念与群体意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然面临“失语”的现象。受西方学术规范的影响,现代的学术体制确立以后,学者们渐渐摒弃以传统的话体批评形式来研究各类文学现象,科学严谨而富有逻辑性的专论开始成为主流的学术写作方式。对于话体批评,学界更关心的是其学术批评功能,对作为其根本特征的“闲谈”一直不够重视。这种倾向在话体批评研究领域,几有买椟还珠之嫌。正确认识话体批评的内涵与功能,对于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与文学流派,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具体到“兴味派”小说话,“闲谈”固然有着巨大的分量,其间的批评意味已不可低估。何况其中还有大量理论色彩浓郁的小说话,“或记作小说之程序,或评为小说之优劣”,⑦民哀:《小说丛话》,《小说新报》,1920年,第6卷第9期。都有加以整理与研究之必要。这些小说话都是“兴味派”理论声音的表达。借助于小说话,“兴味派”在中国文坛上的形象将由自己的声音所塑造,而不再仅以“他者”的形象存在于新文学的对立面。因此,小说话必然会成为了解“兴味派”的重要工具。随着小说话研究的不断深入,“兴味派”的真实面目也将逐渐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