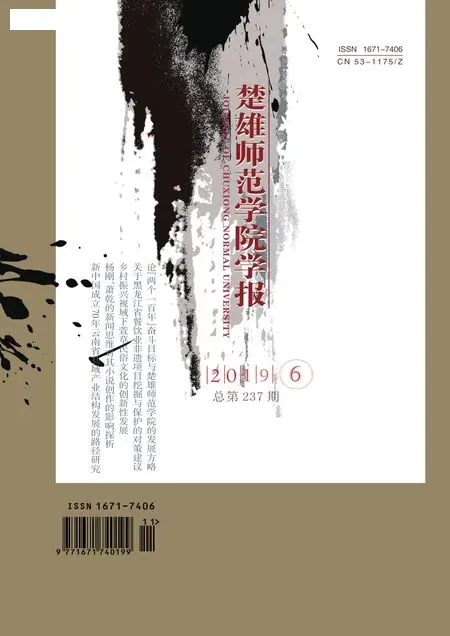《查姆》《梅葛》与《圣经·创世纪》中女性形象的对比研究
2019-03-23王玉芬
王玉芬
(楚雄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云南 楚雄675000)
《查姆》和《梅葛》是云南楚雄地区彝族的两部创世史诗,描述了彝族人类的创世神话及早期彝族先民的生产、生活;而《圣经·创世纪》是西方创世史诗,是希伯来圣经的第一卷,描述了天地万物、人类及罪恶的起源、以色列祖先的故事以及以色列民族与上帝的关系。
虽然《查姆》《梅葛》和《圣经·创世纪》分别属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但它们都反映了远古人类在同恶劣自然环境斗争中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再现了人类祖先的早期社会生活场景,是人类的“原始意象”或“原型”,蕴含着人类早期哲学宗教思想和伦理观念。《查姆》《梅葛》和《圣经·创世纪》中的创世神话、人类起源、洪水神话故事则是这些“原型”和早期哲学宗教思想及伦理观念的表征。史诗故事经过了人类漫长岁月的“过滤”后慢慢沉淀于彝族人民和希伯来民族的心灵深处,它们分别是彝族和希伯来民族共同的“心声”,也分别是彝族和希伯来民族共同记忆的体现。在《查姆》《梅葛》与《圣经·创世纪》史诗中,出现了许多女性人物形象。从这些女性在史诗中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体现来看,能窥见彝族原始先民和古希伯来先民的女性伦理观和哲学宗教观。目前,女性研究成为伦理学、宗教学和文学等研究的焦点,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对彝族史诗与《圣经·创世纪》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对比研究,能管窥两者不同的女性伦理观和哲学宗教观,有助于二者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同时,也有助于宣传民族特色文化,让民族文化变成世界文化的一分子。
一、《查姆》《梅葛》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哲学内涵
彝族史诗《查姆》和《梅葛》流传于楚雄的大姚、姚安和双柏等地,与云南弥勒的《阿细的先基》和四川凉山的《勒俄特依》合称为“彝族四大创世史诗”。它们记载了彝族先民对自然万物和人类起源的猜测与探索,反映了早期彝族先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及朴素的哲学观念。在《查姆》《梅葛》中,有大量的女性形象,她们代表着彝族先民的女性伦理思想及朴素的哲学宗教思想。《查姆》《梅葛》高度赞扬了女性在生产、生活及人类繁衍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赞扬了彝族女性的勤劳、勇敢、智慧,体现了彝族先民在母系氏族时期的“女神崇拜、生殖崇拜”思想,也折射出“阴阳相济”“贵柔守雌”的道家思想,这与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查姆》《梅葛》史诗中,天地万物由男神和女神在生产劳动中共同创造,神仙之王是男性,掌管着诸神和天地万物,体现了彝族古代先民“男主外、女主内,男女共同参与生产劳动的局面”。《查姆》史诗对男神、女神共同创造天地万物有如下描述:
“远古的时候,天地连成一片。下面没有地,上面没有天,分不出昼夜,分不出白天。涅浓倮佐颇,是所有神仙之王。他召集众神仙:仙王儒黄炸当地,水王罗塔纪,龙王罗阿玛,天王和帝王,还有他们的儿女。众神聚一起,共同来商议;要安排日月星辰,要铸就宇宙山川,要造天造地。……造人之神的女儿涅滨矮,设法造河川。……水王罗塔纪,是水中神仙。她用海水养鱼养虾。……龙王罗阿玛心最细,星星走动能听见,……罗阿玛呵,想得最周到,罗阿玛呵,想得最远”。[1](P233—243)
《查姆》史诗的上部描述了天地的起源、人类的诞生及其进化。水王罗塔纪、龙王罗阿玛、造人之神的女儿涅滨矮、龙王的姑娘赛依列、造人之神儿依得罗娃以及下凡帮助人类繁衍的仙姑撒赛歇,她们都是女神,是勤劳、智慧的化身,像男神一样积极参与天地万物的建造。从史诗对女神更细致、生动的描述中,我们可洞悉出史诗高度赞扬女性的勤劳、智慧及细腻的心思,透露出对女神的尊重和崇拜,反映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因对人口增长的渴求而产生对女性生殖能力的崇拜以及母系氏族时期女性的极高社会地位。除此之外,在男神、女神共同创造天地的过程中,当遇到困难的时候,神仙之王涅浓倮佐颇召集男女众神共同商量来解决困难:“涅浓倮佐颇,是所有神仙之王。他召集众神仙:仙王儒黄炸当地,水王罗塔纪,龙王罗阿玛,天王和帝王,还有他们的儿女。众神聚一起,共同来商议”。[1](P233—302)这样的描述在《查姆》的上部共出现过6次,充分体现了男女共同参与生产劳动和“男女平等”的思想。
《查姆》史诗的下部展现了人类生产劳动中勤劳、智慧的女性形象。第一个采桑养蚕的满五月姑娘、会缫蚕丝的列贵挨姑娘、峨阿拉姑娘、峨奇俐姑娘、峨佐作姑娘都是心灵手巧的彝家姑娘的代表:“列贵挨姑娘真能干,领头缫丝织绸缎。六个姑娘十二只手,织的绸缎数不完……漂洗绸缎没有水,六个姑娘找水源,她们走过八十个坝子,经过八十八座高山……六个姑娘来挑水……。[1](P303—359)除此之外,还有知道长生不老药的西说阿墨勒姑娘,她是敢于挑战权威的代表,任凭棍棒、恐吓也拒绝交出长生不老药给皇帝,而是交给了救母心切的牧羊人拉兵也欧。为了找回被月亮偷走的长生不老药,西说阿墨勒姑娘和拉兵也欧不幸为之献出生命。
《梅葛》史诗中的女神或女性形象主要展现在第一部《创世》篇中。其中,天神依然由男性角色格滋天神充当,他吩咐自己的儿子、姑娘来共同创造天地。“格滋天神要造天,他放下九个银果,变成九个儿子,九个儿子中,五个来造天……格滋天神要造地,他放下七个金果,变成七个姑娘,七个姑娘中,四个来造地。造天的五个儿子,胆子斗大,个个喜欢赌钱,个个喜欢玩闹,……赌着来造天,玩着来造天,睡着来造天,吃着来造天。造地的四个姑娘,心灵手又巧,个个喜欢干活,个个喜欢造地。……天造好了,地造好了,……天造小了,地造大了,天盖地呀盖不合。放三对麻蛇来缩地……天拉大了,地缩小了,这样合适啦,天地相合啦。天上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什么也没有,虎的各个部分做了天地万物。”[2](P3—14)《梅葛》史诗中,天地万物的创造依然由男女共同完成,但史诗赞扬了女性的勤劳善良,同时批评了男性的懒惰、贪玩和不负责任。无独有偶,远古彝族先民的观点和当代英国生态女性作家莱辛的观点一拍即合,她在《裂缝》中,就描写了女性的勤劳坚强,指责了男人的懒惰和随遇而安。田祥斌和张颂在《〈裂缝〉的象征意义与莱辛的女性主义意识》中指出:“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男女的栖息地,就能发现‘裂缝人’住在海边,靠山而居;‘怪物’面对山谷,依水而建。山是固定的,相对静止的;而水则有较大的流动性,是动态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影射到女人和男人身上,可以这样说:山决定了女人的坚强性格,有坚定的责任心和对于出生地无限的眷恋;水影响了男人的冒险精神,随遇而安的生活本领和不稳定的生活态度。”[3](P93)
《梅葛》的第二部《造物》描述了男耕女织诗意般的和谐生活:有放猪的女人、放羊的男人,男人犁地、女人撒种,这些都是古代彝族先民社会分工和生产、生活的写照,谱写了一曲男性女性和谐的生产、生活的诗歌。
《查姆》《梅葛》中生动、积极、正面的女神和女性形象也得到了其他彝族创世史诗的呼应。如流传于滇南元阳的《阿黑西尼摩》,楚雄彝族叙事史诗《三女找太阳》等。这些女性形象不仅丰富了史诗的内容,而且更多地传达了史诗对女性的高度赞扬,是彝族先民“女神崇拜”的表征。詹石窗认为,“女神崇拜的社会属性的形成是由母系氏族妇女的崇高地位所决定的”。[4](P8)在母系社会中,妇女在氏族内较高的社会地位使其成为祖灵崇拜的对象,成为原始宗教中女神崇拜的对象。张芮菱也持相似的观点:“因祖先崇拜而形成的女神崇拜,随着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与因生殖崇拜和土地崇拜而形成的女神崇拜不断融合,其宗教功能不断加强和扩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神话传说中的众多女神形象。”[5](P59)
二、《圣经·创世纪》中的女性形象
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在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根据上帝的意志来创造人类掌管天地万物,因此,西方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就被创造出来了。但是,亚当和夏娃不仅创造的顺序不同,而且所用材料也不同。上帝用尘土创造亚当后,害怕亚当孤独寂寞,所以就趁亚当熟睡时取出他身上的肋骨又创造出夏娃。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合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6](P2)
由上可知,西方的圣经研究者认为,上帝造人方式的不同是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社会性别关系,通过自然性别的差异表现了出来。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是供男人排遣寂寞之物。而男人、女人的社会角色在原罪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女人因受蛇的诱惑而违背上帝的话偷吃了禁果,并且给她的丈夫也吃了,此后男人和女人眼睛明亮起来,知道了害怕和羞耻。上帝勃然大怒,重罚了意志薄弱、容易受到诱惑的夏娃,同时惩罚了听信于女人的男人。上帝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上帝对男人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6](P3)上帝对女人的惩罚是非常严重的,她不仅要承受生育之苦,还要受到丈夫的管制,而且上帝同时也否定了女人的身体,每个月通过月经的方式来提醒女人犯下的原罪,让她知道自己身体的缺陷与不洁。而对男人的惩罚是必须劳动才能得到食物,并且剥夺了他长生不老的权利。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首次社会角色和社会分工,也是最初的“男强女弱”的男权性别伦理思想和“男尊女卑”及人的“二元论”思想的原迹。
《圣经》的研究者认为,整部《圣经》体现了极强的男权思想,是男性的《圣经》,而女性在《圣经》中处于“无声”的地位。美国学者菲利斯·特丽波说:“在父权制土地上出生成长的《圣经》充满男性形象与语言。”[7](P37)程小娟也认为“《圣经》产生于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背景,由男性写成,反映了男性的利益和思想。”[8](P17)李滟波则说:“《旧约圣经》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折射出父权制文化中男性作者贬低女性的倾向和对女性所持有的矛盾心理。”[9](P2)据《圣经》研究者的数据统计,《圣经》中出现的人物约为“1426人,约占《圣经》人物的95%,但仅有111人是女性。”[10](P10)在为数很少的被记载的女性人物中,负面的女性形象占据很大比例,除了犯下原罪的夏娃,还有帮助次子雅各欺骗以撒而让雅各得宠的利百加;偷走父亲神像的拉结;为金钱出卖力士参孙而让参孙丧命的大力拉等。她们都是《圣经》中负面女性形象的集中体现者。《圣经》中对女性地位的贬低,成了数千年来社会现实以及文学作品贬低女性的“原型”。女性只能借助男性的蒙恩才能生存,取悦男性成了女性生存的唯一途径,美貌的外表和曼妙的身姿是女性吸引男性的唯一资本。因此,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有许多“美丽非凡”但却“愚昧无知”的女性形象。综上所述,《圣经》折射出早期西方基督教“男尊女卑”及“二元论”的哲学思想。
三、《查姆》《梅葛》与《圣经·创世纪》中女性形象的对比分析
通过对楚雄彝族史诗中的女性形象与西方《圣经》中的女性形象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在楚雄彝族史诗中,无论是女神还是普通女性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她们不仅参与天地万物的创造,积极参与生产劳动,而且是勤劳、勇敢、智慧的化身;而在《圣经·创世纪》中,女性地位是被贬低的,不论是人类的始祖夏娃还是其他的女性,都处于“他者”的从属地位。西方女性主义作家伍尔夫生动地描述了女性的“他者”地位:“在大人物的传记里,我们常常看到她们一眼,可是又轻捷地躲到暗中去了”[11](P55)。因此,长此以往,“弱者”“祸水”就成为西方女性的代名词,女性被认为是男人灵魂救赎中的障碍。与《查姆》《梅葛》中积极、正面的女性形象相反,《圣经·创世纪》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是负面的、被否定的,这为西方贬低女性地位提供了依据,也是西方女性长期以来受“男尊女卑”的早期基督教伦理思想束缚的原因之一。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和阿奎那都有很强的“菲勒斯”情结,他们认为女人的身体结构是“发育不健全”的,由于身体的缺陷,女人的精神和人格也是病态的,生育才能让女人由病态变成健康的人。阿奎那认为:“就单个人的本性而言,女人是有缺陷的人和发育不健全的人。”[12](P92)刘文明在《早期基督教神学人类学中的男尊女卑观念》里进一步阐释了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观点:“人由于受造的物质不同而有男女之别,男人用尘土造成,女人则出自男人肋骨,受造目的是为了男人,因而她处于屈从地位;而且,女人肉体的卑微又导致了其理智的脆弱,使女性成为弱者。”[13](P70)除此之外,奥古斯丁认为,夏娃的存在意义附属于男性,是为了帮助男性繁衍后代而生存:“用取自这个男子的肋骨为他造了一个妻子,在生育子女的神圣工作中帮助他。”[14](P23)教父们对女性大加指责,莱基在其《欧洲道德史》中做了很好的概括:“女人被视为地狱之门和人类罪恶之本。她只要想到她是一个女人,她就应当感到有愧。她应当在不断地忏悔中生活,因为她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灾祸。她应当为她的服饰而羞愧,因为这是她堕落的象征。她尤其应当为她的美貌而内疚,因为这是魔鬼最有威力的武器。”[15](P42)总之,在长期的历史中,西方女性以被否定的负面形象出现,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在文学中,都被置于“他者”“边缘”和“无声”的地位,而《圣经》就是女性负面形象的来源和依据。
笔者认为,《查姆》《梅葛》对女性形象的解读与《圣经》截然不同,这反映了古代彝族人民和古代希伯来人民不同的哲学观念。《查姆》《梅葛》的形成年代是母系氏族时期,女性在生产、生活、人类繁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早期道家“阴阳相济”“贵柔守雌”思想理念的原型再现;而《圣经》中女性的负面形象是西方早期基督教神学、人类学“男尊女卑”与“二元论”思想的体现。
四、结语
通过对彝族史诗《查姆》《梅葛》与西方创世史诗《圣经·创世纪》中女性形象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查姆》《梅葛》蕴含着深刻的“男女平等”“女神崇拜、生殖崇拜”思想,同时也折射出“阴阳相济”“贵柔守雌”的道家思想。而《圣经》中女性的负面形象则是西方早期基督教神学、人类学“男尊女卑”与“二元论”思想的体现。形成于远古时期的楚雄彝族史诗《查姆》《梅葛》对自然、社会的认识有限,但却能蕴含深刻的道家思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虽然社会历史在变迁,人类也从原始的母系氏族时期过渡到21世纪,但“男女平等”“阴阳相济”“贵柔守雌”的思想一直是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的两性生存状态,所以说,《查姆》《梅葛》能为我们研究性别伦理学提供可资借鉴的观点。而早期基督教神学的“男尊女卑”和“二元论”可以在《圣经·创世纪》中寻到原迹,这也为我们重新解读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了解古代西方女性的生存境遇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最重要的是能加强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最后笔者认为,和谐的两性关系依然是当今社会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诸多领域研究的重点,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比研究彝族史诗《查姆》《梅葛》和《圣经·创世纪》中的女性形象,发现不同民族史诗中所蕴含的女性伦理思想及其哲学宗教思想,可以加深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能加强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