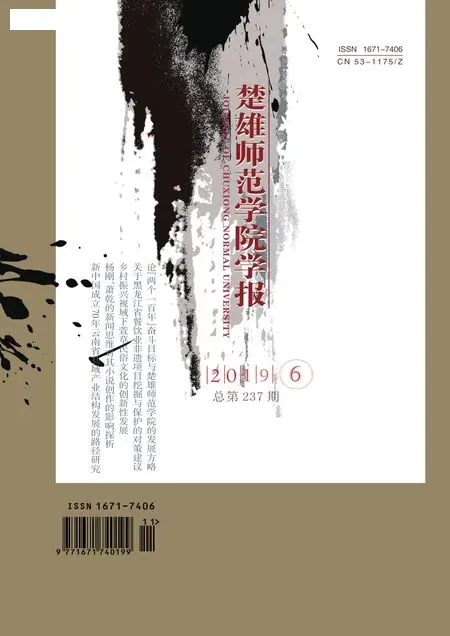非遗视域下西双版纳哈尼族服饰制作技艺传承研究
2019-03-23洛婕
洛 婕
(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党校,云南 景洪666100)
哈尼族是云南独有的15个少数民族之一,西双版纳哈尼族人口有209158人,全州共有3个哈尼族乡(景哈哈尼族乡、格朗和哈尼族乡、西定哈尼族布朗族乡),从行政区域上来看,景洪市、勐腊县、勐海县均有哈尼族分布。西双版纳两县一市的哈尼族服饰在款式、颜色等方面大体相似,但在刺绣花样、配饰样式等细节上又各具特点。总体而言,哈尼族服饰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凝聚了哈尼族的历史发展痕迹,展现了哈尼族社会生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多方面的信息。
目前,学术界专门对哈尼族服饰进行详细梳理和深入研究的文章较少,毛佑全先生是最早对这一领域进行挖掘的学者之一,他在20世纪90年代就发表过一系列对哈尼族服饰所蕴含的文化进行解剖的文章;王清华先生在其著作《梯田文化》中也探讨过哈尼族服饰中梯田文化的体现。除此之外,哈尼族简史编写组编撰的《哈尼族简史》、云南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撰的《哈尼族文化大观》、中央民族大学哈尼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哈尼族》中,都从不同角度对哈尼族服饰作了宏观的介绍。
一、哈尼族服饰的文化内涵与价值
(一)西双版纳哈尼族服饰的文化内涵
1.服饰图案题材
西双版纳哈尼族属于雅尼支系,自古以来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服饰作为一种视觉语言,承载着哈尼族的历史,一针一线的图案里诉说着哈尼族的民族文化。西双版纳哈尼族服饰图案的题材丰富多样,主要通过刺绣的方式,以线条为主,对各类题材主体进行抽象化的展现。不同的图案,或经过提炼、或经过夸张化,但背后都蕴涵着不同的寓意,共同组合成立体的、丰富的哈尼文化。在图案的题材内容上,大体可以分为植物、动物、生产工具及防御工具、建筑、民俗、吉祥寓意、历史故事几类。
植物:对植物图案的描绘属于哈尼族服饰图案刺绣中较为常见的一类,例如葫芦的图案。哈尼族神话传说中认为葫芦是开天辟地的生命摇篮,孕育了祖先,创造了大地,因此,葫芦作为哈尼族文化的标志性图案在刺绣中常有体现。除此之外,哈尼族日常饮食中比较喜爱的辣子,也会用简化的刺绣线条在服饰上体现出来。
动物:动物图案在哈尼族服饰中的展现并非完整的呈现出动物的体态,而是适当取舍,以生动的线条去勾勒动物身上的某个部分,例如对螃蟹的眼睛、老虎的脚印、蝉蛹等。此类图案背后,反映了哈尼族先民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状况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即有表现对动物的感恩之情,也有表现对部分动物的敬畏之心。
生产工具和防御工具:生产工具的图案是哈尼族服饰图案刺绣中一个重要的主题,阿卡人背篓上的背板、用葛根藤织的鱼笼、犁田的牛耙、砍伐木材的刀斧等,都在哈尼族服饰图案刺绣中有所反映;用来抵御毒蛇猛兽的篱笆、箭羽等保护哈尼族生命的防御性工具,也被常常绣在服饰上。
建筑:适用于哈尼族居住的房屋样式,被绣在服饰上作为“设计图”留存下来;另一类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图案,是寨门样式的刺绣。哈尼族村寨的寨门,在原始宗教信仰上被作为区分阴阳两界的标记而存在,是人鬼之间的明确生活区域界限,因此在刺绣图案上也有所反映。
民俗:模仿风车式样的图案刺绣叫作“旦练”,哈尼族认为把风车插在门寨上可以防止鬼神的打扰,因此被作为一种守护图案绣在服饰上。
吉祥寓意:哈尼族女性到出嫁适婚年龄时,会把定情信物放在红匣子里,结婚的时候要带红匣子出嫁。这一寓意美好爱情的物品也成了哈尼族服饰、绣包上的流行图案。
历史故事:哈尼族的历史,是一部关于迁徙的历史。为了铭记这部历史,哈尼族服饰刺绣中把象征蜿蜒之路的图案用“七针花”的形式表现出来,让子孙后代记住这条充满挫折的迁徙之路。
除上述几类图案外,还有代表人名的图案、代表开放包容各方文化的八角星图案、象征命运的满月/半月图案、山寨的炊烟等各类刺绣图案,均被用作哈尼族服饰图案的题材。
2 西双版纳哈尼族服饰的制作技艺
传统的哈尼族服饰制作程序可细分成四十二道,大概的程序分为:选地,砍树枝插地(显示已被人所占),除杂草,放火烧地,挖地,碎土,放火二次烧地,用棉花籽拌土(为了更均匀),撒棉花籽,摘棉花,晒棉花,滚筒压籽(留下棉花),弹棉花,搓棉花,绕线坨,固定线长,撒灰固线,煮线(增加线的韧性),织布,过滤火灰水配蓝靛配出染料,染布,缝制,刺绣。整个过程人工操作的程度很高,且耗时漫长,前期主要费时是布料的制作,仅棉花的栽种生长等过程就需要数月时间。
后期的耗时则主要体现在刺绣上,一块约3cm×3cm的图案,需要绣一整天才可以完成。传统的挑绣配线有固定的口诀:亢略(深绿线)、亢内(大红线)、亢瀑(白线)、亢配(深蓝线)、细内(橙线)、略勒(浅绿线)、亢裱(玫瑰线)、亢细(黄线)、亢尔(紫线),从头循环。只要记背口诀,按其顺序重复,就可绣出传统配色的挑绣图。
(二)西双版纳哈尼族服饰的价值
首先,哈尼族服饰承载着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哈尼族服饰从原料到样式,从图案内容到制作技艺,都折射出其经历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痕迹。如哈尼族服饰布料采用土布,既保暖又透气,适宜于常居山区的哈尼族生产生活;样式方面,女性裙摆长度均靠近膝盖附近而非拖地长裙,利于行动和劳作;另一方面,传统的哈尼族服饰在不同的性别、年龄阶段、活动场所、身份地位上都有着不同的款式区分,是识别着装人的年龄、社会地位的显著标志。又如前文所示,哈尼族服饰上的图案记录了哈尼族的传统风俗、传说、神话、信仰等丰富的内容,是一种重要的视觉图画资料。因此,哈尼族服饰承载着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其次,哈尼族服饰制作彰显了民族特点,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哈尼族服饰以黑色为主色调,在袖口、衣摆、裙摆、肩线等位置绣以各类图案,再搭配五彩缤纷的绒球、大大小小的珠子、形状各异的银饰,所有元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哈尼风格,对于民间传统工艺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审美意义和艺术价值。
最后,哈尼族服饰还是展现哈尼文化的一张生动名片,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哈尼族服饰展现了哈尼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是扩大哈尼族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生动名片,也是展示自身文化内涵的亮丽品牌,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二、哈尼族服饰制作技艺的传承现状
2013年6月8日,西双版纳州哈尼族服饰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时,在勐海县格朗和乡南糯山村委会成立了哈尼族服饰制作技艺传习所。哈尼族服饰制作的传承人基本上都是女性,对于哈尼族服饰制作技艺的传承现状,本文采取了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角度是以哈尼族服饰制作技艺传习所所长李金梅的访谈为主,即专业的官方角度;另一个角度则以勐腊县关累镇X村哈尼族妇女M的访谈为主,即民间制作哈尼族服饰者的角度。两个角度代表着哈尼服饰制作技艺在社会不同层面的两个缩影,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传承现状。
(一)李金梅女士访谈信息整理
李金梅女士是出生于勐海县格朗和乡的哈尼族妇女,1978年毕业于西双版纳州民族师范学校,同年参加工作。在工作期间历任教师、乡妇联主席、副乡长、副书记、县计生委主任、县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2008年10月退休。[1]李金梅女士长期深入村寨,访问老人、民间艺人,共收集不同款式、不同材质、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传统哈尼族服饰近300套,整理出32种传统图案的来历含义及制作传统刺绣图案的口诀,该口诀已译成汉语、英语。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李金梅女士发现许多优秀哈尼文化随着社会的变迁正面临着不可挽回的消失,为延续哈尼族传统刺绣文化,她于2009年起和西双版纳州职业技术学院一起举办了7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手工)哈尼族民间刺绣文化培训班。除此之外,她还到县级党校、村寨做专门的哈尼刺绣培训,总共培训学员约6000人,其中有2107人经过培训已取得国家颁发的手绣制作工的职业资格证书。为弘扬哈尼刺绣,李金梅女士积极参加各种展会、博览会、艺术节、比赛,通过电视台、报纸专题报道等渠道对其进行广泛宣传。
(二)村寨妇女M访谈信息整理
M是勐腊县关累镇土生土长的哈尼族妇女,13岁和母亲学习制作哈尼族服饰,至今已断断续续制作了30多年的哈尼族服饰,总数量约60件,主要用于满足家族成员的日常活动着装需求(为兄弟姐妹及其儿女每人准备2—3套)。M有两个姐妹,姐姐学过刺绣和制作服饰,但并不热衷,很早就不做服饰了;妹妹则是去城里读书工作,没有学过。M认为,自己制作哈尼服饰,是雨天无法割胶或停割期的一项消遣活动。除割胶、做饭、种菜、养鸡、照顾老人等农活和家庭事务之外,M没有过多的社交活动和爱好,就把休闲的时间用来制作服饰。对于传统哈尼服饰制作程序,M可以进行简单描述,但不能够清晰表达。而对于服饰图案上所蕴意的含义,M表示不了解,“只是看人家绣的好看的图案就去学,但并不知道具体有什么意思”。M学习不同刺绣图案的途径主要以观察身边人的新绣法为主,未参加过正规、专业的培训班。M对刺绣的进一步学习提升有着强烈的愿望,但因年纪渐长,视力减弱及腰椎出现问题,无法长时间伏案刺绣,近几年缝制频率已大幅减少。在谈到制作技艺的传承问题时,M表示,自己村寨及附近村寨的年轻一代群体里,很少有人会制作哈尼服饰,大部分人都外出打工或在城镇工作,对本民族服饰制作感兴趣的年轻人寥寥无几。
(三)哈尼族服饰制作技艺传承现状分析
从调研及访谈资料显示,哈尼族服饰制作技艺的传承现状不容乐观,存在短期内难以攻克的各类难题。
首先,生产效率低,实用性弱。传统哈尼族服饰制作以手工为主,虽然在原料的使用上已不再从耕地种棉花的程序开始,而是直接购买布料缝制,极大地缩减了时间,但刺绣耗时长,完成一件服饰制作仍需数月时间。服饰制作不仅耗时耗力,产品的价格与价值也并不匹配,难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在对李金梅女士的访谈中她提到,传习所会有手工订单,但能接的量很小,且无法短期内交货。速度慢,效率低,数量大的订单需求只能放弃;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哈尼族服饰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逐渐减弱。一是因社会的变迁,不少哈尼族从山区向城镇迁移,以前适宜于山区的厚重保暖型布料,在景洪等常年高温的坝区无法长时间穿戴;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服装市场里可供选择的服饰琳琅满目。哈尼族服饰相较于花样繁多的现代服饰而言款式较为单一,尚不能根据时代的需求而开发出更多样的款式。因此,哈尼族服饰的实用性在日常中的体现有所欠缺,传统哈尼村寨中老百姓的日常着装也几乎被现代服饰所取代,哈尼服饰目前仅用于节日、活动、文艺表演等特殊场合。
其次,市场意识淡薄,品牌打造欠缺。哈尼族村寨中能够制作服饰的人并不少,如M所在村寨,基本上同年龄段40—70岁的女性都掌握制作技艺,一家一户的世代相传,是哈尼族服饰的主要传承方式。但从调研访谈中显示,几乎大部分制作出来的服饰都是满足自家用或者馈赠亲友,仅有极少数的人会拿出少量外销。没有销售的意识和欲望,更不懂如何创建经营模式打开销售渠道,尚未能迎合市场需求,如此现状反过来又对哈尼服饰的生产和创新产生了制约,导致市场狭窄,同时缺乏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在西双版纳哈尼服饰制作群体中的佼佼者如李金梅女士,目前也尚未创建自己的品牌。一是大环境上哈尼族服饰制作世代的传承方式以家庭手工作坊为主,没有形成市场的气候;二是以哈尼刺绣为基础的一些延伸创新产品,如茶叶枕头、筷子袋、钱包、门窗门帘、坐垫、杯垫等都没有自己的品牌,因技术难度不高所以容易模仿,会出现同质化的问题。
最后,高层次人才匮乏,对文化内涵的挖掘不足。一是西双版纳制作哈尼族传统服饰的群体多为村寨妇女,学历水平普遍为小学或初中,整体偏低。虽然曾经有过一些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培训班,但培训时间短、培训内容丰富度不足、培训质量不高。目前仍有很多哈尼服饰制作者未接受过专业培训,主要依靠在村寨耳濡目染的自学,因此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质量上都与市场要求有所差距。二是对哈尼服饰背后蕴含的文化价值认识及深挖都存在不足。哈尼族服饰制作群体年龄普遍偏大,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且存在技艺传承断代的情况,致使其对哈尼服饰制作的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理解不够清晰,也缺乏对哈尼服饰文化深入挖掘的意识和能力。因此,缺乏既懂制作技艺、艺术理论基础,又对哈尼族历史文化、民族风俗有深入了解的高层次人才从事此行业。
三、对哈尼服饰制作技艺传承的思考
(一)批量生产与高端定制相结合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需求。哈尼族传统服饰的制作可按需求进行手工生产和机器生产,走出两条不同的路径。机器生产满足规模化的市场需求,手工生产走高端定制的路线。机器生产需要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做到能够初步满足市场需求,并在保留部分哈尼元素的基础上进行大量创新,以满足当代着装需求为主,向日常化方向改良。服饰的生活化、日常化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其生命力的持续程度。高端定制则立足于“非遗”这一落脚点,重点在于保留传统制作技艺、样式,以纯手工的形式制作,其成品并不是简单的一件“衣服”,而是融入了民族文化内涵的艺术品。在不计时间成本及原材料成本的前提下,高端定制可在手工打造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人的主导性和创造性,满足高品质的个性需求,体现机器无法取代的灵性及精致,增强文化附加值,在保存制作技艺与产业开发之间寻求良性互动。
(二)壮大经营主体,实施品牌战略
市场意识的增强需要政府的规划和引导,对哈尼服饰制作技艺的发展模式进行准确定位,给予税收、信贷方面的政策支持,帮助其融入市场。另外,可组建哈尼服饰行业协会及合作社,汇集各方力量,壮大经营主体,扩大融资渠道。并且引导其利用互联网、电子商务等先进手段开拓市场。在打造品牌方面,可充分利用非遗文化的优势,抓住民族性的特点建立本土文化品牌,树立品牌意识,向专业化和特色化方向发展。在品牌宣传方面,政府可提供官方宣传平台,以非遗传承、哈尼族历史文化等为宣传内容,通过展览会、艺术节、博览会、媒体报道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
(三)培育高层次人才队伍,彰显哈尼服饰的文化内涵
非遗的传承关键在人,目前已有李金梅女士创建的哈尼族服饰制作技艺传习所,拥有了基地优势,但具体的运作上,还需要扩充队伍。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努力调动群众参与其中的积极性,提供相关的政策补助,鼓励和支持开展传承培训工作和宣传活动尤为重要。从管理上,可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和意见,让非遗传承的保护、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培训上,可与当地教育机构加强合作,扩大培训群体,丰富培训内容,提升培训质量,并作为课程融入当地职业教育中,为培养非遗人才、推动产教融合提供更为完善的平台和环境。另一方面,应把哈尼族文化的当代发展融入哈尼服饰制作之中,进行创新理解。不仅让现代人能够从服饰中看到哈尼文化的过去,也要赋予其新的文化内涵和生命力,在哈尼服饰中讲好哈尼族过去与现在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