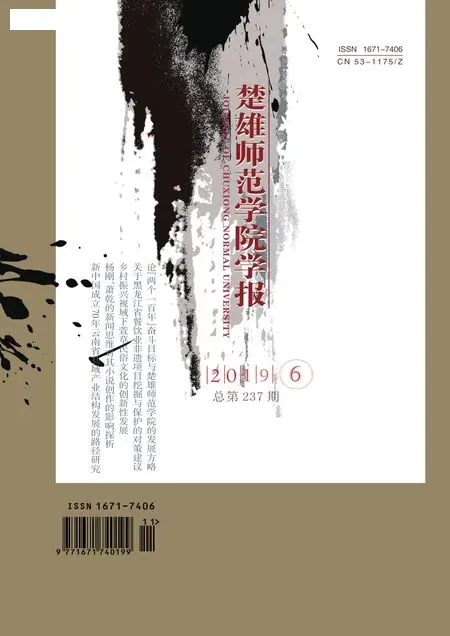杨刚、萧乾的新闻思维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探析
——以1933年至1951年间的作品为例
2019-03-23布小继梁雪梅
布小继,梁雪梅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云南 蒙自661199)
杨刚和萧乾自1929年冬天相识于燕京大学包贵思教授的家庭朗诵会开始,人生就有了交集。两人相互写信共同探讨文学、时事与人生,一起帮助埃德加·斯诺编选《活的中国》一书。1939年萧乾赴英国前夕,举荐并邀请杨刚赴香港接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1949年,向来以“未带地图的旅人”自居的萧乾,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在结束美国学习工作任务、回到国内的杨刚之劝说下,放弃了高薪的香港报人工作和在英国执教的机会,回到祖国成为一名共产党的干部。可见,文学与新闻是沟通两人关系的桥梁和纽带,他们相互影响、互相支持,交汇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使命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和新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铿锵有力的精彩篇章。
本文以1933年至1951年间两位作家创作活跃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为例,厘清新闻思维与文学思维的关联性和差异性,探析新闻思维对各自小说创作的影响。
一、杨刚、萧乾的新闻思维与文学思维的关联性与差异性
自1933年起,杨刚的不少文学作品就先后发表或出版,如Fragment from a Lost Diary(自译为《肉刑》在1935年4月15日的《国闻周报》上发表)被收入了埃德加·斯诺主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 (1933年),开始了她的创作活动。其文学作品主要表现了以下内容:
第一,女人的悲苦命运。如《肉刑》《爱香》《母难》《生长》《桓秀外传》和《黄霉村的故事》等。作家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女人的痛楚与无限的悲哀——她们天生就回避不了作为女人的宿命:结婚、产子、为夫愁、为子愁和要想摆脱各种羁绊又被命运死死钳住而无路可逃的痛苦。
第二,底层人物的悲惨生活和深受压迫、哭告无门的酸楚。如《殉》《翁媳》《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的自传》等。着力表现了底层人物苦苦挣扎的生存困境和反抗不成反而受到重重压迫的惨剧,包括作家自己奋斗、反抗的艰辛生活历程。
这些作品都是在个体生活实际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譬如《肉刑》,文洁若曾言:“现据杨刚女儿郑光迪回忆,这篇小说写的是她父亲郑侃的十弟郑佩及其妻司徒平的经历”,[1]其痛彻心扉的苦楚与无力感极其真实感人。
作为编辑,杨刚自工作伊始就开始了通讯特写类型的文章之创作。比如发表于《大众知识》一卷2—3期的《绥行日简》,就是一篇兼有游记和特写性质的长文,在朴实无华的叙事中展现出了作家对民生的关怀,对东北沦陷区的悲痛之情。她的代表性通讯特写集中在《东南行》中,该书共有12篇,是她1942年与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Wilsred Burchett)一起到浙赣前线和福建战区采访后写的,既有边走边看、观察记录的性质和“随手写”的特征,又有鲜明的不言败、不言弃的革命热忱,可以见出作家观察视角的敏锐和观察眼光的独到,自信与豪迈之情时常溢于言表。比如在记述了赣东的战事后,她放眼时局:“顿河两岸,莫斯科中原正在紧张,敌人似乎在期待着,我军似乎也是有所期待。飒飒秋风,为时不久。万木屏息,暴雨如何?”[2](P7)《美国札记》中的不少篇什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山川地理形势和民生的介绍、调查与评说。还有一些以记者身份进行的观察,如美国大选、小城镇和广大农村的日常生活状况,所写的风物志和评论既有客观的描述,也有从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出发所作的论说。
萧乾自1933年以小说《蚕》的发表崭露头角到1951年,创作《篱下集》《栗子》《小树叶》《梦之谷》和《珍珠米》等小说集多部。主要表达了如下内容:
第一,对家庭生活及苦难人群的“儿童化”书写。如《篱下》《矮檐》《落日》《俘虏》《放逐》《花子与老黄》《邓山东》等,以儿童眼光叙写了童年生活的乐趣和悲哀以及对人与人之间地位不平等的思考。
第二,对某种观念的诠释或传达。如《蚕》《邮票》《雨夕》《皈依》《昙》《道旁》以及旅居欧美期间所作的《珍珠米》 《堡》《法学博士》等,有对自己所接触到的宗教(基督教)观念及其传播的对抗,也有爱国抗日、反抗压迫的正义呼声,还有对欧美人生活态度之描述和价值观的评价。
第三,对个人情感世界的描摹和追忆。在《栗子》《梦之谷》等篇什中,或者以亲身体验为基础点染刻画,追述了自己年青时候的爱情体验;或者对生活感受进行夸张和变形,但其故事主线依然是“我”的亲身经历。
萧乾的小说创作有着一个“由虚向实”、不断转向的过程,1933年至1939年前创作高峰期间的大多数作品比较注重虚构,注意把握生活与文学之间的距离感,加工、提炼、升华的部分较多,这与其作为“京派”之重要一员有关。他曾说:“一九三五年我接手编《大公报·文艺》后,每个月必从天津来北京,到来今雨轩请一次茶会,由杨振声、沈从文二位主持。如果把与会者名单开列一下,每次三十到四十人,到(倒)真像个京派文人俱乐部。每次必到的有朱光潜、梁宗岱、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徽因及梁思成、巴金、靳以……还有冯至,他应也是京派的中坚”[3](P634)。作为后起之秀,萧乾在文学趣味(反都市)、文学书写(意境营造)和文学理念(美在生命)上与沈从文、杨振声等人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
自1939年《灰烬》(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和《见闻》(重庆烽火社)出版起,萧乾的创作重心转向明显。《南德的暮秋》(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初版。内收萧乾先后在香港《大公报》、重庆《大公报》上发表的报道欧洲战场战况的文章若干篇)、《人生采访》(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初版。以作家在欧洲、美国、南洋及国内多地的采访作品为主)等分量极重的新闻作品集,都打上了鲜明的新闻理念之烙印。《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我爱芒市》《剑桥书简》《暴风雨前的英国》《银风筝下的伦敦》等特写、通讯名篇,细节描写具体生动,环境刻画极有气魄,真情实感投入多,长于描绘地域风光、风俗人情。在文体、文类特点上与散文有很多重合之处,在思维方式上有极大的相通性。也就是说,这些几近于实绘实录性质的作品充满了纯正的“新闻味”。
和小说等文学作品比较,杨刚、萧乾的新闻作品有以下特征:
首先,求真求实,诉诸新闻的真实性。杨刚冒着枪林弹雨亲临现场进行实地采访,力求新闻作品能够诉诸真实与细节。杨刚赴赣西吉安实地采访时,写下了《请看敌人的新秩序》一文,其中的细节描写力求还原真实场景:“满街全是破门板、床板、窗栏、桌椅、破神柜等等,每一所房子除墙壁外,就只有破板断柱,里面乱堆着一些风车、簸箕、破柜子之类,大半是空虚无人”。[4]萧乾不顾生命危险报道欧洲战场,随英军几次横渡过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也曾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地区。在战地通讯中,凡涉及数据,都极力考证求真。在《银风筝下的伦敦》中介绍“难民善济金”的分配办法时写道:“一个四十以下的妇人如丧失丈夫,每周领十五个先令六便士。到她四十以后,周领二十二先令六便士。孩子的补助金:第一个领八先令六便士,第二个六先令三便士,余每名五先令。男子因空击残废者,住院期间每周二十五先令六便士,出院领三十三个先令。”[5](P303—304)显然,这些内容需要记者对数据进行艰苦细致的核实和一丝不苟的求证。
其次,饱含爱国心、正义感的社会责任观。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应该对社会和公众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在杨刚、萧乾有关战争的新闻作品中,饱含着鲜明的爱国心和正义感,站在民族、国家的角度,体现出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杨刚的东南战地采访中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情况,对战争灾民做了丰富翔实的报道。萧乾坚定地站在弱者一方,他认为:“新闻记者应尽力眼睛朝下……首先着重报道受灾情况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哪些中央或地方领导同志(名字一个不漏)立即前往慰问,然后才笼统地加上一句‘已作了妥善安置’”。[6]
再次,追求进步、正义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导向。杨刚主持下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红色文化”的宣传阵地。新中国建立后,她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期间,注重评论特别是国际评论的战斗性,在重大问题上发出了中国的声音。“二战”时期,萧乾的新闻通讯中无数次提及或引用外媒,对比中外战争宣传的差异,对宣传技巧和舆论攻势进行了有益的思考。
当然,也要看到,两人的区别也颇为明显:
杨刚的新闻创作主要集中在1942年以后,数量相对较少,其作品注重对老百姓痛苦体验的描写和期望摆脱痛苦的情态之描绘,对敌人侵略所造成的惨状之细腻刻画,就具体问题对政府建言,对异域文化、体制制度进行拷问和思考。结尾部分善于总结升华,或鼓舞民气,或发出号召,或寄望未来之改变;萧乾的新闻特写、通讯、印象记中,注重对老百姓在困境中所爆发出的伟力之歌颂,对异邦战事情况的细腻感受之描绘。结合亲身见闻勾勒出比较宏阔的场景,对国家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决策善于从多个信息来源予以佐证,对当地风俗文化也有不少描绘。条分缕析,既有纵向解剖世界大事之深度,也有横向铺陈迅疾发展的时势之广度。
再来看他们新闻思维和文学思维的关联性与差异性。
新闻思维是指人们用已感知的具体事实和抽象的理性事实,遵循一定的认识规律和认识程序对客观世界进行有意识的证实活动的反映过程。新闻思维是一种社会思维、证实思维、政治思维、大众思维。[7]“从宏观的层面看,‘文学思维’很简单,即文学活动中的思维过程……那么,文学思维最重要的形式何处可觅?我以为在文学思维过程的最后一环——符号达意阶段……当然,以文达意并非只是文学的专利,不少学科也须通过文字进行思维传达,但这些学科只是以此作为手段,惟有文学才将其视为终极目的。”[8]“文学思维(并不等同于文学作品)——或以富于艺术想象力的方式使用文化资源(当然包括文字)的思维——可能较自然而言在自我与现实之间起着更多的中介作用,它为人类维持着一个独特的世界,或可视为一个实在于历史之中或之上的世界,人类的文化传统、习俗甚至政治、经济活动等等都能体现它的存在。”[9]相较而言,新闻思维与文学思维在思维的指向性、目的性和价值评判尺度上都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
毋庸置疑,新闻与文学都来自于现实生活,具有借助文字传情达意、干预现实生活的共性,都以传播出去、影响受众为旨归。杨刚描写底层妇女大众饱受的生活苦难和制度性的压迫,萧乾通过儿童视角思考社会生活中的诸多不平等,抑或是表现自身经历的自传性小说文本,都和他们唤起受众对于真相的关注,回应和保障受众知情权的新闻作品一样,都要传达时代的呼声,为弱者和被压迫者呐喊、声援,彰显正义、昭示理想,赢得广大受众的认可。
杨刚和萧乾这一代新闻人,以小说家的身份介入新闻界,开始新闻创作。小说创作就成为了新闻创作的起点,新闻思维脱胎于文学思维。而随着新闻角色介入程度的加深,新闻人职业习惯的养成、职业素养的提升和职业语言风格的完善,这两种思维方式在他们身上的分野越来越明显。这也恰好代表了现代中国新闻人的思维演变历程。具体比较如下:
其一,新闻思维重程序、相对理性和规范化。受到新闻价值、报道范围、题材选择、写作思路、交稿方式、审批制度和见报(刊)条件等的限制,作者要把自己的观察、体会、理解以合乎程序的方式,按照规则书写和传达。文学思维则重感悟,灵活性强。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可以缘于某种初衷或电光火石般的瞬间灵感,顺着自身的意图去创作而不必顾虑行业、职业限制,自由度、开合度较大。
其二,新闻思维重特征化、类型化和求真求证。既要抓住表象,又要抓住规律;既要做正面的舆论引导,又要把见解适当地隐藏在新闻事实背后,人物刻画上讲究“写谁就是谁”,事件还原时要有强烈的现场感。新闻专业主义还要求记者对道听途说的信息要去伪存真,对文章的每一个字负责,不能虚构杜撰,更不能在涉及数据时不加以考证。文学思维则重个性化和思想性,人物刻画和形象塑造讲究“写谁谁都是”,情节描写和感情抒发沿着能够引起共鸣的思路去设计。容许和鼓励虚构、夸张等成分的存在,甚或对现实中的主人翁进入小说文本时加以适当的改写和夸饰,以凸显文学思维的主观性。
其三,新闻思维重作品的可读性和传播的及时性。新闻作品要回应受众关切,要有可读性才能吸引受众。要及时将信息传递给受众,报刊在市场环境中才有生存空间;而文学思维除了关注可读性外,还特别强调思想性和内容、技巧上的创新性。
杨刚、萧乾的新闻思维把文学中的灵动感性、讲究塑造技法和创新以及记者的严谨求实、逐新求异、重视特征化和类型化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他们新闻思维的特异之处。在战争期间,他们新闻的政治思维被无条件地放大且置于诸要素之首位。而其文学思维中通过对人性、人情、人生各个层面的书写以唤起受众的审美体验,激发对人类及生命个体美好境界的追求、向往等要义,也因为战争、革命等因素而在一定程度上异变成为进步、光明、独立、解放的工具性宣传,从而向新闻思维移位。
二、杨刚、萧乾的新闻思维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杨刚1931年即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又亲历过阎锡山的监狱考验和血与火的革命,彻底背叛了所属的阶级和家庭,对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和艰巨性有着明晰的认识和刻骨的体会。其作品中对家庭情、阶级仇、民族恨、妇女遭受的苦难和底层人物生存的困厄着力最多,表现力极强。在其职业生涯中,杨刚的新闻从业者身份与其“勇往直前、献身祖国”[10](P531)的革命家身份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新闻从业者身份是从事党的工作之掩护,党的工作可以借助这一身份得以更好地完成。换句话说,杨刚的文学创作之所以会以极大的热情去关注底层和弱者,既与她向下看、完成党的革命任务分不开——唤醒群众、展示痛苦、吁请支持,也与她的新闻从业者身份分不开——报告国内外最新的重大事项,提请民众需注意的事实和沟通各界信息。从中还可以发现素材,找到创作的契机。二者在其身上形成了一个客观的却又不能回避的悖论——新闻作品需要抓住特色、亮点和大众兴奋点进行写作,要以忠实于事物原样的方式进行叙述;同时,又要尽到告知的义务,情感表现、思想传达时常需要转换为一种被强行压抑的平静和无法尽情诉说的深沉。这在其写于1936年的《绥行日简》和前线访问的《东南行》一书中表现得比较鲜明。
杨刚的新闻思维与小说创作有一个冲突——碰撞——平衡的过程。杨刚的新闻思维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爱国情感的表达、爱国思想的传递、民族精神的张扬和对受难同胞的同情等思想主题表现上,并使其部分特写、通讯和散文在文体特征上有了重叠;另一方面是新闻创作叙事的即时性、客观性和平实性在小说中得到凸显,类似《肉刑》中的那种撕心裂肺般的痛楚、心理幻觉、错位叙述在《桓秀外传》《生长》《黄霉村的故事》和《挑战》等作品中被替换为顺叙、条理性、细节的清楚交代、追求故事完整性和巧合、误会的设计。其不断平衡的结果就是小说创作由比较浓烈的感性色彩而趋于理性,新闻思维对小说创作的影响逐步彰显,作品的规范化、真实性和可读性得到强化。
1996年,萧乾回忆:“一九三八年我写完《梦之谷》之后,就对自己做出结论:我不适于写长篇。从那以后,我写过些长篇报道,可再也没写出长篇或中篇小说了。至今,我对自己 当 时 所 做 的 决 定 从 未 后 悔 过。”[11](P394)在《〈一只受了伤的猎犬〉:证明我不能写小说》一文中他又说道:“写小说就得跳出回忆的圆圈,得把生活凭想象重新组合成一个完整体,得有活灵活现的人物,感人的情节。这篇东西证明我不能。首先我跳不出回忆的圆圈,不能使人物走出纸面。放在个人照相册里可以,作为摄影艺术作品则不可以,是败笔。所以,自那以后,我几乎未在尝试了。”[11](P402)萧乾的这一说法可以从两个方面看,第一、长篇小说往往需要宏大的结构、复杂的故事情节和众多的人物,既需要耗费时间去精心打磨,更需要作家把许多事件进行编织以切合表达需要;第二、早年萧乾以记者身份在外奔忙,无暇把自己所经历的诸多大事进行加工,独立思考的时间、空间受到限制。《梦之谷》就有着叙事平淡、人物刻画简单、满足于交代情节的特点。《一只受了伤的猎犬》情节单一,叙事与生活贴得太紧,平实得近于实录,显然也无法把其当作一篇有意味的小说作品来看待。
另外,萧乾对小说这一文体的理解与他的新闻思维密切相关。一方面,他以“京派”作家的身份积极投入到新闻工作中,历尽艰难险阻,留下了不少传世的特写和通讯,如《鲁西流民图》《刘粹刚之死》等。其中饱含着对祖国山河破碎、遭受强敌凌辱的愤慨,对同胞奋勇抗敌、保家卫国精神的赞赏;旅欧后又有《血红的九月》《银风筝下的伦敦》等诸多篇章,忠实地记录了英国面对强敌入侵时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和国民的精神风貌,极大地鼓舞了同为反法西斯战场主力的中国人民的斗志。另一方面,在错综复杂的战场形势面前,萧乾的小说创作思维已经新闻化,其对乡村文化价值的回味,对小说中浓郁抒情色彩和意境的营造已经被新闻作品的敏感性、即时反映性和客观性所取代。小说中的虚构变成特写中的真实,其在创作思维的层面上难以再次回到虚实结合、虚实相生的境界。散文由于其文体特征的相对宽泛性、包容性和文体边界的模糊性,能够把不少特写归入其中。可以说,高强度的采编工作、剧烈变化的战争态势使得萧乾的新闻思维固化,与小说创作二者间不能再取得平衡。
杨刚、萧乾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汉英双语小说作家。杨刚的英语作品Fragment from a Lost Diary以日记体的形式叙述了“我”怀孕的痛苦经历和悲催的生活。编选者认为“她生于湖北一个高贵门第,父亲是省政府要员。作者敢于运用社会题材来表现解放,这一定会使那些深信中国文艺家不能同过去决裂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人大吃一惊”[12],编选该文的宣传目的明显。遗作长篇小说《挑战》,从“六姊”品生预备进洋学堂——林德格伦学校叙述起,涉及其读书、与林宗元恋爱及参加革命的成长经历。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前者有着不少对细节的精心描述,心理描写丰富,借局部以窥整体的命意显豁;后者注重情节的推进及其与革命历史事件的关联,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使小说在获得了开阔的叙述视野之同时,失去了对挖掘人物内心的纵深感之控制。萧乾旅欧期间著译的《吐丝者》(Spinners of Silk)于1944年和1947年分别由英国艾伦—恩德出版社与瑞士布尔—弗拉格出版社出版,有《雨夕》《蚕》等12篇散文小说。“在眼前这本书里,萧乾正在一个短短的篇幅里进行写作实验。尽管有着战时中国的激荡,他能在情致上不反常态,表现出一个艺术家的高尚情操。他的标题小说蕴藏着无限激情,因为那正是他从中寻找鼓舞力量的极大勇气与同情”[13](P548),显然,萧乾前期的小说作品中所具有的艺术力量是超越国界与民族的。与How the TillersWin Back Their Land(《土地回老家》)比较,可以发现前者较好地保留了“京派”文学的审美特质,不少篇什在悲哀、亲切而富有诗意的语境中传达出了中国人人性中的种种善良、美好的精神特质;后者是萧乾于1950年11月以英文刊物《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记者的身份到湖南岳阳县筻口乡参加土改,通过黄友毅等人物、回龙乡等村庄的土改情况对外报道土改运动的过程和结果,文学性受到约束而极大地弱化。在该书的“附言”中,萧乾认为:“《土地回老家》的意图,是通过农村几个典型人物和几个典型事件,来说明土地改革的基本过程。它不是文艺作品,因为,在这里,创作必须服从报道,人物发展必须服从过程环节。它只是土地改革文件的一种例证。”[14](P223—224)可见,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萧乾的小说创作思维越发被新闻思维同化、固化甚至替代,难以再用文学语言来进行成功的长篇小说表达了。
三、余论
萧乾在谈到新闻写作与文艺写作的区别时说:“新闻特写,或叫报告文学,一般说来,比文艺创作要粗糙一些,外在的东西要多一些,要抓情节,抓人物的经历,不宜也来不及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最重要的区别还在于文艺创作允许虚构,也应该虚构,而特写绝不允许虚构。这一点五十年代就有争论。我认为新闻特写为了加强效果而搞虚假的东西是要不得的。”[15](P375)其实,新闻从业者与小说家同属于文字工作者,在信息传播、文化传承和思想引领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主要借助形象思维来达成上述目的,但也不能忽视以下区别所致的新闻思维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第一,对真实性的理解把握。新闻从业者的工作要求对外传播、沟通信息,个人风格必须得到约束,新闻的倾向性在事实的客观性中呈现出来,个人的主观意图只有在特写等新闻文体与文学文体交叉的地带才会有所体现,追求的真实具有绝对性和已然性。而小说创作具有内在性,作家对题材进行加工、提炼,使之与所要表达的思想观念相符,进而运用适当的技巧、方式完成创作;基于想象联想的小说创作思维变通性更强,其所追求的真实也是相对的艺术真实,对真实性的表达可以基于想象的内容或心里的感受,是可能的真实、个性的真实。新闻的真实性是社会生活现象的真实,是耳闻目睹的表象真实;小说的真实性是虚拟的真实,是基于客观的主观真实。杨刚从《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的自白》到小说《挑战》的变化,就是对真实性的理解与把握的逐步深入的过程。萧乾小说从《雨夕》到长篇报道《土地回老家》的变化是小说真实向新闻真实转变的过程。
第二,表现时代主题。小说创作的主题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抗战时期,新闻从业者与作家一样,要把救亡图存放在首位,宣扬正面典型、突出抗战精神,要以那些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为表现重点。新闻从业者重在发现、挖掘能够表现中国革命战争精神风貌的人物和事件,小说家则是重在宣扬自己所见到的、所能够表现的有利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物和事件。杨刚的小说作品较多地介入了现实,充满战斗力,即便是1942年后,依然为革命鼓与呼,而且观察变得更为深邃,这与其共产党员身份、个人的革命者气质分不开。《挑战》中历史事件叙述的方式又和其为欧美读者写作的对外宣传意图紧密关联。
总体来说,杨刚的新闻思维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与萧乾相比是有限的,萧乾由于新闻思维对小说创作的“侵扰”,使得《土地回老家》这样的土改作品只能囿于宣传而无法取得像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一样的成就,从此思维上的不平衡难于打破,以至于自认为与长篇小说创作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