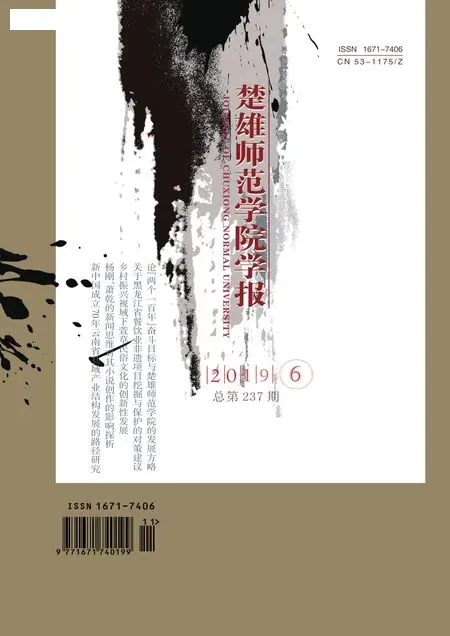情感就是视野与格调
——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中的情感教育
2019-03-23卢燕娟
卢燕娟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5)
相对于目前高校普遍推行的知识教育,德育教育则更接近于情感教育的范畴,情感教育是走向“德育树人”的必进之阶。就这一点而言,文学教育天然具有知识教育和情感教育的双重使命。首先,作为一级学科,文学学科和其他所有学科一样,有自己明确的知识框架和研究范式。大学文学学科教学,首先要完成这个使命,向文学专业的学生传递正确、完整的学科知识,并训练他们本学科的初步研究能力。但是,较之其他更纯粹于知识的学科,文学本身就是人类情感的艺术,天然携带着巨大的情感能量。好的文学作品,首先是能够表达人类美好高尚的情感,能在情感上引发广泛共鸣,能感染人、打动人的作品。文学经典的形成,本身就镌刻着人类在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中强大的情感记忆。因此,不仅传递知识,也要建构学生美好、高尚的情感结构,是大学文学教育的天然使命。因“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从属于文学一级学科,理所当然地承担着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的双重使命。具体到其情感教育的使命而言,这门课又有自身的特殊性。“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的内容,在时间上正好对应新中国的产生与建立。这门课所涉及的文学经典、文学事件,既是中国文学的一个进程,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进程,而且正好是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获得解放、建立新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这一段历史,是与我们的今天密切相关的历史,更是与我们的未来紧密联系的历史。因此,如何在教学中唤起学生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让学生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中理解一百年的苦难、辉煌,进而激发起他们面向未来的创造精神和担当意识,也是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中不能回避的重要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的宏观层面与教师课堂教学的具体层面,探讨自己对如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中进行情感教育的一点粗浅思考。
一、要立足于大时代、大叙事,培养学生的大视野、大格局
“情感”不同于“感情”,感情可以基于个人,情感则要基于更加宽泛的社会历史基础,“情感教育是关注人的情感层面如何再教育的影响下不断产生新质、走向新的高度”。[1](P4),情感教学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在文学教学中,容易唤起学生情感的,可以是作品中明确写出来的人物关系与命运,但更加重要的,其实是那些没有体现在字里行间、但却真正决定了作品在什么层面能够唤起读者共鸣的创作背景。在教学中,如果只看作品之内、不看作品之外,教学是不完整的。2016年12月7日,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强调: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2]。“大先生”的使命是塑造“大学生”,而培养“大学生”不仅要赋予相应的专业知识,更应该通过知识教育塑造学生的大视野、大格局、大灵魂。特别是现当代历史,其特点是大割裂、大苦难、大转折、大激宕、大变迁、大时代、大使命,这些决定了同期文学作品创作的根本基调与底色,那些站在创作高峰的作品,都是在这个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教学中不应割裂,而应该努力捏合,唤起学生的情怀。
在当前的教学中,上述环节比较缺位。国内一流高等院校倡导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多数采取“10年一个跨度”的范式,一整个恢弘磅礴的历史被割裂为晚清、五四(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延安时期、建国初期、“文革”时期、新时期等等。需要指出,这是研究视野,不是教学视野。即使从研究的角度,断代研究在阐释大脉络中的定位与功用时,也往往是不全面的;而把这个研究范式直接带进教学,一是不足以教给学生全面整体的历史观,二是给学生一种错觉,认为断代研究可以脱离整个大时代,无论是从知识普及、还是培养后继研究人才的角度,都有所欠缺。但目前这个不理想的现状,已经通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固化,其弊端也已经体现出来:在选拔研究生时,一是发现新学生的研究意识更局限于局部问题,脱离了大叙事,事实上是脱离了问题意识产生的土壤;二是不同“断代”的学生之间交流性降低,事实上是减少了学术碰撞带来新意的可能;三是学生普遍对“文学”这一人类瑰宝级行业日益缺乏投入度,归根结底,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并没有使学生产生内心激荡,只是单纯交给他们考点而已,不可不警醒。
我在教学中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对“十七年文学”感兴趣的同学,往往更能认同爱国主义、民族情怀这样一些比较宏大的情感,从这样的情感出发,他们往往更能被柳青、丁玲这样以文学投身民族解放、国家建设的作家怀抱着更多的认同与敬意。而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学更感兴趣的同学,往往更认同人道主义、人性解放这样一些比较个体的情感,从这样的情感出发,他们往往对坚持精神独立与个体尊严的作家体现出更多的认同与敬意。应该说,从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与现实国情来说,民族解放、建设祖国、追求更美好的社会,与人的觉醒、个体的独立自尊,都是内在于现代中国思想建设中的问题,缺一不可。但我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的问题,是这两部分同学往往很难从整体的、辩证的角度来理解、接受和判断这些作品,往往执其一端而攻其另一端。认同家国情怀的同学,往往不太容易理解新时期文学的合理性,将其视为“格局狭窄”或者“过于自恋”;而认同新时期文学的同学,又往往对“十七年文学”缺乏兴起,认为那是“假大空”或“僵硬刻板”。这就需要我们反思:文学说到底,是人类情感与灵魂的艺术。对文学的接受、理解,首先是与世界上各种人、各种生活——尤其是那些与我们现实经验相去较远、通过文学作品呈现出来的人与生活——的情感相呼应、相沟通、相共鸣的能力。只有这样的能力,才能帮助学生跳出狭隘逼仄的自身经验,获得更广博的胸怀、更开阔的视野。而缺乏情感教育,学生的知识很难升华为更加宽大的视野和格局,事实上也就无法转化成切实的能力,也就成为不了合格的“大学生”。
二、要发挥教师在情感教育中的主观、正面的推动作用
德国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第斯多惠曾说:“教师本人感情空虚,意志薄弱,这怎么能使人相信会教好学生呢?”[3](P170)教师在教学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只有教师从主观上认识到情感教育的不可或缺,才会去主动调整讲课策略,有意识地把情感教育的因素揉进去。
(一)从教学的技术环节讲,要善于“借风起火”
教师授课当然首先是传授知识,不是传授情感。但《荀子·劝学》云:“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借助外力可以更好地达到目的。苏联著名教育学家、心理学家赞可夫也说:“扎实地掌握知识,与其说是靠多次重复,不如说是靠理解、靠内部的诱因,靠学生的情绪状态达到的。”[4](P208)这就要求教师授课除了介绍知识,更要注意渲染课堂氛围和学生情绪。很多教师也注重这一点,善于从个人教学魅力出发很好地捕获学生的注意力。但情感教育有一个特点:人的心理更易于受大环境影响,中国现当代百年激荡的历史远比个人有魅力,为人师者善用此因素当事半功倍。
比如介绍郭沫若的历史剧,学生能够看到的只有文字形式的剧本,里面的修辞和用语带有很强的剧场特点,脱离剧场时就略显夸张。让学生单纯看剧本对把握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就难免偏颇。我在课堂教学中就多次遇到,学生自己预习相关内容后,表示不能理解为何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放置到如此经典的地位,也不能理解为何郭沫若历史剧在20世纪40年代能够引发那么热烈的反响,能够激动全国观众的心灵。针对这样的问题,我在教学中就做了一下调整:首先不介绍具体的剧作文本,而是讲述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故事。讲述现代中国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文化危机。给学生勾画出一个民族与文化俱危、风雨飘摇的时代画面。在这样的描述中,让学生首先跳出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理解一个较为整体的时代情感,去理解在这样的时代情感经验中,激烈、昂扬、悲壮、宏大的情感为什么会成为主流和基调。然后,再勾勒从晚清以来,现代话剧发生发展的简要历史线条,由此就可以把历史剧产生的时代特点,与五四时期的小剧场做个比较。在这样的比较中,不同时代主题的呼唤,就鲜明地体现在了作品的语言风格上。然后,再荡开一层,这个比较同样可以同样建立在郭沫若的白话诗与历史剧之间,可以看出同一个作家在回应不同时代主题时,其语言风格内在的延续性。更进一步会发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戏剧的比重并不重,从五四小剧场、到抗战历史剧、到延安秧歌剧、再到曹禺的两座高峰《雷雨》和《日出》分别收尾。这就给学生构建了一个“现代话剧在现代中国历史命运、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发展”的视野网络,而这个视野网络也就把学生们所未曾经历的历史情感带入课堂上,使学生能够从情感上去理解危机、压迫、反抗这样一些较为沉重悲壮的历史主题。这样的课程安排,不仅内容充实饱满、而且主题之间存在渐进关系、授课基调可自然而然转为高昂。
在完成了这样的知识视野与情感经验相交织的铺垫之后,再进入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的历史剧。学生就对那些他们一开始读来觉得过于夸张的情感,有了从时代特色和话剧艺术特色出发的双重理解。这个时候,教师在讲述的过程中,虽然不能还原一个话剧舞台现场,但也要尽量在自己的讲述中投入话剧的情感,使学生通过自己饱含情感的讲述,去感受屈原的悲愤、聂政的悲壮、信陵君的大智大勇。这里说的“饱含情感”,不是说教师要像话剧演员念台词那样在讲台上再现话剧,而是说,教师自己要首先能理解、进入这些话剧的情感经验,要能被其感染打动,然后把这份感染打动浸透在知识性的传授中传递给学生,让学生被作品和教师对作品的诠释打动。在基本做到了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会最后让学生现场朗诵历史剧段落。每每此时,朗诵的学生沉浸其中,情感丰沛到位,而作为听众的其他学生,也能被带入剧本所融入的历史情感中,被感染、被打动。在这样的课堂氛围中,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均能到位。更重要的是,学生通过一堂课就摸清现代戏剧的一整个脉络,比单独地分四个章节分别讲,效果要更好。一个有志于深入研究的学生,日后再遇到单独的主题,他已经有了整体视野做参考,有助于产生新的判断;即使是一般的学生,一堂课相当于走完了一段历史,爱国主义情感升华将比知识传授在他心中留下更深的印象。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情感教育本身也是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维度。
(二)要注意补足教材条件与情感教育所需之间的空白
当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更加注重解释流派、作品和文本,花了大量精力解释彼此之间的区别,并把这个区别嵌入到一套专业标准当中。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证客观,回避让学生形成某种“先入为主”的看法。但弊端是:教材在解释文学作品对时代重大问题回应时深度有限,学生确实没有“先入为主”,但往往也形不成任何看法。《文心雕龙》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5](P99)作家是生活在具体时代的人,他的情感不可能不受时代的影响。不理解作家的情感,直接切入作品难免片面,有些时候会非常片面。
以诗歌为例,主流教材介绍“信天游体”也会提及《王贵与李香香》,但这个作品现在来读离得太远,强求学生进入作品效果不会很好;而且除非来自陕北地区,否则学生对“信天游”的理解也不直观。单独依靠知识教学,教学将陷入“干巴巴”,这个时候不如浓墨重彩介绍李季。李季是被诗歌史忽略的重要诗人,曾经有《人民文学》主编和中国石油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的双重身份。李季与其他作家最重要的不同,是他的人生一直奋斗在实际生产劳动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赶赴玉门油田主持实际工作,是新中国石油行业的缔造者之一。李季不是单纯的文学创作者,而是真正的“文学为时代主题服务”的践行者。在延安时期后,“信天游体”的长诗事实上通过李季的创作一直在延续,并非销声匿迹,而且像《杨高传》的封面木刻画有极高的美术价值。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一改诗歌江河,而李季(当时已经是《人民文学》主编)则身着石油工人的朴素工装入殓,这之间的反差耐人寻味。学生也许不理解《王贵与李香香》,但不会不尊重李季这样一个纯粹的人。尊重一个值得尊敬的作家,就能最快地去理解一个作品流派的美学特点和历史意义,才能真正了解为什么茅盾会把“信天游”这种有浓厚地方色彩的长诗称之为“民族形式的史诗”。
再以“十七年文学”为例,“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广泛采取的是“多元化—一体化—再度多元化”的论述框架。用这个框架能让学生迅速、清晰地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有一个整体把握,但要全面解释新中国成立后这么长时期的文艺工作与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历史现实变迁之间的关系,这个框架的有效性会降低。特别是对“十七年文学”更是如此,甚至一些专业学生也会抱着“刻板、落后、全无可读性”这样的幼稚观点,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的失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与进步很快,让现在的学生从美学特征上去理解那个时期的文学确实有隔阂,而且当下时髦的文学理论也极少沿用“现实主义”标准(事实上也极少能达到这样的高度),这些都使学生难以获得理解这个时期文学的客观参照。因此从教学上,教师有责任给学生还原那个年代的普遍情感基调——事实上,如果有哪个时期的文学只能以情感为钥匙,那一定是“十七年文学”。不能理解那个年代新生中国的情感基因,就不能准确领会那个时期的文学是在怎样的标准下、达到了怎样的高度,才会留下因为不理解一个时代、而不能理解这个时代作品的学业遗憾。因此,尽管高校普通使用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出自北京大学,但该校中文教研室的老师在使用教材时,或多或少会对这个方面进行弥补,特别是对文学专业的学生教学,非但没有用“一体化”简单地处理“十七年文学”,反而高度强调“三红一创”、《青春之歌》这类宏大主题的时代作品对当代文学的创作意义。即使在“文革”之后,也没有一下子跨入伤痕文学,而是特别指出一个称为“五七作家群”的小流派(其特点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平反后依然保持着人生、社会、国家理想的创作风格),有的老师对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等作家的介绍,超过了后面那些耳熟能详、更加熟络、声誉也更隆的伤痕文学作家,抱着这样的情怀教学,对学生来说是极其负责任的。在面对这些有时代隔阂的命题时,情感教学比知识教学更加有效。
(三)要引导学生建立全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
在教学中,不仅要关注作品的题材、内容、人物、情节、寓意,更要注重从作品的风格、底色、格调与情怀出发,引导学生注意文艺史脉络出现了怎样的变化。事实上,一个时期的作品往往有共同的风格特征:五四时期总体偏向冷峻深沉,延安时期则是朴素刚健,“十七年文学”洋溢着乐观主义,伤痕文学记录一个时代的创伤,随后的市场化则开文学多元多样的众声喧哗……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进程,没有什么比这些风格变化更能直接体现社会思潮的更迭。这些现象不足以作为独立的学术研究主题,但在课堂教学中却能有效引导学生建立全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相反,如果教师不能带领学生“跳出此山”,反而会造成学生对其感兴趣的部分十分沉浸、对其不感兴趣的部分则一无所知,这对后继研究人才的素质形成很不利。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中,上述不利因素体现得非常明显,因为这个时期的文学史整体上情感资源比较匮乏。并不是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没有好的、重量级的作品出现,但少数几部重量级作品不能掩盖此后的作品风格越来越单一、格调越来越逼仄、整体上越来越远离情感呼唤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之后个体写作兴盛,一段时间内,社会上几乎把作家作为超越社会表象的存在,好像一个人的力量能够穿透历史一般。而作家为了迎合这个定位,也不断地在开放时代从国际优秀作品里汲取营养,比如说从欧洲的“存在主义”、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借鉴了荒诞、魔幻的写法,用来表达更深的命题。但是那个时期的作家几乎没有注意到“存在主义”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纠葛,更没有注意到拉美文学传统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事实上具有鲜明的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反抗的特征,只是单纯地“拿来”若干美学特征和技术手法。这就使得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的一线作家作品都以表达人性阴暗、历史荒诞为至高追求。虽然熟络、时髦的技巧确实给作品带来一定的可读性,但格调的逼仄却使文学创作丧失了对社会历史的回应。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文学,颠覆有余、再造不足,所取得的成就其实恰恰来自于他们所颠覆的传统,在此之后却不能依靠“拿来”、嫁接与拼凑形成一个新的文学传统,因此也就难以形成时代性的情感积淀。电影《芳华》恰好证明,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我们的文艺创作仍要从改革开放之前来汲取集体无意识层面的情感资源,这无疑折射出文艺创作被时代抛下之远;电影《三体》则证明,主流文学、严肃文学对当下中国社会群体的情感呼唤,竟远远落后于通俗文学。中国文学的现状是一个怪现象:一方面,学生崇拜着当下声誉愈隆的作家,但另一方面并不能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与时代的回应,他们的崇拜缺乏使命支撑,严肃文学却作为一个整体在时代中日益边缘、失语。“文学”正在将自己荒诞化,越来越缺乏有辨识度的公众形象。读者难以从文学作品中获得情感养料,专业人员难以从研究对象中获得情感养料,整个行业难以在社会公众中获得情感共鸣。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的情感特征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变化、该怎样识别,文学无力回答这个问题,最终沦为了这个时代的“屠龙之技”。
这些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上没有涉及,但又现实存在、正在演绎着的事情。而在高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中,如何在正确向学生传递知识的同时,帮助学生处理、回应这样的现实问题?如何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帮助学生获得健康、开阔甚至堪称高尚的情感格调?这是横亘在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中的大问题、真问题,也是极困难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我个人的教学实践中,也一直在苦苦寻求解决之道。迄今为止,我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进行初步尝试的有以下方式:
第一,把“格调”作为一种情感基调,引入不同时代的课堂教育中。每讲述一个时代,除了讲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所涉及的经典作家作品、重要文学事件之外,会在引导学生总结,这个时代的文学情感基调是什么。并且把这个问题一时放置在每一个作家作品的讲述中,让学生除了了解作家写了什么,更能够感受作家传递了什么样的情感?那个时代的人们从这个作品中获得了怎样的情感经验?由此理解一个时代的经典与一个时代的情感格调的关系。
第二,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将自己所置身的时代理解为漫长的现代中国历史中的一个环节,理解这个时代的情感诉求与时代格调的成因、现状。这样,学生不会天然地以自己所习惯的文学趣味去评价其他时代的作品,也不会无批判地认同一些当下流行的理论,而是会在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的整体把握中,去反思、去重构自己的价值立场和情感认同。当学生在这样的视野中重构了自己的情感结构,他们就会对自己时代的文学形成更理性也更有整体眼光的判断,而不会限在盲目崇拜与无从共鸣的困惑中。从我自己教学的实践经验来说,这样的补充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不向学生点透,不向学生突出那些不同的风格代表的不同意义、不同的情感体验,那“培养后继研究人才”终将成为一句空话。
三、结语
文学是直接触摸人类心灵的媒介,情感教育本来就是文学天然的伙伴。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其实都是情感教学的直接运用。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浇花浇根,育人育心。高校里的青年学生依然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只有给学生正确的情感体验方面的引导和培养,才能真正发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的内容,真正“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踏踏实实修好品德,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真正尽到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