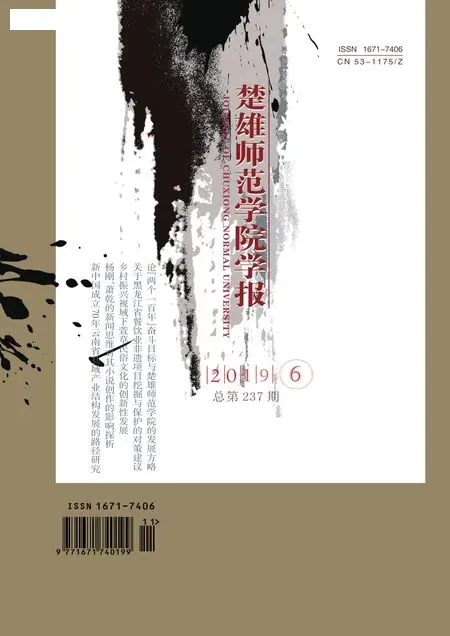纳西族农业民俗谫论
2019-03-23杨杰宏
杨杰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民以食为天”,古人又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这说明人类的文明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农业生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总结了一整套的经验及生产技术,与此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生产仪式,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很多民俗事项都是在农业生产民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纳西族东巴字的“幸福快乐”写成碗里有饭,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纳西族源于我国西北的古羌人,秦汉时期逐渐南迁,唐宋时期就定居于川西南、滇西北。[1](P49)这说明纳西族由大西北迁徙到大西南的过程中,由游牧民族变成了农耕民族,这些文化变迁在纳西族传统农业民俗中也有丰富的表现与反映。
一、纳西族传统农业生产民俗的发展概述
方国瑜先生认为,纳西族渊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带的古羌人,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向西南迁至雅砻江流域,又西迁至金沙江上游东西地带,古羌人以游牧为主,逐水草而居。秦汉时期,纳西族先民就已经分布在川西南的雅砻江、大渡河流域,一部分已经进入到了金沙江上游的丽江地区。方国瑜先生以为蜀汉时期的牦牛羌是磨些的先民,并作了说明,“髦即牦,以产牛著,与蜀地经济联系很密切,为蜀郡边境之部族。”[2](P3)
唐宋时期,纳西族处于“酋寨星列,不相统慑”的状态。从生产方式上看,唐朝时期一部分进入金沙江流域的纳西族先民开始向农耕经济转变,但相当部分的纳西族先民仍保留着传统的游牧方式。如唐朝时纳西先民中的一部分沿雅砻江南下,跨过金沙江,占据了今宾川地界,建立了越析诏。史称越析诏“地最广、兵最强,素为南诏忌”。越析诏后被南诏所灭,究其原因“在于以纳西先民‘磨些人’为代表的畜牧文化与南诏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纳西族先民‘磨些人’虽能凭借武力逞雄于一世,却对平地农耕生活缺乏适应性,难于在新占领的土地上长治久安。”[3](P8)
唐朝樊绰《蛮书》卷四记载:“磨些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明等川,皆其所居之地。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终身不洗手面,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饮酒歌舞,此等本姚州部落也。”据考证铁桥在今塔城乡,大婆、小婆在今华坪、永胜,昆明即今盐源县,三探览疑为永宁坝,又疑是三赕,探览三赕即今丽江坝,今藏语犹称丽江Samdo。[1](P109)说明那一时期,纳西族先民以游牧业为生,“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往返生活于上述广阔地区。
由于纳西族先民所居住的区域位于中央王朝、南诏(大理)和吐蕃三大势力之间,而内地、白族及藏族地区已经进入农耕社会,这不能不对纳西族的生产方式产生影响。同时,地理环境的改变,已经无法再从事大规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加上与周边民族的商品交换十分活跃,纳西先民拥有盐铁之利,生产工具的改进,促使纳西族先民由游牧经济转向农耕经济。
原始农业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刀耕火种,因这种耕作方式无需施肥,无需薅锄,花工少,仅靠原始简陋的生产工具就可连续种植农作物,成为古代人类获取谷物的最佳选择。这种生产方式在丽江纳西族地区保留了较长的时期,《光绪丽江府志稿》载:“丽江居万山中,玉龙凝阴,盛夏积雪,居民刀耕火种”。清代纳西族诗人杨品硕对此也有过详尽的描述:
刀 耕
高田陡峻不涂泥,两手扶叉脚踏犁。
胜似牛耕翻赤壤,晚耨秋获种春时。
火 种
块压松枝火有烟,铲平待雨种荞田。
先苦次甜继燕麦,收在三禾荒几年。
轮歇制是丽江纳西族耕作的重要方式,这主要是丽江气候严寒,施肥不足,地力不足所致。明末徐霞客到丽江考察时,对这种轮歇制作了记载:“其地田亩,三年种禾一番,本年种禾,次年即种豆菜之类,第三年则停而不种,必次年,乃复种禾。”[4](P938)
元朝时,丽江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后设丽江路,立军民总管府,阿良(木氏土司之先祖)为首任土司。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这一时期丽江的纳西族进入了封建领主制社会。这种封建领主制伴随着整个木氏土司在丽江的统治,从元初至清雍正元年,历470年,劳役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直到雍正元年改土归流后,丽江纳西族地区进入封建地主制的社会,土地买卖、租佃关系盛行,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成为主要剥削形式。当时虽有部分畜牧业作为家庭经济的补充,但农业经济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而永宁及盐源地区的纳西族因地理、历史原因,仍长时期停留在封建领主制社会中。
相对于以前的生产方式,改土归流后丽江的生产技术及经济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刘慰三《云南志略》卷三记载:“二牛挽于前,中压、后驱。平地种豆麦,山地种荞稗,弃地种蔓菁。”乾隆《丽江府志略》物产条目记载:“谷属:稻,红、白、黑三色分饭糯二种,惟沿江产之。粱有红、白二色产石鼓一带地方。菽有黄豆、菜豆、红豆、黑豆、豌豆、蚕豆六种。麦有大麦、小麦、大稞麦、燕麦、无芒麦五种。大麦造水酒味甚薄,大颗、无芒作馒首,煮蔓菁汤咽之,燕麦粉为干粮,水调充腹,此土人终岁之需也。小麦面非享客不轻用。黍有饭黍,糯黍。……荞有甜、苦二种,苦者较多,郡四山皆种之。稗有龙瓜、鸭瓜、铁杆、米稗数种,郡土所宜,高下皆收,里民合荞,麦恃以为生。……蔬属:蔓菁……宜抑生土,夏播冬收,户户晒干囤积,务足一岁之用,荞糕、稗粥外,饔飨必需。”这一时期,生产技术上引进了汉族地区的二牛抬杆犁田技术,并根据地方气候形成了一年两熟轮耕制,创造了间套耕种制,圈肥施肥、火烧土、利用排沟泥增肥、以黄豆根瘤菌固氮提高土地肥力等等。农作物种类也大有增加,大多为内地引进的新品种,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及新品种的引入,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根据光绪《丽江府志》记载:“自雍正元年改流起,至雍正十年,共清出成熟并报垦上中下三则田地一千三百一十八顷五十七亩,实征夏税秋粮麦折米一千五百二十六石九斗三升五合零。”到民国时期,在这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提升,据民国《丽江县志》载,全县务农人数52589人,农田120500亩,其农作物种植情况统计结果粗略分析,稻谷面积12000亩占栽种面积(下同)的9.5%,包谷37000亩占26.4%,豆类42800亩占30.5%,麦类48000亩占34.2%,棉花300亩占0.3%,复种指数为116.3%,由此表明麦类(小麦)、包谷、水稻为主要粮食作物,豆类作为培肥恢复地力所占比重也较大。[1](P499)从以上材料可看出,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丽江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种经济的增长又促进了商品交换的产生。由于丽江地处茶马古道及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道,客观上也极大地推动了丽江商品经济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滇缅通道被堵,丽江更是成为中印交通的重要枢纽,丽江工商业盛极一时。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还在丽江成立了“丽江工业合作事务所”,帮助和促进丽江手工业、家庭手工劳动向半机械手工工场进展,这一时期纳西族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刍型。
从“逐水草而居”到资本主义萌芽,纳西族的物质生产方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嬗变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应时之变。当然,这种嬗变是渐进的、曲折的,有时也会有重复,甚至倒退。但它一旦适应了特定的时代及环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后,就体现出相应的继承性与稳定性。
二、纳西族西部方言区的传统农业生产民俗
从语言属性上,纳西语分为东、西部两个方言区,原丽江县(现为古城区、玉龙县)基本上属于西部方言区,泸沽湖区域的纳人属于东部方言区。西部方言区较早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受汉文化影响较深,而东部方言区一直到1949年以前仍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受藏文化影响较大,从而呈现出同源异流的文化多样性特征。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中把纳西族西部方言区简称为西部纳西族,把纳西族东部方言区简称为东部纳西族。西部纳西族的生产习俗是在游牧向农耕过渡中逐渐形成的,并在近代发展为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形态。农作物以小麦、玉米、稻谷、豆类、洋芋、蔓菁等为主,在田间地头种些果木、蔬菜作为副业。农作物一年种两季,称小春、大春。种植时序分为耕、种、浇、锄、收、晒、打等七个工序。纳西族西部方言区的农业生产民俗主要有以下几类:
1 二牛抬杠
纳西族地区的山区,旱地犁田一般用黄牛,种水稻的地区以水牛为主,主要是因为犁耕水田费力大,只有水牛才能胜任。二牛抬杆是把一根木杠横架在并列的两条牛肩上,一人在前一手压杆以控制方向,另一手压犁架以控制犁地深浅,即“前挽、中压、后驱”;后一人把持犁尾。可以说,“二牛抬杠”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一般一天能犁田0.2~0 26公顷,耙地0.33公顷,这比人工犁田耙地提高了效率近十倍。
2 牛亲家
牛亲家,纳西话称为“ee leeq ga ddee ddee”,意为“耕地互助组”,是一种纳西族农业生产中的传统互助合作形式。以养牛户在自愿的基础上相互结成互助关系,有的是两家为主,有的多达十多家。有时结成的牛亲家不只是在犁地上互助,在春种秋收的农忙季节、婚丧嫁娶等事情上也互相帮助。牛亲家一般以村中的家族或以亲戚为主,有的以村中平时关系较好的家庭之间结成。如果各自家的田地犁完了,没有养牛的农户相请,牛亲家双方都要前往,这种情况有的算工钱,有的算换工时,即农忙时节到养牛户抵工时。
3 烧火土
烧火土,俗称“bee qi jjil”,是纳西族传统的一种增加土地肥力的农业技术。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在田地间先挖一尺深的坎沟,其间埋上松枝、松毛、灌木,上覆以细土,点火烧之,有两个好处:一是增加磷、钾类地肥;二是烧死地下害虫。第二种方式是在田边地头或家附近空闲地,先垒土堆,高约一米,中凹半米,填塞草木后,上覆带草的土块,以通气利燃。如果用量大,可以多烧几次,第二次是在此基础上增加土块,再塞草木燃烧,如此可反复多次。这种方式烧出来的火肥肥料较足,一般用在大春的稻田及玉米地里。
4 掏挖沟泥
掏挖沟泥,俗称“ke tel”(可透),“可”即河沟,“透”即掏挖。掏挖沟泥主要有两个好处:一是疏浚河道,便利灌溉;二是沟泥多为腐蚀土,撒到田间可增田地肥力。每三年轮流掏一次沟泥,掏沟泥时,先将水戽干,用椭圆扁平的特制掏泥木盆(俗称“锣坝”),将沟泥掷到岸边。有时河沟过深,一人之力难以胜任,就采取两人合作方式:一人将沟泥挖出后,轻抛到岸边人手中,再由其倒到沟岸边。掏挖沟泥是在冬季,因冬季天干物燥,利于晒干沟泥,同时也避免了雨季排水困难之忧。沟泥晒干后以锄头跺碎后撒到田间,是上好的肥料。当然,掏挖沟泥附带的还有捉鱼,等把水戽干了,里面就有鱼虾等着下手,尤其是泥鳅最多。
5 打粮
打粮,俗称“geel lee lal”,打粮工具称为“geel lee”,是一种连枷工具,即以一根短皮绳将两根木棍连在一起。甩连枷很讲究节奏及用力松弛力度,一般是先往一左一右各轻打两下,然后抬起左脚往中间重打一下,力求劲道匀实,以保证粒粒脱壳。打完头遍后,用连枷把作物翻过来再打一遍。打连枷是集体劳动项目,男女各站一边,两边间隔甩连枷,一起一落,节奏鲜明,宛若一首丰收进行曲。有时男女双方以歌和之,连枷声就成为配乐。
6 生产劳动歌
劳动歌产生于人们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它是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其作用是协调合作,活跃气氛,激发干劲,增进交流等。相比于传统大调,它的特点是节奏鲜明,旋律简单,易学易唱,群众参与性强,生活气息浓厚。其功能是振奋精神、愉悦身心、解除疲劳、统一节奏、传播知识等。纳西族的劳动歌有犁田歌、栽秧歌、薅秧歌、割麦歌、打稗子歌、背柴歌、盖新房歌、夯墙歌、赶马歌等。
(1)《栽秧歌》
《栽秧歌》纳西语叫“夕独热”“夕独”意为栽秧,“热”意为唱曲,源于祭祀谷神的东巴仪式,后演变为在农历五月栽秧时唱的劳动歌。栽秧劳动负荷重,属于集体劳动行为,唱栽秧调可以起到鼓舞干劲、协调劳作之功效。其形式为一人在田边领唱,众人在田间相和,也有的是即兴对唱。栽秧调要求唱腔婉转圆润,“增缀”应用恰到好处,内容活泼生动。丽江栽秧调大多为单声部唱法,也有领唱齐唱等形式。玉龙县塔城乡的栽秧歌为三拍子的男女声三部合唱,唱起来男女声交错,节奏错落起伏,气氛欢快热烈。歌词大意是:
五月栽秧天,
“热热”唱得欢;
待到秋收时,
金谷堆成山。
(2)《吆牛调》
《吆牛调》又称犁牛调,在纳西族地区广为流传,是在犁田时唱的调子。犁牛调有两种形式:一是在边远山区的单牛独耕时所唱,主要是支使耕牛所用的唱腔,在牛下田或转弯时,以喊调形式唱出对牛的命令,语气亲切,宛若与它谈话。二是二牛抬杆类型的,除了以上第一种形式保留外,在田间劳动的人们也可伴随犁田人相唱和。内容、曲调各异,主要是调节气氛、解除疲劳。
掌犁人用歌声喊牛转弯,牛听到歌声便调转头另犁一沟。同时还辅以其他唱词,其内容多为劝慰耕牛再辛苦一下,不要偷懒;对耕牛付出辛劳的赞美;自己劳动时的心情等。曲调长短乐句相互结合,长调以高亢悠长的音调为主,中间吆喝耕牛听话则以短句为主。主要歌词为:
哎哦哎,转回来了哟哦,乖乖转回来;
哎哦哎,折回去了哟哦,慢慢折回去;
哎哦哎,快要完了哟哦,不要泄气呀。
7 堆松毛
在纳西族居住的村寨可见到一堆堆的松毛堆,这些松毛堆由山上拉回的松毛堆积而成。每到冬季,纳西族妇女到山上拉松毛,一般是四五个人相约而行,路上以吟唱“谷气”“喂默达”相娱。拉松毛的工具是五齿耙,松毛拢成一堆后,用脚压实,在其四周箍上树枝,用晒玉米的粮架再以麻绳捆牢。堆松毛的地点是房前屋后,堆松毛时先垫实基础,然后再一层层垒高,下宽上窄,底座直径约一丈,高约一丈,松毛堆顶上有的压以石头,有的插一松枝。松毛主要用在点灶火,作牲畜睡觉所铺垫之物,也是积累圈肥的方法。
8 稻草人
丽江江边及拉市海北、七河、九河皆种水稻。水稻成熟时节,为防鸟类前来啄食,在田边竖上稻草人。稻草人做法简单,一个以木棍弄成十字架形状,在上面套上一些破旧衣服,上顶一帽子。也有的在田的四周拉上绳子,上系一些塑料布条,风一吹动,也可起到惊吓鸟类的作用。
9 粮架
粮架,俗称“gol”(过),用来晒粮。在纳西族农家院落里几乎家家都竖有粮架,其样式是在并排竖立的三至五根栗木柱之间横向贯穿五至七根木椽子。木柱之间相隔四五米,每根柱上都凿有圆孔,椽子之间相距半米多,农作物收回后要挂到粮架上晒一二个月。这种粮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通风、两面受阳的特点,有利于防止霉烂。
三、永宁地区纳日人的生产习俗
永宁纳西族支系摩梭人,自称为纳日,与西部方言区的纳西族为同源异流,其农业民俗既与西部纳西族有着共源性,也有其地方特色。
1 种植习俗
永宁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有稗子、稻谷、燕麦、包谷、小麦、荞子、洋芋、四季豆、黄豆等,经济作物主要有火麻、向日葵。蔬菜类主要有圆根蔓菁、南瓜、青菜、萝卜、白菜、莲花白、蒜、葱、辣子等。土地分水浇地、干地和园圃三类。水浇地和干地主要分布在坝子(盆地)中央和河流沟渠的两岸,水浇地多种稗子、稻谷、小麦、包谷。干地则种植燕麦、荞子或四季豆。园圃地一般都在住宅周围,种植麻和蔬菜,有的也种少许包谷和洋芋。在耕作技术方面,坝子的水浇地,采用轮种和休耕制度。纳日人把以河流或沟渠自然分隔成的一大块土地划分成三片,每年每个片分别种植稗子、燕麦和小麦三种作物。在同一片之内又以上述三种作物实行轮作,一般是第一年种稗子或稻谷,第二年种燕麦,第三年种小麦,第四年有的休耕,有的则再种小麦,第五年复又种稗子或稻谷,如此轮回播种。这种制度,已形成固定规律,不能任意改变,凡在轮作区有土地的人家,都必须遵守。
2 “依底”组织
在生产上,普遍存在以两三家组成的“依底”组织。“依”是牛,“底”是伙用,即伙用牛之意。在实际生活中,也有无牛户与有牛户合组的“依底”,这是农业生产中的一种互助组织。组成“依底”的双方,一般从犁地开始,一直互助到稗子收割完毕,在整个互助期间,不论对方有无耕牛,出工多少,一律不计报酬,也不还工。建立“依底”的双方,有的是亲戚、家门,有的则是“阿夏”关系,维持“依底”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三五年,有的十多年,除固定的“依底”组织外,在农忙时期,不少人还组织临时互助,但这种互助双方必须互还劳动日,有似换工性质。据郭大烈主编的《纳西族文化大观》载:纳日人每日投入农业生产的时间不长,且在家庭内,一般按性别、年龄进行自然分工。女子未满13岁前,牧放牲畜,青壮年承担主要农业生产,还要管理家庭生活等繁重家务,年老以后只管饲养猪、鸡和照顾小孩。男孩主要是牧放猪羊。青壮年从事农业生产和赶马经商以及为封建土司服役或当喇嘛,老年时以放牧大牲畜为主,在农业上做参谋。相当一部分男子脱离农业生产,妇女是农业生产上的主力。他们一般在早上9时半左右出工,中午1时至2时半休息,下午6时左右收工,全天劳动不过7小时。在一年之内,直接投入生产的劳动时间约6~7个月。[5](P212—218)
3 《打稗子歌》
历史上,稗子是永宁纳日人百姓的主要口粮,相传土司只允许百姓种稗子,不准种稻谷。打稗子是集体协作的劳动,秋收后晒好的稗子铺在打谷场上,村中男女分成两列相对,手持连枷一齐节奏鲜明地打稗子,连枷的响声与合唱的歌声相映成趣,气氛欢快热烈。歌中唱道:
连枷甩,甩连枷,
我们齐把稗子打;
你也打来我也打,
稗杆打成碎渣渣;
今年稗子长得好,
桩枷桩枷展劲甩。
下!下!下!
四、农业职官民俗
1 水官
在丽江、维西、中甸、宁蒗等地的纳西族地区,几乎每一个村寨都设有水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河堤安全,保证水道畅通,有效地分配有限的水资源,合理地调解各个用水户之间发生的冲突。在若干个村落共同使用一条河道时,各个村落的水官之间应作一定的协商,按上游到下游的顺序以及各村拥有土地的多少,决定用水之先后及多少。这些水官从村中公田,或是用水户那里收取一定的实物或现金作为报酬。
2 麦官
在永宁,小春作物主要是小麦,为了加强管理,专门设有两个麦官。如果有牲畜吃他人地中之麦苗,则由麦官对畜主进行惩罚。对初犯者罚一碗酒,再犯者罚一筒粮,连犯者罚一驮粮,被罚物品全部归麦官所有。为了感谢麦官的护麦之功,种麦农户一般要每年各送他两根猪肋骨、一碗酒、一个稗子饭团、两筒小麦,过年时还要另送一块猪膘肉、一碗酒、一块玉米糖、一块稗子糖。在丽江,不仅设麦官,还有苗官,其所辖范围更广。苗官之报酬与水官相同,其职能与永宁的麦官无异。[6](P166)
五、农业信仰民俗
1 麦神节
四月初八,被称为麦神节。此时丰收在望,人们在这一天祭祀麦神,祈求丰收。后来宗教色彩逐渐淡化,变成农忙前的休闲活动,参加者多为妇女。白天到城隍庙烧香拜佛,聚餐娱乐,夜间观看滇戏,新中国成立后此节逐渐冷落。
2 尝新节
尝新节是庆祝丰收,感谢自然神及谷神的节日,在稻谷成熟时的八月十五日前举行。尝新即品尝新米,农妇到还未收割的稻田中选出一些稻穗,以手工脱粒、去壳,炒干,蒸熟成米饭,再炒几样菜,邀请亲友邻里一起尝新。开饭前先给狗喂新米饭,以谢天狗从天庭盗回谷种之功。丽江一带在这一天有祭拜三朵之俗。
3 祭谷神
西部纳西族的祭谷神时间在秋收以后,第一次打粮时举行,参加者为家庭成员及帮助打粮的全体亲邻,已出嫁的女子也要于当天回到家中参加祭谷神仪式。行祭前,要由家主制一粮架,一板耙,一连枷,一爪耙,一棵用犁木制成的谷神树。打完粮、扬完场后,要将粮食堆于院子中央,其上插以粮架等祭器,男女主人各背一袋装得满满的粮食请谷神。请谷神仪式由东巴主持,先在陶盆中烧火除秽,火中放些许酥油、面粉、柏枝,其前供以甜酒、茶点。迎请谷神之后,将其接至里屋所设的仓房之中。男女主人将所背两袋粮亦放在仓中横台上,同时将耙、粮架、连枷等祭器均立于圆箕之中,陶盆也要放入台上继续烧除秽火。这时,由东巴诵《请谷神经》。诵毕,杀祭猪,并将猪头供于撒有青松毛的谷神树上,复请东巴诵《向谷神献食经》,举行祈祷仪式:从谷神树上折断一梢放入酒碗之中,参与者一起跪拜品尝。最后,将耙、粮架等祭器放入仓中,将谷神树送至门口的送别树处。
在永宁纳日人地区,祭谷神节一般在农历十一月举行。收割完毕后,各户主妇把所收各种谷物炒熟后撒在房屋内外。将糌粑面捏成谷堆形,与水果一起放在竹筛中,作为谷神的祭献放在粮仓旁边,祈求谷神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4 白沙农具节
白沙农具节,纳西语称为“崩石当美空扑”,即白沙大宝积宫开门。白沙大宝积宫供奉的是护法神——大黑天神,每年正月二十日开一次门,附近群众前来拜神烧香,后逐渐发展成为一年一度的集市节日。因开门日期正值春耕农忙前,集市交易物品多为农具,故又名“白沙农具节”。节日期间,人们进行耍狮舞龙、跳麒麟、喂默达等歌舞活动。
5 棒棒会
棒棒节因会期所卖物具多为作农具的棒棍而名,是从佛教节日“弥勒会”演化而来的民族节日,故又称为“弥勒芝”,“芝”即纳西语的“集市”。会期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也是西部纳西族地区盛大的农事准备活动,现已逐渐演变成花卉树木的交易大会,会期也从一天延长到三天。
丽江新婚夫妇有赶棒棒节的习俗,这一天二人要合买一根吹火筒,男的购买锄把、斧把;女的购买簸箕、箩筛等农具。新婚夫妇应合买一小把松明,一束韭菜,意喻新婚夫妇的日子犹如松明一样红红火火,粮食犹如韭菜割了一茬又生一茬,永远吃不完。
6 三月龙王会
又简称为“三月会”,为一年一度的物资交流会,由纳西族传统的祭署神仪式发展而来。西部纳西族地区在改土归流以前并无祭龙王习俗,民间以祭自然神——素神为主,祭自然神俗称“术库”,在农历三月三举行。祭自然神主要在山神树或水源地举行,以祈求署神保佑人类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改土归流后,受汉族龙文化影响,民间逐渐把祭署神流变为祭龙王,成为一年一度的庙会。后来规模扩大,民国初期把“三月龙王会”改为商业劝工会,新中国成立后又改称为三月物资交流会。
7 祭土地神
农历十一月三十日,是纳日人祭祀土地的节日,摩梭语称“底补”。届时全摩梭寨子以某一家为重点,请达巴念诵土地祭祀经。在念祭祀土地经文的同时,还要念祛虫除灾经,并邀请天地山神到场,祈求禁止一切旱涝雹洪虫等自然灾害,保护地里的庄稼茁壮成长,获得丰收。在达巴念诵土地祭祀经文的同时,要砍青枝绿叶置于田边地角,到处烧放烟火,以此来祭祀土地神。
六、余论
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大多基于农耕文明,纳西族的传统文化也是如此。虽然说纳西族源于西北河湟流域,系游牧民族古羌人之后裔,但经历了长期的民族迁徙与文化变迁,尤其是进入滇西北高原后,逐渐适应了这里的山地环境,从游牧经济形态变迁为畜牧与农耕兼容的农业经济形态,从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高原山地农业民俗。譬如为了节约耕地,选择住址时偏向于半山或山下不适耕种区;纳西族妇女平时穿戴的七星羊皮更多是为了适应高原气候及背重物的需要;丽江凉粉的出名与丽江特定的气候、土质密切相关;丽江马体型不大但耐力强,尤其适合在山地行远路,由此不仅是农家的重要运输工具,经济产品,而且成为茶马古道的主力军;纳西族的东巴教(永宁地区称为达巴教)及其仪式大多是为农业生产生活服务的,祭天、祭自然神、祭谷神、畜神、雷神、土地神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剧,农业民俗呈现出衰微趋势。但作为传统的构成,已经深深扎根于这方水土中,浸透了民众的心灵世界与精神空间,所以决定了其草根般顽强的生命力。如原来的棒棒节已经演变为花卉树木交易会,原来的畜牧节已经演变为国家法定的民族节日——三多节,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融合成为新节日的文化内涵,这也是新形势下农业民俗的新发展。从中可以看出,纳西族民俗体现出变迁性、继承性、创新性、包容性、多元性等特点。费孝通认为:“创造不能没有传统,没有传统就没有了生命的基础。传统也不能没有创造,因为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的,只有不断地创造才能赋予传统的生命。”[7](P329—331)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