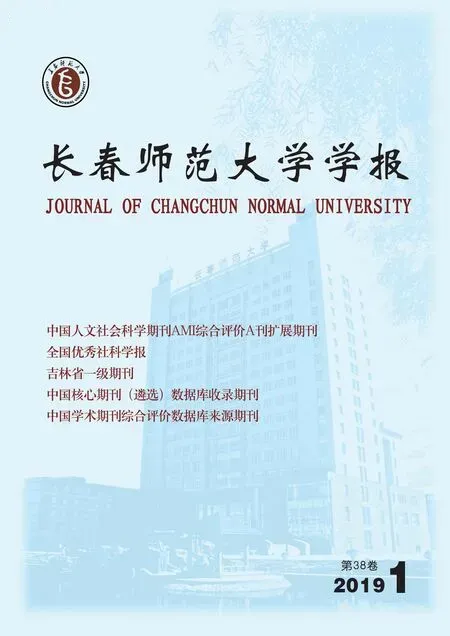试论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矛盾生命观
——基于莫尔特曼的生态神学视角
2019-03-22罗芬芬
罗芬芬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教师教育系,福建 漳州 363000)
生存还是死亡?我们是否有权利、有勇气决定别人和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是那些面对困境的人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更有勇者匈牙利的裴多菲说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壮志豪言。厄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一位曾经激励了无数人的伟大作家,在他面对疾病时竟然选择了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对这个举动的原因众说纷纭。对海明威的家族而言,他不是第一个选择轻生的,他的爷爷、爸爸和姐姐都以类似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海明威却厌恶他父亲的自杀行为,认为他是个懦夫,这点在他的作品《丧钟为谁而鸣》中可以找到一些端倪。这部作品是以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的带有自传体色彩的小说,主人公罗伯特的爸爸“用这支手枪自杀了”。罗伯特认为他的爸爸是个懦夫,然而他自己最终也是用来复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研究海明威的著名学者杨仁敬归纳了批评家的几种说法:基因论、顽疾说和精神忧郁论。杨仁敬认为:“主要是他百病缠身,无法再自由地从事创作。”[1]可是无论怎么说,他最终是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下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从激励人的作品《丧钟为谁而鸣》到厌恶父亲的轻生,再到最后海明威选择自己放弃了生命的权利,这中间如此大的落差和矛盾好像很难让人理解。本文试从生态神学的角度探讨海明威的作品《丧钟为谁而鸣》中所表现出的这些生命意识的矛盾性。
生态神学是一个神学运动,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德国著名神学家莫尔特曼。他重点从生态上帝观、宇宙论和人伦的角度探讨生态问题。他认为,一方面人是上帝的形象,在创造史中人类具有既代表创造物共同体又代表上帝的双重功能属性;另一方面人是灵肉统一的具体形象,人是灵与肉统一的具体形象,创造物的具象性是世界的核心和上帝的目的。人的上帝形象是人与上帝关系的显示。[2]这一点对于海明威来说并不陌生,所以他本能地尊重具有上帝形象的人,珍惜生命。
从《丧钟为谁而鸣》的文本中,我们可以从多处读到海明威珍惜生命、看重生命的价值的一面。然而,在文本中,我们同样会发现每一个人物心中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面对战争、杀人及自杀等现实,他们的内心往往出现扭曲。身处战争年代,海明威被战争的残暴剥夺了对生命的期待。本文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海明威作品《丧钟为谁而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态神学人论观,但由于现实的扭曲,海明威对待生命的态度具有矛盾性。
一、《丧钟为谁而鸣》中轻视生命之表现
在生态神学的人论中,上帝首先为自己创造了形象并进入与这一形象的特定关系,然后创造这一形象的人。人的本质就在于这一特殊的关系。自从人类扭曲了这一关系,世界就常常出现不和谐和混乱。生态神学理论告诉我们,罪进入这个世界,人类便偏离本来的状态,甚至迷失。罪人是上帝荣耀的扭曲,也就是人与上帝特殊关系的扭曲。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中的法西斯分子被罪恶的欲望所驱使,企图控制西班牙。无论是反对他们还是跟从他们的无辜的人们,都成为战争的受害者。其中,最为尖锐的矛盾在于杀人或自杀的伦理问题。
海明威明白生命宝贵、尊重生命,也厌恶父亲的自杀行为。但是,他无法回避他自己对杀人和自杀的观点。作品中的主人公罗伯特给出了一个简单而直截了当的回答:“把我的话听明白了。如果我有一天要请哪位帮点儿小忙的话,到那时候我会请求他的。”[3]24甚至在事关生死的一周之中,玛丽亚也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她的爸爸最好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命,只可惜她的爸爸“当时弄不到枪”。她听说罗伯特的爸爸自己结束自己生命时,为自己的父亲无法做到这一点而感到惋惜。他们的谈话中几次提到卡希金的死给人带来的焦虑。罗伯特对“聋子”说“他伤势太重,无法行动,所以我向他射击”。卡希金被认为是少有的神经质的人,“他老是说非得这么干不可,这恰是他摆脱不了的念头”。为避免当俘虏,玛丽亚一直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枪杀我,我也可以枪杀你或者自杀”。她一直随身携带“一张刮胡子用的单面刀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派上用场。战争中被俘虏不仅意味着失败,也意味着将面对任何可能的残暴虐待。这部小说发表于1940年。到了1955年,为了规范俘虏的行为,艾森豪威尔将军颁布了成文的《美国军人行为准则》,其中没有要求为避免被俘虏而主动自杀。自杀是否是最妥当的解决办法,各人的回答也许会不同。这反映了人类有一个认识:人的生命并不是最重要的,为了某个更重要的目标或是理想,可以放弃生命。这个目标或理想因人而异,有的可能是金钱,有的可能是美貌,有的可能是名誉,有的可能是爱情,有的可能是伟大的理想。每个人所认为的比生命更重要的事物不一定一样。莫尔特曼认为,对生命的热爱必然意味着对苦难的接受,对死亡、痛苦的排斥也不能达到不朽。
谈到敌方时,有时谈话变得冷酷而真挚。“罗伯特对他微笑,他呢,一手指着哨兵,用另一手的食指在自己脖子上划了一下。罗伯特·乔丹点点头,没有笑”。[3]39对安塞尔莫来说,他不想杀人。罗伯特毫不动摇地执行他的任务,“可是在必要的时候,我并不反对。尤其是为了我们的事业。”[3]42在战争中,事实就是如此:“要打胜仗,我们就必须杀敌人”。罗伯特不得不承认,他有时想要主动杀害人。他被巴勃罗激动的时候,好几次想要向他射击。罗伯特曾想:“我真想把他杀掉,一了百了啊”。罗伯特想让自己“像那些杀人成性的志愿兵一样,承认自己喜欢杀人好了”。[3]292他听完玛丽亚的故事,心中充满恨,并且“高兴的是明天就要杀人了”。[3]356在行动前,罗伯特教安塞尔莫“别把他们当人看,就当他们是枪靶子”。[3]408战争使人类成为上帝荣耀的扭曲,处于与上帝特殊关系的扭曲之中。
生态神学家认为,上帝最后创造了人,并且唯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所以生命是有尊严的,应当被尊重。人作为人的尊严是不可否认的,因为人与上帝的特殊关系纵然扭曲,可并未丧失。
二、《丧钟为谁而鸣》中珍视生命之表现
海明威明白生命的价值,并且尊重生命。因此,为了避免更多的死亡,他对反战做出了很大努力。在他的作品《丧钟为谁而鸣》中,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描写表达出他反战的情感。老人安塞尔莫,本不想伤害任何人。可陷于战争的困境,他目睹了人类一次又一次面对死亡,又在无可奈何的战争中要杀害生命。因此,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憧憬,想生活在和平的年代,“要是我还能继续活着,我要好好儿活着,任何人都不伤害,这样就能被人宽恕。”[3]44罗伯特勇敢地为共和国献身。跟其他战士一样,罗伯特也有他的家庭和他所爱的人。对一个在战场上的战士来说,有很多人在家中等待他回家。当罗伯特爱上玛丽亚之后,他也想活着回去,求生是人类的本能。玛丽亚的爱并没有动摇他的决心,但是“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影响他的决心,然而他巴不得活在人间。他宁愿放弃英雄或烈士的结局。”[3]170即使是在战争中,人类也有保护自己的生命愿望。
在作品《丧钟为谁而鸣》中,人们不仅意识到自己生命宝贵,甚至敌人的死亡也震撼他们的心灵。在比拉的镇上发生的暴乱中,她为她参与到对别人的迫害而有罪疚感。她想和别人“一起承担良心的谴责”,就像占领这个镇之后与大家分享战利品一样。安塞尔莫觉得杀一个像他自己一样的人一点也不好。他清楚地表态:“杀人就是罪过。我觉得害人一命可不是儿戏。必要的时候我才杀人,不过我和巴勃罗那号人不一样”。[3]44安塞尔莫喜欢打猎,而且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杀人与杀一头熊的区别的道德话题。“依我看,杀人是罪过。哪怕是杀那些我们必须要杀的法西斯。依我看,熊和人大不一样……”[3]44他认为杀人是有罪的,“可是开枪杀人使我觉得好像是在兄弟们长大成人后打自己的兄弟”,这与吉普赛人和摩尔人不同,他们认为杀死一个外族人不是犯罪。他说他要打死哨兵时,其实感到进退两难。“考虑到我们的任务,当然得杀,而且心安理得。不过心里是不高兴的”。[3]45在一场战争中,在不同阵营的人们成为敌人。如果没有什么冲突和任务的话,这些人可以把对方当作人类友好相待。战争将他们推向敌我双方。安塞尔莫深谙他与哨兵之间的最重要的不同:“我们之间只隔着一道命令”。就像比拉心中浮现的罪疚感,安塞尔莫也希望“等战争结束了,总得有些对杀人的行为好好苦行赎罪的办法”。[3]203如果没有赎罪,安塞尔莫的心中无法平息。没有什么事像杀戮这样让他感到羞耻。“在每个人的心中都驻守着一个心灵家园,当这个家园荒芜,杂草丛生的时候,就需要人们去污除杂重新拥有一个鸟语花香、景色和谐,沐浴在阳光之中的家园。”[4]这部作品中有两处提到了罗伯特的杀害行为。一个是他的朋友和同志卡希金,另一个是很可能已经发现他们营地的一名骑兵。读完了那名骑兵随身携带的信件后,罗伯特心想“在战争中,你杀的任何一个人总不是你想杀的人”。[3]306在他心中很自然地出现这样的想法:“你以为自己有杀人的权力吗?没有。可我不得不杀。你杀掉的人中间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有几个?很少。可是他们都是敌人,大家以武力相抗。”[3]307同样,敌方的贝仑多中尉在和“聋子”战斗之后也有空虚感,心想“砍头是残酷的。但是有个必要的手续是必须要验明证身。”[3]328
生态神学人论让我们看到,人是灵与肉的统一的具体形象。人并非是行尸走肉,心灵之中会产生良心的不安、罪疚感和空虚感。[5]这也反映出海明威对生命的珍视,生命在他的作品中是有价值的。
三、绝望与希望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海明威被战争所造成的混乱深深影响。《海明威短篇小说集》中的那些短篇小说反映了海明威的悲观情绪和虚无。因此,他被认为是现实主义作家。海明威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时代,他希望在这样的时代保持头脑的清醒,找到生活的秩序。[6]很可惜的是,他没有摸索到和谐的平衡。个人信念纵然坚定,残酷的战争剥夺了他理想中的盼望,使他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之下,他陷入绝望,放弃了生存的权利。
与之相比,莫尔特曼,这个二战中的战俘,却能够奇迹般地从战争的痛苦中存活下来。这两位伟大的人物之间的不同是在莫尔特曼的心中有高于生活的盼望。把他们放在一起对比发现,海明威更倾向于写生活本身。而莫尔特曼在盼望的支撑下建立了希望神学。盼望的动力来源于在安息中等待将来的荣耀。莫尔特曼认为,有身体和灵魂的人只能在安息中享受真实的平静。“在他那里健康被视作一种能力。生活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或者说如何选择生活。生态生存的追求其实就是对符合上帝创造信仰的生活方式的选择。”[7]
四、结语
总而言之,面对充满死亡的战争和无序,海明威失去了盼望,被他身处的环境引入迷惘。关于罗伯特和安塞尔莫对杀戮的矛盾心理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海明威矛盾的生命观。海明威珍视生命,最终却失去对生命的期待,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选择提醒我们“他们生活的历史受到他们对生命的期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