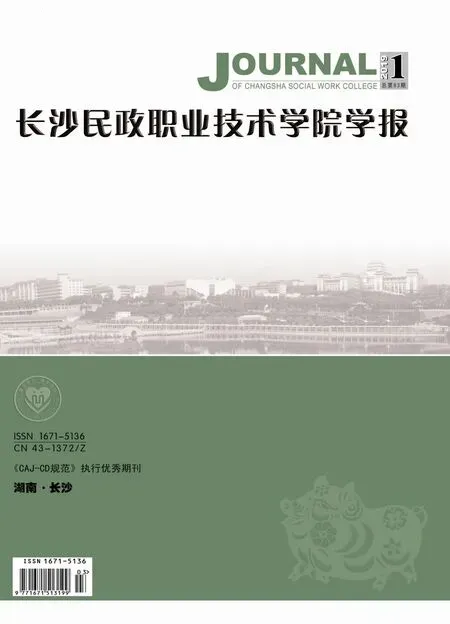文化翻译观视域下华莱士·史蒂文斯禅诗汉译技巧探析
——以《雪·人》为例
2019-03-21李玲琳
李玲琳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湖南长沙410211)
一、引言
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是美国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出生于宾夕法尼亚,自幼好静、超脱,热爱东方水墨画,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曾数次参观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钱兆明认为东方式的禅宗画给了史蒂文斯灵感,启发诗人塑造了蕴含禅宗意识的现代派诗歌,开创了美国诗歌一代新风。史蒂文斯的代表作有《六帧有趣的风景》(SixSignificant Landscapes,1916)、《十三个角度观黑鸟》(Thirteen Ways of Looking at a Black Bird,1917)、《雪 人》(The Snow Man,1921)、《胡恩广场饮茶》(Tea at the Palaz of Hoon,1921)、《西尾岛秩序感想》(The Idea of Order at Key West,1934)、《晴天、失去了记忆》(A Clear Day and No Memories,1955)等。
二、《雪·人》原文赏析
《雪·人》一诗,始于诗人观赏雪景,终于诗人领悟宇宙真理。诗人启发读者,投入全身心去真正地生活、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去认识世界、摈弃内心杂念,化自己为无,去认识宇宙真理。
此诗的音美有两个特点。其一,《雪·人》一诗通篇只有一个句子,由5个三行诗节构成,诗行为不规则四音步(varied tetrameter),诗人强调的内容不是通过音节(syllables)而是通过句法(syntax)来实现的。句法使全诗节奏流畅、对话效果极佳、为此诗提供了耐人寻味的魔力。在由五个诗节构成的句子中,史蒂文斯精心地把主语(不带个人色彩的“one”)、情态动词(暗示读者必须具备条件的“must”)、不定式短语(“to behold、to regard、not tothink”)及从句串在一起,带领读者脱离主观思想进入“冬天的心境”,体验冬天的景致、宇宙的真理。翻译时,音步大体相当、读起来顺口即可。其二,《雪·人》一诗虽然音步多变,但诗中押韵独具匠心,如尾韵(mind/regard/crusted/and/cold/behold/shagged/sound/wind/land),翻译时应在重点移植原诗文化的同时,尽量补偿原诗的音韵美。
此诗的形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整体感。《雪·人》全诗5节,每节3行,共15行。一眼看上去干净、工整、错落有致。第二,画面感。5个诗节呈现出5个不同的画面,独立却又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整体。诗歌一、二节好比一帧美丽的风景画。画面中,寒霜、松枝、刺柏、云杉,依次出现,由近及远,由详实变隐约。诗歌三、四节从视觉描写(sight)变为听觉描写(hearing)。诗人不再感悟、停下思考,景色被抽离,仅留风声、叶子声、大地声。诗歌第五节,本来隐隐绰绰的风景隐没不见,雪地里正在倾听的雪人和白茫茫大地合为一体,整个世界一片凛冽、静谧、虚无。第三,排比修辞。动词不定式短语的排比“To regard the frost and the boughs(第二行)/tobehold the junipers shagged with ice(第五行);介词短语的排比“Ofthe pine-trees crusted with snow;(第 3 行)/Of the January sun;and not to think(第7行)/Of any misery in the sound of the wind(第8行)。本诗的形美大半可仿译。
此诗的意美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不均匀、简素、枯高、自然、幽玄、脱俗和寂静。首先,诗歌有5节,一节有3行,全诗有15行。全诗仅有1个句子,主语为英语中的不定代词“人”(one)。诗歌形式上充分体现了禅宗对“奇数”的偏爱。其次,这首诗充分体现了禅宗的“简素”。诗歌简练、素雅、没有明亮的色彩,以简约的禅宗素描开头,禅宗素描结尾。其三,这首诗体现了禅宗美的“枯高”,即没有皮肉感官刺激。全诗只有松树、刺柏、云杉、风、雪、霜冻、冰凌、落叶、太阳等禅宗画常用的意象。诗歌标题中的“The SnowMan”就是禅宗画里不求真的人影。其四,这首诗体现了禅宗美的“自然”。全诗自然朴实。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出于本能:“银装素裹的松枝、冰花累累的刺柏、高高低低的云杉”。其五,这首诗体现了禅宗美的“幽玄”。诗歌的第4节第10行开始,诗歌由视觉模式切换成听觉模式,尤其是最后一节,隐含意义颇多。第六个特征“脱俗”同样充分体现在这首诗里。这首诗观察事物的角度独特。不仅观察雪人,还观察人、不仅感悟“雪人与自然合一”,还感悟“雪人、人、自然三者合一”。这首诗也诠释了禅宗美的“寂静”。诗的第3节和第4节“高高低低的云杉;/在风声中,树叶声中,/不去想任何痛苦/那是大地的声音/旋起同样的风/在同一荒野上呼啸”,表达出了禅宗山水画之幽静画面中永不停息的声音。《雪·人》一诗的意美体现在它用诗歌语言重构了东方禅宗美,大半可仿译。
三、《雪·人》汉译策略及汉译技巧举隅
首先,分析译入语文化来确定译文文体风格。这首诗写于1920年,彼时中国诗坛流行白话诗。因此,将史蒂文斯的《雪·人》译成白话诗较妥。另为了让年轻的当代读者通过诗歌译文的阅读,了解史蒂文斯所在国的风情、史蒂文斯诗歌中的文化背景,尤其是东方文化对诗人的影响,似以译成白话体为佳。从翻译目的来看,欲保留和移植史蒂文斯诗歌文本语言结构中的东方文化因子,译成白话体为佳。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首诗的语言风格朴实无华,明白易懂,译成白话体最佳。
其次,确定翻译策略。巴斯内特认为,文化因子不可翻译,只能移植或传递,译者可以根据语境灵活地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策略;译者在翻译中可和谐地、均衡地运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如语音翻译法、直译法、音步翻译法、以散文译诗法、韵律翻译法、素体诗翻译法、阐释法以取得整体效果;译者可以摆脱制约翻译惯例的限制,解放自己,通过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参与到意义的建构之中。本文作者根据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来汉译《雪·人》,以求最大程度地保留和移植《雪·人》原语作品的禅宗文化、再现原语作品的音美、形美及意美、实现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功能等值。具体的汉译技巧如下文所示。
标题:《雪·人》。首先,史蒂文斯的《雪·人》一诗,英文标题为 The SnowMan,“Snow”和“Man”由空格分隔开来,故不宜直译为《雪人》,因为“雪人”的英文是The Snowman。其次,从诗歌内容来看,此诗的主语是开篇的不定代词“人”(one),且诗中没有直接出现“雪人”的形象,诗中甚至没有提到“雪人”,故不宜直译成《雪人》。再次,诗歌主题为“要观赏冬天的雪景就要具备冬天的心境”,所以诗歌中的“雪”、“人”、表层意义上是独立的意象,深层意义上却有多重阐释的空间。诗歌第1至2节,人将悲喜之情投射到无情感知觉的“松枝、刺柏、云杉”上,使其具有与人同样的情感。第3至4节,诗歌意境从视觉形象逐步转为听觉意象,“聆听者”排除了情感、想象和知见(“不想任何痛苦”)。第5节,“聆听者”中止思维,全无自己,以物观物,最终达到开悟的境地,彻悟到鲜活的事物本身与虚无的融合,获得一种永恒的宁静,一种绝对的平衡。(“只有自己化为无,才能无所不见和见到根本之无。”)故将The SnowMan意译成《雪·人》最能移植原诗的禅意和参禅的三重境界。
第1行:人需有冬日的心境。原文为“One must have a mind ofwinter”。意译为“人需有冬日的心境”,文字简练、素雅,能最大程度移植原诗的“简素”,禅味较浓。
第2行:去凝视霜冻。原句为“To regard the frost and the boughs”,翻译时打破句子结构,把“To regard the frost”译为一行。 把“and the boughs”和第 3行中的“Of the pine-trees crusted with snow”译成一行。“regard”字典中有两重意思,分别是“把自己…视为,把自己…当成,把…变成”,和“注视,凝视”。结合上下文语境,“regard”译为“凝视”较佳。第一,“凝视”比“注视”更能呈现原诗的禅宗美“寂静”。第二,“regard”译成“凝视”能呼应第2节第5行的“behold”,呈现原诗的排比修辞美。(“Toregard the frost and the boughs(第1节第2行)/to behold the junipers shagged with ice(第 2节第5行)。
第3行:和银装素裹的松枝。原文为“Of the pine-trees crusted with snow;”。翻译时把第2行中的“and the boughs”和“Of the pine-trees crusted with snow”译成一行。此句中的“crusted”一词字典释义为“硬层,硬表面”,如直译太过于生硬,因此意译成“银装素裹的松枝”,以求最大程度移植原诗的“简素”、“枯高”和“自然”美。
第4行:在寒冷中长久。原文为“And have been cold a long time”,直译,即可传达原诗的“枯高”和“寂静”美。
第5行:凝视冰花累累的刺柏。原文为“Tobehold the junipers shagged with ice”。此句中的“shagged”一词字典释义为“疲惫不堪的,很累的”。此谓人将悲喜之情投射到本无情感知觉的刺柏上,认为挂满冰花的刺柏不堪负荷,疲惫不堪。比之直译,意译成“冰花累累的刺柏”更能传递原诗的意象美及移植原诗的“简素”和“自然美”。且原诗中“behold”和“shagged”两词尾音押韵,译成叠音词“累累”,有助于补偿不能传递原诗音韵美之不足。
第6-7行:和远处一月阳光下闪烁/高高低低的云杉。原文为“The spruces rough in the distant glitter/Of the Januarysun;and not to think”,翻译此句时需打破句子结构和语序,把“and not to think”和第8行的“Of any misery”译成一句方符合原诗上下文语境。此句中的“rough”一词,其它译者在翻译时都把它忽略不译。殊不知,它也是原诗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词。“rough”的字典释义为“粗糙的、不平滑的、高低不平的”,这三个中文词到底哪个更合适呢?从文化对等的角度来看,“高高低低”是三个词中最合适的。因为,“高高低低的云杉”最能移植原诗的“不均匀”美,即“不规则的美”,此乃禅宗美的七大特征之一。
第8-9行:在风声中,树叶声中,/不去想任何痛苦。原文为“and not tothink/Ofanymiseryin the sound of the wind,/In the sound ofa fewleaves,”英语中习惯把定语后置,中文则相反,故汉译时调整了句子语序,把介词短语“在风声中,树叶声中”放在前面,把“不去想任何痛苦”放在后面。“misery”的字典释义为“痛苦,悲惨,穷困,悲惨的生活。”将其译为“痛苦”禅味较浓。
第10行:那是大地的声音。原文为“Which is the sound ofthe land”。直译。
第11行:旋起同样的风。原文为“Full of the same wind”。根据上下文增译。
第12行:在同一荒野上呼啸。原文为“That is blowing in the same bare place”,句中的“blowing”字典释义为“吹、刮、哨子,乐器”等意思,将其译成“呼啸”能最大程度移植原诗的“幽玄美”,即一种仿佛来自无底深渊、萦回不息的声音。另从全诗的描写由具体至抽象,由近及远以及由小及大来推断,“bare place”一词所指比“land”一词所指大,它也是美国生态主义批评中的关键词,译为“地方”,其概念类似于“wilderness”,故将其译为“荒野”,以求传递原诗的“枯高美”。
第13行:雪中的聆听者。原文为“For the listener,who listens in the snow,”直译为“雪中的聆听者”,比原诗语言更简洁,力求传递禅诗的“简素美”。
第14行-15行:只有自己化为无,才能/无所不见和见到根本之无。原文为“And,nothing himself,beholds/Nothingthat is not there and the nothingthat is.”是诗中最关键也最难懂的两行。这一行的前半部分“(behold)Nothingthat is not there”,为双重否定,强调“看见那里的一切”。后半行里的“nothing”(the nothingthat is)意思更加隐讳。肖明翰认为诗人把定冠词“the”置于“nothing”前面,意在暗示读者它是指某种唯一而根本(与前一个nothing相对)的东西,比如最终真谛(the ultimate truth)。“the nothing”就是禅宗文化里的“无”,而前面的“一切”(Nothingthat is not there)就是‘有’。为追求文化对等,故将第14行和第15行译为“只有自己化为无,才能/无所不见和见到根本之无。”最大程度地再现了禅诗的“不均匀、简素、枯高、自然、脱俗、幽玄、寂静”的特点。至此为止,诗歌到达顶峰,诗人也借诗歌呈现了参禅的第三重境界。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史蒂文斯的《雪·人》一诗现代语言气息鲜明,形式干净工整,重构了东方禅宗美的“不均匀、简素、枯高、自然、幽玄、脱俗和寂静”。在汉译史蒂文斯的《雪·人》及其它诗歌时,译者应注意到史蒂文斯诗歌中的美学思想与东方禅宗美有契合之处,在翻译时保留和移植其诗歌文本语言结构中的东方文化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