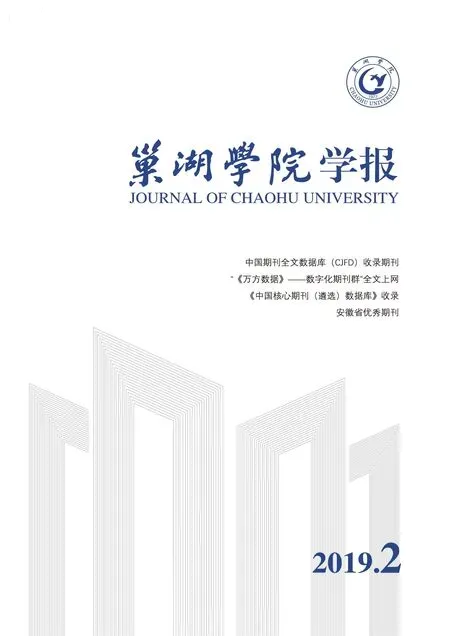《窦娥冤》与《哈姆雷特》叙事美学之比较
2019-03-21雷晶晶
雷晶晶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窦娥冤》与《哈姆雷特》是中西悲剧的两朵奇葩,分别代表着中西戏剧独特的艺术成就,一度成为学界研究中西悲剧差异的重点。前人从不同的视角探析了二者动人艺术魅力之所在。孔莉通过比较二者的叙述结构,提出中西悲剧的不同范式——“大团圆”与“一悲到底”[1];陈园关注了二者中的死亡叙事,提出中西哲学思想“主客对立”与“天人合一”影响下,东西方戏剧的冲突动态美和单纯静态美的不同特征[2];刘治国通过比较中西戏剧的道德叙事与精神追求,提出道德叙事模式下,《哈姆雷特》体现出对个体救赎与个人价值实现的重视,《窦娥冤》则表现出对集体意识和男权社会的认同[3];陈红玉就二者的“反权力中心观念”进行比较,认为《哈姆雷特》表现出个性与命运的冲突,是个人对权力的决裂;《窦娥冤》表现出道德伦理的自我分裂,是真与假、美与丑的伦理较量[4]。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西悲剧的不同内涵,以及中西不同的叙述风格,但就戏剧这一舞台综合艺术本体而言,尚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本文拟从时空意识、叙事结构、美学形态三个方面对《窦娥冤》与《哈姆雷特》进行比较,以期小中见大,对中西“悲剧”的内涵、叙事思维和美学精神等有更为具体、客观的认知和阐释。
一、时空意识之比较
戏剧是一种时间和空间高度集中的艺术形式,戏剧的剧情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进行展示。剧作家把无比丰富的社会生活浓缩成戏剧舞台上“有一定长度”的“微型画”,以引起观众激动。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大体相似,都是在一块数十平方米的特定空间内进行表演,演出时间通常不超过一天。但是,在如何利用有限的舞台时空方面,中西戏剧却有着明显的差别。
(一)时间意识之比较
戏曲《窦娥冤》四折一楔子,在楔子中通过蔡婆婆、窦天章、窦娥的先后出场,略述窦娥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十七岁成亲,十八岁守寡的不幸身世,戏曲以不同人物上下场时的空隙来省略事件时间,交代事件发展和人物处境,解决了在很短的演出时间里表现长时间跨度生活事件的矛盾,表现出戏曲“善于在时间的流程中展示家庭的兴衰变化和人物的命运”[5]的特点。第二折堂上含冤与第三折奔赴刑场同样通过幕间省略的方式,第三折结尾“(张驴儿做扣头科,云)谢青天老爷做主!明日杀了窦娥,才与小人的老子报的冤。(卜儿哭科,云)明日市曹中杀窦娥孩儿也,兀的不痛煞我也! ”[6]第四折开头,“(外扮监斩官上,云)下官监斩官是也。今日处决犯人,着做公的把住巷口,休放往来人闲走。”[6]通过人物的上下场,时间从张驴儿、蔡婆婆口中的“明日”转换到监斩官口中的“今日”。第四折时间转换同样如此。通过人物的上场与念白交代现时的故事时间。“(窦天章冠带引丑张千、祗从上,诗云)自离了我那瑞云孩儿,可早十六年光景。今日来到这淮南地面,不知这楚州为何三年不雨?”[6]在人物的语言动作中完成较大跨度的时间流转。独自陈情的念白使得演员与观众在外交流系统的互动中,剧中人与局外人的时间意识达成了一致。
除幕间省略,《窦娥冤》还采用场上省略的方法,“通过演员的演唱和程式化的表演将与剧情发展关系不是太大的时间跨度作大胆的省略,即所谓‘一个圆场百十里,一句慢板五更天’,通过演员数分钟乃至几秒钟的表演,让观众感觉到时过境迁。”[7]如第一折中蔡婆婆向赛卢医讨债遇歹,巧逢张驴儿父子搭救,却被其逼婚赖着蔡婆回家,通过窦娥的念白“婆婆索钱去了,怎生这早晚不见回来?”[6]便省略了从药铺外荒僻的所在步行回到楚州家里几个小时的时间跨度,使得演出时间远远小于事件时间。
另外,通过心灵瞬间的延展来表现舞台时间意识的主观性。在戏曲舞台上,不是时间制约着人物的行动和事件的发展,而是人物控制着事件时间或急或缓地律动、流逝,重在披露戏剧人物内在的情怀意绪。“在戏剧发展至高潮的时候,剧作家往往使事件发展速度减缓乃至暂停”[7],使人情委曲必尽,内在心灵的深刻揭示成为戏剧高潮精彩的演出。如《窦娥冤》第三折中,窦娥蒙冤临刑前怒不可遏的控诉,感天动地的悲怨,人物的心理活动在舞台上的展出逼停客观时间和事件的运动,舞台上的演出时间成为经过心灵改塑的心理时间,具有强烈的主观性。
而在以《哈姆雷特》为代表的西方悲剧中,剧作遵循“三一律”,即行动、时间、地点的一致,演出时间与剧情时间大致相等,戏剧严格受到客观时间的限制,相较于中国古典戏剧明显地呈现出客观性、物理性。“三一律”要求之下,剧作突出对冲突与矛盾的强调,使得叙事组织结构较为复杂,却也使得戏剧表现得更加真实可信。为保证演出时间与事件时间大体一致,戏剧往往利用幕间省略的方式省略客观时间。《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一场到第四场,时间由前一夜的“打过十二点钟”转换到第二夜的过十二点钟,老哈姆雷特的魂灵再次出现。虽然与客观时间不符,但密集的叙述内容(四场演出)已经削弱了观众的叙述时间意识,在印象中强化了戏剧故事时间的客观性。《哈姆雷特》时间的流转凭借空间的变化、不同人物的上场得以实现。场(幕)间省略突出了戏剧重点,人物行动线索更明晰,戏剧冲突更集中。
此外,也可以利用前情揭露的方式压缩戏剧表演时间。如《哈姆雷特》中隐含的另一条福丁布拉斯为父报仇的线索,通过第一幕第一场中霍拉旭与勃那多的对话,霍拉旭交代出福丁布拉斯的复仇背景,从而把老哈姆雷特生前的英武与老哈姆雷特死后丹麦国内戒备原因勾连起来。通过戏剧语言对其背景的勾勒,使得这一隐含的复仇行动首尾始备。但前情揭露的方式仍是在人物对话的客观时间中进行的,演出时间与叙述时间大致相等。
再者,通过模糊剧情时间,使观众不去关注人物活动所占用的剧情时间,以实现对“三一律”的忠实。如《哈姆雷特》第四幕中哈姆雷特在国王克劳狄斯的安排下,由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监视送至英国,只点明了人物的活动地点。而在第五幕开头,哈姆雷特便出现在丹麦王国的墓地、奥菲利娅的葬礼上,至于哈姆雷特在英国待了多久,回国途中经历了哪些事情,人物活动的时间剧作没有给予关注。
从以上比较中不难发现,《窦娥冤》与《哈姆雷特》的时间意识在戏剧演出上同样强调演出总时间集中于某一特定、具体的时间段内,而在处理方式上,带有中国古典戏剧鲜明特色的《窦娥冤》表现出鲜明的主观性、心理性,剧作家往往以省略或延展的方式把握剧情时间,重在表露戏剧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时间的缓急与否在于人心的感受,人的主观意绪超越了客观时间的限制,从而表现出戏剧中以人为中心的人的主体性与主动性。《哈姆雷特》的时间意识则表现出客观性、物理性,在“三一律”的影响下,剧情时间约等于事件时间,虽然剧作家也通过幕间省略、前情揭露和有意识地模糊时间等处理方式,最终目的乃是要使核心事件的时间与客观时间大致相似,从而产生真实的效果。客观时间限制着剧作家的剧情组织,同时却又成全着剧作以其“真实”震撼人心的审美功能。
(二)空间意识之比较
戏剧舞台的大小以人的视觉能力为依据,太大则失去美感,太小又无法展开表演。中西戏剧舞台空间相差不远,同是在十几至几十平不等的地面及其空间的特定场所中,但在处理方式上又存在明显差异。
在《窦娥冤》第一折中,蔡婆婆向山阳县南门外药铺的赛卢医家讨还本利二十两银子,蔡婆婆“(做行科,云)蓦过隅头,转过屋角,早来到他家门首。”[6]空间便实现了蔡婆婆家到赛卢医家的转换。赛卢医起歹心骗蔡婆婆到他的庄上去取钱,途中经过“东也无人,西也无人”[6]的野外,舞台空间背景并没有改变,而是再次通过演员的行科动作和道白语言实现空间转换的效果,表现出舞台空间的虚涵性。
《窦娥冤》中主要的三个空间,蔡婆婆家、楚州府衙和刑场,这三个现实逻辑中相距甚远的空间,其间转换依靠的是人物设置(如衙役、刽子手)、具有象征意味的物件摆设(如杀威棒、惊堂木)以及人物表演(行动、语言)来实现,并不大幅搭建舞台背景和改变舞台空间位置,体现出中国古典戏剧舞台空间的特征之一虚涵性。手扬马鞭即是马越关山,摇桨划拨便为舟涉险滩,在有限的空间内跑个圆场加上几段唱词便可看见大街小巷和衙门刑场,演员的表演成为达成空间转换的关键。
虚涵性的空间使得剧作家在创作时较少受到空间限制,境随人造的空间设置能够充分调动观众的想象力和审美力,并能节约演出成本。戏剧通过演员的唱词将客观外在空间与人物主观内在世界连接起来,二者相互感染,相互生发,使得客观空间的存在通过人的观照而具有了人的情感、思维和意志。空间的存在与转换为人物的情感和心境服务,实现了存在于空间而又超越空间的艺术效果。
相较于《窦娥冤》,《哈姆雷特》的空间则更为集中,人物活动和事件进行空间主要存在于艾尔西诺的城堡:老哈姆雷特魂灵多次出现于“城堡前的露台”;克劳狄思的密谋与刺探、哈姆雷特的装疯与其所设计的“戏中戏”、奥菲利娅的试探、克劳狄斯、雷欧提斯与哈姆雷特的死亡都发生在“城堡中的大厅”,增强了戏剧的冲突性。单一、固定是西方戏剧空间意识重要的特点。在一场或者一幕剧中,戏剧空间大多是固定不变的,空间的转换主要通过幕间转换来实现。空间是独立存在于剧情当中的,限制着剧情发展,与《窦娥冤》境随心造的空间意识体现出明显的差别,反映出剧作家为追求与现实生活逻辑一致而作出的努力,从而使戏剧表现出现实主义倾向。
在同样有限的舞台空间上,《窦娥冤》的空间意识表现出明显的虚涵性,境随心迁、境由心造的空间转换方式是对客观空间的一种主动的超越,相较于《哈姆雷特》中通过换场、换幕的方式来实现空间的转换有明显的主观性、情绪性。《哈姆雷特》中的空间具有单一、固定的特性,独立存在的空间始终让观众和舞台保持一定距离。舞台空间和剧情空间同一,其高下广狭是物理学、建筑学意义上的。戏剧舞台通过对现实的模拟,意欲达到“再现”生活场景的目的,进而促成戏剧作品对人物行动、事件运动的逼真叙述。
二、叙事结构之比较
戏剧结构是剧作家精心作出的艺术安排,戏剧结构不仅关联着外在的事件发展,同时关合着戏剧人物的情感起伏,牵涉着题旨思想走向,使事件、人物、主题成为完整自足的统一体。因此,戏剧结构不仅是一种客观上的事件组织,更是主观上的思想表达,是主客观相互交织,互融一体的艺术构思。叙事结构“意味深长地暗示出人对生活和宇宙的观照角度,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思维模式。”[8]叙事结构顺序之妙,在于它按照对世界的独特理解,重新安排了现实世界中的时空顺序,从而制造了叙事顺序和现实顺序的有意味的差异[9]。受各自文学传统的影响,中西戏剧在结构上差异比较明显,但依然有其相似所在,成为人类艺术追求的共同取向。
(一)线状与网状
受史学传统影响,中国戏剧单一线型叙述十分突出。清代曲论家李渔首次提出“结构第一”[10],认为“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10],要求突出中心人物和核心事件。“一人一事”,要能够贯穿始终,索要明白,“止为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而“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10]“一人一事”的艺术要求之下,中国古典戏剧多直叙式、开放式结构。
《窦娥冤》剧中主要人物有窦氏父女、蔡婆婆、张驴儿、赛卢医、桃杌六人,主要事件即窦娥含冤负屈被枉杀的悲惨遭遇。“一人一事”在《窦娥冤》中得到对照,“一人”即核心人物窦娥,“一事”即冤杀窦娥之事。剧情结构简单,采取线型叙述方式,事件完整自足,情节不枝不蔓,使观众产生洞悉戏剧始末的快感。
叙事的结构往往关联着事件的因果、情节的断续,它在以时间性牵连着空间性的时候,展示了描写对象的许多偶然性或必然性的情态[9]。为了便于空间转换和宏大时空的结构安排,在元代家庭剧中,往往楔子或第一折里家庭家族中的重要人物都要亮相,或者通过剧中人之口对家庭情况作以介绍,以便于以后的叙事空间的安排[11]。在《窦娥冤》中,通过楔子交代窦娥的丧母离父,与蔡家作童养媳的不幸身世,及其父窦天章赴京赶考的事实,既对剧中重要人物的基本情况作以概述,又为第四折窦天章的出场埋下伏笔;窦娥十八岁丧夫守寡的悲惨变故既是剧情发展需要,又是窦娥个体悲“冤”之强化;遇张驴儿父子逼婚、为浑蠢贪腐的桃杌县令拷打判斩是促成窦娥悲剧的单一、直接动因;刑场窦娥赌发三桩誓愿并一一应验既是人情发展的高潮,又预示着冤情终能昭雪的结局;第四折窦天章果然应举做官归来,为窦娥申冤,处奸恶罪罚,人之意感应通天终消除天灾,表明剧作家对人间及天地宇宙的认知和理解。人生与宇宙有着某种精神上的一致性,并通过自然界的沟通显现出宇宙人生的一体性。六月飞雪、三年大旱反常的自然征兆与窦娥蒙冤受屈、人间混乱的悲惨世相相契合,以技巧性的结构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性结构,技巧性结构成为哲理性结构的表征,哲理性结构反过来统摄、深化技巧性结构,二者互为表里,使得剧作家将生存体验和思想哲学融入叙述结构当中,进而形成技与道、天与人的双构同一性思维。
西方戏剧在“三一律”的影响下,剧作家被要求在极有限的时空内,再现矛盾集中的生活万状,便不得不使头绪纷繁的剧情在精心构造和压缩下,呈现出互相勾连的网状结构。
《哈姆雷特》从一开始便充斥着重重疑云,哈姆雷特从威登堡归来参加老国王老哈姆雷特的葬礼、新国王克劳狄斯的加冕礼和新国王与自己母亲(原丹麦王后乔特鲁德)的婚礼,一时间,悬念的设置牵引出观众心中的诸多疑问:原国王老哈姆雷特死亡真相是什么,为何其灵魂多次出现却欲言又止;克劳狄斯为什么取代名正言顺的哈姆雷特继承王位成为新国王;乔特鲁德为何会答应嫁给其丈夫的弟弟;伴随着老哈姆雷特的死亡真相浮出水面,哈姆雷特的复仇行动也渐渐明晰,与此同时福丁布拉斯为父复仇的暗线也在霍拉旭的对白中隐隐埋藏;哈姆雷特出于自保和刺探老哈姆雷特死亡真相而装疯、设计“戏中戏”,误杀恋人奥菲利娅的父亲、御前大臣波洛涅斯,引起波洛涅斯之子雷欧提斯的复仇行动。三条复仇线索明暗交织,矛盾网罗密布,形成互相作用的有机体。在克劳狄斯借刀杀人的密谋之下,哈姆雷特、雷欧提斯、克劳狄斯、乔特鲁德在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的决斗中都死于城堡的厅堂里,戏剧由此在高潮中落幕,戏剧冲突也就此得以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奥菲利娅与哈姆雷特、乔特鲁德与老哈姆雷特之间的爱情线索,奥菲利娅的爱情在怯懦和被利用中,乔特鲁德的爱情在自私愚昧和虚伪虚荣中都成为哈姆雷特复仇行动的陪葬。“死亡”成为网状叙述结构的结点,成为复仇成功的标志,同时也成为悲剧人物命途的归宿。
(二)“横云断山”的共同取向
“横云断山”是叙事技法之一,常出现于中国古典小说评点当中,首提于金圣叹。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认为“横云断山法”“如两打祝家庄后,忽插出解珍、解宝争虎越狱事;又正打大名城时,忽插出截江鬼、油里鳅谋财倾命事等是也。只为文字太长了,便恐累坠,故从半腰间暂时闪出,以间隔之。”[12]由此观之,“横云断山”重在强调一“断”字,断开原来连续的剧情发展,阻绝大事件在一气呵成之下带来“累坠”的审美缺陷,引入另一事件而使原叙述暂停,对剧情当下的发展并无推动作用,却使整个事件运动跌宕起伏,夺魂摄魄。
《窦娥冤》与《哈姆雷特》分别代表着中西悲剧的杰出成就。无独有偶,二者都有“鬼魂诉冤”的情节。“鬼魂诉冤”在戏剧中出现的位置不一,其功能也各不相同。《窦娥冤》中安排主人公窦娥“鬼魂诉冤”的情节,出现于戏剧的尾声,不仅是剧中事件矛盾冲突得以解决的关键,更是浪漫主义手法的生动呈现。《哈姆雷特》中老哈姆雷特的“鬼魂诉冤”,成为哈姆雷特复仇的直接动因,也使得戏剧成功设置悬念后又蒙上了浓郁的悲剧色彩。虽功能各异,但叙述技法却多有相似。
“一人一事”的线性结构并非意味着事件的平铺直叙,与之相反,“一人一事”在高低起伏、疏密缓急中发展推进。《窦娥冤》第四折中窦娥的冤魂终于在三年后等到父亲窦天章的归来,但并没有直接诉冤。戏剧颇费笔墨周折,写窦父怀疑,门神阻拦,窦娥见父难认,有冤难诉。如窦天章在审阅案宗时分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窦”字,但见名为一“娥”字,且认为其所犯罪行所受罪罚合理,故未将其与女儿窦瑞云相关联。此时观众处于全知视角,心里却十分清楚,窦娥就是窦瑞云。紧接着,窦娥的冤魂出现,由于门神户尉的阻拦却无法托梦于窦天章“诉冤”。窦天章惊醒再看案卷,仍不迟疑。多次反复压窦娥案卷于最下,案卷却又无端翻到上面,通过窦天章的行为动作与心理活动,故意拉开事件运动与“诉冤”的距离,令观众在愁肠百结中“提心吊胆”,产生心理激动。最后窦娥终于一吐实情,观众也因“真相”得以被听见,“冤情”得以申诉获得道德快感。
《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一场中老哈姆雷特鬼魂出现于艾尔西诺城堡前的露台,第二场并没有直接接着叙述霍拉旭和马西勒斯当天早上告诉哈姆雷特其所见异事,而是大量插入克劳狄斯对哈姆雷特的试探和安排,最后二人才将消息送达,哈姆雷特答应当夜赴约。第三场更是推开“鬼魂诉冤”这一线索,转向波洛涅斯家中一室,雷欧提斯在临行英国时,和其妹奥菲利娅、其父波洛涅斯告别时的对白。一个白昼之内事件安排得相当密集。第四场哈姆雷特终于见到了老哈姆雷特的鬼魂,但鬼魂并没有“诉”冤,直到第五场,才完成这一动作。从“看见”鬼魂到“诉”冤情,中间共隔了四场,这一断而再续的叙述方式使得第一幕起伏跌宕,在短时间内易引起观众的审美激动。
剧作家“横云断山”的叙述技法在充分调动观众的审美感知后,又阻滞“合情”的情绪发泄,观众沉浸在荡气回肠中,最终在矛盾的解决下、朴素愿望的达成下实现审美愉悦。纵观事件的发展全过程,又出之以“合理”的人情,即剧中人物由于限制性视角对奇闻怪事的怖惧与怀疑是自然而然的,从而使整个事件发展过程“合情入理”。要之,“错综跌宕的艺术效果是 ‘横云断山法’的着眼点,‘叙而有断、断而须续’是‘横云断山法’的表现形态,‘断’与‘连’的巧妙结合是‘横云断山法’的关键所在。”[13]《窦娥冤》《哈姆雷特》中近似的叙述技法,展现出关汉卿、莎士比亚相近的创作思维和自觉的艺术追求。
三、美学形态之比较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14]《窦娥冤》广为传唱时,中国还没有“悲剧”这一概念。《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从反向对“悲剧”的概念作了界定,并肯定了《窦娥冤》“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15]的文学地位。而西方从古希腊柏拉图的《斐列布篇》开始,便逐渐对悲剧的观念、形态、功能作出了明确要求。中西虽同用“悲剧”这一指称,但其基本内涵却大相径庭,组织结构各有千秋,价值追求泾渭分明。
(一)苦情与怜悯、悲壮与崇高
人物既是叙事的核心,又是推动故事发展的行动元。人物的身份地位既限制着叙述的视角,也深刻影响着叙事结构的安排。从人物身份上看,《窦娥冤》中主人公窦娥是传统观念中弱者的代表,是三岁丧母、七岁离父的“孤儿”,是新婚燕尔痛失爱夫的寡妇,是善良却命途多舛的“苦主”;《哈姆雷特》中主角哈姆雷特则是强者的化身,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瞩目的中心”[16],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完人”。身份上弱小与强大、贫贱与高贵的差异迥然在目。人物身份的差异直接影响了戏剧各自的事件组织和价值追求。
在组织形态上,《窦娥冤》与《哈姆雷特》同样由顺境转入逆境,但《窦娥冤》属于“双重结局形式”,《哈姆雷特》属于“单一结局形式”。《窦娥冤》中,窦娥由于蔡婆婆的收养倒也能够食饱衣暖,免受饥寒之苦,人物看似走向顺境;而新婚丈夫的去世又增加了故事的悲情色彩,同时也为核心事件——张驴儿的逼婚埋下伏笔。另一条线索,窦天章赴考官显回归,为窦娥洗白冤情,又使得枉杀窦娥的结局有了喜剧的因素。“光明的尾巴”是中国几乎所有戏剧的共同之处。窦娥冤魂诉屈,冤情得报,恶人得到惩罚,好人的心愿得以实现。尽管如此,仍然没有改变整个戏剧“悲”的性质,其没有逆转事件的发展,没有反控人物的悲惨命运,而是为着多数观众的善良心愿着想,使“象征性的亮色”出现在戏剧尾声。哈姆雷特出身显赫,是丹麦王国的继承人,而在戏剧一开始,他便身陷囹圄。在识破克劳狄斯杀父娶母、夺位乱伦的真相后,人物命运急转直下,在监禁和谋杀中,终与敌人同归于尽。死亡是英雄人物最终的运命。“一悲到底”的悲剧形态是莎剧的鲜明特色。
在情感激动上,《窦娥冤》以好人受冤、弱小被凌虐而使观众为其悲苦洒泪。窦娥是悲苦剧情的“苦主”,受冤凌虐是悲苦的事实,“苦主”倾吐的是一腔的“苦情”,从而打动观众的是由“苦情”引起的怜悯之情。如《窦娥冤》第三折中窦娥的唱词:
【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这段唱词是窦娥面临死亡、愤而起之,以自然宇宙暗示人间事态,呼告乃至控诉人间秩序的不合理,其于推动剧情发展、推动矛盾解决并没有作用,但浓郁的抒情却成为叙事的高潮,对窦娥磊落刚正的人格塑造,对戏剧感人肺腑之所在的构建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确是“于叙事的架构之上,展现了抒情的精神”[17]。《窦娥冤》强调感知、感情,主人公通过语言动作对内心世界进行表白,以情动人,突出了戏剧的抒情性,“更强调在追求‘神采动人的艺术生命体’的叙事过程中的‘生命体验和交流’”[9],故抒情成分多于《哈姆雷特》。如戏剧第一折【仙吕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等都是窦娥内心情感的绘饰,通过主人公的独白而抒发“苦情”,令观众进入剧作家创设戏剧情境当中,和戏剧人物产生共情,与之同悲共喜。
《哈姆雷特》不同于《窦娥冤》将悲苦乃至悲愤的情感高涨作为戏剧高潮发生的表现手法,而是以现实生活中复杂关系在戏剧中浓缩反映的深广、激烈程度,以及伴随着矛盾的解决即戏剧主人翁英雄的死亡作为事件高潮的标志。《哈姆雷特》在第一幕老哈姆雷特亡魂的诉冤、奥菲利娅听从父兄、拒绝哈姆雷特的爱情中便进入戏剧第一个高潮,哈姆雷特在证实克劳狄斯的种种罪行后矛盾更加集中和尖锐,而哈姆雷特的延宕,其软弱性格与其所背负的血海深仇的矛盾、人文主义理想与社会黑暗敌对势力的矛盾中再次激起戏剧高潮,最终在刺死克劳狄斯复仇成功自己却中毒剑中落下帷幕,达成悲剧发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事件组织的密集和波折,矛盾的相互关联,人物命运的回旋与跌宕,解决矛盾的集中,在观众心中激荡起痛感与快感,恐惧与悲悯的多维情感,短时间内涤荡日常魂灵的尘垢,从而实现崇高的悲剧激情。
《哈姆雷特》强调叙事对高潮的推进作用,并通过人物对话推进剧情发展。独白的抒情功能被降低,而是人物在对事件的认知、分析和判断中仍然作为动作推动事件运动。如哈姆雷特“生存还是灭亡”的一段独白,“它既是对前面因疑虑和自我保护而装疯的总结,又预示着为父复仇阶段的开始。它打破了矛盾双方相互试探的僵局,进入正面交锋的新阶段。因此,虽是独白,却也是一种动作。 ”[7]
值得指出的是,《窦娥冤》中窦娥在悲剧中是被动的承受者,《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则是悲剧结果的主动推进者。窦娥之被动,更突显出其正义性、无辜性,加深了其悲惨悲苦的情感维度。哈姆雷特主动的复仇行动和其延宕动作,使人物的毁灭成为一种作茧自缚、自食其果的报应,戏剧对人性格的弱点给予不对等的惩报,激发出观众的恐惧与悲悯。
(二)善与真的价值追求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18]中西戏剧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呈现出“善”与“真”不同的价值追求。
《窦娥冤》予“善”的追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窦娥善良形象的塑造。首先,窦娥不愿其公公东奔西走创下的家业为无赖张驴儿父子窃夺是窦娥拒绝逼婚的理由之一;其次,窦娥为保护年老体衰的蔡婆免受刑罚而冒死含冤领罪,其孝情背后更是人心的良善;再次,窦娥亡魂在申冤成功后仍不忘蔡婆无人赡养,遂托与其父窦天章。窦娥是善良、是(所有符合封建传统要求的)“好人”的化身,“善良”被“无良”凌虐和践踏、“善良”的合理要求和表达成为戏剧表现的中心。从此意义上讲,《窦娥冤》是“表现”的艺术。“善良的人,出于正直和坚贞而遭到邪恶势力的迫害,备受摧残,却宁死不屈,在关汉卿看来这不仅值得悲痛,而且可歌可泣。”[19]《窦娥冤》是关汉卿悲剧意识的集中体现。其二是冤情得报、正义必胜的叙事导向。“鬼魂诉冤”的情节安排导向,沉冤昭雪的事件结局,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因果报应成为观众认可的一种生存意志,成为普遍意义上对正义和美好的追求。《窦娥冤》的杰出成就恰是“传非文字之传,一念之正气使传也”[10]的明证。
《哈姆雷特》予“真”的追求主要体现在“真实感”的营造和强调戏剧价值在于对社会生活本质的把握。第一,“真实感”的营造是为了强调戏剧“事件”真实,由此引领观众对人自身生存境遇的观照和反思。“真实感”的营造通过戏剧时间和空间的物理性、矛盾的客观和复杂性,以及人物对白的自然合理来实现。剧作家被要求要有对人物(背景、性格)、环境(时间、空间)和矛盾等给予符合现实生活逻辑刻画的能力。相较于《窦娥冤》,《哈姆雷特》是“再现”的艺术。第二,戏剧要能够体现出剧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知和理性思辨。《哈姆雷特》在一定程度上不失为家庭家族叙事,家庭家族叙事中“家庭家族既是演叙的内容中心,又是描叙的结构线索。”[11]尽管这个家庭十分特殊。戏剧通过“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20],从家庭叙事角度出发勾连、观照当时整个欧洲的社会面貌。整个社会都是一座大牢狱,“丹麦是其中最黑暗的一间”[16],“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这重整乾坤的责任。”[16]如此,哈姆雷特的复仇行动就超出了个人意义而具有典型性,哈姆雷特与克劳狄斯的对抗成为人文主义理想与社会邪恶势力的对抗。戏剧通过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对哈姆雷特性格的观照,揭示悲剧的主客观原因,成为人文主义者行动衰微的生动、深刻的注解。
人际冲突在特定的条件下成为社会冲突的缩影。《窦娥冤》与《哈姆雷特》的戏剧冲突都通过具体的人际冲突一定程度上反映悲剧产生的社会因素,但各自在价值追求上却表现出对人性的关怀与对理性的求索之间的差异。
四、结语
综上,《窦娥冤》与《哈姆雷特》时空意识和叙事结构的差异深刻影响着戏剧的美学形态。通过对其叙事艺术的比较,能够发现中西戏剧各自独特的艺术成就,对其各自所代表的美学精神有更为客观的认识和阐释。《窦娥冤》时间意识的主观性、心理性,空间意识的虚涵性是剧作家和观众对戏剧是“故事”的一种共识,其以情感人、以情动人的程度成为衡量剧作优劣的尺度,因此强调戏剧对人物心灵体验的揭示,对内心世界的关注,强调人的情感、意志的作用。《哈姆雷特》时间意识的客观性、空间意识的物理性形成戏剧现实主义的基础,其对社会的关注和理解,通过个体命运和性格的反映,在矛盾的集中产生和集中解决下,到达审美上的顶峰。因此,强调事件的真实感,强调理性的透彻和逻辑的深刻。诚如陈园所言:“无论是冲突还是‘单纯’,死亡虽然是人类永远无法逃脱的阴影,而正义却是人类永远的光明。”[2]《窦娥冤》与《哈姆雷特》是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的遥相辉映,其以超世高标的人文性和思想性共同丰富着世界艺术园地的宝库,跨越时空的限制而成为人类艺术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