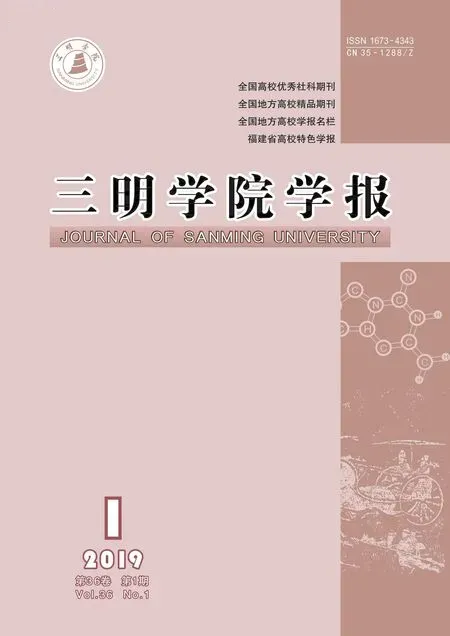论“永嘉四灵”诗之“清苦”
2019-03-21梁思诗
梁思诗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南宋宁宗时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并称“永嘉四灵”,其诗学晚唐,以贾岛、姚合为宗。严羽《沧浪诗话》以“清苦”评价“四灵”诗风:“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1](P27)清代顾嗣立《寒厅诗话》云:“‘四灵’以清苦为诗,一洗黄、陈之恶气象、狞面目。”[2](P83)翁方纲 《石洲诗话》云:“西江以粗劲反之,‘四灵’以清苦洗之。”[3](P81)前人对“四灵”诗之“清苦”少详论而仅概述之,但我们不难看出,其所谓“清”多与“四灵”的写景、隐逸的内容及清新细巧的语言相关;而“苦”则多指其苦吟创作,遣词用字推敲斟酌。人们评价“四灵”诗之“清”多与“苦吟”联系在一起,如葛天民《简赵紫芝》诗云:“清坐有仙骨,苦吟无宦情。”[4](P743)赵平点校《“永嘉四灵”诗集》亦将“四灵”诗风概括为“精秀清圆、苦吟寒狭”[5](P4)。其实,“四灵”诗之“清苦”的内涵并不仅限于此,且“清”与“苦”往往是紧密相联的。正如叶适《徐道晖墓志铭》说徐照“嗜苦茗甚于饯蜜”[6](P321)。“四灵”诗歌题材皆以山居、宿寺、寄赠、写景为主,风格大体一致,因此笔者不将四人分开论述。本文主要从内容、语言、意境三个方面探讨“四灵”诗歌的“清苦”书写。
一、内容:清静野逸,病瘦贫饿
文学作品的风格体现的是作家本人的个性,不同性情、不同阅历的诗人会写出不同格调的诗作。“四灵”诗风清苦,首先与其生活经历和个性特征有关。如徐照自己所言:“贫与诗相涉,诗清不怨贫”(《和潘德久喜徐文渊、赵紫芝还里》)。他将“清”作为诗作的风貌,与自身的贫苦联系起来。于诗人个体而言,“清”指的是个性与品位之清静超脱、野逸疏放;“苦”指的是生活之贫穷困苦。由于穷困且志不达,所以转而追求清静超脱的隐逸生活方式;然而清静无为的同时,又无法摆脱穷困带来的穷愁潦倒之苦。“四灵”的身份介于江湖谒客与隐士之间。徐照终身布衣,或在农村耕作,或在城里谋生,生活极其贫苦,是真正意义上的寒士。徐玑只在偏远地区做过小官,难得升迁,不惑之年重新参加科考,后依然任闲职。翁卷省试不第,在各地幕府任职,当过塾师,亦是个漂泊寒士。赵师秀虽是宋太祖八世孙,中过进士,然而也只做过小官。孝宗隆兴元年(1163),宋金签订隆兴议和,此后宋金维持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和平对峙。生活于这个时期的“四灵”,既没有抗金热血,也没有辅佐君王、致君尧舜的宏图大志。现存“四灵”诗中表达出仕抱负的诗作很少,关心民生之作亦不多,“四灵”自伤的往往是贫病的生活困境,其诗的内容多为唱和、访僧寺、登楼、游园、耕种、采药、煮茶;他们常与隐士、僧人交往,深受禅风熏染,多出世超尘之思。“四灵”天性喜僻静,徐照自号“山民”,翁卷自称“野人”,他们对于这种清静离世的生活乐在其中。“四灵”喜在诗中写自己的隐逸生活,不少诗歌如同日记、游记。“四灵”诗多为友人间的寄赠,通过赠友、赞友来表达自己与友人的共同趣向,树立自己脱俗的隐士形象。这部分诗歌大体以“清”为主,如以下几首诗:
一生嫌世俗,不向市中居。既是未攀桂,却堪同钓鱼。疾除禅老药,诗答野人书。又说成丹鼎,吾生愧不如。(徐照《赠刘明远》)①
隐居须是僻,君向数家村。自以闲为乐,何嫌贫尚存。碧波连草舍,白日掩柴门。挂得一瓢在,风来应恶喧。(徐玑《次韵刘明远移家其一》)
不奈滴檐声,风回昨夜晴。一阶春草碧,几片落花轻。知分贫堪乐,无营梦亦清。看君话幽隐,如我愿逃名。(翁卷《春日和刘明远》)
相逢楚泽中,语罢各西东。天下方无事,男儿未有功。边风吹面黑,市酒到肠空。早作归耕计,吾舟俟尔同。(赵师秀《赠张亦》)
徐照与赵师秀之诗如散文,都是诗人直接剖白,说自己虽然清闲无功,但反而喜欢这远离世俗的生活。徐玑、翁卷之作则加入了对隐居环境的描绘,“草舍”“柴门”可见生活之清贫,“春草”“落花”可见意趣之悠然。在这几首诗中,“四灵”写离世超脱的同时不忘提及自身的贫困、无作为;与“四灵”赠诗者也都是隐逸之士,他们在赠诗往来中得到了心灵的慰藉,下层生活的穷苦在此被淡化了。
“四灵”作诗的关注点多在自己身上,常将自我形象写入诗中,且往往集病、瘦、贫、饿、老于一身。有时,诗人写景是为了衬托诗人自身的形象,以凄清之景衬诗人之困苦,因而这部分诗歌在写“清”的同时,更多地流露出“苦”的意味,如以下几首诗:
三行三步歇,屋漏坐频移。妻欲藏茶鼎,僧能施药资。邻园梅尽发,河岸草生迟。天解怜贫病,难令不作诗。(徐照《病中作》)
古都依蛮楚,身来作冷官。老怜兄弟远,贫喜妇儿安。分菊乘春雨,移梅待岁寒。又传家信至,入夜着灯看。(徐玑《古都》)
闲居观物化,几叶又飞东。清氯全归月,寒声半是风。病多怜骨瘦,吟苦笑身穷。折得邻家菊,还思靖节翁。(翁卷《秋日闲居呈赵端行》)
宵长非一梦,欲记已迷茫。照镜枯于腊,梳头落似霜。病疴如退愈,贫屡又商量。所嗜惟崖栗,今年不敢尝。(赵师秀《栗禁》)
徐照诗首句形象地写出了自己行动不便的病态。“梅”说明时间为冬季,“河岸草生迟”写了无生机的荒芜之景,与“天解怜贫病”连接,实现了景荒与人病之交融。徐玑诗虽不直接写自身形象,但“冷官”“老”“贫”几个字已使其形象隐现于诗句之中。徐玑诗在写“清苦”的同时表现自己安贫乐道的心态。翁卷诗“病多怜骨瘦”也是直接写出自身形象,颔联“清氯全归月,寒声半是风”将风和月写成没有温暖、没有人情味的物象,形成冰冷凄寂的意境。赵师秀诗不以景物自衬,但每一句诗都写及自己衰老颓唐的形象:记忆衰退、白发苍苍、贫穷年迈。
二、语言:洗炼精致,戒绝尘俗
较早用“清”来形容文学之人是西晋陆云,其《与兄平原书》云:“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7](P60)其后《文心雕龙》也提到“雅好清省”[8](P356)这一概念。将“清”与“省”结合在一起,说明文学中“清”的审美内涵中包含了简省、省净之意。蒋寅在《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中指出:“清的基本内涵是明晰省净。”[9](P49)在“四灵”的作品中,这种“省净”的特点首先直接体现在诗歌体裁的选择上。
从表1可以看到,“四灵”在诗体中最多选用五律,其次是七绝,也有部分五绝诗。②“四灵”爱写近体,于近体中又偏爱五言,而近体五言诗具有精致简约的特点。刘克庄《野谷集序》载赵师秀语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也。”[10](P86)

表1 “四灵”诗体选用情况 单位:首
针对“四灵”诗之省净,叶适《西岩集序》云:
若灵舒,则自吐性情,靡所依傍,伸纸疾书,意尽而止。乃读者或疑其易近率淡近浅,不知诗道之坏,每坏于伪,坏于险伪则遁之而窃焉,险则幽之而鬼焉,故救伪以真,救险以简,理也,亦势也。能愈率则愈真,能愈浅则愈简,意在笔先,味在句外,斯以上下三百篇为无疚尔。[11](P2626)
叶适提出翁卷诗“简”的特点,既反驳了一些人认为翁诗浅率的观点,又针对当时诗坛上“险伪”的道学诗和江西诗进行反拨。理学至南宋而鼎盛,当时的道学家认为诗文只是用以明道说理的工具,剔除了诗歌表情达意的作用。而江西诗派末流一味使用僻典,使诗歌呈现出险峭的风貌,亦是对诗歌性情的消解。叶适不满于这些不含真意、不抒性情的诗,因而提出“救伪以真,救险以简”,他认为”四灵”诗正是以“真”“简”取胜,因而对其大加推崇。
然而“四灵”诗之“简”并非单纯意义上的简单浅显,实则是一种几经锻炼后的洗练精致,是“清苦”的一种体现。如陈衍《石遗室诗话》评曰:“洗练而熔铸之,体会渊微,出以精思健笔。”[12](P30)另外,其锻炼不仅是为求工巧,而更多地是为了戒绝陈俗:一是出于求新变的自觉意识,避出陈语;二是因其清雅的审美意识而刻意追求脱俗。观“四灵”诗,虽立意不新,但在用语上确能看出其求新脱俗的努力。
“四灵”最爱写五律,于五律之中,又常对颈联两句加以锻炼(部分诗于颔联求工)。首联和尾联多陈述,用于交代写作因由,语法结构以主谓、主谓宾、述宾结构为主,是散文或口语的习惯性表达。而颈联两句则打破这种语序惯性,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意象化的、诗性的语言结构,以实现陌生化的艺术效果。由于景物描写主要浓缩在颈联两句里,因而诗人通常要极尽才思,以仅仅十字涵盖之。颈联大多采用意象的组接方式,也即名词与名词的组合、名词与短语的组合、短语与短语的组合,以“二二一”的语式呈现;与此同时,不用虚字,并以形容词作谓语。如:“笛冷君山月,帆轻夏浦晴”(徐照 《送翁诚之》);“幌红花日影,香断寺钟声”(徐照《题何仙姑旧居》);“鸿声秋浦冷,雨气海山深”(翁卷《送赵明叔明府》)等。这些诗句常以对仗的形式出现,并列在一起的意象具有一大一小的特点,于小处见细微,可见出诗人体物之细致;于大处见整体环境,渗透着诗人虚静之心;这一大一小的结合正好将诗的意境和盘托出。这种以大小意象组接的句法结构,亦是简省的体现。
叶适《徐道晖墓志铭》说徐照诗“无异语,皆人所知也”[6](P321);而徐象梅《两浙名贤录》也曾说“四灵”“日锻月炼,一字不苟下”[5](P258)。“四灵”诗不用生僻字,而多用寻常语,但这些寻常字眼却也是几经苦思而得。“四灵”诗意象的组接方式,一是粘贴式的并列(如上文所举之例),二是以动词来连接意象。如“山色含疏雨,蝉声带夕阳”(徐玑《同友人乘舟》),诗人为了展现景色之混融,使用了“含”字和“带”字,读者还能看出这是对远景的状写,即烟雨笼罩下的山色和伴随着蝉唱的夕阳。有时候,为了造成语言的陌生化,诗人往往隐去了动词的主语,如“窗静吹寒雪,舂鸣落夜泉”(徐照《能仁寺》)。在这里,“吹”的主语是风但没有写出来,而是单以“吹”字表现雪花纷飞之状;而后一句诗中的“落”字则是倒装前置,用以将“舂鸣”和与其毫不相干的“夜泉”联系在一起,写出了泉落声和舂鸣声夹杂在一起的听感。为了求新、求脱俗,“四灵”往往喜用一些不自然的、尖新生峭的字词。如“光凝兰叶腻,冷逼鹤阴晴”(徐照《露》),在这句诗中,我们很难想象出诗人所描绘的景色,因为诗人仅仅点出了光、兰、鹤几个联系不甚密切的意象,并用“凝”“腻”“逼”来与之相连,尤其是“逼”字,在写景诗中并不常见。语言的陌生化阻止了读者的想象,并限制了读者的感官能力,使得读者与诗人描绘的世界产生了距离感,也产生了新奇而生硬的艺术效果。又如“宿禽翻树觉,幽磬度溪闻”(徐玑《夏夜同灵晖有作奉寄翁赵二友》),这两句诗的诗意也不是读者能够凭本能迅速领会的。句中“觉”的主语并不是“宿禽”,而是省略去的诗人的形象,意谓栖居于树中的禽鸟翻腾之时,诗人才察觉到鸟的存在,暗指当时环境之清幽寂静。若联系下一句,其正常语序应为“度溪闻幽磬”,读者才知原来人在景中。古代诗人写景时锻字炼句是为了形象地描摹景物,或是为了借景抒情,但“四灵”将这两种书写目的都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戒绝陈俗的刻意追求。“四灵”诗以不相干的意象的组接、不合常规的动词的使用、颈联之过分求工使全诗意境不融合,达到有意阻碍读者顺畅接纳诗意的效果。“四灵”以苦吟求新巧,是诗歌语言陌生化程度的提高,是诗歌语言自觉发展的体现。
三、物境:凄冷野寂,敛情约性
“清”也表示凄厉冷冽之意,在诗歌中表现为凄寒萧飒的审美特征。凄冷可以说是“四灵”诗歌的主要特色,主要体现在其所取之象与所造之境中。严受云《诗词意象的魅力》提出:“即兴意象作为组成元素进入诗歌作品时,不携有约定性的既成涵义。……一个个具体的即兴意象,只有处在若干个意象组成的审美结构中,才能呈现出确定的含义与色调。”[13](P164-166)即兴意象是与情感内涵已在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定型的原型意象相对,是诗人就眼前之景随意赋予其情感的意象。“四灵”诗歌中的意象基本上属于即兴意象,即均为诗人在山居行旅之时的即景记录,具有真实性,并非为了表达某种特定情感而使用的象征或隐喻。“四灵”诗中常见的意象有雨、草、松、鸿雁、苔藓等,其中除了在行旅诗中常用于表达思乡之情的“鸿雁”意象为原型意象外,其他均为即兴意象。这些意象都具有细小、凄寂的特点,如草、苔,都是生长在地上,不具有鲜明的审美性,平凡而不惹眼之物。“四灵”诗使用最多的意象是“雨”,在徐照诗中出现了19次,在徐玑诗中出现了40次,在翁卷诗中出现了22次,在赵师秀诗中出现了27次。“四灵”主要用“雨”意象来营造孤寂凄清的氛围,用在诗的开头,如“江城过一雨,秋气入宵浓”(徐照《宿翁灵舒幽居期赵紫芝不至》),为全诗罩下一层哀怨的气氛;或用在诗的颈联,如“鸿声秋浦冷,雨气海山深”(翁卷《送赵明叔明府》),写出诗人身处凄清的荒野,使诗歌的清寒之意至此达到最大化。一方面,雨声淅沥,天暗阴沉,自有一种凄楚美,符合贫老病衰的诗人凄寂的心境,如“园林春易老,乡岸雨难匀”(徐玑《寄上泉州许参政福州薛端明谪居》);另一方面,雨有洗刷大地,带来雨后清新的明净之美,与诗人追求超脱的志趣有些许关系,如“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赵师秀《有约》)。在古典批评中,批评者多强调诗歌意象的蕴含性,甚至追求深邈,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王廷相《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云:“言征实则寡余味也,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14](P39)显然,“四灵”诗中之象大都止于物象的表面,仅由诗人为其披上一层衰飒的外衣,表现隐士的野逸之思,既没有饱满的内涵,也未达到“情有余”的艺术效果,他们笔下的意象是不丰满的、不圆融的,没有言外之意的。
“四灵”多数诗歌通常仅在颈联写景,以这两句诗统摄全诗的意境。但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诗的颈联与其他部分不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呈现出造境不够浑成的结果。“四灵”诗的整体意境大都具有荒寒凄冷的特点,但这种凄冷并未能与诗人主体达成交融。张瑞君指出:“诗是情感的艺术。‘四灵’却认为情感并非诗歌创作的根本因素,而是要心源澄静,安闲自在,不惹世氛。”[15](P22)造境凄切,但极少人的愁情,人只是空间上在景中,情思却不与景相连,从形而上的层面来说,人与境是分离的。凄清的意境仅仅体现了诗人的审美趣向,或者只是诗人对隐居或旅居生活环境的描写,这些环境大多远离闹市,体现的更多是隐逸、野趣,也是诗人对脱俗超尘的人格境界的自我标榜。“四灵”造境凄清的诗歌,根据其情感内容,可大致分为如下几种:其一,没有作者的愁思,而只是取境凄清;其二,写诗人之老、病、寒等,但这些往往不构成境凄的主要原因,只是稍带提一下,以增加诗歌的凄楚感;其三,思友、离别;其四,羁旅。综合起来,又可以分为没有具体愁情和有具体愁情两大类。
第一类:
古殿清灯冷,虚堂叶扫风。掩关人迹外,得句佛香中。鹤睡应无梦,僧谈必悟空。坐惊窗欲晓,片月在林东。(徐照《宿寺》)
古木山边寺,深松径底风。独吟侵夜半,清坐杂禅中。殿静灯光小,经残磬韵空。不知清梦远,啼鸟在林东。(徐玑《宿寺》)
一宿此禅宫,身同落发翁。深窗难得月,老屋易生风。灯冷纱光淡,香残印篆空。独怜吟思苦,妨却梦西东。(翁卷《宿寺》)
石路入青莲,来游出偶然。峰高秋月射,岩裂野烟穿。萤冷粘棕上,僧闲坐井边。虚堂留一宿,宛似雁山眠。(赵师秀《龟峰寺》)
以上几首诗都以“宿寺”为主题,皆造境凄清,有浓浓的寒野苦寂之味。诗人的情感在此被减到最弱,我们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诗人孤寂的心境,这种心境是因诗人置身于佛寺这样一种超尘脱俗之所而诞生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具体原因。每首诗都写出了佛寺以及佛寺周围山林的景象,“清灯冷”“磬韵空”“纱光淡”“萤冷”等都是能代表佛寺清幽虚寂的典型意象,又与“冷”“淡”等清空的形容词搭配,极显意境之清寒,人心之虚空。我们知道“四灵”生前受佛禅影响极深,但其诗呈现出的却并不总是僧人式的超脱,而是既不能摆脱世俗又不能完全进入禅境的寻常人苦涩的寂寞。
第二类:
江城过一雨,秋气入霄浓。蛩响移砧石,萤光出瓦松。月迟将近晓,角尽即闻钟。又起行庭际,思君恨几重。(徐照《宿翁灵舒幽居期赵紫芝不至》)
三任来得禄,兹行亦是缘。地宜惟有鹤,清职但看船。逝水通青海,吴门隔远烟。别离春欲半,草色正芊芊。(徐玑《送华亭薛运干》)
千山落叶深,高树不藏禽。游子在何处,故人劳此心。闲灯妨远梦,寒雨乱愁吟。僧奭曾相约,花时共一寻。(翁卷《寄赵灵秀》)
虚窗风飒然,独卧听残蝉。家务贫多阙,诗篇老渐圆。清秋添一月,故里别三年。最忆君门首,黄花匝野泉。(赵师秀《寄薛景石》)
以上几首都是送别、寄赠诗,表达的都是诗人对友人的不舍或思念之情。这是古诗的传统题材,“四灵”也是按照思友与景物环境相结合的传统写法进行抒情的。其中徐玑诗写送别时的情景,以“逝水”“远烟”等悠远无尽的意象来写友人离去的旅途,意境清透绵邈。另外三首则写诗人独处时对友人的想念,“秋气”“寒雨”“残蝉”“野泉”皆是诗人从身边摄取的景象,无不具有衰颓冷寂的特点。诗人思友,使这些常见的景色也染上了一层凄清之色;同时,这种思友情又都极其轻薄,不痛不痒。松浦友久曾提出:“所谓友情诗,特别是士人间友情的描写,则正因为它是主体的、第一人称的,反而产生出增加相互信赖、保障作者人格的结果。”[16](P56)同性文人之间的友情与亲情、爱情不同,它是文人沟通趣味、保持人格、寻找志向共鸣的渠道,这种“情”是社会交往的结果,而非生理或血缘上的羁绊,况且交结聚散本是社交常态。因而文人友情从本质上就不可能达到刻骨铭心。“四灵”以友情为题材所作的诗,虽有情在其中,但仅是幽情单绪,是诗人无聊时的闲思,没有多少动人的力量。
清往往又是和弱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17](P134)在观物的过程中投入主观的情感,从文字流出,才能成为“意境”。然而饱满的情感的缺失,是造成“四灵”诗“清”,或者说“弱”的主要原因。“寂”“孤”“愁”等古代诗人常用在凄冷意境中表现主观情感的字词,在 “四灵”诗中较为少见,他们多用“野”“寒”“残”“荒”“老”“腥”等词来形容景物,但并不用于表达自身情感。这种凄冷只是事物在特定的季节、时刻和环境中呈现出来的外在状态,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而非诗人主观情感的投射。“四灵”因置身于荒芜之所,受景象之凄冷所感染,才生出凄寂的心境。徐照《宿寺》诗云:“掩关人迹外,得句佛香中。”可见“四灵”总是爱到“人迹外”去作诗,也即到人情外去写诗,脱离了社会与世情,将精神与眼界封闭起来。“四灵”住在山中、寺内,都是与外界相割离的孤绝的世界,诗人置身于这样一个孤绝的世界中 (偶有联络者多属隐士、僧人之辈),自然不与世俗人事发生情感的关联,能写入诗的情感也自然不多。翁卷《送蒋德瞻节推》诗云:“《楚辞》休要学,易得怨伤和。”“四灵”诗歌之乏情,与他们的“约情敛性”的文学观有关。翁卷在此显然是排斥写作中肆意的哀怨,所以即便“四灵”有情之时,也不会张扬于笔下。
综上所述,“永嘉四灵”诗的“清苦”主要由于“四灵”生前常年游走于中下层社会,过着贫寒的生活,加之生性喜静,使其诗作内容清静超脱又贫瘠苦涩。在创作上,“四灵”通过选词用字和句式的变化使诗歌语言达到陌生化的效果,表现出褪去陈俗之“清”。在表情达意上,“四灵”诗有“约情敛性”之特点,通过细微而不起眼的意象的使用,营造凄清苦寒的意境,呈现出诗人苦寂的精神状态。“四灵”诗之“清苦”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宋诗平淡化、议论化、内向化的特点。诗人多关注自身生活与心境,爱从身边环境取景,较少对社会和国家的忧心,情思轻薄,多超尘之思。
注释:
① 本文所引“永嘉四灵”诗皆出自赵平校点《“永嘉四灵”诗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不再一一出注。
② 此表中的数据是笔者根据赵平校点《“永嘉四灵”诗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统计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