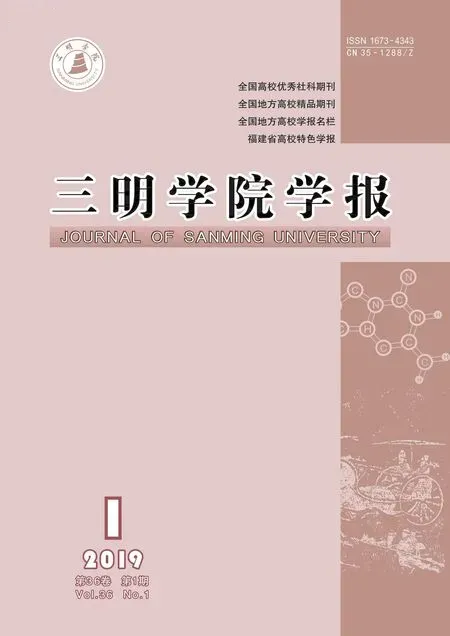《现代汉语词典》中多义词义项处理指瑕
——以动词“打”为例
2019-03-21吴春生吴清秀
吴春生,吴清秀
(1.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传学院,贵州 兴义 562400;2.宁德师范学院 中文系,福建 宁德 352000)
《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以推广普通话、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为宗旨的工具类语文辞书。作为我国第一部规范型现代汉语词典,它的权威性、科学性早已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但《现代汉语词典》词语条目繁多,数量浩大,在内容上难免还存在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①特别是在多义词的义项处理上,还存在着较多的瑕疵。例如《现代汉语词典》里列举了“打”作为动词时的多条义项,其中如“打草鞋”“打毛衣”的“打”既可以是义项(9)的“编织”,可以是义项(6)的“做”,也可以是义项(6)的“制造(器物、食品)”;再如义项(3)是“殴打;攻打”,其动作与义项(1)“用手或器具撞击”所表述的动作高度重合,义项(3)和义项(1)可以归纳为同一义项。
类似的例子在 《现代汉语词典》中还有不少。有鉴于此,本文拟以义项较多的“打”(动词)为例,试图对《现代汉语词典》中多义词义项的处理问题加以探讨。
一、《现代汉语词典》“打”的义项处理现状
从现有研究来看②,多义词的义项的处理中最大的问题集中在对互有关联的义项划分上。这种划分是否具有清晰度,要以这个清晰度是否能够为每一个义项在语义场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为标准。事实上,从目前的辞书来看,多义词的义项处理带有着词典编纂者自身的主观色彩。这种主观性大约表现在对义项的交叉、包含关系的认识和对义项的使用范围及意义范围的认识上三个方面。前两点是基于对义项质的方面而言,后者则是基于对义项的量的方面而言。下面我们以《现代汉语词典》中的 “打”(动词)为例,从这三个方面来对《现代汉语词典》中多义词的义项处理作一讨论。
(一)义项的交叉关系
如果多义词的义项在语义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之处,我们称之为义项间的交叉。在标注词义的过程中,如果多义词的两个义项中只有各自一小部分为区别性的词义,而其余大部分的意义是相近的,那么我们在区分这两个义项的时候,注意到的主要是其语义相同的部分,而语义的区别部分则容易被忽略,难以准确辨别出来。如果出现在语料中的这些多义词义项的词义落在这个交叉重叠的区间内而词典中又没有给出相应的区分线索的话,就容易造成判断上的困难。
各版《现代汉语词典》共列举了动词“打”的25个义项。现摘录如下:
(1)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门—~鼓。(2)器皿、蛋类等因撞击而破碎:碗 ~了|鸡飞蛋 ~。(3)殴打;攻打:~架—~援。(4)发生与人交涉的行为:~官司—~交道。(5)建造;修筑:~坝—~墙。(6)制造(器物、食品):~刀—~家具—~烧饼。(7)搅拌:~馅儿—~糨子。(8)捆:~包裹—~铺盖卷儿—~裹腿。(9)编织:~草鞋—~毛衣。(10)涂抹;画;印:~蜡—~个问号—~墨线—~格子—~戳子—~图样儿。(11)揭;凿开:~开盖子—~冰—~井—~眼儿。(12)举;提:~旗子—~灯笼—~伞—~帘子—~起精神来。(13)放射;发出:~雷—~炮—~信号—~电话。(14)〈方〉付给或领取(证件):~介绍信。(15)除去:~旁杈。(16)舀取:~水—~粥。(17)买:~油—~酒—~车票。(18)捉(禽兽等):~ 鱼。(19)用割、砍等动作来收集:~柴—~草。(20)定出;计算:~草稿—~主意—成本~二百块钱。(21)做;从事:~杂儿—~游击—~埋伏—~前站。(22)做某种游戏:~球—~扑克—~秋千。(23)表示身体上的某些动作:~手势—~哈欠—~嗝儿—~踉跄—~ 前失—~ 滚儿—~晃儿(huàngr)(24)采取某种方式:~官腔—~比方—~马虎眼。(25)定(某种罪名):他曾被 ~成右派。
这25个义项中,具有交叉关系的约有以下几处:
第(1)个义项与第(11)个义项有交叉,如“打冰”,我们既可以说这里“打”为(1)的“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也可以说这里的“打”为(11)的“凿开”。
第(4)个义项与第(24)个义项有交叉,如“打官腔”中的“打”,可以是义项(4)的“发生与人交涉的行为”,也可是是义项(24)的“采取某种方式”。
第(6)个义项与第(21)个义项有交叉,如“打烧饼”的“打”,可以是义项(6)的“制造”烧饼,也可以是义项(21)的“做/从事”——比如“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做/打烧饼的”。
第(6)个义项与第(9)个义项有交叉,如“打草鞋”“打毛衣”的“打”既可以是义项(9)的“编织”,又可以是义项(6)的“制造”。
义项(6)与义项(20)有交叉,如“打草稿”的“打”,可以是义项(6)的“制造/制作”——草稿从无到有,可以视为制造/制作的过程,也可是义项(20)的“定出”草稿。“打主意”的“打”亦是如此。
义项(13)与义项(23)有交叉,如“打信号”的“打”,可以是义项(13)的“发出”,但当此信号是肢体的某些动作时,也可是义项(23)的“表示身体上的某些动作”。
义项(12)与义项(17)有交叉,如“打车票”的“打”,可以是义项(12)的“印制”车票,也可以是义项(17)的“买”车票。
义项(12)与义项(14)有交叉,如“打介绍信”的“打”,可以是义项(12)的“印制”介绍信,也可以是义项(14)的“付给或领取”介绍信。
义项(16)与义项(17)有交叉,如“打水”“打粥”中的“打”,可以是义项(16)的“舀取”水或粥,也可以是义项(17)的“买”水或粥。
(二)义项的包含关系
在多义词的众多义项中,其中一个义项的语义被另外一个义项的语义完全包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两个义项间存在着包含关系。在词典中,具有这种义项之间存在包含关系性质的多义词,大部分可以通过“特指、泛指、专指”等指示词指明,另外一部分并没有指示词,只能通过语义上是否存在包含关系加以判断。多义词义项间的包含关系对于词义标注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词典编纂者因误判包含关系而使得标注一致性大幅度降低,这给词义标注带来很大的困扰。
《现代汉语词典》中“打”(动词)的义项中有包含关系的约有以下几处:
义项 (1)“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包含义项(15)“除去”。义项(15)是“除去”,所举例证如“打旁杈”,“打旁杈”也可以解释为义项(1)的“用手或器具撞击旁杈”。“旁杈”归属于物体之列,义项(1)与义项(15)基义相同,二者的动作一致,撞击的对象存在着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因此义项(15)的“除去”也从属于义项(1)“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
义项(6)“制造(器物、食品)”包含义项(9)“编织”。义项(9)是“编织”,所举例证“打草鞋”“打毛衣”,“打草鞋”“打毛衣”也可以解释为义项(6)的“制造草鞋”“制造毛衣”。“草鞋”“毛衣”属于器物一类,义项(6)与义项(9)的基义相同,二者的动作一致,制造的对象存在着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因此义项(9)“编织”包含在义项(6)“制造(器物、食品)”中。
义项(10)“涂抹;画;印”包含义项(14)“付给或领取(证件)”。义项(14)是“付给或领取(证件)”,所举例证“打介绍信”,“打介绍信”这一行为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动作,即“印介绍信”以及“付给或领取介绍信”,而在这两个动作之中前者的意义更为重要,前者动作是后者动作能够得以完成的前提,义项(14)给出的注释“付给或领取(证件)”也应该有两个步骤,首先“印证件”,然后才是“付给或领取(证件),因此义项(14)的动作与义项(10)的动作一致,义项(14)包含于义项(10)之中。
义项(24)“采取某种方式”包含义项(12)“举;提”。义项(12)是“举;提”,所举例证“打灯笼”“打伞”等也可以解释为用“提”或者“举”的方式,也就是义项(24)中的“采取某种方式”。由此可见“举;提”这一动作方式包含于“采取某种方式”中,即义项(24)的动作包含着义项(12)的动作,因此义项(12)“举;提”包含在义项(24)“采取某种方式”中。
义项(19)“用割、砍等动作来收集”包含义项(18)“捉(禽兽等)”。义项(18)是“捉(禽兽等)”,所举例证“打鱼”往往“打”的不是一条鱼,而是至少两条以上的一批鱼,故“打鱼”之“打”带有收集之义,所以“打鱼”既可以是“捉鱼”,也可以是义项(19)中的“收集”。
义项(1)“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包含义项(3)“殴打;攻打”。义项(3)是“殴打;攻打”,其动作与义项(1)“用手或器具撞击”所表述的动作高度重合。因此,义项(3)的动作包含于义项(1)之中。
(三)义项的使用范围及意义范围
一个义项的使用范围及意义范围就是词的义项根据其词义而确定的组合范围,也就是义域。在词典中能否正确标注词义的另一个难点就是,多义词的义项划分完备与否,是否能够囊括词语在语言中的使用情况。这在标注过程中具体表现为词典给出的词义并不能覆盖语料库中词语的所有使用情况,即不能覆盖全部义域,从而有可能导致词典编纂者无法对语料中的词标注准确的词典义项的情况发生。
就《现代汉语词典》中动词“打”的25个义项来看,义域不明的有义项(16)所举例词,水、粥如果为商品,则“打”的义项也当为“买”,其余情况则为“取”,义项(16)在是否为商品这个义域上不明;义域存有差异的有义项(20),“打草稿”“打主意”和“成本打二百块钱”,这三项例证不属于同一类,前两者后接抽象的东西,后者则用于假设的语境;类似的还有义项(13),打雷是自然现象,而打炮、打信号、打信号和打电话等则是人力所致,亦不属于一类。
二、关于“打”义项处理的建议
(一)“打”义项处理的原则
关于“义项”处理的讨论始于赵应铎的《关于确立义项的几个问题》一文。赵文从汉语史的角度,对怎样从一些具体意义中概括出普遍意义、怎样使用古书注释以及怎样处理词类活用等问题提出了个人观点。[1](P88-96)之后的符淮青[2](P86-112),[3](P98-105)、汪耀楠[4](P99-106)、宛志文[5](P70-77)、王志学[6](P45-47)、杨桦[7](P73-76)等分别就义项以及词典多义词义项处理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纵观前人理论,笔者以为对多义词义项的处理要重点关注以下两点:
1.义项与本义的关系
正如王力所言,“词的本义应是第一义项”,这就好比一棵大树的根部一样,任何枝蔓的生长都离不开根部提供的营养,词的本义就是树根,是词典的第一个义项,其他的义项作为枝蔓都是在它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这一点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因此,在讨论多义词义项时,应首先关注本义,其次要关注由本义引申发展出各义项的路径。
2.概括性和区别性
所谓概括性,是指一条义项能够涵盖多个具体的言语义(具体语境中的意义),不能随文立义;所谓区别性,是指义项之间要有明确的区分度,不能纠缠不清。两条原则角度不同,概括性对内,区别性对外。当然二者也存在一定的矛盾:概括过度可能导致模糊性,对区别性会产生一定影响;区分过度,同样也会影响概括性。因此,笔者以为要首先确立一定的标准,比如可以按照充当话题主语的论元角色变换情况来观照多义词的各个义项,或者按照动作本身的强烈程度来观照各个义项,再或者按照受事宾语的情况等来观照多义词的各义项,并把此标准贯彻下去,义项应该能够划分清楚。
总之,在处理多义词义项时,既要多考虑词义共时的存在状况,又要注意追寻每个词的本义,并在此基础上弄清其各引申义的脉络。然后按一定的标准进行适度的概括和归并,注意各义项的区别特征。
(二)关于“打”义项处理的尝试方案
1.“打”义项归并之理据
关于“打”的研究,相关文章达130篇之多,但是上溯探其本义及义项源流关系的仅有熊应标[8](P65-67)、周晓彦[9](P36—41)周远富[10](P23-26)等的寥寥几篇,且均有不足之处。比如熊文认为动作的强烈程度对“打”的词义引申起着核心的作用,并总结了义项引申的路径,这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周文一方面强调“打”的基本义限定了其所有义项只用于与手部运动有关的活动,这与其文中“打3”是思维言语发生作用的动作相矛盾;另一方面,其所规定的“打 1”“打 2”“打 4”所指的手部动作存在着撕扯不清的情况。鉴于此,笔者从上文所总结的历时及概括性和区别性两方面尝试对“打”的义项做一处理。③
《说文·木部》云:“朾,橦也。《说文新附·手部》云“打,击也。”“橦”即为“撞”,“木”旁和“手”旁常有混用,段玉裁以“木”写为“手”是隶变之常例。[11](P161)“朾”和“打”之间是否异体字,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但无论是“朾”和“打”,其撞击的本义是确定的。既为撞击,则必然要牵涉到施动者、借助的工具及技术、动作本身、受撞物、受撞部位及后果等几个论元,如下例:
他用木棒把小猪的头打伤了。
上句用论元来表示,即如下:

熊应标认为动作的强烈程度对“打”的词义引申起着核心的作用,并归纳“打”的词义引申途径为:

笔者以为“打”动作本身的强烈程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起意义上的变化,但并不是引领词义变化的核心。理由有如下三点:
第一,如果动作本身的强烈程度起核心作用,那么其他论元的变化就会在“打”的意义变化上起效甚微乃至不起作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设“A打了B”中,AB均为人,此时“打”为打架,而当A不变,B由人变为动物时,比如B为野猪,此时“打”则由打架义变化为打猎、捕获义。此处“打”意义的变化与动作的猛烈程度无关,因为AB为人时,A即便把B打死,“打”也不可能是打猎捕获。再如两个直接接触的物体A与B,假定A为一块石头,B为液体,A打B可以说是石头挤占了液体的空间,但如果A变为一根木棒,此时的A打B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木棒挤占了液体的空间,而只能说是木棒搅动液体。此时“打”的意义由挤占变化为搅动,而引起这个意义变化的并不是动作本身的强烈程度,而是A所发生的变化——由石头变成木棒。因此,笔者以为,论元表达式中,论元 1(施动者)、论元3(受动者)以及与论元3直接接触的论元2是关键论元,它们的变化,才是引起“打”意义变化的主要原因。
第二,如果动作本身的强烈程度起核心作用,那么这个引申的路径至少应能全面反映“打”这个动作在不同程度上所带来的变化,但是事实上,在程度加强时的“挤占”似乎并不能准确反映这种程度增强时所带来的变化。设有A“打”B,如A物体积小,而B物体积大,比如以针打人,撞击程度强时,从B物角度看,确可致使A物挤占B物一部分空间,但如从A物角度看,A进入B物体内,相当于A物发生了位移;而且与前述相反,当A物体积大,而B物体积小,撞击程度加强时,会使B物发生位移。此时从B物角度看,是B物位移,从A物角度看,A物如果停留在B物原来位置上,可以说A挤占了B,但在强烈撞击之下,A也有可能会停在另一个位置。此时,挤占就无从说起。由此可见,挤占似有不确定性,而位移却是必然存在。因此笔者以为“打”的词义引申途径当为:接触——撞击——位移。
第三,如果动作本身的强烈程度起核心作用,那么所有“打”的义项应能用“接触”“撞击”和“挤占”来归纳,但实际情况是,“打”有较多的义项显然并不能用这个来概括。比如熊文把《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打伞”归入挤占类还可勉强一说,而把“打手势”“打哈欠”“打嗝”“打官腔”“打比喻”等都列入挤占类,就明显于理不通,有悖其设计此路径的初衷。
其实,在“打”的多重义项中,完全从“打”本义直接发展而来的并不多,多数是通过相关性和相似性联想而间接得到。比如,由“撞击”义的“打墙”可以经相似联想到制造新东西,于是“打烧饼”“打造”产生;由肢体动作的“打手势”可以经相关性联想到与手势相关的拦车,于是 “打车”产生(当然,“打车”可以由打手势而来,也可以由位移而来);由位移义的“打跑”“打开”可经相似性联想到“打饭”“打水”——部分饭和水因“打”而从原空间转移到新空间;也可经相似性联想到“打灯笼”“打伞”等——静止的灯笼,一般只用“挂”或“提”(“提”可用于静止,也可用于移动),移动的灯笼一般才用“打”,“打灯笼”常和位移相伴随,“打伞”亦是如此(当然“打伞”也可理解为“伞”原有状态的改变);也可由实体的位移联想到抽象的位移,比如由正常人的位置到右派位置的“打右派”,由没有精神到有精神的“打精神”,有正常语言到官腔的“打官腔”等等。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比如“打杂”“打游戏”等,似乎无论如何也不能通过联想“接触——撞击——位移”来解释,唯一的办法只有通过对动词进行抽象使其上升到一个更泛化的层面,比如泛化“接触——撞击——位移”为“接触——处理(实施)”,上述论元表达式要调整为:

唯其如此,才能全面观照“打”的全部义项。有鉴于上述,笔者结合上节中所讨论的义项处理的2个注意点,拟从论元以及动词本身的变化,来尝试对《现代汉语词典》中“打”的全部义项做如下概括归纳 (这里仍然采用上文所列的25个义项):
论元1和论元3均为有生命体,由于主体的限定,“打”只有打架、打火热、打官司等,即《现代汉语词典》中的(3)(4)。义项可表述为人与人之间发生某种接触或交涉。
论元2和论元3均为无生命物体,二者直接接触,二者中被打烂的可以出现在表层,另一个与之碰撞的论元可不出现,比如蛋打了,碗打了,即《现代汉语词典》中义项(2)。义项可表述为因撞击而破碎。
论元1是人,论元3是无生命物体,可分为三个小类:一是生产设计类,即论元3从无到有,如打墙、打坝、打家具、打草鞋、打毛衣、打井、打信号、打介绍信、打车票、打证件、打电话、打草稿、打主意、打成本等,义项可表述为:借助工具或技术来制造、测算。如《现代汉语词典》中的(5)(6)(9)(10)(11)(14)(20)以及(13)中的“打雷”、(17)中的“打车票”,其中(10)可有制造和接触两解——用笔在纸上画问号、画格子以及用印章盖戳子,既可理解为纸上从无到有的,即“制造”新格子、新问号以及盖出新图样等,又可理解为笔、印章等与纸张的轻接触。因笔者偏前者,故本文列其在生产设计类中;(11)中不含“打冰”。二是转移类,即论元3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如打开抽屉、打开盖子、打饭、打油、打旁杈、打柴,打帘子,打伞等,义项可表述为借助工具或技术等使某物发生位移。如《现代汉语词典》中的(12)(13)(15)(16)(17)(19)条义项,其中(13)中不含“打雷”“打炮”,(17)中不含“打车票”。三是接触撞击搅拌类,如打鼓、打门、打包、打馅子等,即《现代汉语词典》中(1)(7)(8)以及(11)中的“打冰”。义项可表述为:借助手部动作及工具来处理某物。
论元1是人,论元3是事件,如打游戏,打杂、打球、打扑克、打炮等,即《现代汉语词典》中(21)(22)以及(13)中的“打炮”。义项可表述为:借助工具或技术来实施某事。
论元1是人,论元3是人的肢体、语言、精神等,如打手势、打官腔、打精神等,即《现代汉语词典》中(23)(24)(25)。义项可表述为:人的肢体动作或语言方式。
论元1是人,论元3是动物,如打鱼、打猎等,即《现代汉语词典》中的(18)。义项可表述为打猎、捕获。
论元1是人,论元3是标签称号类,如打烙印、打右派等。义项表述为:定上或贴上某种标签。
2.“打”义项归并之结果
归纳上述论元变化情况,“打”(动词)的25条义项就只有9条,即:
(1)借助直接的手部动作及工具来接触、撞击、搅拌某物:~门—~鼓—~馅子—~包—~冰。
(2)物体因撞击而破碎:碗~了—鸡飞蛋 ~。
(3)人与人之间发生某种接触或交涉:~架—~官司—~得火热。
(4)打猎、捕获:~ 鱼。
(5)借助力量或某些工具或技术使某物改变原状态或发生位移:~开—~饭—~粥—~油—~旁杈—~帘子—~柴—~灯笼—~伞。
(6)制造、生产、设计:~刀—~墙—~坝—~家具—~井—~毛衣—~草鞋—~草稿—~证件—~成本—~问号—~格子—~戳子。
(7)借助某些工具或技术来实施某事;~杂—~游戏—~球—~扑克—~炮—~call④。
(8)人的肢体动作或语言方式:~手势—~官腔—~比方—~马虎眼。
(9)定上或贴上某种标签:~右派。
三、结语
首先,《现代汉语词典》在处理多义词义项时,于概括性和区别性上存有个别瑕疵。比如《现代汉语词典》中“打”的动词各义项在交叉、包含关系以及义域范围上均有牵扯不清的现象。
其次,“打”的本义是撞击。撞击的强烈程度并非引领词义变化的核心。“打”的各义项均是经转喻或隐喻所引申得到的,其引申路径约有“接触——撞击——位移”和“接触——处理(实施)”两条。据此动词“打”的义项应由《现代汉语词典》中的25个归并为9个。
最后,多义词义项划分是否适当、义项间是否有足够的区分特征是决定辞书词义标注正确率的关键。要正确标注多义词义项,就必须根据词典编纂宗旨,既要考虑词义共时状况,即充分占有多义词在一个共时平面内所呈现出的包括分布在内的全貌及相关工具书中可供参考的全部释义,又要注意从历时追寻其本义,弄清其引申脉络,然后按一定的标准进行适度的概括和归并,注意各义项的区别特征。本文以动词“打”为例对《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多义词义项处理所进行的尝试,正是对上述处理方法和原则的贯彻。
注释:
① 本文参考主要文献:刘艳娟《〈现代汉语词典〉研究三十年》,山东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赵贤德《〈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释义问题商榷》,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1);周钟灵《略论〈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辞书研究,1980(1);张志毅《〈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的语文性》,辞书研究,1981(3);王楠《用语不同,作用有别——谈〈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中的“也作”“也叫”“也说”》,语文研究,2004(1);冯海霞、张志毅《〈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体系的创建与完善——读〈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国语文,2006(5);符淮青《关于〈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的讨论》,辞书研究,2014(6)。
② 关于多义词义项的研究,主要参考文献:肖航《词典多义词义项关系与词义区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1);赵越《义项分合问题补议》,语言文学研究,2009(7);林进展《多义动词义项距离与义项分合》,厦门大学学报,2012(5);杨凤仙《义项分合的原则》,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1)。
③ 在尝试对“打”义项进行处理时,主要参考文献:郑剑平《说“打”》,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4);祁保国《释“打”》,河套大学学报,2008(1);吴静《对“打”的多义性认知浅析》,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8(4);徐时仪《“打”字的语义分析再补》,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4);俞敏《“打”雅》,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1);罗晓春《“打”的意义演变及使用范围考察》,兰州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 “打call”是2017年出现的网络流行语,《现代汉语词典》中并无“打call”一词。此处是用其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