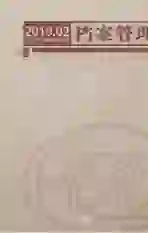论现代公共权力建构档案的合法性
2019-03-20谭倩
谭倩
摘 要:档案建构过程中渗透着权力因素,而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权力腐败和滥用对档案和档案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使得档案建构过程中公共权力的参与面临合法性危机。本文认为合法性是权力建构档案的起点,并从起源意义上的合法性、工具合法性、价值合法性三方面论述了公共权力建构档案的合法性,提出应通过制度建构、法律制约、意识形态认同三条路径共同确立和维系公共权力建构档案的合法性。
关键词:公共权力;档案;合法性
Abstract: The power factor exis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ves, and the corruption of power in the construction between power and archives h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archives and archival work. There is a crisis of legitimacy of the public power factor taking part in construction of archives. This paper argue that the legitimacy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public power constructing archives, and analyze the legitimacy in the meaning of origin, the instrumental legitimacy and the value legitimacy.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 three ways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the legitimacy of public power, which are institution building, law restriction and identity in ideology.
Keywords: Public Power; Archives; Legitimacy
1 引言
“没有一种政治势力不对档案加以控制,不对记忆加以控制。”德里达在《档案狂热》一书中这样说道,并认为档案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性范畴。[1]档案作为人类文明和社会实践的产物,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权力因素的干预、影响和作用,并从各个方面参与了档案的建构。在政治学和社会学视角影响下,档案建构中的权力因素也逐渐受到国内外档案学者的关注,并且有学者注意到了权力对建构档案的消极作用。在国内研究方面,张林华和蒙娜认为档案生成管理过程中来自权力的消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并从国家权力、职能机构权力、档案工作者权力三方面论述了权力因素的消极影响;[2]赵月霞认为权力对档案正义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来自国家通过档案制度维护当权者的利益、个人通过职业权力迎合当权者的需要。[3]不少欧美学者也注意到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会受到权力的干扰,从而影响社会记忆的真实性。
事实上,权力的扩张性和腐败倾向使得权力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权力腐败和滥用,即使是公共权力也伴随着谋取私利的可能性,从而对档案和档案工作产生较为明显的消极影响,使得档案建构过程中公共权力的参与面临合法性危机,并由此引发对档案客观中立性、档案正义和社会记忆构建等方面的质疑。这种合法性危机如果不能加以消解并逐渐加剧,可能会导致社会档案管理组织体系的崩溃。因此,只有从根本上确立现代社会背景下公共权力参与档案建构的合法性,才能使社会民众对公共权力的认识建立在正确、客观和善意的基础上,有效维护档案的客观中立性,并促使公众积极参与档案建构实践,形成民众与政府在档案建构实践中的良性互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档案建构过程中现代公共权力参与的合法性进行研究,分析权力参与的合法性基础和维护路径,是权力与档案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2 现代档案建构中的公共权力因素
公共权力是用以处理公共事务或满足公共需求的一类权力形态,它来源于公共区域全体成员的共同同意,因此体现的是公共意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府的形成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基于满足共同体内成员的共同需求而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因此公共权力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政治权力,是以合法性治理为基石的强制性力量,是国家机关运用其所拥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资源,对社会实施的支配力、强制力和其他国家行为能力。它的存在以维护社会统治秩序和公共利益为目的,权力主体是宪法和法律授权和规限的各类国家机构及其负责官员,而档案领域公共权力的主体可进一步理解为各级各类档案机构。这一权力类型由此在建构档案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目前,学界对于权力对档案的建构已经形成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即认为权力对档案的建构主要包括权力对档案观念的建构和权力对档案实体的建构两个层次。[4]首先,建构档案意识包括了建构档案工作者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大众的档案意识。档案是确立和维系权力的重要资源,公共权力出于确立其合法性地位以及延续其统治的需要,通过权力运作及经年累月的实践和反复演示,在社会大众和档案工作者中树立了“档案是客观的、中立的,在还原历史面貌方面是具有权威性的”这一认识。之后,这种观念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通过国家教育和文化传播两种方式传递给了广大民众,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建构了社会的档案意识。其次,权力还通过建构档案工作的原則、制度、方法和程序等上层建筑来实现对档案实体的影响。档案制度涉及档案机构设置、档案人员安排以及指导、规范档案行为的系统性行为规则,公共权力通过对档案制度和档案工作各个环节的建构,影响着档案工作的原则、方法、程序和惯例,使得无论是档案的形成、整理、鉴定还是开放利用都体现着公共权力的意志。
3 合法性:公共权力建构档案的起点
3.1 起源意义上的合法性。人类社会为什么必须通过运用权力的方式进行社会管理呢?由于生存规律与生活状况的约束,人们只有在相互依赖的社会群体中才能生存与发展。然而,由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具有不同的利益与愿望,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分歧与冲突,所以,如何实现社会秩序就成为人类社会中的首要问题。[5]任何社会秩序的实现都离不开强制性力量的运用,所以,在特定社会中通过运用权力来构建社会秩序则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方式。在古代封建社会,帝王们为了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而宣称自己为神的化身或子嗣,世俗统治者代表“上帝”或者“天”进行了早期的档案管理活动,档案仅体现当权者的个人意志。然而,这种外在于人类权威的神圣权力,不是从人类自身出发寻找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并且往往通过暴力和强制权威等形式实现统治与管理,本质上来说是不具备社会公共性的。事实上,与主权国家的形成同步的人民主权思想的诞生才意味着现代公共权力真正具有合法性依据。
人民主权理论反对将外在于人类的神权当作世俗权力的来源,主张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人民的同意,认为社会成员应当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人民主权思想下的权力才因此具有了实质意义上的社会公共性。在人民主权思想下,政府权力实际上是一种委托权,政府机关的每一项职权都可以溯源至作为国家主人的民众享有的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权,又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委派给其代理人具体实施。在现代社会,档案是国家全体民众的共同财富,档案从保障统治集团的特权变成了维持国家机关和社会各方面运转的积极力量,应该为整个社会发展服务成为各国的共识。在这种思想转变的背景下,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通过权力的运作积极组建档案工作机构、完善档案制度、创办档案高等教育,迅速建立了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档案工作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挥作用,档案的公共性和服务性越来越彰显,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实现了档案从体现统治者个人意志到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的转变。从社会契约的角度来看,这种来源于全体成员共同同意的公共权力形成的服从不同于暴力所获得的服从,因此源于人民授予和认同的现代公共权力对档案的建构具有了起源意义上的合法性。
3.2 工具合法性。马克斯·韦伯是工具合法性的典型代表,他把合法性分解为工具合法性和价值合法性两类。所谓工具合法性,是指行动基于对达成目的的可资运用的手段的估计,行动目的通过计算和预测后果有条件地实现。在工具合法性行动中着重考虑的是手段对达成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强调政权的工具性价值(如维持政治秩序、提供公共物品、捍卫民众利益,等等)。[6]现代公共权力建构档案的工具性价值首先体现在对档案工作秩序的维护。受权力结构和权力导向的制约,社会中的个人难以对档案进行有意识的收集和系统的管理,而以国家权力为代表的政治力量才有系统化保存档案以及满足大规模档案利用需求的能力。由国家权力保障的档案工作是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在政策规范、资金投入、技术保障、人力支持等方面均有国家作为强大的后盾和支持,能够保障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收集和管理社会各方面各层次的档案资料。[7]无论是我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实行的集中式档案管理体制,还是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实行的分散式档案管理体制,都在不同程度上保证了各级档案工作的有序开展,保障了国家层面的档案收集、整理和保管,维护了档案工作秩序。其次,现代公共权力建构档案的工具性价值还体现在档案资源的开放利用,在公共权力的运作下,以往只掌握在统治阶层以及依附于统治阶层的少数知识分子手中的档案资源在更广泛的服务领域上实现了其社会功能的发挥,档案的利用范围大大扩展、利用对象更加广泛,使得档案工作真正成为一项社会性的工作,有力捍卫了公众利益。
3.3 价值合法性。不同于韦伯对工具合法性的强调,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还有其客观性的一面,有自身所内含的某种价值。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的统治仅仅具有形式的合法性还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具有实质的合法性,即包含着价值的肯定,权力合法性不应纯粹从经验性、技术性来寻找其合理性论证。他要求对一种权力是否具有合法性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追问,也就是说,权力只有包含着被认可的类似终极价值的实质内容,才是权力合法性的最好证明。[8]现代档案建构档案的价值合法性也理应落脚在对档案“客观中立性”的维护、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构建社会记忆等维度上。首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虽然档案实体是伴随社会实践活动产生的直接历史记录,但档案工作是人类社会有意识、有计划地利用各种物质手段来保存信息记录以备查考的过程,这其中渗透着档案价值观的参与。在古代封建社会,受档案一元价值观念的影响,档案“资政”的工具价值被强调,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档案的社会价值逐渐得到认识,体现共同意志的公共权力促进了档案社会价值的发挥。这种档案价值观不再仅代表某一统治阶层的利益,而是体现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价值追求,使得档案和档案工作具有了相对意义上的“客观中立性”,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其次,在社会记忆视角下,国家必须承担起保存和传承历史文化的责任,构建社会记忆,为社会成员提供情感维系、身份认同和根源感。但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下,尤其是社会变革的环境下,社会公众一般更关注于自身的人身財产安全,很少有人有意识地留存档案和文化典籍。这时,国家层面对档案的收集、整理和保管为社会记忆的建构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档案资源。出于对档案相对“客观中立性”的维护、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构建社会记忆的价值追求,公共权力对档案的建构具有了实质意义上的价值合法性。
4 公共权力建构档案的合法性优化路径
4.1 制度建构·合法性优化的程序要求。权力合法性的确证绝非一次能够完成的,即使一种权力被确认具有起源意义上的合法性,其权力实施过程的合法性问题也必须受到重视,否则权力的合法性就成了一座空中楼阁。公共权力合法性的确立需要建立在合法性程序的基础上,这一指向是面向实践和技术层面的,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公共权力应如何行使、如何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和公共权力应采取的适当形式,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建构建立一个维系权力稳定运作的机制。首先,如何合理运用权力实际上涉及如何表达与实现公共意志的问题,因此制度建构必须以确保公民的协商和参与为基础,将公民的合理协商行为贯穿整个行政权力运作过程。具体来说,依托现有民主机制的管理体制,档案机构应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在程序上尽可能地推进开放和公众有效参与,发动更多的社会主体包括那些以往被权力边缘化的群体参与到档案管理与社会记忆的建构中来,实现从政府单方面行政向社会联合行动的转变。其次,制度的建构还需要体现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需要构建以公众监督为核心,档案机构、社会组织为保障的联合监督机制,使权力主体的决策过程和权力运行过程变得公开透明,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
4.2 法律制约·合法性优化的法理保障。权力的公共性与它谋取私利的可能性总是相伴随着的,会经常性地出现掌握权力的人们利用权力攫取个人的或小集团的利益以及渎权、滥权等行为,这不仅违背权力的公共性质而且也会造成管理效率的下降。所以,需要对权力进行制约,而法治正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种要求的管理方式,法律是公共权力运作合法化的通道,只有对权力实施制约,才能保障公共權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及保证权力能够起到维护公民权利和保障公民权利的作用。法律的制定与完善需要充分考虑其制定的合理性和实施的有效性,一方面以明确的法律条文为支撑对参与档案形成和管理的权力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划分和限定,为权力的行使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法律条文需要严格规定档案的形成、管理和利用要求,档案工作人员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使权力行为在法治框架内进行。随着我国档案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档案收集、整理、保存、利用也会越来越规范,档案内容质量及真实客观性也会得到自下而上层层把控,从而有效维护和保障公共权力建构档案的合法性。
4.3 意识形态认同·合法性优化的价值追求。公共权力对档案的建构如果仅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是远远不够的,在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日益凸显的今天,不论工具理性如何张扬,权力合法性的获得和维系也脱离不了以意识形态认同为核心的价值追求。公共权力合法性认同并非来自掌权者的自封,也非来自强权和暴力等权力工具性的攫取,关键在于它是否得到广大社会成员的信服与认可,因此公共权力建构档案的合法性优化路径也最终应落脚到寻求广大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认同。只有建立在成员认可和赞同基础上的公共权力才具有合法性基础,才有可能得到广大社会成员的忠诚。为了获得公众的意识形态认同,公共权力机关应该积极培育社会档案意识,通过国家教育和文化传播等方式,让社会大众意识到档案在维护历史真实性和构建社会记忆中的积极作用,并通过档案理论研究和档案实践工作的持续改进,加深公众对档案和档案价值的认识,在社会中建构积极的社会档案意识。只有当社会公众真正意识到公共权力对档案的建构是体现人们的共同意志和维护人民的利益,民众与政府之间才可能形成有效的、声势浩大的“互动”,在共同发展中向共同的价值追求前进。
参考文献:
[1]Jacques Derrida. Archive Fever:A Freudiam Impression.[J] diacritics,1995(2):10-11.
[2]张林华,蒙娜.权力因素在档案建构社会记忆中的消极作用及其应对策略[J].档案,2007(05):7-10.
[3]赵月霞.论权力对档案正义的消极影响[J].档案管理,2017(05):7-10.
[4]陆阳.论权力对档案的建构[J].浙江档案,2009(12):26-28.
[5]彭斌.认真对待权力——关于权力的正当性与权力运用方式的合理性的思考[J].学海,2011(05):119-125.
[6][美]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8.
[7]王静.权力选择与身份认同: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的两个维度[D].山东大学,2017.
[8]姜朝晖.权力论:合法性合理性研究[D].苏州大学,2005.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来稿日期:2018-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