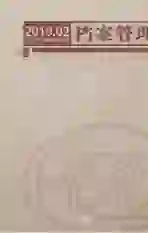论权力建构视野下档案职业活动主客体的角色转变
2019-03-20李永波
李永波
摘 要:随着权力与档案的关系逐渐成为档案学界的研究热点,档案职业活动中档案管理者和档案实体的传统角色与定位开始受到一些档案学者和历史研究者的质疑。本文从档案职业活动主客体两个角度出发,在探讨两者角色变化的同时,阐明两者在面对质疑时应如何完善新的角色定位,以突破权力构建档案时造成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权力;档案;档案工作者;档案职业活动
Abstract: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archive having become a heated discussion in archival field, some archival scholars and historians question the traditional roles of archives and archivists.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negative effects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this thesis not only discusses the change of roles about archives and archivists, but also demonstrates how they can refine the location of their roles confronting incredulities from archival circle.
Keywords: Power: Archive; Archivist; Archival Professional Activity
权力是社会科学中的基本概念,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近些年,档案学界对于权力与档案之间关系的探讨为我们认识档案职业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笔者认为,作为档案职业活动的主体和客体,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实体自产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权力关系的建构与影响,两者传统的、“被视为当然”的角色定位需要得到转变与重塑。
1 传统:对档案职业活动主客体角色的固有认知
1.1 档案:客观中立的真实记录。在传统的观念中,“档案是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性信息”[1],由于它承载了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在办理事务的过程中直接生成的原始信息,因而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现存文献中最为客观真实的记录,具有良好的可信性以及极高的证据价值和情报价值。
早在20世纪初,英国档案学者希拉里·詹金逊就指出:“档案不是为了后代的利益或为后代提供信息而拟制的……档案是在行政管理或公私行政事务过程中拟制或使用的,并构成该事务过程的一部分;事后由该事务的负责人或其合法继续人加以保存以备查考的文件。”[2]从现代档案学的角度来看,虽然詹金逊在对档案下定义时忽略了一些文件转化成档案的必备条件,但他的这种定义却试图将档案形成者的主观意志从整个档案形成过程中抽离出去,尽量减少这个过程中主观因素对档案的影响,从而保证档案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到了20世纪中后期,一些档案学者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后逐渐认识到,文件在完成自身的业务目的之后,只有那些被认为是今后具有查考和研究价值的一部分才能成为档案得以长期保存。这种归档标准的确定,依据的也是对于档案具有客观中立性的认识:由于档案能够提供形成者业务活动的原始记录,在日后查考和研究时,档案对于历史面貌的还原也将更具有权威性,這种权威的“历史重现”才能成为可信度更高的证据。
综观以上档案学者的思想认识,不难发现档案客观中立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档案学者的一种共同认知。
1.2 档案工作者:可信任的历史信息保管者。基于对档案原始记录性和客观中立性的认同,传统的、固有的观念认为,档案工作者是从中立的角度出发,对档案实体进行客观公正的整理和保管。正如詹金逊所言,档案工作者“其信条是证据的神圣;其任务是保护他负责的档案中的每一寸证据;其目标是毫无偏见地为所有求知者提供知识财富”[3],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像一座隐形的桥梁,将档案实体中蕴藏的大量历史信息客观地呈现在档案利用者面前。
可以看到,在传统的档案意识里,为保证档案信息的可信性和神圣性,档案工作者在进行职业活动时不能对档案施以任何形式的人为干涉,档案工作因此也是不带有任何偏见的。再加上当时人们对档案客观中立性的固有认知,档案工作者一时成为“现代社会真理最无私的信徒”,人们对档案工作者的信任也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
2 现实:权力建构下的档案职业活动主客体
马克斯·韦伯关于权力的论述很经典,他认为:“权力”是在一段社会关系中,一个人或很多人哪怕遇到其他主体的反抗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机会。简而言之,权力就是一段社会关系中即便遭到抵制和反对仍能执行预想行动的可能性。基于对权力的这种理解,下文将阐述权力如何构建档案实体和档案工作者,从而促成他们的角色转变。
2.1 档案:权力贯彻自身意志的文字产物。通过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到在传统的档案观念中,人们对档案具有客观中立性似乎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但实际上,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和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的档案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权力对于档案的干预和建构。例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是档案的社会政治侧面,历史上的档案话语正是(通过)扩展、分裂、调遣知识和权力,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4];而雅克·德里达也认为,“历史的书写不可避免地受到制度,尤其是政治因素的影响,这种介入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对档案的客观性,也就是它对事件原始状态的描述应该有另一种维度的思考:制度化空间从什么角度介入了档案的形成、保管及利用,使之呈现何种面貌,后人又如何根据档案来塑造文化记忆和社会记忆”[5];受此启发,特里·库克就曾鲜明地指出,“档案被制作者以及档案工作者进行了深度干预,档案馆是权力、记忆和身份论争的地方”[6]。至此,权力这种主观因素在档案中的建构作用越来越被档案学者们重视,在整个档案职业活动过程中,权力影响力逐渐显现,传统档案观中档案所具有的客观中立性也因此受到诸多质疑。
第一,档案的形成过程是权力意志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档案作为机构或个人业务活动的原始记录往往被认为具有无可比拟的客观中立性。但实际上,权力已经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干预整个过程。首先,权力会干预档案的内容。正如兰德尔·吉默森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是由统治者创造的”[7],在档案的前身——文件的产生阶段,权力机构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人为地对文件的内容进行选择和干预,决定特定内容的记录顺序和记录方式。而在归档阶段,权力机构更是可以将对自己不利的文件进行销毁或掩盖,不让相关内容成为档案保存下来,这些具体的操作程序处处都体现着权力的意志。其次,权力会干预档案的类型。有学者指出,档案的“类型和功能并不是自然形成和随意变化的,而是取决于政治行政权力的需要”[8],面对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权力在进行自我调整的过程中,一些新兴类型的档案应运而生,例如民生档案、医疗档案、廉政档案等,这些不同类型的档案功能各异,但都有效地维护了权力的自我完善和正常运行。
第二,档案的管理环节受权力意志的影响。在档案管理过程中,权力最为显著的干预主要体现在档案的收集和鉴定两个方面。在收集档案时,权力的拥有者具有档案的收集权和所有权,能够通过权力控制和审查决定档案的收集倾向,一些与权力拥有者利益诉求不一致的档案(例如边缘人群或地位较低人群的档案)不会被纳入档案的收集范围。以这样的收集形式构建的档案资源体系必然是以权力主体为核心的,权力就这样通过监督和影响档案的收集,实现了贯彻自身意志的可能性。而在鉴定档案时,由谁鉴定、为谁鉴定、以何种标准鉴定更是不可避免的权力问题。比如,早期的“行政官员决定论”将档案鉴定的权力赋予行政官员,这就使得行政官员同时具有档案形成者和档案鉴定者两种身份,在决定档案是留存还是销毁时权力就有了更合法更便捷的运行空间。而来源标准虽然看重的是文件形成者,但文件形成者在社会中的权力地位和参与的业务活动直接关系到文件是否能够被归档以及归档后档案的密级和保密时间。也就是说,“立档单位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越重要、级别越高保存价值就越高,这实际上是权力的主体和级别决定了档案价值的大小”[9]。
第三,档案的开放受权力的制约。档案的开放是档案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前提,与权力的关系尤为紧密。权力对档案开放的制约主要表现在档案是否开放和开放程度两个方面。档案是保密还是开放,这本身就体现了权力的选择。在权力的制约和干预下,档案的开放活动必须符合权力主体的利益诉求,满足其进行政治统治的需要,那些威胁到权力主体的利益和统治的档案必然无法得到开放。近年来,社会公众对于档案的利用需求越来越迫切,对档案开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档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密、向谁开放、程度如何等,都需要服从于权力主体的利益诉求和统治需要。
2.2 档案工作者:权力贯彻自身意志的执行末梢。和档案一样,档案工作者的客观中立性也受到档案理论研究界的质疑与反思。其实通过回顾整个档案职业活动过程不难发现,在档案工作的具体环节中,档案工作人员可以轻松实现对于档案实体的控制。正如美国档案学者兰德尔·吉默森所言,“通过对诸多文件进行有选择的留存与保护,档案工作者影响着社会成员对于历史记忆的共同理解”[10]。即使档案工作者将客观中立作为自己的工作准则和信条,他们在进行档案职业活动过程中仍然不可避免地输入自己的价值、经验和教育,映照出各种外部压力,他们决定哪些社会记忆传递给后人,哪些记忆被掩盖、淡忘,自身主观色彩对档案职业活动的影响在所难免。
另外,档案工作者是带着被建构的观念从事档案职业活动的,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等都受到權力的干预,他们在工作中所执行的方法和原则也都由权力主体事先规定,处处体现着权力的声音,档案工作者需要做的只是遵循这些规定而已。从这个层面上说,档案工作者在档案职业活动中想要做到绝对的客观公正是不可能的,档案工作者不再是客观中立的保管者,反而更像是权力贯彻自身意志的执行末梢。
3 重塑:对权力建构档案职业活动主客体的突破
正如前文所述,随着权力对档案实体和档案工作人员的建构逐渐为档案学者所熟知,档案职业活动主客体的客观中立性也随之遭受消解。在这种消解中,权力的建构不可避免地给档案职业活动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减少这种消极影响带来的危害,对于重塑档案实体与档案工作者的角色定位、深化权力建构视角下对两者的认识和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3.1 维护档案形成主体多样化,保障多元主体利益诉求。在权力的建构下,权力主体是档案的单一形成者,档案基本上只能反映权力主体的利益诉求。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档案的形成主体和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传统的以权力主体为中心构建的档案资源管理模式已经难以维系。面对复杂多样的人类活动,仅维护权力主体的档案利益势必会造成人类社会记忆的缺失和断层。实际上,“在社会权力结构之外,甚至是一些被权力边缘化的群体也有建立档案体系、建构群体记忆的需要,且这些群体的记忆是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不该被排挤甚至忽略”[11]。因此,在构建档案资源体系时充分考虑到权力主体层次以外的其他阶层,多倾听弱势群体和边缘化人群的声音,克服权力建构档案带来的倾向性,兼顾多种档案形成主体的利益诉求。
3.2 推进档案资源多角度开发,实现与公众的对接互动。在开发档案资源,提供利用服务的过程中,必须突破早期以社会权力主体为中心的单一利用模式,除了让档案帮助社会权力结构实现自身利益、巩固统治地位之外,还应该积极关注权力结构之外的普通社会公众的档案利用需求,尽量减少档案利用服务上的限制,扩大档案服务的覆盖人群,依法保障公民使用档案的基本权利;听取社会公众对于档案工作开展状况的意见和建议,使档案资源与社会公众实现良性互动。
3.3 明确档案工作者权责范围,尽量保证工作客观中立。在档案职业活动中,档案工作者作为活动的主体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权力的干预下,客观中立只能是相对的,所以档案工作者在扮演好保管者角色的同时,更“要成为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忠实捍卫者,成为信息前沿的积极干预者,为有真实、完整的历史投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12],遵守档案工作伦理与准则,不受社会权力阶层不当干预的干扰,深刻认识到自身所从事的职业对于构建社会记忆的重要作用,采取积极行动尽量维护档案工作的客观中立性。
3.4 加强权力运行的公开监督,增强档案工作的透明度。不受制约的权力容易导致腐败,权力体系对档案职业活动的不当干预会导致档案的客观中立性遭到损害,只有公开透明的权力运作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档案造假和档案篡改的可能。知情是打破权力独断权威的关键所在,信息公开能够保证社会公众对于行政信息的知情权,使权力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过程更加公开透明,并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增强档案工作的透明度,不但能够使档案利用者充分了解档案工作,还能促进档案工作者不断审视和反思对自身职业权力的运用,在对待档案材料时尽量做到公平公正,维护社会公众对于档案职业活动的信任。
在权力建构的视角下,档案和档案工作者今时的角色早已不同于往日。面对对于其客观中立性的质疑,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突破权力对于档案职业活动主客体的建构,从而减少两者的角色转变带来的消极影响,促进档案职业活动的有序进行。
参考文献:
[1]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
[2][5]曲春梅.解构与重建:后现代背景下对档案职业公信力的思考[J].档案学通讯,2016(3):8-11.
[3]特里·库克.四个范式:欧洲档案学的观念和战略的变化[J].档案学研究,2011(3):81-87.
[4]韩平.福柯的权力观[D].吉林大学,2005.
[6]Joan M. Schwartz, Terry Cook. Archives, Records, and Power: The Making of Modern Memory [J].Archival Science, 2002 (2):1.
[7]兰德尔·吉默森,马春兰译.掌握好档案赋予我们的权力[J].档案,2007(3):40-43.
[8]陈建.论权力与档案形成的相互建构[J].档案管理,2017(5):4-6.
[9]陈建.论权力与档案管理的相互建构[J].档案管理,2017(2):8-10.
[10]Randall Jimerson, Archivists and the call of justice [EB/OL].
http://faculty.wwu.edu/jimerson/ArchivistsandJustice.htm.
[11]王静.权力选择与身份认同: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的两个维度[D].山东大学,2017.
[12]张林华,蒙娜.权力因素在档案建構社会记忆中的消极作用及其应对策略[J].档案,2007(5):7-10.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来稿日期:2018-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