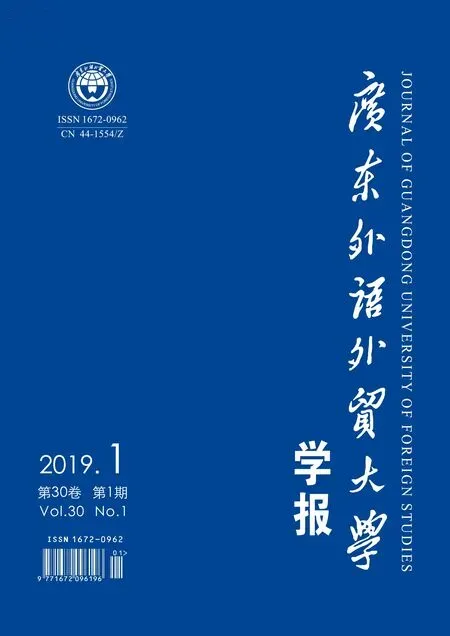论术语narratology的统译:叙事学
2019-03-18江澜
江 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图书馆, 广州 510420)
1969年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托多洛夫(T. Todorov,1939—2017)提出法文术语narratologie(德译Narratologie,英译narratology),其实作为学科的叙事学在1966年就已诞生,并可以追溯到元叙事学(meta-narratology)时期(1910—1965年)。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这门独立学科,却对术语narratology没有形成公认的译法。因此,有必要从这个术语的汉译之争谈起,通过分析这个术语的特征、历史与词源,甄别出术语narratology的正确译法:“叙事学”。
一、汉译之争
关于术语narratology,谭君强的译法有变化:在译著《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2003)里则兼用“叙述学”与“叙事理论”,在专著《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2008)里则通译“叙事学”。针对术语使用的混杂性,赵毅衡撰文《“叙事”还是“叙述”?——一个不能再“权宜”下去的术语混乱》,总共列举了八种术语混乱,并分析了从众原则、使用方便性与学理层面等问题,然后主张一律使用术语“叙述”(2009)。针对赵毅衡的一刀切,申丹(2009)撰文《也谈“叙事”还是“叙述”》,从从众原则、学理层面、使用方便性等方面进行客观分析,主张“区分对待”:叙述是联合或并列结构,指称表达层面的叙述技巧,如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2004);而叙事是动宾结构,同时指涉讲述行为(叙)和所述的对象(事),如申丹、王丽亚(2010)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
从这个术语的汉译之争来看,申丹的反驳针对性强,论证充分,尤其是在从众原则与使用方便性方面,有待深思的是学理层面的分析与建议。申丹从托多洛夫提出的术语narratology(1969)以及“故事”与“话语”的二分法切入,思路极对,只不过尚未深究作为叙述对象的事件及其内在的事件性,因而将叙事文的“故事”与“话语”——像托多洛夫与写《故事与话语》的查特曼(S. Chatman)主张的那样割裂开来,将侧重“话语”——如热奈特(G. Genette)——的术语narratology译为“叙述学”,而将侧重“故事”——如普洛普(V. Propp)——或兼顾“话语”与“故事”——如普林斯(G. Prince)——的术语narratology译为“叙事学”。其中,将术语narratology译为“叙述学”可疑,因为热奈特的研究虽然侧重话语,但是话语是用来叙述事件的,即事件是话语成为叙事研究对象的前提。脱离事件,孤立研究话语,就会转入语言学的范畴。对于叙事学而言,即使研究话语,那也是为了理解事件甚或整个叙事作品。因此,即使在热奈特这个极端个案中,术语narratology也同事件和事件性休戚相关,理应译为叙事学。
二、特征
不难发现,这个术语的汉译之争牵涉叙事作品的内在特性,尤其是叙述性与事件性。其中,叙述性是叙事的本构特征(Schmid,2014:251),这是没有争议的,争论的焦点是事件性。
事件性源于事件。在《叙述学:叙述理论导论》中,巴尔(M. Bal)(2003:219)把事件界定为“过程”,更确切地说,“由行动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的转变”。而施密德(Wolf Schmid)(2014:15)则进一步把叙事定义为“状况变化的表述”。可见,表述或叙述的对象就是“状况变化”,只不过不是所有的状况变化,而是在文学作品中不可忽视、并满足一些特殊条件的那些状况变化,即事件:“事件是状况的变化,以现实性与结局性为前提”。首先,现实性就是事实性,在虚构世界的框架内,愿望、想象或梦想的各种变化不构成事件,但是愿望、想象或梦想本身可以是事件;其次,构成事件的那些变化不是表示开始的动词,即不仅有开端,不是意动,也不仅是试图,也不是持续的,不仅处于执行的状态,而且还是有结局性的,即在文本各自叙述的世界里都会到达一个结局。在事件的定义基础上,施密德(2014:15)定义了“事件性”:事件性是事件具有的分层级的性质,即层控性。
作为分级性概念(张新军,2011:88),事件性有强弱之分,而这种区分取决于符合施密德述及的那些准则的程度。其中,判定事件性的第一个基本准则是重要性。一方面,叙述的那些状况变化必须具有重要性,否则不具有事件性。另一方面,重要性是相对的。以契诃夫(Anton chekhov)的《事件》为例,对于小孩而言,猫产仔已是最重要的大事,而狗吃光猫仔则是毁灭性的;不过对于成人来说,这些事都无足轻重。而不可预测性则是判定事件性的另一个基本准则。在叙述的世界里,叙述内容不一定要违反规约与越雷池,但一定要背离读者的期待。譬如,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新娘》里,在筹备好的婚礼前不久新娘逃婚。
此外,还有三个判定事件性的重要准则:结果性、不可逆性与不可重复性。其中,结果性就是行为主体的思想与行动要有结果。即使故事采用开放式结尾,解释者也可以从它的潜在性挖掘出现实性,赋予状态变化以故事本身尚未创造的结局性与结果性。譬如,在契诃夫的《文学教师》里,尼基丁向玛霞求婚成功,不过他意识到这是定期造访女主人公府邸的结果。由于觉醒,尼基丁想逃离平庸的幸福,以便获得写作的成功。叙述至此中断,构成开放式结尾。不过,可从觉醒的思路推断,尼基丁势必将思想付诸行动,而行必果。不可逆性是另一个重要准则,指思想与行动的决定不可反转。譬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Fyador Dostoyevsky)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皈依的人不会回到无神论的状态。作为第三个重要原则,不可重复性要求叙述不同性质的变化,否则,叙述就缺乏事件性。譬如,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忧伤》里,女主人公普列杰尼科娃虽然与不同的几个男人结婚,但是她的本性与生活毫无改变。在每一段婚姻里,她都围着丈夫转,重复地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这种重复性极大地降低了小说的事件性(Schmid,2014:17-19)。
值得一提的是,巴尔(2003:5)把确定事件性的规则称作“事件的逻辑”。在叙述中,事件的逻辑分为两种:时间关联与非时间关联。时间关联,包含时间的次序与因果的次序。其中,叙述性的最小定义只需涉及时间的次序。而非时间关联的原则是等值或等价。在叙事文本里,尤其是在装饰性叙事散文——如死侃——里,可观察到的是在“故事”与“话语”层面上理据的形式等值与主题等值(Schmid,2014:9-11、161-62)。
可见,尽管事件性基于依赖于解释的归因判定,因为对于面对状态变化(即事件)的主体——包括主人公、虚构叙述者、虚构读者、作者、抽象读者与具体读者——而言,状态变化的事件性会截然不同,可是在叙事作品中事件不仅客观存在,而且还会或多或少地具有事件性。即使是主张把术语narratology译作“叙述学”的赵毅衡(2013)也无法回避叙事作品里的事件,不仅探讨事件,而且还认可“叙事诗”的提法:除了叙事诗,还有叙事散文。因此,在不容忽视叙事作品的事件与不可抹杀事件性的语境下,术语narratology理应译为“叙事学”。
三、历史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叙事学有着自身的发展历史。大叙事一般把叙事学分成三个阶段:叙事学的发轫阶段、经典叙事学阶段与后经典叙事学阶段。弗鲁德妮克(Monika Fludernik)利用大叙事的线性结构,分别将俄国形式主义(20世纪10、2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经典叙事学视为叙事学的童年、青年与成年。由于弗鲁德妮克的划分明显受到大叙事的误导(Martínez,2012),舍纳尔特(Schönert,2006)把叙事学史细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元叙事学阶段、经典叙事学阶段、叙事学转向阶段与新叙事学阶段。
尽管叙事学家们的阐述略有不同,可元叙事学阶段(或“叙事学发轫阶段”)与经典叙事学阶段(20世纪60、70年代)有个较大的共同点:叙事研究对象囿于文学(尤其是虚构叙事散文,如小说),因而具有叙述性、事件性与虚构性(Schmid,2014:31-43)。由于事件性的存在,把术语narratology译为“叙事学”不成问题。
不过,在叙事学转向阶段(1980—1995年)和后经典叙事学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人文学与文化学研究的新发展,叙事学的各种原因、功能与范围已根本改变。譬如,在叙事学转向阶段不仅批判和解构经典叙事学,而且还发现电影、历史编纂学、圣经文本、法律实践等非文学领域的叙事。又如,在后经典叙事学阶段,叙事学向顾及文化、政治与认知语境的特异性的后经典叙事学拓展或修正,产生更加符合文化理论的普遍意义的新叙事学,如“大统一场叙事学”(Sommer,2012)。总之,在大变化的语境下,术语narratology的内涵与外延都已经扩展。当今的叙事学具有三大新特征:跨文类、跨媒介与跨学科。因此,舍纳尔特提出广义叙事学,不过,不是用广义叙事学取代别的叙事学(赵毅衡,2013),而是把广义叙事学与狭义叙事学相提并论,因为两者的应用领域不同。其中,狭义叙事学用于以下三个领域:(1)叙事理论(如小说理论):作为面向理论的叙事学,它的基础理论可能源于哲学、人类学或文化理论、认知理论、交际理论、语义学、文本理论与语言学;(2)叙事史(尤其是叙事散文的体裁史):作为面向历史的叙事学;(3)叙事文本或叙事的分析与解释:作为应用叙事学。而广义叙事学则用于跨学科实践:(1)作为全面文本理论的部分观点;(2)作为文本分析与解释的探索法与工具;(3)作为系统发展的描述模式;(4)作为跨学科的知识体系。
不难发现,舍纳尔特的狭义叙事学同前述的元叙事学和经典叙事学差不多,因此,术语narratology理应译为叙事学。至于广义叙事学,它在本质上是一门科学。所谓“学”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整体。尽管与狭义叙事学相比,在理论、方法、模式、知识体系等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可这属于“学”这个整体的内部发展,在术语的翻译时并不受影响。影响术语翻译的是造成这些差异的源头因素:叙事研究对象的扩大。除了狭义的虚构作品,包括跨文类的(如叙事剧)与跨媒介的(如电影与漫画),还有纪实作品,包括跨媒介的(如图片叙事)与跨学科的(如法学叙事),甚至还有介于虚构与纪实之间的虚构真实作品,如互动的游戏叙事(Matuszkiewicz,2014),以及最为复杂的电视叙事,既包括虚构的连续剧,又包括纪实的视频,如纪录片与新闻报道。在这些广义叙事中,大多数都叙述虚构的、事实的或虚构真实的事件,而且都具有较高的事件性,所以术语narratology译为“叙事学”也无可厚非。
此外,除了前述的“事”,叙述对象还有“理”,如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的教诲诗《物性论》。依据传统文艺理论,说理的教诲诗也属于叙事文学,因此并不影响术语narratology的翻译:译成“叙事学”即可,不必译成“叙理学”。事实上,如上所述,叙事学本身就是说理或学理探究,包括理论建构方面的,如可能世界叙事学、认知叙事学与空间叙事学,也包括方法论的,如语境叙事学。
总之,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在叙事转向之前还是之后,无论狭义还是广义,无论研究对象是虚构作品、纪实作品还是介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作品,术语narratology都该译为“叙事学”。
四、词源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术语narratology又该如何译?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从争议的关键词“叙述”与“叙事”说起。
德语Diegesis可以追溯到希腊文διZrησιH。在柏拉图的《理想国》(Staat III,392d)中,这个概念指称诗人的“单纯叙述”,与主人公话语的摹仿叙述相对。《文艺对话集》的译者朱光潜认为,单纯叙述属于间接叙述,而摹仿叙述属于直接叙述(柏拉图,1963:47)。
当然,在narratology这门学科中,Diegesis有别于古代修辞学中的意义。新概念叙述由电影叙述的理论家索里奥(Etienne Souriau)于1951年引入,他把diégèse理解为艺术作品(尤其是电影)中所表述的世界。广义来说,Diegesis指所叙世界,对应的德语形容词diegetisch意为“属于所叙世界”。
依据施密德的交流叙事框架,“所叙世界”是叙述者虚构的世界,属于叙述者交流层面,或者是一些叙事理论家——如瑞安(Marie-Laure Ryan)——提出的“可能世界”(张新军,2011:8-9)。在这个世界之内是人物交流层面的“引用世界”,而之外则是作者表述的文本世界,属于作者交流层面(Schmid,2014:44、46)。可见,与叙述密切相关的是叙事研究对象:叙事文本(narrative text)或叙事文(narrative),包括中介的叙事文本与摹仿的叙事文本。
舍纳尔特高度认同托多洛夫的二分法,把叙事文本研究对象确定为“故事”和 “话语”(即如何讲故事)。申丹对“叙述”与“叙事”的考察也是从托多洛夫的二分法切入的。撇开“叙事”的意思是“记述”或“叙述”“事情”不说,从《古今汉语词典》(2000)与《现代汉语词典》(2002)来看,即使是“叙述”也同“事情”不可分割:“叙述”是“对事情的经过做口头或书面的说明和交待”(赵毅衡,2009)或“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记载下来或说出来”(申丹,2009)。不过,由于赵毅衡囿于书面与口头的表达,而申丹则纠结于1966年托多洛夫提出的故事与话语的二分法,争论双方均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重要的叙事学元素“事件”(即“事情”)。这种忽视显得与中国叙事传统格格不入,因为在中国语境中话语层面的叙述向来都离不开故事层面的事件。唐代贾公彦在注疏《周礼·春官宗伯·乐师》时将“序事”改为“叙事”,成为使用“叙事”一词的第一个人。可见,“叙”不仅与“序”(如《周礼·春官宗伯·职丧》中的“序其事”)相通,而且还与“事”连用,构成动宾词组。在汉魏六朝时期,叙事指称史学才能,如《三国·魏书》中赞扬司马迁“善叙事”,后来,叙事一词的使用略微泛化,导致“文体变迁”,譬如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开始从书写手法谈及叙事,并且扩展到碑碣、哀辞文体;《隋书·经籍志》中“叙事缘情”涉及古诗叙事。不过,直到唐宋年代(7—13世纪)叙事才成为文类术语,如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标志着“叙事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书写策略的确立和比较充分地展开论述”;南宋绍定年间(13世纪前叶)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把叙事同其他文类区分开来,为叙事竖起了真正的界碑。之后,“叙事作为文类概念,开始受到承认”(杨义,2009:10-15)。因此,从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角度看,作为叙事研究的学问,术语narratology也应译为“叙事学”。
1969年,托多洛夫在《〈十日谈〉语法》(GrammaireduDecameron)中提出术语narratologie(申丹,等,2010:3),这个法文术语起初就是指叙事文本或作品的理论。如前所述,由于故事与话语是叙事文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术语narratology与故事的“事”密切相关,没有理由把“事”抹去,仅仅译为“叙述学”,因此,理应译为“叙事学”。
随着历史的发展,术语narratology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变化。譬如,巴尔(2003:1)扩展了这个术语的定义:“叙述学是关于叙述、叙述本文、形象、事象、事件以及‘讲述故事’的文化产品的理论”。可见,“叙述本文”(即叙事作品)讲述的仍然是“故事”,叙事研究的对象仍然包含“故事”中的“事件”、“事象”与“形象”,而“叙述”仅仅是与“故事”并存的一个方面,所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整体科学,术语narratology译为“叙述学”欠妥,正确的译法是“叙事学”。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术语narratology理应统译为“叙事学”。首先,从驳论的角度看,假如这个术语统译为“叙述学”,那么这种译法抹杀了叙事作品的“事件”与“事件性”。假如这个术语可以同时译为侧重话语研究的“叙述学”与侧重或兼顾“故事”研究的“叙事学”,那么一个术语代表两个学科,这明显违反了作为独立学科的术语的排他性原则。可见,无论是译为“叙述学”,还是让“叙述学”与“叙事学”的译法并存,都是值得商榷的。更为重要的是,从立论的角度看,可以从历史发展与词源学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术语narratology都与叙事研究的对象“事件”及其内在特征“事件性”不可分割,因而统译为“叙事学”才是比较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