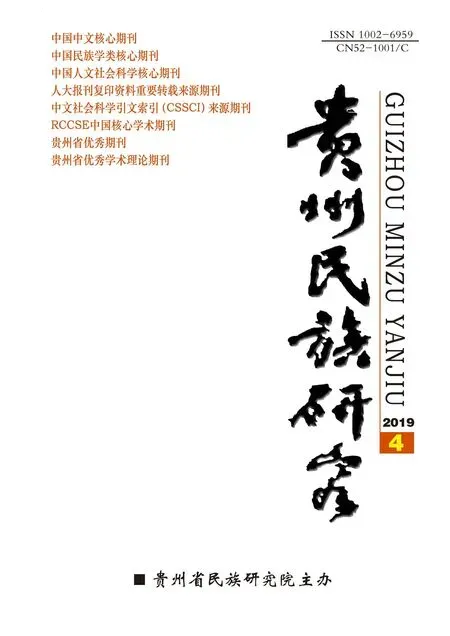论潇贺古道瑶族聚居区族群特质及“瑶文化”元素的现代呈现
2019-03-17潘雁飞
潘雁飞
(湖南科技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永州 425199)
一
一般认为,潇贺古道起于道县双屋凉亭,出道县至贺州有三条线路走向。一是由江永过广西的古道;二是由江华沱江至大路铺惠风凉亭,向左过勾挂岭经小圩、大圩出湖南进入贺州;三是经大路铺惠风凉亭向右过白芒营,由涛圩、河路口入广西富川、钟山至贺州。古道陆路连通道州贺州,向北延伸至永州,北通中原;向南延伸至梧州(广信);水路连通潇水、贺江,向北连通湘江、长江,向南经南江、北流江、南流江至合浦出海,由是开创海上丝绸之路,且起着沟通中原与岭南的重要作用。
“瑶”首见于《梁书·张缅传》附传卷34。南北朝至隋唐称“莫徭”。唐末,史籍开始出现“徭”的称谓,表明过去的“莫徭”已正式有了“徭”的族名。宋以后一直称徭人。至此,“南岭无山不有瑶”。瑶族作为一个迁徙不定的“游耕”民族,岭南岭北的瑶族应基本是以潇贺古道为核心往返于岭南岭北。在历史上的迁徙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食尽一山更徙一山”的自然形式;二是被迫迁徙,如元大德九年(1305年)千家峒的瑶族大迁徙;三是明代抚瑶政策,招抚瑶民下山定居。
正因如此,岭南岭北,潇贺古道两侧山上山下,星罗棋布散落不同支系的瑶族村寨,也有了湖南的江华瑶族自治县,广西的富川瑶族自治县两个瑶族大县,其主要地域又是汉代初年所置的冯乘县县域。
观察今日之地图,在湖南境内,潇贺古道两旁从江永出广西富川的主要瑶族乡有千家峒瑶族乡、兰溪瑶族乡、源口瑶族乡,瑶族村寨的瑶民,以清溪瑶、古调瑶、扶灵瑶、勾蓝瑶等四大民瑶为典型。广西的富川、恭城亦有分布。这实际上是平地瑶的支系。
从江华大路铺向右过白芒营镇、大石桥乡、涛圩镇、河路口镇出湖南入广西路线中,有上五堡百里瑶岗,有名的瑶族村寨有漕渡村、秦岩村、尖山村、井头湾村、牛路村等,村寨族群也是以平地瑶为主。
明万历《江华县志》载:“上伍堡,乃平地瑶也。”平地瑶自称为“爷尼”“爷贺尼”“丙多优”,意为“瑶人”“瑶话人”“平地瑶”。江华县西南部与广西接壤的上伍堡一带(大致为现涛圩镇与河路口镇地域范围),是平地瑶的主要聚居区。这一丘岗地区,地分三宿:旦久宿(分为上半宿和下半宿)、平岗宿、竹子尾宿。据清同治《永州府志》记载,上五堡李东仂等十七户约三百名瑶民,在明洪武初年被“抚瑶下山”,编户入籍。《武昌府永州江邑铜牌》载:奉、唐、李三姓瑶民自元末从千家峒逃出,几经辗转,移民上伍堡,于明朝永乐二年归化,分为三宿,分防把守三条九隘之夷。上伍堡凤尾村(属于上伍堡三宿中的竹子尾宿)李松助家珍藏的一份竹子尾宿李仲武户的编册,载有“洪武贰年设立江华”等内容,他们被“招抚”下山之前“左腰长刀,右负大弩,种黍菽以为食,猎山兽以续食”达六代之久。以每代25年推算,正好是宋时进入江华的。[1]
据《江华旧县志》记载:自明嘉靖以来,“梧州流民”多起多批进入这一地域与当地“抚瑶”结盟而居,相互通婚,形成了“半瑶僮、半梧州流民”的平地瑶村。聚居于这些村落的平地瑶人,因在日常生活中通用当地独特的一种汉语方言“梧州话”,同时他们又都自称是“梧州人”,故这部分瑶人有时有人称之为“梧州瑶”(也有称之为“寨山瑶”的),其实并不科学。此“梧州瑶”与目前居住在广西梧州地区的瑶族人有所区别。聚居在湖南江华和广西富川的“梧州人”是一个较特殊的族群,江华的“梧州人”被划为瑶族,而富川的“梧州人”则被划为汉族[2]。
从江华大路铺向左过勾挂岭经小圩、大圩、两岔河乡出湖南进入贺州路线的瑶族村寨众多,主要是过山瑶(高山瑶)等。江华这两条路线一为“岭东”线,一为“岭西”线,瑶族族群不一,民情风俗亦相异。
综上所述,潇贺古道周边的瑶族族群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根源性特点。无论是过山瑶,还是民瑶等平地瑶,其族群渊源久长,且有共同的瑶族盘王崇拜,具有明显的根源性特征。上五堡瑶传说是从千家峒迁徙而来,可与江永四大民瑶遥相呼应。又如富川瑶乡的平地瑶,自言是瑶王盘瓠的后代,汉唐时期祖先沿潇贺古道从湖南千家峒、南京会稽山迁徙到富川。
二是多元性特点。前述潇贺古道周边聚集的瑶族支系众多,来源不一,但都体现为民族的统一性,可见民族的包容性强。
三是融合性特点。其实多元性中,就包含了融合性。这种融合有三:一是主体瑶族与部分汉人融合,瑶人认同汉人部分文化,汉人融入瑶族之中。如上五堡主体瑶族是奉唐李三姓头人带头迁徙过来,且自称来源于千家峒,但也有一部分客家人、民家人(有人认为是来往潇贺古道的生意人,是当地平地瑶对在圩市做买卖的汉族人的称呼),由于长期往来,生活居住地同一,久而久之,语言相通,融合为一,在解放后民族成分认定时,统一定为瑶族,归为平地瑶。但他们并非融合无间,如上五堡一些称为“家”的村寨在朝踏歌时,就只能是十二姓的瑶族参加,那些被称为“家”的村寨的平地瑶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这说明他们虽然和合,但却有某种区分和隔阂,其内部还是有些微的区别。二是瑶族的汉化,如四大民瑶、上五堡平地瑶汉化的痕迹均很明显,其婚俗、节庆、歌谣等在保留一部分本民族特色的同时,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汉族文化。三是汉族村落的瑶化。一些中原南迁或江西、江浙西迁的潇贺古道周边的汉族村落,常常为瑶族村寨所包围,汉族人的衣饰、节庆、风俗,往往受到瑶族村寨影响渗透(如瑶族盘王节十月十六,汉族有些村落称之为祖先节),表现为文化交融汇通现象。但汉族的根底或文化核心又没有改变。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和众多的少数民族直接接触中,我才深切体会到民族是一个客观普遍存在的‘人们共同体’,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同一民族的人们具有强烈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感。由于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和经常生活在一起,形成了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亲切社会关系网络。”[3]
四是不失民族本色,本真性强。过山瑶的民族本真性自不待言,民瑶、平地瑶后来被编户入籍,供赋税,开始逐步定居,主要种植水稻、薯、豆、芋等农作物,故史籍又称其为“熟瑶”“良瑶”。虽然在风俗习惯上,保留的民族特色不明显,但其一直有着高度的瑶族认同心理。
二
今天,历史进入了信息化的大数据时代。古老的瑶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起走在新时代的大道上。信息化、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民一体化,没有民族差异和特色。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更注重民族特色文化的挖掘、发展、传播与弘扬。在潇贺古道这一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建设上更应注重民族元素的展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体现这一点呢?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活态化传承便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那么活态化传承或传播,应该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呢?应该要有一个充分挖掘、研究认识、提炼升华、活态呈现、有效传播、品牌营销的过程。
首先,充分挖掘潇贺古道瑶族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古道特性与山水形势,二是文化融合与瑶族特质。之所以要充分挖掘,是因为信息化社会的今天,瑶族已普遍汉化,无论是居住、行止、衣着、教育、语言、风俗、节庆无不深受汉族影响和同化。“总体而言,当你置身于潇贺古道区域的瑶族村落中,并未感觉到与汉族的差异。这一切表明,在漫长的族群交往与互动中,瑶族的文化习性已经越来越多地认同汉族文化。”[4]要通过深入挖掘,甄别瑶族文化的自我特色。
据上五堡瑶族保留的手抄古籍记载,上五堡百里瑶岗(从大路铺到河路口),土地肥沃,瑶民希望定居下来过美好生活,再加上这里有几条沟通岭南的通道,易于守住“三条九隘”(三条道路,九个隘口),可以不受骚扰而保证生活的稳定。所以,一些瑶民宁愿入籍缴纳赋税,也不愿再享受祖先“莫徭”的荣光。因而平地瑶在保留对始祖崇拜的前提下,自觉认同汉民族文化并融入本民族文化中,表现出了与过山瑶不同的文化特质。其所经营建筑的村寨也与汉族村落相似。而自己本民族的祭祀、节日、长鼓舞、度戒、歌谣与史诗等却一直在传承不息。
其次,通过深入研究,认识瑶族文化特质,瑶族族群特性,保护瑶族文化的纯真。毋庸讳言,时至今日,对潇贺古道周边的瑶族族群与文化研究仍然相对滞后,民族文化文献整理不全面,研究挖掘不深入,并没有复活或复兴真正的瑶族特色文化,导致古道周边在开展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时,走的仍然是停留在表面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老路,急功近利地利用浅层次的瑶族标签来号称瑶族特色文化,也就出现了“千村一面”近乎雷同的现象。
在研究与认识问题上,也存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倾向。如对《过山榜》《千家峒源流》中记载的犬图腾问题,只是一味强调“龙犬是龙不是狗。”却没有分别从神话学、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等流变的角度去进行科学的认识,导致民间学界出现了一些伪认识。
从人类学角度说,任何民族都有图腾,这源于人的万物有灵观念。图腾意识是神话时代初民的民族起源意识。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万物有灵观念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会有一个发展过程,由狗到龙犬到民族始祖英雄神。
从民族学角度看,一个民族一定会具有民族的文明意识、民族自觉意识、民族觉醒意识(自我意识、尊严意识)走向,如瑶族的龙犬形象,恰恰寓示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高贵和吉祥,此谓民族觉醒意识。
从历史学角度看,一个民族的起源与形成一定是由一个英雄始祖带领本部落在迁徙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特有文化而定型为一个民族,此谓历史意识,瑶族盘王作为瑶族始祖就是一种历史意识,也是历史事实。
再次,提炼升华瑶族文化的本真。研究是为了认识,认识是为了更好地提炼与传承。在潇贺古道这样一种复杂、融合、多元的瑶族文化里,应提炼最能反映瑶族文化元素,最能体现瑶族文化本真的内核来传承、弘扬,以使瑶族民情风俗、瑶族味道绵延不息,浓郁芬芳。
第四是创意呈现。民族文化传承是需要创意,需要高端策划的。唯有如此,才能将瑶族元素有机地巧妙地呈现出来。不仅让专家不想走,也要使游客还想来!这就需要有一种文创功夫。“文创”重点是“创”,要将瑶族文化元素价值与当代流行紧密相结合,既体现瑶族文化元素价值观,又具有流通性。潇贺古道的瑶族文化就要在提炼与升华中找出流变的元素、融合的元素、勾连的元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旨在深度融合。
第五是有效传播。一是传承式的活态化传播,二是辐射式的扩散传播。前者保持瑶族文化元素的原汁原味和生命力。后者塑造瑶族文化元素的影响力、渗透力、扩展力。
瑶族文化元素的活态化传播,即在现代文明状态下建立潇贺古道典型瑶族原生态文化的生态保护区。模拟建立这样的保护区,就是一种生态保护形式。当然,由于“当时当地人们的精神氛围、风俗民情等”不复再现,我们还可以采用全息性数字化保护以弥补这一损失。即对《盘王大歌》的场合、述者、纸质歌书、图像、声音、动作、音乐、仪式、程式、物具、听众及精神氛围、风俗民情等进行分析、阐释、提炼与数字化处理保护。
而辐射式的扩散传播,则可用现代展演、视觉传播、体验式传播、碎片化传播等方式来体现。以鲜明性,故事化,小品化,系列化,人性化,互动化的网络视频等多样化方式展现瑶族本真的文化元素,达成瑶族文化想象与诗意生活的结合,以达到辐射式传播的目的。
第六是品牌营销。文化创意不仅要培育文化,也要培育市场品牌。瑶族文化资源如何细化和整合?瑶族文化品牌如何推广?除了政府行为推广,更要通过品牌营销转换成为大众的口碑传播。这就必须使品牌有特色、特别、特殊之性,才能积聚人才、人气、人缘。品牌传播推广应先通过广告或品牌推广活动召唤人气,进而让人们慕名而来,然后让人感到“就是人们想去的地方”,让人有一种归属感,栖息感。
潇贺古道周边瑶族文化元素的呈现一定要有品牌观念。品牌是品名、品记、品类、品味、品质、品德、品行的相乘,是一种有机结合与融合,惟其如此才会形成品牌资产。具体到潇贺古道瑶族聚居区而言,应该从全域旅游角度,细分旅游瑶族文化产品,以应对目标旅游消费者。潇贺古道瑶族文化元素的品牌营销倡导什么样的瑶族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均会决定其品牌的导引效应。犹如绘画,不在形似,而妙在神似,瑶族文化元素的呈现正在于民族精神的视觉呈现和内心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