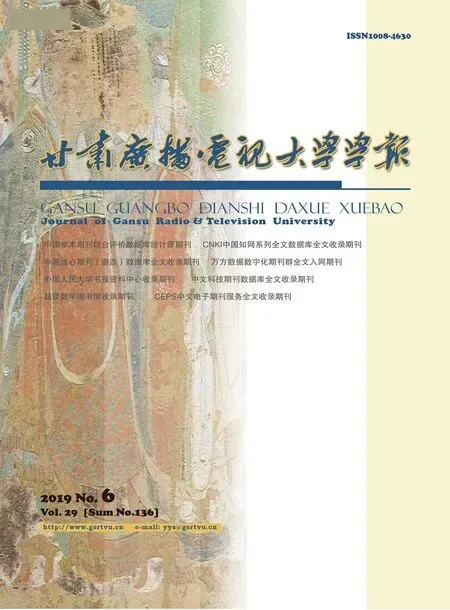归义军政权僧人出使中原王朝情况探究
2019-03-17王珊珊
王珊珊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兰州 730000)
自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起事收复敦煌起,归义军政权屡次派遣使者出使中原,高僧担任使者的情况屡见不鲜,僧使也成为归义军政权与中原王朝交往的一个重要群体,肩负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任务,为密切双方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研究通过对比张氏归义军和曹氏归义军两个时期的僧使情况,探讨僧使在双方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一、张氏归义军时期悟真出使中原的情况
根据汉文典籍和敦煌文书记载,归义军最早派遣至中原的僧人使团是大中五年(851)到达长安的悟真使团。关于该使团的出发时间,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冯培红为代表,认为悟真使团出发时间为大中二年(848),是张议潮收复瓜、沙二州之后派往中原报捷的十道使团之一[1]451。二是以杨宝玉、吴丽娱为代表,认为悟真使团是大中五年(851)初前后出发的后续使团[2]。之所以产生分歧,主要是对史书记载“以部校十辈皆操挺,内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军”[3]中“辈”的解释不同。冯培红将“辈”解释为“道”,认为大中二年(848)有十道使者分赴长安;杨吴两人则将“辈”解释为“个数”,反对十道使者的说法,提出悟真使团乃后续使团的观点。因为史料中尚未发现十队使团出使的具体资料,故笔者比较认同将“辈”解释为“个数”的观点,因而认为唐悟真使团是大中五年(851)出发的后续使团。作为后续使团,入京时间只比高进达率领的第一批使团晚三个月,该使团的出使背景,出使目的等就十分有探讨的必要。而敦煌文书和汉文史籍等相关记载能使我们较为清晰地了解其中的一些细节。
关于出使目的,牒文、邈真赞等敦煌文书中有大量记载。P.3770V《敕河西节度使牒》中对大中五年(851)入朝一事记载为“入京奏(事),为国赤心;对策龙庭,申论展效”[4]364,这是较为官方的记载;P.3720中的《受赐官告文牒诗文序》是唐悟真辑录自己重要官告文献时写的自序,对此事记载为“大中五年入京奏事,面对玉阶,特赐章服”[4]113;P.4660《都僧统唐悟真邈真赞并序》则是前河西节度掌书记试太常寺律郎苏翚在悟真病危时写的较为盖棺定论的评价,关于入朝事件评价道:“大中御历,端拱垂衣。入京奏事,履践丹墀。升阶进策,献烈宏规。”[5]而右街千福寺大德宗茝写给悟真的《七言美瓜州僧献款诗两首》中也对出使之事评价为“沙漠关河路几程,师能献土远输诚”[6]163,对其敬献河西图籍之事大加赞赏。
总之,入京奏事是悟真生涯中较为重要的事件。“为国赤心”明确说明这次出使担负的政治使命。由于路途遥远,音信阻隔,大中二年(848)派遣的高进达使团,直至大中五年(851)初仍未传回唐廷的相关信息,此时派遣新使也就十分必要。另外,从大中二年(848)收复瓜州、沙州到大中五年(851)初,甘州、肃州、伊州等早已收复,再次报捷也十分必要。在这种背景下悟真使团虽然并非首批使团,但同样担负着首批使团的政治任务,即向中原王朝报捷、建立联系、得到中原王朝认可敕封等重大使命。所以,此次使团虽然由僧侣组成,主要进行的是佛教交流方面的活动,但其根本目的还是文化外交推动政治外交,以僧使来加强两者之间的政治交往。正是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悟真的出使才能受到唐廷的重视,悟真也才能受到宣宗召见,对策龙庭,申论展效。也正是由于此次出使的政治目的,悟真入朝这一事件才会被官方、民间大力称赞,悟真本人也以此为荣。
悟真使团的出使既肩负着政治任务,又有其僧侣身份的特殊性,其在京活动也就具有政治、宗教双重意义。
首先,巡礼诸寺,与大德高僧和诗酬答。悟真奉诏两街巡礼诸寺,足迹遍布右街千福寺、右街崇先寺、报圣寺、荐福寺等名寺,并与辨章、宗茝、圆鉴、彦楚、沙门子言、建初、太岑、栖白、有孚、可道、景导等高僧辩论佛法,相互和诗留下了多首佳作。其次,悟真还与朝官交往应和,朝官杨贯庭在《谨上沙州专使持表从化诗二首》中记载“朝享西邦真敕坐,来晨课述笔自行”[6]179,点明悟真入朝的待遇,被诏上殿朝贺圣主,宣宗特敕悟真座位以示恩宠等。可见,悟真入朝既以使者职责向圣主课述对答,与朝官往来和诗,又利用僧人身份与大德高僧辩论佛法、诗文互酬。但总的来说其在京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政治使命,为密切归义军政权与唐朝之间的关系做出重要贡献。
二、悟真之后张氏归义军派遣中原之僧使情况
大中五年(851),继悟真使团后,张议潭率领官方使团出使中原。此次出使受封情况在杜牧的《沙州专使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制》《敦煌郡僧正慧菀除临坛大德制》中有所记载。冯培红通过以上两篇僧俗制诰推测出此次出使唐廷的应是僧俗两界,慧菀是僧界使团代表,并认为僧俗两界使团规模相似[1]453。现摘录《敦煌郡僧正慧菀除临坛大德制》内容如下:
勅。敦煌管内释门都监察僧正兼州学博士僧慧菀。敦煌大藩,久陷戎垒,气俗自异,果产名僧。彼上人者,生于西土,利根佛事,余力通儒。司执迷尘俗之身,辟喻火宅;举君臣父子之义,教尔青襟,开张法门,显白三道,遂使悍戾者好空恶杀,义勇者徇国忘家,裨助至多,品地宜峻。领生徒坐于学校,贵服色举以临坛,若非出群之才,岂获兼荣之授,勉宏两教,用化新邦。可充京城临坛大德,余如故。[7]
对比悟真受封告身“奉使魏阙顿出其迷津……奖道途之勤”[8]的明确入朝记载,慧菀的出使记载则比较模糊。如果慧菀作为与俗界使团规模相当的僧界使团代表出使中原,那么作为与悟真使团同一年入京的僧界代表,其功劳虽不如悟真,但在敕文中也应提及。另一方面,作为僧界使团代表出使,多少会参与佛事活动,与当世高僧交往应答,应留下一些活动痕迹,但《宋高僧传》等文献中并无相关记载。故笔者推测慧菀很有可能并未出使中原,该敕文只是进京使团为高僧慧菀请封的敕文。当然另一种可能是慧菀作为此次使团中的一员随从入京,而此次出使主要是向唐廷奉献十一州图籍,奉唐廷正朔,获得唐朝敕封。慧菀作为使团一员,其活动淹没于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记载较少也情有可原。但是,冯培红提出此次出使是僧俗两界齐头并进的观点需要存疑。
咸通二年(861),归义军收复凉州,张议潮再次派遣僧使入朝。《宋高僧传》记载:“咸通四年三月中,西凉僧法信精研此道,禀本道节度使张议潮表进恩之著述,勅令两街三学大德等详定,实堪行用,勅依,其僧赐紫衣,充本道大德焉”[9],记述了凉州收复之后高僧法信的敕封经过。咸通七年(866),张议潮再次遣使入唐,在《旧唐书》中记载为:“七月沙州节度使张议潮进甘峻山青骹鹰四联、延庆节马二匹、吐蕃女子二人,僧昙延进大乘百法门明论等。”[10]可见,以上两位僧人的出使目的主要集中佛教文化交流层面。从进献物品来看,法信进献“恩之著述”,昙延进献《大乘百法门明论》,均为佛教著作;从目的来看,两位僧人进献佛法主要为了得到中原僧界的认可,从而得到敕封。
总之,从悟真之后张氏归义军派遣至中原的几次僧使情况来看,其政治目的随着政权之稳固、与中原王朝关系之紧密而逐渐减弱,僧人出使更多是处于佛教交流以及乞赐高僧制诰等方面,与悟真出使之境遇大不相同。
三、曹氏归义军时期僧人出使情况
曹氏归义军时期,僧人出使中原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册府元龟》就记载了曹氏归义军时期向后周派遣僧使的情况,“十月,沙州僧兴来表辞回纥阻隔。回纥世世以中国为舅,朝廷亦以甥呼之。沙州陷蕃后有张氏世为州将,后唐同光中长史曹义金者,遣使朝贡,灵武韩洙保荐之,乃授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处置使。其后久无贡奉,至是遣僧辞其事。”[11]可见,后唐同光二年(924)至后周广顺二年(952),由于回鹘阻隔河西旧路,归义军政权与中原王朝来往较少,直到此次派遣沙州僧兴出使后周。此次出使主要担负的是政治任务,即向中原王朝奏明“回纥阻隔”之事,重新建立双方联系。回鹘这一时期信奉佛教,僧人往来中原更为便利,因而僧人担负政治任务出使中原也就成为必然。
曹氏归义军后期,由于战局需要,归义军政权与宋朝联系更加紧密,希望双方联合以牵制西夏。在这样的形势下,归义军政权与宋王朝之间多有僧使往来,在政治、文化多个领域为密切双方关系起到了推动作用。现依据《宋会要辑稿》将曹氏归义军时期遣至中原的僧使情况摘录如下:
1.淳化二年,沙州僧惠崇等四人以良玉、舍利来献,并赐紫方袍,馆于太平兴国寺;
2.(至道元年)五月,延禄遣使来贡方物,乞赐生药、臈茶、供帐什物、弓箭、铙钹、佛经,及赐僧圆通紫衣。并从之;
3(至道元年)十月,延禄遣使上表,请以圣朝新译诸经降赐本道。从之;
4.景德元年四月,宗寿遣使以良玉、名马来贡,且言本州僧惠藏乞赐师号,龙兴、灵图二寺修像,计金十万箔,愿赐之,又乞铸钟匠及汉人之善藏珠者至当道传授其术。诏赐惠藏师号,量给金箔,余不许;
5.(景德四年)闰五月,沙州僧正会请诣阙,以延禄表乞赐金字经一藏。诏益州写金银字经一藏赐之;[12]9836
6.九年,沙州遣使米兴、僧法轮等贡珠玉、名马。《玉海》:是年三月,河西贡马五百八十匹。[12]9951
这一时期归义军派遣至中原的僧人主要有惠崇和法轮,其他几则材料涉及的僧人可能并未到达中原,只是由使者代为乞赐物品及封号。从进献的的物品来看,惠崇以良玉、舍利来献,法轮贡献珠玉、名马。而乞赐的内容则主要为封号、经书、金箔等。对比之前,此时出使目的在乞赐封号、佛教交流的基础上又多了经济方面的诉求,僧使交往也更加利益化。而中原王朝对于佛经、封号等乞求一般予以同意,但对金箔、工匠等要求大都拒绝,从侧面反映了利益之下曹氏归义军政权与宋朝之间既合作又提防的矛盾关系。
四、结语
无论是张氏归义军还是曹氏归义军,僧人充任使节出使中原王朝屡见不鲜。随着时代的不同、社会政治背景的不同,僧使的出使目的、规模、朝贡物品等均会发生变化。无论是张氏归义军还是曹氏归义军,在政权确立之初,僧使在使团中地位较高,一般担负着政治任务。无论是唐悟真的奉河西地图出使,还是沙州僧兴来表“辞回纥阻隔”之事,都反映了在政权地位不稳的情况下,僧人出使是达成外交目的的一种常用手段。当政权逐渐稳固,僧人出使文化符号的意味更为突出。但曹氏时期僧使的地位比张氏时期更低,其出使的世俗化程度也更深。张氏时期的慧菀、法信、昙延等僧人出使,大都精研佛法,献有佛教著作。而到了曹氏归义军时期,僧人出使与俗界使者并无太多差别,进献多为“良玉、舍利、珠玉、名马”等,其进献贡品应与俗界礼品合二为一,并未有单独礼单。而从《宋会要辑稿·藩夷》中辑录的材料4来看,惠藏并未进献佛教著作,只是由使者代为上表请赐封号,这与张氏时期法信等人进献佛教著作,乞赐封号形成对比。从乞赐物品来看,曹氏归义军时期更加注重经济利益,佛法交流以及获得敕封已不再是僧人出使之重点,僧人出使也不如张氏归义军时期之纯粹。这些细节也从侧面反映了曹氏时期使团中僧人地位较之以前略有下降,开始逐渐走向世俗化,为政治利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