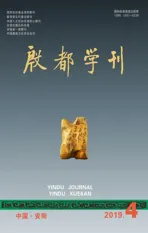殷墟甲骨“先用字体分类再进行断代”说评议
2019-03-13常玉芝
常玉芝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李学勤提出的“先用字体分类,再进行断代”方法,颠覆了董作宾、陈梦家的甲骨断代学说,在甲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该种甲骨分期断代方法的提出、目的,李学勤及其追随者在以字体分类并断代的实际操作中的主观臆断,给甲骨学科学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笔者从他们使用的甲骨材料、研究方法、成果结论着手,抽丝剥茧,条分缕析,评议这种方法的不科学性。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一、分类(分组)方法的提出及评议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李学勤的“先用字体分类,再进行断代”的说辞,并不是在近期提出“历组”卜辞的时代问题之后才提出的。而是早在1957年,他在《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一文中,就已提出了。他批评陈梦家分“卜人组”的断代方法,主张用字体分类,他说:“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是两个不同的步骤,我们应先根据字体、字形等特征分卜辞为若干类,然后分别判定各类所属时代。”他的这个分类断代法在其后的近40年间,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学界仍是以陈梦家的“卜人组”和董作宾的五期断代法为准绳,对卜辞进行断代研究的。那么,为什么在时隔四十年之后他又重提此说呢?这个问题最好还是用李先生自己的话来回答吧。1996年,他在与彭裕商合写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的“后记”中说:“随着殷墟考古的进展,甲骨材料的辑集,分期研究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文武丁卜辞问题,在70年代以后则是历组卜辞问题。由后者出发,逐渐形成了殷墟甲骨的两系说,有关争论迄今仍在进行之中。这本《殷墟甲骨分期研究》就是两系说的较全面的叙述。”[4](P419)这里,李先生交待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两系说”是在“历组”卜辞时代提前说之后提出的,也即“两系说”是由“历组”卜辞时代问题引出的;另一个是提出“两系说”后,为了对“两系说”进行“较全面的叙述”,再重提“先用字体分类,再进行断代”。由此,我们得知李先生的断代路线图是:“历组”卜辞提前说→“两系说”→“先用字体分类,再进行断代”;如果把上述路线图的箭头倒着指,就是“历组”卜辞提前说 ←“两系说”← “先用字体分类,再进行断代”,它表示“两系说”是为“历组”卜辞提前说服务的,“先用字体分类,再进行断代”又是为“两系说”服务的。也即归根到底,“两系说”和“先用字体分类,再进行断代”都是为“历组”卜辞的时代能够提前服务的。曾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两系说”是为了“摆脱历组卜辞在地层上遇到的困境”而设置的。[5]

李学勤提出“先用字体分类,再进行断代”的方法,将董作宾、陈梦家甲骨断代标准中处在末端地位的“字体”,一下子提升到了断代的第一标准,颠覆了董作宾、陈梦家的甲骨断代学说。因此,李先生说董作宾的五期分法“早已陈旧了”,[1]他的断代方法是“同原有的分期理论扞格不合”的,[7](李序P2)这确实是实话。李学勤、彭裕商说他们的字体分类的新方法“揭开了甲骨分期研究新的一页”,“甲骨分期的理论方法自陈梦家先生‘三大标准’以来,又有了重大进展,标志着该项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是“一套新的具有指导意义而行之有效的方法” 。[4](P13-14)事实是否如此,还需要经过实践来检验。下面分别介绍、分析他们及其追随者运用“类型学”进行字体分类及断代的情况。
二、各家分类、分组与断代情况评议
目前见到的对殷墟全部甲骨做过系统分类、分组及断代研究的有两家:一是李学勤、彭裕商合著的于1996年出版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4]一是黄天树于1991年出版的《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一书。[7]如果按着两书出版时间的早晚顺序,黄天树的书出版在前,但黄氏写作此书时,李氏的“两系说”尚未系统提出,故黄氏的分类、分组没有按照“两系说”的框架操作(常按: 但在20多年后的2013年,黄氏在其主编的《甲骨拼合三集》附录中,[8]列有按“两系说”框架设定的“殷代卜辞分类分组表”,此表对1991年的表有改动)。因此,最早按“两系说”进行分组、分类断代研究的是李学勤和彭裕商(注意:黄氏是“分类分组”,李、彭二氏是“分组分类”)。此外,还有2007年发表的徐明波、彭裕商合著的《殷墟黄组卜辞断代研究》一文,专门对黄组卜辞进行分类断代。下面对李学勤、彭裕商的分类断代,徐明波、彭裕商对黄组卜辞的分类断代情况做较详细地介绍与评议。
(一)李学勤、彭裕商的分组、分类与断代评议
1996年12月,李学勤、彭裕商发表了合著《殷墟甲骨分期研究》,说该书的宗旨是对“两系说”进行“较全面的叙述”。[4](P419)作者在第一章第三节“甲骨分期研究新说”中,对李学勤1957年在《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一文中提出的断代方法:“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是两个不同的步骤,我们应先根据字体、字形等特征分卜辞为若干类,然后分别判定各类所属时代”,自我评价说:“这实际上是将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运用于甲骨分期研究,这样就从理论方法上揭开了甲骨分期研究新的一页”,是“从‘十项断代标准’开始,经过数十年,又逐渐总结出一套新的具有指导意义而行之有效的方法”,是“自陈梦家先生‘三大标准’以来,又有了重大进展,标志着该项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这是自诩李学勤的断代方法超过了董作宾、陈梦家的断代方法。
李学勤为什么要在距1957年已有四十年之久的1996 年,重提并自夸数十年来一直不被学界注意的“先分类,后断代”的方法?其目的,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要对“两系说”进行“较全面的叙述”。所谓“两系说”,是李学勤采用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对殷墟前五次发掘甲骨出土的“区位”记录,以及对卜辞的断代(董氏用区位断代不科学,对卜辞断代有错误,陈梦家已指出),[9](P140)臆造出来的殷墟甲骨发展有两个系统,简称“两系说”。他制造的“两系”,将“历组”卜辞、无名组卜辞,从殷墟甲骨发展的传统序列中抽出,认为这两组卜辞只出于或主要出于村中、村南,其它各组只出或主要出于村北,遂制造出“村北”、“村中、南”两系。他分两系的缘由和目的是为了“摆脱历组卜辞在地层上遇到(的)困境”。[5]
李学勤制造“两系说”、叙述“两系说”(实际是用字体周全“两系说”),都抬出了“考古学”这面大旗。自称制造“两系说”是根据考古学的“层位学”和“坑位学”,叙述“两系说”是根据考古学的“类型学”,自以为挂上考古学的旗帜就能使“两系说”立住脚。关于他制造“两系说”所依据的“层位学”和“坑位学”,经过一辈子从事殷墟考古发掘的学者们、用80多年殷墟考古发掘的铁的事实证明,“两系说”恰恰是违背了殷墟甲骨出土的层位和坑位记录,所谓殷墟甲骨分“两系”发展是与殷墟考古发掘的事实不符的。而他叙述“两系说”依据的所谓“类型学”,是违背殷墟甲骨出土的地层关系而主观臆造的。


(一)大字类
1.大字类
2.大字类附属
(二)小字类
1.小字一类
2.小字二类
B、宾组
(二)宾组一类:“时代大致属武丁中期,下限可延及武丁晚期”
1.宾组一A类
2.宾组一B类
(三)宾组二类:“年代大致属武丁晚期,下限可延及祖庚之世”
C、出组
(一)出组一类:“主要属祖庚,上限可到武丁之末”
(二)出组二类
1.出组二A类:“时代应在祖甲前期”
2.出组二B类:“时代应大致处在祖甲后期”
D、何组
1.何组一类:“上限到武丁晚期,下限及于祖甲,大致是祖庚祖甲时之遗物”
2.何组二类:“时代大致属廪康之世”
3.何组三类:
1)何组三A类:“大致属廪康之世”,“下限已延及武乙早年”
2)何组三B类:“上限当在廪辛之世”,“下限当在武乙中期以前”
E、黄组
“本组卜辞有数千片,但其书体风格和字形结构彼此间并无多大差别,本书就不再作进一步的类别划分了。”其时代“上限在文丁,下限到帝辛”
F、历组
(一)历组一类(历组父乙类)
1.历组一A类:“本类只有父乙称谓,年代不会晚至祖庚”,“大致属武丁中期偏晚”
2.历组一B类:“称谓主要是父乙,但也有个别父丁(《合集》32680),其下限当已延及祖庚”,“上限应到武丁中期偏晚或中晚期之际,下限延至祖庚之初”
(二)历组二类(历组父丁类):“称谓以父丁为主,个别有父乙”
1.历组二A类:“重要称谓有父乙和父丁,但不同版,应为武丁到祖庚时期的称谓”,“本类的年代应在武丁末到祖庚初”
2.历组二B类:“主要称谓是父丁,大致是祖庚时期的遗物。其中《合集》32723有‘父乙’”。作者又将本类分成甲、乙、丙三群。“本类大致属祖庚时,上限可到武丁之末”
3.历组二C类:“本类重要称谓只有父丁,可知不会早到武丁之时”,“本类大致属祖庚后期,其中第二种字形组合有一部分卜辞可能已延及祖甲之世”
G、无名组
(一)历无名间组:“字体介于历组与无名组之间”(注意:是“历无名间组”,不是类。又将历组排在无名组前面),“大致是祖甲时期的遗物”,“附属于历无名间组的历无名间组晚期卜辞,称谓系统以父甲、父已、父庚为主,另外,《合集》27364字体近本类,有‘兄辛’,然仅此一见,故我们推测本类卜辞大致属廪辛时代,其上限可及祖甲之末,下限延及康丁之初”
(二)无名组一类:“本类卜辞中A、B、C三小类都有‘兄辛’称谓,故其中大部分都应为康丁时物”
1.无名组一A类:“大致属康丁前期”
2.无名组一B类:“称谓以父甲、父己、父庚、兄辛、母己、母戊为多见,其大部分应为康丁时物,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少数卜辞已开始出现‘父丁’称谓,如《合集》32223、32717、32715、32720等,这些卜辞又可在本类中划出一个小群……可暂称B类晚期”,“这些卜辞的父丁应为武乙称康丁”
3.无名组一C类:“称谓以祖丁、父甲、父己为主(《合集》27348、27371、27453等,多数也为康丁卜辞”,“其中有‘引吉’的一些卜辞已晚至武乙中期”
(三)无名组二类:“本类卜辞的称谓系统以祖丁、父甲、父己、父庚、母戊、兄辛为主,其大部分应属康丁之世”,本类卜辞中有些有“父丁”称谓,“主要是武乙早期之物”;“有占辞引吉的卜辞应大致属武乙中期,其上限或可到武乙早期偏晚或早中期之交”,“本类卜辞多数为康丁时遗物,有一小部分已延及武乙,其下限不晚于武乙中期”
(四)无名组三类:“基本上都是武乙时的遗物,大致处于武乙中晚期”
(五)无名黄间类卜辞:可据字体再分为两类。[10](2)该文中,已将“无名黄间类”卜辞改称作“无名组晚期”卜辞,对其时代也改为延伸至帝辛时期。“包含的年代大致从武乙到文丁”

不难看出,上面李、彭二氏的所谓大“字体组、类”,其所指的范围,实际上就是陈梦家的“卜人组”范围,他们只不过是换了个“名称”而已,即以“字体组”代替“卜人组”称之,以示有别于陈先生的断代成果。




这里,顺便提一下,不仅是对卜辞的分类与断代要以地层学为依据,就是缀合甲骨,也是要以甲骨出土的地层为依据的。甲骨缀合大家桂琼英先生(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之夫人)早就告诫:“为确保正确无误,缀合不能只看拓片表面,因为同文的卜辞不少,还得参以实物;无实物者,出土地层的坑位、流传的情况也是重要考虑因素。”她指出:“甲骨中有不少同文卜辞,一些同文卜辞不仅字迹出于一人之手,而且卜辞的契刻部位也多有相同者,有如同一模具所铸。因而,有的缀合虽然纹理、字形、刻辞内容都能对得上,但也不见得就很可靠,特别是不连接的所谓遥缀。”故而她在缀合甲骨时,特别注意甲骨“出土地层的坑位、流传情况”,“特别注意是否同批出土,谁家所藏。”[11]以此对比近年一些人不参验原骨,不考虑甲骨出土的地层关系,不追究甲骨的流传情况,而随意地对甲骨进行大量的所谓缀合,甚至弄出诸多遥缀。那么,这些缀合出的“成果”,究竟有多少是可信的呢?

在“大字类”中,除了“大字类”,又分出一个“大字类附属”。作者说这两类卜辞在下面几版中共存:《合集》19773、19946、19945、20576、19957(正、反),他们说这几版中属于“大字类”的只有《合集》19945、19946甲戌扶卜一辞、19946、20576反面刻辞,“其余全是另一种字体的卜辞。这些卜辞如果以字体特征进行联系,可以划出一个小类……将其作为大字类的附属”。笔者检查了上述各版卜辞,发现各辞字体风格区别并不大,特别是《合集》19773和19957正、反,更是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要分成另一类。查《合集》19946版卜骨,正面有12条卜辞,作者只将其中“甲戌扶卜一辞”分在大字类,其他11辞皆分在“大字类附属”,反面的一辞也分在大字类。再查《合集》20576,正面有24条辞,反面有两条辞,作者只将反面的两条辞分在“大字类”,正面的24条辞则分在“大字类附属”。这种将刻在同一版甲骨上的卜辞分在不同的类中,在李、彭的分类中很普遍。


由于上述“两系”的安排太过完美,已被人质疑是主观人为拟定。李学勤于1980年对“两系”的尾部做了改动:他将“无名黄间类”卜辞改称作“无名组晚期卜辞”,使“村中、南系”的无名组卜辞与“村北系”的黄组卜辞脱离干系,力图证明两系自始至终都是独自发展的,最后“村中、南系”并没有融合于“村北系”中。在1996年时,李学勤、彭裕商说“无名黄间类”卜辞可据字体再分为两类:“一类没有可供判定时代的重要称谓”,“其上限当在武乙之世”;“二类卜辞字体与黄组非常接近,重要称谓有武乙(《屯南》3564),这样的称呼只能出现于文丁以后,但是否已晚到乙辛之世呢?我们认为可能性不大”;“武乙在位年数长达三十五年以上,其后的文丁,据古本《竹书纪年》至少也有十一年,而本类卜辞数量不多,故其包含的年代不大可能从武乙一直延续到帝乙帝辛”;“黄组中的武乙应是文丁称其父,武祖乙才是帝乙帝辛时的称呼。本类既早于黄组,而黄组中已有文丁卜辞,则本类的武乙理应与黄组一样,是文丁时的称呼”;“本类卜辞包含的年代大致从武乙到文丁……其中一类卜辞大体上是武乙晚期之物,其上限可及武乙中晚期之交。”[4]但到1980年,李学勤改“无名黄间类”为“无名组晚期卜辞”之后,对其时代来了个不同于前说的大翻转,即对同一类卜辞的名称改变之后,对其时代也完全推翻了1996年时的观点,认为原来的“无名黄间类”,也即改名后的“无名组晚期卜辞”的时代,已从武乙、文丁延长到了帝辛时期。[10]我们将在另文分析,说无名组晚期卜辞已延续到了帝辛时期,其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说实话,笔者阅读李学勤、彭裕商及下面要谈到的黄天树对各类卜辞的细分类、细断代,很费脑力。他们有些字的分类无“标准”可言,只凭个人观察来决定;断代多有模棱两可的推测,有的说法还前后矛盾。总之,他们的分类断代烦杂且让人难以理出头绪。特别是对同版卜辞按字体的再分类,再对各类进行的断代,作者既说同版各类卜辞有联系,又说它们的时代不同,也即同一版中不同字体的卜辞时代不相同。这就引发了笔者对他们的“历组”卜辞断代的质疑,如被他们认定是“历组”卜辞时代提前的铁证《屯南》2384,该版上出组卜辞字体与“历组”卜辞字体同版,他们就说这是“历组”卜辞与出组卜辞时代相同的铁证,但对其它如上述所举的某些同版卜辞,因字体不相类又说是时代不相同。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只能说明作者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卜辞时代的,在断代中采取双重标准。
(二)黄天树的分类、分组情况评议
最早系统贯彻李学勤“先分类,后断代”方法的是黄天树。1991年,黄氏发表博士论文《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导师为裘锡圭)。[7](7)本文引文均据2007年版。“王卜辞”的提法是李学勤提出有“非王卜辞”后产生的。他的分类、分组情况如下:
C、宾组
1.典宾类
3.宾组一类
D、宾出类
1.宾组宾出类(宾组三类)
2.出组宾出类(出组一类)
F、历类
1.历一类
2.历二类
3.历草体类
H、何组
1.事何类
2.何组一类
3.何组二类
I、历无名间类
J、无名类
1.无名类
2.无名类的左支卜与右支卜
K、无名黄间类
L、黄类


其实,这种用字体分类的难度,提出者自己也是有体会的。如李学勤就说:“历组中以父乙为中心的卜辞有多种作风,有些和有父丁类的卜辞无法分开。在《南地》书里,505卜骨有兄丁,与《拾掇》1.422、《邺中》3下46.1系联,称谓也是以父乙为中心的,其字体却和《南地》所论武乙卜辞近似。”[2](10)李先生说《南地》505与《拾掇》1·422系联。笔者查与原版甲骨不符,当是《拾掇》1·423之误。裘锡圭也说:“历组”中“父乙类和父丁类卜辞的字形结构,大多数也完全相同或十分相似”,“仅仅根据字体很难把这两类卜辞完全区分开来”,“事实上,有不少历组卜辞,很难确定它们究竟属于父丁类,还是属于父乙类”;“宾组晚期和出组早期的文例、字体很难区分”。因此,他认为饶宗颐在《殷代贞卜人物通考》[16]中指出的“据字体断代之不易。这话是有道理的。”[12]李、裘二氏所说还是对有明确称谓的“历组”、宾组、出组卜辞进行分类都有难度,那么对那些不带称谓的卜辞的分类,其难度就更不必说了。黄天树也说:“字体并非一成不变,情况错综复杂。对同一种客观现象,由于各人观察上有出入,有时会作出不同的分析。因此,所分出的类与实际情况就不一定相合,这是甲骨分类难以掌握之处。”[7](绪论)这确实是大实话。这与李先生所说字体分类“应用起来还是简易适用的”,是不相符的。以字体分类,在实际操作中有难度,其原因,一个是卜辞的字体复杂多样,同一版甲骨上的字体许多时候都不属一类,甚至属多类。正如陈梦家所说:“在同一朝代之内,字体文例及一切制度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逐渐向前变化也非朝代所可隔断的……这一朝代的变例或例外,正是下一朝代新常例的先河。已经建立了新常例以后,旧常例也可例外的重现”。[9](P153)这就是“类型学”应用在字体分类上的局限性。另一个是缺乏科学的统一判定标准,每个人在判定字体上存有差异,相信如果让多人参与分类,恐怕不会出现有两个人完全相同的分类,这是不言而喻的。
李学勤、彭裕商说:“分类是断代的基础,分类的精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断代的质量”,[4](P17)此话正确。下面再通过李学勤、彭裕商和黄天树对“无名黄间类”卜辞的断代;彭裕商、徐明波对黄组卜辞的分类断代,看看分类的精确度和断代的质量究竟如何。
(三)关于“无名黄间类”卜辞的分类与断代评议
关于“无名黄间类”卜辞,黄天树说:“本类卜辞的内容绝大多数是田猎卜辞”。黄氏主要以“灾”字的写法区分“无名类”和“黄类”。他说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举的《写》218=《甲》405,即《合集》29087(《甲》405+《甲》399)是“典型的‘无名黄间类’字体”,董氏认定该版卜辞为“第四期的武乙时代”,对此,黄氏说“董说可从”。关于“无名黄间类”卜辞的时代,他认为“无名黄间类的上限以定在武乙之世为宜”;关于下限,他举《屯南》3564说:“这条卜辞有‘武乙宗’,时代至少应晚到文丁之世。当然也有可能晚到帝乙时代”。不过,他又举《屯南》4343,根据字体定其“也有可能是文丁时代的东西”。他的最后结论是:“可以把无名黄间类的下限定在文丁之世”。即黄氏认为“无名黄间类卜辞是武乙至文丁时代的东西”。他又说:“如果把无名黄间类插入无名类和黄类之间,看作是两者的中介也不甚合理。”看来,他并不确定“无名黄间类”就是连接无名组和黄组的卜辞。
李学勤、彭裕商认为“无名黄间类”卜辞“包含的年代不大可能从武乙一直沿续到帝乙帝辛”,“本类卜辞包含的年代大致从武乙到文丁”。[4](P305)这个意见与黄天树一致。但到2008年,李先生在《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一文中, 将“无名黄间类”卜辞改名为“无名组晚期”卜辞,并力图证明此类卜辞的时代下限已到帝辛时期,否定了之前他和彭裕商的观点。他还说:“只出于小屯村中、南的无名组晚期卜辞,近年有学者称之为‘无名黄间类卜辞’,主张其时代下限为文丁”,“我在《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文中误认这些卜辞为文丁时卜,就是因袭着这样的观念”。由他在该文的注解知“有学者”指的是宋镇豪、刘源合著的《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一书。[17]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上文已指出,黄天树在1991年,李先生和彭裕商在1996年,就已在各自的书中先后定该类卜辞为“无名黄间类”了,并且定其时代上限在武乙时期,下限在文丁时期。[8] (P4)而宋镇豪、刘源的书是在2006年才出版的。谁先谁后,谁影向谁,不言自明。总之,到目前为止,对于所谓“无名黄间类”或“无名组晚期”卜辞的时代,有武乙至文丁和武乙至帝辛两种意见。我们在另文(待见)已逐条分析了李先生提出的“无名组晚期”即“无名黄间类”卜辞延长至帝辛的证据不能成立。
(四) 徐明波、彭裕商之黄组卜辞的分类评议
黄天树在《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7]中,将“黄组”卜辞称作“黄类”卜辞,认为此类卜辞的“字体可以说是相当的清一色”,因此,没有对其再进行细分类。对“黄类”卜辞的时代,他说:“黄类的早期卜辞应上及文丁之世”,“晚期卜辞属帝辛之世”,即“黄类”卜辞是文丁至帝辛之物。李学勤、彭裕商在《殷墟甲骨分期研究》[4]中称作“黄组”卜辞,认为此组卜辞的“书体风格和字形结构彼此间并无多大差别”,因此,“就不再作进一步的类别划分了”。对“黄组”卜辞的时代,他们的意见是:“上限在文丁,下限到帝辛”。即黄、李、彭三人对黄组卜辞时代的认识是一致的。
但是到了2007年,彭裕商在与徐明波合撰的《殷墟黄组卜辞断代研究》一文中,[18]改变了1996年与李学勤合作时的观点。他们采用李学勤的“先用字体分类,再进行断代”,即所谓“类型学”方法对黄组卜辞进行再分类再断代。至此,彭裕商与李学勤、黄天树在黄组卜辞的分类与断代上出现了不同意见。下面详细介绍与评议徐、彭二氏对黄组卜辞的分类。
徐、彭二氏说,他们对黄组卜辞字体的分类是:“根据字体结构和书体风格的不同将黄组卜辞大体划分为二大类”,又将第二大类细分成3个小类。情况如下:
黄组一类
徐、彭二氏所举“黄组一类”卜辞字体风格相同的标准片(下称“标准片”。笔者在每片著录号后面用括号简注其卜问事项)有:
作者描述“黄组一类”(简称“黄一类”)卜辞的字体特征是:“刀锋圆润柔和,刻手擅长用圆笔,很多字体转折处有弯曲的弧度”、“字体方正、规整。布局上,工整严饬,字与字之间,列与列之间距离均等,同版卜辞字体大小较为一致。” 他们又举出11版有“黄一类”特征性字体的甲骨(下称“特征片”),举出37个特征字(括号内的卜问事类是笔者标注的):
《合集》35695:癸、贞、月、吉、旬。(周祭卜旬翌祭)
《合集》36751:午、辰、庚、今、往、来、灾。(王步)
《合集》36871:未、酉。(卜旬、地名)
《合集》36946:戊、寅。(王步)
《合集》35399:其、翌。(周祭卜旬翌祭)
22《合集》37462:亡、王、子、申、亥。(往来亡灾)
《合集》38556:己、宾、岁、尤。(王宾岁、燎)
《合集》36975:受。(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受年)

黄组二类
作者说:“本类卜辞与上述一类在字体结构与书写风格上有明显的区别。如月、吉、亥、其等字特征尤为显著”。他们将“黄组二类”再细分成A、B、C三个小类。
黄组二A类

作者举出有“黄组二A类”特征性字体的甲骨即“特征片”五版(括号内的卜问事类是笔者标注的),共举12个字:
《合集》37903:丑、亥、王、贞、月、亡、旬、酉。(卜旬)
《合集》37903巳、贞、吉、月。(查此片《合集》号或错,因为37903上面已举,并且无“巳”、“吉”二字)
《合集》37898(+35400+38307+38732,作者不知37898可与35400、38307、38732拼合):吉。(卜旬附周祭翌祭)
《合集》37945:辰。(卜旬)
《合集》35424:未。(卜旬附周祭彡祭)

黄组二B类
作者所列“黄二B类”的“标准片”有(括号内的卜问事类是笔者标注的):《合集》36376(王步)、36380(王步)、36541+《英藏》2529(天邑商宫。作者不知该片与《英藏》2529可以拼合)、36544(天邑商宫),共四片。

作者举出有“黄组二B类”特征性字体的甲骨五版,共18个字(括号内的卜问事类是笔者标注的)。
《合集》36377:丙、己、子、王、亡、申、辰。(王步)
《合集》35400+(《合集》37898+38307+38732,作者不知该片与37898、38307、38732可拼合,也不知该拼合版就是《合补》12927):翌、吉、旬、月。(卜旬、周祭翌祭)
《合集》36540:巳。(天邑商宫)
《合集》36541+《英藏》2529:酉、贞、兹。(天邑商宫)
《合集》39145:丑、亥、未。(卜旬)

黄二C类
作者所列“黄二C类”的标准片有(括号内的卜问事类是笔者标注的):《合集》35830(祊祭)、《合集》36251(王宾卜辞,周祭先妣)、《合集》36234(王宾卜辞,周祭先妣)、《合集》36561(往来亡灾)、《合集》36591(往来亡灾)、《合集》36592(往来亡灾)、《合集》36640(往来亡灾)、《合集》36645(往来亡灾)、《合补》10960(王宾卜辞,周祭先王),共9版。
作者说:“黄组二C类是典型的黄组二类卜辞,其数量较多,所出现的单字字形多,可与黄组一类一一比较。”作者举出“黄组二C类”有特征性字体的甲骨11版(括号内的卜问事类是笔者标注的),共37个字:
《合集》36251:贞、亡、翌。(王宾卜辞,周祭先妣)
《合集》35364:午。(祭先妣,缺字较多)
《合集》36561:己、巳、戊、辰。(往来亡灾)
《合集》38894:申。(今夕亡祸)
《合补》10942:吉。(卜旬,周祭先王)
《合集》38606:宾、岁、尤。(王宾岁)
《合集》37387:受、月。(王受又等)
《合集》38838:庚、寅、丙、戌、今、子。(今夕亡祸)
《合补》12741:癸、亥、旬、丑、王、酉、未。(卜旬)


由上面介绍的徐明波、彭裕商对黄组卜辞字体的再分类,可以看到,如果不管卜辞内容是否相同,将整个黄组卜辞,即将诸如祭祀(包括已成系统记录的周祭、祊祭等)、战争(包括已成系统记录的征人方、盂方等)、卜旬(包括附记周祭先王祭祀的卜旬辞)、卜王事、卜天象、卜历法等等内容的卜辞,混杂在一起进行字体分类,就会出现下述问题:
一是同类卜辞所列“标准片”和“特征片”多有不同。如在“黄一类”中,列出了11版标准片和11版字体特征片,其中只有《合集》36751一版是标准片和字体特征片都有的,其余10版皆不相同。在“黄二A类”中,列出了5版标准片和5版字体特征片(其中《合集》37903重复,实为4版),二者竟然没有一版相同。在“黄二B类”中,列出了4版标准片和5版字体特征片,其中只有《合集》36541(作者不知该片与《英藏》2529可以拼合)一版是标准片和字体特征片都有的,其余二者皆不相同。在“黄二C类”中,列出了9版标准片和12版字体特征片,其中只有《合集》35830、36251、36561、36592四版是标准片和字体特征片都有的,其余二者皆不同。很奇怪,作者为什么要采取选用标准片和字体特征片不一致的做法?难道标准片中没有或少有特征性字体吗?



(五) 徐明波、彭裕商之黄组卜辞断代评议
徐明波、彭裕商对黄组卜辞先以字体进行细分类后,再进行断代,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们是如何断代的。他们将黄组卜辞按字体分成两个大类,即“黄组一类”、“黄组二类”;在“黄组二类”中又分出三个小类,即“黄组二A类”、“黄组二B类”、“黄组二C类”。但在断代时却是只对两个大类进行断代,对“黄组二类”里的三个小类不再分别断代,真不知道他们费力分成三个小类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说先分类后再对各小类进行细断代的吗?
关于黄组卜辞的断代,他们说:“对黄组卜辞各小类进行时代的推定时”,“所依据的是称谓系统和卜辞间的相互联系”,“卜辞间的相互联系……其中有一项为发展演变脉络清楚的字体”,又说:“推定出来的早晚关系只要符合各类卜辞中的称谓就可认为是可靠的”,这是说要用称谓来检验用字体分的类是否正确,这不正说明了“称谓”才是断代可靠标准吗?其实,断代的程序应该是:先用“称谓”断代,再来探寻各代字体的演变脉络,而不是相反。
对“黄组一类”卜辞的断代,徐、彭二氏说是从“字体特点”、“称谓”、“卜辞内容”三个方面进行的。
关于利用字体特点断代

关于利用称谓断代
徐、彭二氏说:“一类中有父丁、母癸的称谓,我们认为这是帝乙对其父文丁、其母文丁之配的称呼”,即认为“黄组一类”卜辞是帝乙卜辞。因为黄组的“父丁”、“母癸”称谓只出现在“祊祭”卜辞中,又因为他们用字体分出的类都是跨事类分出的,所以其实他们是用“祊祭”卜辞的称谓来对“黄组一类”中各种事类的卜辞进行断代。因为笔者曾专门撰文讨论过黄组中的“祊祭”卜辞、周祭卜辞以及其它文例卜辞里带有称谓的卜辞,所以他们在论述自己分的“黄组一类”和“黄组二类”卜辞的时代时,主要是以批评笔者的《祊祭卜辞时代的再辨析》、《说文武帝——兼略述商末祭祀制度的变化》两文进行的。[19]
首先需要申明的是,徐、彭二氏说笔者“所分的祊祭一类卜辞字体特征”,同于他们的“黄组一类”卜辞。此说不确。因为笔者并没有首先利用“字体”对“祊祭”卜辞进行分“类”,而是根据“祊祭”卜辞出现的“称谓”共版关系将“祊祭”卜辞分成两个大“组”,根据各组的称谓组合分别判定各组卜辞的时代,然后再探讨各组卜辞中某些字的特征及其演变。
徐、彭二氏利用“父丁”、“母癸”两个称谓证明他们的“黄组一类”卜辞的时代是在帝乙时期,批评笔者以多个称谓的共版关系论证“祊祭”卜辞的时代分别是在文丁、帝乙时期是错误的。因此,这里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祊祭”卜辞的内容、特点及笔者的断代情况。
所谓“祊祭”卜辞,是指文例为“干支卜,贞:祖先名祊,其牢”的卜辞。(12)还有“干支卜,贞:祖先名宗祊,其牢”、“干支卜,贞:祖先名宓祊,其牢”两种文例卜辞,它们只适用于祭祀武乙、文丁二王。笔者总结“祊祭”卜辞共出现以下一些称谓:武丁、祖丁(武丁的另一称呼);祖甲;康丁、康、康祖丁;武乙、武、武祖乙;文武丁、文武、文;母癸,共有十三个称谓。这十三个称谓所指的祖先分别是:武丁,祖甲,康丁,武乙,文丁直系五先王和母癸。笔者发现这十三个称谓的组合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武乙”(包括“武”)与“武祖乙”,即同是指武乙的这两个称谓,从不在一版卜甲中出现;(13)“祊祭”卜辞主要刻在龟甲上。二是对武乙的这两个称谓,一个称“祖”,一个则直呼庙号不称“祖”,这就提示我们载有武乙这两个称谓的卜辞,应该是分属于不同时代的;三是“武乙”(包括“武”)从不与文丁的各称谓同版出现,而“武祖乙”则是与文丁的各称谓同版出现的,这说明武乙的两个称谓与文丁的各称谓在共版关系上,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因此,笔者按着“武乙”(包括“武”)与“武祖乙”两个称谓的共版情况,将“祊祭”卜辞分成两个大组。在有“武乙”(包括“武”)称谓的第一大组中,“武乙”是与“武丁”、“祖丁”[19](14)第五期的“祖丁”是武丁的另一称呼。、“祖甲”、“康祖丁”、“母癸”5个称谓共见于一版的,也即“武乙”是与其前的直系三先王武丁、祖甲、康丁共见于一版的。这种同版卜辞有3个特点:一是对康丁称“祖”,称“康祖丁”;二是对武乙皆不称“祖”;三是不见有文丁的各称谓出现。我们知道,对康丁称“祖”的可以是其孙文丁,也可以是文丁之后的帝乙和帝辛,但是对武乙不称“祖”的,就只能是其子文丁了;而不见有文丁的各称谓出现,说明文丁当时尚在人间,不在祭祀之列。即在这组卜辞中,“武乙”是该组卜辞中受祭先王最晚的称谓。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带有“武乙”称谓的“祊祭”卜辞都是武乙之子文丁在位时占卜的,它们都是文丁卜辞。由此又可以得知,到商代晚期的文丁之世时,对父辈祖先一般已不再加亲属称谓“父某”了,而是直称其庙号。

总之,徐、彭二氏在论证“黄组一类”卜辞的时代时,只用在“祊祭”卜辞中出现的“父丁”、“母癸”(下文论述)两个称谓作论据,来论证包括其它各种事类的卜辞的时代;并且在选取论据时,忘记了自己对卜辞的分类,找出“黄组二类”卜辞作证据;同时他们用非“祊祭”卜辞来反驳笔者对“祊祭”卜辞的断代;还有他们不分卜辞事类,不懂得黄组中各种事类的卜辞都有各自的规律,而是将各种事类的卜辞混杂在一起进行断代。这些做法必然会造成断代的错误与混乱。
上文已指出徐、彭二氏利用“祊祭”卜辞中出现的“母癸”、“父丁”称谓,指称“父丁”是帝乙对文丁的称呼,“母癸”是帝乙对文丁之配的称呼,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用字体分出的“黄组一类”里各种事类的卜辞都是帝乙卜辞。这个运作是以批评笔者对“祊祭”卜辞第一大组中“武乙”从不称祖,即不称“武祖乙”,也没有文丁的各称谓出现,证明“祊祭”第一大组卜辞是文丁卜辞的观点进行的。上文已详细分析了他们的所谓论据都是不能成立的。下面再分析一下黄组“祊祭”卜辞中的“父丁”、“母癸”称谓究竟指谁。
关于“母癸”称谓

关于“父丁”称谓的所指

由黄组“祊祭”卜辞中的“母癸”是指武乙之配,“父丁”是指文丁来看,在进行卜辞断代时,不能仅凭想当然就把同辈亲属称谓安排在一个世代里。黄组中的“母癸”是文丁对武乙之配的称呼(“妣癸”当然就是帝乙或帝辛对武乙之配的称呼了),“父丁”是帝乙对文丁的称呼,两个称呼不属于一个时代。其实,“祊祭”卜辞中的“母癸”称谓与“父丁”称谓从不在一版卜辞中出现,就已经说明此二称是不属于一个时代的了。
关于利用“卜辞内容”断代

以上的论证表明,徐、彭二氏对所谓“黄组一类”卜辞不分事类,不问辞例,将各种不同事类、不同文例的卜辞混杂在一起进行断代,其结果必然会出现错误、混乱和前后矛盾的现象。
对“黄组二类”卜辞的断代,徐、彭二氏也是从“字体特点”、“称谓”、“卜辞内容”3个方面进行的。
关于利用字体特点断代
前文已指出,徐、彭二氏利用字体将“黄组二类”分成A、B、C三个小类,但在断代时,却不是对每个小类都分别进行断代,而是将三个小类合并以“黄组二类”的名义进行断代,并且又主要是以“黄组二C类”作为“黄组二类”的代表进行断代的。由此笔者不明白作者费力将“黄组二类”分成A、B、C三个小类的作用是什么?他们又说:“从黄组二类字体与黄组一类字体有同版关系来看,黄组二类卜辞的上限也可及于帝乙之世”,这种说法又一次证明了他们认为一个王世只能有一种类型的卜辞。他们还说:“从黄组二类卜辞没有出现与何组、无名组字体同版的例子来看,我们认为黄组二类卜辞时代应晚于黄组一类卜辞”。总之,徐、彭二氏认为“黄组二类”卜辞是帝辛卜辞,但其上限“可及于帝乙之世”。
关于利用称谓断代
徐、彭二氏说:“黄组二类卜辞的重要称谓有武乙、武祖乙、文武丁、文武帝、妣癸”,“由于黄组卜辞二类中还没有可据于推断时代的‘父某’、‘母某’之称,要判断其时代是有困难的。”徐、彭二氏面对这么多的祖先称谓,却仅仅因为没有“父”、“母”辈的亲属称谓,就对卜辞断代犯难。不过他们找到了断代的突破口,就是“文武帝”一称,说:“以上称谓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文武帝’一称”。“文武帝”一称缺少日干名,它指哪一位先王,以往学者们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指文武丁,即文丁;[22]、[19]一种认为是指文丁之子帝乙。[23]、[9](P421—422)近年葛英会又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认为“文武帝”一称可指两个王,即它既可指文丁,也可指帝乙。[24]1980年,笔者在《说文武帝——兼略述商末祭祀制度的变化》一文中,对“文武帝”一称的所指作了详细考证,得出“文武帝”是指文武丁即文丁的结论。[19]徐、彭二氏在推断“黄组二类”卜辞的时代时,反对笔者的意见,认同葛英会的意见,即认为在丁日受祭的“文武帝”是指文武丁,在乙日受祭的“文武帝”是指帝乙。既然“黄组二类”中的“文武帝”可指帝乙,那么“黄组二类”的时代就应该是帝辛卜辞了。因此,对“黄组二类”卜辞的断代,关键问题还是要弄清“文武帝”一称的所指。
究竟如何考证没有日干名的“文武帝”一称的所指,这是个需要借助其它材料进行详细论证的问题,不是个简单地仅凭祭祀日期就能下结论的问题。
查黄组中有“文武帝”一称的卜辞有10多版,多为残辞。徐、彭二氏没有举出新的材料,他们只是对笔者过去提出的材料做出另外的解释。笔者在《说文武帝——兼略述商末祭祀制度的变化》一文中,是通过分析黄组中的祭祀卜辞来论证“文武帝”一称的所指的。早在1956年,陈梦家就曾举出10条有“文武帝”一称的卜辞,即《合集》35356(有两辞)、36173、36169、36167、36172、38230、36176、36175、36179,来证明“文武帝”是指帝乙。(20)各辞的《合集》号是笔者查对的。陈先生说:“以上凡干支未残者,皆于乙日祭文武帝,仅有一辞卜于甲日则可能是牢祭。如此文武帝应是帝乙。”[9](P421—422)这里,陈先生是要证明文武帝全于乙日受卜祭,所以“文武帝”的日干名应从卜祭日“乙”,为乙名王帝乙。笔者检查了这十条辞,发现:《合集》35356上有两条祭祀“文武帝”的卜辞,一条辞的卜日是“乙丑”日,另一条卜日的天干日残,地支日是“子”,根据后面的“丁丑”日,知卜日当是前一天的“丙子”日。《合集》36169祭“文武帝”的一辞干支日残,陈梦家释作的“大乙日”实是“翌日”的误释。《合集》36167是“祊祭”卜辞,所祭先王实非“文武帝”而是“文武丁”。《合集》36172、38230、36176、36179均无干支日。总计十条辞中,只有《合集》35356中的一辞、《合集》36173、36175三条辞是“干支未残者”,三条辞中前两辞的卜日是“乙丑”日,后一辞是“丁卯”日。所以陈先生列举的十条辞是无法证明“文武帝”的天干庙号的,因为它们没有统一的卜祭日。不过,笔者认为,陈先生的十条辞排列在一起却反映了一个规律:即不同文例、不同祭名的卜辞即使在祭祀同一位祖先时,也是没有相同的卜祭日的。不仅如此,检查黄组的祭祀卜辞可知,在祭祀同一个祖先时,如果只卜辞文例相同而祭名不同,或者祭名相同而卜辞文例不同,都能使卜祭日不相同(后者有特例)。
徐、彭二氏列举《合集》36168、36170、35356、36173、36167五版卜辞反驳笔者总结的上述规律,他们说这五版卜辞“就是祀典名相同,卜辞文例不同,卜祭日与祖、妣名一致的例子,因此,在丁日受又祔祭的文武帝指的是文丁,在乙日受又祔祭的文武帝指的是帝乙”,也即认为《合集》36168、36170两版卜辞中于丁日祭祀的“文武帝”是指文丁,是帝乙卜辞;35356、36173、36167三版卜辞中于乙日祭祀的“文武帝”是指帝乙,是帝辛卜辞。前已指出,《合集》36167是“祊祭”卜辞,所祭实非“文武帝”而是“文武丁”,文武丁也不是在乙日被祭,而是在丙日被祭祀的。徐、彭二氏并说前两版卜辞的字体为“黄组一类”,后3版卜辞的字体为“黄组二类”,即“黄组二类”卜辞是帝辛卜辞。徐、彭二氏上举四版卜辞(剔除《合集》36167非祭文武帝一辞)中的《合集》36168、36170两辞文例与祀典名均相同,但《合集》35356和36173两辞的文例与祀典名都不相同。对这种有在丁日祭也有在乙日祭的“文武帝”的日干名如何求得,并不是如徐、彭二氏所说的那么简单,即并不是“文武帝”在哪一日祭祀,他的日干名就应是那一日(天干日)。
众所周知,商代的祭祀种类繁多,对同一位祖先往往都进行多种不同的祭祀。卜辞反映,对同一位祖先由于使用的祭名不同,或者卜辞的文例不同,都能使祭祀日期不同;相反,有的祭名相同,卜辞文例不同,但祭祀日期却又相同(如周祭)。情况错综复杂。目前对第五期即黄组卜辞祭祀祖先的情况,经过国内外几代学者的研究已经比较明确了。笔者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第五期黄组卜辞中的“周祭”卜辞、“祊祭”卜辞以及其它一些祭祀卜辞做过探讨,基本上掌握了这些卜辞的契刻规律,可以用来回答徐、彭二氏提出的关于“文武帝”一称的天干庙号问题,也即“文武帝”一称的所指问题。

前两版卜辞都是卜问祭祀阳甲的,两条辞的类型不同,祭名不同,但卜祭日却都是与王名一致的,即都是在甲日祭祀阳甲。第三版是祭祀大乙之配妣丙的,与第二版一样是王宾卜辞,(21)周祭先妣只有“王宾”卜辞一种类型。祭祀日期与妣名一致。笔者考察了220多条以五种祀典祭祀先王、先妣的卜辞,仅发现2条卜祭日与先王名不一致的例子(《合集》35621、35729),未发现与妣名不一致的情况,这就充分说明了卜祭日与王名(或妣名)一致是周祭卜辞的特定规律。因此,只要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可以在王名或妣名残缺时,根据卜祭日求得,或者在卜祭日残缺时,根据王名或妣名求得。
但有在同一种类型的卜辞中,祭祀同一个祖先时,由于使用的祭名不同,就能够造成卜祭日的不同,例如:
丙申卜,贞:王〔宾〕外丙彡日,〔亡〕尤?
庚子卜,贞:王宾大庚彡日,亡尤?《合集》35566
该版的两条辞分别以五种祀典的彡祀祭祀外丙和大庚,祭外丙在丙日,祭大庚在庚日,卜祭日与王名一致。但在下面两版卜辞中:
乙酉卜,贞:王宾外丙彡夕,亡尤? 《合集》35532
己卯卜,贞:王宾大庚彡夕,亡〔尤〕? 《合集》35567
这是以“彡夕”之祭祭祀外丙和大庚的,祭外丙在乙日,祭大庚在己日,即卜祭日都比王名提前一天。“彡夕”之祭不是周祭祭祀,检查行“彡夕”之祭的“王宾”卜辞,卜祭日都是选在先王名的前一天的,没有一条例外,(22)黄组卜辞的“彡夕”之祭不适用于女性祖先。因此,卜祭日比先王名提前一天是以“彡夕”为祭名的“王宾”卜辞的特定规律。我们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可以对残辞进行互补,即如果王名残缺,可由卜祭日求得,如果卜祭日残缺,也可由王名求得。总之,上述四条卜辞表明,卜辞的文例相同,即都是“王宾”卜辞,但是因为祭名不同,即使在祭祀同一个祖先时所选的卜祭日就不相同。

总之,第五期的周祭卜辞、“彡夕”祭卜辞、“祊祭”卜辞证明,掌握一种类型卜辞的规律是很重要的,它对我们考察一些祖先的日干名或卜祭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考察“文武帝”一称的日干名,也必须要遵循上述原则,即找出一种既适用于文武帝,也适用于其他祖先的卜辞,这种卜辞不但要文例相同,而且祭祀方法也要相同,先从祭祀其他有日干名的祖先的卜辞中,找出这种类型卜辞卜祭日与祖先名之间的特定规律,然后再用这个规律去考察祭祀文武帝的卜辞,从而就可以准确无误地求得文武帝的日干名了,“文武帝”一称的所指也就清楚了。
前已说明,目前见到的祭祀文武帝的卜辞只有十多条,而且又多是残辞,这就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我们仍发现其中有与其他祖先使用相同文例、相同祭祀的卜辞,这种卜辞的文例是:“干支卜贞翌日干支王其又升于祖先名宓正王受又”,它不但适用于文武帝,还适用于武乙及妣癸。在这种文例的卜辞中,卜祭日与祖先名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先看祭祀武乙的卜辞,共有3条:
(1)癸酉卜,贞:翌日乙亥,王其又升于武乙宓,正,王受又=。《合集》36123
(2)〔甲辰〕卜,贞:翌日乙巳,王其又升〔于武〕乙宓,正,王受又=。《合集》36124
(3)甲午卜,贞:〔翌日〕乙未,王〔其又升〕于武宓,〔正〕,王受〔又=〕。《合集》36170
第(1)辞于癸酉日卜问,问在未来第三天的乙亥日商王要到武乙的庙室里去行又、升、正之祭,王是会得到(上帝)的保佑吧?这里乙名王武乙是于乙日(乙亥日)被祭祀的,祭日与所祭祖先的日干名一致。第(2)辞卜日残,祭日是乙巳日,根据“翌日”多指次日的原则,可补卜日为甲辰日;王名存日干名“乙”,由于除武乙一名乙名王外,未见有其他乙名王受此种祭祀,故知所祭之祖先仍是武乙。此辞与上辞一样,乙名王武乙仍是于乙日(乙巳日)受祭的,祭日仍是与所祭祖先的日干名一致的。第(3)辞于甲午日卜问,残掉“翌日”二字,祭日是甲午日的第二天乙未日,所祭之祖先省略了日干名,单称“武”,由于黄组卜辞中对武乙有单称“武”的(《合集》36058),所以该辞所祭是武乙(其实,由上两辞可知,该辞在乙日受祭的“武”的日干名必是“乙”,即是“武乙”),则该辞与前两辞一样,乙名王武乙仍是于乙日(乙未日)受祭的,祭日也是与所祭祖先的日干名一致的。
祭祀妣癸的卜辞又是怎样的呢?卜辞:
(4)〔壬寅〕卜,贞:翌日癸卯,王其〔又升于〕妣癸宓,正,王受又=。《合集》36315
该辞卜日残,祭日是“癸卯”,根据“翌日”可补卜日是癸卯日的前一天“壬寅”日,祭祀的祖先是“妣癸”,于癸卯日祭祀妣癸,则祭日是与所祭先妣的日干名一致的。
由以上祭祀武乙和妣癸的卜辞可知,在“干支卜贞翌日干支王其又升于祖先名宓正王受又”这种文例的卜辞中,卜日与祖先名是没有关系的,而祭日(即“翌日”之后的天干日)则是与所祭的王名或妣名一致的,即祭武乙在乙日,祭妣癸在癸日,这就说明了:祭日与祖先名一致是这种文例卜辞的特定规律。因此,我们只要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可以在祖先名缺少日干名时,根据“翌日”之后的祭日(天干日)来求得,或者在祭日残缺时,根据祖先的日干名来求得。而“文武帝”一称正是因为缺少日干名才引起各家的争论,现在我们就可以利用上面所揭示的规律来考察祭祀“文武帝”的同种文例的卜辞,辞中“翌日”之后的祭日为何,则“文武帝”的日干名就为何。请看下版卜辞:
(5)丙戌卜,贞:翌日丁亥,王其又升于文武帝,正,王受又=。《合集》36168
此辞与前举祭祀武乙和妣癸的卜辞文例相同,只在祖先名“文武帝”后省略了一个“宓”字,我们曾在分析“祊其牢”、“宓祊其牢”、“宗祊其牢”卜辞时,均发现有省略“祊”字的例子,但都不影向卜祭日与祖先名之间的关系。[19]而“宓”与“祊”意义相同,均指庙室等建筑物,[25]所以此辞省略“宓”字也不影向祭日与祖先名之间的关系。该辞于丙戌日卜问,问于第二天丁亥日对“文武帝”举行又、升、正之祭,按照上面揭示的此种类型卜辞的规律是:卜日与祖先名之间没有关系,而祭日则是与祖先名一致的。因此,在丁亥日祭祀的“文武帝”的日干名应从祭日为“丁”,即“文武帝”应是丁名王。同样的辞例还找到一条,它与前举的第(3)辞(《合集》36170)祭祀武乙的卜辞同版,而且卜辞文例也完全相同,辞为:
(6)丙戌卜,贞:〔翌日〕丁亥,王其〔又升〕于文武〔帝宓〕,〔正〕,王受〔=〕。《合集》36170
该辞与第(5)辞完全相同,也是于丙戌日占卜,祭日也为丁亥日,祭祀的祖先也是“文武帝”,辞中“文武帝”的“帝”字残掉。何以知道“文武”之后必为“帝”字?这可用同类型的第(5)辞加以印证,还有《合集》36169、36171也可证明此类卜辞祭祀的是“文武帝”一称:
(7)□□卜,贞:翌日 ,王其又升〔于〕文武帝宓,正,王受又=。 《合集》36169
(8)□□〔卜〕,贞:翌日 ,〔王其〕又升〔于文武〕帝,正,〔王受〕又=。 《合集》36171
该两辞均因为残掉了干支日无法作为考证文武帝日干名的例证,但它们可证此类卜辞所祭“文武”之后必为“帝”字。第(8)辞所残是“文武”二字,而第(6)辞所残是“帝”字,因此这两辞可以互为补证。总之,第(5)、(7)、(8)三条卜辞都证明了第(6)辞“文武”之后所残之字必为“帝”字,所祭祖先名必是“文武帝”。第(6)辞与第(5)辞一样,也是于丁日(丁亥日)祭祀文武帝。同样,根据此类卜辞祭日必与祖先名一致的规律,在丁日受祭的文武帝的日干名必是“丁”,即文武帝是指丁名王。那么,“文武帝”一称是指哪个丁名王呢?查文丁以前的各期卜辞中均未见“文武帝”一称,也就是说,康丁及以前各丁名王均无称作“文武帝”的,所以此“文武帝”必是指文武丁无疑。
“干支卜贞翌日干支王其又升于祖先名宓正王受又”这种形式的卜辞所祭的祖先名有武乙、武、文武帝、妣癸四称,也就是说,这种形式的卜辞祭祀的是武乙、文丁二王和妣癸。笔者曾证明“祊祭”卜辞中的“母癸”是文丁对其母即武乙之配的称呼,那么,此种文例卜辞中的“妣癸”当是帝乙对武乙之配的称呼了。“祊祭”卜辞中武乙与“母癸”同版被祭,“干支卜贞翌日干支王其又升于祖先名宓正王受又”卜辞中,武乙与“妣癸”同时被祭,所以黄组中庙号为“癸”的女祖先是武乙之配,当无疑问。因此,上述祭祀武乙、“文武帝”、“妣癸”的卜辞应是帝乙卜辞。
需要指出的是,卜辞中除了丁日祭文武帝外,还有两条乙日祭文武帝的例子:
(9)乙丑卜,贞:王其又升于文武帝宓,其以羌其五人,正,王受又=。酒。 《合集》35356
(10)乙丑卜,〔贞〕:〔王〕其又升〔于文〕武帝〔宓〕,三牢,正,〔王受〕又=。 《合集》36173
这两条辞都是于乙丑日卜问以又、升、正之祭祭祀文武帝的,但所用祭品不同,第(9)辞是用五个羌人,第(10)辞是用“三牢”,即3头经过特殊饲养的牛进行祭祀。这两条辞的文例与前举的第(5)、(6)、(7)、(8)四辞均不同,一是没有“翌日干支”,二是祭品不同,是用人牲或牛牲。因此,与前面祭祀文武帝的第(5)、(6)、(7)、(8)辞相比,可以说明即使祭名相同(都为又、升、正之祭),但如果卜辞文例不同,祭品不同,卜祭日是不相同的。至于为什么祭丁名王文武帝要选在乙日,这也不奇怪,前已举彡夕之祭、祊祭卜辞祭祀祖先时都不选在祖先的日名之日举行。现因缺乏以这两种牲品祭祀其他祖先的辞例,所以还无法进行比较,或许这是当时规定,即用牺牲(人牲、牛牲等)祭祀时要选在乙日祭祀丁名王也未可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文武帝”既然已被证明是指文武丁,就绝不会只根据有乙日祭祀的现象就又定其是指帝乙。

(11)乙丑卜,贞:王其又升于文武帝宓,其以羌其五人,正,王受又=。酒。
这是一块龟甲,上面刻有两条祭祀文武帝的卜辞。第一条辞前面已引,即第(9)辞。该辞于乙丑日卜问以五个羌人祭祀“文武帝”,按着徐、彭二氏的意见,在乙日被祭的“文武帝”是指帝乙,属帝辛卜辞。同版的第二条辞的卜日天干日残,只存地支“子”,根据后面的祭日“于来丁丑” ,[26](P31-32)(23)辞中“来”字后面的天干日只存两小竖划“”,似是缺刻横划的“丁”字。几位学者均如此认定,如李学勤。知卜日当是前一天的“丙子”日,则该辞“文武帝”是在“丁丑”日受祭的,按徐、彭二氏的意见,在丁日受祭的“文武帝”是指文丁,则该辞是帝乙卜辞。如果果真如此,就会出现下面的现象:即在一块龟甲上,其上下紧挨着的两条辞,一条于乙丑日卜问的是帝辛卜辞,在11天后的丙子日卜问第二天丁丑日祭祀的是帝乙卜辞,帝辛卜问的在前,帝乙卜问的在后,王世颠倒;或者说帝乙在丙子日卜问于第二天丁丑日祭祀文武帝,过了四十九天之后,帝辛在乙丑日再卜问祭祀文武帝,两个王祭祀的文武帝又不是指同一个人,有可能吗?这样解释该版两条祭祀文武帝的卜辞,不是很离谱吗!而用文武帝是指一个王文丁,帝乙在相距十一天的时间内,两次卜问祭祀文武帝,则文通意顺。徐、彭二氏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找根据,还说于丁日祭文武帝的卜辞的字体属于“黄组一类”,于乙日祭文武帝的卜辞的字体属于“黄组二类”,将同一版祭祀同一位先王的卜辞分属于两个王世。但检查该版的两条卜辞,实在看不出它们的字体有什么明显区别,两条辞的字体出于一人之手无可质疑。由此可以看出,所谓字体分类,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有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甚至可以任由个人随意决定。总之,“文武帝”一称只能是指文武丁即文丁,徐、彭二氏说还指帝乙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帝乙的称谓

这里还需附带说一下,徐、彭二氏以字体分类,得出:“黄组二类卜辞相对于黄组一类卜辞来说数量较少,卜辞内容也不如一类丰富”。因为他们认定“黄组一类”是帝乙卜辞,“黄组二类”是帝辛卜辞,所以,这个结论就是说,帝辛卜辞的数量比帝乙卜辞的数量要少,卜辞内容也不如帝乙丰富。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于他们没有系统地研究过黄组卜辞,他们的断代还只是如同对早期卜辞那样,过多地依赖祖、父、妣、母等亲属称谓,如他们说:“从断代的主要标准——称谓来看,真正属于帝辛祭祀父祖母妣的卜辞没有几片可以认定。”他们不知道到了商代末期黄组卜辞的时代,商人的祭祀制度、亲属称谓制度等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时对父辈、祖辈祖先往往也是直称庙号,不再加亲属称谓“祖”、“父”、“母”、“妣”等。徐、彭二氏没有系统整理、研究过黄组卜辞中记录的诸多重大事类,如周祭、祊祭、战争(征盂方、征人方)等等,故其慨叹:“在没有对黄组卜辞字体进行分类之前,要寻找帝辛卜辞,区分帝乙、帝辛卜辞,其困难是相当大的。”而他们的字体分类,是在打乱了各种事类的基础上,仅仅凭个人的主观臆断,将黄组卜辞按字体分成两大类,仅仅直观地凭“父丁”、“母癸”两个称谓,将这两个称谓放在一个时代,就断定“黄组一类”为帝乙卜辞;仅仅靠分解“文武帝”一称,就定“黄组二类”为帝辛卜辞。正如李学勤、彭裕商所说:“分类的精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断代的质量”。[4](P17)我们说,按字体分类,很难做到“精确”,自然也就无法保证断代的“质量”,从上文揭示的徐、彭二氏分类的混乱和断代的错误就可证明。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秉承了李学勤提出的“先对字体分类,再进行断代”的错误的断代方法。
对于第五期黄组卜辞的断代,前辈学者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如董作宾、陈梦家、岛邦男(日本)、许进雄(加拿大)等,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先对第五期卜辞记录的事类进行分类,然后通过研究各种事类的卜辞,来探讨商代末期各种制度的构成和演变;探讨各种文例卜辞的特点;探讨各种事类卜辞所属的时代。他们重点研究的事类有周祭、“丁”祭(即“祊祭”)、征战等等,得出这些卜辞分属于帝乙和帝辛二王,其中帝辛卜辞并不在少数,卜辞内容也与帝乙一样丰富,具体请参阅他们的著作。[27](第十一章)上世纪80年代以后,笔者也步前辈学者的后尘,对第五期的周祭、祊祭等类卜辞进行了详细地研究,[20]、[19]、[28]进一步论证出黄组卜辞含有文丁卜辞:具体是论证周祭卜辞分属于文丁、帝乙、帝辛3王;祊祭卜辞分属于文丁、帝乙2王。笔者还通过复原黄组卜辞的周祭祀谱,得出文丁在位22年,帝乙在位25年,帝辛在位34年。[20](增订本第五章)“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商后期年代整合的结果是:文丁在位11年,帝乙在位26年,帝辛在位30年,[29](P61)与笔者对帝乙、帝辛二王的在位年数的推定结果相近,这两种结果都显示,帝辛的在位年数比帝乙的在位年数还要稍长一些。再看笔者复原帝乙、帝辛周祭祀谱所使用的材料:复原帝乙祀谱用甲骨材料69条;复原帝辛祀谱用甲骨材料56条,另外还有12条金文材料,共是68条。二者材料数量也相差不多。因此,徐、彭二氏说帝辛卜辞材料较少,卜辞内容不够丰富,只是没有根据的臆断。
由以上徐明波、彭裕商对黄组卜辞的分类和断代,可以看到,以字体对卜辞进行分类缺乏确定性,难以掌握。本文揭出的事实证明:以字体分类,不但在观察者之间会产生差异,就是观察者本人前后也会发生改变。如李学勤、彭裕商的分组分类与黄天树的分类分组,在数目和组别、类别上都有差异;李学勤对“无名黄间类”卜辞的命名与断代,彭裕商对黄组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前后都发生了改变……等等。这些情况说明,以字体分类即使是在提出者和赞同者之间都难以达成共识,更何况别人。李学勤说他的分类断代方法“应用起来还是简易适用的”,但事实上连他的追随者黄天树都感觉并非如此,黄氏说:“字体并非一成不变,情况错综复杂。对同一种客观现象,由于个人观察上有出入,有时会作出不同的分析,因此,所分出的类与实际情况就不一定相合,这是甲骨分类难以掌握之处” ,[7](P8)一个说“简易适用”,一个说“难以掌握”。李、彭二氏曾言“分类是断代的基础,分类的精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断代的质量”,[4](P17)因此,分类的模糊与莫衷一是,绝对保证不了断代的质量。总而言之,以字体对陈梦家的各个卜人组再进行细分类,再对各细类进行断代的方法,在理论上看起来似乎有理,但在实践中却是难以行得通的。

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