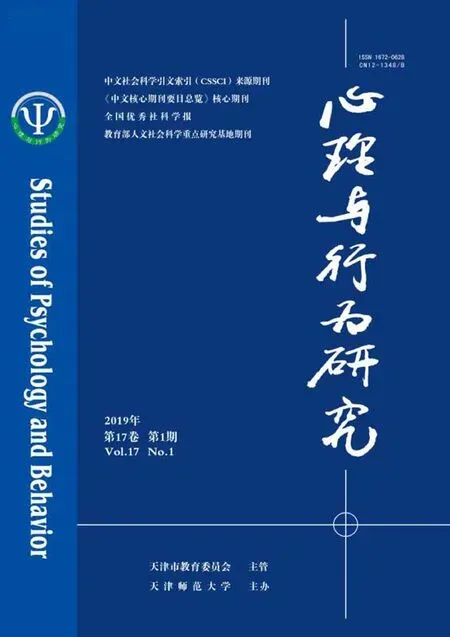“对不起”有用吗:道歉对群际宽恕的影响 *
2019-03-12张田傅宏
张 田 傅 宏
(1 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南京 210094) (2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 210028)
1 引言
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宽恕是人际侵犯发生以后,被侵犯者对侵犯者消极因素(例如回避、报复等)的释放过程,取而代之的是对侵犯者的同情和爱(compassion and love)(Enright, Gassin,& Wu, 1992)。可见,宽恕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侵犯,然而,侵犯并不总是发生在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亦会有侵犯和伤害。例如,对中国人民而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无疑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外群体侵犯之一。然而,我们在谴责军国主义的同时,也应将军国主义分子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所说,“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张连红(2000, 2003)的研究也显示,即使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其对待历史的态度更多的也是宽容。这就涉及宽恕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群际宽恕(Inter-group Forgiveness)。
相对于人际宽恕已经有明确的界定而言,群际宽恕的界定尚不完善,概念表述也相对比较模糊(艾娟, 2014)。有学者借鉴人际宽恕的概念,从消极因素减少和积极因素增加的角度对群际宽恕进行了界定,将群际宽恕看作是群体成员对曾经侵犯过本群的外群体所具有的报复感、愤怒感以及不信任感的减少,同时有意识地去理解、接近对方群体并积极地参与到对方群体中去的行为(Staub, 2006; Tam et al., 2007)。除此之外,Swart和Hewstone(2011)则从人际宽恕与群际宽恕区别的角度出发,对群际宽恕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四点区别:第一,人际宽恕源自于个体间的人际互动,而群际宽恕则发生于群体之间,而且通常伴随有政治色彩;第二,人际宽恕通常出现在冒犯者的真诚道歉之后,相反,群际宽恕发生之前的道歉通常是官方层面的道歉,这种道歉的真诚程度不得而知。第三,人际宽恕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个体间冒犯所造成的伤害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退,而群体冒犯造成的伤害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消除的;第四,在人际宽恕中,冒犯者与被冒犯者的身份比较容易界定,而在群际宽恕中,面对不同群体间的冲突和纷争,有时很难界定到底哪一方是冒犯者,哪一方是受害者。
对于群际宽恕影响因素,艾娟(2014)将其归纳为群体认知、群体情感和群体行为三个方面。其中,在群体行为层面,道歉是常常被提及的一种影响群际宽恕的群体行为,早期的研究显示,道歉在群际宽恕过程中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近期的研究却提示我们,道歉对于群际宽恕的作用并没有那么简单。既有研究的结论与早期研究一致,也有研究发现,道歉并不能促使群际宽恕的发生。
2 道歉对于群际宽恕的不同作用
2.1 道歉对于群际宽恕的促进作用
在群际宽恕的研究中,群际侵犯事件是必不可少的,而无论是基于真实侵犯事件还是虚拟侵犯事件,都有研究支持道歉对于群际宽恕的促进作用。例如,Brown, Wohl和Exline (2008)基于真实侵犯事件研究了道歉对于群际宽恕的作用。研究中,研究者向加拿大被试描述了阿富汗战争中,一架美军战斗机向加拿大军队投下炸弹造成加军伤亡的事件。被试被分为两组,其中一组被告知美国国防部对该事件表达了深深的歉意,另一组被试则被告知美方并未就此事做出过道歉。结果显示,无道歉组的被试更多地表现出对美国人的回避和报复心理,而道歉组的被试则更愿意宽恕美国人,甚至依然认为加拿大应该出兵阿富汗支持美国。
Leonard, Mackie和Smith(2011)则通过虚拟现实事件研究了道歉对于群际宽恕的作用。他们首先向大学生被试描述了一件虚拟的事件:大学里的一些教授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并在公开信中猛烈抨击了学生们的校园文化。随后,这些大学生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前者被告知这些教授已经为他们的言行作出了道歉,而后者则没有道歉。结果发现,实验组被试的宽恕水平要显著高于控制组。
除了以上两例,还有很多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Hamber, 2007; Montiel, 2002; Mullet & Neto,2009; Philpot & Hornsey, 2011; Wohl, Branscombe, &Klar, 2006)。总结这些研究可以发现,学者们大多认为,道歉并非直接作用于群际宽恕。一方面,有的研究者认为,道歉对于群际宽恕的作用受到某些变量的调节,因此在某些变量条件下,道歉对于群际宽恕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例如Hayes(2013)认为,对于侵犯群体可改变性的认知,决定了道歉对于群际宽恕作用的大小,如果被侵犯群体认为对方群体是可以改变的,尤其是往积极方向改变,那么在得到对方群体的道歉后,群际宽恕就更容易产生。另一方面,还有研究者认为,道歉是通过某些变量而对群际宽恕产生作用的。例如Leonard等人(2011)基于群体情绪理论,认为道歉能够有效降低群体的消极情绪(例如群体愤怒)、提升积极情绪(例如自尊和满意度),从而提高宽恕对方群体的可能性。即群体情绪作为中介变量对道歉和群际宽恕之间作用的影响。
2.2 道歉对于群际宽恕的非促进作用
尽管从前文的叙述来看,近期的研究大多支持道歉对于群际宽恕的促进作用,然而Philpot和Hornsey(2008)的研究却提示我们,问题可能没有那么简答:他们以澳大利亚人为研究对象,基于不同时期澳大利亚遭受到的外群体侵犯事件(例如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对澳大利亚战俘的虐待,法国在南太平洋进行核爆实验对澳大利亚的影响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在所有研究中,被试均被随机分配到道歉组和无道歉组。结果显示,尽管不同组的被试在某些方面有所差异(例如满意度),但在群际宽恕层面,两组并没有显著差异,即该研究并不支持道歉对于群际宽恕的促进作用。
此外,Chapman(2007)以及Bombay,Matheso和Anisman(2013)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前者基于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South Africa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的资料而进行的文本分析显示,作为种族隔离政策的受害群体成员,他们很少表现出对侵犯群体的宽恕,即使有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宽恕的决定,这也和对方群体是否做出过道歉没有任何关系。后者基于加拿大的“土著同化政策”①对加拿大土著居民进行了研究,该政策被Gebhard(2017)看做是加拿大历史上最负面的事件之一。尽管加拿大原总理哈珀已于2008年6月在议会众议院向同化政策的受害者表示了正式的道歉,但该研究显示,道歉并不足以提升受害群体的宽恕水平。
对此,研究者们也有着不同的解释,总的说来,以下几种解释较为典型:第一,在基于历史事件的研究中,被试并非群体侵犯的直接受害者,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并没有选择宽恕的权利,而且在他们看来,选择“不宽恕”侵犯群体对侵犯的直接受害者而言是公平的(Philpot & Hornsey,2008)。第二,如果群体侵犯对于被侵犯群体的不利影响延续至今,那么道歉并不能起到促进群际宽恕的作用,例如在Bombay等人(2013)的研究中,当“土著同化政策”的受害群体依然能够感受到生活中的歧视和区别对待时,群际宽恕的水平会大大降低。第三,宽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产生是随着情绪体验和认知加工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发展的过程,而当前群际宽恕的研究范式并不能给被试以充足的时间对群体侵犯事件进行情绪体验和认知加工,进而不利于群际宽恕的产生(Hornsey & Wohl,2013)。
3 道歉对群际宽恕作用差异的分析
从上文的论述不难看出,尽管早期的研究更倾向于认为道歉对于群际宽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进入本世纪以来,有关道歉对于群际宽恕作用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研究显示,道歉能够提升受害群体的宽恕水平;然而也有研究则认为,道歉对于群际宽恕并没有直接的作用。甚至来自于相同研究者的研究,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Philpot和Hornsey既有研究支持前一个结论(Philpot & Hornsey, 2011),也有研究支持后一个结论(Philpot & Hornsey, 2008)。
那么,面对这种差异,甚至是矛盾之处,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呢?进一步梳理文献可以发现,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可能是因为道歉并不能直接决定群际宽恕水平的高低,在两者之间,还有诸多因素在发挥作用,如果脱离这些因素而单独讨论道歉与群际宽恕的关系,结论自然会存在差异。换句话说,道歉对于群际宽恕的作用受到其他调节变量的影响。在诸多因素之中,以下几个因素常常被提及。
3.1 群体身份的认同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1974),个体对于所在群体的认同程度将决定他处理与群体相关事件的态度。Jetten和同事们的研究也显示,在诸多群体事件中,群体身份认同都起到了关键的调节作用,即高群体身份认同者更倾向于选择对群体有利的态度和行为(Jetten, Spears, & Postmes,2004)。例如,高群体身份认同者会认为本群体的成员更有价值(Pratto & Glasford, 2008)。
因此,与群体密不可分的群际宽恕也可能受到群体身份认同的影响。例如在前文所述的Brown等(2008)借用真实历史事件对道歉和群际宽恕关系所进行的研究中,尽管结果显示,无道歉组被试更多地表现出对侵犯群体的回避和报复心理,而道歉组的被试则更愿意宽恕对方群体。然而,作者还特意指出,并非所有的被试都表现出相似的反应,对于那些高群体身份认同者(即该研究中那些认为作为一名加拿大人对自己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人)而言,道歉对于群际宽恕的作用不及低群体身份认同者(即该研究中那些认为加拿大国籍对自己而言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人)。图1较明显地表示出了这种差异,即无论侵犯群体道歉与否,受害群体中的高群体身份认同者在回避和报复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低身份认同者。
此外,群体身份认同不仅直接调节道歉与群际宽恕之间的关系,它还会影响个体对于道歉的认知,进而影响道歉对群际宽恕的作用。例如前文所列举的Philpot和Hornsey(2011)的研究,该研究发现当被试确定侵犯群体已经作出道歉时,他们对侵犯群体的宽恕水平要显著高于那些认为侵犯群体没有道歉的被试。然而,作者却进一步指出,道歉与群际宽恕之间的这种显著关系比较微弱,仅能解释4%的结果变异。于是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道歉与群际宽恕的关系还受到群体身份认同的影响,低身份认同者更愿意相信侵犯群体已经做出了道歉(即该研究中日本对于二战的道歉),进而选择宽恕侵犯群体;相反,高群体身份认同者不愿意相信侵犯群体已经作出道歉,或者认为对方的道歉不够真诚,因而不愿意宽恕对方群体。
对于为什么群体身份认同能够调节道歉与群际宽恕的关系,Hornsey和Wohl(2013)提出了两点猜测:一是高群体身份认同者对于什么是道歉,尤其是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道歉有着更高的标准,因此会出现不同身份认同者对道歉认知的差异;二是不同群体身份认同者会接收到不同来源的信息,尤其是关于群体侵犯事件的信息,这造成了他们对于侵犯群体及其道歉的不同认识。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高群体身份认同者之所以不认可侵犯群体的道歉,进而选择不宽恕对方群体,是因为这种受害群体的身份能够使得本群体更加团结,并且能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抗侵犯群体(Noor, Shnabel, Halabi, & Nadler, 2012;Sullivan, Landau, Branscombe, & Rothschild, 2012)。
3.2 道歉所蕴含的情绪
Wohl, Hornsey和Bennett(2012)结合两种情绪的划分(一是害怕、愤怒、高兴等人和动物所共有的初级情绪, 二是羞愧、嫉妒、内疚等人类所特有的次级情绪),提出了一个概念——亚人性化(Infrahumanization),指的是本群体成员认为侵犯群体成员缺乏人类所必备的次级情绪。Leyens等人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人们对于初级情绪表达的感受,在本群体和外群体之间并没有差异;相反,相比外群体而言,人们却能更多地感受到本群体次级情绪的表达(Leyens,Demoulin, Vaes, Gaunt, & Paladino, 2007; Paladino,Vaes, Castano, Demoulin, & Leyens, 2004)。
然而,与道歉相联系的情绪往往表现为次级情绪,由于“亚人性化”观念的存在,受害群体不认为外群体侵犯者能够表达出羞愧、内疚、懊悔等次级情绪,因而选择不接受、不认可对方的道歉,进而阻碍群际宽恕的产生。Wohl等人(2012)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研究中加拿大被试被分到两组,其中一组被告知,加拿大士兵意外地杀害了来自于阿富汗国家警察的盟军士兵;另一组则被告知,盟军士兵意外地杀害了加拿大士兵。尽管两组被试都被告知,军方部门已经为此做出了道歉,但第一组被试感受到的次级情绪依然多于第二组被试,同时前者表现出的宽恕水平也更高。
其实不仅是初级情绪和次级情绪之间存在差异,甚至同为次级情绪,其对于受害群体的影响也可能有所差异。例如,有学者发现,同样是道歉,当侵犯者因为内疚(guilt)而道歉时反而会引起受害群体的不满,而当侵犯者因为羞愧(shame)而道歉时,受害群体的这种不满情绪会明显降低(Giner-Sorolla, Castano, Espinosa, &Brown, 2008)。可见,道歉所蕴含的情绪表达是极为丰富的,并且会影响受害群体的宽恕决定。
3.3 人际信任
在包括群体道歉在内的群体互动过程中,群体间的人际信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Hornsey, 2005;Hornsey & Imani, 2004)。例如,前文指出,道歉有时并不能提升受害群体的宽恕水平,究其原因,我们可以认为是受害群体不信任对方做出了真正的道歉、不信任对方伴随道歉而表达出的情绪、不信任道歉能够修复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等。基于此,Hornsey和Wohl(2013)提出一个道歉影响群际宽恕的人际信任模型(图2),该模型较为完整地描述了信任是如何影响道歉与群际宽恕之间关系的。
该模型将个体所处的情境分为高信任情境和低信任情境两种,这两种情境的划分源自于个体、群体互动情境和道歉本身三个因素。首先,在个体因素中,Hornsey和Wohl认为,具有高信任取向、低群体身份认同、与对方群体接触较多的个体更适合被划入高信任情境,反之则被划入低信任情境。其次,在群体互动因素中,群体侵犯的意图、伤害程度、侵犯群体所负的责任、群体距离、共同的身份认同等是区分高信任情境和低信任情境的关键因素。第三,在道歉本身这个因素中,道歉伴随的初级或次级情绪、侵犯群体内部对于道歉的支持度会影响两种信任情境的划分。
在不同的信任情境下,道歉有着不同的过程。在高信任情境下,接受道歉的群体并不怀疑侵犯群体道歉的目的性和真实性,在此过程中,道歉被表现为一个和解的姿态;在低信任情境下,接受道歉的群体对侵犯群体道歉的目的性和真实性表示怀疑(例如怀疑侵犯群体是迫于压力、为了躲避惩罚或为了树立一个良好的道德形象而道歉等,并非出于真心地道歉),在此过程中,受害群体会仔细甄别对方道歉的真实性,并且严密关注对方当前或今后可能表现出的行为是否会对本群造成再次伤害。
经过这样的过程,受害群体在不同信任情境下所表现出的行为结果也各不相同:在高信任情境下,道歉能使受害群体感受到对方的悔意,从而提升满意度和宽恕水平;反之,在低信任情境中,道歉并不能使受害群体感受到对方的悔过之心,进而阻碍满意度和宽恕水平的提升。
4 研究展望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看出,道歉对于群际宽恕的产生具有明显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是简单的促进或阻碍作用,而是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研究,对于道歉对群际宽恕作用的解释并不一致。然而,在明确了这一点以后,依然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值得后续的研究去深入探讨:
首先,宽恕涉及侵犯者和被侵犯者两个方面。在人际宽恕层面,除了宽恕认知和行为的主体——被侵犯者以外,近年来,从侵犯者角度出发进行的宽恕研究也日益增多(例如Wallace,Exline, & Baumeister, 2008; 张田, 傅宏, 薛艳, 2016;张田, 傅宏, 朱婷婷, 2017)。但在群际宽恕层面,绝大多数研究还集中于被侵犯者群体的层面,道歉与群际宽恕关系的研究亦是如此。然而,侵犯群体是如何看待道歉的、他们对于道歉有什么体验,这些因素可能也会对道歉与群际宽恕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正如前文提及的信任模型所指出的,侵犯群体内部对于道歉的支持度会影响两种信任情境的划分,进而对群际宽恕的产生造成影响。基于此,Zaiser和Giner-Sorolla(2013)就提示,从侵犯群体出发而进行的相关研究值得我们关注。
其次,道歉的类型有很多,但目前的研究并没有将这些类型加以区分。例如有的研究中是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的道歉(例如Philpot & Hornsey,2011),有的研究中是一个人对一个群体的道歉(例如Giner-Sorolla, et al, 2008),还有的研究中是某个部门对一个群体的道歉(例如Brown et al., 2008)。这些道歉的类型并不相同,它们对于包括群际宽恕在内的群体心理所产生的影响是否也有差异?对于这些差异的探索,能否在现实生活中帮助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解决冲突?这些问题值得后续的研究加以关注。
第三,之所以道歉对于群际宽恕的作用尚存在差异,本文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道歉并不能直接决定群际宽恕水平的高低,在两者之间,还有诸多因素在发挥作用,其中群体身份认同、道歉所蕴含的情绪、人际信任三个因素被重点介绍。然而,我们相信,除此之外,依然还有很多因素需要挖掘。例如Philpot和Hornsey(2008)的研究发现,相比官方的道歉,侵犯群体成员在个体层面上的道歉更能促进群际宽恕的产生。可见,道歉的主体也是可能影响道歉与群际宽恕关系的因素之一。因此,对于其他调节因素的探寻,也是后续研究可以关注的一个方向。
最后,与个体层面的人际宽恕不同,群际宽恕发生于群体之间,通常伴随有政治色彩(Swart& Hewstone, 2011)。这也提示我们,对于群际宽恕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群体的心理层面,相关的政治因素也需要考虑在内。例如中国人民对于日本的态度,恐怕不仅仅受到中国人与日本的接触程度、中国人的国家身份认同等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日本政府对于侵略历史的态度的影响。当然,至于这种与政治相关的因素到底如何影响包括群际宽恕在内的群体心理,还需要后续研究进行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