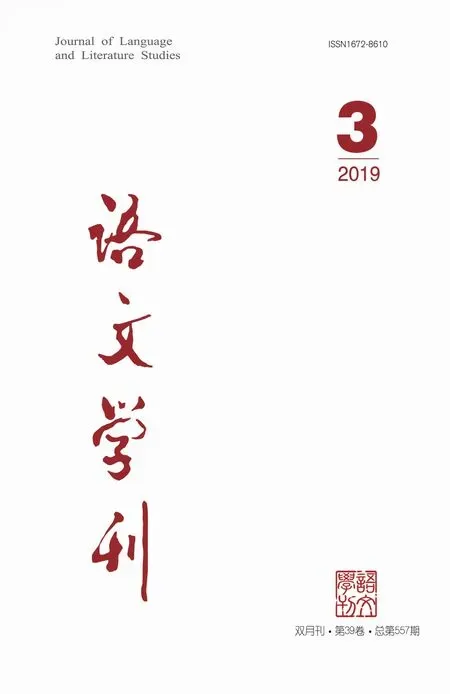詹锳对“意象”和“比兴”的心理学解释略论
2019-03-05胡海王子珺
○胡海 王子珺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詹锳先生在北大和西南联大时,修习的主要是国学与文学课程,毕业后在中文系任教,从讲师做到教授。1948年他辞去教授职务,去美国南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心理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53年归国后,在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前身)教育系任心理学副教授,编写过心理学教材,和同事共同翻译了苏联鲁季克的《心理学》,发表了一些心理学研究论文。1958年,康生将心理学打成“伪科学”,发动批判。詹锳于1961年调中文系任教授,教中国古代文学。“文革”期间,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些英文论文、法语、俄语、英语译作及一部心理学方面的书稿都在抄家中丢失,只留下几篇早期心理学论文。在《文心雕龙义证》中,詹锳从心理学角度,对揭示文学特性的重要范畴之——“意象”,及营造意象的最重要手法之一 ——“比兴”,提出独到的解释。本文就此予以探讨,挖掘这位早期海归心理学博士在龙学领域的独特贡献,并深化对这两个古代文论核心术语的认识。
一、意与象是两种不一定结合的心理现象
“意象”一词,最初见于王充《论衡·乱龙》:“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1]705据《仪礼·乡射记》中记载,射箭时的礼仪制度是,在布靶上画各种兽头,等级不同的人射不同的布靶,其寓意有征服凶猛者,教育巧佞者,远离蛊惑者,或寓意天子与诸侯相支撑而不相犯,如此等等。以诸侯命名画有熊麋的布靶,这种礼仪制度真正注重的是这种具有寓意的形象,是为了彰显某种意义。《汉语大词典》“意象”词条有一释义为“寓意深刻的形象”,引的就是这一例句。
“意象”作为一个文论术语,初见于《文心雕龙·神思》篇:“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汉语大词典》“意象”词条的另一释义“经过运思而形成的形象”,即引“窥意象而运斤”为例句。
陆侃如《文心雕龙译注》中翻译“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为:“正如一个有独到见解的工匠,根据想象中的样子来运用工具一样。”[2]380王元化将“意象”作为一个专门术语予以探讨,认为意象是表象与概念的综合[3]。《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中的解释为:“文学作品中表达作者主观情感和独特意境的典型物象。‘意’指作者的思想情感;‘象’是外在的具体物象,是寄寓了作者思想情感的艺术形象。”[4]111其他还有种种大同小异的解释,或者直接用此概念,不加解释。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解释“意象”为“意想中之形象”“心意中的形象”,引例一是《韩非子·解老》对《老子》中“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的解释:“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二是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对《易·系辞上》中“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解释:“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前者是形象记忆,有此记忆,方可联想、想象,从记忆中唤起形象;后者是表意的象,具有近似语言符号的功能,意义与符号结合成为整体即是意象。
“意象”不一定是意与象的结合。詹锳说:
在西方心理学中,意象指所知觉的事物在脑中所印的影子;例如看见一匹马,脑中就有一个马的形象,这就是马的意象。其所以译为“意象”,是因为和王弼的解释类似。[5]983-984
意与象不一定结合,但毕竟象可以表意,因而仍然可以叫意象。作为心理学术语的意象是一般意义上的,不特指寓理或寄情的形象,它有表意功能但不等于是意和象的结合。它是直觉层面的,是人凭感官对外物的第一反应,未唤起思维器官的进一步反应,是一个表象记忆或直觉形象。从认识发生过程看,它是对事物产生感觉、知觉并形成了表象,没有形成概念、判断、推理。它与思想、概念、情感、意志的结合都有可能,也可以独立存在——相当于艺术直觉。
“象”首先是独立存在的,与意无关。按《韩非子·解老》对“象”的解释,人见过大象,会形成表象记忆,看到象牙,就会联想到象的整体,这是表象记忆的唤起,“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生也”。因此,人们就将唤起联想与想象的形象叫作“象”。《易经》卦象也是如此,简单的图案唤起人们记忆中关于某事物的完整形象即相应感受、认知;卦辞和爻辞,是人们将进一步认知附着于卦象,并非这些卦象本来就包含这些意义。《易传》是在卦爻辞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关于《周易》言、意、象的关系,王弼解释说:象是显示(唤起)意义的,言辞是说明这种意义的,根据言辞可以认识卦象背后的事物与现象,根据卦象可以看到早期思想家对事物与现象的认识。王弼反对汉代有些学者对卦象的任意解释和对卦爻辞的随意发挥。《周易略例·明象》中说:
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6]609
也就是说,将乾卦比附为马,取马矫健之意,寓意人之精神矫健,坤卦则比附为牛,取其柔顺之意,寓意人的柔弱。王弼认为没必要这样任意联想、牵强比附,不能将这种比附固化。
从心理学上讲,意与象是人对事物的两个层面的反应,彼此独立存在,实践活动中难以分割,理论上则要区分。形象唤起思想,不等于形象与思想一体。我们可以在它们之间建立起联系,但不能认为它们有固定的、普遍必然的联系。一般来说,意象是物象或形象,作为意与象的结合体,只在特定范围内成立。比如说,陆游笔下的梅意象,与梅妻鹤子林逋笔下的梅意象是不一样的,和《病梅馆记》中梅的隐喻更不一样。我们不能脱离具体作品而绝对认为梅是一个意象。意与象的结合是可变的,某一意象的意是丰富的而不是唯一的。
当然,意与象的结合也具有约定俗成性。有些形象所附着的意义成为共识乃至共同记忆。这方面论述较多,从略。
比较各家对意象的释义,詹锳将“意象”释为“心意中的形象”,有其心理学依据;将意象理解为意与象的结合,则是社会学、文化学性质的。也就是说,中国文论注重作品的思想性、社会意义、文化蕴含,总是将主观认知、意志、情感诉诸物象,也总是要将物象阐释为某种思想观念或社会性的普遍情志,因而物象就不再是独立存在的了。
二、比兴是文艺心理活动的特定表现手法
意象是文艺心理活动的重要特征。比兴是将情意诉诸物象、形成意象的重要手法。王元化认为比和兴分别主于附理和起情;比兴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则可以解释做一种艺术性的特征,近于今天所说“艺术形象”一语[3]:
“艺术形象”这个概念取得今天的意义是经过了逐渐发展和丰富的过程,我们倘使追源溯流,则可以从早期的文学理论中发现“艺术形象”这个概念的萌芽或胚胎,尽管这些说法只是不完整不明确地蕴含着现有的艺术形象的概念的某些成分。例如Imege一字,在较早的文学理论中就用来表示形象之意。这个字原脱胎于拉丁文Imego。它的本意为“肖象”“影象”“映象”,后来又作为修辞学上“明喻”和“隐喻”的共同称谓。“象”是诉诸感性的具体物象,“明喻”和“隐喻”则为艺术性的表达方法或手段。因而这里也就显示了今天我们所说的艺术形象这个概念的某些意蕴。我国的“比兴”一词,依照刘勰的“比显而兴隐”的说法,(后来孔颖达曾采此说),亦作“明喻”和“隐喻”解释,同样包含了艺术形象的某些方面的内容。《神思篇》:“刻镂声律,萌芽比兴”,就是认为“比兴”里面开始萌生了刻镂声律塑造艺术形象的手法。
《比兴篇》是刘勰探讨艺术形象问题的专论,其中所谓诗人比兴,拟容取心说法,可以说是他对于艺术形象问题所提出的要旨和精髓。
由Image派生的一些词有想象、虚构、幻想、联想等意思,与明喻、隐喻有关,至于说三者是修辞学上的共同称谓,恐怕不能成立。将比和兴分别对应于明喻、暗喻大致成立。比是明喻无争议;兴,若按朱熹解释,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似乎离暗喻比较远,因为一个暗喻本身就够了,并不要引起其他言辞。如果将兴解释为,先言他物而暗示一己情志,那就与暗喻相当了。《诗经》中的兴实际上也是如此。《蒹葭》全篇都是他物,诗人的情志蕴含于整体,不能从文字上分物我,我在物的背后。
黄春贵《文心雕龙之创作论》(1978)专门从手法角度讨论比兴:比是一种类似的联想、类似的譬喻,以丙譬喻甲,甲与丙之间必有乙即某种相似性。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肌如白雪”一句,肌为甲,是本义;雪为丙,是譬喻义,乙是甲与丙的相似性。兴是一种继起的联想,即由甲联想至丙,甲与丙之间不一定具有某种相似性,重在前后衍生关系,一因一果,不求形似,随兴所之。
詹锳从心理学角度对比兴的解释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詹锳是在《文心雕龙义证·神思篇》中解释比兴的。这也表明了《神思》篇与《比兴》篇的内在关联,亦即意象与比兴的关联。他解释该篇赞语说:
刘勰把“物以貌求”和 “心以理应”结合起来,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塑造形象不但不排斥理性,而且需要把写物图貌、喻理抒情紧密结合起来。
运用形象思想,不能不采比、兴等手法。可见“萌芽比兴”实际上已接触到如何运用形象化的艺术手法来表达思想感情的问题。《比兴》篇说:“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文艺创作要通过各种创造性的想象活动,如心理学上讲的类比联想(类比联想,大致相当于“比”)、接近联想(接近联想,大致相当于“兴”)等等,把本来不相关的东西(“物虽胡越”)联系融合一起,创作出优美的艺术形象。[5]1008-1009
物以貌求、心以理应与拟容取心是一个意思。王元化解释“拟容取心”说:
“拟容取心”这句话里面的“容”“心”二字,都属于艺术形象的范畴,它们代表了同一艺术形象的两面:在外者为“容”,在内者为“心”。前者是就艺术形象的形式而言,后者是就艺术形象的内容而言。“容”指的是客体之容,刘勰有时又把它叫作“名”或叫作“象”,实际上,这也就是针对艺术形象所提供的现实的表象这一方面。“心”指的是客体之心,刘勰有时又把它叫作“理”或叫作“类”,实际上,这也就是针对艺术形象所提供的现实意义这一方面。“拟容取心”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塑造艺术形象不仅要模拟现实的表象,而且还要摄取现实的意义,通过现实表象的描绘,以达到现实意义的揭示。现实的表象是个别的、具体的东西,现实的意义是普遍的、概念的东西。而艺术形象的塑造就在于实现个别与普遍的综合,或表象与概念的统一。这种综合或统一的结果,就构成了刘勰所说的艺术形象的“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个别蕴含了普遍或具体显示了概念的特性。
刘勰重视文章的思想性,所以说心以理应,而不说应以情感、意志。不过呢,按《文心雕龙》骈文体的特点,为求工整,刘勰经常用一个词代表相关的一组词。这里说心物关系,在心当然包括思想道理、情绪感觉、意志愿望等三方面。
詹锳说比是类比联想,这个心理学术语比较容易理解,运用比较广泛。所谓类比联想,就是看到一样事物想到另一样与之相似的事物,二者外形相似或某些内在性质相关、相通。前文所说由卦象联想到某种事物与现象,主要是类比联想。如由坤卦联想到女性,联想到生长万物的大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君子比德如玉”,都是用的比法。
詹锳说兴相当于“接近联想”,这个心理学术语难懂一些。其英文词是association by contiguity,又译作“时近联想”或“邻近联想”。指的是当一个人同时或先后经历两件事情、接受某种刺激,这两件事情,或两度刺激产生的反应会在人的脑海里建立起联系,此后,当他想起其中一件事情的时候,另一件事情也会被唤起。比如说,某人吃一个红苹果和一个青苹果,前者产生快感,即愉快的条件反射,后者可能有涩味,效果相反。多次这样的经历,可能使该人在看到一个红苹果,乃至于画上的红苹果时,就会唤起愉快的心理反应。詹锳在其心理学论文《巴甫洛夫心理学观点的历史探讨》中,介绍了心理学家巴甫洛夫做过的这类关于条件反射的实验。条件反射的情绪反应,不是基于理性判断,而是由生理反应积淀为心理反应。这是比较简单的接近联想。复杂的接近联想如,某人行至河边,无路无桥无舟,只见芦苇苍苍,过河不得,上下求索,倍感迷茫失落,这种情绪、感觉,在功名不就或爱情失意时,可能出现,就会唤起蒹葭苍苍的记忆,而作《蒹葭》之诗。这种不易觉察的时近联想即是兴,是暗喻。在后人眼里,蒹葭这一意象,就是迷茫失落情绪的象征。
类比联想与时近联想有时难以区分,需要联系现象、事例具体分析。如某男子喜欢果实,因而喜欢花;他还喜欢果树边的女孩,于是用花比美女,这属于比喻手法。冬天万物萧条,独有寒梅绽放,有人因为怀才不遇而孤独,咏梅而抒怀,全篇无“我”,又到处都是主体的行迹与心迹,这就是暗喻了。
思想学问领域的意象,一般是遵循一定事实与逻辑的由此及彼,不过如果没有联想与想象,就会少很多科技创新。知识和科学程序会阻碍想象力,不过没有知识基础和科学程序,也不会有切实可行的知识、理念与方法创新。在文艺领域,因为联想主要是借助形式,所以更加自由,记忆可以无限组合、变形,因此想象无边无际。文艺领域的意象,就是意与象的自由组合,是非逻辑非事实的类比和接近联想。
心理学是一门应用学科,依托于实验。心理活动千变万化,不同人的心理千差万别,要寻求一些共性与规律很难;较之社会历史分析,又自有另一种深度。这个高难领域,在民国时期引起很多学者的注意。按我国思想学术传统,关注社会、历史、现实生活更多,关注个体心理较少,心理学之所以引起关注,与新民、改造人心和国民性有关。梁启超倡导小说新民、新政治,王国维致力于美学新民,蔡元培实施美育新民,鲁迅在创作中贯彻改造国民性主题,使得心理学一开始就与文艺结合在一起。朱光潜在出版我国第一部《文艺心理学》前,先出版了其普及本《谈美》,强调了改造人心的目的:“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7]5-6
显然,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传承了新民、启蒙主题。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流文艺思想强调社会历史分析而不强调个体心理分析,文学的教育作用取决于作家的思想改造,隐隐贯穿了一条移植正确思想于文学、进而移植给读者的思路,要求以理智支配情感。这大概是心理学被视为伪科学的主因。直到1984、1985年,文艺学界提倡文艺学观念与方法更新,文艺心理学才重新获得重视。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中运用他的心理学专长,启示古代文论研究要自觉运用这一理论方法。
西方美学、艺术理论包含了心理学内容,直觉、移情、想象、联想、灵感等理论术语,是借助古代诗文评中类似词语来翻译的,同时也不无各自语境所带来的先天差异。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中直接运用心理学分析文论问题的材料并不多,不过以上数例表明,切实把握和合乎规范地运用西方文艺学方法,对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是有推助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