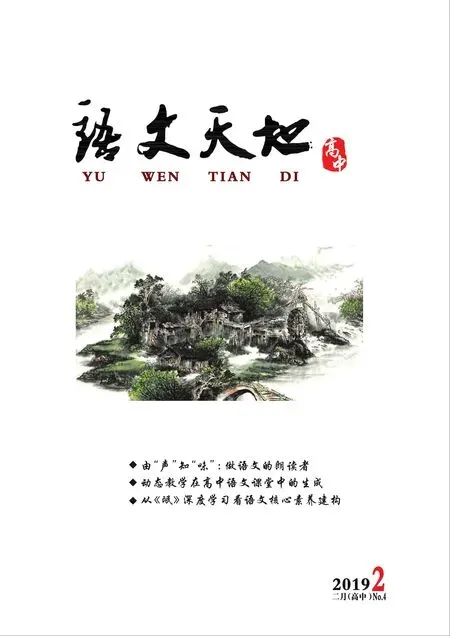艾青的“诗学宇宙”
2019-03-05
艾青是我国现当代著名诗人,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走过了将近60个春秋。他一生创作长诗二十多部,短诗二千多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艺术资源,他的诗歌《我爱这土地》《大堰河——我的保姆》分别被选入初高中教材。他不仅唱出了自己的心声,而且吹响了时代的号角;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抒情风格,同时也开创了一代诗风;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在诗歌理论上也多有建树。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理论文章,并集结成书。他的诗歌理论虽然很多只是只言片语,但却蕴涵着深刻的思想。诗人从诗歌与人民和时代的关系、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建构起一个闪耀着真、善、美光芒的独特的“诗学宇宙”。
一、强烈的生命意识
艾青的“诗学宇宙”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首先表现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童年时的独特经历,使诗人自幼就形成了一种“忧郁”的气质,这种气质让诗人深深体会到了个体生命存在的孤独感和漂泊感。这种孤独感和漂泊感促使诗人对个体生命投入极大的关注,而最先映入诗人眼帘的是衰败的农村和苦难的农民。因而,这种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注便是对农民生存的关注,他心中的那份忧郁也是一种“农民式的忧郁”。随着抗战的爆发,诗人辗转于中国大江南北,亲眼目睹了“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的种族”的苦难,感时忧世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心灵上产生了强烈共鸣,“农民式的忧郁”升华为新的时代精神,个体生命意识也因此转化为民族的忧患意识。
其次,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还表现为对生命力的张扬。艾青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忧患意识的忧郁诗人,但绝不是一个悲观的诗人,个体生命的苦难与民族的忧患并没有把诗人击倒,相反,他的叛逆个性和反抗精神使他发出愤怒的呐喊和猛烈的抗争。他就像一块“礁石”,带着微笑屹立在海水中,风吹不化,浪打不退。他要用生命“拥抱自己的痛苦”,他要“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直到啼血、死亡也要把自己的羽毛腐烂在土地里。这不仅是一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悲壮,更是一种“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崇高。这种生命意识中的悲剧性体悟使诗人的诗歌永远在生命的张力场上飞扬,给人以信心、勇气和力量。这种敢于抗争、勇于牺牲的悲剧品格,既是对我国儒家传统文化“殉道”精神的传承,又是苦难时代赋予诗人的历史责任。唯有如此,才能赢得胜利,才能换来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鲁迅说:“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时,这个民族还没有希望。”而是要有“我以我血荐辕轩”的战斗激情和牺牲精神。这种战斗激情和牺牲精神是生命力的张扬,是在苦难中绽放出的血色花朵。
对生命的独特体悟,使艾青的诗歌充满忧郁感、流浪感、忧患感、悲剧感……这一切构成了他的“生命诗学”,而这一“生命诗学”恰恰来自于时代精神、民族传统与个体生命的高度融合,来自于他那挥之不去的“大堰河”情怀。
二、一首诗必须崇高
在生命诗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诗人关于崇高的美学思考。艾青认为,艺术应该是艺术家思想情感和性格气质的真实再现,艺术家的胸襟气度决定了其作品境界的高下。他说:“一首诗是一个人格,必须使它崇高与完整。”关于这一点,我国古代文论里早就有“文如其人”的说法,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布封也有“风格即人”的观点。诗人之所以在此强调这一点,一是要求艺术必须是作家真实生命体验的情感流露,二是这种情感应该是崇高的。
诗人所理解的崇高首先是真实,也就是要说真话,抒真情。这是就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说的,一方面要忠实于客观现实,一方面要如实表现作者的灵魂与人格。首先要忠实于客观现实,如果不忠实于现实,而是一味追求所谓的技巧,那连艺术也算不上,就更不用说崇高了。艾青认为,忠实于现实,就是要求诗人说真话,并且指出,因为人生有限,“所以,我们必须讲真话。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随时用执拗的语言,提醒着:人类过的是怎样的生活。”虽然诗人认识到说真话有时是很危险的,但他仍然坚持这一点,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诗人必须做到的。其次是如实表现作者的灵魂与人格。诗人明确地告诉我们,诗歌不是空喊口号,不是无病呻吟,更不是矫情和欺骗,而是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艺术个性。说真话、抒真情,才能在诗歌中表现出诗人的人格,同时,这也是一个伟大人格的最基本的前提和保证。
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要想使它崇高还必须要有善。这种善,不仅指个人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更是一种甘于为人民、民族,甚至人类而牺牲自己的大善。朗吉弩斯认为,崇高的对象应该是“不平凡的”、“伟大的”。他说:“崇高的风格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诗人所说的善与此相近,同时又是对这一观点的发展,因为诗人在这里所强调的善,具有很强的社会功利性。虽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是非标准和善恶观念,但诗人的善恶观念始终是以人民利益为标尺,符合人民利益的就是善的,违背人民利益的就是恶的。如果说符合个人或少数人利益的是善的话,那还只是小善,只有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善才是大善,才是真正的善。
艾青能如此深刻而又辨证地看待崇高的艺术个性和社会价值,这在当时是很有创见的,即使在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对崇高的社会价值的强调,既是诗人自觉充当时代歌手的赤子情怀使然,也符合当时革命斗争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对它的过分强调,必然会导致对诗人艺术个性的忽视,使诗歌沦为政治的化身,也就谈不上崇高了。
再次是指一种语体风格。艾青强调诗歌的纯真、朴素、明朗,反对任何艰深、晦涩、难懂的诗。这与西方古典主义艺术理论家温克尔曼在论希腊艺术时所强调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人在与青年谈创作时说:“用正直而天真的眼看着世界,把你所理解的,所感觉的,用朴素的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同时,他还提出了诗歌的散文美这一重要观点。但他所提倡的散文美不是散文化,不是不要韵律和节奏,而是主张通过诗歌情绪的变化所体现出来的内在韵律和节奏,一种单纯的、本色的美。他在谈诗歌的语言时提出,语言应该遵守的最高的规律是:纯朴、自然、和谐、简约和明确。诗人的这一理论主张,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与诗人所推崇的崇高美学思想相一致。
此外,艾青还对意象与意境、联想与想象、构思与灵感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其“生命诗学”的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具有崇高美的独特的“诗学宇宙”,为我国新诗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艾青之所以在诗歌创作和理论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不仅得益于他植根于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得益于西方文学艺术的熏染。深沉博大的大堰河情怀,复杂多维的西方艺术的影响,使艾青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