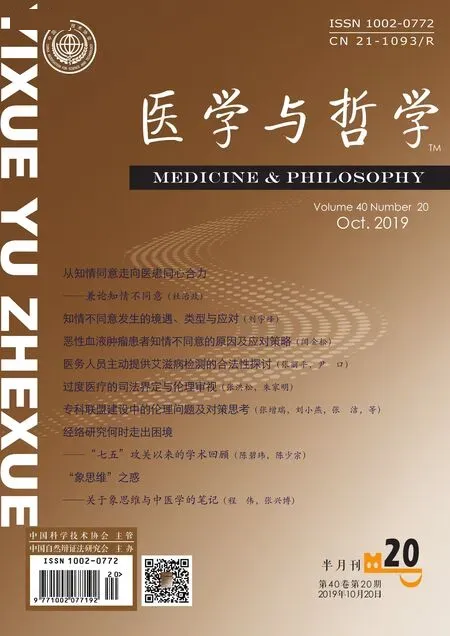医务人员主动提供艾滋病检测的合法性探讨
2019-02-27张丽平
张丽平 尹 口
通过检测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本文中包括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病人),对加强艾滋病的防治具有重大意义。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主题就是“主动检测,知艾防艾,共享健康”。出于保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基本人权,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在1994年起就开始通过一系列文件将自愿咨询检测作为艾滋病预防的重要公共卫生政策,我国在2006年开始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中,也确立了艾滋病自愿咨询和检测制度。
在2014年第二十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了2020年将力争实现“90%的感染者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90%已经诊断的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90%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病毒得到抑制”的防治目标;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中,也把“经诊断发现并知晓自身感染状况的感染者和病人比例达90%以上”作为主要工作目标。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我国艾滋病检测人次数从2012年的1.0亿上升到2017年的2.0亿。但中国疾控中心专家估计,至少还有30%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没有被发现。因此,扩大检测范围势在必行。
其实,早在2006年底,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就发布了在医疗机构由医务人员主动提供的对就诊病人进行的咨询和检测(provider-initiated HIV testing and counseling,PITC)的详细指南,并推荐了基于知情不拒绝原则(opt-out)的进路,强调患者享有拒绝检测的权利。在我国,2012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中,也明确提出扩大艾滋病检测范围、适用知情不拒绝原则的具体措施:高度流行的县级医疗机构将艾滋病检测纳入住院和门诊的常规检查,按照知情不拒绝的原则对高危行为人群提供必要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中度流行的县(市、区)要根据实际扩大艾滋病检测范围,县级医疗机构按照知情不拒绝的原则对重点科室就诊者和住院病人主动提供必要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
然而,也有学者对按照知情不拒绝原则实施PITC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和知情同意权。对此,有学者从伦理学的角度提出了辩护,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从法学角度对此原则进行探讨。笔者不揣冒昧,尝试从行政法视角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1 PITC中的知情不拒绝原则
1.1 知情不拒绝原则的背景
HIV检测之所以从自愿咨询检测原则发展到知情不拒绝原则,除了力求早日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利于艾滋病防治以外,还与人类对HIV的认知密切相关。在医学认识方面,已经发明了有效且可及的药物治疗方式,检测出艾滋病后不至于和以前一样束手无策;在公众态度方面,随着时间的推进和相关宣传的作用,社会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视和污名化明显减少。这使得尽早地检出艾滋病感染者具有现实意义,扩大艾滋病检测范围成为共识。
1.2 知情不拒绝原则的内涵
关于HIV检测中的知情不拒绝原则,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在PITC指南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学者也没有对其内涵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其来源于英文“opt-out”,本意为选择退出,蕴含以明示方式表示拒绝,以默示方式推定同意之内涵。与之相反,英文“opt-in”本意为选择参加,蕴含以明示方式表示同意,以默示方式推定拒绝之内涵。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06年将知情不拒绝原则描述为:要让病人明确地知道HIV测试是常规医疗保健的一部分,但是病人可以拒绝检测。在病人拒绝之前,病人应获得HIV的基本知识及阳性和阴性检测结果的意义,同时有机会提问[1]。原卫生部疾控局组织国内艾滋病防治专家[2]编写的《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手册》中,将其描述为“患者在接受了检测前提供的信息以后,不对检测提出拒绝,即视为同意接受HIV检测”;王陇德院士[3]主编的我国首部艾滋病专著中,将其描述为“在就诊者没有明确拒绝的情况下进行HIV检测,包括简化的检测前信息提供,使HIV检测作为就诊者常规检测的一部分”。也有学者进行了相对详细的定义:知情不拒绝原则是指医疗机构在就诊环境中利用宣传活页、宣传画、多媒体等多种方式醒目地主动向就诊者介绍艾滋病咨询检测知识和本单位提供咨询检测的服务方式,并充分告知拒绝检测的权利,在就诊者没有明确表示拒绝的情况下,向就诊者提供艾滋病咨询检测服务[4]。
但是,从这些定义中,很难看出这一原则的具体内涵,更难以区分“知情不拒绝原则”与“知情同意原则”的区别。对此,有论者认为,将opt-out翻译成“知情不拒绝”原则会引起公众对此种方式存在抵触心理,并建议将opt-out翻译为“选择不参加”,而将opt-in翻译为“选择参加”;在预设前提上,前者是患者默认检测,后者是患者默认不检测[5]。
可见,知情不拒绝原则的基本内涵包括以下方面:一是适用前提是医疗机构把HIV检测作为常规检测手段,适用于普通病人;二是检测前应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但通过何种方式提供,医疗机构具有一定的裁量权;三是医疗机构必须告知患者具有拒绝权,但以何种方式告知其有拒绝权,医疗机构同样具有一定的裁量权。
2 作为行政行为的PITC
对疑似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检测,并非患者和医疗机构之间普通的医疗民事行为,而是医疗机构履行国家防治艾滋病义务所实施的行政行为。从行政行为类型上来看,该行为属于行政指导行为,并具有授益性行政行为的特质。
2.1 艾滋病检测是行政行为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三条的规定,艾滋病是法定的乙类传染病。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对关于传染病的检验和采集样本行为是行政行为。
该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和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从文义来看,该款设定了有关单位和个人接受调查、检验、采集样本等方面的配合义务;从权利义务对应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也授予了疾控机构、医疗机构实施传染病的检验和采集样本的权利。
该条第二款规定: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因违法实施行政管理或者预防、控制措施,侵犯单位和个人合法权益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这里的“行政管理或者预防、控制措施”,就是第一款中所规定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和控制措施”。该款赋予相对人对违法实施检验、采集样本行为的行政救济权,也从另一面表明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实施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是行政行为。
可见,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关于艾滋病的检验和采集样本行为应定性为行政行为。同时,不同形式的检测行为还对应不同的行政行为类型。就医疗机构而言,其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实施的强制检测行为,属行政强制措施;对自愿接受咨询检测者实施的免费检测行为,属行政给付行为;而适用知情不拒绝原则实施的PITC,则属于行政指导行为。
2.2 PITC属行政指导行为
所谓行政指导,指行政机关就其所掌事务,对于特定之个人、公司或团体,以非强制之手段,取得相对人之同意与协力,以达到行政目的之行为。
PITC的实施目的,一是力求早日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二是尽可能广泛发现艾滋病患者,从而能够实现防治艾滋病之行政目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推荐实施PITC,就是因为在原有的自愿检测原则制度下,由于恐惧羞辱和被歧视,很多人不太选择自愿咨询和检测。在PITC指南中,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由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主动发起的检测和咨询可以提高艾滋病病毒被检测出来的机会,改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获得医疗救助的机会,进而促进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长远发展。
从理论上来说, PITC的实施不具有强制性,并不违反自愿检测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医务人员只能主动劝告、建议普通就诊者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无论是采用知情同意原则还是知情不拒绝原则,就诊者都享有不同意或拒绝的权利。
根据行政法理论通说,行政指导之最大效用在于补足法律之未规定或规定不足,使行政机关能够机敏地应对行政需要,以落实行政责任,故行政指导不需要有法律依据。同时,行政指导原则上不采取书面要式主义,但在相对人要求交付书面文书时,行政机关如不回应,可能推定行政指导行为不存在[6]。
2.3 PITC是授益性行政行为
PITC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其授益性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对受检者来说,一旦确诊为艾滋病患者,可以提早得到免费治疗、有效控制病情,并得到行为指导;二是就诊者在受到行为指导后可采取安全措施,其配偶或性伴可免受传染的危险。
对PITC行为是否具有侵益性,可从以下方面来考察:一是是否侵害就诊者人身权。就目前所提供的PITC服务而言,主要通过采集血液或唾液进行快速检测。如根据病情本来就需要进行血常规检查,那么PITC就不会对患者产生额外的疼痛;如病情本身不需要采血,PITC可能需要额外采血,这可能引起患者疼痛,但此种不适应属正常人均可接受范围之内。二是是否侵害就诊者财产权。据了解,目前部分地区需要就诊者额外负担检测费20元~30元。即使考虑到医保报销因素,但毕竟也需要就诊者部分自负或从个人账户中扣除(个人账户实际上相当于个人存款),故PITC可能涉及到侵害就诊者财产权的问题。三是是否会侵害就诊者名誉权和隐私权。在PITC条件下,医务人员对所有就诊人员提供艾滋病咨询检测服务,就诊者均受到同等对待,不存在污名化问题。即使检测出HIV阳性,一般情况下就诊者的隐私能够得到有效保护,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泄露的可能性。四是检测过程是否会导致就诊者时间的浪费。目前的快速检测方法只需要半小时左右,与做血常规检查时间差不多,不会浪费就诊者过多的时间。
可见,PITC行为同时具有侵益性和授益性因素,但考虑增加就诊者个人负担相对较小且基本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泄露隐私的可能性较小且与检测行为本身无关,故整体上可将其界定为授益性行政行为。
3 PITC合法性的展开
医疗机构适用知情不拒绝原则实施PITC,必须满足合法性的基本要求。按照行政法学理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主要包括权限要件、依据要件、事实要件、程序要件四方面[7]。以下分述之。
3.1 权限要件
即使是行政指导行为,也必须在该行政机关所掌管的范围之内[8]。如前所述,医疗机构具有作出检测和采集样本的权限。但根据《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的相关规定,高度流行的县级医疗机构按照“知情不拒绝”的原则将艾滋病检测纳入住院和门诊的常规检查;中度流行的县级医疗机构按照“知情不拒绝”的原则对重点科室就诊者和住院病人实施PITC;而低流行县的县级医疗机构和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则并没有明确授权按照知情不拒绝原则实施PITC。但在具体实施中,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
3.1.1 随意扩大授权范围
如《浙江省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12-2015)》要求“县级以上医疗机构按照‘知情不拒绝’的原则在住院病人和皮肤病科等艾滋病相关科室门诊就诊者中主动开展艾滋病检测咨询”,按此推算,浙江省所有县的艾滋病流行水平至少都是中度流行水平;而《甘肃省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则要求“医疗机构要主动提供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按照‘知情不拒绝’的原则将艾滋病检测纳入住院和部分门诊病人的常规检查,按此推算,甘肃省所有县的艾滋病流行水平都处于高流行水平;在《池州市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中要求“具备检测条件的医疗机构要对有感染艾滋病危险的就诊人员开展知情不拒绝检测,到“十三五”末所有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均应对住院病人开展HIV检测”,该市也是把所有的县作为高流行水平对待。然而,浙江省、甘肃省、池州市所辖的所有县不可能都居于高流行或中度流行水平,而这些地方政府要求所有县级医疗机构按照“知情不拒绝原则”扩大检测范围,明显过度授权。
3.1.2 艾滋病流行水平信息公开不足
尽管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艾滋病流行水平分类标准(试行)》中,设定了县(市、区)的三级分类标准。然而,笔者查阅了数个疾控中心的网站后发现,县级以上疾控部门均没有公开所辖县(市、区)的艾滋病流行水平,县级疾控部门也未公开本县的艾滋病流行水平。也就是说,某县到底是否具备适用“知情不拒绝”原则的前提条件,就诊者无法获悉也必然是不知情,医疗机构完全有可能自我授权。
3.2 依据要件
实施 PITC在整体上作为一种行政指导行为,对相对人没有直接的强制力,依据侵害保留的原则,不需要法律依据。但是,实施 PITC过程中也存在就诊者承担费用、额外抽血、时间耗费等侵益性因素,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行政机关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在“知情不拒绝原则”下实施PITC,其依据是国务院《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从行政法学理论来看,该依据是经国务院同意、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行政规定”。然而,关于行政规定的法律属性,目前还存在一定争议。
一方面,根据《立法法》规定,合法依据的表现形式只有法律、法规和规章三种形式,而《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作为行政规范,显然不属于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范畴。故从实定法意义来看,其只有行政机关内部适用的效力,而不能作为对外适用的合法依据。
另一方面,从法律效力来看,国务院行政规定的效力高于部门规章。根据《宪法》第九十条第二款、《立法法》第八十条规定,部门规章的制定必须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的决定、命令作为上位根据,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但也有论者认为,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决议、决定和它发布的行政命令,亦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具有同等效力;研究也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国务院行政规定(“法规性文件”)的法律地位“相当于行政法规”[9]。
因此,从严格依法行政的角度来看,《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能否作为实施PITC的依据,尚存在一定疑问。当然,其中损益性因素只是具体实施的问题,对就诊者不利影响也有限,这些都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予以改善。
3.3 事实要件
在PITC指南中,只是推荐使用知情不拒绝原则,但并没有否定知情同意原则,各地区应根据本地的艾滋病病毒流行状况和抗病毒治疗可及性来决定。《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采取以下分类指导措施来适用知情不拒绝原则:高流行的县级医疗机构将艾滋病检测纳入住院和门诊的常规检查,按照“知情不拒绝”的原则对高危行为人群提供必要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中度流行的县(市、区)要根据实际扩大艾滋病检测范围,县级医疗机构按照“知情不拒绝”的原则对重点科室就诊者和住院病人实施PITC。根据PITC的具体过程,主要存在以下事实要件。
3.3.1 适用对象
根据要求,适用知情不拒绝原则的对象包括两类:一类是具有与他人发生体液交换的高危行为的住院和门诊病人(艾滋病高流行县);另一类是重点科室(主要包括性病专科、结核病专科、妇产科和其他手术科室)就诊者和住院病人(艾滋病中度流行县)。显然,适用知情不拒绝原则实施PITC的事实要件就是:就诊者是否存在高危行为,就诊科室是否为重点科室。
但现实中,却存在扩大适用范围的情况,甚至部分地方政府明确要求医疗机构扩大检测范围。如《甘肃省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要求“医疗机构要主动提供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按照‘知情不拒绝’的原则将艾滋病检测纳入住院和部分门诊病人的常规检查”。该要求与《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相比,服务方式从“提供必要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扩大到“主动提供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检测对象从“住院和门诊病人中的高危行为人群”扩大到“住院和部分门诊病人”。
3.3.2 告知内容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检测服务综合指南》的要求,向就诊者推荐艾滋病检测时要提供如下清晰简明的信息:艾滋病检测的益处;HIV阳性和阴性诊断的含义;在HIV阳性诊断下可获得的服务,包括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地点;如果受检者正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有可能得到错误的检测结果;简要描述预防手段并鼓励性伴检测;检测结果以及和就诊者分享的任何信息都是保密的;就诊者有权拒绝接受检测,且拒绝不会影响就诊者获得艾滋病相关服务或一般医疗关怀;在涉及法律问题的情况下,检测阳性者和/或那些性行为或其他行为被污名化的就诊者,检测可能有潜在的风险;有向卫生服务人员提问的机会。
据笔者调查了解,目前适用知情不拒绝原则的PITC中,医疗机构主要是利用提示牌向就诊者介绍将进行艾滋病检测和患者有拒绝检测的权利。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由于指示牌较小,能够提供的信息有限,无法达到《艾滋病检测服务综合指南》的要求;二是部分就诊者可能没有留意到提示牌,即使对最基础的信息也不知情,更不知道自己的拒绝权。
3.4 程序要件
在医疗机构适用知情不拒绝原则实施PITC的程序,主要包括告知相关信息、征求就诊者意见等两方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检测服务综合指南》的相关要求,进行快速诊断检测时不强化检测前的咨询,也不再建议在检测前信息交流时进行个人风险评估和个性化咨询;同时,可根据当地条件和资源,项目还可以通过个人或小组信息交流,以及媒体,如海报、宣传册、网站和候诊室视频短片播放等方式来提供检测前的信息。
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实施PITC要受到行政程序法的约束,在法律无明确要求的情况下,至少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作为一种医疗行为,其还要符合知情同意原则的基本要求。
3.4.1 行政程序法的要求
目前,并无关于实施PITC的明确程序要求。同时,PITC作为行政指导行为,原则上并不需要书面形式,故医疗机构以提示牌、宣传活页、宣传画、多媒体等形式向就诊者提供信息具有合法性;同时,根据正当法律程序要求,在做出对他人不利的决定时,必须听取相对人的意见。由于从整体上来说PITC是授益性行政行为,对就诊者实施检测并非对其不利的决定,故实施PITC可不受正当法律程序的约束。但是,考虑到PITC过程中也包含有微小的侵权性因素,如果就诊者要求医务人员作出进一步解释或要求提供书面文件,医务人员必须满足。
3.4.2 医事法的要求
知情同意原则的基本要义是患者在知情前提下拥有自主决定权,但具体实施的方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对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等可能对患者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医疗行为,医务人员需要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性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在临床实践中,对普通门诊患者,医务人员只需要口头告知病情和医疗措施并征得患者口头意见即可。由于PITC并非可能对就诊者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检测行为,故并不要求书面告知。因此,即使采用 “广而告之”的形式,只要告知过就诊者有提问和拒绝的权利,无论是否采用知情不拒绝进路,也不违反知情同意原则。
在实施中,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部分医疗机构提供信息途径有限,并未以提示牌、宣传活页、宣传画、多媒体等形式提供充分必要的信息;二是由于医院信息化的开展,就诊者手上并没有检验申请单,根本不知道是否实施了艾滋病检测,就谈不上要求医生解释、提供关于艾滋病的信息,实际上被剥夺了是否同意检测的决定权。
4 完善合法性的对策和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PITC基于指导性、授益性行政行为的秉性,其合法性并未受到严格的拘束。相应的,依附于PITC的知情不拒绝进路,也得到诸多的豁免。但是,如果从最严格的合法性要求来看,我国目前在知情不拒绝进路下的PITC,还面临着一些挑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其合法性问题,还需要从以下方面完善。
4.1 努力消除损益性因素
一是免费实施知情不拒绝进路下的PITC,减轻就诊者的经济负担。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的规定,国家对艾滋病实行免费自愿检测的制度。知情不拒绝进路下的PITC实际上也属于自愿检测,因此目前的收费措施既不合法,也增加了就诊者负担。同时,免费检测虽然可能增加财政负担,但此种负担也是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因为接受检测的就诊者有限,检测成本大概在10元左右,整体增加的幅度不大。
二是仅对本身就需要进行血常规检查的就诊者实施知情不拒绝进路下的PITC,以减少就诊者的额外疼痛和在等候时间方面的浪费。同时,对不需要进行血常规检查的就诊者,可实行知情同意策略。
4.2 完善告知内容和程序
医疗机构除在候诊大厅采用多媒体、宣传海报等多种形式充分告知相关信息外,还实施以下措施:一是在医务人员接诊桌显著位置处放置提示牌,提示牌只需告知将进行HIV检测和就诊者有拒绝权利即可,但必须在字体大小和颜色方面突出显示;二是对实施检测的就诊者,应提供书面的检测申请单,让就诊者有进一步知情的机会。
4.3 加强信息公开
县级以上疾控中心在网站上公布本辖区内各县(市、区)或本县艾滋病流行水平,实施PITC的医疗机构;县级医疗机构在网站上公布实施知情不拒绝进路下的PITC策略和具体实施办法,既让就诊者有更多知情和决定的机会,也让PITC真正成为常规检测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