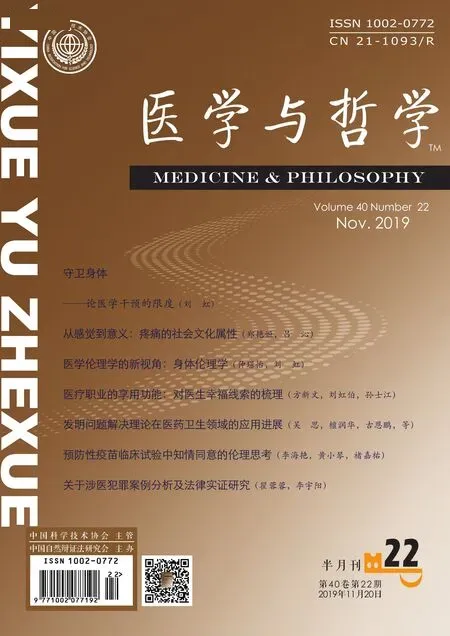医疗职业的享用功能:对医生幸福线索的梳理*
2019-02-25方新文刘虹伯孙士江
方新文 刘虹伯 孙士江
医学何以从古到今聚拢了一只长长的医者队伍乐此不疲地伴随人类前行的脚步?也许我们仅从“救死扶伤”的刚性需求去回答略显简单和草率。医学与其实践者具有深切的同一性,用后现代伦理学的语言来说,“规范性特点和个人的特性共同构成了在世界上的行为基础”[1]137。医者生动、具体的个体人生成就了一个拥有庄严历史和显著道德传统的医学领域,但医者绝非仅作为达到医学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必是在时时依据自己的愿望、目的、意义和价值创造着自己,那医学中恰也蕴含对实践者的精神感召与滋养,具备使他们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得以达成的必要条件。法国思想家涂尔干[2]13专门以《社会分工论》探讨劳动分工问题,他提醒我们:分工产生的道德影响远比它的经济作用更重要,“谁想要了解劳动分工的功能,就必须去考察与其相应的需要”。首先,此“功能”不是事先设定的目标、目的或意图,而是分工本身“这些运动与有机体的某种需要之间相应的关系”所产生的道德影响。其次,“需要”不是增加生产能力和工人技艺,而是指个性中纯粹的需要倾向:情感或价值态度。不言而喻,医者是医学功能的体验者,医学的功能在向外扩散为一种社会现象之前一定在实践者身上最早被感知。所以,去揭示医学与医生幸福人生的相关性线索,有望为问题答案补充更为清晰和贴切的部分。
1 医疗职业的享用功能的缘由
我们处在一个专业化和崇尚专门知识技能的时代,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职业”一词所涵盖的内容极广而且不断有新成员加入。在人类事务日益广阔的领域中,职业归属仅被视作个体的实际自我和社会关系的一个读数[3]217,标识其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履行的职能和所处的位置。在我国历史上,“先生”是尊称,代表一种修为,医生是少有的几个获此称谓的职业群体之一;在西方,传统意义上“职业”的门槛极高,唯致力于实现他人利益和抵制拜金主义者方能登堂入室[4]266。也可以说,职业即志业或事业,在庄重的职业清单里成员了了,仅有神学、法律和医学三者相互顾盼便不足为奇。近代以降,人们把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工商业领域,社会呈现“职业”资格不断放宽的历史节奏,以往的职业轮廓正在消失,各种独立的职业之间的鸿沟正在被填平[2]97,但医学以其稳定的精神气质——利他主义、无私忘我以及自我牺牲等卓尔不群。快乐之道无他,在于献身于一份能够让心灵满足的工作[5]。仅仅从货币的角度来考虑“报酬”、从谋生的角度“靠医学生存”(医学被限定在单纯的物质利用的范围里)去归结医者的工作动机与心理期待,不免有低估和简单化之嫌。
首先,从人性的角度看,个体的需求有物质与精神或曰高低之分,保持持久活动的最可靠的动力无疑是精神需求。按照美国思想家大卫·格里芬[1]223的观点,驱动人类的各种价值分为三个方面:接受性价值、成就价值或自我实现和奉献价值。接受性价值即从他人那里接受创造性奉献,但从根本意义上讲,人是创造性的存在物,需要实现自己的潜能,依靠自己的实践去获得某些东西(成就价值),更进一步说,需要对他人做出贡献,即奉献价值。接受性需要、成就需要和奉献需要共同构成人性,而后两者则为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心理学家的实证研究恰与伦理学的总结相互印证:人有一种“似本能的”的高级本性,包括对工作意义的需要,对于责任的需要,对于创造的需要,以及对于做好工作的渴望等。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6]。
其次,医学之为医学,最重要的不是其实践者的数量,也不是其组织结构和手段,而是“一组独特的精神系统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表现”[3]190,保持着持续的自我认同的存在的性质。名定而实辩,道行而志通。柏拉图曾断言,医学具备让专业工作者从劳动必需性中摆脱出来的技艺[7]。用今天的语言表述,这个特殊的“技艺”无他,即谦逊、诚实、正直、同情和自我牺牲等在世界医学领域内被推崇备至的高贵美德[8]。于是,医生按与职业成员资格相符的“身分”行事,一方面,是接受来自医学精神系统的调节、保持独特的选择性偏向以表达医学整体的性质,况且追根溯源,诸多规章是从人们共同具有的道德情感中产生的;另一方面,区别于顺从或自私的意向,驱使医者表现出持久性与坚定性的是其内在的生动意志。正如鲍桑葵先生[3]226所言,当一个体系在某一点上影响到我们存在的较深刻的可能性时,我们的注意力就变得活跃起来,并积极认真地维护我们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医学本身逻辑具备吸引和鼓励医者“为医学而生存”、与其精神需要相契合的一面,暂且称之为“医疗职业的享用功能”。
2 医疗职业的享用功能的具体细节
2.1 医学:解放心智的力量
首先,选择了医学,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选择了一种自我实现的标准和路径。医学最初是人类的,其后才是专业的,它当属于塑造人类本质、体现人类创造性的“劳作”(work)(卡西尔语)。从人类学角度来说,疾病属于整个生命世界,但病痛仅属于人类。医学是基于病痛发生的领域,它把一个人挣扎在不想要的状态中的无助模样演绎成一个个帮助与受助的暖心故事,知识和道德不分主次地共同在场。无论在哪里发祥,也不论治病救人运用的知识和采取的路径多么异彩纷呈,慰藉和施善与对技艺的热爱都不约而同地共同构成医学的理想,照亮医者形象的既有生命、疾病疑团被澄清和应对的技艺细节,也有标示他们爱人类、爱病人的生活细节,这就是医者与其他职业身份相区别的双重忠诚。且不说在医学的初级阶段的医巫不分,到后来公众和专门的医者群体都笃信不疑“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断不可作医以误世”,即使今天医者有了特殊的装束——白衣来标识他的角色,代表科学引导的智慧在今天的医学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好医生身上的超自然光环仍清晰可见:白衣天使,兼具仁慈的内心与化腐朽为神奇的过人之处。患者对医者的依赖是经常性的,身处疾痛时的自由缺失、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夺路而逃的无奈使他们宁愿相信医生就是天使。如果我们在“权力”即确保获得结果的“能力”[9]这个层面上使用权力这个概念,那么医者的权力无疑是患者的希望,这个权力越充分越好。因而,从医学自身的逻辑看,它能尽人具备之性,将医者的知识理性、实践理性之潜能不偏不倚地充分挖掘出来。清儒戴震在《原善》中提到:“人之不尽其材,患二:曰私,曰蔽。”拜医学逻辑所赐,医者最有可能兼具度德量力之功,生活最有条件稳健而充分。
2.2 从医:人性的自由
与其他领域相比,医者的职业选择体现出更充分的自主性,享有自我发展和自我创造的自由。选择从医的人更有可能受大家公认的职业典范的鼓舞而把他当作自己最想成为的样子。他们刚入行时想的都是如何治愈患者和服务他人,这个目标巨大的吸引力可以让很多经济前途光明的职业黯然失色。对他们来说,当个“好医生”是一件贴近其价值、情感需要的“好事情”,而与借职业获取如发家致富之类的任何工具性“有利”大异其趣,所以他们往往最忌讳被人认为自己从医是为了世俗的目的。据观察,较之其他职业,医学生往往表现出对导师更多的服从[4]268,因为在他们看来,导师真正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最能帮助“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尽早实现。
选择同时就是创造。当一个人断言他喜欢从医而不是其他职业,这是自愿承担某种责任的开端。“人,最重要的,我希望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而积极的人,是一个能够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的人。”[10]自主选择当医生就是在认可、接受、履行一种责任中自主地塑造自己的生活。由于认清了职业的价值,他们的意志和存在围绕着病患的需要积极运行起来,尽力地让自己更接近入职时心中暗自崇敬的职业榜样。杜威[11]将这种职业专注的状态称为“兴趣”:“它所代表的事实是,一个行动过程、一项工作或职业能彻底地吸引一个人的能力,行动着的人发现他自己的福利已经与一个对象发展的结局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这是一个自己构建的生存状态,一个能证实并发展自身的世界,对自己的价值感到自信,对内心深处的自我与存在持肯定态度,倾心履行情愿参与其中的社会行动系统分配的责任,体验精神的自由与充盈:成就感、自豪感、荣誉感、幸福感等,不一而足,这些力量足以消解工作中负面因素的影响。
2.3 为患者服务:幸福的源头
医学是为患者利益采取行动的过程[12]147,“患者至上”即使在医学商业化的氛围中偶尔被疏离但绝不会被吞噬。哪怕再多的行业认定“时间就是金钱”,都不影响医学笃信“时间就是生命”。在“专门利人”的职业生涯中,医者是否在“毫不利己”中一无所获?“人是目的”中的“人”如果仅是患者,那么作为医者的“人”又在何处安放呢?
第一, 医生绝非单方面给予,会从患者一方获益良多。从根本上来说,医患属于关系范畴[12]173,在任何一方身上发生的事情均与对方当事人高度相关,但人们历来比较习惯侧重于医者一方关注、界定医学实践中的授与受:患者是求助者,医生有能力施以援手而不需要获得他的帮助,只要医生在尽心尽力地为患者服务,他就是一个好医生。事实上,道德本身是一种关系,关系各方角色不同因而对关系的贡献也有所不同。力量有单边力量和关系力量之分,单边力量突出控制、居高临下的特点,关系力量则在于通过受影响的方式来影响他人[13]。当医生仅在技术层面上确认和满足患者的需要,没有意识到患者也有做贡献的能力,实际上是自恃专长行使一种单边力量,把患者贬为一个道德人的“客体”,从而痛失进一步从患者一方获得帮助的机会。事实上,单边力量也无法彻底消解关系力量。仅就关于疾病与健康的医学知识技能而言,医患之间体现专家与外行的落差,这是患者信任、托付的重要依据,但并不意味着患者是一个关系层面上绝对的弱者。信任在先,托付在后,郎景和大夫说过,“再年轻的医生,在病人眼里也是长者,他可以向你倾诉一切;再无能的医生,在病人眼里也是圣贤,他认为你可以解决一切”,可堪此番期待的远非确定性的知识与技能所能胜任。医者的价值感、神圣感产生之时,这无疑是在接收来自患者方面的影响。从另一角度讲,医患是共同体,医生的诊断、决策和治疗需要患者的实质性参与。患病的经验、判断最早属于患者,他是医患交往的发起人。医生的专业观察固然为患者所不及,而发生在患者身上的体验又恰恰是医者观察的盲区。确切地说,完整的疾病经验包括“患者正在经历什么”与“医者看到了什么”,没有充分利用患者经验的医者经验是狭隘的、不全面的。当然,患者才是医疗效果的体验者,医生不仅要依靠患者判断出了什么问题,还应依靠患者判断治疗方案是否已经起效[14]。由此看来,患者的需要是医生成长的基石,患者的参与是医者成就的条件,一个好的医生一定是善于在保持对患者的开放、有效接受患者影响中积淀服务患者的能力。
第二,医者在给予患者时必然收获幸福。生活中的确存在着将“成人”与“成己”分割开来的二元论:要么牺牲自己去做有益于别人的事,要么牺牲别人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从伦理学角度讲,这属于人我关系的不对称:当强调道德行为的为他性时,自我必然遭遇被限制乃至被否定的命运[15]。显然,好医生势必会付出更多,远不止“好人”的平均值,但他们的实践确是消解此二元论的最好素材。对医生来说,“修己”与“安人”是其行为的一体两面。在医患交往过程中有所收获的绝非仅患者一方,医生的获得感有其正当性与必然性。“人不仅要求被满足,还要求能够满足别人。不仅需要拥有所需要的东西,而且要求自己成为一种需要。”[16]对患者而言,医生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安慰甚至不失为一种治疗,用郎景和大夫的话来说,给患者的第一味药就是医生自己。做医生绝无可能中立地“做”,时刻感到被患者需要和期待,人性中最细腻、最有温度的部分——爱心、同情心、责任心、耐心、宽容心(因为患者有时是不讲理的)等被触动或曰被激发,伴随着力所能及的技术性帮助提供给患者。主体德性是享用美好世界的器官,医生幸福的敏感性会随着对病患的专注而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和患者一起亲历如抽丝般的康复过程,医生在捕捉一切积极变化的蛛丝马迹中收获自信与欣喜;能够看到一个患者重返社会,成就感、满足感、荣誉感会不请自来。那么如何解释医生群体中幸福感平平或欠缺的现象呢?抛开国家政策、社会风气等对医者幸福感的消解外,仅就医者个人层面寻找原因,杜威先生[17]的话也许帮助我们寻得原委:无论何人,如果不知道他所造成的对别人有价值的东西只是有内在价值的经验过程的副产品,他就没有领会他的职业。平心而论,在体认“给予即收获”的真诚行动方式中定能收获持久的幸福,而“给予然后收获”属于有条件的道德行为方式,医生是“靠医学而生存”,医学是工具或手段,医学逻辑自带的条件将黯然失色,幸福会成为稀缺资源,有的只是暂时的快乐与不断降低的痛苦的阈值。
医生的存在大部分是在工作中实现的,医疗职业的享用功能是医生存在质量的先在条件与保证。虽然医生的生存质量不完全取决于医学本身,但认清医学的逻辑对医生来说确是一种“自知之明”。而对其他人来说,会多一些对医学、医生的理解和敬意,至于在政策制定者身上产生的效应会更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