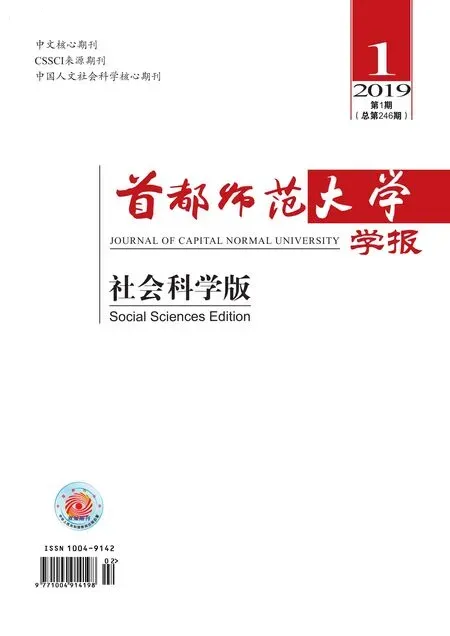中国古代本性美学及其对现代美学的影响
2019-02-22左剑峰
左剑峰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和价值追求,都与儒道释思想相关,尤其深受其中所包含的三种审美方式的影响。本文首先对儒道释三种审美体验进行考察,继而探讨它们对中国古代美学的导向作用,最后分析其基本精神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影响。本性体验是中国古代美学特色的根本体现,本文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以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美学精神及其价值。
一、儒道释中的本性体验
作为人生智慧,儒道释哲学离不开理性的论说和引导,例如孟子对人性善的论证,道家、禅宗对宇宙世界和人生命运的透彻论述,儒道释对体道的意义所进行的说明,等等。但理性说明始终是外在的和辅助性的,熟知非真知,“知”道亦非“体”道。因此,在理性解释和引导之外,人生智慧的最终获得还有赖于个人本性力量的觉醒,即个体的本性体验。
先看儒家的本性体验。性善论是儒家主导的人性理论,由孟子明确提出来。善性“是一趋向,是一等待被实现的潜能”,“此潜能本身充满动力,表现行善之要求”。[注]傅佩荣:《儒家哲学新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1页。因此,它不仅是一般先验形式,还是一种动力趋向和潜能。善性在外境的感发下由一种动力潜能产生出现实的道德情感。《孟子·公孙丑上》举了“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的例子。“恻隐之心”即“不忍人之心”,它不是理性算计和思索的结果,只要人亲临孺子将入于井的情境便会率然自生。孟子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合称为“四心”(或“四端”)。焦循说:“四端一贯,故但举恻隐,而羞恶、辞让、是非即具矣。”[注](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5页。在心理经验中,“四心”常结合在一起,难以明确区分,以恻隐之心为标志。朱熹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注](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39页。由现实情境感生“四心”,就是儒家的本性体验。其实,“四心”(即道德情感)集感知、想象、情感和直觉等感性因素于一身。在“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本性体验中,有对孺子的危险境况的感知,有怵惕恻隐之情,还隐含着对他将承受的痛苦和毁灭的想象,以及产生“应加以救助”的直觉判断。《孟子·梁惠王上》载齐宣王见“有牵牛而过堂下者”一事。牛将以衅钟,王“不忍其觳觫”,“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在齐宣王的悲悯中,有对牛体缩恐惧的敏感,对其无罪就死的想象,以及“以羊易之”的情感决定。站在理性的角度看,以羊替牛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羊也会恐惧畏缩,也是无辜的。然而,“以羊易之”是因为齐宣王“见牛未见羊”。“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审美感受在此成了重要选择依据。
儒家思想中有两种情感感发方式:一是在外在环境的作用下感生自然情感(“七情”),二是在外在境遇作用下感生道德情感。前者在诗学中发展为感物说,后者往往与前者交织在一起,使感物之情更为深厚广博,表现为富有悲悯和同情意味的生命共感。应该说,后者(即儒家的本性体验)更能代表儒家的价值追求,对古代艺术创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再看道家的本性体验。道家自然无为的“道”落实为具体事物的“德”,即具体事物的本性。对于人而言,“德”就是人的本性。《老子》二十八章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希望人回归本性,内心像婴儿般纯真。《庄子·缮性》提出的“反其性情而复其初”,也包含着同样的意思。《庄子·人间世》说:“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庄子告诫世人不要因争名求利而丧失了淳朴的自然本性。道无为,人也应当如此,“为无为,事无事”(《老子》六十三章),“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从根本上讲,“为无为”正是人性(“德”)作用的体现。
以无为之心观照万物,老子称其为“涤除玄鉴”(《老子》十章)。“玄鉴”喻指心灵在涤除贪欲、成见和机心后明澈如镜,可以真切地照见万物。庄子也有类似的说法。“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庄子·天道》)“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庄子·应帝王》)。人内心澄明莹彻仿若镜子,如其本然地映照万物。对这种观照的心灵状态,《庄子》用“心斋”作了具体说明。“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气”是心灵虚静状态的比拟词。[注]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0页。以虚廓的心灵应接万物,既非外在感官感觉(“无听之以耳”)活动,亦非产生与对象相应的情感和知识的心理活动(“无听之以心”),而是一种更为内在的心灵感性活动或审美活动。道家审美心境是虚静的。“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是谓复命。”(《老子》十六章)内心的虚静即复归人的清静本性(“复命”)的过程。可见,涤除玄鉴也是一种发挥人性力量的本性体验。如果从主体内心的自由效应来说,涤除玄鉴就是“乘物以游心”(《庄子·人间世》)。
最后看禅宗的本性体验。禅宗以“人人皆有佛性”为依据,在修行上主张顿悟。佛性也被称为“自性”“本心”和“本性”等。顿悟即向内回到本心,明心见性。“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坛经·般若品》)觉悟的个体体验难以言表,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故禅宗强调“自性自度”“自悟自性”(《坛经·忏悔品》),而无法从他人那里借得现成成果。
在禅宗看来,通过理性思虑、逻辑推理是不可能获得觉悟的。“思量即不中用”(《坛经·行由品》)。与此相关,禅宗主张“不假文字”(《坛经·般若品》)。语言与日常思维都是对象化、主客分立的产物,不能抵达被言说的对象。故抽象的语言与逻辑都不能真正把握作为现实而微妙之体验的禅宗智慧。若止于言语,心意行动跟不上,就仍处于未觉悟状态。但禅宗在传道时还是要使用文字的,只是真正的觉悟在舍筏登岸、超越语言之时。超越语言就是进入现实体验之中。惠能明确反对北宗禅“看心观静,不动不起”(《坛经·定慧品》),认为一味枯坐是将人视同草木瓦石等无情之物。觉悟虽是发明本心,却不离见闻觉知。禅宗不主张牺牲此生以期进入彼岸世界,它认为只要“念念见性”,西方极乐净土便可“目前便见”(《坛经·疑问品》)。而且,禅宗也不要求出离世间,逃向山林。“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坛经·般若品》)。真觉悟必须直面烦恼人生。“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坛经·护法品》)。总之,禅宗没有对彼岸世界的信仰,不主张隐居避世;它又反对执空,落入枯坐冥思中;自性发挥作用不是展开抽象的思索,而是一种随缘化用的感性活动;它要求摆脱各种杂念的困扰,而凝心专注于眼前所现之境。因此,发挥本性的觉悟体验也是一种审美活动。
在儒道释的本性体验中,人回归本性。而本性是先天禀有的,是天道下贯于人的结果。因此,回归本性亦即返归一切价值的最终源头——天道。于是,在本性体验中发生了一种“位移”,由小我、私我进入大我、无我。儒道释均在本性体验中进入“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的天人合一之境。
在本性体验中,物我一体,拆除了“我”与对象的界限、隔阂,生命个体联结为相互感通的整体,保持彼此牵动的敏感。儒家所谓仁体即万物一体。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注](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页。相对而言,人对自己家人牵挂得更多,所以张载又用家庭血缘关系来比喻万物一体。他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注](宋)张载:《正蒙》,《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人或许最容易从自己的身体上产生一体相联的感受,因此程颢用身体来比喻万物一体。他说:“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注](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页。儒家的本性体验实际也是仁体的具体运用,体现出物我一体的特点。 “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时内心产生“怵惕恻隐之心”,说明本性体验是以他人之恐惧为己之恐惧,以他人之痛为己之痛。道家的本性体验消除了人与自然万物间的隔阂、对立,“天与人不相胜”,“与天为徒”(《庄子·大宗师》),“与天为一”(《庄子·达生》)。走出小我,回归本性,心灵变得自然虚空,从而与天地万物相通。在此相通状态中,人与物没有分别,“伦(沦)与物忘”(《庄子·在宥》),即所谓“物化”(《庄子·齐物论》)。入乎斯境,欣赏时的“我”就是一只蹁跹翻飞的蝴蝶,一尾水中游曳的鲦鱼。禅宗认为,“万法从自性生”(《坛经·忏悔品》),“万法在诸人性中”(《坛经·般若品》)。因此,禅宗的本性体验超越了主客分立,我与物、我与人息息相通,“一即一切”(《坛经·般若品》),一切都在“我”的感念中,一体无间。“普愿见性同一体。”(《坛经·忏悔品》)
儒道释三种审美方式都是用本性去体验,但由于对本性内涵的不同理解,在体验的内容上各异其趣。儒家本性体验以人的良知良能去关注生命对象的生命需求、生存遭遇,并感生温厚的道德情感。道家本性体验以自然无为之心去欣赏流布于天地间的“大美”(《庄子·知北游》),即宇宙世界在自然和谐地运行、变化、生灭过程中所绽现的活力生机。禅宗本性体验则以一颗不起生灭之心,去欣赏宇宙世界的清净与寂寥。三种体验都超出了个人利害计较,而道禅不像儒家那样主张感生道德情感,故显得空灵超逸。不过,对古代文人而言,三种体验常相互渗透,结合在一起。特别是纯粹的禅宗本性体验是很少的,往往交织着道家对生命活力的推崇。儒家也极力崇尚宇宙生命力,甚至赋予它以道德色彩。如朱熹的著名诗句“万紫千红总是春”(《春日》)。这里,“春”是宇宙活泼的生命力,也是天地之仁。可见,中国古代审美充满着和谐的生命情趣。这种和谐的生命情趣,若从主体感受上讲,又体现在“乐”的体验中。儒家的“孔颜之乐”,道家的“天乐”“至乐”,以及禅宗的“常乐”“涅槃真乐”,都是指本性力量发起时内心的和谐、平宁、坦荡与充实。
西方传统美学是一种静观美学,它强调心理认识能力在审美中的作用。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意识到,鲍姆嘉通的美学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缺席”,即将“身体”(身体的“所欲、所为和所受”)排斥在外,因而提议发展“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学科,旨在探讨“身体在审美经验中的关键和复杂作用”。[注][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彭锋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8页。而本性美学让我们认识到人内心深处灵性力量在审美中的作用。身体美学和本性美学都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感性”的内涵。如果说,身体美学向外扩充了感性,那么,本性美学则向内深化了感性。由此,不难发现,古代本性美学在今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静观审美中的感性具有中介性,它趋向概念而又尚未达到概念。这决定了西方传统美学在整个哲学体系中处于一个由自然向理性过渡的环节。但在中国哲学看来,理性概念的表述虽然明确,但又只能是对象化的和外在的,而本性体验则超越语言,其所观照的感性世界就是最终目的地。因此,本性美学在中国哲学中具有核心地位。也正因此,我们常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审美型(而非理性或宗教类型)文化。本性美学与西方静观美学都认为审美超出了个人利害计较。不过,西方静观审美只是一种活动方式,它本身固然也有价值,却可以承载各种不同的意义内容。本性体验则不仅是审美方式,而且有明确的价值内容指向,直接指示着现实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是审美方式与人生意义的合一。
二、本性美学的整体性及其人生功能指向
儒道释三种本性体验在古代哲学中具有核心地位,对中国古代美学起着导向作用。儒家的本性体验较为平易,而道禅的本性体验似乎与普通人日常生活距离较远。尽管如此,无论在何种体验中,本性觉醒后还有可能被蒙蔽,再度陷入迷惑之中,正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尚书·大禹谟》)。因此,修身是人终生不能放松的功夫。一切修身之根本在返归本性,发挥本性力量,但本性觉醒后仍需要修身以巩固其成果。对古代文人而言,本性体验及修身功夫均为艺术创作的前提条件。反过来,艺术活动虽有心理愉悦功能,却也常有助于修身。
古代艺术家的人格修养首先表现在洗涤心胸,抛弃种种算计和世俗成见。《庄子·田子方》记载,大画师将画图时“解衣盘礴”。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论屈原作《离骚》时说:“然非其人洁廉高韵,具嘘风漱雪之肠,即按谱为之,凡气终不断。”王原祈《雨窗漫笔》中提到,作画时“须要安闲恬适,扫尽俗肠,默对素幅,凝神静气”。这些都说明,在艺术创作时需洗尽平庸之气(“凡气”),内心不被妄念搅扰,更无世俗攀比之念,精神专一,心灵莹澈如镜。惟其如此,心灵才会活泼,各种意象才纷纭聚集于心。艺术构思和创作时的这种心境,必须以平素的人格修养为基础,是人格修养效应在艺术领域内的延伸。
在中国古代,理想的艺术创作需以本性体验为基础。张璪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璪《文通论画》)画家固然以自然造化为师,但又要用本性去体验眼中所见景象,艺术表现的是一个本性体验出来的世界。符载对此进一步解释说:“观夫张公[即张璪]之艺,非画也,真道也。当其有事,已知夫遗去机巧,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故得于心,应于手;孤姿绝状,触毫而出。气交冲漠,与神为徒。若忖短长于隘度,算妍媸于陋目,凝觚舔墨,依违良久,乃绘物之赘疣也,宁置于齿牙间哉……则知夫道精艺极,当得之于玄悟,不得之于糟粕。”(《观张员外画松石序》)“物在灵府,不在耳目”,说明艺术所要表现的不是耳目所见的外在世界,而是“玄悟”(觉悟)中的世界。觉悟就是“回归悟性,以悟性去体验”[注]朱良志:《大音希声——妙悟的审美考察》(上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悟性”即人的“本性”或“本心”,玄悟其实也就是本性体验。艺术创作所要表现的对象,主要不是通过思虑和计算,而是凭借觉悟来获得的。包恢在《答曾子华论诗》中说:“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鼓以雷霆,豫顺以动,发自中节,声自成文,此诗之至也。”“天机”即人的本性、灵性。诗人应待天机发动、本性觉醒之时进行创作,这样的诗作得之天然,如天籁自鸣,而非穷极心智所能及。石涛把“一画”作为其艺术理论的中心范畴,提出了著名的“一画”说。“一画”即顿悟,作画就是表现自性体验出的万物。
中国古代艺术没有离开人格修养而走向西方式的自律之路,它往往是人格修养所达到的内心境界的真实投放。中国艺术创作特别强调真诚。扬雄说:“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扬子法言·问神》)范梈说:“诗之气象,犹字画然,长短肥瘦,清浊雅俗,皆在人性中流出。”(《木天禁语》)唐顺之说:“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与洪方洲书》)“本色”即“直写胸臆”,将内心真面目不加遮掩地写出来。那么,艺术作品内容能否如实反映作家的人格特征呢?在中国美学史中,人品和艺品的关联理论有两种倾向:道德主义倾向和妙悟的倾向。[注]朱良志:《大音希声——妙悟的审美考察》(上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前者主要讨论艺术家的道德品质与创作的关联,后者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讨论艺术家的人格修养、人生境界与创作的关系。中国古代很多相关论述都是从这种更宽泛的意义上展开的。邓椿说:“其人品既高,虽游戏间,而心画形矣。”(《画继》)王昱说:“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文如其人,画亦有然。”(《东庄论画》)按这些说法,艺术家的人品、人格与创作之间应该具有一致性。
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第六首中说道:“心声心画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元好问在诗中表达了两重意思:前两句承认作品内容与现实人格之间存在的不一致,后两句又对这种不一致表示失望和不满。换言之,他否定了扬雄的“心声心画”说作为事实判断的普遍性,却肯定了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有效性。人格是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特征和倾向,而非一个人的全部内心世界。人总是复杂的,环境对人的影响力也时强时弱,迷惑的人会有偶然的醒悟,醒悟的人又可能重陷迷惑。之所以出现人格卑下者写出高卓格调的作品,是因为艺术家不是凭着那个稳定人格的“我”,而是凭借偶然醒悟的“我”进行创作。这两个“我”虽处于分裂、撕扯的状态中,但不能因为一个人现实品格的低下而粗暴地否认他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我们在事实上必须正视人品与艺品不一致现象的存在,但在价值上却应追求二者的统一。所以元好问又把“诚”作为诗歌创作之“本”,他说:“唐诗所以决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三者相为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皆可以厚人伦,敦教化,无他道也。”(《杨叔能小亨集序》)对于这种言论,我们不能套用西方艺术自律观念来进行解释,而应该发现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理想追求。强调人品与艺品之间的一致性,把它当作一种信念来坚守,实际是通过艺术对创作者提出了人格上的要求,即将一时的甚至佯装的高迈卓拔的内心状态,最终转变成稳定的、真实的人格特征。同时,也只有在欣赏者相信作品是艺术家人格的真诚体现的情形下,才能更好地发挥艺术的感化作用及其对生活风俗的改造功效。
艺术创作固然离不开技巧,但与人格修养和本性觉醒相比,又是次要的。明代洪应明说:“节义傲青云,文章高白雪。若不以德性陶熔之,终为血气之私,技能之末。”(《菜根谭》)说明离开了精神修养,技巧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董其昌说:“多少伶俐汉,只被那卑琐局曲情态担阁一生。若要做个出头人,直须放开此心。令之至虚,若天空,若海阔。又令之极乐,若曾点游春,若茂叔观蓬,洒洒落落。一切过去相、见在相、未来相,绝不罣念。到大有入处,便是担当宇宙的人。何论雕虫末技!”(《画禅室随笔》卷三)说明一味在技巧上苦心经营反而对创作构成束缚,成功的创作是在心灵的虚空和自由下完成的。
艺术家的精神修养可以作为一种突破既有技法的力量。石涛反对泥古,其目的是想由对成法的追随转向对“心”的追求。他说:“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千百年来,遂使今之人不能一出头地也。师古人之迹,而不师古人之心,宜其不能一出头地也,冤哉!”[注]俞剑华:《石涛论画》,《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画家向古人学习的主要不是成法,而是古人立法的根本所在,即“古人之心”。艺术家若能抵达心源,发挥自性,技巧创新自然有之,或者说创新与不创新已不成问题了。石涛提倡的是最根本的法,即“至法”或“无法”之法。“‘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画语录·变法》)所谓“至法”“无法”,其实就是“一画之法”。“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画语录·一画》)对于中国艺术而言,形式创新问题最终归结为人生境界的提升问题,而那种在形式内部自我指涉中或在创新的焦虑中所追求的突破,并不那么重要。
以本性的觉醒为众法之源,为最高法,其实还包含着对使技巧得以充分发挥的理想心境的追求。人格修养、本性觉醒使人抛开各种妄念和顾虑,从而凝神静气,使技艺发挥到艺术家所能达到的最佳水准,同时又可以使内心得到真实吐露,实现技巧操作与情意表达完全合一。在这种艺术最佳物态化过程中,艺术家注意力高度集中,原有本性体验再度出现或者得到加强。恰如石涛所说:“吾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注]俞剑华:《石涛论画》,《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在本性体验中主客合一,时不时地还会出现自我意识的丧失。苏轼描述文同画竹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这种自我的消退,是凝神专注的结果,也是本性体验物我一体的极致状态。
本性体验迹化为作品,作品便具有“真”的特点。一方面,“真”指作品表现了道。如王微《叙画》中说:“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太虚之体”即道。当然,道不是抽象的,它体现在大化流行之中。另一方面,“真”指作品意境纯粹空灵,即恽南田评倪瓒画时所说的“洗尽尘滓,独存孤迥”(《南田画跋》)。本心所观照的世界是一个远离私欲、成见、妄念、计较和尘寰喧嚣的世界。黄庭坚说:“虚心观万物,险易极变态。皮毛剥落尽,惟有真实在。”(《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其八)“变态”指内心虚静时所看到的不同以往的情景,也就是去除表面赘物而留下的一个真纯世界。后来石涛也说过类似的话:“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画语录·絪缊章》)去除表面“毛骨”,画境便显得光明莹洁。道的表现和意境的纯粹空灵两方面的“真”,最终都落在本性体验这一本根上。究其实质,艺术作品之所以具有“真”的品格是因其体现了人的本性。作品境界的“真”是艺术家人格修养的结果。
既然艺术家需要一定的人格修养,艺术作品也表现了本性体验,那么艺术欣赏活动就有助于欣赏者人格修养的提高和本性的觉醒。沈宗骞说:“画直一艺耳,乃同于身心性命之学。”又说:“画虽一艺,古人原借以陶淑心性之具。”(《芥舟学画编》)说明绘画艺术向来被用于涵养性情。况周颐对这种艺术功效的发生做了具体说明。他说:“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吾性灵与相浃而俱化,乃真实为吾有耳外物不能夺。”(《蕙风词话》卷一)在集中心意,反复涵咏、玩味作品的过程中,作品意境便逐渐对欣赏者内心进行渗透,最终变为欣赏者现实的心境。
然而,人格修养又是欣赏活动的前提。辛弃疾说:“青山欲共高人语”(《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鸣的发生,有赖于欣赏者是否具备相应的素养。郭熙《临泉高致·山水训》说:“看山水亦有体,以林泉之心临之则价高,以骄侈之目临之则价低。”“林泉之心”即体现了道家精神的超逸心态,郭熙认为只有它才能真正欣赏到自然山水的美。在人格修养和欣赏活动之间存在着双向影响:一方面欣赏活动有益于人格修养,另一方面人格修养又是展开深入欣赏的前提。正是在这种双向互动中,欣赏活动始终与人格修养密切相关,最终推进欣赏者走向本性的觉醒。欣赏者若能提高人生修养,本性得以觉醒,那么原本的生活便焕发出新的光辉。蔡邕《琴操·水仙操》与《乐府解题·水仙操》提到“移人情”“移我情”,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记有邵茂齐“天上月色能移世界”之论。“移人情”“移我情”即去除尘情,洗涤心胸,若此便能“移世界”,改变原有世界,以故为新,一个新世界立于眼前。诚如王羲之所云“从山阴道上,犹如镜中行也”。[注]陈桥驿、叶光庭、叶扬:《水经注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97页。有了一颗超然玄远之心,眼前一切都变得光明莹洁、清新朗亮。
由人格修养到本性体验,再到艺术审美,最后又返归人格修养、本性体验,从而使整个生活得以改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本性美学的整体性。本性美学的内容,除了儒道释三种本性体验之外,还包括深受其影响的艺术审美、自然审美。通过以上多方面考察,不难发现,本性美学有非常明显的人生修养、人格塑造和生活改造的功能指向。这种功能指向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本性美学对现代美学“生活改造论”的影响
中国现代美学是在改造国民性格同时也改造现实生活的氛围中诞生的,具有明显的“生活改造论取向”。所谓“生活改造论取向”,即通过审美来培养中国人的超越性精神,并以此“来具体引导中国社会、中国人生活现实的改造”。[注]王德胜:《功能论思想模式与生活改造论取向——从“以美育代宗教”理解现代中国美学精神的发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生活改造论取向”最集中地体现在“美育”和“人生艺术化”两大主题中,它显然赓续了本性美学的基本精神。改造国民精神状态和生活现实,必然要向西方学习,激进派甚至主张全盘西化。然而,在大多数美学家那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思想智慧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作为古代哲学之核心的本性美学对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和人生艺术化思想的具体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儒道释的本性体验原本是古代三种理想的审美化生存方式,而受其影响的艺术理论最终也指向生活境界的改变。中国现代美学继承了这一传统诗性文化精神,将“超脱”“无所为”“情感”“趣味”等审美因素融入生活活动之中,致力于将现实生活从机械、枯燥、麻木、虚伪和狭隘中救赎出来。
蔡元培以审美的“超脱”(无个人利害计较)与“普遍”两种特性为根据,拟通过美育陶养出作为高尚行为推动力的情感。[注]蔡元培:《美育与人生》,《蔡元培全集》(第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如此一来,道德活动便审美化了,不再仅仅是遵守外在规范的强制性行为,而有内在情感的支撑。梁启超说:“人若活得无趣,恐怕不活着还好些。”[注]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7页。他也特别注重情感在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注]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1页。“趣味”和“情感”在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正是梁启超对生活艺术化的追求。朱光潜主张“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注]朱光潜:《悼夏孟刚》,《朱光潜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页。。他还说:“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注]朱光潜:《谈美》,《朱光潜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6页。朱光潜以“出世的精神”和“情趣化”来实现入世生活的审美化。宗白华认为,人生不能殉于追求种种目的的劳作,而要将外在目的收归于自己内心的兴趣,这样就以“游戏”的方式举重若轻,行所无事。“‘美的教育’就是教人‘将生活变为艺术’。”[注]宗白华:《席勒的人文思想》,《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丰子恺说:“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把创作艺术、鉴赏艺术的态度来应用在人生中。”[注]丰子恺:《关于学校中的艺术科》,《丰子恺文集》(2),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26页。他还认为,艺术教育“就是教人学做小孩子”,“培养小孩子的这点‘童心’,使长大以后永不泯灭”。[注]丰子恺:《关于儿童教育》,《丰子恺文集》(2),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页。“童心”不灭也就是使内心保持趣味、真诚和同情。丰子恺的“艺术的生活”和“艺术教育”思想都显露出谋求生活的审美化的努力。
中国现代美学家大多坚持审美无利害性这一信条,但不同于西方传统美学对审美自律的追求,将审美置于生活之外,而注重审美对于狭隘的个人利害的超越,将审美与生活联结起来。换言之,西方传统美学谋求审美与生活的区别、分离,而中国现代“生活改造论取向”则赓续了古代审美化生存传统,追求审美与人生、生活的融合。本性美学对20世纪中国美学的影响,使其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中:一方面,它借鉴西方美学及其科学理性以完成学术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不愿将审美与生活区分开,而持守中国传统美学的实用理性精神。
第二,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人生境界之学,作为其核心的本性美学致力于去除迷惑的私心和机心,从而发挥本性的价值源头作用。中国现代美学延续了这一传统,将人格修养和心灵态度的转变视为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的根本。正因如此,美育和“人生艺术化”问题才引起美学家强烈的关注热情。
蔡元培意识到,科学越来越昌明而宗教衰落了,物质越来越发达而情感衰颓了,因此“人类与人类便一天天隔膜起来,而且互相残杀”[注]蔡元培:《与〈时代画报〉记者谈话》,《蔡元培全集》(第六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14页。。如何才能走出这一困境?他主张通过美育,让人们在审美中重拾那美好的温情。“我以吾国之患,固在政治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而其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以提倡美育足以药之。”[注]蔡元培:《在天津车站的谈话》,《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30页。很显然,蔡元培是把人心陶养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所在。梁启超说:“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没趣的民族。美术的功用在把这麻木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为有趣。”[注]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8页。因此,梁启超希望通过趣味教育和情感教育来塑造“新民”,进而改变中国社会现状。王国维把宗教和美术(艺术)作为禁烟的根本,如果不从根本处下手,就如庸医治病治标不治本。他甚至还认为:“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注]王国维:《教育偶感四则》,《王国维文集》(下部),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这就把艺术和审美的意义看得相当高了。宗白华曾提出一种“唯美主义”的生活态度:“我们把世界上社会上各种现象,无论美的,丑的,可恶的,龌龊的,伟丽的自然生活,以及俗的社会生活,都把他当作一种艺术品来看待。”[注]宗白华:《青年烦闷的解救法》,《宗白华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这样便超越小己,打消现实所引发的烦闷了。朱光潜在《谈美》中写道:“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注]朱光潜:《谈美》,《朱光潜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他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完全在制度上,更在人心上,因而企图以审美精神来净化人心,改造社会。受佛教等传统思想影响,丰子恺特别注重心性修养对于现实人生的意义。他在桂林师范任教其间,十分赞同校方“以艺术兴学,以礼乐治校”的宗旨,甚至认为这些“实比抗战建国更为高远”。[注]丰子恺:《教师日记》,《丰子恺文集》(7),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在他看来,抗战建国只是一时的历史任务,而艺术教育是洒扫心田的恒常事业。
就古代本性美学而言,本性觉醒只有在摆脱情欲的束缚后才有可能。这一点恰与西方美学的无利害性、审美态度等理论有相契合处。因此,中国现代美学往往将去除私欲妄念的传统思想与西方审美态度混在一起,致使无利害性、审美态度等美学学科概念染上了浓厚的人生哲学意味,也致使这些本来对审美有着多重限定的概念,偏指对个人利害的超越。
第三,在本性体验中,宇宙世界具有了一体关联性。本性美学的物我一体思想影响了现代美学。
蔡元培认为,在现象世界中有人我之差别,遂有种种区分,于是,需要弥合现象世界的差异而入于实体世界的浑同之中。美育正有益于此,因为它能“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逐渐消除。[注]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蔡元培把实体世界解释为无人我差异的混同世界,显然受中国哲学万物一体观念的影响;而作为由现象世界到实体世界之津梁的审美,也就具有了物我一体(破除人我之见)的特点。梁启超认为,情感“把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迸合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众生迸合为一”。[注]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全集》(第七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1页。情感教育“使人成为不忧的仁者”,而仁者则在于体认“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注]梁启超:《为学与做人》,《梁启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5页。可见,实现物我一体的境界是梁启超所谓情感教育和生活艺术化的重要目的。宗白华认为,同情是社会结合的原因,也是艺术的起源,艺术就是将人的同情心向外扩张到宇宙自然里去。在同情中,“人我之界不严,有时以他人之喜为喜,以他人之悲为悲。看见他人的痛苦,如同身受。这时候,小我的范围解放,入于社会大我之圈,和全人类的情况感觉一致颤动”[注]宗白华:《艺术生活——艺术生活与同情》,《宗白华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17-318页。。丰子恺也认为,在“艺术生活中,视外物与我是一体的”。[注]丰子恺:《艺术修养基础》,《丰子恺文集》(4),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125页。
可以说,同情是物我一体产生的心理原因。我们这里所说的同情、物我一体与西方美学中的“移情”有一定的联系,但文化色彩极不相同。移情的世界观背景是物我对峙,而同情的世界观基础是物我皆同类(庄子说“与天为徒”,禅宗说“一切色是佛色,一切声是佛声”,张载说“民胞物与”)。因此,移情是异类间的想象性赋予,而同情是同类间的相互感应。移情必须超越它的世界观背景,具有不同于现实生活的虚幻性;而同情由于已有世界观作为基础,因而具有现实感受的真实性。较之移情,同情更契合生活艺术化的需要。当然,移情与同情在心理上毕竟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中国现代美学又往往不太注重二者的区别。
第四,中国现代美学继承了本性美学中的和谐生命情趣。如前所述,本性美学中的和谐生命情趣包括两方面:一是人内在的和谐生命体验,二是对遍布于宇宙世界中的和谐生命力的欣赏与秉承。
梁启超自称信仰趣味主义,而且认为孔子也追求趣味生活。他说:“孔子因为认趣味为人生要件,所以说:‘不亦说乎?不亦乐乎?’说:‘乐以忘忧’,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注]梁启超:《孔子》,《梁启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3页。到了“乐”的阶段,人与道一体,内心安宁和谐。林语堂把“幽默”作为“生活的艺术”的一方面。在他看来,中国人的幽默与道家超脱精神有关。他说:“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注]林语堂:《论幽默》,《林语堂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也就是说,幽默可以摆脱生活的苦闷,有助于保持人的生命活力,使心灵和谐发展。朱光潜受儒家礼乐精神的影响,认为一个理想的人或理想的社会必须具备乐和礼的精神。“乐的精神是和,静,乐,仁,爱,道志,情之不可变;礼的精神是序,节,中,文,理,义,敬,节事,理之不可易。”[注]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宗白华力倡“艺术的人生观”,希望人们像艺术创作那样来创造自己的生活。这种思想可以为现实人生注入活力。其实,宗白华的意境理论也没有离开对人生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合理人生观的探索。艺术意境所要表现的不是盲目冲撞的生命力,而是通过文理节敛了的、有节奏的和谐生命力。宗白华认为中国画 “所描写的对象,山川、人物、花鸟、虫鱼,都充满着生命的动——气韵生动。但因为自然是顺法则的(老庄所谓道),画家是默契自然的,所以画幅中潜存着一层深深的寂静”。这种“寂静”是中国绘画所表现的“最深心灵”,它没有“烦闷苦恼,彷徨不安”。[注]宗白华:《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气韵生动是宇宙世界的和谐生命力,没有“烦闷苦恼,彷徨不安”是心灵上的安宁。
中国现代美学,甚至在同一美学家那里,既有对古代生命和谐精神的强烈批判,也有对它的高度肯定。中国古代的“中和”思想,“不免有保守一面,但作为士人精神修养有其重要意义。然而在其流转、普泛化过程中,中和的内在精神完全被掏空,成了保守、懦弱、苟且的托词”。[注]左剑峰:《蔡元培美育思想与孔门仁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中国现代美学对中和的批判是在反省国民性格上展开的,而在精神文化的建设上又对它极力推崇;批判是从一时的需要出发,而推崇是着眼于长远的精神需求;批判的是表层的和谐,而推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和谐精神。但无论是批判还是肯定,均非出于审美本身的原因,而是出于人格修养和生活改造的需要。
整体看来,现代美学对本性体验的直接讨论已不多见,但接续了其中人格修养、人格塑造及生活改造等精神。不抓住中国现代美学与古代美学的内在关联,就很难理解这些美学家何以如此重视美育,又何以力倡“人生艺术化”。当然,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和人生艺术化思想不是对古代美学传统的简单重复,除做出了一些具体探索外,还引入了不少西方美学思想,特别是这些研究“被置于对国人进行现代性背景下的感性启蒙和反思现代化及其理智主义弊端的复杂语境之中”[注]杜卫:《简论中国现代美学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