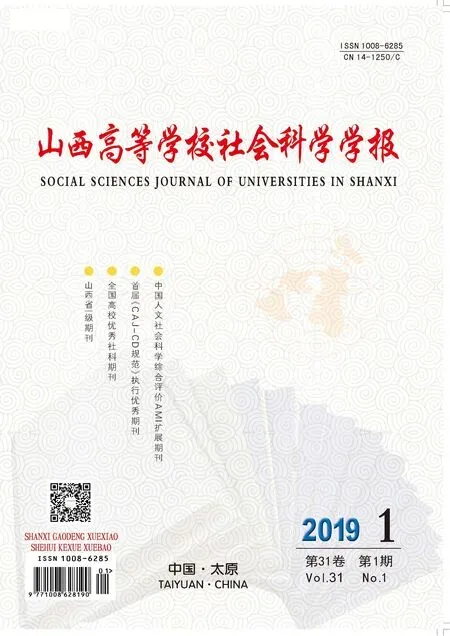论儒家对《抱朴子内篇》伦理思想的影响
2019-02-22宁俊伟
宁俊伟,赵 懿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晋朝丹阳句容人,生活在东西晋相交之际。葛洪是著名的道教学家、炼丹家、道教思想家;同时也是丹鼎道派创始人,神仙道教奠基人。葛洪著有《抱朴子内篇》,形成了其神仙道教理论体系,素有“小《道藏》”之称,对哲学、宗教学、化学、医药学、民俗学等都有较深远影响,是道教的重要典籍。
《抱朴子内篇》不仅把神仙道教理论化、系统化,同时在修仙伦理思想方面与儒家纲常相结合。葛洪生活时代的统治集团为了巩固既定的伦常秩序一以贯之地用儒治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伦理仍占主导地位,期间亦有争论,但只不过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小修小补,实质并未改变。
一、引儒入道的伦理依据
(一)家庭出身
葛洪出身于魏晋江南地区的士族名门,所谓士族是由东汉时期的儒生演变而来,他们以儒家仁义礼智为道德信条,因而葛洪的家世背景决定他骨子里印有深刻的儒家纲常礼教。葛洪在其《抱朴子外篇·自叙》中介绍了自己的家世背景,他称赞其父“以孝友闻,行为士表”[1]649。可以看出,葛洪之所以这样称颂父亲,极力地标榜前人的功绩、传颂祖辈的德行,是由于当时社会仍旧以出身于奉行儒家纲常的名门士族为荣耀。虽然儒学在当时社会思潮之中处于微弱发展的态势,但儒家文化的纲常礼教对于维护统治阶层的地位仍具有不可动摇的作用。因而,从葛洪自身家世背景出发,或者从当时社会世俗约定出发,标榜儒家仍旧势在必行。
从葛洪个人受教育情况来看,他在《抱朴子外篇·自叙》中称:“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1]655《晋书·葛洪传》说葛洪以精通儒学而闻名于世。通过葛洪的《自序》及《晋书》的记载,便可明确得知葛洪深受儒家文化熏习,并且精通儒家名教,这就是葛洪在著述中不断引用、融合儒家文化的原因。由此才产生魏晋神仙道教修仙的伦理思想,为道本儒末思想的提出打下坚实的内在基础。
(二)政治坏境
魏晋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朝代,由于战乱不断、朝代更迭频仍,上层统治者渴望能有一套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思想工具。虽然儒学在当时学术中虽处于弱势,但儒家礼教却一直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所沿用。魏晋是玄学盛行的时代,亦是道教在上层同民间繁衍滋长的时代,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同时能够给道教合理合法的成长空间,因此儒道结合绝非偶然,而是势在必行。
从魏晋门阀本身来讲,门阀士族源于东汉儒生,他们深受儒家纲常的教化,“天地君亲师”是封建礼教的核心根源,四书五经则是教化的典籍,而“君亲”是宗法制度的核心。这一套理论体系是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建立,因此也一直被封建帝王所延续。而葛洪所处的时代,恰好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上层士族为了可以继续享有既得的国家权力,必然要自上而下遵循固有的儒家宗法纲常。这是从魏晋门阀官僚阶层的出身本质而言的,即使朝代更迭不断、社会思潮层出不穷,儒家名教不仅是门阀集团世代出身所沿袭的教化,更是维护国家政权的需要。
“宗教神学都要曲折地反映国家的社会政治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关系,以天国的幻想给处在苦难世界的人们以‘安慰’和麻醉,并把一朵朵假花装饰在统治者的锁链上来束缚被压迫的人们。”[2]157正如胡孚琛先生所言,道教向来都是依附于皇权,在皇权的庇佑下才得以成长,带有深刻的封建宗法性 ,道教徒同教规礼仪一样必须服务于君王才能够正常进行宗教活动。而道教只是在统治者的控制下用来麻痹民众的思想工具而已。生活在东西晋相交之际的葛洪,出身于士族门阀,他站在上层统治者的立场,对道教进行审视和改革,把儒家教化与道教理论相结合,建立起符合政治统治、社会伦理的一套道德说教,不仅利于壮大道教的发展规模,更有利于维护魏晋国家的政权稳定与统一。
(三)社会背景
从葛洪个人种种遭遇与当时社会背景来看,有以下五个社会原因促使引儒入道成为可能。第一,魏晋正是玄学鼎盛时期,出现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他们崇尚自然、排斥名教,到了后期甚至贪图感官享乐、虚无放诞,社会风气、朝纲秩序受到极大损害,统治集团的利益日益遭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形之下,就需要一个代表门阀集团利益的人物出现,这个人就是葛洪。他竭力在神仙道教的伦理世俗方面将儒道融合,用儒家礼教劝世警世醒世,以使国家社稷复归正统纲常。第二,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开始,魏晋时期不断出现民间道扰乱社会秩序的现象,因而有必要对道教进行整体改革,规范道教。第三,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为后世思想的发展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即便学术思想再活跃,仍旧无法走出儒家旧礼教的束缚。后世的读书人深受汉代独尊儒术的影响,社会主流思想意识已被限定在儒家思想的条条框框之内。第四,魏晋战乱频仍、政权不断更迭,儒家士族的社会地位已大不如前,他们对社会现实绝望,出现儒生转向道教来适应时代的发展。在两晋期间,江南士族并不受重视,统治者多年把江南学子排除在经试之外,再加上学风糜乱,很自然地,士族儒生基于现实的种种不堪,多数出儒入道,期望过闲云野鹤逍遥清逸的恬淡生活。不难看出,饱读四书五经的儒生便是构成魏晋道教的主流人士。第五,儒家礼教是古代封建帝王的思想统治工具,儒家名教亦是整个人伦社会的秩序,名教实质是统治集团为了加强统治对社会设置的一种思想规范。这是引儒入道的历史原因。只要封建统治继续存在,儒家礼教就在封建宗法里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回顾历史进程,不论世事如何变迁,古代中国思想脉络如何演变,一种思想若想在中国占一席之地,就必须与儒家思想相融合,道教是如此,佛教亦是如此。正是上述原因,促成葛洪《抱朴子内篇》中的伦理思想体系更贴近于现实生活与统治阶层的利益,儒道融合,为后世道教自身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二、儒道并重的伦理本源
(一)葛洪之“道”
葛洪的哲学是以道为本的哲学体系,他在《抱朴子内篇》中对道的本源做了具体阐述:“道者,万殊之源也”[3]138。“凡言道者,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3]185道是天地之间形质各异的万物之开端和本源,包罗万象,生生不息的。凡天地万物都与道有关,广博到天地两仪,渺小至沙粒尘埃,皆由道而来,也囊括在道中。葛洪将“道”作为《抱朴子内篇》哲学体系的核心,他所言明的“道”更像是道教文化。其实魏晋时期,玄学与道教在社会思潮中最为盛行,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道家的含义已和神仙家混为一谈。《抱朴子内篇》记载了神仙经符二百八十多种,神仙鬼怪之事百余桩,但很少提及老子、庄子等道家文化,反而对黄帝之事列举颇多。因而,葛洪之“道”实属道教之“道”。胡孚琛先生说:“葛洪所说的‘道’,也不同于先秦和汉初的道家学派,而是汉末神仙方士的黄老道。”[2]98
(二)道本儒末
正是基于对“道”的理解,葛洪提出道本儒末的伦理本源。这一立论通过倡行儒道融合,使出世的神仙道教能够顺利地进入世俗社会,用形而上的道体去指导儒家形而下的世俗社会,以便将虚幻的神仙理论纳入社会实践的领域。葛洪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3]184《抱朴子内篇·明本》主要对儒道进行比对,在本篇第一段便开门见山地提出道本儒末的立论基础,之后的种种论述都是在论证二者之轻重与优劣。葛洪道本儒末的提出,把道教的宗教信仰与儒家的伦理纲常相结合,这种性质既是宗教的也是世俗的。从伦理角度来看,葛洪无疑是在推行儒家思想,无论外在形式如何变化,仍旧脱离不开儒家名教作指导。为了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因而在伦常关系上,封建统治者仍是将儒家礼教奉为巩固王权的第一准则。此外,葛洪创建了魏晋神仙道教体系,是为君王服食仙药求得长生不死而服务的。葛洪本人是一个道教徒,求长生不死、飞天成仙为其毕生之愿,因而他极力地站在道教立场上制定理论与规则,在这里他很有必要给“道”留一席之地,因而他将儒道关系称之为道本儒末。但究其根本,与其说道本儒末,不如讲是儒道并重。
(三)儒道并重
“儒道并重”才是《抱朴子内篇》伦理思想的本源。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塞难》中明确指出:“且夫养性者,道之余也;礼乐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后,则仲尼未可专信,而老氏未可孤用。”[3]138儒家与道家在伦理修道方面地位同等重要,二者相互补充,尊道且贵儒。此外,葛洪在儒道兼修方面指出实践之途径。“长才者兼而修之,何难之有?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者,上士也。”[3]148
从葛洪对孔子的评价,也能看出他对儒家的重视。“仲尼,儒者之圣也;老子,得道之圣也。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3]138葛洪视孔子与老子皆为“圣人”,“圣人”一词惯用作对圣贤哲人的至高评价,在思想文化领域拥有最高殊荣之人才能够获得此种称号,它是最高完美境界人格的特指。在《抱朴子外篇》中,葛洪还称:“纣为无道,见称独夫;仲尼陪臣,谓之‘素王’。”[1]34葛洪不仅将孔子称为“圣人”,还敬封为“素王”。不需要臣民、土地与权力,但凭德高望重的名声早已成为永远存在着的王,他留下的制度与文化足以世代沿用,虽无王者之位,但有王者之道。可以看出,葛洪对孔子有极高评价,将仲尼与老氏放在等同的位置上。
不难看出,儒家文化对《抱朴子内篇》伦理思想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即使道教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完善,但是在世俗纲常伦理这一块,任何思潮都无法撼动儒家宗法思想的正统地位。而后期道教的发展,也包括葛洪的改革在内,都只是对儒家礼教的小修小补,他们只是为了儒道融合,为了道教能够更好地为上层贵族与普通大众服务,将道教发展壮大。儒道结合这一理论构架从葛洪这里初现端倪,而后儒道融合的格局不断扩大,例如后世的寇谦之、陆修静等人对道教的改革,不仅引儒入道,甚至援引更多更具体的儒家礼教细则。
三、积善修德的伦理归宿
除了儒道融合产生的缘由同儒家息息相关,葛洪儒道并重的伦理本源理论的建立以外,儒家文化对《抱朴子内篇》伦理思想的影响还体现在积善修德的实践范畴之上。葛洪创建的魏晋神仙道教最终的教旨是服食仙丹、飞天成仙,那么怎样成仙呢?《抱朴子内篇》给出了明确答案,必须通过积善修德来实现。由此,德行便成为通往神仙世界的必然条件。一方面葛洪是为了向统治集团靠拢,对修道之人进行规范和约束;另一方面,也是对自东汉末年开始的民间动乱的警示、打压和规正。
(一)忠孝大德
葛洪称:“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3]53“然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3]125-126“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3]53-54可以看出,葛洪把忠孝仁信作为求仙的道德品质,将做善事积功德看作是具体的道德行为。只有通过积善修德才可以通达仙道,若单单依靠服食仙丹大药而未做善事,求仙亦是徒劳无门的。积善修德的理论不仅是葛洪伦理思想的实践归宿,更是《抱朴子内篇》修仙伦理的基础。具体来讲,葛洪把忠孝这一道德品质排在众品质之首位,并要求落实到行善的实践上。早在《太平经》中就提到:“天下之事,孝为上第一。”[4]593“夫天地至慈,唯不孝大逆,天地不赦。”[4]116天地间诸多善事,行孝乃是第一位的。葛洪生活的魏晋时期延续了历朝历代以孝德感导天下的礼教制度,忠孝是魏晋朝代评价时人的伦理道德标准。
葛洪对修仙德行之中的孝道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抱朴子内篇》中的孝主要是从成仙前与成仙后对家庭与社会的影响两个方面来说明的。在道教徒修仙过程中,一方面,葛洪提倡在家修道,这样不仅不会耽误宗法祭祀和后代的延续,也可娶妻生子、照顾父母。不过,葛洪也指出,如若想远离尘嚣,去深山修行,亦能积累功德,福泽亲人。总之,修仙对家庭的益处颇丰。另一方面,忠孝的践行对修仙也是大有裨益的。奉行孝道对修道者自身心性的养成有很大的帮助,可让人远离烦扰、忘却世人之忧思,安心修炼。这亦是修仙之法门。同时,履行孝道,容易得到神灵的庇佑。总的来说,修道与践行忠孝之礼互为增益,相得益彰。至于飞天成仙以后对家庭与社会的益处葛洪列举出以下三点:一是修仙成功便可长生不死,身体发肤可永葆不损,这是中国古代孝道之始;二是若一人得道便会光耀门楣,实属光宗耀祖之事,这是大孝之终也;三是成为神仙便可以神仙之名教化世人、传授方术、救民间之疾苦,更可辅佐君王、治国平天下,这是孝之大者。葛洪更是构架出“地仙”的生长模式,长生不死、逍遥快活,且不必生活在天上,可在人间逍遥遨游,为士族成仙后在人间社会建功立业指明了道路。葛洪始终代表着魏晋官方神仙道教,“地仙”的提出更是为君王士大夫修仙提供了现世的可能。
葛洪继承了儒家忠孝伦理,缩短了凡人与仙家之间的距离,使成仙之路更为通达。对于儒家忠孝伦理来讲,与道教结合,使得儒学转入神秘的宗教范畴。魏晋时期引入的忠孝伦常,是为了服务于封建宗法制度、维护社会既定的封建伦常秩序而设立的,让君臣父子之序有条不紊,上敬下孝。葛洪忠孝的引入实质是借助道教神人的力量来维护封建秩序。
(二)道教诫律
对积善修德、忠孝仁信之事如何去约束规范呢?葛洪建立起一套适用于神仙道教赏善罚恶的道规道诫监督体系。葛洪的道诫涉及群体甚广,上至君王臣子下到市井小民,对他们日常所做之事一一做了规定。可见葛洪创立的道诫不仅对道教徒适用,也对社会各阶层适用,具有普适价值。葛洪将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与魏晋神仙道教相结合,许多儒家道德细则被改造成为道教戒律,以至诸多道诫与儒家道德规范趋同,根本上是将儒家伦理道德善恶准则作为神仙道教赏善罚恶的标准。并且葛洪还将儒家道德伦理进行了改造,涂上了神秘的宗教色彩,儒家历来倡导的善恶之报,在葛洪这里交由神仙去考量,从而有效地加强了魏晋神仙道教道诫仪轨的监督与执行力度。
其实,早在《太平经》与《老子想尔注》中就有劝导世人行善之说,如“可复得增年,精华润泽,气力康强,是行善所致,恶自衰落,亦何所疑……念之复念,不顺作逆,而求久生。”[4]601“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以此为身宝矣。”[5]这些论述正是表明积德行善是求长生之必要条件。而葛洪则是把积善修德的道德戒律更加细致地落到实处。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微旨》中云:“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算减则人贫耗疾病……又言身中有三尸……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所为过失。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3]125这里说天上有司过神、灶神等神灵,掌管人间的善恶之事,对善恶进行监督夺算,根据人们的功德罪过对其寿命进行增减赏罚。向来道德伦理只能靠社会舆论来自觉约束,而通过葛洪将儒道进行融合之后,道德伦理就受到了天神的监督与控制,道德戒律可以更加有效地执行下去,从而更好地调节了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也维护了既定的社会统治秩序。葛洪正是注意到了神仙世界同现实世界之间需要用善恶机制来进行连接,因而除了上述著作论述赏善罚恶之事外,还在其《神仙传》中也记载了许多惩恶扬善的故事情节。伦理道德基础渐渐成为通往仙途的关键。
葛洪修仙体系中的伦理道诫基本上奠定了中国道教伦理规范的基础,后世虽有改革和发展,但只是在葛洪理论之上的修修补补。如寇谦之、杜光庭以及设立“十戒”的陆修静等人,他们同样是在遵循儒家道德伦理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使得之后道教的伦理规范越来越细致。另外,后世的人还从葛洪的道诫之中衍生出各种劝善书,如《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功过格》等。可见在中国道教数千年历史长河的发展中,也未曾从根本上脱离开儒家礼教的制约。换言之,道教的发展深受儒家思想的牵制与影响。
综上所述,《抱朴子内篇》伦理思想的产生、确立到后期的发展,始终与儒家礼教息息相关,儒家纲常是葛洪伦理思想的根基所在。儒道结合是魏晋时期社会思潮的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葛洪伦理思想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文化本就有特殊的多元化格局,因而各个学派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在古代中国封建制度的大格局之下,儒家宗法纲常立于不败之地实属必然之事。质言之,古代中国思潮的脉络本就是以儒家学说为主线,融合诸子九流,使之交汇并行,调和交融、相互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