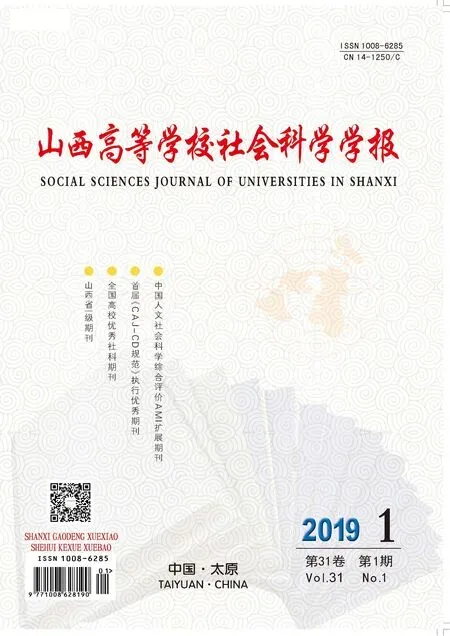清初地方官吏贪腐原因与政府应对
2019-02-22董竹馨
郝 平,董竹馨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有清一代深受贪官污吏之患,贪腐之风给国家政治局势、财政税收、社会秩序和百姓生活都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贪”,《说文解字》解释为“欲物也。从贝今声”[1]131,是从心理层面的阐释,指人内心深处对于身外之物的追求或是面对功名利禄而无法克制的欲望。“腐”,《说文解字》解释为“烂也。从肉府声”[1]90,从结果层面刻画了腐败之后果——糜烂与败坏。有学者从现代法律层面界定贪腐:“指的是所有企图增加个体私利益的不合常规的行为。贿赂、勒索、挪用公共资产、徇私、任人唯亲及拉帮结派等在传统中国都被看成是贪污行为。”[2]149贿赂、勒索等行为,都是清代官员贪腐最常用的手段。
清初,为从明末战乱中恢复,清廷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政策。顺治、康熙、雍正诸帝厉行节俭,试图成为官吏加强自律、廉洁奉公的表率。然而事与愿违,纵观从顺治至乾隆四朝,贪腐之风盛行、贪腐大案频发,更有甚者,出现了大规模贪腐链条和网络。关于清代官员贪腐现象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有诸多相关成果问世①孙季萍的《清代贪污腐败犯罪成因分析》,载于烟台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李海鸥的《贪污:文化的抑或制度的——西方学者关于清代贪污的研究》,载于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边秀双的《清代惩贪机制研究——清代官吏贪污犯罪的社会学分析》,2011年山东大学硕士论文;孟姝芳的《乾隆立法惩贪与实施之探析——对乾隆朝吏治“积疴”问题的再思考》,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等等。。然而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清前期这一较长时间段内地方官员的贪腐问题,较少予以重视。本文拟通过对清初地方官吏贪腐状况进行梳理,研究清代官员大规模贪腐行为的直接表现,分析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原因,探讨清廷应对地方官吏贪腐过程中的得与失。
一、清初地方行政系统的贪腐情况
官员贪腐现象,从清朝入关之初即已显露。清廷为尽快恢复统治秩序,将明代原“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3]57,因此,官吏腐化很大程度上是晚明政治作风的延续。清朝官员贪腐,又以地方上更为恶劣。
清代地方行政系统,以州县官为核心运转。州县官职责广泛,《清史稿》概括为:“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滑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4]3357巨大的政务负担给州县官员造成巨大工作压力,因此,清代地方官多雇佣大量行政辅助人员从旁辅佐,逐渐形成以“书吏、衙役、幕友、长随”为主体的、较为固定的行政辅助系统,地方腐败主要集中在这一系统。
(一)州县官贪腐情况
清代州县官掌握着地方行政权,其贪腐方式或依陋规向下级与百姓索取,或是将历年亏空的摊捐支出,或是将招待上级、送往迎来、贿赂送礼等支出向下摊派。于成龙在《禁革里排碑记》记载了州县官吏摊派与陋规情形:“经承有费,差役有费,科派杂项有费,以及站柜、修仓、解饷、兑漕、种植有费,大半入官胥之囊,而小民倾家败产,甚且流离死徙矣。更有劣衿蠹棍,包揽代充,议贴银一二百两不等,此辈竟尔中饱,且包纳钱粮,多勒耗费。不肖官吏,倚为腹心,指一派十,通用分赃,故乡愚视里役为畏途,而衿蠹以里役为生涯也。”[5]472
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地方官吏的肆意摊派,无疑已经成为造成社会动荡、百姓生活困苦的重要因素。除向下摊派外,州县官为追求权力或是谋求自保,贿赂之风亦颇为猖獗,表现最明显的即是向上级官员行贿。这种送礼行贿行为往往伴随着许多馈赠的理由,诸如节假日、上级亲人的婚丧嫁娶等,甚至行贿者之间还伴随有严重的攀比与交易之风气。典型例证如地方官张九善与任一鸿之间的贿赂交易:“张九善原送一鸿祭奠礼物,值银二两,阎有德馈送奠礼,值银六两,比一鸿不合,皆收入已。张九善原无用银七十两,托一鸿买三岔防守,阎有德亦无畏,委别人惶惧,央令一鸿与于参议过送银一百二十两,一鸿得谢礼银一十两。”[6]三方之间,既是掩盖在礼节性馈赠之下的行贿与谄媚,更是彼此之间都有直接目的的交易。而这种交易,在清代地方官之间可谓比比皆是。
(二)行政辅助人员贪腐情况
清代州县衙门书吏、幕友、长随、衙役四种行政辅助人员中,真正拥有实权者当为书吏、幕友和长随,这三种力量曾一度达到架空州县官员的地步。这些人员同时也是清代官吏贪腐的最基层势力,影响颇为恶劣。
1.书吏。书吏——清朝各官署吏员的总称,是地方政府中操办具体事务的人员,与州县官除了主仆关系外,往往也是其最为亲信的团体。正是由于书吏直接处理州县最基层事务,他们的行为可以很大程度上左右州县官的判断。因此,向书吏行贿现象普遍存在。如清廷曾一次性惩处“崞县县丞方道济、临晋县县丞辛乐尧、忻州吏目王进学、介休县典史庄应麒、曲沃县典史高日葵、浮山县典史李国栋、荣河县典史胡允遂、平陆县典史李梦熊”共八名官吏,罪名为“贪酷踰闲,肆淫罔忌,此抚臣所谓脏私有据者也”[7]。县丞主要负责文书、仓库等的管理,典史、典吏是地方上的“吏”,有时还会兼任县丞。由此可见,地方官吏贪腐,在当时的山西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为防止地方州县官在本省集中势力,进而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清廷曾规定:“州县官既不允许在本省任职,也不允许在距其家乡500里以内的邻省任职。还有一个‘回避法’禁止同宗和外亲姻亲在同一省任职。”[8]40在此规定要求下,远赴他乡的州县官为熟悉所管辖州县的地方情势,利用当地书吏协助自己迅速熟悉和办理当地事务就成为有效的方法。官员的迁徙与吏役的相对稳定形成对比,因此,书吏在一地,拥有长时间的较为稳定的势力基础,可以利用州县官的重视和对地方事务的熟悉,为其收敛钱财制造机会。书吏的职能包括草拟公牍、填制例行报表、拟制备忘录、填发传票、填制赋税册籍、整理档案等[8]73-75。在这些职能中,拟制备忘录、填发传票和填制赋税册籍为其贪腐受贿、勒索敲诈提供了极大便利。与此同时,每年夏秋两季的征税也是书吏们伺机盘剥的绝佳时机。催科过程中收取百姓所给的宽限费、收税过程中以各种理由进行敲诈,以及要求以官价购买物品等行为都成为其收敛钱财、中饱私囊的手段。
2.幕友。幕友,又称为幕僚、幕客,是清代地方政府中行政长官的助手,主要职能在于为州县官员出谋划策。关于幕友的来源和身份,郑天挺归纳为朝廷指派、随长官出差、特殊机会物色得来、国内著名学者、国内名流、地方人士、丁忧人员、退休或失意官吏、京官(未补缺者)、新贵(进士、举人)、秀才、门生故吏、亲属、专业幕宾(绍兴师爷)等14类[9]。如此广泛的来源,再加上幕友之间常采取推荐上任的行为,使幕友集团形成一个拥有众多关系且与官府关系密切的职场网络,“各省上司幕友,多有包揽分肥。州县幕中,非其与类,一切详案多苛驳。州县官势不能支,向上官禀请荐举,以图照应,上下勾连,作奸行贿”[10]1028。在这个网络中,幕友与上级、幕友之间、幕友与下级之间的互动往来,为其贪腐敛财提供了机会。此外,幕友作为外省人,要想对任职地民情有所了解,也必须与书吏保持密切联系,这也就为其串通书吏弄权舞弊提供了便利,形成了地方幕友书吏间的贪腐网络。
3.长随。长随,主要指长期随侍在官员身边的家丁。由于中国悠久的宗法传统影响,官员在选择随侍家丁的标准上,与其有血缘关系的姻亲家属或有过交往的故旧友人家属便成为首要对象。这些亲族、家丁凭借与官员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把持官员与他人联络渠道,伺机索贿;另一方面甚至直接插手官府政务,收贿行为和贪腐行为较之书吏与幕友更为直接。有的官员甚至纵容长随行为,“任内多用亲族,或以手足而充奴隶之事,托以腹心;或以子弟而作内幕之宾,任其喜怒;甚至女婿,娇客也,无事不管;郎舅,内亲也,无恶不为”[11]358。如潞城县知县唐朴,大肆贪婪,直接唆使“官门家人萧二勒取银匠,倾销元宝、陋规银五十两”[12]。他们或是有人求见官员,非使银不可见;或是以官员的名义收受见面礼;或是与吏役合伙,向有事办理者索取银两。更有地方官的亲族打着官员的名义,行使特权,在百姓中树威,进而对百姓进行敲诈索取,形成令百姓痛恶的污浊势力,助长了贪腐风气。
书吏、幕友、长随,除了各自有各自的贪腐手段与途径外,彼此之间也存在诱导性的利益关系,这层利益关系使他们为了扩大财源,相互结成谋取私利的小团体,沆瀣一气、欺上瞒下,大大增加了惩治贪腐的难度。
二、清初地方官吏的贪腐原因
通过以上对清代地方最主要的几股贪腐势力的介绍可知,从清前期开始,贪腐之风在地方上便以难以遏制的趋势蔓延开来。而究其贪腐盛行之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从制度层面来看,顺治十八年(1661),清朝废除了沿自明代的巡按御史,宣告中央监察官以临时地方官的身份监察地方的制度被取消。巡按制度有三大特点:一是内外相维、以小制大;二是巡按御史一年一代,以中央监察官监督久任的地方官;三是监察官受法律和皇帝“敕令”约束,职责分明[13]88-89。以小制大可以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所导致的权力滥用;一年一代又避免了监察官在某地长期逗留,培养势力、收取经济利益,也将监察官与地方官的合流贪腐几率降低。巡按御史取消使得地方权力之间的平衡与制约受到破坏。
在明代,制定有在地方政府中正官与佐官相互牵制的措施以使其互相监督的制度:“凡内外各衙门印信,长官收掌,同僚佐贰官用纸与印面上封记,俱各画字。”[11]281这一制度虽然不能完全避免正官与佐官的同流合污,以权制权的方法却也不失为抑遏贪腐现象的一种有效手段。而时至清代,正佐监督机制名存实亡,州县多以主官负责为主,许多州县已不再设置佐官,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央对地方权力的约束和管理。
第二,清代官员薪俸微薄,无法养家。据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梳理,在顺治、康熙时代,州县官仅能得到一份名义上的薪俸。其中州县官的薪俸大致为:知州每年名义薪俸80两银子,知县在首府者年俸60两,在外地者年俸45两[8]41。从雍正朝开始,在名义薪俸之外,还发给州县官一份实质性的津贴,即养廉银[8]40。但实际上,经过层层盘剥,州县官所得养廉银是非常少的。顾炎武就曾明确提出:“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14]510仅靠薪俸,连维持州县官平日里的各项支出都有困难,更莫论对下属岗职经费的支出和填补历年亏空的摊捐支出,以及招待上级、送往迎来、贿赂送礼等支出。向上的高额支出,导致了向下的杂费。州县官利用自身权力,从顺治到康熙年间,火耗加收现象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直接向下级及百姓索取,以此来充实自己的私囊,并以各种理由将其纳入约定俗成的合理范围。
第三,对权力的追求是清代地方官员贪腐的直接动机。“作为个人具有的属性或品质,权力可能被视为人们追求的,甚至是人类奋斗的基本目标。因此产生了涉及人性本身性质的人类基本动机问题。”[15]3中国古代政治中“官本位”文化深入人心。在这种文化影响下,将公共权力转换为私人权力或是如何在私人领域扩大个人的权力和影响,无论对官员还是普通士人都具有巨大诱惑力。儒生向士大夫阶层不断转化,也是社会观念从重伦理道德向重名分和社会地位的转化,以此谋求更大的权力。这种心态和作风,在清代科举舞弊案频发、无法保证公平以至于士人对官府失去信任的社会环境里,一些长年求仕不得者便开始试图以贿赂手段谋求所愿,更加剧了科举舞弊行为并导致恶性循环,卖官鬻爵亦随之猖獗。与此同时,不满足于自己所处地位的官员,也通过相同的方式向上级“馈赠”。他们认定不同价值的礼物能够换取不同等级的权力和地位。而在赠礼和行贿并没有绝对的界限的清代,所产生的恶果更为严重。
第四,诸多特权阶层的存在加剧了贪腐之风。清代最庞大的特权阶层是满族贵族。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最大的忧患即在于防范汉族。清代官僚系统最重要的使命,亦在于维护统治的稳定。在这一前提下,地方官员的贪腐问题被大大忽略,甚至贪腐曾一度被接受和纵容,以用作帝王分散地方官僚政治野心的手段。因为贪腐而被严惩的案例,大多包藏有政治动因。以乾隆帝为例,即位之初频繁向雍正旧臣发动攻势,以此来树立新朝权威,多以贪污腐败作为罪名和攻击武器。后来,又以此为由,告诫官员们不得谋反或是对抗皇权[2]150-153。体现在科举考试和授官方面,州县官员的入仕途径既有科举考试,也有捐纳、荫生,无论以何种途径当官,州县官一职如果由汉人担任,便要求同时有满人官员任同级之职。“满族人谋求官位靠得是出身……而大批有能力也有崇高志向的汉族人则被排除在官僚机构之外,在谋求官位时屡遭挫折与失败。”[2]151满人更易为官的优势使他们拥有汉人所不及的各种特权,而对汉人来说,这种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和法律地位的低下使其将眼光转向实利,汉族官员对金钱名利的追求是对满汉不平等地位的反击,也是其在经济领域寻求的一种暂时的心理平衡。
与此同时,在民间士绅和百姓之间,亦存在严重的司法不平等。根据黄宗智的研究:“二十世纪前的国家政权没有完全渗入自然村。它直接的权力,限于这个双层的社会政治结构的上层。在下层之中,它一般只能透过士绅间接行使权力,并靠吸引下层结构中的上移分子进入上层来控制自然村。”[16]229士绅作为乡村的领导阶层和地方官在乡村中的代表,其身份具有特殊性,士绅既帮助地方官吏管理民众,传达命令,参与催粮、征税、司法等活动;也帮助民众传达对上级官吏和清政府的意见。士绅享有社会、经济和法律上的各项特权,“不在当地司法管辖之下,也不受常规司法程序的约束。学绅和官绅可以免除徒刑之下的刑罚”[8]295-296。这些特权无形中助长了士绅肆无忌惮搜刮百姓的气焰。士绅受到当地官员敬重,打着官员名义为自己谋取私利,甚至与地方吏役勾结,形成小团体,在各项基层经济活动中贪污、勒索、敲诈,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日常负担。
百姓的容忍和默认也是促成地方官吏贪腐风气盛行的直接推手。中国古代官方长期倡导的君权神授的天命观使百姓对官府的畏惧心理较强,逐渐培育出驯服的、具有强烈依赖色彩的国民性,容忍程度甚高。加之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小农经济环境中,民众被束缚在土地上,地域的封闭性、对土地的依赖性,都造成了民众安于现状、缺乏创造力、以安定和谐的生活方式作为唯一诉求的心理特征。因此,在无力改变眼前困局的时候,“大事化小、小时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成为无奈之下的选择。
如陕西吏员董思义,于顺治五年(1648)除授山西平阳府蒲州临晋县樊桥驿丞,顺治十年(1653)便被革职,因其“于顺治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就不合,故远官犯赃,问发为民事例,揩印马骡、查验肥大,向本驿四十五家马户每家索要银一两,共索银肆拾伍两,入己”[17]。从这条资料中可以看出,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位“不入流”的吏员就凭借微薄的权力,向马户索要贿银,而四十五家马户无一拒绝缴纳。民众容忍度之高,可见一斑。而一年两税,即每年夏秋两季的征税更是吏员们扩大收入的最佳机会,催科过程中百姓所给的宽限费、收税过程中以各种理由进行敲诈,以及要求以官价购买物品等行为都为其收敛钱财、中饱私囊提供了便利。
三、政府应对——清代的惩贪措施
(一)加强制度建设
清朝初年对于官吏贪腐问题,曾采取大力整肃官场风纪和一经发现严惩不贷的处理方式。如顺治十二年(1655),吏部书吏章冕“讦告顺天巡按顾仁悖旨婪赃,陷害无辜”,顺治帝亲自审理,并以索收贿赂之名将其处斩。然顺治十四年(1657),又随即发生震惊朝野的重大科场受贿舞弊案,“蔓延几及全国”[18]29。为根治这一官场弊病,清廷除了对官员贪腐严惩不贷外,还出台多项措施进行防范,并将地方监察纳入行政体系。雍正元年(1723),将明代“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事”的六科给事中系统并入督察院,成为督察院的附属机构。督察院职责在于“掌言职,传达纶音,勘鞠官府公事,以注销文卷,有封驳即闻”[11]275,从此台谏合一形式确立,给事中的监督重心由皇帝转为官员,督察院监察百官职能大大强化。此外,雍正、乾隆等帝常采用提交“密奏”的方法,将地方官吏置于中央密查的网络中。
为了选拔廉吏,从源头上治理地方贪腐问题,清廷建立严格的地方官吏选拔制度。清代在明代官职课考制度的基础上,确定了“四格八法”的选官标准。“‘四格’即守(操守)、政(政绩)、才(才能)、年(年资);‘八法’即贪、酷、罢软无力、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涉及违纪违法或不称职,按情节给以惩处和降调处分。”[11]382虽然这一制度在初期实行阶段收效甚微,但不可否认,“四格八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官员的正常晋升;另外,也规范了地方官吏的职能,对贪腐人员起到一定震慑作用。嘉庆、道光以后,清廷更是不断改革地方官吏的选拔和监察制度,重点惩治贪吏、加强廉政建设。
(二)增强法律措施
针对地方官吏贪腐严重的这一情况,清廷虽然持续加大对贪腐行为的惩处力度,但在《大清会典》与惩贪相关的规定上,却依然延用《大明律》。如在其“刑律·受赃”一条中,将“受赃”划分为“官吏受财、坐赃致罪、事后受财、官吏听许财务、有事以财请求、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家人求索、风宪官吏犯赃、因公科敛、克留盗赃、私受公侯财务”十一方面[19]6087-6088。这是对《大明律·赃罪》的完全承袭。以其中“官吏受财”为例: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无禄人各减一等,官追夺除名,吏罢役,俱不叙用。说事过钱者,有禄人减受钱人一等,无禄人减二等,罪止杖一百,徒二年[19]6087。
以上“官吏受财”及“说事过钱”,亦与《大明律》规定相同。《大明律》修订于明初,清代官僚体制与社会形态与明时已发生巨大变化。而律例中的规定又有颇多模糊之处,对于官吏受赃的界定和案件的判定缺乏依据,处罚细节也不够明确。“有禄人”“无禄人”的区别、王公贵族的诸多特权,更是从根本上造就了这项律例的不平等性。因此,面对具体而复杂的贪腐案件,据此量刑,难度颇大。与此同时,皇权对贪腐案件的干预程度在有清一代达到顶峰。在清代处理贪腐案件的奏疏中,经常可见“曾养心所犯赦前居多,赦后居少,应否宥罪,恭候圣裁”[20];“樊桥驿驿丞董思义,贪婪存心,邮苦罔恤,验马骡则恣意吓索……但查事犯赦前,应否有罪,赃仍照追,恭候圣裁”等行文[17]。然皇权的干预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可以省去诸多繁琐、耗时的行政程序直接处理贪腐案件,对贪官污吏的震慑程度尤甚;另一方面却也渐渐成为一些功勋卓著或深受皇帝信赖的官员大肆贪腐索贿的挡箭牌。督抚直接对皇帝负责和“密奏”制度虽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官吏的监督,但也直接导致各项政策的推行多以皇帝好恶为凭,为善于顺势逢迎的官员提供了可趁之机,欺上瞒下,罗织贪腐网络,无形中导致清代官员贪腐作风愈加严重。
增强法律措施,不能仅仅沿袭前代,法律建设必须切合实际、因时而变。清前期地方官吏贪腐网络不断扩大,针对这一情况,至嘉庆朝,将《乾隆会典》的“则例改为事例,按年编裁行政事例,一事一例,作为会典的辅助,把各部门的严格损益、行政制度变化,都作了详细对照,以便于实际运用”[21]。光绪朝在新修订的《大清会典》中又增加了大量事例,把措施落到实处,将法律建设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法律措施逐步精细化、实际化。除了《大清会典》这一具有总领性质的法律外,清代各部院也推行了一系列法律措施,如《劝惩则例》《六部现行则例》《钦定颁行六部则例》《六部处分则例》《钦定吏部则例》《开复革职办法》《侵贪犯员罪名》《侵贪案条例》《职官犯罪逃脱治罪例》等[22],严格官吏管理。在这些官方法律中,以康雍乾三朝最盛,关于惩贪的法律明显增多,中央、地方一体的监察立法网络逐步建立。
(三) 地方宣传教化
除了制度建设和法律文化,社会宣传教化也是廉政的重要手段。针对地方官吏贪腐现象,清朝一面惩恶,一面扬善,在严惩贪吏的同时,进行官吏日常奖励和廉吏典型树立的工作。口头褒奖、加俸加封、升职迁官等是常见的官吏奖励形式,给予地方官吏钱财上的支持及名望上的肯定,这些形式在激励地方官员追求政绩的同时,也在树立良好道德操守、抵制不良贪腐风气方面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廉洁奉公是地方官吏的基本原则,为此,清廷极力突出这方面内容。如《清史稿》把于成龙、彭鹏、陈瑸、陈鹏年、施世纶等5人合在一传之中,其作为康熙年间廉政官吏的代表,被皇帝赞扬,被百姓传颂,甚至发展为小说的主人公,成为地方宣传教化的正面典型。
为了遏制地方贪腐风潮,清政府同时也在民间进行过大量的宣传和教化工作,以求解决廉政政策缺失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如要求“每年初一和十五,州县官必须到孔庙和城隍庙祭拜”[8]33,将自己一年政务得失进行反省。山西代州五台县更是在顺治十六年(1659)就立起“永禁吏役害民碑”,碑中提出要“除加收火耗之害;除签民解钱之害;除派养马之害;除勒取借领之害;除宝兰钱粮之害;除索扰行户之害;除衙役索诈之害”[23]。这些条款,正是对清前期社会中的贪污腐败、勒索敲诈现象之直接反映。而祭拜自省、立碑宣传、告诫教化等方式,在官员无限膨胀的权力面前虽然很难起到实质性作用,却也是一种有效的文化熏陶。
四、结语
清前期地方官吏贪腐原因是多样的。但就地方来说,一方面形成一条从州县官员到低层胥吏均深陷其中的纵向贪腐链条;另一方面也在所谓“礼”和“利”的驱动下,贪官之间在一定范围内形成沆瀣一气、利益交织的横向贪腐网络。在这种环境中,即使是起初清正自廉的官员,为求自保或是升官,也往往不得不同流合污,以致慢慢走上贪污腐化的不归路。典型例证如山西省潞城县知县唐朴,为官之初“尚知检束,身心不敢荡闲踰矩”,然而在混乱污浊的官场环境中日久之后,“因乱服,知府季进德既系同乡,又属瓜葛,遂敢藐视功令,日渐纵恣”[12]。唐朴的堕落过程,是个人意志力和心理的抉择,更是迁就于整体官场环境的无奈之举。而清政府对于官员贪腐的预防和惩治措施,却是在中央革除六科给事中、在地方废除巡按御史,大大降低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力度。具体行政过程中,又往往只将“贪腐”作为惩治犯有政治错误官员的借口,对于真正的贪腐行为长期忽略,反而试图通过皇帝对清廉官员的嘉奖、宣传来对官员进行感化,成效甚微。伴随着政府的监管不严、制度漏洞,清朝整体地方官场贪腐规模日益扩大,对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的和谐稳定,都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而加强贪腐治理、增强行政立法、完善制度体系、巩固廉政建设仍是当时清政府应对地方官吏贪腐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