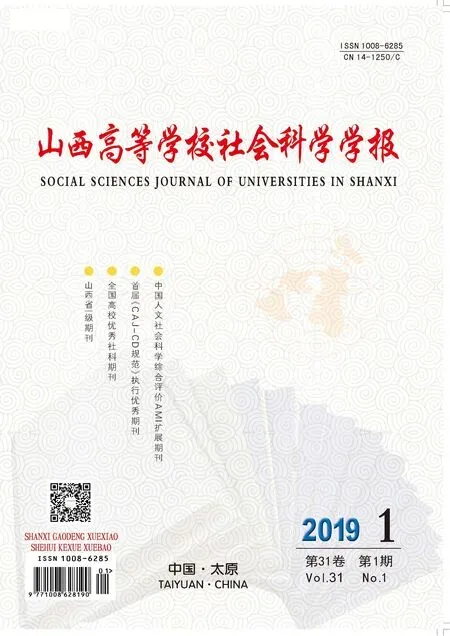论儒道传统技术思想对克服当前技术虚无主义的借鉴意义
2019-02-22李刚
李 刚
(遵义医科大学 人文医学研究中心,贵州 遵义 563000)
高扬“理性”一直贯穿着现代性的各个发展阶段。理性的标举促使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可是到了后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某种独立性,其自身要求理性以极端的形式为现代技术服务。如何促使科学良性发展?如何应对现代性背景下全球性的技术虚无主义?中国儒道两家传统的技术观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一、技术虚无主义:当今世界的整体图像
由理性的标举到技术最终取得统治地位,现代性的负面效应越来越触目惊心。现代性的概念是流动的。流动的现代性可以划分为五个主要阶段或类型: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启蒙时期的现代性、德国唯心论的现代性、19世纪到20世纪初含混的现代性和当代的高度现代性。这些阶段或类型的前后相继呈现的是现代性进化的轨迹[1]。现代性从其字面意思就可以看出,其代表着一种试图与传统决裂的勇气。而现代性的各个阶段发展虽然各有特点,但是对于“理性”的高扬是贯穿其各个发展阶段的核心。正是由于对“理性”的标举使得科学技术一步步取得飞跃式的发展,人类社会各方面呈现出与古代社会的“差异”,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代性问题。正是技术发展使现代性成为可能,如果人们不充分了解技术发展,怎么会有希望理解现代性[2]?而人们现在谈到“技术”时,往往不会忘记在其前面加上“科学”两个字,似乎“科学技术”这样的称呼本身暗含着其与古代技术相比,有着后者无法企及的优越性。海德格尔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已经背离了古代技术的初衷,越来越走向了一种可怕的深渊。
海德格尔认为,在古希腊,“技术”首先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让某物显现,并让其处于现身中。“技术”这个词也意味着被遮蔽的人与物关系的解蔽。 “倘我们逐步逐步地追问被看作手段的技术根本上是什么,我们就达到了解蔽那里,一切生产制作过程的可能性都基于解蔽之中。”[3]930-931也就是说,在古希腊,技术是让真理发生的一种方式,是人对存在领悟的一种方式。古希腊人对技术的理解“自古以来就遮蔽于建筑的构造之中了。后来它仍然更果断地遮蔽于强力机器的技术之中”[4]143。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本质上也是一种解蔽,不过,现代技术的解蔽却是一种促逼,这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于是,一切都陷入到摆置自然的订造之中,而这种被订造之物的特有状况就是持存。海德格尔将这种促逼着的要求命名为“座架”(Ge-stell)。这种促逼着的要求把人聚集起来,让人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的东西。现代技术的本质便是“座架”。现代技术促逼着人进入解蔽,首先是促逼人用索取之心对待自然,从自然中榨取供我们消耗的能量。
科学无疑是当今时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现代科学将自身囿于存在者的范围内进行所谓的研究,而却要将其研究成果上升到存在领域。海德格尔反对科学对真理的垄断。在他看来,科学有一套严格的研究方法和程序,并有企业活动的特点,仅仅注重所谓眼见为实的结果,却无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科学制造了一种表象,而人们却以为此表象是事物本来的样子,世界于是被把捉为一个由众多存在者表象所拼凑的图像。海德格尔强调:“唯当科学从形而上学而来生存,科学才能不断地重新赢获它的根本任务。”[5]140关于科学与现代技术的关系,他的观点同样深刻:“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单纯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唯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6]66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并非是对现代科学的直接应用,现代技术是相对独立的。现代科学已经沦为现代技术的奴仆,为现代技术的蔓延与扩张出谋划策。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则认为:“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安逸,统治也以更为沉稳的压榨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尽管机器供养了人们,但它使人们变得软弱无力。”[7]技术的异化造成了人自由的丧失和社会的退步。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统治的意识是不太可能受到反思攻击的,因为它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因为它所表达的不再是‘美好生活’的设想。”[8]汤普森认为:“启蒙进程曾经设法以技术统治自然来控制世界,最终导致了一个理性化的、物化的社会总体,而人类在其中不是主人而是奴仆和牺牲品。”[9]
现代技术造成对存在的遗忘以及意义世界的失落,其本质是最高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海德格尔指出:“虚无主义意味着:一切在任何方面都是虚无。……虚无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存在本身是虚无的。”[3]817-818虚无主义是根植于现代性的内在危险。对海德格尔来说,造成现代人“无家可归”状态的虚无主义,其历史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但在其本质中,形而上学就是虚无主义。”[6]239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本身就会导致虚无主义,从传统形而上学产生的那一天起,虚无主义便始终伴随着它。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把存在者整体区分为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而且超感性世界总是包含、规定着感性世界。人们在超感性世界中设定的一系列不断追求的神圣目标,比如理念、上帝、一般主体、理性、科学、技术、进步、文化、文明、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等,由于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方式所设定的,所以导致了虚无主义。尽管尼采反对柏拉图主义,宣告“上帝死了”,但是,超人的诞生意味着尼采用自己设定的另一个上帝代替了基督教的上帝。尼采向虚无主义宣战,最终却走进了另一种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导致遗忘存在,对虚无主义来说存在本身就是虚无的。虚无主义与存在一同行进在历史之中,虚无主义的本能就是遮蔽存在本身,与此同时,存在在虚无主义面前便自行隐匿了。
现代技术作为最高形态的虚无主义,可以称之为技术虚无主义。当代技术虚无主义已经具有某种独立性,可以自我繁殖并自我消化。其自我繁殖和自我消化的表现便是消费主义。技术虚无主义促使消费主义盛行,反过来,消费主义使技术虚无主义找到市场并不断革新与强化。现代技术不断突飞猛进、更新换代,而在对“效率”的极端追求下,大量的消费品被制造出来了。这些消费品进入流通环节而成为“商品”。如马尔库塞所说:“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10]人成了自己制造的消费品的附属物;人已经被他创造的消费品和创造消费品的技术所异化。而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1]人被自己的制造之物异化;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各种各样的异化便是现代性下技术虚无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后果。
为了克服虚无主义的空虚与消费的疲倦,享乐主义成了现代人最后的归宿。人们试图从各种各样的消费中获得快乐与解脱,到头来无非是一场宣泄和随之而来更深的迷茫。人们不仅消费有形的商品,同时也在消费无形的商品。当人们从电影院走出来的一瞬间感觉自己上当受骗时,文化工业便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刷新票房的壮举。当人们沉浸在技术与消费品拼凑的感官空间时,人们最后感觉到的是对自己的厌恶和对世界的绝望,进而迷失在更大的虚无之中。正如大卫·雷·格里芬所言:“当人们随着丧失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也丧失从前对任何传统形式的宗教不朽性的信仰时,就会陷入及时享乐的境地。”[12]
技术虚无主义与消费享乐主义相互交织在一起,彼此促进,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总体景象。而产生现代性问题的最终根源却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在海德格尔看来,当柏拉图用对象性的思维模式追问“存在是什么”的时候,西方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从此便以不同形态重复着柏拉图的问题。答案却依旧是作为不同的存在者被给予的。当柏拉图一旦问及“存在是什么”时,古希腊人原初所理解的既绽开又持留的、不断涌现的、强力的存在便被把捉为存在者,而不是存在自身了。而这种首先从柏拉图发端的“哲学”,此后便具有了后人所谓的“形而上学”的特征。柏拉图本人在其洞穴比喻所叙述的故事中,说明了形而上学的基本形态[5]271。现代科学技术就是不断将自身拘囚在对存在者的实证化、对象化的所谓“发现”中不能自拔,从而遗忘了存在本身。从柏拉图到笛卡尔,再到尼采,西方形而上学的发展是人的主体性不断膨胀的过程,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不断得到形形色色的强化。而现代科学技术在人主体性膨胀的对象性思维模式主导下不断突飞猛进。现代科学技术用实证化的手段将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变成一幅幅异化人的现实世界图像。
哈贝马斯认为,要克服启蒙理性独断的、“主客二分”的主体性思维,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主体间交往关系,然后进行相关的社会变革。马尔库塞将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流浪汉、局外人、失业者等弱势群体的革命性的要求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但是后现代主义者似乎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现代性主张的“理性”“主体性”“宏大叙事”等的反叛和解构上,尤其是其在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之后并没有注重建构,后现代最后却走向了个体主义、相对主义、语词中心论与碎片化。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问题根本上是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基础上产生的,要克服现代技术所产生的虚无主义等问题,必然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根本的变革,这就是他所说的技术世界要实现的“转向”。海德格尔后期转向通过语言来领悟存在。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5]366海德格尔认为,当我们用“诗”与“思”的态度对待与我们照面的存在者时,主客分裂的情形便不复存在了,此时领悟到的是在主客统一基础上存在意义的不断涌现和绽出,古希腊人那里原本的physis(自然)的意义就会被我们所把握。这样,“物”便不是一个个与我们相对立的、供我们使用的物件,而是我们和物一同处在天、地、神、人四元下的敞开之中。海德格尔用“诗意地栖居”[13]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诗意并非飞翔和超越于大地之上,从而逃脱它和漂浮在它之上。正是诗意首先使人进入大地,使人属于大地,并因此使人进入居住。”[4]189
海德格尔晚年接受《明镜》记者采访时提到解决现代技术问题的方法时说:“我深信,现代技术世界是从什么地方出现的,其转向也只能在那里准备,这个转向不可能通过接受禅宗思想或什么其他东方的世界经验来完成,还是要借助于欧洲传统及其新格局来转思。思只有通过具有同一渊源和同一规定的思来转变。”[14]76但是海德格尔在同一采访里又说:“我们当中又有谁能说得清,有朝一日会不会在俄国和中国一种‘思’的古老传统被唤醒,这一古老传统帮助人们实现对技术世界形成一种自由关系呢?”[14]75由此可见,在海德格尔看来,源自中国和俄国的古老思想可以帮助解决现代技术带来的问题。另外,海德格尔又认为,对于技术问题的克服必须依靠西方思想自身来完成。表面上看起来,海德格尔的说法似乎存在矛盾,但其实并不冲突。海德格尔之所以这样说,恰恰是基于他对西方思想和东方思想在解决技术问题上的互补性的认识。从上述海德格尔回答《明镜》记者的采访来看,他认为来自中国的“思”的古老传统是可以帮助克服现代性中的技术异化问题的。海德格尔本人就吸收了很多道家的思想,并一度在1946年夏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将《老子》翻译成德文。两人在翻译了有关“道”的八章内容后,由于萧师毅的退出,《老子》的翻译不得不终止。但是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对中国道家的兴趣是非常浓厚的。
其实,在中国,不仅道家,还有儒家也给我们克服技术虚无主义以重要启示。下面笔者对中国古代儒道两家带给我们克服技术虚无主义的借鉴意义进行具体分析。
二、儒道传统技术思想对克服当前技术虚无主义的借鉴意义
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天下失范,孔子的理想就是复周礼以匡正天下。对孔子和孔子以后的儒家来说,一个社会中“仁道”的确立远比某种技术的应用重要。儒家对君子人格的要求便是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对于技术在整个社会的作用,儒家并不是没有考虑,只是认为和君子修身、从政、治理国家来比,技术并不居于主要地位。“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以下所引《论语》,只注篇名)这里,孔子坚定地认为,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好,最重要的不是某种生产性的技艺是否得到了发展,而是治理国家的人是否实行仁道。如果一个国家按照仁道来治理,则各种生产技艺自然能得到发展;如果一个国家背离仁道,即使生产技艺短时间发展很快,也是不好的。孔子高足子夏进而认为,那些小的技艺,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对于治理天下这种宏伟的事业来说,小的技艺就不行了。 “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子张》)
在孔子那里,技艺往往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物质生活需要,是必须的,但不是崇高的。“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孔子将“技艺”称为“鄙事”,是基于把“技艺”和一个君子对“仁道”的追求作对比而言的。孔子对“技艺”多少带有一些鄙薄,但是并不是完全排斥,只是他认为对于求“仁道”的君子来说,从事“技艺”之类的事情,并不是他们要致力去做的。孔子明确说:“吾不试,故艺。”(《子罕》)他说自己早年不被国家所用,才学得一些技艺。这和他所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一样都在强调:从事技艺不足以治理国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对孔子来说,一个社会里“义”永远比“利”重要。孔子对于“技术”在器具层面的局限性是很清楚的。为此他说:“君子不器。” (《为政》)皇侃疏曰:“此章明君子之人不系守一业也。器者,给用之物也。犹如舟可汎于海不可登山,车可陆行不可济海。君子当才业周普,不得如器之守一也。”[15]朱熹承皇侃之意,曰:“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16]《周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关于“器”,《说文解字》释之曰:“皿也。象器之口,犬所守之。”段玉裁注曰:“有所盛曰器。无所盛曰械。”显然,无论是作为器皿的“器”,还是作为器械的“器”,在孔子看来其作用都是有一定局限的,而制作这些器具的技术之类的事情,对于孔子来说当然同样是有局限的。君子之所以“不器”,就是要突破器具以及技术本身形而下的物的局限,达到对“仁道”的复归,君子不能受器物宰制,而要以道御器,以道统物。
古代儒家致力于社会“仁道”秩序的建立与维系,与之相比,技术的发展被放在次要的位置。用仁道秩序构筑意义世界的儒家更是强烈地反对一味崇尚技术与器物的做法。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一生的意义在于孜孜不倦地追求“仁德”。“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为仁之“志”在孔子那里十分重要。一个人只有树立了“志”,才会有之后一系列“求志”的行动,他的生命才会有意义。在任何时候,为仁之“志”是不能丢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孔子虽不赞成子路式轻视生命的鲁莽,但是对于成就“仁道”的勇往直前的态度本身就表明了人生的意义在于对“仁道”的追求。
孟子继承孔子的“志”论,提出“浩然之气”,并认为:“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孟子·公孙丑上》,以下所引《孟子》,只注篇名)“志”在孟子看来是调动“气”的首要条件。孟子认为:“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公孙丑上》)“气”乃“配义与道”“集义所生”,正是孟子用儒家的价值标准给“气”做的重要诠释。
儒家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培养“仁德”,践行“仁道”,这便是人生的终极意义和快乐的真正源泉。“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孔子的这段话正是指出了快乐的来源不是某种技术的推广而获得更多的感官物质享受,而是“为仁”。“君子忧道不忧贫” (《卫灵公》),在孔子看来,物质的贫穷并不值得一个人去忧愁,相反一个人更要在乎的是对“仁道”的体悟和践行。孔子之所以最赞赏颜回,是因为颜回虽然家贫,但是却以“为仁”为最大的快乐。孔子因而感叹颜回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论语》一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说的也是一个人学习“仁德”,践行“仁道”所获得的快乐,以及朋友之间因为信义而获得的快乐。
《论语》中孔子和弟子们一起谈论各自“志向”总共有两处,两处对话体现了孔子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愿景。一处是在《公冶长》篇,孔子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志向”: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
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敞之而无憾。”
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孔子看来,在一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和睦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孔子一生追求之“仁道”在社会层面的落实,体现了孔子“泛爱众,而亲仁”(《学而》)的主张。
在《先进》篇,孔子也谈到了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孔子与弟子当时讨论各自为政治国的“志向”,孔子鼓励曾点说出自己的想法后,表示他同意曾点的想法。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曾点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曾点这里说的一番话同样也是对孔子心中要实现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仁道”理想社会的诗意描述。所以,孔子表示他与曾点的志向是相同的。
可见,孔子心目中完美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技术发达,工具理性发展到极限的、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恰恰相反,孔子认为社会的物化是“鄙事”,君子不为。而真正美好的社会是要突破物质技术层面的局限,而进入“仁道”层面。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温情有礼,人们不是受制于技术而疲于奔命,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螺丝钉,而是悠然自足,怡然自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正是说明每一个人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实现了其自身的意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更是说明了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里不仅人与人之间温情和睦,而且实现了个体的真正自由。在孔子心目中这样一个“仁德”的社会里,每一个人自然会获得真正的快乐。
梁漱溟先生认为,西方人科学方面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理智的活动太强太盛,因此,西方人“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这是十九世纪暴露不可掩的事实!”[17]70他反对用理性的、算账的态度对待一切,而提倡儒家的“仁德”,并说:“最与仁相违的生活,就是算账的生活。所谓不仁的人,不是别的,就是算账的人。仁只是生趣盎然,才一算账则生趣丧矣。”[17]139
与儒家从社会整体的和谐出发来认识技术的局限性相比,道家更为警惕技术对个体的异化作用。
老子深刻地认识到了技术的负面作用,认为技术的本质是一种“巧智”,其本身是对人心质朴状态的残害,为此他主张“绝巧弃利” (《老子》十九章,以下所引《老子》,只注章名)。老子认为,追逐“技巧”是失道的表现。他指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五十七章)为此,人要避免“巧”,却要“拙”,也就是“大巧若拙” (四十五章)。人心的躁动产生出机巧之心,要去除机巧之心就必须“归静”,对大道直接体悟,正所谓“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十六章)归静彰显为“朴”。“敦兮其若朴” (十五章),这是老子对古之善为道者的描述。他认为“朴”是“道”的一个本质属性,并说“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三十二章)老子提出“朴”就是要把“技巧”里过分高涨的主体性去除掉,体现了人在大道面前的谦逊。
庄子在继承老子对技术的批判思想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对“技术”的异化作用进行批判。
《庄子·天地》(以下所引《庄子》,只注篇名)篇中有一则寓言,说子贡南游楚国,返回晋国时,途经汉水的南岸,看见一老者在菜园子里整地开畦,用水瓮浇地,很是吃力而见效甚少。子贡于是对他说:“有一种机械,一天灌溉上百个菜畦,用力很少且见效颇多,先生您难道不愿意用吗?”灌园的老者抬头看着子贡说:“那该怎样做呢?”子贡说:“用木加工而成机械,后面重前面轻,汲水就像抽引,非常快,这个工具名字叫桔槔。”老者面带怒色讥笑道:“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听了以后非常羞愧,低头不语。
庄子在两千多年前已经提醒人类技术的异化作用,可谓是振聋发聩。庄子在这里借浇地老人之口,在“道”和“技”的关系层面,谈论对“道”的体悟和实践问题。在庄子看来,技术虽然具有便利性、高效性等特点,但是技术却可以使人产生机巧之心,而机巧之心会破坏人内心原本对“道”的质朴体验,让人“神生不定”,不能载道。这是庄子对老子“绝巧弃利”观点的一个发挥。
不过,庄子并没有因此全面否定技术。庄子认为,人们对技术的实践应该上升到“技艺”的层面,由“技”入“道”,通过“技艺”,达到对“道”的领悟。但是庄子并非试图向我们展示技术的艺术化过程。在庖丁解牛、梓庆为鐻、轮扁斫轮等寓言中,庄子都是在借这些匠人高超的技艺来谈他们对“道”的领悟。在庄子看来,他们之所以有这么高超的技艺,那是因为他们能达乎道境,是一些善为道者。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养生主》》)
当文惠君惊讶地问庖丁为何其技艺精湛到如此程度时,庖丁并没有说自己是怎样练习解牛的具体技艺的,而是说他爱好的是一种比“技”要高深的规律:“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养生主》)可见,与其说庖丁的解牛技艺高超,倒不如说庖丁是一个善为道者。庄子这里的用意显然是借“技”谈“道”。庄子认为,“道”高于“技”,“道”是统“技”的,庖丁之所以有着高超的解牛技艺,是由于他对“道”的领悟非常深刻。庖丁借解牛讲出了自己对“道”的领悟过程:“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养生主》)刚开始学习解牛的时候,庖丁眼中的牛都是有形体的、完整的牛,三年以后看到的便不是整个的牛了,和文惠君说话之时,庖丁已经不再用感官来把握牛了,而是从无形的“道”的高度来把握牛了。庖丁解牛的过程就是一个对“道”的体悟与践行的过程。
庄子指出,“道”要高于“技”,而且“道”在“技”中,通过“技”便可以认识“道”。这揭示了“人”“技”“道”三者之间的本真关系。不是说任何一种技术都是对“道”的一种体现,只有人首先对“道”进行深刻领悟后进行操作的技术才是真正合于大道的。
庄子论述“道”与“技”的关系时还提到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气”。正是“气”沟通了“道”与“技”,使得对形而上“道”的领悟能够顺利地转化为得心应手的“技”。《达生》篇梓庆为鐻的寓言中,鲁候好奇梓庆削木为鐻简直是鬼斧神工,便问他是为何?梓庆回答道:“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曰,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梓庆静心养“气”的过程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心斋”的过程。这个过程实质上是对个人的主体性偏见的消解过程。经过“心斋”,梓庆进入山林,仔细选择外形最接近鐻的林木,然后动手加工。这样进行的技术活动完全是一个“以天合天” (《达生》)的过程,自然就会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达生》篇中列子问关尹“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的原因,关尹答曰“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庖丁解牛里庖丁说他解牛时“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轮扁斫轮时说他已经七十岁了还不能把他斫轮的绝技传给他儿子时说:“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天道》)在“道”与“技”之间,这些得之于心而不能言的体验就是“气”,所以,庄子主张“纯气之守”。
道家对于技术的异化持批判态度,并探索“道”“气”“技”的实践模式,认为人在从事技术活动时,其实是对“道”的领悟过程。在道家看来,“道”作为万事万物的根源,当然也是人的一切实践活动的来源。人行动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道”的领悟与复归。老子对此称之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在对“道”的领悟与践行中人便能够获得最大的快乐。道家一再反对感官之乐,认为沉溺于感官物质享受是极大的危险。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十二章)庄子进而认为从“道”而来的快乐是“天乐”“至乐”。 “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道》)“吾观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誙誙然如将不得已,而皆曰乐者,吾未之乐也,亦未之不乐也。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至乐》)在老子和庄子看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实现的世俗的物质享受之乐其实是一种“苦”,真正的快乐必定是从“道”而来的“天乐”“至乐”。
现代性的社会原型乃是改造自然的主体的人。道家的基点则不仅超越主体性,而且超越人[18]。不过,道家消解人的主体性,并不是让人沉浸在主观的精神世界中消极避世,而是提倡人顺应自然而为,过淡泊宁静的社会生活。为捍卫个体的“自然”天性、自由本性和自足个性,道家强烈反对一切来自外部和后天的可能会压制、戕害人的“自然”本性、压缩人的自由空间的东西[19]。但是这并不是说道家反对人去过任何社会生活。道家只是主张,人的社会生活必须建立在尊重和彰显个人的“自然”天性的基础之上。
老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老子在这里通过强调“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态度明确地表明最好的社会其实并不是技术多么发达,能够给人们制造多少器具,提供多么大的便利社会,而是人心复归淳朴,天下太平,人与人相安无事的自足社会。庄子进一步提出至德之世的说法:“夫至德之世,同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秉承老子,庄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弃绝技术的异化及一切巧智与多欲的活动,从而“无知”“无欲”,复归自然与素朴的社会。
三、结论
与西方现代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强力机械技术不同,中国古人所提倡的技术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技艺”。但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人对征服自然的强力机械技术的思维模式在根本上不了解。儒道两家传统对工具理性以及技术虚无主义异化的本质的认识相当深刻,十分具有预见性。现代工具理性的泛滥、技术虚无主义的危机根本上是西方主客二分的传统形而上学造成的危机。要彻底克服技术虚无主义,就要克服西方主客二分的传统形而上学。我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与道家的主张,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儒道,都立场坚定地反对技术的异化,都提倡“以道统技”,并一直秉持“道”与“技”的最佳平衡点。作为中国文化根基的儒道两家的思维方式从来就不是主客对立的对象性思维,而是主客统一、天人合一的非对象性思维。与以技术虚无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科学的主客对立的技术发展模式相比,古代中国有着生长在自己传统文化根基之上的良性自足的、天人合一的技术发展模式。尽管我们不可能再完全回到古代儒道两家的技术发展模式,但是,为了促进科学良性发展,在寻求克服当代技术虚无主义的探索中,儒道两家传统的技术观所提倡的“道”与“技”平衡发展的思维与做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