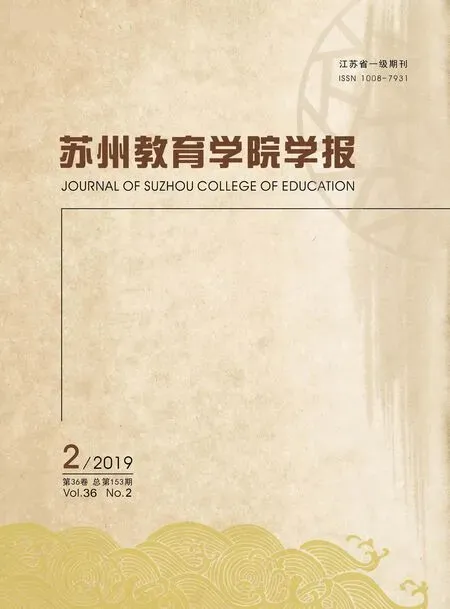语言、细节与生活:奥莉维娅·克莱尔及其短篇小说
2019-02-21张良红
张良红
(南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译林》杂志2015年第3期发表了美国新生代作家奥莉维娅·克莱尔(Olivia Clare,1982—)短篇小说《安静!安静!》的中文译作[1]。对中国读者来说,奥莉维娅·克莱尔的名字还相当陌生。克莱尔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进入南加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后又参加了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获艺术硕士学位。目前,克莱尔在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担任助理教授,讲授文学创作。克莱尔创作的诗歌和短篇小说散见于《南方评论》《肯庸评论在线》《耶鲁评论》《格兰塔在线》《过渡带》《伦敦杂志》《诗歌》等多家文学杂志和网络期刊,至今她已出版了诗集《26小时的白昼》(The 26-Hour Day,2015)和短篇小说集《第一世界的灾难》(Disasters in the First World,2017)。
克莱尔的文学创作始于诗歌,但真正令其声名鹊起的却是她的短篇小说。2014年,克莱尔摘得两项重要的文学奖项:罗娜·杰斐基金会作家奖(The Rona Jaffe Foundation Writer's Award)与欧·亨利小说奖(The O.Henry Prize Stories)。这在克莱尔的小说创作的道路上,是极其重要的里程碑。作为一位文学新人,克莱尔的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她以诗人对语言独有的感知力,敏锐地把握生活中的细节,用看似平静的方式,讲述了当代生活中不平静的主题:成长、女性问题、自由与梦想。本文聚焦克莱尔的《派特》(Pétur)[2]、《露莎卡的长腿》(Rusalka's Long Legs)[3]、《安静!安静!》(Quiet!Quiet!)[4]和《撒旦》(Satanás)[5]四篇短篇小说,分析其创作特色。
一、诗化的语言风格和舞台式对话
在小说创作中,克莱尔非常关注语言文字的运用和创新。语言文字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载体,历来受到作家们的重视。当代美国文论家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在《论文学》一书中指出:“文学的力量在于虚构性地使用最简单的词和句。……文学力量的最不一般之处就是语言文字描述的虚拟现实生成时带给读者的舒适感。”[6]克莱尔的短篇小说创作也不例外,作品的力量首先来自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审美追求。在2014年获得欧·亨利小说奖时,克莱尔谈论自己的小说创作:“我以诗人的身份开始小说创作。这左右了我对语言、节奏和句法的认识。语言的细微之处以及句与句之间的联系让我心生兴趣。我可能不会从A句顺其自然地写到B句、C句、D句等等,相反,我尝试直接从A句过渡到D句,再到L句,有时甚至直接写到‘兰花’句、‘孔雀’句、Ω句。”①Olivia Clare:The O.Henry Prize Stories Author Spotlight,https://www.randomhouse.com/anchor/ohenry/spotlight/clare.html。克莱尔用诗人的眼光打磨小说语言,通过跳跃性地处理语句联系剔除“冗余”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小说的阅读难度,但也因此使她的小说语言浓缩了大量信息,表现了很强的文学张力,犹如一幅幅水墨画,大量的留白赋予读者广阔的思考空间。
以小说《派特》的开头为例:“灰烬随风飘落。她开始外出长距离散步。她会在早餐之前以及午饭之后踏上杂草点缀的小路,走向湖边。白色灰烬已将湖面装扮成沙漠状,将山顶遁于无形。”[2]在信息量的处理上,这短短四句话体现了很大的跳跃性,句与句之间还可填充更多的句子,以保证叙述的自然过渡。灰烬、一位女性、长距离散步、沙漠般的湖面、消失的山巅,这更像是诗歌语言,描绘了一幅令人难忘的意象画,从而激起读者一连串的思考:灰烬从何而来?“她”什么样的女性?“她”为何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去湖边散步?小说以诗化的语言激发读者的阅读期待,读者需要不断通过自己的想象去填补克莱尔在小说语言中有意造就的信息阻断空间。
除了在句与句之间制造跳跃性信息外,克莱尔还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大量使用短句和客观陈述句,遣词造句少用评价性词汇,造就了一种接近于海明威小说的语言风格。《撒旦》讲述一群墨西哥人偷渡去美国的故事,小说开头这样描写这些偷渡客:“三个男人在她对面,肩挨着肩坐在一块木板上,背靠颤动的车厢铁皮。他们给女孩的弟弟取名‘我的’。我的,那是我的。男孩连续叨咕了几个小时。他横躺着睡在妈妈的双腿上。女孩坐在木板上睡着了,黑裙子被弟弟拽皱了,掀过了膝盖。他们坐在一辆没有窗户的卡车车厢里,离开村子去萨波潘,然后再去洛杉矶。一盏灯笼挂在钩子上。女孩心里想着,现在的时间是夜里,要么快到夜里了。”[5]虽然句式结构简单,叙述口吻客观,但小说揭示了一群藏匿于封闭车厢内的大人和小孩在沉闷、紧张的长途偷渡旅程中的状态:疲惫不堪中夹杂着百无聊赖与无限渴望。寥寥几笔,克莱尔就让读者体味到一种极简之下的丰富内涵。应该说,克莱尔自身的诗歌创作经验使她清楚地意识到短篇小说的语言应该如何反复锤炼与雕琢。
舞台式对话是克莱尔短篇小说另一语言特色。在这四部短篇小说中,小说人物之间的对话都占据了大部分篇幅,并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派特》呈现了一位失去丈夫多年的61岁女性与其36岁儿子在冰岛度假期间的母子对话;《露莎卡的长腿》中是一位从医院逃离的女病人与女儿之间的温馨母女对话;《安静!安静!》是三个小伙伴玩过家家游戏时天真童趣的对话;《撒旦》展现的则是一群偷渡客在封闭车厢内自娱解闷的对话。
在克莱尔的短篇小说中,起居室、客厅、湖边、河岸的草坪、小商店、小树林、花园、封闭的卡车车厢等都可以成为人物对话的舞台。在这些舞台上,没有哄闹的争吵,没有病态的、歇斯底里的内心独白,也没有陌生人之间的礼仪式客套,有的只是家人之间、邻里之间和伙伴之间的日常生活对话的再现。克莱尔用自然、真切的语言吸引读者,她甚至将短篇小说分节,每节均设有不同的场景,用对话推动情节发展,令读者感觉仿佛置身于剧院内观看一幕幕舞台演出,而舞台上对话的人物就是你和我,就是我们知晓的某个身边人。
二、捕捉日常生活的细节
克莱尔的短篇小说多属“小叙事”,然而这种“小叙事”却有着令读者反复研读的魅力。克莱尔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寥寥几笔就能定格生活中容易被人忽略的微妙之处,这也是理解克莱尔“小叙事”艺术的关键。有研究者指出:“日常生活只有通过文学形式才能够熠熠生辉。”[7]克莱尔通过短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将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放大,创造了非同凡响的文学艺术效果。
《露莎卡的长腿》中描述母亲黛儿在小商店为女儿尤拉买棒棒糖玩偶的场景:“黛儿只有十分钱。她买了一只三分钱的玩偶,那是昆特不得不踮起脚从货架上取下来的。玩偶样子很丑,光秃秃的眼睛上方是黑色的三角形图案,没有眼睫毛,手臂和腿用厚厚的辣味薄荷棒棒糖做成,外面裹了层点状图案的绉绸。”[3]在这段文字之前,克莱尔用了整整一个段落详细描写了货架上摆放着的孩子们喜欢的物品:抓子、色子、悠悠球、杂志、口香糖、字谜游戏等。黛儿想送件礼物给女儿,目光一度落在了四分钱一把的梳子上,但最终她为女儿买了廉价的棒棒糖玩偶。这是因为小尤拉罹患关节炎导致腿部萎缩,走路不便,母亲期望女儿能够长出长长的双腿。棒棒糖玩偶高高地搁在货架上,无人问津,但在黛儿眼中,那是胜过一切的贵重礼物。克莱尔通过描写小商店内的货架,抓住细节表现至深的母爱,诸如此类的细节描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细节不是一种无意义的点缀,在这个作品内容的最小组成单位、‘最小的面积’上,‘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它对于塑造人物形象,展示故事情节,流露作者情致,深化作品主题等方面,都有其举足轻重的作用”[8]。
克莱尔对细节的把握还表现在充分利用小说中曾经描写过的内容上,这有点类似契诃夫的风格。如《派特》中详细描写了劳拉和儿子亚当租住房子的起居室的内景:灰暗的旧地板、木制炉、咖啡桌、女性时尚杂志、昂贵的吉他、一盒采自湖底的黑色石头、条纹沙发、一个破旧的靠垫等,这些反映了房屋女主人的情趣。读者很容易忽略这样的室内描写,不会过多关注女性时尚杂志之类的物品,但这看似无意的描写却是克莱尔关注细节的最好表现。后来,劳拉站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取下墙上的水彩画,从咖啡桌上拿起她讨厌的时尚杂志并把它塞进抽屉,甚至这样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它们太恶心了,我本该早这样做”[2]。显然,克莱尔描写起居室的内景,不是随意为之,而是一个极为巧妙的叙述安排,它让读者可以通过前后对比,认识到劳拉这一女性人物形象不同于一般的女性,她的行为体现了独有的特质:个性反叛,心情极易受到环境的滋扰,有些神经质。《露莎卡的长腿》中,母女俩曾经遇到的那只沉睡的猫在小说接近结尾处再次被描写,这显然不是克莱尔的无意书写。由于短篇小说篇幅所限,克莱尔必须惜墨如金,猫的意象在文未再次出现实则传递给读者这样的信息:猫的状态就是对一些女性所处“沉睡”状态的隐喻。
三、对现实、梦想和女性群体的关注
作为一个文学新秀,克莱尔的小说创作才刚刚起步,现在定义她的小说风格显然为时尚早。不过,从克莱尔已经发表的作品来看,她的文学眼光紧跟时代生活,关注普通人以及周边环境中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一切,使读者觉得她写的就是自己的身边事、身边人。而身为一位女作家,克莱尔在短篇小说中关注的问题大都围绕女性展开。值得注意的是,克莱尔作品中的女性既不属于“天使”那一类,也不属于“魔鬼”那一类,而是当代社会中的“弱势女性群体”:孤独的老妪、女性精神病人和女幼童等。从这一点来看,为弱势女性创作可以算是克莱尔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派特》聚焦中老年妇女因孤独而产生的行为异化。小说将背景设在冰岛的一处山谷之中,亚当带着母亲劳拉来这里度假疗养,正值火山喷发,白色的火山灰掩盖了一切,让人难以呼吸。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劳拉天天外出散步。一次偶然的机会,亚当跟踪母亲来到一处无人居住的房子,发现了母亲怪异的举动。他突然明白,母亲之前口中所说的朋友“派特”其实根本不存在。小说在描写母亲劳拉蹲在床上的怪异行为中戛然而止,留给读者的不仅仅是震撼,更是无可名状的惊骇。
《露莎卡的长腿》聚焦另一类女性:女性精神病人。小说讲述了小尤拉与母亲黛儿一次难得的母女相处时光。黛儿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住在医院的病房里,尤拉被父亲送来探访母亲,黛儿趁护士们不注意,带上尤拉翻过医院花园的篱笆,开始了兴奋的徒步之旅。旅途中黛儿给女儿买了最好的礼物——一个名叫露莎卡的棒棒糖玩偶。到了晚上,在一所无人居住的房子内,尤拉枕着母亲的头发,吮吸着薄荷棒棒糖进入梦中。当她突然惊醒时,发现自己躺在父亲的怀里,母亲早被送回了医院。故事由一位无名的叙述者讲述,他的高曾祖母正是尤拉。尤拉早在1990年去世,去世前身患癌症,债台高筑,每周在赌场玩两次牌。叙述者期待高曾祖母的遗体会缩成孩子般大小的木乃伊,继而等待一次新的生命。显然,这样的等待寓意颇深,母亲黛儿是觉醒的,她想永远逃离象征男权的医院病房,但在女儿沉睡过程中又被送回了医院。小说临近结尾的那句“有时你很长时间都不会醒过来”[3],其实是在警告所有沉睡不醒的女性:只有觉醒过来,女性才有可能长出一双“长腿”。
《安静!安静!》讲述了“我”在2014年回忆童年时与两位小伙伴们嬉戏的场景,叙事时间在“现在”与“过去”之间来回跳动,小说构思精巧,立意深刻,字里行间充溢着“我”对一位失踪20年之久的童年小伙伴的无尽思念。“我”列数了童年小伙伴20年来错过的事件:“克隆羊、新行星、地震、飓风、海啸、青春期与性行为、9 · 11事件、电子邮件、失业、移动电话”[4]。小说看似在回忆“我”失去的童年小伙伴,寄托自己的哀思,实质在思考自己一直以来的成长。面对瞬息万变的后现代生活,“我”甚至怀疑起“现实”,感觉自己拥有的一切就是“两万四千件毫无用处的东西”[4],小说暗喻了后现代社会中人的典型成长状态。
《撒旦》讲述三位男性、一位女性和她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从墨西哥偷渡入境美国的旅程。他们当中年龄最长的是一位拄着拐杖的男性,在沉闷的车厢内,他不想睡去,想方设法排解偷渡旅途的苦闷。那位女性和两个孩子醒一程、睡一程,另外两个男性则一路沉睡。每当卡车猛地停下,他们就保持异常的警觉,吹灭车厢内的灯笼,母亲甚至会捂住小男孩的嘴巴。最终,当卡车进入美国境内时,司机让所有人下车观看路边的奇观:陨石坑。小说讲述了偷渡者的梦想,但又有些超现实主义的情节。在小女孩的想象里,卡车由几匹马拉着行进在颠簸的路上,一匹马身上带有白色的斑点,只要一停下来就喜欢吃苹果。小女孩甚至想象自己进入无名之境,在那里马儿吃着灌木丛里的玫瑰,而玫瑰的花心里爬行着一长串的蚂蚁。每当卡车停下来,一些奇怪的想法就涌入小女孩的心头:她想象自己在一艘沉入海底的轮船上,但她能够呼吸;想象自己名字里的字母变成奇形怪状的动物,如有六条胳膊的河马和长着乌龟头的海豚。小女孩的怪异想法代表了偷渡客们希望摆脱现实处境的梦想,在他们心中,只要能够偷渡成功,他们就进入了人间天堂,可以自由地将幻想变成现实。
四、结语
奥莉维娅·克莱尔的文学创作道路虽然才刚刚开始,但无论是语言层面,还是主题层面,抑或是叙事技巧层面,其短篇小说的成功创作已经让读者领略了克莱尔非同凡响的写作风格。简约与跳跃性的语言处理,用对话推动情节发展,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描绘,以及对女性问题、现实与梦想等文学主题的深层揭示,构成了克莱尔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