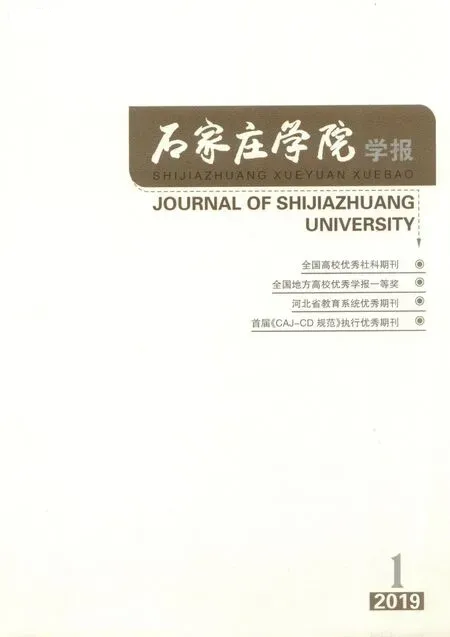历史时期河北雄安地区佛教的嬗变及其特点
2019-02-21冯金忠
冯金忠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学刊》杂志社,河北 石家庄 050051)
雄安地区的宗教在历史上一度主要以佛、道和民间宗教为主,后随着伊斯兰教、天主教等的传入,至20世纪初宗教格局大变,佛、道的主体地位逐渐丧失,佛寺道观或废毁或改作他用,信徒寥寥。据民国《雄县乡土志》载,雄县回教徒约1 000余人,天主教徒约2 000人,佛教徒僧尼约100余人,道教徒10余人。[1]99这虽是雄县一县的数字,其实也是当时雄安地区宗教状况的一个缩影。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在东汉中后期已传入河北,最早的中心在河北南部。由于临近都城洛阳,在洛阳佛教的辐射之下开始发展起来。但河北佛教的大发展却是在十六国的后赵时期。从传播路径来看,大致经过了从南到北,从西徂东的过程。①河北学界有的学者,如张志军先生认为南宫普彤寺塔成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57年),比著名的洛阳白马寺齐云塔还早两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佛塔,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普彤塔寺比向来被视为中国佛寺之祖的洛阳白马寺还要早一年的结论。参见氏著《河北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坚持认为河北最早的中心不应在南宫所在的河北中部,而应在毗邻当时国都洛阳的河北南部。参见冯金忠《燕赵佛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雄安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开发较晚,从现有史料来看,后魏时期才开始出现佛寺。例如,安新县北的天宁寺和安新县边吴村的古塔寺,均始建于后魏。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名寺林立,大德辈出,形成了以禅宗等为代表的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一时期雄安地区的佛寺也发展迅速。昊天寺,隋建,在安新县曾家村。雄安地区佛教在地域分布上的一大变化便是雄县佛教的崛起,并逐渐取代了安新佛教的地位。佛寺主要集中在雄县,容城、安新几无一所。如雄县的崇兴寺,在雄县留镇村,唐元和元年建,县志云该寺“气象雄伟,为本境最古之寺”[1]120。除此之外,还有镇海寺、观音寺(在瓦济街)、观音寺(在齐观村)、增福寺、定慧寺等。从修建时间来看,既有唐初,也有唐后期。
值得注意的是,增福寺,位于雄县李村,方志云为唐尉迟公所修。尉迟公,实即“尉迟恭”,为唐初名将、开国元勋,字敬德,后遂以字行。尉迟敬德在中国民间以门神形象为人所熟知。实际上,方志和民间传说中托名于尉迟敬德是中国各地特别是华北地区佛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实际上多不可信,它本为唐代匠人尉迟恭韬之讹传,由于尉迟恭和尉迟恭韬形近而讹,遂被误植到尉迟敬德身上。于是,尉迟敬德从一个赳赳武夫变成了一个修寺善士,其形象的再造是与元明清时期民间对尉迟敬德的造神运动相一致的。也就是说,借助尉迟敬德的影响力以提高佛寺的知名度。[2]
唐武宗和五代周世宗都进行了灭佛,这是中国历史上两次著名的所谓“法难”,当然雄安地区的佛教也不能幸免,故唐末五代时期佛教在方志中几乎是一片空白。北宋建立后,又推行扶植佛教的政策①在北宋诸帝中,宋徽宗崇尚道教,他在位时对佛教发展有所限制,政和八年(1118年),颁布诏令将六千卷佛经中含有诋毁儒、道内容的进行清理。。太祖时,知雄州的安守忠一次就施给广慈禅院土地5 770亩。但这一时期辽宋对峙,在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以白沟为界,雄安地区成为边地和战争前沿。如雄县县境一分为二,南为宋之归信,北为辽之归义(一作归易),侨置新城。虽然议和之后,宋辽双方维持了长期的和平,鲜有大的战事,但双方在边境屯集重兵,彼此防范戒备。由于这一地区地势平坦,几乎无险可守,北宋缘边安抚司与屯田司皆雍塘水,种植水稻,以限戎马。辽方常常以僧人充当间谍,刺探宋方情报,故宋王朝对边境地区的佛寺修建和度僧活动,多有限制。例如,据李焘记载:“诏代州五台山诸寺收童行者,非有人保任,毋得系籍。时雄州言契丹遣蔚、应、武、朔等州人来五台山出家,以探刺边事,故条约之。”[3]卷一七七还比如,李允则守雄州时,曾出官库钱千缗,复敛民间钱起浮图(即佛塔),“是时飞谤至京师,至于监司,亦屡有奏削。真宗悉封付允则,然执政者,尚暄沸”,宋真宗不得已遣中人,密谕李允则中止佛塔之建。李允则谓使者曰:“某非留心释氏,实为边地,起望楼耳。”[4]卷二李允则修建佛塔之举引起朝臣一片反对之声,其原因并非在于靡费钱财,而主要是朝中大臣包括宰相等担心在边境建造佛塔,大兴土木,会使辽方误以为在缮修城池、整军备战,以引起边衅。李允则此举也非出于宗教信仰,正如朝臣所忧虑的,主要是为了边备的需要,打着建塔的幌子,实作瞭望敌情之用。其实李允则修建佛塔的例子在宋代并非个案,最著名的当属定州开元寺塔,实际上也是为了瞭望敌情,故又称作“料敌塔”。李允则所修佛塔,在雄县境内,史佚其名。今容城有一座佛塔,名曰白塔,耸峙入云,高七丈,周六丈五尺,“白塔鸦鸣”是明清时期容城八景之一。此塔亦宋时建,盖亦出于军事目的。[5]374概言之,宋代雄安地区佛教由于特殊的政治军事原因,在朝廷严密控制下,发展趋缓,但这一时期的佛教,特别是佛塔具有浓郁的军事色彩,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
金灭北宋后,混一河北,形成了与南宋南北对峙的局面。不过这时期的宋金分界线不再是白沟,而是大散关—淮河一线。金又改幽州为中都,作为正式都城,雄安地区由边地和战争前沿,一跃为畿辅之地,成为了政治核心区,这是雄安地区政治地位的一大变化。随着政治地位的抬升,军事色彩的消褪,佛教又重新得以恢复发展。如静聪寺,金明昌年间建,在安新县城内北街,本金章宗元妃香火院。但雄安地区佛教进入高潮还是在元代之后。
元代雄安地区佛教仍主要集中在雄县。据嘉靖《雄乘》、光绪《畿辅通志》、《河北通志稿》、民国《雄县新志》、民国《雄县乡土志》、民国《容城县志》、《河北省志·宗教志》等材料记载,安新县11所佛寺中,建于元代的只有1所。②即净业寺,在安新县西,元大德七年(1303年)建。而雄县佛寺29所,其中明确记载建于元代的则有9所,占总数的31%。即普觉寺(至正年间)、大觉寺(至正五年)、普照寺(至正五年)、百尺寺(元至正十年)、清凉寺(至正六年)、百福寺(至正年间)、云岩寺(至正五年)、观音寺(在孙村,至正五年)、观音寺(在东羊,或作东杨村,至正十年)。从时间上全部集中于元末的元顺帝至正年间。即使建于前代的寺院,在元代也进行了重修改建。例如,定惠(慧)寺,始建于唐,在雄县东赵村,宋元迄明皆有重修。
有明一代,从京师到各地,是中国佛寺的井喷式发展时期,“营建寺观,岁无宁日”,“僧尼道士,充满道路”[6]。方志所记载的各地佛寺中,始建于明代或明代重修者占了大多数。雄安地区方志所载的40所佛寺中③当然,方志所记亦非全部,例如对雄县而言,据民国《雄县志》东羊(杨)、大谢王、槐中营、文家营、河西营皆有佛寺。大步村有明国寺、海潮庵,河岗有清凉寺,洪城有兴隆寺、地藏寺,南沙窝村东有金沙寺,平王村有兴国寺。这些寺院由于无碑记可考,附记于此。,明确言建于明代者有17所,占总数的42.5%,如果加上明代重修的则达27所,占总数的67.5%。这一时期,相比唐宋元时期主要集中于雄县相比,地域范围更为扩大,安新县境佛教有较大的恢复,新建者4所,重修前代旧寺2所④这4所是保安寺(明嘉靖年间建,在安新县北六里村)、镇龙寺(明建,在安新县东)、朝阳寺(明万历年间建,在安新县城内,旧置僧正司于此)、大悟寺(明万历年间建,在安新县老河头村)。两所重修旧寺者为天宁寺(后魏始建,在安新县北,明宣德重修)、静聪寺(金明昌年间建,在安新县城内北街,明宣德重修)。,合计6所。虽然与雄县佛寺数量仍有差距,但差距已大为缩小,显示出县域间大致均衡发展的态势。这也是明代雄安地方佛教大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
明代雄安地区佛寺,从修建主体来看,多为民间集资修建,少部分为官员出资。如圆通阁,在雄县圆通街,乃由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云川指挥王俊建。在官员建寺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宦官修寺。例如,观音寺,在雄县东西里(或作东李),明成化元年(1465年)建,崇祯十四年(1641年)太监谢文□重修。地藏寺,位于雄县西楼东赵村,明天顺元年(1457年)建,明太监王姓、李姓等所建。[1]114天宁寺,在雄县圆通街,明永乐间创建,太监李钦等施经一藏于天宁寺,见万历二十年(1592年)重修天宁寺碑。[7]243华公庵,俗呼为来僧庙,崇祯间县人内监华显金于观音庵门前,开井筑舍,为施茶之处。以上4个寺院为宦官修建或与宦官密切相关。
隋唐以后,宦官的来源变为由民间供奉为主,穷苦人家子弟在宦者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在深受佛教影响的民间社会,宦官自小浸润其中,进入宫廷后,自幼培植的信仰也不会因生活环境的改变而骤然放弃。况且封闭的、充斥着勾心斗角甚至刀光剑影的宫廷生活环境也会进一步强化佛教信仰。虽然历代以来,宦官建寺者并不鲜见,但明代宦官建寺则是最为突出者,其中不乏巨珰大阉。如明英宗宠幸宦官王振,王振所建智化寺,穷极土木,建大兴隆寺时,“日役万人,糜帑数十万,闳丽冠京都”,明英宗赐号“第一丛林”[8]卷一六四。明代许多宦官于生前建寺以作功德,年老后所建寺院便成为他们的退养之所,死后也往往葬于寺旁,或者于葬所起寺。寺院的僧人兼管守护坟墓。这主要集中在京郊。光绪《顺天府志》云:“京城之外,而环城之四野,往往有佛寺,宏阔壮丽,奇伟不可胜计。询之,皆阉人之葬地也。阉人既卜葬于此,乃更创立大寺于其旁,使浮屠者居之,以为其守冢之人。”[9]548
明代迁都北京后,宦官多来源于京畿附近地区,雄安地区密迩京师,自然也是宦官的重要来源地。以上4所与宦官相关的寺院,在性质上显然与建于京师或京郊者有所不同,它们具有为家乡作贡献的纪念性质,当然也包含着为自己作功德以及光耀门楣的目的。在这点上与王振在家乡蔚县所建灵岩寺有些类似。
明代对佛教寺院控制大为加强,不许随便置寺,曾对佛寺大加裁并。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七月,敕令“凡僧人不许与民间杂处,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听令归并成寺。其原非寺额,创立庵、堂、寺院名色,并行革去”[10]。明成祖即位后,重申禁止私创寺院,并对“旧额”重新加以厘定:“凡历代以来,若汉、晋、唐、宋、金、元,及本朝洪武十五年以前寺、观有名额者,不必归并。其新创者,悉归并如旧。”[11]卷一四《大明会典》卷一六三《律例四》严申:“凡寺观庵院除见在处所外,不许私自创建增置,违者杖一百,还俗。僧道发边远充军,尼僧女冠入宫为奴。”[12]卷一六三
虽然明廷对佛寺僧人人数和新建寺院多有限制,乃至加以厘革,但从实际来看,效果并不显著。例如对雄安地区而言,所谓“新创者”,如上所言即有21所(雄县17所,安新4所),前朝旧寺不过12所。朝廷诏令难以得到切实贯彻,除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张力外,此一时期佛寺主要分布于乡野村坊间的特点,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从中国佛教寺院的分布来看,一般来说,京城辇毂之下最为稠密,名寺大刹更是多集中于此。在地方上则主要集中于州县治所和各交通要道。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包括宗教中心)合一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普遍现象,这在唐中期以前尤为明显。同时,佛教寺院往往选址于山川秀美之处,大凡名山,都遍布梵宇琳宫。峨眉山在唐代曾建有上百座佛寺;九华山鼎盛时,寺院也有近百座;嵩山、泰山更是如此,难怪世人要感叹“天下名山僧占多”。而有明一代,佛寺多出现在乡村中,显示出佛教进一步向底层民间延伸的趋势。根据上述方志材料,雄安地区佛寺26所(包括明代始建和重修),其中建于县城内的只有9所,而在乡村者则有17所。有的村庄乃至有数座寺院。
众所周知,明代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三教融合,对于佛教内部而言则是禅教合流,显密融通。学界长期认为明清佛教属于衰落期,对明清以来的佛教多有忽视,确实此时期佛教在理论上罕有大的建树,失去了隋唐时期那股磅礴冲天的气势,但此时期佛教同儒学、道教乃至民间宗教相融合,以一种更为百姓喜闻乐见的面貌出现,几乎渗透到民间社会的每个角落,与中国民间社会血肉相连,完全融入了百姓日常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明代佛教并未衰落,从社会影响力来讲,比起前代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后,中国化的进程随之开启,至唐代形成了完全中国化的诸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在佛教中国化的同时,对中国各地区、各民族而言,还存在着本土化的问题,即与各地区、各民族乡风民俗的当地社会的融合,可以说,本土化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佛教本土化在中国各地、各民族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在雄县县城西后街,南首有观音堂,北向,堂西有芥子庵,庵南有五道庙,北有新建药王行宫,佛、道、民间信仰诸祠庙共处一院,“是可谓丛祠者矣”[1]107。还比如,东照村,村多古庙,西为定慧寺,有鹦哥殿。鹦哥,即鹦鹉。在佛寺中竟然有以鹦鹉名称命名的殿堂,显示出佛教不再是那么虚无缥缈,而是充满着世俗的生活气息。
当然,雄安地区的佛教缺乏名寺名僧①《景德传灯录》卷二三记载有雄州华严正慧大师,为抚州曹山慧霞禅师法嗣,还有雄州兴云石琳瑀禅师。此雄州,又称南雄州,今广东韶关南雄市,非河北之雄州。,但作为一个地方小寺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们构成了中国佛寺的绝大多数,更具有普遍性,从它们身上或许能更深入了解佛教在中国民间社会传播流行的实态,换言之,雄安地区佛寺是中国佛教民间化、世俗化的一个绝佳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