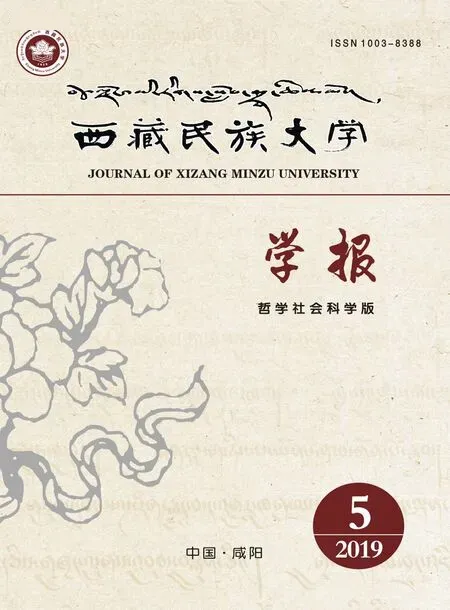论仓央嘉措诗歌汉译文本的时代演变及艺术取向的变化
2019-02-21栗军
栗军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藏族诗人仓央嘉措以及仓央嘉措诗歌一直是学术界颇有争论的研究热点。仓央嘉措诗歌从主题意蕴解读,有人认为是情歌,有人认为是道歌,也有人认为是政治抒情诗等等;从艺术层面欣赏有人在肯定其质朴、纯真一面的同时,因其借用藏族“谐体”民歌形式,其诗也缺少一定的内涵和意境,艺术水平不高。仓央嘉措诗歌汉译文本,因翻译和流传时间距当下较近,没有太多的异文或变文,但近年出现的网络文本和冠之于仓央嘉措名下的歌曲歌词,却很受读者和听众的喜爱而不断传播。
仓央嘉措诗歌汉译文本的流传,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于道泉翻译文本开始,至今已有各类译本二十余种。在近九十年的时间当中,其诗从最初被人发现、认识、翻译、到现在的广为传播和流传,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趋势。梳理仓央嘉措汉译文本,能够看到其诗从最初呈现民歌形式,今日却总是与六世达赖喇嘛传奇身份关联起来,这种微妙的演变发展也反映了各个时代不同艺术取向和变化,看出社会政治和娱乐大众因素对于民间流传的翻译文学作品的影响。近九十年的仓央嘉措诗歌汉译历史,大体可以呈现出四个相对集中的时段:一是20世纪30年代;二是20世纪50年代;三是20世纪80-90年代;四是21世纪初至今。本文将从这四个时期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
最早的仓央嘉措诗歌汉文翻译文本是于道泉先生1930年出版的单行本,定名为《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在北平出版[1](P231);之后又有刘家驹译的《西藏情歌》①,由上海新亚西亚月刊社1932年7月出版[1](P257);接下来有刘希武译《仓央嘉措情歌》,原刊于《康导月刊》1939年1卷6期[1](P285),以及曾缄译《六世达赖情歌六十六首》,原刊于《康导月刊》1939年1卷8期[1](P273)。
这些译作者的翻译方式和风格各有千秋,于道泉先生编译的仓央嘉措诗歌,严谨精确,基本保持了原诗的风姿。[2]在他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一书中,不仅有汉译文,还有藏文原文和国际音标注音和英译文,书之前后,还有序言和附录,介绍仓央嘉措其人其事以及藏文诗歌特点。此外还有46个附注,对不易理解的原文解释,据作者称其中很多都是经藏族朋友的讲解得来的。[1](P7)比如于道泉翻译的第一首:“从东边的山尖上,/白色的月儿出来了。/‘未生娘’底脸儿,/在心中已渐渐地显现。”[1](P209)于道泉对“未生娘”中还做了藏文注解,即ma-skyes-a-ma,同时指出为“少女”之意。所以译成“未生娘”,即指还没有出嫁,没有生过孩子的姑娘,本意是指非常纯洁,但没法用汉语同样语义的词替代,译者就生硬地把缺少艺术感的文本呈现出来了。从这里看出于道泉首先是个研究者,他特别尊重原文。学术界对于道泉译本逐字逐句的直译的方式比较认可,认为他基本忠实原文,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作的风貌。但是,有人对于道泉先生最早把仓央嘉措的诗译成“情歌”表示不满,认为仓央嘉措诗歌应译为“道歌”。[3]其实,于道泉最先看到的就是藏文民间流传的文本有关诗歌本意即为“情歌”,而且在汉文本翻译后的流传过程中,大多数人认为其更具备情歌特性,而逐渐认可了仓央嘉措情歌这一称谓。
刘家驹基本沿袭了于道泉的路子,其翻译相对通俗顺畅一些。他在30年代译为《西藏情歌》,没有拘泥原文采用硬译的方式,而在诗作中做了变通,例如第三十首:“东山上,/现出皎洁的月光;/这时慈母容颜,/不禁地萦绕着侬的心肠。”[1](P239)刘家驹就把“玛杰阿玛”译成是“慈母”,也未作过多说明。而他译的100首诗作颇具民歌风格,也有一些口语入诗,含蓄优美,语言通俗浅显,长短句结合,抑扬顿挫,活泼生动。比如第十首“亲爱的人儿,/能否同我长相聚?/她说‘除非死别,/决不生离。’”[1](P234)
而曾缄的七言译本和刘希武的五言译本,由于采取了中国古体诗词的形式,甚至用汉文典故,在内容和意境上与原文就有很大的出入。曾缄译为“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1](P258)不仅原文的前后顺序被打乱,同时呈现的是一首古诗的情绪和韵味。刘希武的五言相对简洁明快,“明月何玲珑,初出东山上,/少女面庞儿,油然萦怀想。”[1](P274)仍是古代诗词的韵味。更值得一提的是,据称曾缄不懂藏文,依据的是于道泉的本子,同时听懂藏文的人讲解给他,而后进行重新创作润色而成的。
从这个时期流传的汉译文本来看,数量不多,诗作均呈现出民歌的质朴无华,且极富感情的特点。不同的是,于道泉特别讲究语言本意;刘家驹则以民歌示人;曾缄和刘希武是把仓央嘉措诗歌作为一种个人艺术品位的文学作品,重新加工润色创作,更多是看重仓央嘉措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歌成分,抒发共通的情感,挥洒其艺术境界,依据底本重新进行自我创造,尤其是曾缄和刘希武采七言和五言古体诗的形式,是本时代人们在自由体诗歌还未完全成熟状态下的一种自觉选择,古体诗呈现的某些韵味和意境与仓央嘉措诗歌的多意蕴性在某些方面不谋而合。
二
新中国成立后,藏族民歌的搜集整理成果比较突出,在阶级论的思想主导下,仓央嘉措特殊的达赖身份,在那个时代也被认为是统治阶级阶层,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仓央嘉措命名的出版物根本没有,但其诗歌仍然在民间流传。如火如荼的“新民歌”运动让仓央嘉措诗歌有意无意地被搜集和整理出来。各种仓央嘉措诗歌数量较多,其中就有:苏朗甲措和周良沛1956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藏族情歌》译有仓央嘉措诗歌32首;有《人民文学》1956年10月号刊载《仓央嘉措情歌选》33首;1956年王沂暖先生编辑的《西藏短诗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其中翻译了仓央嘉措诗歌57首;1959年出版的《西藏歌谣》的第十二辑中,有傅师仲、王沂暖、何良俊和九光等人选译的部分仓央嘉措诗歌;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苏岚编的《藏族民歌》搜集有29首。零星地散布于西藏民歌中,出现在各类杂志、报纸中没有以仓央嘉措诗歌命名的民歌更是无法完全统计。这其中还包括一些随部队进藏的艺术工作者,有些人搜集整理后,一直到近年来才拿出来发表出版的作品,如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周艳炀收集整理的西藏民歌《云中的经幡》,因大都是谐体民歌,有多首情歌与仓央嘉措诗歌类似[4]。
这期间所搜集的诗歌,相对看重其民间的艺术价值,诗作清新自然,能表现藏族人民率真,炽热的情感,语言朴素无华,明白晓畅,且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如苏朗甲措和周良沛所译的三十二首:“在东山的高峰,/云烟缭绕在山上,/是不是仁增旺姆啊,/又为我烧起神香!”[1](P309)东山的高峰是诗作的起兴,情人为其烧起神香,既能表现感情的热烈,也有浓郁的藏民族的特点。在1956年的《人民文学》中,也有编者对仓央嘉措的诗歌有一段评价:“情歌感情炽烈而真挚,语言通俗,描写动人,诗风清新自然。”[1](P320)
尽管肯定了诗作的艺术价值,本时期的译者在选取上却有一定的倾向性,1956年10月的《人民文学》在选取了33首情歌之前有一段引言,肯定了诗作在藏族诗歌史上的地位,但同时指出了仓央嘉措在诗歌中呈现的封建道德和宿命论思想的不健康性。所以,这里在选取诗歌时也是具有一定的倾向性。所选33首诗作基本表现出诗人对爱情的真挚感情。尤其前三首诗作即人们说的“闲言杂语”“看门的老黄狗”及“大雪留下脚印”,其诗的情节本身就是从仓央嘉措本人角度来写,而且也能表现诗人率真之情和对人们闲言碎语的无所畏惧的态度,因为这几首最能表现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不愿做傀儡,对当时的西藏统治阶层的一种反叛,是一种最强烈的反叛的声音,把这三首放在33首中首位,这或许正是选译者所看重的。而这个时期的译者大都比较看重宗教对感情束缚的之类的诗作,选取了如《没想到心上的容颜》《想她想的放不下》等等,都是用宗教和感情进行强烈比照的作品,表现出宗教对纯真情感的束缚。
从本时期的译作来看,大多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因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身份属于统治阶级,有人不愿将仓央嘉措诗歌直接以藏族诗人命名的方式呈现出来,甚至在选取上也有取舍,多选择一些不满宗教礼教对爱情束缚的作品,而直接表现失恋或者宗教意味的诗都没有选取。但很多译者还是能够发现诗作的艺术性,称它们贴近民间,它们率真,热情,直白,也有着质朴无华的语言。但由于时代的局限,选取的作品很多都不直接冠之以仓央嘉措之名,而把其隐藏在浩瀚的藏族民歌中,同时,带着强烈的主观意识去评判,在看重其艺术价值的同时首先用阶级方法来框定,以正反辩证的方式分析,从其身份背景中,更强调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能够发声公开反叛自己的阶层,代表人民渴望自由,渴求真正爱情的一面,他的真挚情感代表的是藏族人民的愿望,是人民对真情的渴望。
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仓央嘉措诗歌发掘与研究的又一个高峰,不仅有公开发表出版的诗歌译本,也有大量的研究作品出现。主要的译作有毛继祖在1979年2期《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的《试谈仓央嘉措情歌》,用整齐的六言诗的形式翻译了52首仓央嘉措诗歌;1980年《西藏文艺》1、2期选载了《仓央嘉措情诗译集》(40首);198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沂暖翻译的《仓央嘉措情歌》(74首);1980年庄晶翻译编著的《仓央嘉措及秘传》选译124首仓央嘉措情歌;1995年出版的《中国歌谣集成·西藏卷》选取仓央嘉措情歌50首。此外,散布于地方性藏族民间歌谣集成、藏族民歌、藏族情歌、少数民族情歌集当中以及评论性的文章中的仓央嘉措诗歌更是无法具体统计。这时期,仓央嘉措诗歌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突出,颇能显示本时期的艺术取向。
这时期的研究者大多从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去分析仓央嘉措的诗。在思想内容上,肯定其人民性的一面,多认为仓央嘉措是一位宗教叛逆者,在诗歌中表达追求自由生活的心声,诗歌反映了诗人宗教和爱情之间的矛盾,渴望打破宗教戒律的束缚,表达宗教生活对爱情的摧残和破坏。同时,也指出仓央嘉措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诗歌中也有着玩弄女性,不负责任等等思想糟粕。而在艺术表现上,则分析得较为深入透彻,从谐体民歌形式、民歌的比兴手法运用、塑造人物形象、抒情艺术、富于浪漫主义气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2]
随着研究的深入,这时期出现了不同声音,虽不能形成潮流和趋势,但颇为引人注目,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萧蒂岩的观点,他认为仓央嘉措的诗为政治抒情诗,他主要从仓央嘉措的生平和历史上的达赖喇嘛所作诗歌进行比照出发进行分析,他也承认过去人们分析其诗歌有人民性的特点,但是藏语“古鲁”究竟是否为情歌值得商榷,也有人称其为“宗教诗”,作者从诗人的生平判断诗人做这些诗的原因是“歌诗百首,心事一桩”,说其诗都是“意在言外”的表达自己政治理想和矛盾的诗歌。[5]之后也有理明认同萧蒂岩的观点,并且更为客观地希望能有仓央嘉措诗歌的精校本,供大家研究。[6]
由此可见,本时期对于仓央嘉措及其诗歌是有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但是大多数人仍旧沿袭了20世纪50年代从阶级论的角度分析其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性,甚至从仓央嘉措生平入手分析,认为他不可能写情诗,只是借“谐体”民歌表达“道歌”意蕴,甚至是写“政治抒情诗”。在认识其艺术性方面所体现的民歌质朴通俗的特色有很多共识。而有人不认同其诗为情歌,发现诗歌具有宗教道歌的特点,认为其是政治抒情诗,这些则显示出本时期诗歌流传中的多意蕴性的端倪。
四
进入21世纪,文艺环境的宽松,仓央嘉措的诗歌出版和研究又出现与以往不同的现象。一是出版物品类繁多,数量巨大;二是认识研究各有不同。
这时期出版的仓央嘉措诗歌,第一类是过去曾出版过的修订版,如庄晶1980初版、2010年再版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诗》,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诗作数量未变,只是有少量修改。再如2008年龙仁青编《仓央嘉措情歌》,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年再版的24开本《凡情与佛心——六世达赖情诗选》等等,这类出版物大多是沿用20世纪50或80年代老一辈译者的风格,取淳朴、自然的民歌情歌风格,对诗作也未作太多分析解释,但这类中也有把曾缄和刘希武等人的古体诗作品拿来重新编排重印的。
第二类是把仓央嘉措诗歌看成是以道歌为中心来翻译的。这里主要有龙冬译《仓央嘉措圣歌集》,羊本加编译的《心儿随之而去——仓央嘉措诗歌新译》,耷·琼培翻译《仓央嘉措之喜·六世仓央嘉措道歌集》。龙冬译诗“把仓央嘉措看成是一个特定历史环境中的青年的达赖喇嘛,从仓央嘉措的生活环境和政治际遇来理解他诗歌的含义,从而对他的诗歌作出新的翻译和新的解释。”[3](P2)而羊本加编译的诗作虽没有明确每首诗都有明确的宗教意味,但在“译后记”中说“阅读仓央嘉措上师的道歌,按唯物主义的观念,可以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去欣赏。”[7](P170)羊本加编译的这首“东方山峦顶上,/升起白净月亮;/未生母之尊荣,/频频浮现心头。”[7](P7)羊本加是按佛教意蕴来翻译的“玛吉阿玛”一词,于是用极为恭敬的“尊容”修饰。而龙冬译的这首诗直接在“玛吉阿妈”下注释“译者认为,最简便的理解,是密宗本初佛或如来的明妃,即佛母,象征着佛、菩萨两轮化身明王的修法女身,比如度母、金刚母、白衣等”。[3](P3)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佛教领域中活佛也加入译者中,耷·琼培仁波且也翻译了123首仓央嘉措诗歌,文本名字叫《仓央嘉措之喜·六世仓央嘉措道歌集》,②此文本虽没明确说明其道歌原因,但在展示其诗歌时,大多数也是采取四行体,个别是五行到六行,每首诗都配有作者的图画,极有艺术感。
第三类则以马辉、苗新宇的《仓央嘉措诗传》为代表,他们所选择翻译的70首仓央嘉措诗作在形式上是标新之举,不仅打破了原诗的顺序,用了自由体现代诗的写法,10到20行不等,有些分小节,有些则不分,诗作的内容也是翻译者自己所领会的,在修辞和表现技法上,运用现代审美技巧。同样如《从那东山顶上》:“心上的草/渐渐地枯了/心上的杂事、杂物……次第消失/我也随之空下心来/这时,玛吉阿玛的脸/浮现在我的心头/而月亮正在攀过东山/不留任何因果/……/此刻,除了这无边的宁静/还有什么值得我拥有呢”[8](P47),原诗没有标题,被编入“火空”辑中,属于其中的第4首。此类诗作带有更多的个人创作成分。译者在其《仓央嘉措诗传》前言中也坦然承认仓央嘉措的诗歌“平易近人,十分朴素,有点类似于民歌”,而他们更关注于“所谓高贵的艺术还给了自由创作的民间”。[8](P9)因此,其借用仓央嘉措创作的成分更浓。
第四类,本时期出现了很多有关仓央嘉措传记类作品,也涉及一些汉文本的仓央嘉措诗歌。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龙仁青、梅朵译著的《仓央嘉措诗歌地理》,[9]用仓央嘉措一生所走过的路完成了他的传记,同时附录收集了124首仓央嘉措诗歌的最新译本。这类传记作品很多把仓央嘉措的诗与纳兰性德的词,编排在一起赏析,有些作品甚至是直接将网络或歌曲中的作品拿来当成仓央嘉措的诗歌,此类作品数量巨大,公开的出版物目前就不下40种,且形成了有关仓央嘉措的出版高潮,但是,出版物的质量也是良莠不齐,有很多问题,诸如很多出版物翻译者有语法上的差错,知识性和逻辑性的差错,甚至CIP数据类号差错等等,很多作品都是出版社盲目跟风出版的产品。[10]
本时期对仓央嘉措诗歌的研究也是比较突出的。由于以往把仓央嘉措诗歌都当成情歌来研究,甚至命名问题也有人探讨,本时期从各个方面论证仓央嘉措的诗歌的道歌特性。这里比较突出鲜明的观点有王艳茹的《关于仓央嘉措诗作“道”歌与“情”歌之辩》[11]、硕士学位论文才仁嘉《论仓央嘉措的道歌》[12]。在本时期仓央嘉措的诗歌研究可谓是有开拓性的进展。有学者称在“该领域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表现在把计算机统计,实验语言学,语料库研究,比较文学,传播学等引入其研究且取得了重要成果。③”[13]
从出版和研究两方面看,本时期对于仓央嘉措诗歌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深入,认识兴趣更浓,艺术取向上更多元化。就出版的仓央嘉措诗歌来看,一方面,深入研究的趋向较明显,有人把它看成宗教意味的道歌,有人则是在艺术规律中探索,包括将其和词人纳兰性德比照,更突出其真实、赤诚之心,为爱执着的一面;另一方面,大众娱乐化的倾向也较为突出,本时期汉译文本的出版物数量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除了少数以学术为依据的文本外,大多数都是以娱乐消遣,赏心悦目,慰藉心灵为目的,很多人仅仅依据仓央嘉措神秘的生平,以及网络媒体中误传的情歌,就从少量的资料中想象和杜撰出仓央嘉措的这个人物形象,把所有可以添加到其身上的诗歌都重新创作,使之成为这个时代的情圣形象之一,因此,也有人称其诗歌在传播过程中有流俗化的倾向。[14]
从历史脉络梳理藏族诗人仓央嘉措的诗歌,各时代不同的艺术取向变化更为清楚明朗。20世纪30年代,由于仓央嘉措诗歌翻译传播较少,对其认识还停留在研究领域或者是个人欣赏阶段,也没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政治意识形态较浓,甚至不敢公开称其为仓央嘉措情歌,所以对于仓央嘉措的诗歌更多地把它们和藏族民歌一起看待,看重诗歌的人民性内容,看重其民间性的价值;20世纪80-90年代,研究中已出现了道歌、情歌、政治抒情诗等不同观点,但主流还是看重其诗歌的人民性特点,看重其质朴无华的民歌风格特点;新世纪,诗歌呈现出意蕴多元化和大众娱乐化两种倾向,则是当今新媒体时代艺术取向的表现。本时期出版的仓央嘉措诗歌,以及网络、流行歌曲中出现的以仓央嘉措署名的诗歌和歌曲,虽也有粗制滥造,未精心打磨的,但众多的公开出版物,满足了各层次读者大众的需求。首先是多元化文化时代包容性的体现,显示本时期鲜明的艺术取向。既有研究类的深入深化,也有娱乐欣赏类的浅易而不计真实。其次,从仓央嘉措诗歌的热度,也显示了现代社会的读者对于赤诚之心、率真之情的渴望,同时每个读者也可解读他们自己心中的仓央嘉措诗歌。从仓央嘉措汉译文本不同时代艺术取向的变化,可见汉藏文化交流的渐趋密切,已经有越来越多仓央嘉措诗歌翻译成汉文;也可见社会政治环境对于民间流传的翻译文学作品的巨大影响,文学的多元化包容性趋向也影响着读者的阅读和接受。
[注 释]
①虽命名为《西藏情歌》但其所选100首诗作中,对比今译作品,大部分都为大家所公认的仓央嘉措情歌,因此,后面所选诗歌,也考虑了数量较大的西藏民歌。
②《仓央嘉措之喜·六世仓央嘉措道歌集》,此文本为作者私印本。
③虽然该文作者选取的是1990年后,但笔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研究,还未真正形成高潮,21世纪后的研究更为突出,所以把这一论断归入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