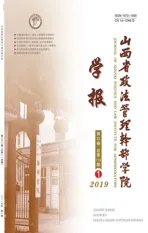海外流失文物追索的国际私法问题浅析
——以福建肉身坐佛为例
2019-02-21朱忻艺
朱忻艺
(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上海 200042)
2014年10月,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举办“木乃伊世界”展览,一尊约公元1100年的中国佛僧肉身宝像作为最重要的展品被单独安放在一间展厅。2015年3月,该“肉身坐佛”被我国文物部门认定为“被盗文物”。2015年12月,福建省大田县阳春村和东埔村村委会起诉肉身坐佛持有人——奥斯卡·范奥弗里姆,于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2016年6月,该案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正式立案。2017年7月,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就中国福建村民向荷兰收藏家奥斯卡·范奥弗里姆追索章公祖师肉身像一案举行了首场听证会。唐代以后,佛教在福建开始兴盛,肉身坐佛最早出现在唐朝文献《全唐文》中。佛教认为,佛菩萨或高僧大德圆寂后可得舍利。据考证,肉身坐佛是章公祖师在北宋年间圆寂后,被镀金塑成佛像。肉身坐佛的四肢和身首俱全,相比于普通的泥塑菩萨,更给人强烈的崇敬感和皈依感,是福建省大田县阳春村村民的精神寄托。针对类似的文物追索诉讼案件,首先需要确定管辖的法院,根据《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二条规定,荷兰管辖依据采取住所地标准,则荷兰的法院可以作为该案的管辖法院。在确定管辖后,进入实体问题的审理。原告是否适格、诉讼标的即肉身坐像是动产抑或不动产、准据法应采取何种冲突规范?在确定准据法后,根据准据法所在国的国内法判断文物究竟归属于文物原所有人还是善意取得第三人。本文从以上角度对这些问题作出初步梳理。
一、原告的确认
对于文物追索的司法程序,原告的确定往往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原告是指谁可以作为适格的主体提起诉讼,从而得到法院的认可。第一,原告必须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亦即法律所认可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第二,原告须对诉讼标的拥有或曾拥有所有权,也就是要适格。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我们可知在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出的肉身坐佛属于“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属于我国指定保护的文物,应当受到国家保护。
作为国家所有的文物,由谁代表国家的身份提起诉讼或应诉仍存在不少的争议。有学者提出,巴拉卡特案和其他国外类似案例中都是由文物来源国国家政府出面作为原告起诉,而我国政府历来都不愿意接受外国法院的管辖。[1]2009年圆明园拍卖兽首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该诉讼案件是由律师刘洋出面组织,没有得到圆明园管理处人员的支持,最后由在巴黎的一名华人律师求助欧洲中华艺术协会作为原告起诉。在案件审理阶段,法国法院认为欧洲中华艺术协会只代表协会利益,不代表中国利益,对于本案没有直接请求权,最终驳回其诉讼请求。
在本案中,阳春村和东埔村村委会作为肉身坐佛文物追索案的原告,在被告看来不可被认定为具有法律人格的有效实体。村委会这一主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否可以以原告身份在其他国家提起诉讼,在未来的举证责任上必将困难重重,在流失文物追索之诉中会被严重质疑。为满足适格原告的要求,而不因程序性问题遭遇文物追索诉讼的失败,建议尽可能增加相关主体作为原告。在其中一部分主体不为外国法院认可时,文物追索之诉中依然有其他适格的原告,从而提高成功起诉的几率。[2]笔者认为对于文物追索这一类特殊的涉外诉讼,我国可以适当放弃主权及国家财产豁免权,在诉讼结果中承担主导角色。另,由于在国外提出类似民事诉讼的费用较高,私人主体由于缺乏适格的原告资格,涉入该类案件收效甚微。
二、动产及不动产的识别
在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提起的诉讼中,将文物识别为动产或不动产将会导致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将文物识别为动产还是不动产,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1988年法国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的阿布格诉日内瓦村案是文物追索领域的典型案例,体现出对某些类型文物识别对法院管辖权的重要性。在法国南部一座私人教堂内壁,曾经有一幅创作于十一世纪的湿壁画,其所有人为四名农民。但由于其中两名农民未经其余两名农民同意,擅自将该壁画出售给他人,这两位农民故提起诉讼要求受让人返还。因壁画售出后位于瑞士,该诉讼性质为涉外民事诉讼。针对该起案件,法官的首要职责是确定法国还是瑞士法院享有案件的管辖权,所以首要问题即对该湿壁画的定性。
而在福建肉身坐佛一案中,我国和荷兰对于其属于动产达成了一致。根据《荷兰民法典》第三条第一款对不动产的列举结合第二款“所有不动产以外的物均为动产”,肉身坐佛显然未属于列举出的动产范围。但对于肉身坐佛是否属于“尸体”,双方各执一词。根据荷兰《埋葬与火化法》,无人可拥有尸体所有权,故我方可从肉身坐佛属于尸体的角度寻找合法依据,证明荷兰收藏家无权拥有该坐佛。
从各国立法及英美法系的判例来看,大部分国家的法院在处理动产及不动产的定性问题时通常采用法院地法这一系属公式。这对我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启示是,注重研究提起文物诉讼所在国的法律规定,分析其对于动产及不动产的定性,争取拥有管辖权的法院的文物保护规定有利于我国。
三、海外流失文物追索的法律适用
在判断法院是否有权管辖、原告资格是否适格、动产及不动产的识别之后,文物追索诉讼案件的冲突规范选择对案件的审理结果举足轻重。对于文物诉讼,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规定不同,具体体现在适用了不同的系属公式。纵观国际社会上,解决海外流失文物追索案件的系属公式主要有物之所在地法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来源国规则等。不同的系属公式有其各自合理之处,但因其缺乏对文物保护的针对性故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合理性。
(一)物之所在地法
物之所在地法是作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的物所在地方的法律。它常用于处理物权方面,特别是不动产物权方面的法律抵触。美国1971年《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则除采纳“物之所在地法”这一系属公式之外,抑或用“物之所在地法院将予以适用的法律”这种软性连结因素来取代硬性的“物之所在地法”。[3]利用该系属公式可以体现国家的主权,能有效实现文物所在地国家对文物的控制。物之所在地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确定性、可预见性、商业便利性。但同时会使文物购买者,不管其为善意或恶意,利用冲突规范进行法律规避,造成交易“合法化”即所谓的“文物漂洗”现象。这将导致文物流转的速度更加快速,严重损害文物来源国的利益,不利于其文物的追索。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指当双方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或选择无效的情况下,由法院根据这一原则在与该合同法律关系有联系的国家中,选择一个与该法律关系本质上有联系、且利害关系最密切的国家的法律予以适用。该系属公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机械适用物之所在地的弊端,提高了法律适用的灵活性,能公正合理地处理各种不同类型的案件,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而这极大的灵动性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利于裁判结果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这就导致倾向于保护文物来源国还是善意第三人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法院地国。但这将使海外文物追索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文物所在国一般都是被盗文物所在地。这给文物来源国包括我国的启示是,在未来的文物追索诉讼中,加强论证流失文物与来源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争取在准据法的选择中适用文物来源国的法律。
(三)文物来源国规则
国际法学会认为文物来源国是指从文化角度看与该财产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但该定义适用的与财产有最密切联系与最密切联系不免殊途同归。西米恩教授认为,如果在文物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的情况下,某人根据文物输出国的法律可以被认定为所有人,那么所有人应该获得文物输出国的保护,此处的文物输出国即是文物来源国。由此可得,文物所有人的判断标准是按照文物输出国的法律,这显然更有利于保护文物输出国的文物追索法律问题,其不必受到文物所在国司法的限制。文物来源国规则将流失文物的特性作为其重要的考量要素,文物作为一种特殊的动产,与一般动产的区别就体现在其“文化性”和“民族性”。
文物作为一国的文化财产,蕴含着该国的历史和底蕴,非一般动产可比拟。文物同时作为一国的象征,体现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民族性。虽然有此定义作为文物来源国这一系属公式的理论支撑,其在实践中也难以把握,甚至并未在国际公约中得以体现。且文物来源的国家多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发展甚至落后状态,没有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去保护海外流失的文物。
2008年伊朗诉巴克拉画廊有限公司案就是适用文物来源国的典型案例。英国巴拉卡特画廊从法国、德国和瑞士三国购买了一批古代雕刻文物,而伊朗认为这些文物归其国家所有,要求巴拉卡特画廊归还。伊朗二审法院认为该批古代雕刻文物归属伊朗。文物来源国原则倾向于保护文物来源国文物的追索,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同时给众多国家的立法提供参考。
(四)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适用建议
以上列举的三个系属公式各有利弊,但都在具体案件中得到各国法院的支持。考虑到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物权一章中只规定动产的法律适用,并未将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适用做出单独规定,而文物因为其财产表现形态通常被归为动产,沿用关于一般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规定。笔者建议在物权一章中参考其他特殊动产如运输中的动产、有价证券等,将文物作为特殊动产处理。
未来的法律修改可以在该章中増加一条冲突规范:对于因为偷盗、盗掘、走私到海外的中国文物,适用文物来源国法;但是来源国无法被知晓或不可能被知晓,则适用与文物联系更为紧密或有利于保护文物的国家的法律。该条冲突规范也是基于我国《文物保护法》对海外流失文物的规定,也考虑到文物来源国不能查明的情况。这既在国际私法层面对文物追索诉讼案件提供了法制保障,也体现出我国对流失文物的重视,展现出我国对流失文物追索的决心。
美国斯坦福大学J.H.Merryman教授曾提出“文物的保存原则”。他认为文物的保存是第一位的,在处理返还问题时首先要考虑这一因素。对于文物来源国无法被知晓或不可能被知晓的情况下选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和最有利于文物保护原则,为避免非法占有人对文物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充分体现出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同样有助于国际上文物流失问题的解决。
四、先决问题——所有权的归属
肉身坐佛经过20多年的流转,所有权归属到底是善意取得人即荷兰收藏家还是文物来源国即中国。关于流失文物所有权的归属,各国作出了不同的规定,主要的法律冲突即善意取得制度和时效制度。两大法系国家在这两项制度上存在着本质差异,如果原告选择不同国家的法院起诉,将会导致不同准据法的适用和不同的审判结果。
(一)善意取得制度
国际社会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主要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下简称1970年公约)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5年《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以下简称1995年公约)。在国际社会分裂成文物资源国与文物市场国的历史背景下,1970年公约最大限度地弥合了两大利益集团的分歧,为保护文化财产、打击文化财产贩运、促进流失文物返还制定了最低限度的规则,在国际立法史上留下了历史性印记。[4]
1970年公约第七条第二款规定肯定了文物追索的合法性,但提出归还文化财产的要求国需要给予公平的赔偿、通过外交部门进行、提出相应文件及其他证据以及自行负担归还和运送过程中的费用。然而,公约的缺陷在于此处对“不知情的买主”未给出明确的判断标准,对于那些明知是赃物仍然购买的人,本条款无从甄别,恶意购买者可以声称自己是“不知情的买主”而要求获得赔偿,这可能使得非法交易者成功规避惩罚,不利于打击非法交易。
1970年公约第十三条规定作为义务性规范,将非法出口国和其主管机关的合作设定为需要遵守的义务,并且在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根据本国国情的前提下,为文物的追索提供了便捷。这确实是从法律层面上为文物的追索提供了良好的参考,鼓励众多文物来源国提高自身综合国力,在未来的公约制定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1995年公约第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明确了非法发掘和合法发掘,但是非法持有的文化财产应当予以归还,这未免给部分文物所在国的非法占有敲响了警钟,警告其尽快遵守公约规定,尽早归还非法占有历史上侵略得到的文物。相较于1970年公约,该公约增加了关于被盗文物的定义,即无论合法或非法发掘,只要非法持有的文物都定义为被盗文物。这一全新的规定体现出对文物来源国的倾斜性保护。
根据1995年公约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我们得知文物的合法购买者至少在购买当时是善意的,也就是其在购买时并不知道或没有理由知道该文物是来自盗窃、盗掘等非法来源的,那么他可以从文物来源国得到一定合理的赔偿。文物的价值本来就难以估量,再加上没有明确的补偿标准的指引,可能会促使善意购买人借此机会漫天要价,损害请求国国家的利益。在本案中,被告要求中国给予其2000万美元,遭到村民的拒绝。
虽然1970年公约和1995年公约对于文物保护提供较成熟的规定,但荷兰在1996年签署该公约后至今未获得议会批准,因此根据“条约不拘束第三国”原则,该公约无法约束荷兰。我国在追索福建肉身坐像的诉讼中,很难通过上述国际公约寻求合法依据。
(二)时效制度
有关于消灭时效的期限,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的规定都不同,甚至差距很大。我国《民法总则》仅规定了三年的消灭时效,而荷兰民法典规定三年和十年的取得时效。荷兰虽然针对《文化遗产保护法》中规定的动产或者构成公共收藏物或馆藏物的一部分动产不适用上一条款,但这部旨在防止具有重大历史及科学意义的荷兰文化遗产从荷兰流失的法律,显然不能为我国阳春村村民追索肉身坐佛提供直接帮助。[5]由于文物流失方式多样化且来源国家不定向,最终多数文物在脱离来源国后,就消失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致使来源国无从得知文物的去向,加大文物追索的难度。
纵观文物保护的国际公约,根据1995年公约第三条第三款,可得其诉讼时效是从请求者知道该文物的所在地、该文物拥有者的身份时起算,期限是三年。而最长的期限是五十年,从文物被盗时起开始算。五十年难以有效实现对流失文物的追索,从这一角度解读来看该公约规定不利于文物来源国,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善意第三人的权利。这提醒我国在文物保护的国际公约制定中,要积极发挥大国作用,借鉴美国“发现规则”及“要求并拒绝规则”的时效起算点,积极维护文物来源国的利益,保护众多文物来源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
除了国际公约对文物追索的相关规定,欧美博物馆的态度也值得各方关注。2002年12月9日,英国大英博物馆等19家欧美博物馆、研究所联合发表了《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无非是想借所谓的“文化普世价值”来淡化自身已经面临或即将面临的流失文物追索风险,从而为已经存在于这些知名博物馆中的他国流失文物披上“流失文物守护者”的伪外衣,试图以一纸“声明”阻断流失文物的回归之路。[6]
结语
文物追索是一条漫漫长路,这需要国人以极大的智慧同时在法律层面及私人层面去解决。近几十年来,国际市场上文化财产的价格飙涨,这直接导致文化财产贩运的泛滥与文物黑市的火爆。在暴利的诱惑下,大量犯罪分子铤而走险,盗窃、盗掘、走私等文化财产犯罪遂进入高发期。[7]在法律层面中,需要我国众多的国际法学家运用学术知识和实践经验打响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同时,国际社会需要文物来源国与文物所在地国家进行和平协商,在双方妥协让利的前提下签订双边协议。
经统计发现,从1949年至2017年,我国成功收回海外流失文物共计49例。其中,通过国际执法合作回归的17例,通过国际民事诉讼回归的2例,通过谈判与协商回归的4例,通过回赠与回购回归的26例。[8]该数据证明通过民事诉讼回归文物胜诉率极低,通过国际执法合作和回赠回购才是较为稳妥的方法。为应对珍贵文物流失严重的现状,我国应积极发挥大国作用,加强在国际公约制定中的话语权,使文物来源国的保护有法可依、有理有据。希望本文在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动产及不动产的识别、海外流失文物追索问题的法律适用、文物的所有权归属等问题的解读中,能为我国以法律方法追回海外流失文物提供有效的参考,以此指导我国未来漫长的保护文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