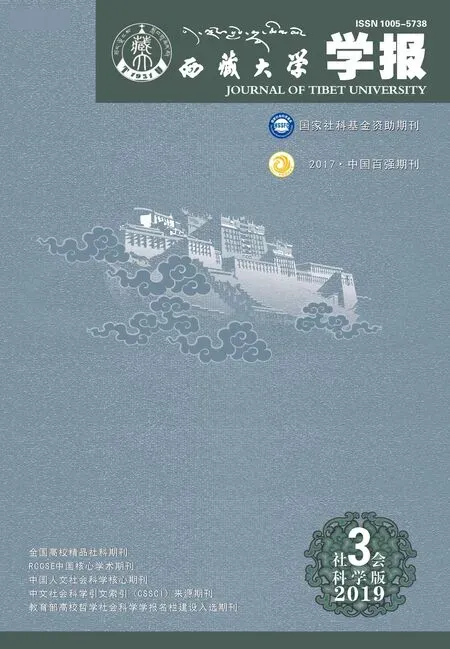达木蒙古八旗综论
2019-02-20边巴琼达
边巴琼达
(西藏布达拉宫管理处 西藏拉萨 850000)
自元代蒙古势力进入西藏以来,蒙古族和藏族之间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渗透于政治、文化、宗教、血缘的历史关系,时至今日仍然斑斑可寻,对蒙藏社会政治、文化、宗教、军事等方面产生着重要影响,在祖国统一史和各民族交往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达木蒙古的历史渊源
翻开著名史学家谭其骧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我们就会发现,早在宋、元、明时期,“达木”“达木曲科尔”等地名就已经赫然在目,说明“达木”一词古已有之,可见“达木”一词来源于顾始汗在此驻军而得名的说法值得商榷①谭其骧编著,中国地图出版社《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40-41页,“元明时期”36-37、85-86页。。
13世纪中叶,忽必烈统一西藏,在贡(今公塘)、官藏(今宁中)、甲哇(今羊八井)设立了驿站,不少蒙古人也随之纷纷进入西藏并在达木地方驻牧定居。到14世纪后期,当地蒙古人已渐成规模,于是当时西藏地方的帕竹第司政权便在此设立八个部落,以白仓部落首领为第巴,统管一切事务。[1]
但是,关于“达木蒙古”的来历及其形成时间,有史可考而且被人采信的说法,仍然是与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和硕特蒙古首领顾始汗在此驻牧军队有关。《中国古代地名大词典》关于“达木蒙古”词条解释:“在西藏境,一名玉树汭哈暑番,本居青海,当达赖喇嘛五世时,随青海蒙古王丹津入藏,住持达木地方,后嗣安土不归,遂成部落,初隶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清乾隆十五年珠尔墨特谋逆败后,改归驻藏大臣节制”。《卫藏通志》上也说:“达木,一名玉树纳哈署番,青海蒙古王丹津于五世达赖喇嘛时带领蒙古官兵赴藏护卫,留住五百三十八户在达木地方驻牧”。①《卫藏通志》二四九页.卷十五.部落。二者都认为达木蒙古是在顾始汗时期形成的。不过,按照冯锡时的观点,“清代达木蒙古主要是卫拉特蒙古的和硕特部人,但其中也不能完全排除有元、明时期在此地区活动过的蒙古人后裔的成份。”[2]也就是说,元、明时期的确曾有过不少蒙古人在此居住。
为了解决大量蒙古骑兵的战马饲养问题,具有游牧民族习性的顾始汗便选择了这片西北以念青唐古拉为屏障、东北毗邻羌塘草原和青海大本营、具有部族群众基础,而且地势开阔平坦、水草丰美的当雄草原作为自己的驻牧之地,并把今当雄县公塘镇中嘎村作为其夏宫,常年在此居住。从此,这支骁勇善战、驰骋祖国西北部边地多年的蒙古骑兵,便作为一支受蒙古汗王调遣、坐镇藏北高原、监视和掌控青藏地区局势的机动军事力量,在此安营扎寨下来。他们按照蒙古族的行政体制,由部落头人自主其政,至有清一代均不受西藏地方政权约束,“达木蒙古”之名由此诞生。
公元1751年(乾隆十六年),在平定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乱后,清中央政府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将达木蒙古划归驻藏大臣直接管辖和节制,并正式将其划分为八个旗的军事单位进行管理,遂称作“达木蒙古八旗”。公元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驻藏大臣辅鼐与积福将扎什城清真寺改修为万寿寺,并“在草地达木发给牛厂一处”,以其收入向万寿寺喇嘛的念经祈祷活动提供所需酥油②西藏博物馆藏“乾隆59年驻藏大臣辅鼐、积福颁发扎什城万寿寺执照”“嘉庆19年驻藏大臣瑚图礼、祥保颁发扎什城万寿寺执照”。,位于今当雄县城以东的“达木牛厂”由此产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瓦解。1912年,清帝被迫退位,驻藏大臣回到内地,十三世达赖把当雄地区划归色拉寺俄巴扎仓管辖,建立了丙级宗(小县)政权,达木八旗的特殊地位不复存在,达木蒙古势力被瓦解,达木蒙古人的生活习性和文化特征渐趋消亡。达木一词也成为了今天令大多数当地人陌生的历史地名。
这里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达木八旗”亦或是“达木蒙古”都不过是历史上由蒙古民族为主体并按照自身特有体制进行自我管理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达木蒙古地方并非只有蒙古人,当初顾始汗选择在这里驻牧的时候,当地早已有不少藏族土著群落在此生产和生活。蒙藏民族在此长期混居与交融的过程中,特别是清末时期,随着历史的变迁和受政治风暴的影响,当地蒙古人自身的民族认同感也随着达木蒙古八旗地位的变化而没落,迅速消弭于无形。至末任驻藏大臣联豫时,“其达木官民,不惟不解蒙语,即中文中语亦俱不识,而衣冠品级,亦俱与番官同,”[3]并最终与当地藏族融合而成为今天具有某些蒙古民族特征的当雄藏族人。
二、达木蒙古的生产生活方式
达木地势开阔而平坦,再加上念青唐古拉山脉对来自西北风雪的阻挡,使这里占地域总面积的70%左右的广阔地带成为优良的草原牧场。因此,顾始汗将“放牧军马”作为在此定居最初的动机和目的,主要以游牧为生。历史上将达木八旗的核心区域称为“达木牛厂”,说明随着达木八旗军事功能的退化,以放牧牛羊作为其基本生产活动的功能逐渐呈现出来。
由于当雄草原地处藏北,海拔较高,气候寒冷,经常遭受干旱和雪灾,达木百姓和官兵也就不得不“于附近商属租厂游牧”③西藏博物馆藏“嘉庆15年理藩院西藏夷情事务衙门鄂罗锡叶勒图、佛尔泰阿令牌”。。通过给付租金的方式,前往与达木接壤的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草场放牧,其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如上所述,“八旗连年夏天干旱,冬天又遭大雪连绵,草厂尽被雪压,以至牛马得症倒毙甚多。”“商属哈拉乌苏所管拉木措海子边及达布纪噶尔一带。”“三巴呼图克图所属草场”。正因为达木百姓以游牧为生,每当遇到干旱或者雪灾等重大自然灾害、草场被严重破坏的时候,理藩院都要赈灾安民。公元1829年,达木遭受雪灾,清政府下令理藩院赈灾。“道光九年,西藏达木蒙古八旗多遭雪灾,理藩院柔远司筹备茶叶二百斤,银五百两作为赈济之用。”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案卷号2372.
采取盐觔。藏北有大小一千多个湖泊,其中大部分为咸水湖,仅盐湖就有170余处,地处达木地界的纳木错本身也是咸水湖。因此,拥有丰富自然资源而且喜欢过游牧生活的达木蒙古百姓自然就过上了采卖盐觔的生活。《卫藏通志·卷十五·部落·达木蒙古》记载:“达木驻牧之蒙古等赴盐池采取盐觔,每年缴纳商上税盐一百驮。”收藏于西藏博物馆的有关清代处理达木蒙古事务的四件文档中,一件内容为租借草场放牧,其余三件为调解盐业纠纷,即“嘉庆十六年钦差署理西藏夷情事务内阁中书佛尔泰阿颁发令牌”“同治五年驻藏大臣景纹与理藩院西藏夷情衙门颁发令牌”和“同治年间驻藏大臣景纹断事牌”。这些文件在调解和处理达木八旗与西藏地方政府盐税纠纷时,都详细地记载了达木蒙古百姓采取盐觔并四处贩卖的事实:“奉钦宪大人批准,逹木人等采取盐觔交纳商上税盐一百驮,以作定例。”“前往各处采取盐觔易换青稞,事竣后交纳商上税盐一百驮。”②西藏博物馆藏“嘉庆16年钦差署理西藏夷情事务内阁中书佛尔泰阿令牌”。“达木八旗百姓每年在达赖喇嘛所赏海子内取盐向四外出卖,籍资养活家口。”③西藏博物馆藏“同治年间驻藏大臣景纹断事牌”。可见采取和贩卖盐觔是达木蒙古八旗百姓的基本生产活动之一。
三、达木蒙古八旗人口与兵员
目前发现的最早记载达木蒙古人口的文件,始出于顾始汗驻牧达木半个多世纪以后。在蒙古汗王治藏的末期,公元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清中央派往西藏协同拉藏汗办理事务的第一位钦差大臣赫寿上奏:“闻额鲁特原在藏有五千余人,其所居地方于人丁不相宜,生育者少,即生育亦难以长成,所以人丁比先渐减。”④中国藏学出版社《汇编》311页“赫寿奏拉藏汗态度及其与准噶尔交往情形折”。这段话说明,在顾始汗时期的达木蒙古人口约为5000人。到拉藏汗时期,已有所减少,但差别并不太大,当仍在5000左右。
其次,是公元1793年(乾隆58年)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第六条指出:“达木蒙古官兵共五百三十八户,在藏当差官兵八十三员,每月商上发给钱粮,其余均在达木地方游牧,听候调遣。”这里是按照蒙古人特有的兵民一体的户数计算,按照每户大概四至五人计算,“五百三十八户”也大概就是2000余人,比起赫寿所说拉藏汗时期的5000人左右,减少了一半之多。如果赫寿的数据基本属实,那么,经过抗击准噶尔、“阿尔布巴之乱”、廓尔喀入侵等战事,造成大量兵员伤亡和大规模人口掳掠与财物洗劫之后,达木八旗人口和兵员锐减是极有可能的。况且,在清朝鼎盛时期,大规模用兵驱逐侵藏的廓尔喀之后,清中央有能力而且也确实挟大胜之余威,下了很大的决心、花费了大力气来处理善后,借机整治西藏政治体制,从而制订了历代中央治藏史上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因此,“五百三十八户”这一数据是比较可信的。
公元1717年至公元1718年的准噶尔一役后,由于达木地方是主战场而且达木蒙古人是主力军,因而导致达木蒙古人口数量锐减。《颇罗鼐传》载,达木官兵与准噶尔势力激战,损失十之八九,而且百姓被准噶尔人掳掠殆尽。雍正三年,四川提督周瑛曾在奏折中说,拉藏汗被害后,“其部属蒙古尚遗留千有余口,为康济鼐收管”,并收拢集中在藏蒙古人“听其自往”或“移驻于达木一带地方驻牧。”⑤中国藏学出版社《汇编》367页“周瑛奏请升赏西藏官员并恳随钦差入藏料理事宜折”。可见当时达木蒙古兵员损失之惨重和人口减少幅度之大。后来,在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同为顾始汗子孙的青海蒙古各部因躲避战火,避乱达木,达木蒙古八旗再次得以重新发展,人口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曾一度达到了800余户,3000余人。
嘉庆15年,西藏夷情事务官员发布的令牌中表述了珠尔墨特之乱后达木兵员数量:“查达木官兵系于乾隆十五年,奉旨安设骑兵五百名投住展什湯地方。”①西藏博物馆藏“嘉庆15年理藩院西藏夷情事务衙门鄂罗锡叶勒图、佛尔泰阿令牌”。这说明,爆发于公元1717年的准噶尔之战后,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和恢复,达木人口有所发展,达到了800余户和3000余人。但是,期间又经过了“阿尔布巴之乱”,蒙古八旗因为受战乱影响和直接参战而兵员损失,致使人口进一步减少,只有“安设骑兵500名”。据《乾隆朝实录》记载,在与廓尔喀的战事中,第一次调派达木兵500名,第二次仅调派300名参战,连驻藏大臣都叹息蒙古兵虽勇但数量太少。而且因为战事失利,八旗兵又一次严重减员,“唐古忒兵与达木蒙古兵御廓尔喀失利,——达木协领泽巴杰等死之。”②《清史稿》本纪十五,高宗本纪六。故在战后制订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出现了“五百三十八户”这一说法。
嘉庆以后,战争减少,达木人口逐渐有所增加,发展至清朝末年,达木八旗已近800户,约4000人,能募集1000兵员。马丽华在《如意高地》中说,清末之际,“达木八族时有人口近四千,高寒之地游牧人,纯朴而尚武,驻藏大臣联豫于光绪三十四年在此募集民兵千人,欲成立新军一支。”然而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驻藏清军内讧,噶厦政府趁机将达木蒙古收归治下。由于达木地方不从,双方爆发了武装冲突,达木蒙古八旗又经历了一次洗劫,总管固山达也因此毙命。“藏军攻进达木,后来攻进三十九族地区,还做了一些烧杀抢掠的事情,死人多多。”③马丽华《如意高地》“绝塞死旅:古往今来最糟糕的旅行(5)”。
此外,《卫藏通志》和《善后章程13条》均记载,达木蒙古在拉萨亦留住有部分百姓和少量兵丁。“每佐领各派十名,共八十名,驻拉萨以备差遣,并护卫达赖喇嘛。”“自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被诛后,伊等因无人管束,竟尔潜回达木。”④中国藏学出版社《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以下称“研究”)513页之“善后章程十三条”。“惟无依之老弱数十名户口,若一旦令其归回达木,恐失养瞻……令公班第达将老弱无依之人查明造册,准其驻藏留养,并按八个佐领,每佐领下捡派兵十名共八十名轮流来藏听候钦差大臣差遣。”⑤《西藏通志》二四九页.卷十五.部落.达木蒙古。不过,由于数量太少,这部分留住于拉萨的官兵百姓不足以影响达木八旗人口数量的统计。
从总体上看,达木蒙古八旗人口和兵员数量呈现出如下变化趋势:在顾始汗时期,最初屯驻了近万名骑兵,百姓也当在数千户。此后,直至嘉庆朝之前,由于驻牧初期的水土不服和百余年间的频繁战事,达木八旗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兵力严重减员。尤其是经准噶尔的大规模洗劫之后,达木蒙古八旗受到毁灭性打击,人口数量十去其九,军事实力荡然无存,尽管随即有青海蒙古各部的徙居和补充,也一直未能恢复元气,达到驻牧之初的水平。这一时期,达木八旗的兵员数量始终在五、六百人之间,人口数量也大致在五、六百户上下徘徊。嘉庆朝以后,由于战事减少,达木八旗的人口数量曾一度有所增长,兵员数量也有所增加,至民主改革时当雄地方“已生活着一千五百’户牧民,约一万二千多人。”[4]
四、达木蒙古八旗的管理体制
由于达木八旗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军事作用,从顾始汗时期到辛亥革命的数百年间,无论对外属领关系还是内部管理体制,达木蒙古八旗都形成了一套与通常意义上的地方行政体制完全不相同的、具有蒙古民族特色和满清八旗制特点的独特社会结构与管理体制。
关于其外部属领关系,即由谁直接管理和指挥的问题,相关史料均记载其先后受命于蒙古汗王、西藏郡王、驻藏大臣和理藩院,最后纳入了噶厦地方政府的管理体系,其发展和演变脉络殊无异议。这里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在拉藏汗身亡以后至颇罗鼐当政之前的达木管理权限问题。公元1718年至公元1728年的十年期间,西藏政局先后由准噶尔势力和清朝恢复设立的西藏地方政权掌控,其后又经历了阿尔布巴之乱。故在这一时期,达木蒙古也势必首先由以策凌敦多布为首的准噶尔势力及其所设立和扶植的西藏地方政权控制。在准噶尔势力被驱逐后,清朝成立了由康济鼐总理的西藏地方政权,达木蒙古自然受其管辖。其后,贝子阿尔布巴等发动政变并诛杀了康济鼐,取得了对西藏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达木蒙古遂再度易主,被迫接受阿尔布巴管制。
其二,颇罗鼐的执政时间问题。颇罗鼐虽然从公元1729年执掌西藏地方政权之后才正式掌握了达木蒙古八旗的指挥权,但是早在康济鼐执政时期,清朝就已经命令他协助康济鼐管理达木蒙古。“阿里接连阳八景、达木、腾革罗尔一带地方,防御谆噶儿要隘,以扎萨克台吉叵罗奈副之。”①中国藏学出版社《汇编》367页“周瑛奏请升赏西藏官员并恳随钦差入藏料理事宜折”。因此,早在准噶尔势力被驱逐后,颇罗鼐即已事实上开始接管达木事务,进而才能在“阿尔布巴之乱”后随即调遣达木之兵参战并扭转了战争局面,取得了最终胜利。恐怕也正是因为达木八旗在跟随他平定“阿尔布巴之乱”中的英勇表现,才促使其在当政之后始终直接管理和掌控着这支重要军事力量。
其三,有关理藩院与驻藏大臣之间的关系及其在达木事务管理权限方面的划分。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明确规定:“(达木八旗)俱归驻藏大臣管辖……一切调拨,均依驻藏大臣印信文书遵行,噶伦、代本不得私自差遣。一切官员之革除补授,俱由驻藏大臣商明达赖喇嘛施行。”②中国藏学出版社《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以下称“研究”)513页之“善后章程十三条”。首度明确了驻藏大臣对达木蒙古等地区的管理职能。《卫藏通志·部落·达木蒙古》也记载,“达木蒙古自乾隆十五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谋逆之后,钦奉上谕统归驻藏大臣管辖,易于料理。”③《西藏通志》二四九页.卷十五.部落.达木蒙古。此后至清末,历任驻藏大臣均对达木蒙古八旗实施了有效管理。
同时,也有大量史料记载理藩院参与了对达木八旗的管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经驻藏大臣莽古赍奏请,明确由章京随同驻藏大臣办理三十九族及达木八旗事宜[5]。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和坤等遵旨议覆鄂辉等奏西藏善后事宜十九条折》载:“查西藏由理藩院派出司官一员承办达木额鲁特及三十九族番子事务。”④张雨新学苑出版社《清朝治藏法规全编》一八六八页。《卫藏通志.卷十二.条例》载:“(设)理藩院司员一员,管理达木蒙古八旗官兵、三十九旗番民事务。”
那么,对达木蒙古都有管理权限的驻藏大臣、理藩院及其派出机构与官员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从《理藩院则例》的制订及其内容、驻藏大臣兼有的多重身份及理藩院驻藏司员与驻藏大臣之间的隶属关系,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驻藏大臣、理藩院、西藏夷情司衙署这三者之间在管理达木事务时的关系与权限划分。
其一,理藩院制订的《理藩院则例》对包括西藏在内的各民族地区日常事务的具体管理办法进行了规范,因此,理藩院是少数民族事务管理法则的制定者。驻藏大臣作为一方大员,则是西藏地区《理藩院则例》的贯彻者和实施者。
其二,历史上,有不少驻藏大臣兼任理藩院职务,如和宁兼理藩院侍郎,留保柱兼尚书,文康兼郎中,辅鼐兼侍郎。也有部分驻藏大臣与理藩院长官先后相互转任,如清廷派往西藏的首任钦差大臣赫寿返京后转任理藩院尚书,驻藏大臣常宝系由理藩院员外郎调任,隆文卸任后迁转理藩院右侍郎等。
其三,自乾隆十四年开始,驻藏大臣属员中即有章京(理藩院司员)和笔帖式(理藩院拣派)等⑤中国藏学出版社《研究》467页。。《清高宗实录》载:“驻藏大臣衙门向设理藩院司员一,笔帖式一,应仍照旧例,派遣司员一人管理达木蒙古官兵、三十九族事务。”清代,曾任西藏粮台兼摄夷务章京的徐瀛也明确指出:“西藏额设夷情一员,系理藩院司员派出。”可见西藏夷情司衙署的主管官员章京、司员、主事、中书等,由理藩院负责委派任免,但归属驻藏大臣节制。
因此,具体负责管理达木蒙古事务的“西藏夷情司员衙署”及其主管官员由理藩院委派,但需要接受驻藏大臣节制,其主要职能是协助和代表驻藏大臣处理包括达木蒙古在内的西藏地方民族事务。
关于达木八旗的内部管理体制,即内部管理层级与机构设置情况大致如下:在初期为蒙古游牧习俗的部落化自主管理,带有一定的原始性;中期则设立佐领——协领(固山达)——总固山达,按照清朝的旗籍规制进行半军事化管理;末期则纳入西藏地方管理体系,实行具有西藏地方行政特点的宗本管理制度。
1912年的“驱汉事件”发生后,十三世达赖喇嘛把当雄拨给色拉寺,成立了宗,八旗直属宗政府管辖,设“机巧”即总管一人统管八旗。各旗设有甲本、藏革(即章宗)、坤都、久本等头人,各旗所辖的措哇(即部落)则设有马本、休令等官职。[6]
五、达木蒙古八旗的特殊历史地位与作用
达木八旗在西藏历史上也有着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他们自有领地,自成体系,自给自足,不受噶厦地方政权管辖。他们不承担西藏地方劳役,不交租税,却受商上养瞻供应,并有中央赈灾救济,有着诸多的优势和特权。在经济待遇上,当拉藏汗等蒙古汗王掌控西藏时,“达木额鲁特兵员费用由拉藏汗份例内每年支取25000余两。”其食用口粮,“原有班大人任内奏明奉旨准赏田地甚多。”[7]拉蔵汗兵败被杀后的雍正年间,清中央和西藏地方对遗留在藏的蒙古人给予抚慰和安顿。“每月悉于达赖喇嘛库中支给口粮,以资养瞻。”而且“务将藏地所住蒙古人等尽行查出,量颁恩赏,……将达赖喇嘛厂上孽生牛羊骡马之内,按其人口,酌定数目给予。”①中国藏学出版社《汇编》367页“周瑛奏请升赏西藏官员并恳随钦差入藏料理事宜折”。雍正五年,康济鼐被杀,阿尔布巴等在向清廷陈述其罪状时,说他对原拉蔵汗之蒙古给予特殊待遇:“给予口粮,凡仓内之物,不论数目,尽行给予。”②中国藏学出版社《汇编》385页“岳钟琪等奏报询据达赖喇嘛听差阿旺罗卜藏关于康济鼐被杀情由并请示准否允其进京折”。乾隆年间,“西藏赏需一项,向来止赏达木官兵,所有例马银三百九十余两,置买物件,按年奖赏一次,足敷所用。”③学苑出版社《清朝治藏法规全编》一八六九页“和坤等遵旨议覆藏地善后事宜十九条”。《卫藏通志.部落》载,将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产“林清侧颇拉二处差赋”归入达赖喇嘛“赏下动用”,以便“养瞻达木蒙古”④《卫藏通志》二四九页.卷十五.部落。。《卫藏通志·抚恤》一篇中有大量关于达木蒙古给养费用的记载:“达木兵丁钱粮原有班大人奏定以抄产地亩归入商上,每年所收租息二万四千余两酌量分给。”“于边地萨喀(双湖)、那克藏(申扎)、哈拉乌苏(那曲县)游牧等处派羊四千余支分给达木,以致游牧百姓不堪苦累,日渐逃亡。”“达木兵丁钱粮仍应由商上支领。”“每年由布达拉外商发给达木钱粮数目,随时具禀存查。”⑤《卫藏通志》二三四页.卷十四.抚恤。乾隆年间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与达木蒙古八旗性质类似、也同归驻藏大臣和理藩院直接管理的藏北39族,每年每户应缴纳商上“贡马银”八分,却未提及达木蒙古需要缴纳任何差赋,而是“每月商上发给钱粮”⑥《卫藏通志》一二九页.卷十二.条例。。每逢人事变故和自然灾害,清中央和西藏地方则会及时赈灾救济,“道光九年六月乙巳,免西藏喀拉乌苏等处雪灾番族供马银,并抚恤达木八旗被灾官兵户口。”⑦《清史稿》.卷十七'.本纪十七.宣宗本纪一。
清朝中央政府之所以如此看重和扶持达木蒙古八旗,一方面是因为达木蒙古八旗“自拉蔵汗时代以来即以骁勇善战闻名,迄受清廷重视”,是清朝中央政府稳定和制衡西藏地方局势所倚重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既承担着防范准噶尔势力、掌控卫藏局势、护卫达赖喇嘛的重要职能,也是清中央、西藏内部各派别乃至青海蒙古和来自新疆的准噶尔等各种势力争取和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是因为达木地理位置的极端重要性。顾始汗在建立噶当颇章政权之初即选择达木地方驻牧,就是因达木地区前接卫藏、后连青海,具有近可攻、退可守的地理优势,目的在于震慑西藏地方势力,监督西藏地方政权。一旦藏内有事,即可迅速挥师南下,如若不支,则可随时退回青海大本营。尤其是在准噶尔事件发生之后,准噶尔势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威胁西藏安全和清王朝安定的心腹大患,以至于康熙皇帝在谈到西藏于防守准噶尔东侵的重要性时感叹:“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①魏源:《圣武记》,第10页。因而扼守藏北咽喉要道,防范准噶尔自青海南下或自纳仓西来,拱卫卫藏地区,就成为了清政府稳定西藏局势的头等大事。《清史稿》在谈及达木在阻击准噶尔入侵时所占据的地理位置之重要性时说:“盖通准夷之路有三:……中路之腾格里海逼近卫地,故防守尤要。”爆发于公元1723年(雍正元年)的罗卜藏丹津之乱后,为防准噶尔南窜,“每年夏初,西藏官兵赴防北路腾格里海之隘,以备准夷,冬雪封山,撤兵。”②《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五.列传三百十二.籓部八.西藏。
鉴于达木蒙古的重要性,达木蒙古八旗先后由蒙古汗王、郡王、驻藏大臣和理藩院直接管理。在蒙古汗王主政时期,达木八旗是其最可靠的依恃;郡王颇罗鼐当权时期,派其最珍爱的次子、实“封”为长子而成为王位继承人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管理纳木错及达木等地额鲁特骑兵,守护哨卡。珠尔墨特继承王位后,在为其叛乱做准备时,也把达木地方作为其后方基地,“遣兵备喀拉乌苏,徙达木番众。不数旬,扬言准噶尔至阿哈雅克,自率兵往备。”③《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五.列传三百十二.籓部八.西藏。清中央同样深知达木八旗的重要性,在平定珠尔墨特之乱后,首先将达木蒙古直接置于驻藏大臣管理之下;噶厦政府也曾经试图染指达木蒙古八旗,《联豫驻藏奏稿》说:“唐古忒屡欲侵占其地,该达木官民等皆不允从。”辛亥革命爆发后,驻藏大臣被驱逐回内地,从而丧失了对达木蒙古八旗的管理权。西藏噶厦政府立即趁势将达木蒙古收归治下,但因西部千户诺巴基巧拒不服从并杀死了色拉寺派来接管的僧人,双方随即爆发了武装冲突,最后致诺巴基巧被杀,才使噶厦当局多年来管辖达木蒙古八旗的梦想成为现实。
历史上,达木八旗先后参与过击败藏巴汗、平定噶玛噶举派反叛、出击不丹和拉达克、打击第巴桑杰嘉措、抗击准噶尔、反击廓尔喀,平定“阿尔布巴之乱”等无数次大小战役,经常仅以数百骑兵接敌并迅速扭转战争形势,创造了许多辉煌战绩,骁勇善战,为维护国家统一大业和西藏地方局势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达木八旗建立之初,虽然以噶玛噶举派为政治基础的藏巴汗政权已经结束,蒙藏联合执政的甘丹颇章政权已经建立,但是西藏地方尚未完全统一,社会局势也并未立即稳定,卫藏各地的噶举派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威胁依然存在,第悉藏巴的残存势力先后在各地发起了大范围的武装暴动。作为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基本武装力量,达木八旗在顾始汗之子达赖汗的率领下随即承担起了平定武装暴动的任务。大约经过两年时间的征讨,彻底平息了各地的叛乱,维护了新生甘丹颇章政权的稳定。[8]
在1788年至1793年期间的两次抗击廓尔喀侵略战争中,达木蒙古八旗再次参战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当廓尔喀第一次侵藏,逼近后藏威胁到坐床不久的七世班禅的时候,乾隆皇帝上谕:“闻达木官兵尙称强壮,亦着酌量带往。”④中国藏学出版社《汇编》618页“谕雅满泰等廓尔喀抢夺聂拉木等处妥为防备”。“著雅满泰即酌带绿旗及达木额鲁特兵,前赴扎什伦布,将班禅额尔德尼加意抚慰。”⑤《乾隆朝实录》.全本.一千三百九卷。在班禅被接到前藏以后,乾隆皇帝斥责驻藏大臣庆麟意欲放弃后藏,于是庆麟再次调派五百多名达木蒙古兵会同当时驻扎在前藏与察木多的绿营兵前往守卫抵御,直至第一次战争结束。1791年,廓尔喀再次入侵,驻藏大臣保泰又一次征调三百名达木八旗兵作为前锋开赴后藏抵御。此次战争中,数百名八旗蒙古兵与廓尔喀侵略者死战,但是由于联合作战的藏军战力极差,一触即溃,达木蒙古兵虽然勇猛善战,却因人数太少而难以抵挡廓尔喀军队的进攻,最终功败垂成,达木八旗兵又一次遭受了很大的伤亡。“征唐古忒兵与达木蒙古兵御廓尔喀失利,唐古忒公札什纳木札勒及达木协领泽巴杰等死之。”①《清史稿》本纪十五,高宗本纪六。尽管如此,达木八旗兵在面对侵略者的战争中,以他们临敌不畏、临死不退的精神和事迹捍卫了达木蒙古骑兵“英勇善战”的美名,赢得了世人的敬佩,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降旨奖励和抚恤。
事实上,有清一代,达木蒙古八旗也确实是一支始终效忠于清朝中央政府,听命于驻藏大臣的重要军事力量,清中央认为顾始汗及直接管理达木八旗的历任蒙古汗王“皆附中国”②《卫藏通志》一三八页.卷十三上.纪略上。。历史上,达木八旗在控制藏北,拱卫拉萨,羁縻卫藏,协助西藏地方共同抵御外侮的同时,对西藏地方势力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牵制和制约作用,为维护国家统一和西藏地方局势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达木蒙古八旗兴衰荣辱的历史,是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控能力以及蒙古部族势力在西藏影响力的大小相辅相成、相生相伴的。在顾始汗等蒙古汗王当政时期,由于西藏地方政权属于蒙藏联合执政性质,蒙古势力掌控着西藏地方的军政权力,所以在西藏境内为数不多的蒙古人自然具有极高的政治社会地位,其各种权利和利益自然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在驻藏大臣管辖前期,特别是驱逐廓尔喀侵略并制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之后,中央对西藏事务的掌控能力达到顶峰,驻藏大臣及其直辖管理的达木蒙古八旗和藏北39族等地方机构也相应具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反之,在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当中央政权逐步走向衰落,驻藏大臣难以掌控和左右西藏政局的时候,达木蒙古八旗的社会政治地位也随之走向没落,其经济生产活动也受到了当时西藏地方政权的影响和制约,并最终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和驻藏大臣的被逐,被纳入旧西藏地方政府的管辖之下,其民族属性和特殊行政体制也随之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