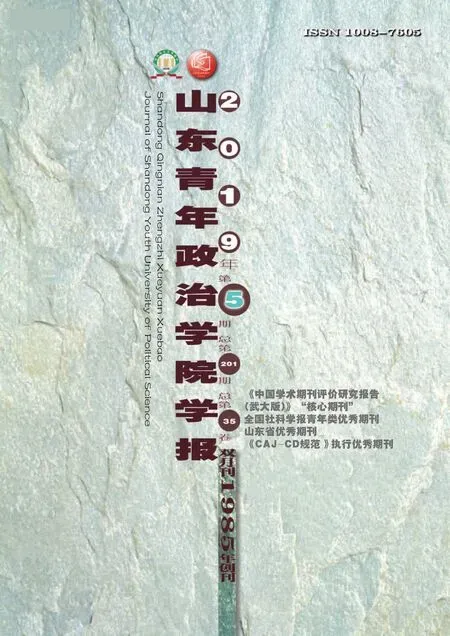马克思恩格斯在清算费尔巴哈哲学上的差异
——以《提纲》和《终结》为比较对象
2019-02-19童建安何中华
童建安,何中华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济南 250100)
人们一般认为,从黑格尔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有一个费尔巴哈阶段。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推崇过费尔巴哈哲学,并把它作为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哲学的中间环节,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被简单化地理解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加上黑格尔的辩证法。实际上,这种理解是十分偏颇的。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是如何清算费尔巴哈的,以及他们在清算时所体现的不同视角,学术界尚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是两位作者分别对费尔巴哈哲学进行清算的经典文献,本文以此作为比较对象,考察他们对费尔巴哈哲学所作批判及其体现出来的差别。这对于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思想,进而更恰当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清算
(一)出发点:是“感性直观”还是“感性活动”?
在《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将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并把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与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对照起来考察。
费尔巴哈将哲学看作是关于存在物的知识,在他看来,事物是怎样的,其本质就是怎样的。同时,他还认为,只有“直观提供本质、真理、现实”[1]。在他看来,只要借助直观就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说一个事物是感性的,就是说它是现实的,从而也是真实的。因为在他那里,“真理性,现实性,感性的意义是相同的。”[2]。
费尔巴哈将自己的哲学视野定格在客观事物上,从而使人们的视野由天国拉回了尘世,无疑有其进步性。但直观事物并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更不能把握事物的真理。这种直观的思考方式,运用到人类社会,只能发现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并不能认识人的社会性本质,其原因就在于他的哲学的出发点是感性直观。
马克思之所以不满意于费尔巴哈哲学,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是把感性活动即实践作为其哲学出发点的,在此基础上批判了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各自的片面性。马克思哲学立足于感性活动,通过人的实践的能动建构,使人的存在获得了自我展现的内在可能性;如此一来,历史便在马克思语境中“活”了起来,人的此在性也被“实践”了出来。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比,在马克思哲学那里,人就由抽象的感性客体、思辨的、精神的人格化转变为真实的历史存在。
(二)“立脚点”:是“市民社会”还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在《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3]正如有学者早就提示的,“这里所说的‘社会’,‘同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并不是一回事’,它‘实际上是指马克思当时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4]而共产主义社会指的就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4]简言之,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本质实现了自我复归,人因而成为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而不再是异己化的、自我分裂的人。同时,在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所揭露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诸如存在与本质、能动与受动、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类等等,也得到了最终消解。
我们再来看看市民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市民社会这个概念虽由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但直至黑格尔才在哲学上将其正式确定下来。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领域,他将其称为“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5]。同时,马克思也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个人只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只为他而存在。”[6]在相互需要、互为手段的格局中,手段代替了目的,这成为市民社会特有的标志。同时,在市民社会中,人的一切关系都变成了可以计量的、可以算计的,以利益获得的大小、多少,来决定行为的选择和人的价值。因此,以物的依赖性为特点的社会取代了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点的社会,人不能不面临被物化的命运。其结果不是人控制物,而是物占有并支配了人。
作为19世纪德国杰出的思想家,费尔巴哈当然不会对市民社会这一异化现象视而不见,但“他主要是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解释社会现象的”[7]。立足于市民社会这个角度,所能够看到的人,其特征只能爱慕虚荣、贪婪、投机、不思进取。然而,费尔巴哈对此无可奈何。他只有大声疾呼我们都是人,应该彼此友爱。任凭费尔巴哈如何解释、揭示市民社会中的人的异化状态,人们的生存状况丝毫也不可能得到改变。
在费尔巴哈那里,“爱”被本体论化。费尔巴哈认为,“只有在感觉之中,只有在爱之中,‘这个’——这个人,这件事物,亦即个别事物,才有绝对的价值,有限的东西才是无限的东西:在这里面,而且只有在这里面,才有爱的无限的深刻性,爱的神圣性,爱的真理和实在。”[8]但是,费尔巴哈所谓的“爱”,不过是脱离了社会和历史条件约束的、从而是抽象、空洞、贫乏而苍白的规定。正如恩格斯调侃费尔巴哈时所说的那样,“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9]费尔巴哈根本想象不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境界,看不到这一切矛盾的消解需要通过实践的批判才是可能的。他对市民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异化现象都是痛恨的,但也只不过是痛恨而已。
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清算
恩格斯认为“旧稿(指《德意志意识形态》——引者注)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11],而马克思认为旧稿“已经弄清了问题”[12]。一个说弄清了问题,另一个则说缺少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对待这一问题的不同立场,表现了二者的思想差别。恩格斯显然低估了“旧稿”对费尔巴哈哲学所作的清算,这也正是他何以还要写《终结》的重要原因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旧稿”的不同评价,折射出他们对费尔巴哈哲学缺陷的判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性。
恩格斯认为,费氏哲学的缺陷是其非历史性,即在自然观上因缺少辩证法而陷入形而上学,在历史观上因未能将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领域而陷入唯心主义。因此,费尔巴哈“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13]。
(一)自然观:是形而上学的还是辩证法的?
恩格斯借助于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清算了费尔巴哈哲学的非历史性。首先,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把建立在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特定理解的世界观同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相混淆了。”[14]
18世纪旧唯物主义最大的缺陷在于采用“还原论”的方法来机械地、静止地看待问题。恩格斯说其特征“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它“从力学的角度来衡量化学性质和有机性质的过程”[15]。恩格斯认为其原因就在于,“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固体(天上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力的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的地步。化学刚刚处于幼稚的燃素说的形态中。生物学尚在襁褓中;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只作过粗浅的研究,并用纯粹机械的原因来解释。”[16]要言之,即自然科学的不发达,自然科学发展的滞后。
费尔巴哈因为未能及时看到科学领域的三大发现,他在思考问题、看待人类社会时所采取的仍然是还原论的方式。费尔巴哈将黑格尔思辨的唯心主义从天国转向尘世,将抽象的绝对精神还原为自然,将宗教哲学中的上帝还原为人,他以为“我们只要将主词与谓词相颠倒,真理就能获得”[17]。同时,费尔巴哈未能将“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而这是由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以及反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造成的”[18]。其实,费尔巴哈哲学不是没有辩证法,只是没有被恩格斯所发现罢了。例如,在关于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上,费尔巴哈说“我们还没有认识的东西,我们的后代一定会认识到的”[19]。在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辩证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只有存在与本质结合、直观与思维结合、被动与主动结合、法国感觉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经院派的热情原则与德国形而上学的经院派的冷淡态度结合起来的地方,才有生活和真理。”[20]在关于世界是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联系的问题上,费尔巴哈说:“自然到处活动,到处化育,都只是在内在的联系之下,凭着内在联系而进行的。”[21]很难想象,恩格斯为何会对这些观点视而不见。
费尔巴哈并不是采取形而上学的方式看待问题的,他采取的是直观的视角。直观的并不一定就是形而上学的,直观的也可以是辩证的。恩格斯要求我们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自然,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这并非费尔巴哈哲学缺陷的要害之所在。
(二)历史观:是历史唯心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
在历史观上,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不仅没有使社会科学同唯物主义相协调,而且也没有在唯物主义这个基础之上,对社会科学进行改造。费尔巴哈因此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在恩格斯看来,只要在历史领域坚持唯物主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就可以“在这里开辟出来”[22]。从此之后,历史便也得到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恩格斯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运用,无形当中,恰恰将历史与人的存在割裂开来;这种二分法反而强化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显然,一直追随马克思的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未能达到马克思致思的合题取向。
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之所以没有在历史领域运用唯物主义学说,从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其主要原因是费尔巴哈孤独的生活环境所导致的。如果说,施达克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时,找错了地方,那么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分析也未必恰当。
费尔巴哈选择孤居乡野,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因此,“他才不仅在自己心灵的深处保存着独立的精神,而且外观上也避免了城市生活的抑郁沉闷、卑微的阴谋攻奸和造谣中伤。”[23]晚年的费尔巴哈在回忆自己生活经历时再次谈到,“我生活中最好的一段时间不是在讲坛上,而是在乡村中度过的,不是在大学教室里,而是在大自然的殿堂中度过的;既不是在沙龙中,也不是在觐见中,而是在我独居时的工作小室内度过的。”[24]正是由于孤独乡居的25年,费尔巴哈才真正有机会来细细研读大自然这部伟大的作品。可见,孤寂的生活,并不是费尔巴哈哲学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原因。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费尔巴哈哲学的差别
上述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清算费尔巴哈哲学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诊断的病因不同,开出的药方自然有别。
马克思把感性直观这一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改造为感性活动(实践),将实践作为自己新哲学的本体范畴。
实践,具有其它本体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首先,实践具有生成性与开放性,它是活的,而感性直观到的感性对象,是死的,静止的。以感性直观为出发点,丧失掉了哲学应有的生机与活力。其次,实践与人的“此在性”相联,以实践为本体,使哲学回到了人的存在。实践之所以具有生成性与开放性,根源就在于它与人的存在相联,是人的存在赋予了实践的生成性与开放性。再次,实践恢复了“时间性”的维度,破除了费氏哲学直观、僵死地思维定式,使历史与实践相接洽。
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既是其逻辑的出发点,又是其历史的出发点。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于实践本身。历史是逻辑建构的内在基础,而逻辑则是对历史的反思形式。没有历史的建构,逻辑就是无源之水;没有逻辑的反思,历史也将无法被人类所把握。
从历史层面,马克思哲学所说的实践,指的就是人的感性活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5]离开了人的实践、人的感性活动,人类历史将不会存续下去。同时,将实践作为历史的出发点,历史就不再是与人的活动无关的纯粹的、抽象的思维活动,也不是亘古未变的一堆僵死的事实的汇集。实践建构了历史、成就了历史;毋宁说,没有实践,也就没有历史。历史不过是实践的表征方式而已。
从逻辑层面说,马克思哲学就是实践本体论。本体论是关于“在”的学说,主要探讨的则是“在”与“在者”的关系问题,即“在”如何“在者”出来,“在者”如何“在”。马克思哲学将实践作为其哲学的本体,以此与人的存在相联,万物因实践而“在”,通过实践“在”了出来。在这里,实践不仅具有绝对性,同时也具有能动性。它先于一切二元分裂,而一切二元对立由它生成、展现,最后又回归于它。简言之,实践本体论不过是对历史的反思性地把握。
针对费尔巴哈哲学将其立足点定位于市民社会的直观立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立足于理想的亦即人性实现了复归的社会。”[26](共产主义社会)致力于改变世界。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共产主义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理想化状态,在那里一切二元分裂得到了消解,人的本质得到了复归。由于立足于共产主义社会这一高度,马克思才能俯视市民社会的一切缺陷,从而对其采取批判的姿态。同时,马克思之所以能将立足点放在共产主义社会这一高度,原因就在于其出发点是实践。共产主义作为一切二元对立的最终消解,无疑是由实践来完成的。没有实践的自我生成与自我消解,共产主义作为一切二元分裂消解的说辞,则是不可能的。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作为出发点的实践与作为立足点的“社会的人类”,二者是相互缠绕、相互影响的。马克思将清算费氏哲学的重点放在了出发点与立足点上,因此,才成就了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出发点的不同,决定了立足点的差异;立足点的分歧,又造成了哲学目标的分殊。
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清算有别,恩格斯的清算工作集中在了其非历史性上,认为只要恢复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历史性,就能够拯救它。恩格斯致力于从自然观与历史观这两个角度来清算费氏哲学。
在自然观上,恩格斯试图恢复费尔巴哈所丢失掉的的辩证法。他认为只要将自然界看作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并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将自然界进一步抽象为物质,其缺陷就可以消除了。同时,他将改造唯物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上。恩格斯认为,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唯物主义必将改变自己原有的形式,旧唯物主义的不科学性就可得以清除,唯物主义哲学就能够得到挽救。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差异在于其原初基础不同,而非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否。当然,不可否认,自然科学是否发展,对哲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这并非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如果不置换掉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原初基础,即使自然科学再发达,唯物主义哲学的性质也不可能得到改变。哲学是一门反思性的学问,它具有批判性,而自然科学是求真、求是的学问,二者的学科性质不同。如果将哲学的发展与否建立在自然科学这个基础之上,那么,哲学也将会丧失其应有的批判特质。
在历史观上,恩格斯致力于改造费尔巴哈哲学的历史唯心主义性质。他认为只要将费氏哲学建立在唯物主义这个基础之上,从唯物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历史,恢复辩证法在历史观领域中的运用,将人类社会看作如同自然界那样,具有自己的发展、变化过程,“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27]如上所述,将费氏哲学在历史观领域的缺陷归结为辩证法的阙如,是不恰当的。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28]费氏哲学不是没有辩证法,而是由于没有贯彻实践的观点。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读历史,固然比采取唯心主义的立场解读历史有其进步性,但这只是解读世界一种方式而已,根本不能达到“改变世界”的宏达目标。
四、马克思恩格斯清算费尔巴哈哲学差别的原因
上述可见,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如何清算费尔巴哈哲学这一问题上,是存在着明显分歧的。将他们的差别解读为“个别具体内容和思维向度上”[29]的差别,显然是避重就轻,不利于还原马恩二者哲学的本来的面目。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在哲学上都曾受惠于费尔巴哈,同是清算费尔巴哈哲学的两部经典著作,清算的差别为何如此之大呢?笔者以为,这主要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立场不同所造成的。
从总体上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采取的是超验的哲学立场,而恩格斯采取的则是经验的、实证的知识论立场。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乃是对当下现实的反思。作为一门反思性的学问,只能是超验的,而不能是经验的、实证的。超验是哲学成其为哲学的内在理由和甄别标准。实证的、经验的思维方式是自然科学必备的,但不是哲学应当具有的。而且,正像马克思所说,“是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批判的”[30]。哲学的批判本性,也要求它必须克服实证性的局限。自然科学作为实证科学,将唯物主义哲学建立在其之上,哲学就会失去其反思、批判的特性,变为一种关于实证知识的学问。恩格斯立足于实证立场,所以自然会“将自然科学的发展看作是唯物主义发展的前提与基础”[31]。
马克思哲学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将实践作为逻辑与历史的出发点,通过实践,一切二元对立因此而展现,同时也由此而消解,最后又复归于实践。人与历史通过“实践”而“在”了出来。从实践出发,不仅恢复了被唯心主义者抽象发展了的人的能动性,也恢复了人的现实性,从而打破了唯物与唯心二元对立的格局。实践不仅创造新事物,同时也否定旧事物,真实的历史正是在实践的辩证法中被建构起来。而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2]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实践与批判是一体两面的,说一个东西是实践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批判的。马克思由此找到了其哲学批判品格的内在理由与原初基础。将实践作为出发点,既清算了唯物主义又清算了唯心主义,跳出了唯物与唯心对立的这个窠臼,使其消解于实践这个“阿基米德”点。
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则把抽象的物质作为其哲学的本体范畴,试图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关系,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归结为哲学基本问题,未曾超越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晚年的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的信(1884年7月)中“将马克思的这种超越唯物与唯心的对立,寻求二者统一的尝试,斥责为陈词滥调。”[33]
恩格斯不满意于费尔巴哈的只是他的唯物主义哲学中缺少辩证法,非历史的看待自然与社会,因此,恩格斯极力提倡辩证法在自然观与历史观的上的运用。而马克思则不然,他对费尔巴哈的辩证法是相当认同的。在历史观上,马克思同样认为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的,但原因并非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是由于费尔巴哈未在历史观领域运用、推广唯物主义,而是实践立场的缺失。马克思批评道:“当费尔巴哈看到病态的社会与穷困的普通民众时,他只能求助于最高的直观与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则会用诉诸于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34]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指的就是实践的批判与改变,而不是通过爱的呼唤。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实践的不在场是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根本原因而非辩证法的阙如,但这并未被恩格斯所理解。
恩格斯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运用而产生的。并将其与辩证唯物主义对立起来,而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因为,历史是由实践建构的,没有实践的生成,就不会有历史的产生。同时,实践本体论则是对历史的反思性把握方式。
哲学出发点的差别决定了对费尔巴哈哲学清算的成功与否。马克思丰富的知识涵养,采用超验的哲学视野,将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由感性直观转化为感性活动,将其立足点由市民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原初基础与最终归宿逻辑地、历史地、反思与批判市民社会的异化,关注人的生存与人的本质的复归。恩格斯采取实证的、经验的知识论视野,从自然观与历史观的非历史性出发,揭示了辩证法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并将其运用于历史领域。由于二者的哲学立场的不同导致了对费尔巴哈清算的不同,二者相比,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清算更为深刻,恩格斯的则较为肤浅。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清算所体现出来的差异,并不仅仅局限于本文所述及的方面。他们在清算费尔巴哈的宗教观、伦理观、真理观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可无视的差异。因主题和篇幅所限,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