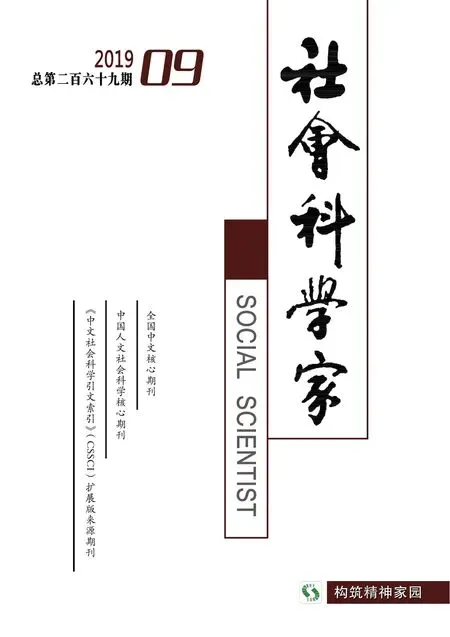消费文化与女性网络文学的变奏
2019-02-19李敏锐
李敏锐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文化转型不断受到两大力量的影响,一是消费社会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逐步确立其主导地位,二是互联网以不可阻挡的速度覆盖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民众的必需品。这两大力量共同引发着社会发生巨变,不仅仅表现在现实生活层面,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社会文化转型已成不可争辩的事实,文化的独立品格不断被消解,消费文化借助互联网以一种强有力的姿态渗透至社会生活内。西方学者丹尼尔·贝尔曾揭示过“在市场成为社会与文化的交汇点之后……经济逐渐转而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示的生活方式……以便提倡享乐型生活方式,诱导人们去满足骄奢淫逸的欲望。”[1]女性是消费市场最受欢迎的群体。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不断往前推进,令女性得以摆脱繁重家务的束缚,逐渐参与到社会运作中。相较于20世纪,新世纪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获得较高的提升,女性越来越成为独立的消费者,市场上大量的化妆品和服饰销量便是最好的证据。“据国泰君安证券此前的测算,2015年中国女性经济市场规模接近2.5 万亿元(人民币,下同),2019年预计达到4.5 万亿元,并且在未来十年内仍潜力巨大,有望成为市场的主流风口。”[2]另一方面,有些女性还拥有社会某些重要事件的话语权:“有资料表明,在中国中产阶层中,中上层男性比例较高,中下层女性比例则比较高。而且两性在文化资源的获取方面已然日益平等化。”[3]
新的社会文化结构催生出新的文学形式。网络文学以开放性与平民性在消费社会里获得了高速发展和流通。被传统文学拒之门外的文学青年利用互联网自由创作的环境,抛弃传统文学的框架和束缚,全凭自己的兴趣和喜好来选择写作题材,这是社会文化解放的一种表征。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过“小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妇女最易写作的东西。其原因并不难找。小说是最不集中的艺术形式。”[4]伍尔夫认为小说创作完全可以写一阵停一阵,这并不影响整部小说的连贯性,所以“乔治·爱略特丢下了她的工作,去护理她的父亲。夏洛蒂·勃朗特放下了她的笔,去削马铃薯。”[4]网络小说实现了“写一阵停一阵”的小说创作方式,智能手机的诞生和普及更令小说创作变得“随时随地”,现代女性更容易参与到小说创作之中。2004年,网络文学VIP 收费制度的确立,使得网络文学成为一种可以被消费的商品。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读者欲求”成为网络文学创作者最需要满足的目标,并因此导致网络文学进行了更细致的类型划分,用来满足读者的不同欲求:玄幻类、仙侠类、历史类、穿越类、古代言情类、现代言情类等等。读者在阅读一部网络作品时,是否能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足够的“爽感”,成为评判一部网络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准。这种评判标准纯粹从消费主义和盈利角度出发,完全抛弃传统文学的精英性标准,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学界的批判。但依然要指出,商品化的网络文学是以满足民众的情感需求为主旨,这是当代消费社会和社会意识的一种深刻反映,也是对当代文学的一种有效的补充。女性网络文学作为当代中国女性文学中的一部分,它从诞生之初就极难摆脱消费社会和男权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它既是女性意识的表达又超越女性意识,它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中国女性文学获得了更广阔的叙事视野和生命视域,也是中国女性文学成长和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本文将从“网络都市言情小说、网络宫斗小说、耽美文、女尊文”四种最热门的类型文对女性网络文学进行分析,阐释处于消费文化下女性对两性建构的新姿态,这些新的叙事文本又是如何与消费文化的语境发生关联的。
一、网络都市言情小说:从总裁到小市民
互联网改变最多的地方是城市。信息交流变得快速便捷,年轻人完全抛弃父辈们循序渐进的认识方式。另一方面,“性自由”逐渐从隐蔽话题变成现实。日渐发达的医学手段和避孕工具的普及,令性行为与生殖行为可以完全分开,年轻人抛弃对性爱的敬畏之心,只通过性交行为享受快感而不用付出婚姻和生殖的代价。两性关系中最重要一环“性行为”发生改变,必然会影响到传统情爱伦理关系质变。女性作为男女性行为的一方,也享有性自由。需要指出的是至今为止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女性文化革命,导致中国女性特别是都市女性在实际行为中出现了对自身性别认识的迷茫,“在漫长的男性规范作为唯一的行为与性别规范的岁月中,在分裂的自我与双重性别角色的重负下,多数妇女已对空泛而虚假的“妇女解放”的现实与话语感到了极度的疲惫。”[5]女性心理构建尚未完工,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令每个人不可避免被卷入消费社会进程中。一方面,女性的就业机会比过往增加许多,女性的经济收入获得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女性又无法马上撕掉被男权社会贴上的“弱者”标签。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女性不再对男权社会下的两性关系模式全盘信任,对于“最平庸的男性面对女人也自以为是半神”[6]这种论断更是抱着可疑的态度,可是又在经济和精神上依赖男性。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继承和创新“台湾言情”的第三代女性网络作者①2000年以前出现且比较活跃的女性写手视为第一代;2000年至2003年出现并比较活跃的女性写手视为第二代;2004年至2008年出现并活跃的女性写手视为第三代;2008年后出现的女性写手视为第四代,参见欧阳友权主编.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C].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00页。所描绘的“男强女弱”相处模式就像“安慰剂”一样安抚了女性的矛盾心理,暂时满足了女性对完美两性关系的幻想。
匪我思存是第三代网络都市言情小说代表作者之一,她的代表作《千山暮雪》是典型的总裁文②“总裁文”是言情小说较为流行的题材类型。男主角一般是企业CEO 或者其他高管人员,帅气多金,且往往兼具腹黑、冰山、偏执等属性,因此又被冠上“霸道”之名。参见邵燕君主编.网络文学经典解读[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9页。。女主角童雪的父亲因为操作失误导致莫氏企业破产,男主角莫绍谦被迫与慕家女儿慕咏飞结婚来搭救自家公司。莫绍谦借着童雪舅舅有商业把柄在自己手上,把童雪困在身边并占有她。俩人在相处过程中,莫绍谦渐渐爱上童雪。童雪明知莫绍谦是“强奸犯”,但是她依然委身于他,甚至还对他产生了感情:
“神智渐渐恢复,我才发现自己失去了什么,我蜷缩在床角紧紧抓着被子,绝望得只想去死。而莫绍谦穿着浴袍从浴室出来,若无其事地对我说:‘洗个澡再回去,你这样子会被人看出来。’
我想杀了他,随便用什么,哪怕要杀人偿命也好,我只是想杀了他。他却走近我,我全身发抖,想要抓住床头灯,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往他头上砸去,而他只是俯身拍拍我的脸:‘明天记得准时,不然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7]
童雪被莫绍谦侵犯时,她并没有反抗,更没有报警,而是继续委身于莫绍谦,成为忍气吞声的“小三”,其中的原因除了“舅舅把柄在他手上”,作者给予读者最大的暗示其实是莫绍谦的物质财富诱惑。这种建立在物质财富上的情爱关系是霸道总裁套路文的根基。男尊女卑并不是男女关系中的固定模式,而是“两性间的相对关系,是在差序格局的人伦关系网中生成的。”[8]女性创作者本该打破这种两性模式,应该宣扬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特性,但事实上她们却利用女性慕强的心理,令笔下的女主角通过最便捷的获取财富方式——出卖身体,来获取财富和社会地位。女性读者阅读此类小说会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并幻想自己也可以遇见霸道总裁,从此改变自己的命运。读者欲求刺激着作者创作,大量都市言情小说描绘着这种“男财女貌”的爱情故事,为读者制造美好的欲望世界。文学本该从生活中汲取养分,记录生活又高于生活,但总裁文却箍住了作者和读者的视线,对于读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现实生活来说也是有失偏颇。一旦“安慰剂”药效过完,女性读者从“霸道总裁只爱我”的套路文提供的快感中苏醒过来,意识到自己这辈子都无法遇上一个“只爱我一个人的霸道总裁”,最终发觉这只是女性一厢情愿编织的自欺欺人的美梦,这一类型的套路文就难以为继了。
晋江文学城最先出现脱离“传统霸道总裁文”的群体动作。2004年前后,晋江文学城的耽美文和女尊文逐渐定型,并成为两个独立的类型文。耽美文和女尊文是对“传统霸道总裁文”的男尊女卑爱情模式最大的反抗。从耽美文和女尊文的出现可以看出年轻女性对传统两性关系已经出现强烈的质疑,她们不再享受“男强女弱”的爱情模式。第四代网络都市言情女作者在这个背景下崭露头角,她们更加愿意让笔下的女性在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在第四代女作者的笔下,男主角并非全是“霸道总裁”,他们有可能位于社会最底层,有可能还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而女主角不再是一味“傻甜白”,她们是互联网时代下的独立女性。相较于第三代作者笔下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角色,第四代作者更愿意用“小市民”的视角来进行创作,反而更加贴近俗世生活。必须要指出的是,第四代女作者笔下的“小市民”与8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中的“小市民”角色还是存在极大的区别。新写实小说诞生于改革开放前后,它以反映真实生活为目的,不再刻意追逐生活的意义,关注生活本身和人的生存困境。比如王安忆的《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池莉的《不谈爱情》《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等等,都是以小市民的视角来描述日常生活。第四代都市言情女作者们大多数出身于90年代,她们是互联网时代下成长的一代。相比她们的母亲那一辈人,这一代年轻人更加愿意以匿名的身份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见解:因为互联网的特性,她们可以隐匿自己的真实身份,反而更可以畅所欲言。她们要表达的“小市民”含义更接近于“废柴”①网络用语,“废柴”或写作“废材”,源于粤语,在ACG 及网络中用于指百无一用、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废人。参见邵燕君主编.网络文学经典解读[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4页。。
2016年起,Twentine 在晋江文学城连载作品《打火机与公主裙》,男主角李峋不同于传统网络都市言情小说里的“霸道总裁”,他出身于社会底层,凭着自己的能力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女主角朱韵父母都是老师,家教严格,循规蹈矩,李峋的出现让她重新审视自己的理想,并最终重新认同自己的身份。她与李峋这段爱情并不是传统的男强女弱关系,就像女主角自己讲的那句话:“我除了是他的女朋友,我还是平均绩点全班第一的人,我选择跟他,并不只是爱情。”[9]与第三代都市言情女性作者相比,第四代作者更愿意尝试建立新的情爱模式。这种写作主题的改变与消费社会对社会生活的改造有着莫大的关系。获得经济独立的女性写作者尝试着探讨女性的生活困境、社会地位及未来规划。爱情不再是第四代都市言情女性作者笔下最重要的事,她们更加愿意笔下的女性人物为了实现自己理想而活着。
二、女性权谋论:宫斗小说
“宫斗”小说属于网络古代言情范畴,于2007年左右从“女性穿越小说”中独立出来。“宫斗”从字面上来解释,主要指古代后宫不限于嫔妃、婢女、宦官、侍从等以及她们身后的家族成员为了争夺皇室特权和财富之间的斗争。有研究者将“宫斗”定义为“以事实存在或者虚拟架空的古代宫廷为背景,主要讲述与后宫争斗、妃嫔争宠、前朝禁苑息息相关的情感纠葛或权力倾轧的网络小说,称为‘宫斗小说’或者‘宫斗文’,同种题材的古装电视剧则称为‘宫斗剧’。”[10]宫斗小说的创作者多为女性,比如流潋紫(代表作品《后宫·甄嬛传》《后宫·如懿传》系列)、瞬间倾城(代表作品《未央浮沉》)、爱打瞌睡的虫(代表作品《宫斗》)、水心清湄(代表作品《后宫升级记》)、慕容湮儿(代表作品《倾世皇妃》《眸倾天下》)等。《后宫·甄嬛传》是宫斗小说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集合了之前所有“宫斗”元素,标志着宫斗这一类型小说自此走向成熟。女主角甄嬛因选秀入宫,攀升的过程如同升级打怪的电子竞技游戏,途中必然遭遇各种的阻挠,甚至中途她还遭受陷害不得不“出宫礼佛”来求生。英雄救美是女性作者最喜欢用的剧情设定,遭遇人生低谷的甄嬛意外收获了皇上弟弟玄清的爱慕,玄清为了保护甄嬛,偷换毒酒,愿意为甄嬛失去性命。甄嬛最终打败了所有竞争对手,就连皇上也及时死去,令她爬上后宫的最高位置。《后宫·甄嬛传》后来被改编成连续剧《甄嬛传》(导演郑晓龙)获得空前的成功,甄嬛不是传统伦理道德下的中国女性角色,她有仇必报有恩必报,对付陷害自己的人毫不心软,她最后达到权力顶峰也是借用了皇上对她的迷恋之情,完全抛弃了中国古代“才子佳人”的爱情模式。之后,流潋紫又写了同类型小说《后宫·如懿传》,女性欲望得逞的规模更加宏大。依然是熟悉的宫斗剧情,女主角如懿与皇上青梅竹马,但是因为各种权利交易,皇上不能独宠她。后宫权位高低一向与皇帝的恩宠挂钩,各路嫔妃为了个人生存和家族利息,拼命争夺皇上的宠爱,如懿遭遇各路利益代表者的陷害,最后她如甄嬛一样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成为宫斗胜利者。
宫斗小说的畅销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无不相关。在市场经济运作下,私营企业数量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偏向于选择企业就业。私营企业强调公平竞争,以“盈利”作为审核员工的标准,职场女性为了在职场站稳脚跟,必须与男性一起争夺有限的资源,尔虞我诈的竞争成为职场常态。宫斗小说的场景如同复杂的职场,如果能获得皇上的宠爱,意味着嫔妃及她身后的家族都能享受皇族特权和荣华富贵。在宫斗小说中,扮演女性欲望对象的是男性及他身后的权力和财富,女主角为了得到想象中的完美男性,必须与各种女性进行斗争。在这个争夺宠爱的过程中,女主角获得同性嫉妒和异性爱怜,女性读者在阅读时获得极大的“爽”感。有学者如此评价:“宫斗戏与某些职场规则不谋而合。建制上,新入宫的众女角如同职场新人:有理想、单纯又有野心,而皇后贵妃和其他男性贵族活像一个深知内幕的企业高管,皇上如同总裁。大家围绕着皇上,抢山头,争靠山。这种与职场潜规则如出一辙的斗争方式,很容易引起新一代小白领的身份认同。而且在这样的争斗里,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除了斗,你别无选择。这与职场的相对封闭性和复杂性极其相似。为生存,每个人到最后都变得有心计,有手段,没有能独善其身的胜利者。而宫斗戏里的权力利益都是捆绑在性这一驱动力上,使这场斗争在血雨腥风之外还尤其香艳。”[11]二十年前,同样是由郑晓龙参与拍摄的连续剧《渴望》,女主角刘慧芳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形象,她的性格与有仇必报的甄嬛截然相反,无论是面对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小芳,还是忘恩负义的丈夫王沪生及薄情寡义的小姑子一家,刘慧芳都是毫无保留的付出真心。尽管如此,刘慧芳一生却过得极其坎坷,好人没有得到好报。刘慧芳饱受生活折磨,却依然不改善良淳朴的品格,勇敢地承担生活重担,刚经历了十年动荡时期的人们在刘慧芳的身上看到了传统美德存续的可能性。时代在变化,财富分配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并进一步激发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渴望。金钱的能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揭示着人性的复杂性,彻底改变社会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刘慧芳这种善良隐忍的传统女性并不太符合争强好胜的现代职场女性形象,甚至年轻一代的女性还给刘慧芳这样没有底线的善良女性取名“白莲花”①“圣母”和“白莲花”含义大体相同,均用来形容和讽刺文学、影视作品中大量出现的一类女性角色:温柔善良,逆来顺受,毫无心机,同情心泛滥,对爱情忠贞不渝,总是无原则地原谅所有伤害过的她们的人,并试图以爱和宽容感化敌人。参见邵燕君主编.网络文学经典解读[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0页。,在她们的定义里善恶不分的白莲花是无法在职场里获得最后的成功。
宫斗小说及它的影视衍生品极大地满足了大众特别是年轻女性读者的精神宣泄,它将中国古代传统与现代独立女性意识相结合,女性读者在阅读这些小说时能够寻找到一种强烈的“代入感”。但是依然要指出的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历史背景上的宫斗小说存在着大量与历史不符甚至相悖的文字内容,为了让读者在阅读中找到游戏升级般的快感,不惜大肆宣传人性恶和权谋论,“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比坏人更坏才能战胜坏人。”[12]这些文本折射出来的价值观无疑会误导大众审美观,从长远来看必然会对行业生态健康发展和民族文化自信、社会伦理道德造成不良的影响。“2011年《甄嬛传》以每集30 万元创下当年版权最高单价;2018年《如懿传》飙升至每集900 万元,版权价格在六七年时间里翻了近30 倍。相反,优质现实题材剧单集版权价格普遍在500 万元左右徘徊,两者几乎相差一倍。SMG 尚世影业资深制片人崔轶认为,宫斗剧天价版权向市场传递错误信号,导致市场失去理性,引发行业盲从。”[13]消费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建立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当市场调节较弱或者调节不完善时,需要政府进行政策性的调控。社会文化的发展要避免被利益裹挟、被资本绑架。文学作品需要反映民生的主流评论声音,而不是单纯依靠消费者的反馈。2017年9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改委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14],特别针对注水剧、宫斗剧、翻拍剧、演员高片酬等问题,大量宫斗剧遭到下架处理,这也是宫斗小说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性别颠覆:耽美文与女尊文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人们把女人称为le sexe,意思是说,在男性看来,女性本质上是有性别的、生殖的人:对男性而言,女人是sexe,因此女人绝对如此。”[6]历史的种种都是在男权统治下进行,人们认为女性的生理构造导致她必须去承当生育和抚育后代之苦。林语堂在其著作《吾国与吾民》里提到:“社会上坚决的主张,即如奴婢到了相当年龄,也应该使之择偶。婚姻为女子在中国惟一不可动摇的权利,而由于享受这种权利的机会,她们用妻子或母亲的身份,作为掌握权力的最优越的武器。”[15]女性通过婚姻离开原生家庭的父权统治,进入了另一个家庭成为女主人,看似摆脱了父权的控制,但是如果她没有为这个家庭生育子女,那么女主人的地位可能就会被剥夺,甚至还会被赶出家门,由新的女主人替代她的身份。《大戴礼记·本命篇》把不能生育子女视为可以休妻的正当理由:“妇有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市场经济的发展,令大量女性得以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变革,女性拥有了比之前更多独立选择和发展的机会,甚至她们还可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和男性同等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从20世纪末开始,社会转型加剧,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变化,逐步形成多元化的社会格局,原有的传统两性模式受到巨大冲击。1994年,林白发表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女主角多米从小到大一直迷恋女性的身体,林白从女性视角出发大胆地把男性排除在情爱关系之外,这种离经叛道的叙事文本在当时社会造成了轩然大波,甚至被人冠上“黄书”的恶名。一年之后陈染带着她的《私人生活》出场,进一步书写了女性同性恋之间的私密情话。这些公开颠覆男性在两性模式中的统治地位的叙事文本最终会受到社会传统道德伦理的批判,《私人生活》的女同性恋者最后戏剧性的和另一个男人发生了关系,这也可以看作陈染对世俗伦理观的一种妥协。网络文学创作“3W”特征(无身份、无性别、无年龄)为女性对现状不满的宣泄创造了条件,无论是文学创作者还是阅读者不但可以隐匿自己的真实性别,还可以通过文字暂时改变社会现有的两性模式。传统“男强女卑”霸道总裁文不能满足心理年龄日益成熟的独立女性读者,她们渴望与男性一样拥有事件的话语权,于是耽美文和女尊文这两种类型文开始崭露头角。
耽美小说,又称 BL 小说(Boys'Love)。“耽”的意思是“沉溺、沉迷”,《诗·卫风·氓》有“士之耽兮”,指的是男子沉迷于爱情。“耽美”是沉迷于美,但是自从“耽美”作为日语TANBI 的中译词之后,“耽美”的含义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特指男性之间的爱情。有学者对“耽美小说”一词做过如下的解释:“主要由女性作者写作、以女性读者为预设接受群体的男男同性爱情或者情色故事。一般根据时代背景划分为现代耽美和古代耽美(或古风耽美)两大类。”[16]笔者采纳这个定义。日本的耽美文化最开始是以漫画形式进入中国,直到90年代末期,日本耽美小说才借助互联网的传播进入中国大陆。随着中国网络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国产“耽美小说”迅速扩张,完全覆盖日本“耽美”小说在大陆的影响力,并形成自己的“耽美”文学。晋江文学城专门开设了耽美同人站,旗下设有现代耽美频道、古代耽美频道等6 个子频道。这是中国大陆地区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耽美小说站点,拥有众多的耽美小说写手,比如priest(代表作《镇魂》)、巫哲(代表作《撒野》)、大风刮过(代表作《桃花债》)、墨香铜臭(代表作《魔道祖师》)等等。耽美文与传统文学中描写男同性恋的小说不同,耽美文创作者的主观目的并不是反映现实社会中男同性恋们的真实生活,大部分耽美文是女性作者幻想出来男男相恋的爱情模式。耽美小说里的角色分为“攻”(日语:め)和“受”(日语:け),虽然二者都是男性,但是在性格上却分为“雄”和“雌”。“攻”处于主动方,拥有攻击力,可以理解为“雄”;“受”是出于被动方,被动接受,可以理解为“雌”。女性创作者包括阅读者借着“受”的男性外衣,大胆地进入了男权社会,暂时摆脱了男权社会下女性肉体被消费的困境以及女性生育和抚育后代的困苦,获得一种“爽”感。
女尊文顾名思义:以女为尊。有学者如下定义:“以架空的方式建构一个以女性为尊、以女性话语为主体的时空背景,女主角的社会地位高于男主角,或女主角的能力强于男性,由此形成‘女尊男卑’的相处方式,甚至发生女性奴役男性、男女颠倒、男性生子等情节,暗示了激进的女性主义倾向。”[16]笔者接受这种定义。与耽美文不同的是,女尊文里的角色生理属性依然是男性与女性两种性别,只是整个社会的性别秩序被颠倒过来。关于女儿国最早的记载可见于《山海经·海外西经》:“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17]《大唐西域记》中也有关于女儿国的记载:“此国境北大雪山中,有苏伐剌拿瞿呾罗国(唐言金氏)。出上黄金,故以名焉。东西长,南北狭,即东女国也。世以女为王,因以女称国。夫亦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种而已。土宜宿麦,多蓄羊马。气候寒烈,人性躁暴。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18]这些记载给后来的网络女尊文提供了传统文化的源头。根据生育来划分,女尊文可以划分为:男性生育与女性生育两大类型。男性生育文可以说是男尊女卑社会的翻版,只不过由女性控制社会话语权,这一类型的代表作品有:《四时花开之还魂女儿国》《青之翼》《湖畔饮烟》等。女性生育文大多是以未来幻想文为主,女性在体力上大大超过男性,或者掌握了最先进的毁灭性武器,但是女性的生理构造没有改变,整个社会依然是女性生育后代,这一类型的代表作有:《男女颠倒的世界》《姬的时代》。这些女尊文给女性读者提供一个充满欲望和权力政治的空间,实现女性自身价值范围的扩大与增值。
耽美文和女尊文的情爱叙事都是对传统两性模式的颠覆,但是这种文字上的颠覆仅仅是女性的美好愿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现实社会的话语权被男性牢牢掌握,所以这种假设的快感持续时间并不太长久,女性读者很快就发现耽美文和女尊文描绘的世界非但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更像是父权概念的偷换。耽美文中的“受”角色其实是披着男性外衣的女性角色,女尊文里的“霸道女总裁”其实是当下社会里男性霸权的投射。再加上某些作者刻意用性行为和奢侈生活场景做噱头来吸引女性读者,这种超意识文本的创意写作虽然能在短时间内能吸引到注意力,但因与中国传统性别伦理相悖,必然会受到社会传统道德的谴责。这种离经叛道的叙事文本一旦泛滥,势必会影响到整体市场的运作。女尊文在2008年前后达到鼎盛时期,之后就逐渐呈下滑趋势。2014年净网行动之后,网络最大的耽美文聚集地晋江文学城把耽美文这一类型文本拆散再合并进纯爱文类型中。
四、结语
正如理查德·霍加特所说:“一部艺术作品,无论它如何拒绝或者忽视其社会,但总是深深地根植于社会之中的。它有其大量的文化意义,因而并不存在‘自在的艺术作品’那样的东西。”[19]消费社会的发展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自由,也为女性写作提供了更多的背景和写作空间,拓展了女性小说的叙事维度。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强调文学的精英性,警惕消费文化对文学的侵蚀。网络文学作为一种商品化的叙事文本,在商业利益的熏陶之下的确存在很多粗制滥造的现象,有些网络创作者为了博取读者的目光,刻意追求小说内容的猎奇性和趣味性,在遣字造句上毫不讲究且毫无逻辑。更甚是很多网络小说基调大同小异,重复着消费市场上年轻人热衷于财富和刺激的生活方式。这样的创作方式与语言艺术的审美特质相悖,也背弃了文学作为反映和揭示生活的一面镜子的深远意义。另一方面,消费社会虽然鼓励女性追求自由和解放,但是过度释放的女性特征或许会变成消费社会中一种讨好男性消费者的商品。因为当下的消费社会“并没有离开男权文化的背景,相反,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暗中支配着消费文化中的女性并通过现代大众媒体不断强化和巩固,女性在消费文化中的对象化、物化现象和被动地位,意味着男权制在消费文化中对女性的控制赫然存在着,并成为现代消费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控制力量。”[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