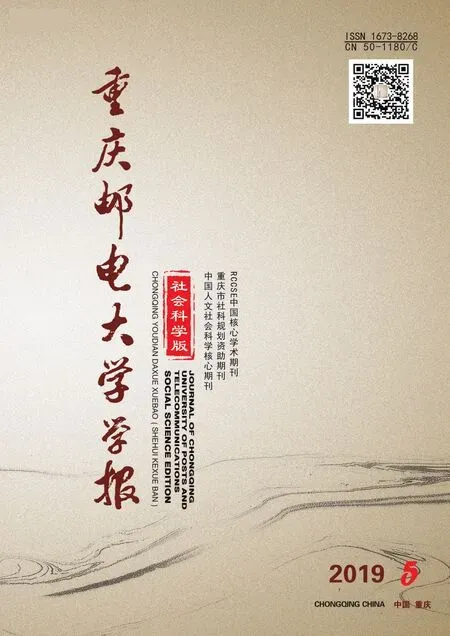“原道”观与中国文论的生成特征
2019-02-16唐定坤
唐定坤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不管认同中国文论的“失语”(1)引发文论“失语症”的讨论,主要是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此后许多学者参与讨论,十余年间成为一个焦点现象(高文强:《失语 转换 正名——对古代文论十年转换之路的回顾与追问》,《长江学术》2008年第2期)。与否,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现代学术的叙事话语中处境颇为尴尬,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探究中国文论的话语规则,进而梳理和描述中国文论不同于西方文论的体系性特征,是解决中国文论“失语”纷争、“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关键。所谓“失语”纷争和“话语重建”,存在着对比西方文论的独立性而进行阐释观照的背景,在比较视野中考量独特的中国文化自性,中国文论所面临的困境既是挑战又是机遇。西方文论一方面肇始于对形而上学的模仿说,另一方面因主客对立的思辨执着而别出一途,甚至与文学愈离愈远,这一历程明显受制于西方哲学体用论的思维方式。与之对应,中国文论的话语规则仍取决于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1],此即本体论意义上的“原道”观。即是说,“原道”观所统摄的思维方式,引导和决定了文论的生成特征和话语言说方式,或者说形成了中国文论独特而“潜在”的体系性。
“原道”是中国早期思想史的既定事实,是各个思想家“知识系统”背后“无需论证”“不言而喻”的“终极依据”[2]。它总是指向先人对现实世界本原依据的深切观照,体现为从人道而至天道的层层追问,终以形上之推指呈为本体的玄远假定,在思辨上体现为自天道而人道的本末体用化生,和自人道而天道的末本道通为一。早期各家的本体论,当推道家论“道”最有旨趣,但“原道”观念对文论生成的影响,本质上是思维方式的影响,故必然指呈为一套逻辑理路和体系性,因此我们径直从《淮南子·原道训》《文心雕龙·原道》《原道》《文史通义·原道》这四篇直接点明“原道”的文章着手,旁涉思想史,考察其思辨特征,藉以梳理中国文论的生成特征。
一
汉代《淮南子》虽本道家,但它的体系构建却有着兼容天地万物的气魄,整体上能“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3],是秦汉以来中国思想世界形成所依据的重要典籍之一,最能见出早期“原道”明确的体用建构。此书开篇即《原道训》,高诱注:“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因以为题篇。”[4]1持论先立其本,上法老子。何以如此?因为此书“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的宏大叙事,暗含着一个有“条贯”[5]4550的体系建构,这显然具有“原道”的方法论考量。按《要略》篇总结道:“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散大宗,惧为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又恐人之离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4]369高诱注“大宗”为“事本也”。显然,“总要举凡”对应“离本就末”的担忧,都体现为本末兼顾的思辨意识;而“本”“末”兼顾又分明是“道”“事”并举的抽象概括,此即该书“原道”体用建构的思维特征和方法论。此外,需要“博为之说”的“大宗”——“道”,则指向于实存性,这与《原道训》中关于道的具体描述正相呼应。要之,《淮南子》的“条贯”性主要体现为论天地万事必溯其本的思维特征,蕴含了本末体用的哲学思辨和“道”的实存性知识建构。
下至齐梁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则称“人文之元,肇自太极”[5]1,正是论文溯源而至“太极”的思路。按《易》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思辨,所原之道即谓“太极”。“太极而无极”,韩注谓“太极者,无称之形,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极况之太极也”。黄侃释“据韩义,则所谓形气未分以前为太极,而众理之归,言思俱断,亦曰太极”[6]6,而“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形成宇宙生成论。以《易》比老庄以至《淮南子》,则本末冥契。“太极”与“道”,只是本体称名的不同。儒者原道,其称名则为“天”或“心性”,唐代韩愈《原道》一篇,其所原之道已非哲学形上之称名,而是周公孔孟的治世之道,故此“道”包含了诸多礼法等形下内容,因此仅就形上论述而言,则“本无甚大哲学的兴趣”[7]802;尽管如此,这依然是韩愈《原性》《原人》《原鬼》《原毁》系列作品的起点,所以仍然展现了体用本末的逻辑思路。下迄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则自称“原道”不同于《淮南子》、刘勰、韩愈三家[8]119,《原道》云:“三人居室,而道形矣。”[8]119按此理解,“道”依然没有溯源到本体的实存性,章氏阐发的焦点是道在人伦日用而彰其无所不在的形下降落特质。不过章氏已在与友人书中自述《原道》之旨在于纠补考据、辞章、义理的学术三分之弊,而欲反归未裂之道术[8]123,所以叶瑛认为《原道》是《文史通义》一书立论之起点与总汇[8]123-124。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校雠通义》也首立《原道》一篇,此篇文字竟与形上和形下的“道”毫不相干,他的目的乃是为了目录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7]945,这明显见出他是将“原道”作为思辨的方法论,进而作系统建构的。总起来看,韩、章二人所原之道虽不着意于本体的形上品质,但他们在宏观建构上都与《淮南子》和《文心雕龙》一样,呈现出一种言事必先言道、自本而末的思维特征。
至于在极重体系建构的理学家程、朱、陆、王那里,“原道”则是通识;甚至极力反对空谈的顾亭林,亦言道器;《文史通义·原道》初出,引发友朋不满,其侄章廷枫解释:“是篇题目,虽似迂阔……诸君当日抵为陈腐恐是读得题目太熟。”[8]141章学诚自已也说此“篇名为前人叠见之余”[8]123,这正可见出时人对于“原道”的熟悉;而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的晚近文人如王韬,在采用泰西观念以图变法的思想历程中,依然要立《原道》为本[9]1。
可见“原道”为古人通识,也是古人宏观立论的起点,而其所呈现的本末体用之思,乃是最为基本的思辨方式。这种思维特征反映在文论中,以《文心雕龙》与《艺概》最为清晰。按刘勰《原道》一篇,首次系统地在文学上“原道”: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爰自风姓,暨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10]1-2
首立《原道》,所谓“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原始以表末”[10]535,正是宏观建构必以原道为起点的本末体用思路,全书的篇目及文论观点也正是按此方法展开,所以它既是逻辑思辨,也是方法论。在具体的人文“原道”论述上,定“太极”为无上玄虚的形上本体,终极依据一旦确立,人文则被悬置于太极之下, “以本达末”则道生天地,进而生天地自然之文,再进而生人;三才并生,唯具“天地之心”的人参之,“心生言立”,顺理成章,“言立而文明”亦乃“自然之道也”。这个逻辑思辨展示了自天道而人文的体用化生,终以层进的方法推导出文章为“自然之道”。在“师圣体经”的立论依据上,则更进一步体现了本末体用思辨作为方法论的深入运用:因为形上之“道心”“惟微”而呈现为自然人文,所以王者要“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以“化成人文”,这样就可以系统地概括为一种本末体用双向互推的关系,即“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只有基于此才能“旁通而无滞”,这与《淮南子》论及“离本就末”的担忧两相冥契,均体现了作者对体用本末双向思辨建构的执着意识。
刘熙载《艺概》立论的思路亦与之相近,其叙云:
艺者,道之形也。学者兼通六艺,尚矣!次则文章名类,各举一端,莫不为艺,即莫不当根极于道。……抑闻之《大戴记》曰:“通道必简。”概之云者,知为简而已矣。至果为通道与否,则存乎人之所见,余初不敢意必于其间焉。[11]
先明艺道之关系,正是“恐人之离本就末”,所以要“言事先言道”;而“艺”乃“道”之一端,“根极于道”,乃为自本而末的思路;论艺“通道与否”则是在终极依据之下,反观万物“道通为一”的思路。姚姬传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12]278;“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12]280,庶几近之。
即便不重体系的文论中也存在着大量的本末体用之思。诸如韩、柳之“文以明道”[13];周敦颐之“文所以载道也”[14];许学夷之“诗有本末,体气本也,字句末也”[15];薛雪亦之“诗之用,片言可以明百意,诗之体,坐驰可以役万象”[16];叶燮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17]。
二
原道的本末体用思辨,落实到具体的表达维度,即产生对文论言说方式的影响,可以从以言求意、以物证道、始琢终朴三个方面进行论证。
1.本体论的玄虚特质影响了中国文论以言求意的本体论旨归。按《淮南子》论道上承老子,通过形上之推确认了本体的实存性,但毕竟道本体“高不可际,深不可测”[4]1,所以只能作“玄之又玄”的想象描述,之前的《老子》《庄子》率皆如此,这也旁通于儒家孔子的“天何言哉”及《易》立“太极”的神秘玄远,是谓本体论的玄虚特质。但因自末而本的形上之推终至“一”与“无”,反之则自本而末、“无中生有”的体用化生,在各家都形成了以少总多的统摄性思辨特征,道家谓“托小以苞大,守约以治广”[4]369,《易》道中简易、变易、不易的三易统摄原理亦冥契于老子的“大道至简”,以佛家论,空观万有和纳须弥于芥子之说同样是其要旨。此外,先秦各家的“哲学突破”自“天道”而转入“人道”,普遍具有“人间性”的特点[18],即是说,在远古思想家那里,原道的终极归趣具有最彻底最现实的当下人间关怀,并自人间秩序的建构最终波及到人的自身性情关怀。所以下至《淮南子》便明确提出《原道训》一篇的最终归趣乃是“尊天而保真”“贱物而贵身”“外物而反情”,“保真”“贵身”“反情”无疑和《易》强调“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求君子之境同属于人的现实关怀。
与之对应,本体玄虚所呈现的体用之辨,作为思维方式体现在文学上则转化为言意之辨,“意之所随”乃“精”之道,不可言传,则必藉象以尽意,这是自庄子而至王弼释《易》而建立的“立言-尽象-尽意”的思辨,汤用彤据此指出了六朝文论的重要问题实以“得意忘言”为基础[19],这形成了以言求意、旨归本体虚廓渺远的文论话语特征,如《文心雕龙》的以“秀”求“隐”、唐代诗学重“三外”追求、宋代严羽论诗当“不落言筌”而求得“言有尽而意无穷”,俱应和于此。但就创作论来说,“以意为主,文辞次之”[20]285则彰示了自本而末所形成的“以少总多”的言说特征,陆机《文赋》谓“课虚无以责有”,又谓“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所说精当,影响于刘勰则以《神思》推衍为“驭文”“谋篇”之要,这正是以体驱用、以意运言,“坐驰”而以“役万象”。事实上,“意”对应于玄虚的本体特征又归趣于人的当下情感关怀,据此我们看到中国文论的本体性范畴大半还具有“生命之喻”的特征:气、骨、神、意、文心、气脉、情志、体,等等。“生命之喻”的言说方式汇通于文学本体关怀的情感论,传统文学的独立自觉总是与政治教化二者间保持着紧张关系,文学主为抒情之用,另面亦必从属于教化功能之一端,但“文以载道”总是不脱抒情之用。此外,“原道”的当下现实情感关怀还对应于另一类本体论范畴,即由实用性倾向导致的当下行为方式产生新文体,亦即因文以立体,由此而衍生出了蔚为大宗的文体学。这种文体批评与情感论旨归的批评,交互构成了诗本理论的主要部分。
2.道不可求而赖即物体道的必由途径,影响了中国文论以物证道式的体悟式批评。道本体玄虚无形而化生万物,本质是形上之道对形下之器的支配与作用,而终与万物一体,呈现为一种规律性的抽象存在,这是原道观中的通识。《韩非子·解老》释道乃“万物之所然”“万物之所以成”,将本体推释为天道自然,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据之以定文的生成逻辑,黄侃阐释为“道尽稽万物之理”,故化为各具“异理”而无“常操”的“万物”[6]5,《庄子》言“道在矢溺”,宋代理学言“理一分殊”,所指明本体降落之实质皆在于此。《易》谓“道”之遍布流行,“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章学诚即此而阐发说:“圣人求道,道无可隐,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8]121因之,“天下事物、人伦日用”皆含道,“三人居室,而道形矣”。显然,本体只是形上之推的一种思辨可能,即老子“强字之曰道”,玄不可解,所能推见者仅是“道”形下降落于现象界对万物的支配与作用。
按道藏于器,则圣人唯能在万物人伦之器中体道,“是故圣人将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沉浮俯仰”[4]18。《易》之为文亦即在此,“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21]。圣人如斯,则一切人上通“天道”的途径舍此而无它,因之“体万物之情”“以天合天”,是各家学说常见的体道途径。这种思维方式联通文学的批评途径,道不可求但化为“万物之理”存在于器之自然造化中,文乃道之一端,而以“言不尽意”难抵道原,所以求文之如何,必期合于自然之造化如何,以得与道冥契,抵达本体自然而成为作文的最高追求,可谓以物证道的体悟式批评。“文章亦如造化”,起承转合疏密快慢,皆如自然四季“有一定之时”[22]1520;又如“天地之道,一辟一翕,诗文之道,一开一合”,则“章法次序已定开合”[22]729;再如“诗有造物,一句不工,一篇不纯,是造物不完也”[23];“夫天地之间,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于造化之自然”[12]278,作文需知“草蛇灰线法”等等,皆求合于造化之万象以达至境。连并著名的“以景喻诗”“随物赋形”“气盛言宜(水与浮物)”等感悟式的批评法,大致都可看成是主张在自然万物中体悟天道自然的思想回应。而既成思维定式,则援以证道的媒介之物不限于自然对象,一首(句)成功的诗文经由原初客体转化、诠释成自足客体,则其诗心自明,从原道观来看,其中也蕴含了一定的“道”,是故诗也是载道之器,可籍此而为论诗之工具,如诗学中著名的“以诗论诗”“以禅喻诗”批评法,终以在“诗境重造”中阐释原诗而汇通于以物证道的体悟式思维方式。
3.体用圆融的相反相成,影响了中国文论二元话语的融合无间,在思辨途径上呈现出始琢终朴的相悖性达成特征。道在万物与人伦日用,即道在器中,其思辨指向体以用显,用归体摄,道器合一而体用相即,遂使体用本末之间圆融无滞。王弼注《老子》三十八章“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24]24,指明体用之间不可断绝。《淮南子·原道》谓道“托于秋豪之末”[4]2,则需联系该篇本末兼顾的思路,下至章学诚《原道》说得更清楚:“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8]132儒道两家思想均具有这种潜在思辨,《程氏易传·序》“体用一源,显微无间”[25],则说得再清楚不过,这是吸收了道家思想的宋代理学,为了抵佛家之万法归于虚空,专门针对其体用隔绝而以气贯通,遂使体用圆融无碍,正是这种思辨保证了天人合一思维方式贯穿于中国文化始终。
推以人文,首先出现了即体即用、上下通融的体用性范畴,这种通融合一统摄了万物的二元相反相成,如意象的通融对应于情景的二元相成,诗文讲求虚实阴阳之变等;究以思辨,则本体系于天道自然,作用有赖人力工夫,遂在言说方式上呈现为始琢终朴的相悖性达成。文章必始于雕琢的人力锻炼工夫,朴者“真也”[24]16,复归于朴乃是对“天道自然”的达成,契合于文学批评的本体论旨归。这主要指向自然与锻炼的相反相成。自然本身就是“道”的直呈体现,并无“成心”之亏,移之于文学,则其作为形上之本玄不可言,为文体之用则存于锻炼之精,所谓“技之精者必近道”;煅炼虽为人力而有悖天道,然其本属天道自然的作用显现,故为天道自然所摄,其旨归亦必指向自然。这在诗法上是最为切要的思辨,“诗中天籁,仍本人力”[22]2328。庶几切近“自然、锻炼,既相成矣,亦相反也,酌斯二义,斯得中道”[26]10。刘熙载甚至说:“西江名家好处,在锻炼而归于自然。”[26]10只是自然虽属天道,但不可径取为用,不然终会陷于熟滑无力,这当是宋人对“元轻白俗”的批评向度[20]455,而勿宁锻炼使之生新古拙有力,譬如韩愈的“以文为诗”,黄庭坚的“生新瘦硬”;如果带有文学的至高期许,则必须归趣于自然本体,三重境界次第与联系分明:“先取清通,次宜警炼,终尚自然”[26]10。所以“郊寒岛瘦”[20]455易为诟病,而“豪华落尽见真淳”[27]则最为推崇。
三
以上从内在义理上考察了“原道”影响中国文论的言说方式,现在我们从《原道》作品的存在形态来考察,又有新的发现。首先,我们确认古人宏观作论好以原道为起点,然而迄今为止,具有体系性建构的著作并不多;他们讨论原道的文字在篇幅上的比例也较小,甚至除了《淮南子》外,其余三家就“道”本体的知识建构都没有展开,《淮南子》二十一卷只有开篇论及“原道”,《文心雕龙》五十篇也只有首篇论及此,韩愈的《原道》作为一整套思想体系的起点依然只有一篇,《文史通义》原道的比例同样很小。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章学诚找到答案。他的《原道》当时已遭“题目”“迂阔”“陈腐”的抵毁,他自称“篇名为前人叠见之余”,显然,原道的思想虽然存在,但大谈此题却令人生厌,这当与考据占主流的乾嘉时代背景相关,《文史通义·原道》中有几句话值得关注:
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8]140
谈“道”属“义理”,易陷入“空言”,从语气上看,这似乎是时代的大忌,同代凌廷堪解释此中原因:
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28]
清人将义理之学与“虚理”“空言”联系起来,此种言行蕴含了时代反省和学术方法论自觉的意义,深刻地指出了“原道”义理的“空谈”之弊。按此思路,义理之学必须下降到百姓人伦日用,才能规避玄虚之偏,这正是章学诚《原道》开篇便从“三人居室,而道形矣”谈起,而抛开了本体讨论的深层原因。清人反对空谈的学术理路,源自明末顾亭林、王夫之等反对王学末流“空谈误国”而倡经世实学。事实上,形上之学玄虚难论,坐而论道极易远离百姓的人伦日用,这是以儒家治国为主体的思想史事实。这肇端于孔子恢复礼乐文化“畏天”而“不语怪、力、乱、神”[29]的当下切用,庄子《齐物论》称引孔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30],一向被认为概括孔子思想精准得当,实际上潜藏了孔子的道原观念,“存”字肯定了“六合之外”未知世界的实存,“不论”形上世界之玄虚另面指向人伦日用的毕生努力。道家虽讨论本体,但同样因为“诸子之兴,皆因救时之弊”[31]的大背景而具有人间关怀的特点。此后历次思想史事件大致都能体现出类似的原道思维特征:在整体建构上体用兼顾,在具体操作上以用为主,承认本体而又反对坐论玄虚,受制于“实用理性”[32]而归依于当下人伦日用。两晋清谈玄学无益于家国强盛而迅速消歇,唐代韩愈斥佛影响世人的人伦不兴与产业不恒,宋代程、朱等斥佛影响士人坐谈真如而失其本职,王阳明不满于朱子学的“流于支离”不能“格”尽当下具体生活而建构心学,都从不同的面向上指明这一点。陈寅恪对比西学而得出中国人“惟重实用,不究虚理”,殊少“精神之学问(原注:谓形而上之学)”[33],这一判断最是有力,只是那少许的“精神之学问”与“实用”学问二者存在何种建构关系尚待发覆。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何极力反对空谈的顾炎武,仍然要“原道”探讨体用,其《日知录》卷一列“游魂之变”条和“形而下者谓之器”条,且承认孔子的“求之象数”[34]38是“下学而上达”[34]42,便是显证,但总的说来,《日知录》又是以论“器”论“用”为主;同理,晚清王韬受西方实学的影响而讨论变法,思路仍然要从《原道》开始,但此篇文字却又未作深入的形上讨论[9]1-2。
这种在整体建构上体用兼顾,在具体操作上以用为主的原道论对古代文论的整体生成起了决定性作用。体用兼顾最终导向体用圆融的上下无滞,这在思维方式上联系于创作理论和实践的不可分离。对应而言则理论为体、实践为用:理论执着于玄虚而受“实用理性”的牵制,断不可独立为体而自分一途,脱弃创作的理论剖析必遭“空谈”之讥,恰如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本身亦是精美的骈文,文论家的批评总是小心翼翼,绝不可悖于文论切近当下的实用功能;体必达用,以用为主,理论必须为实践服务,创作当推首位,理论批评沦为文本的附庸,批评家“用分析、解说仍尽可能点到为止,而不喧宾夺主”[35]9。评点文学的产生亦必如是,绝大多数的批评都潜隐了一己的创作实践和体悟这一前提,同时预设了读者的创作者身份而与之同台对话,据此我们才可以说“实践诗学”[26]1的研究视角具有中国文论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接着讲”的洞见。
以此体用之思为视角,我们可以见出中国文论的“潜体系”特征。在整体论述架构上,或者立体而以用为主,或者以体统用,而必在用中贯注体用之辨;类辑之则有本体论范畴、体用性范畴、功用论范畴,要之不脱简论“道”本体而重点关注功用论范畴的形式。《文心雕龙》最具体系性,《原道》仅一篇,而若以本体范畴论,则文之枢纽的五篇都从属之,这个比例在古代来说不低;但我们必须看到,《文心雕龙》这种批评方式在古代诗学中并不占据主流,它的影响也不如我们今天想象得这么大[10]1-3。刘熙载《艺概》仅在“叙”中追问了艺与道之体用关系。严羽《沧浪诗话》仅《诗体》部分阐发诗本理论,其余所谈《诗辨》《诗评》《诗法》《考证》等,究其质无不是论“功用”;而此书立盛唐诗的“兴趣”、求无穷之言外“意”为体,实为审美标准,遂以统摄一切形下技法。叶燮《原诗》开篇即论体用之辨——“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17],标举“才、胆、识、力”则以体统用。林琴南《春觉斋论文》则先立“意境、气势”等“八则”为本,以统笔法、声律等功用性范畴。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论述方式上,大量功用范畴的讨论则多归于本体的玄虚渺远,“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始于技法的讨论而归趣于诸如教化、情性、天道、意境等本体论范畴,是以诗文终以出境自足、抵达性情教化为上;只是受制于对空谈虚理的警戒,则不必深入讨论本体范畴的层层指向,而势必导向一种期许创作家顿悟的“秘响旁通”[35]65,展示为一种可与智者道、难与俗人言的言说机制。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四篇《原道》呈现了史的变化,仅作横向的“原道”探索,有粗疏而去“真相”的危险,只是如果普遍联系于其他文论,可以管窥一斑。如果考虑思想史变化的对应影响,文论发展在具体的时段则各有偏颇,比如宋代前多有“风骨”“格”“式”“意”“文气”等玄虚的本体性范畴讨论,宋代新儒学构建在思想史上造成的相对稳定的文化语境而导致形上学的讨论难以出现大变化后,则在以黄庭坚诗学为导向中转入了“所说常在字句间”的切实可指的功用论范畴讨论[36],而一以贯之的则是在本体、体用、功用三种范畴之间展示一种特有的言说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