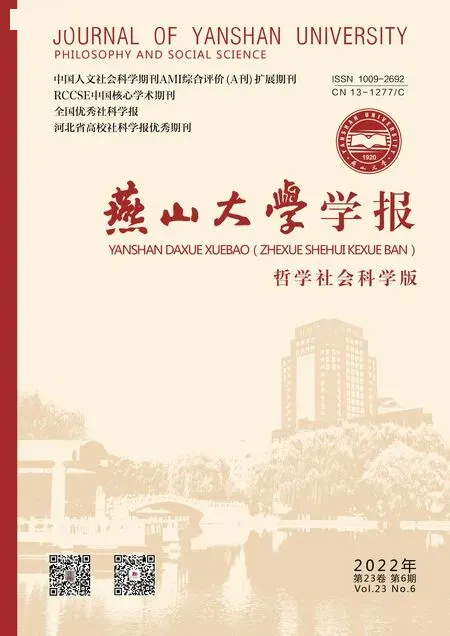《文心雕龙·原道》探原
——“原道”传统与刘勰的突破
2023-01-21羊凌霄
羊凌霄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文心雕龙·原道》篇的学术渊源颇为复杂,这与刘勰熟读各家经典有关。据罗宗强统计,《文心雕龙》一书引及作者322人,引及作品436部。[1]可谓遍及四部,淹贯百家。这种赅博在《原道》篇中尤为典型,刘勰对“道”与“文”的描述颇为驳杂,在多部典籍中均可寻绎其踪影。因此,自黄侃以来的百年间,各家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使得这一问题显得更为扑朔迷离。
过去诸家,大多是从思想的角度,根据《老子》《庄子》《论语》《周易》《礼记》《荀子》《淮南子》《弘明集》等书以及王弼、郭象等人的注解来探明刘勰《原道》篇的学术渊源,对于“原道”这一篇目的体例源流关注不够。刘勰以《原道》为首篇系取法道家的“原道”传统,这一传统由《老子·道篇》《黄帝四经·道原》《文子·道原》与《淮南子·原道》构成。除体例外,刘勰《原道》对这一“原道”传统尚有颇多借鉴。借鉴之余,其又脱离了纯粹的“道家”叙事,而熔各家于一炉,作出新的“突破”。
一、“原道”传统:《文心·原道》的目录学探原
关于《文心雕龙》首篇《原道》的篇目由来,学界早有共识。昔日黄侃曾在《文心雕龙札记》中引《淮南子》高诱注说:“《文心》之作也,本乎道。……详淮南王书有《原道》篇,高诱注曰: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用以题篇。”[2]黄氏引此注,意在说明刘勰《原道》之“道”与《淮南子·原道》之“道”的渊源,虽然未曾明言《文心·原道》之体例袭自《淮南》,但其通过材料的胪列传达出了这种暗示意味。
这一看法不久便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饶宗颐在《〈文心雕龙〉探原》中说:“(《原道》)法《淮南子》首《原道训》。”[3]以极为精审的语言申明了二者联系;王运熙亦认为:“《原道》篇的中心是说明文章的根源是道。汉代《淮南子》首篇名《原道训》,此篇题名当受其影响。”[4]此后陈良运将这一观点发挥至极并认为:“《文心雕龙》全书的结构,实是对《淮南子》有所‘仿依’。‘仿依’更明显的标志,是仿首篇《原道训》而作《原道》为‘文之枢纽’之冠。”[5]陈氏认为刘勰将《原道》篇置于“文之枢纽”之首,是受《淮南子》将《原道训》列为第一的影响,并指出二篇所论之道皆为“自然之道”。(下简称“淮南说”)
(一)“道—道原—原道”的序列
陈良运的看法总结了黄、范、饶、王诸先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但随着20世纪下半叶中国考古工作的推进,许多新的材料得以重现,使得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探讨空间。在诸多出土文献中,尤以1973年发掘的两种最为重要:其一是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的马王堆帛书,帛书中的四篇“《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或即《黄帝四经》,下即称此名。)含有一篇《道原》;其二是出土于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西汉墓的定州西汉竹简,汉简中发现了277枚《文子》残简,其中有3枚与今本《文子·道原》吻合。二书均见载于班固《汉书·艺文志》,成书年代亦早于《淮南子》。
因此,可以说二书的发现动摇了“淮南说”的基础,在两篇更为古老的《道原》存世的前提下,再将《原道训》看作《文心·原道》篇的唯一源头则显得不够全面。细考《文心·原道》之前的同一类型的文献共有四篇,分别是《老子·道篇》《黄帝四经·道原》《文子·道原》与《淮南子·原道》,这四篇文献均出自道家,构成了一个目录学意义上的“原道”传统。故而与其说《文心·原道》篇的设置源于《淮南子·原道训》,毋宁说这一体例源自道家的“原道”传统,《淮南子》仅为其中一环。从体例来看,自《老子·道篇》到《文心·原道》的发展过程,既是一个目录学上的演进,也是“原道”传统由“道家”过渡到“儒家”的过程。
(二)“原道”模式的创建
从现今存世最早的郭店本《老子》来看,其书虽已分为上下篇,但并未冠以“德”与“道”的篇名。目前最早将《老子》分为“德”“道”二篇者是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其上、下篇尾分别题有“德”“道”字样。除郭店楚简本外,韩非本、帛书本、汉简本均为《德篇》在前的传本,这一顺序似乎更为古老。“道经”在前的版本目前最早可追溯到刘向校书时的81章本,此后的敦煌想尔本、河上公本以及王弼本大多依此体例。[6]①
刘勰著《文心雕龙》时,所见者应是这一《道经》在前的传本。而在先秦著作之中,最早将“道”作为篇名,置于其书最前(“道家”传本)或最后(“法家”或“黄老家”传本)的便是《老子》。《老子》篇目虽未冠以“道原”或“原道”的字样,但其以“道”为篇名对“道”的体用进行探讨的做法,事实上开启了道家的“原道”传统,也是刘勰《原道》篇的目录学源头。
(三)“原道”体例的确立
《黄帝四经·道原》紧承《老子·道篇》之后,是这一“原道”序列中的第二部可靠文献,大约形成于战国中期。[7]四经分为《经法》《十大经》《称》和《道原》四篇,《道原》居于全书最末,体现出“法先道后”的意识,其体例与早期《老子》版本“先德后道”相近。但《经法》九章又以《道法》为首,表现出了一种“法原于道”的崇道意识。
从体例上看,《四经·道原》与《文心·原道》更为接近,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以“道原”作为篇名,已近于《文心》;第二,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原“道”;第三,短小精炼,且篇内不再分章。
《四经·道原》篇以专章的形式对“道体”“道用”与“悟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详细地讨论,是其不同于《老子·道篇》的地方。《老子·道篇》分为数十个简短的章节,虽主题较为集中,但各章之间并没有一个明显的逻辑线索,而《黄帝四经·道原》则首次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对“道”的本源、作用以及体悟方式进行探讨,这种体例与《文心雕龙·原道》篇更为接近。
从篇幅上来看,《四经·道原》约460余字,《文心雕龙·原道》约610余字,二者篇幅较为接近,且篇内均不分章;《文子·道原》全篇则有3 400余字,且分为十章;而《淮南子·原道》则将近6 000字,篇幅约为《文心·原道》的10倍,篇内可分为二十章,亦与刘勰《原道》不同。
(四)篇次与篇题的确立
《文子·道原》篇出自今本《文子》,而今本长期被视作伪书。然自定州汉简出土后,伪书之说不攻自破。但简本《文子》内容多不见于今本,两者切合较多者仅《道德》一篇,其他多与《淮南子》重复。据定州汉简小组整理,简本《文子》中有三支竹简合于今本《文子·道原》,分别对应第一章、第七章和第十章[8];关亚婷对勘今本《文子·道原》与《淮南子》全书,发现《文子·道原》第三章、第四章及第十章中亦有部分内容不见于《淮南子》。[9]
简本有三支简合于今本《道原》,《文子》《淮南》此二篇又有互异之处,可推测今本《道原》内容至少有部分承自简本。颇为值得注意的是《文子·道原》的篇名与《黄帝四经·道原》的篇名相合,而《黄帝四经·道原》篇的绝对年代是远超《淮南子·原道》的,唐兰据此认为《文子·道原》《淮南子·原道》的篇名袭自《四经·道原》。[10]
《文子·道原》篇在“原道”传统中的目录学意义即在于将《老子》与《黄帝四经》置于篇末的《道原》改置于篇首,这一体例的变动直接影响了《淮南子·原道》与《文心雕龙·原道》的篇目次序,将“道”从幕后推至台前,使其地位更加重要;《淮南子·原道》则是这一道家“原道”传统的最后一环,其篇名《原道训》之“训”字为高诱作注时所加,则《原道训》之名本应作《原道》,与刘勰《原道》篇已完全相同。“原道”的篇名、篇次以及主题全部定型于此,也是《文心雕龙·原道》篇最直接的来源之一。
(五)以“原道”作首篇的意义
“原道”传统下的道家文献将“道”列为首篇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特别的用意。事实上,先秦著作虽然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但各家在选择首篇时是非常慎重的,这一选择往往能体现出其学术旨趣与立论核心。《左传》引《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11]1028楚简甲本《老子》云:“临事之纪,慎终如始,此亡败事矣。”[12]可见各家对事物的开端与结尾都特别重视,这种重视反映在著作体例上,则体现为对全书首篇的选择异常慎重,多有其深刻用意。
高诱注“原道”篇题时说:“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因以题篇。”[13]1高诱认为《淮南子·原道》篇的设置,体现了“大道本源”的寓意,世间万物以道为本,因此著书亦须以道为先。《黄帝四经·经法·四度》云:“周(迁)动作,天为之稽。天道不远,入与处,出与反。”[14]150提出了“天道不远”的命题,并进一步认为:“执道循理,必从本始,顺为经纪。”[14]156
正因看重“本始”,故各家都颇重视其书首篇。儒家著述常以“论学”为始,如《论语·学而》《荀子·劝学》《潜夫论·赞学》《中论·治学》等,盖因其以“人道”为本,故强调“学”,认为要在“学”之中完善自我,最终建功立德;而道家著述多以“论道”为先,如《老子·道经》《黄帝四经·道法》《文子·道原》《淮南子·原道》等,盖其以“自然”为本,认为“道”无所不在,人要在对“道”的体悟中不断规正自身与社会,最终使天下无为无事。此即在“慎始敬终”的一般原则指导下,道家文献以“道”开篇的用意,而这一“原道”传统便是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的目录学来源。
二、 “原道”的思维的建立
“道”字在东周以前多作“道路”之义,尚未具备抽象概念。道家学派出现后,才真正赋予“道”丰富的哲学内涵。刘勰创作《原道》篇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道”是否可“原”、是否有“源”的问题。这一问题关乎“原道”的可行性,是全篇的逻辑起点,而此疑问恰好与上述“原道”传统有关。《老子》等书不仅回答了“原道”的可行性问题,还追溯了各自的“道”之“本原”。道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文心·原道》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源头。
《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5]3将“道”作为“万物”的源头,因此其推原“万物”时,也往往以“道”为终点,《老子》第十六章曰:“天物云云,各复归于其根……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15]11第二十五章亦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5]12将“天”“地”“人”“万物”的源头皆追原于“道”,是《老子》的创举。但对于“道”的源头《老子》则往往语焉不详,仅设置了一个相对的参照点,将“道”置于“天地”“万物”或“天下”前,如第一章说:“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15]10第五十二章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15]4仅第四十章说道:“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5]3将“道”的源头追溯至“无”。
《老子》的回答逻辑上并不完满,于是各家提出了新的问题。《庄子·齐物论》说道:“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16]70提出了“始”这一深刻的哲学命题,认为“始”之前还有“未始”,“未始”之前尚有更早的“未始”;“有”之前还有“无”,“无”之前尚有“无无”,时间空间,永无穷尽。
时空的无限性使得《老子》推“道”于“无”的说法有了缺陷,与此同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以“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九主》为代表,其假伊尹言曰:“天不见端,故不可得原,是无胜。”[15]30意识到了时空“无始”“无端”的特性,认为“天”这类具有无限性的事物无法追原,可看作首次对“原道”的可能性的否定;另一种则试图调和这种矛盾,《黄帝四经·前道》篇说:“道有原而无端,用者实,弗用者雚。(羊按:“雚”字陈鼓应释为“空”。)”[14]365《称》篇说:“道无始而有应。其未来也,无之;其已来,如之。”[14]393一方面肯定“道”的“无始”“无端”的特性,不再从有限的时间上去追溯“道”的本原,另一方面则从“用”(“道”的功能)与“来”(“道”的运动)中体认“道”的本体,“用”和“来”同人的实践与认识紧密相关,换言之,“道”在被“人”体认时才能显现自身。因此,《四经·道原》在推原“道本”时说:
恒无之初,迵同大(太)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静不巸(熙)。古(故)未有以,万物莫以。古(故)无有刑(形),大迵无名。[14]452
将“道”之本原上推至“恒无之初”,与《老子》推“道”于“无”不同,《四经·道原》在“无”前冠一“恒”字,并进而解释这种状态为“恒一而止”,将时间的无限性与“道体”的“虚无”特质结合了起来,从而解决了“无始”的难题。
《文子·道德》篇亦说:“夫道者,原产有始,始于柔弱,成于刚强;始于短寡,成于众长。”[17]185同样认为“道”有其“原”,《道原》篇说“夫道者。高不可极,深不可测,苞裹天地,稟受无形,原流泏泏。”[17]1《道德》篇又说:“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17]185将“道原”认作“虚无”“天根”,均是受《老子》影响,但《文子》又受稷下学派的“精气说”影响,将“道原”看做一种“先天之气”。《淮南子·俶真训》亦承《庄子·齐物论》论“始”一节而来,但与《齐物论》将“道”认作一形而上的完美本体不同,《淮南子》更为直接地把“精气说”运用到了“始”的问题中,说道:“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虚无寂寞,萧条霄雿,无有仿佛,气遂而大通冥冥者也。”[13]52-53将“气”贯穿于“道”之始终。
《老子》将“道”推原至“无”,《四经·道原》将“道”推至“恒无”,《文子·九守》与《淮南子·俶真训》则将“道”推至“先天之气”,无论是《四经》以“恒无”消解“无始”,还是《文子》和《淮南子》以混而为一的“先天之气”解释“无始”,都为《文心雕龙·原道》篇提供了一个坚实的逻辑支点——即“道有原”。
三、“圣人”的独特地位
《原道》篇说:“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18]非常重视“圣人”的作用。因此刘勰在《文心·原道》中所推崇的“人文”实际上是一种“圣之文”,这种“圣之文”又被称作“道之文”,其特点有二:一是以“道”为本,需要圣人以“道心”来感悟;二是以“教”为归,要能化成天下、流传万世。前者重在对“道”的体悟,因此强调“圣”,即圣人对大道的独特感悟;后者重在对“道”的运用,因此强调“王”,即圣王肩负的教化万民的责任。圣人由悟“道”入“圣”,再经“教化”成“王”。
刘勰的独特之处在于把“文”作为贯通“道—圣—王—民”的主轴,这是其殊胜所在。然而由“悟道”推至“王天下”的思维模式则早在道家出现,《老子》论及“圣王”执道御民之处颇多,如第二十二章说:“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15]12认为治理天下的关键是“执一”“守道”,而《老子》认为“道”具有“朴素”“自然”的特性,所以强调为政也要“无为而治”,并且“功成弗居”。故《老子》说:“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15]4-5将圣王的修为与治理天下连为一体。
《黄帝四经》延续了《老子》的看法,但更强调“圣人”的作用,《国次》篇说:“故唯圣人能尽天极,能用天当。”[14]92《道原》篇说:“故唯圣人能察无刑(形),能听无[声]。知虚之实,后能大虚;乃通天地之精,通同而无间,周袭而不盈。”[14]460认为唯有圣人能通明“道体”,可以“至神之极,[见]知不惑”[14]184-185,勘破世间万物的“名实”,从而掌握“天极”与“天当”,“天极”指事物发展转变的临界点,因此非常重视“时”的观念,“天当”则指行事立法时的正当性,其要在于守“雌节”。
《四经》看重外在的“名理”,《文子》则更加看重“道心”的作用。《文子·道原》说:“圣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17]17《文子》残简亦曰:“0717故有道者立天下,则天下治 ……0695[治矣],毋道而立之者则乱。”[19]认为只要君主具备圣人的修为,天下便能大治。
《淮南子》与《文子》观点类似,《原道》篇说:“天下之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我身。身得则万物备矣。”[13]43但又有些微不同,《原道》篇说:“圣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知大己而小天下,则几于道矣。”[13]39《文子》此句为“圣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侧重点在“圣人”自身,而《淮南子》则重在“道”上,这或许与《淮南子》认为“治在道,不在圣”有关。
以上四书将道、圣、王、民联系起来,完成了一个由“天道”向“人道”的过渡,“圣人”或“圣王”在这一过程中即起到沟通天人的作用,这一点与刘勰《原道》篇的描述是一致的,也是刘勰将“文”推原于“道”的必然结果。刘勰将“文”嵌入这一序列之中,标志了其“原道”目标的实现;在刘勰的叙事中,“文”作为一种能“雕琢性情”“鼓动天下”的方式,被历代圣王所采用。
四、披文入道:刘勰对“原道”传统的突破
刘勰创制《原道》的体例与逻辑均源自道家传统,但《文心雕龙》又是一部以“儒家”为宗、以讨论“文学”为主的著作,与道家传统下的四篇“原道”文章不同。刘勰所作《原道》对前代的“原道”理论有两处突破:即“道”的突破、“文”的突破与“圣”的突破。
(一)“道”的突破
《文心雕龙·原道》篇中,似乎存在三种“道”,大部分学者都能在第一部分(“文之为德”至“其无文欤”)看到“自然之道”;在第二部分(“人文之元”至“亦神理而已”)看到“鬼神之道”;在第三部分(“鸟迹代绳”至“迺道之文也”)看到“儒家之道”。如果再加以更为细密的考据功夫,还能从“太极”中看出“阴阳元气之道”,从“神理”中引申出“般若妙道”。由于诸家所言,难以统一,于是便出现了种种调和论,或“以佛统儒”,或“以道兼佛”,或“三教会通”。但因为刘勰《原道》各节所述之“道”彼此相去甚远,故而这种“调和”也未尽如人意。
在一篇之内推原“道本”,竟然出现如此多的歧义,这在之前的“原道”篇目中是没有的,在《老子》等书中,“原道”的指归都是明确的。鲁迅将这种现象归结于“其说汗漫,不可审理”[20],似乎过于简单。《梁书》记载刘勰早年“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又说其“为文长于佛理”[21],今之学者多以为《文心》之作条理清楚、逻辑严密,便与刘勰精通佛理有关。[22]既然刘勰为文甚有法度,在其著作开篇便出此莫大纰漏是难以理解的,因此当另寻解释。
先秦秦汉间,诸子多有“原道”,如前文所述《老子》原“道”于“无”、《道原》原“道”于“恒无”、《文子》与《淮南》原“道”于“先天之气”;此外,尚有《庄子》原“道”于“浑沌”、《周易》原“道”于“阴阳”、董仲舒原“道”于“天”等等。但以上诸子所原均非刘勰所要原之道,因为诸子之“道”从未将“文”包含在内。因此各家之道在刘勰欲原之“道”面前,都是有缺陷的。刘勰所要原者,是一更为本原的道,是既能涵盖百家又能兼容“文章”的道。
百家都相信宇宙间有一个唯一的普遍真理,此一道理遍及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运转。如《黄帝四经·成法》篇便说:“一者,道其本也,……一之解,察于天地;一之理,施于四海。”[14]340《周易·系辞上》亦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11]268-270各家均致力于探求此终极真理,以作为其学说根本。
但正如孔子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1]241“道”本身是不言的,它要在人的认识、阐述与实践中才会显现,因此诸子对“道”进行阐述时又不可避免地陷入《老子》所说的:“道,可道也,非恒道也。”[15]10诸子往往将自家所体认的一家之理当作终极之“道”,但这种努力常常是失败的。正如《庄子·天下》篇所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16]1298
“道”应该是无所不包的,但百家之“道”却互为抵牾,甚至其学说内部也不尽雷同。此诚为一大矛盾,因此在汉魏六朝时便兴起了会通儒玄乃至会通三教的思潮,而刘勰所述之“道”既有道家之“自然”,又有《周易》之“神理”;既有人心之“情性”,又有儒家之“仁孝”,并将“文”作为“道”的载体,将其纳入“道”的范畴,是前所未有的。《文心·原道》中建立的这种涵盖百家又兼容“文章”的体系,是刘勰在追问“终极之道”时的创新。
(二)“文”的突破
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体系中,“文”的地位并不高。道家言“文”多指“德”,其对“文”的论述多体现在对“言”“名”与“音”的探讨中。道家从“实用”的角度看待“言”,故而认为“言”则落入下乘。对“圣人”来说,“道”是不言自明的,只有在面对一般人时才需要“言”,因此“言”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方便法门,绝无可能享有“道”“德”一般的高位。《老子》第五十六章说:“知者弗言,言者弗知。”[15]4第二章说:“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15]10便是其证。
儒家则好著述、重视学问,文艺则被看做一种装饰性质的派生品,仅仅对学术起到辅助作用,正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11]1024然而文学在儒家的观念里虽然重要,却是处于次要地位的,如《论语·宪问》中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11]183即是“重道轻艺”之意。
道家崇尚“不言”,儒家“重道轻文”。刘勰则不然,《文心·原道》篇将“文”纳入“道”中,大大提高了“文”的地位。道弥漫十方,无往不利,天地间的一切都无法脱离“道”的藩篱,“文”自然也不能例外。因此掌握了“道”的原理,自然也就掌握了“文”的原理,所以通“道”者可以“执一御万”、一通百通。因此,反过来谈文,也就不能停留在以文论文的层次,而要从“文”中寻找“道”,这个“道”不仅要统御一切文章,还要进一步影响万事万物。因此刘勰《原道》篇说道:
至夫子继圣……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18]
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滞,日用而不匮。[18]
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18]
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元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傚。[18]
以上文字足见“文”在《原道》篇中并不是一个掐头去尾的孤立部分,而是从自然中而来到社会中去的中间环节。
(三)“圣”的突破
除“文”与“道”的突破外,刘勰对“圣”的描述也超越了道家传统,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1)变无名为有名;(2)变虚称为实称;(3)变无统为有统。刘勰这一举措,不仅突破了道家的“原道”传统,还成功构建了儒家的“道统”序列,在此序列中,大致做到了一圣配一王、一圣配一典,初步完成了“圣统”“政统”与“文统”的统一。(此问题颇为复杂,待另具文讨论)
道家典籍常论理而不具人名,如《老子》八十一章频频提及“圣人”“侯王”,而皆不具指。《黄帝四经》的《经法》《称》与《道原》三篇亦未见人名,故《庄子》称“圣人无名”,良有以也。《文心·原道》则不然,其构拟了一个自“玄圣创典”(伏羲)到“素王述训”(孔子)的圣王序列,先后列举了伏羲、大禹、神农氏、尧、舜、伯益、后稷、周文王、周公旦、孔子等十余位“圣人”(此外篇中提及“三坟”或包括黄帝,提及“商周”,应包括商汤),将道家的“无名”之圣,转变为儒家的“有名”之王,此其一。
其二,道家典籍有时也会称举具体的圣人,如黄帝、许由甚至孔子等等。但这种称举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凭空捏造,如《庄子·应帝王》中的“无名人”“南海之帝”儵、“北海之帝”忽、“中央之帝”浑沌等,皆无中生有;一种是化实为虚,即借用真实人名来虚构其事,如《黄帝四经·十大经》全篇虚设“黄帝”与“力黑”等臣的对话、《庄子·大宗师》虚构“孔子”与“颜回”的言论,在《说剑》篇中甚至连“庄子”自身也被后学当作了虚构的对象。而儒家则不然,褚补《史记·日者列传》记司马季主批评当时辨士是“言必称先王,语必道上古”,《孟子·滕文公》亦言“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皆有征实疾虚的意识。故刘勰《原道》列举诸圣也力求有所依据,不仅立足于古代经典,精当地描述了从伏羲到孔丘的“圣之文”的发展历程,而且对于难以验证的“炎皞遗事”也仅说其“年世渺邈,声采靡追”,此又与道家不同。
其三,道家称举“圣人”大多是零散的、片段式的,在其叙述中并无一个井然有序的“道统”,而像刘勰这样将“圣统”“政统”以及“文统”合一的做法,不唯道家,在儒家中也堪称创举。
刘勰在《原道》篇中所构拟出来的“道统”序列中,除伏羲等六王外,伯益是秦之始祖、后稷是周之始祖,地位超然;周公曾摄天子位且葬以天子之礼;而孔子在公羊学中更是被尊为“素王”。刘勰通过构建这一“道统”序列不单追溯了“文章”的发展历程,同时也追溯了“圣王”的历史,并借由这一序列的建立传达自身对于完美文章的看法。“道-圣-王”三者在此序列中与“文章”相融无碍,真可谓开宋儒“文以载道”的先河,但刘勰标举“自然”“情性”,又得以免宋儒废文之害。
恰如宇文所安所说:“刘勰的真正意图不是要说明这就是‘文’,而是要说明这才‘应当’是‘文’。”[23]因此很难根据一般的文学观念去揣摩。
注释:
①关于《老子》早期版本,丁四新考证已详,但据高亨、陈鼓应、饶宗颐诸家推测,《老子》的“道家”传本亦同样古老,惜无实物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