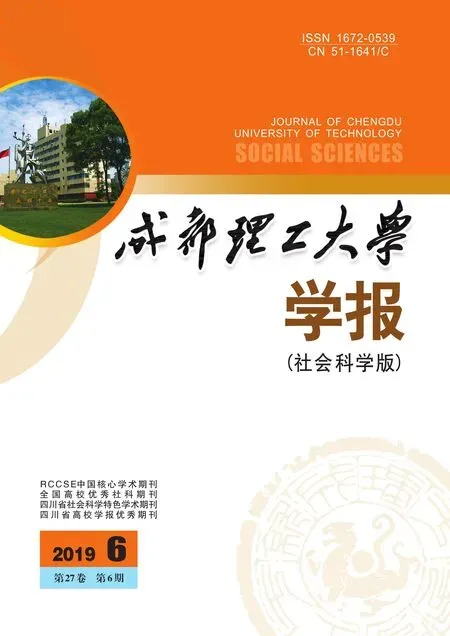谫议张居正《书经直解》的经世思想
2019-02-16林相
林 相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明隆、万时期重要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官至内阁首辅。其著述主要有《四书直解》二十七卷、《书经直解》十三卷、《资治通鉴直解》二十八卷等,皆为经筵日讲而作。其中《书经直解》是张居正经筵讲义之代表性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书为万历初进讲所作。时神宗幼冲,故译以常言,取其易解。”[1]383所谓“易解”,乃不拘于字词训诂、不重今古文辨伪,语言平实流畅,文风通俗易懂。清康熙帝评价是书称:“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义俱精实,无泛设之词。”[2]214盖是书虽文白意浅,却包含张居正经世致用思想,即如柏永济所谓:“其有功于道统、裨益于后学又岂浅尠也哉。”(1)[3]
刘广京认为,“儒家思想素重经世,儒家经世思想包括哲学和学术思想,同时包括社会思想、礼俗思想、教育思想、行政思想、政治思想等——和现实都有关系。”[4]2《尚书》作为儒家重要经典,必然涵括经世一面。张居正据《尚书》编就《书经直解》以授万历皇帝,尤重经世思想的发挥。其在解经时,多借发明经义以阐释自己的学术思想、教育思想、执政理念和政治施为等,以期达到裨益朝政、经世为用之目的。万历八年(1580年)十一月,万历皇帝受近侍引诱,夜饮宫中、寻衅滋事,其后悔过认错,并认为宰辅未尽忠谏之职。张居正则答复圣谕说:“前者恭侍日讲,亦曾将孔子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并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两章书,请皇上加意省览,盖亦阴寓讽谏之意。”[5]319张居正以讲解《论语》时“阴寓讽谏”回应皇帝责问,则其借助经筵日讲惕励帝王之意甚为明确。与之相孚,《书经直解》作为经筵讲义著作,“讲明治道”是其独特所在,其中亦可见张居正作为政治家解经,与文学家解经的不同之处。目前学界关于明代《尚书》学之研究,多从《尚书》文献考辨、《尚书》经文辨伪、《尚书》与科举等层面进行阐释研究,而于经筵《尚书》则所论鲜少。事实上,作为经筵讲章之《书》作,恰最能彰显经学义理对于政治统治和现实关切的适用性。概而言之,对《直解》之研究,不仅有助于寻究张居正解经立言、裨补朝政之用世思想,且于察见明隆万政局、社会风气起到见微知著之效。
一、求躬行实效,弃无用虚词
张居正隆庆二年奏《陈六事疏》说:“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6]3《书经直解》经世功用首先即体现为张居正对“实学”的尊崇。
明代后期,阳明后学渐兴,世人多空言心性、崇饰虚谈,以致仕子之学骄侈浮靡,风俗日坏。张居正对此甚为不满,其在《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中说:“……往闻公好谭理学,雅称同志,意必实有所得,非空言者……今世谈学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于反古之罪,是尚谓能学孔矣乎……仆愿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毋以前辈为不足学,而轻事诋毁;毋相与造为虚谈、逞其胸臆,以挠上之法也……”[7]书牍716-717张居正认为其时学者的不务治世,有悖于儒学正统,是“甘蹈于反古之罪”,进而萌生整饬学风的思想,即反对空谈性理、提倡敦实务本。张居正在进讲经筵时,多借讲章论述其务实的治学倾向,期望通过对帝王的教化,从而形成自上而下讲求“实学”的社会风气。如其在《说命下》篇所作题解云:“这是《说命》第三篇,记傅说与高宗论学的说话。”[8]173其既以是篇主于论学,又曰:
人君以务学为急,而学问以有终为贵……人不肯着实去做,故于道终无所得,而学终无所成。若能笃信而深念乎此,逊志便着实自逊其志,时敏便着实加倍其功,以此求道,而道岂有不得者乎?[8]174-176
张居正首先即明确“务学”之于人君的重要性,认为人君治学当有始有终。既而强调只有“着实去做”,才能学有所成。此即如顾炎武所谓“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9]57。阳明后学认为“学所以明道也,道者率性而已耳”“知则率性而已”[10]728-729。对于此种“率性所行”的治学观念,张居正批评道:“虚寂之说,大而无当,诚为可厌”,又曰“审如此,岂惟虚寂之为病,苟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则曰致曲,曰求仁,亦岂得为无弊哉”[7]书牍140,其危害“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弊丑秽,趋利逃名”,况且“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尤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7]书牍716。除此之外,从张居正对“思”“行”之辩中,亦可看出其求实致用的学术理念。如在解《太甲下》“弗虑胡获,弗为胡成”时云:
既思而得之,又当躬行实践,黾勉从事,或循序以进德,或艰难以保民,或危惧以守位,以谨终则于始,以听言则必审,一一都见之于施行,这事功方才有成。若只思了不肯实行,则亦徒思而已,何由而能成乎?[8]135
思考而后才能得之于己,作为而后方能成其事功。对于“思”与“行”之关系,张居正认为“思而得之”是前提,但是“实行”才是根本所在,否则只是“徒思而已”,强调了“实践”之重要性。正所谓“君子之学,不以记诵为工,而在于能明乎理,不以闻见为博,而在于善反诸心,学者不可以不勉也”[11]72。故为学之关键在于“用”而不在于“记”和“思”。与经筵讲章的内容相呼应,张居正于万历三年(1575年)五月面奏万历皇帝,直陈学校和督学官员对于学术风气所起的关键作用:
窃惟养士之本,在于学校,贞教端范,在于督学之臣……近年以来,视此官稍稍轻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谈贾誉,卖法养交,甚者公开幸门,明招请托……使人皆知敦本尚实,而不敢萌侥幸之心,则振兴人才之一大机也……[5]101-102
张居正于此指出了士子治学不务实际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是官方对于督学之臣的忽视,以及这些官员未能自重以敦实学。张居正一方面借其“帝王师”的特殊身份,借助经筵日讲,使小皇帝接受“崇实摒虚”的为学观念;另一方面又找到了这一不良社会风气的成因及其变革措施,“双管齐下”对万历皇帝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有无实效,从万历皇帝的批复中或可睹见:
学校,人才所系。近来各提学官,不能饬躬端范,精勤考阅,祇虚谈要誉,卖法市恩,殊失祖宗专官造士之意。卿等所奏,俱深切时弊。依拟再行申饬。所开条件,一一备载敕内,着实遵行。[5]102-103
万历皇帝认为大学士的提议“深切时弊”,并要求“着实遵行”。既而又告诫学校师生,说道:“夫为治之道,贵在力行;立教之方,务求诸己。朕方责实考成,率作兴事。惟尔师生,均有修己治人之责者,尚益加毖勉,懋乃教学,助宣风化之原,翊赞文明之治。”[5]139其中“贵在力行”“责诸考成”“修己治人”的核心理念,无一不是《书经直解》所强调的为治之道,此实可见张居正经筵讲学的现实影响。
张居正从社会实际出发,讨论了其时之学术风气,并将自己主“实”之学术态度置诸经解,发挥了经义的经世功用,具有现实针对性。而张居正经筵进讲的现实效用,又于万历皇帝具体的政治施为中得以管窥。
二、修德治人,内圣外王
道德与政治密切相关,“政治的目标不仅在于达成法律和社会秩序,而且还在于通过道德说服来建立信赖社群”[12]59。如此,君主对自身道德的修养则显得尤为重要,张居正进讲经筵即于此一方面多有反映。
《论语》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1]68张居正据此认为:“人君居万民之上,要使那不正的人都归于正,必有法制禁令以统治之。这叫做政。然使不务修德以为行政之本,则己身不正,安能正人?虽令而不从矣。所以人君为政,惟要躬行实践,以身先之……图治者可不务修德以端出治之本哉?”[11]68于张居正而言,己德不修,则身不正;己身不正,又岂能正他人?故而,作为一国之君,必先备德于己身,而后方能“为政以德”。这种德治观在其解《书》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如释《尧典》篇“克明俊德……黎民於变时雍”所论:
惟尧能明其大德,浑然天理,不为私欲所蔽。大德既明,则身无不修,而万化之本立矣。由是推此德去亲爱自家的九族,那九族每,就亲爱和睦,没有乖争,一家都齐了;又推此德去普教那畿内的百姓,那百姓每,就感动兴起,个个晓道理,没有昏昧,一国都治了;又推此德去合和那万国之民,那黎民也就变恶为善,雍雍然成醇美之俗,天下都平了。一家齐,是勋放于家矣;一国治,是勋放于国矣;天下平,是勋放于天下矣。[8]2
盖家国之治,乃源于明德修身。此实借《大学》“修齐治平”之语发论。所谓“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13]226,于宋明儒者而言,重主观人格修养是致“内圣”、达“外王”之关键,即由修身出发,最终归结于治国平天下。所以“人君以一身而统万邦,所以联属而绥怀之者,德也……人心离合之机,系于德之修否如此……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本修德而能得民,亦未有不由学问而能成德者。”[8]112同时,这种修身之“德”还必须是“实德”,即不仅存诸心,还要践行于行事之间:“盖为人君者,固贵乎有德,然所谓德者,非徒存诸心而已,惟当见之于行事之间,使政无不善,才是实德。”[8]31此种“实德”于政教有益,而见之于行事主政中,故其又说:
人君不患臣言之不尽,惟患己德之未修。为君者诚能躬行实践以修其德,真真实实的要做圣君,无一毫虚假间断,则其臣知君必乐于闻善,而所以为之谋者,有知必言,有言必尽,启心相告,无有隐匿而不明者矣!又知君必乐于闻过,而所以弼其失者,一俞一吁,一可一否,同心共济,无有畏忌而不谐者矣!若人君不能修德,或修德而未实,则臣下不免望风顺旨,欲进一言,恐君未必能听,不可不自勉以为纳忠之地也。[8]42
张居正既言实德之重要性,又申述贵在持之以恒:“人君之修德……能着实用功,无有一毫虚假、间断。使实德而无不爱戴归往于下者,这才叫做明君,乃可以嗣守先业,而永保天命也。王欲图终,可不以此自励哉!”[8]129如若做到“实德”,又能一以贯之,则“内无失德,外无失政,心志精明,治道光显,真如日月照临一般,岂不为明明之后哉”[8]101, 即如《中庸》所云:“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14]36
帝王只有修明己德而后方可表率臣民,所谓君行在上,臣下化之、民众效之,君德于国家风化之重要性不言自明。《论语》曰:“德不孤,必有邻”[11]96,意即“人君修德于上,则万姓归心,四夷向化,而天下为一家,不然,则众叛亲离,不免于孤立而已。可不慎哉”[11]96。修德实乃人君图治之本,张居正将“修己治人”观念熔铸于《书经直解》中,是其经世致用解经倾向的体现。
张居正关于“修己治人”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此可与其后内阁首辅的对比中得以显现。申时行继张居正后主政内阁长达八年,但他甚至不能说服皇帝正常御驾经筵,更别提借经筵以“正君心”了。所以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认为,正是因为“世间已无张居正”,故而万历一朝每况愈下的衰弊之象不可避免,且无人可以挽救。
三、君道主刚,权柄不移
张居正万历元年(1573年)奏《请开经筵疏》云:“臣等恭照经筵、日讲,皆所以仰成圣德,讲明治道。”[6]121所谓治道,即为政治国的基本原则。《书经直解》经世思想的第三个层面体现在张居正的执政理念上,即“君道主刚,权柄不移”,认为君子应当以“刚”治国,不致权柄旁落。明代宦官、朝臣专权现象甚为严重,上自王振、汪直,下至刘瑾、严嵩,皆为患于朝,危害国政,此为前车之鉴。张居正任首辅之时,正值主少国疑之际,故其在《陈六事疏》中说:“臣闻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临制四海之广,所以能使天下皆服从其教令,整齐为不乱者,纪纲而已……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6]3“纪纲”乃为政要道,系之于己身,则权柄不移。张居正于《五子之歌》篇以“善医者”比诸“善治者”,认为“纪纲”乃国脉之关键,并云:
五子伤太康之失德而归咎于乱其纪纲,可见纪纲所系之重,有不容一日而少弛者。人主诚能留意于此,凡刑赏予夺,一主之以大公至正之心,使威福之柄常在朝廷,而无倒持下移之患,则人心悦服,而国势常尊矣。[8]99
威福权柄必须握于皇帝手中,因为权柄下移的后果甚为严重:“致威柄下移,奸雄僭窃颠覆我有夏之宗,断绝我配天之祀,岂不可恨也哉!”[8]99权柄下移,君权旁落,有夏一代正是因此以丧亡其邦,实为镜鉴!又如其解《洪范》“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云:“政尚严明,教化振作,谓之刚克。君德以刚克为主,乃圣人所以宰制群动而齐一海内者也……”[8]222张居正将“正直、刚克、柔克”三德理解为“治世”三德,并认为三者虽然同样重要,但于君主理政而言,当主“刚克”,并又言:
人君欲行抚世之大德,当操御世之大权。若非总揽乾纲于上,以致权柄暗移于下,又何以尽三德之用哉……为君者,其可不操大权于己,以表正万邦乎!大抵治世三德,虽说刚柔并用,然君道还当主刚。[8]223
只有总揽权柄于一己之身,方能表正万邦。张居正既言“权柄不移”,必然论及君臣关系,其云:“若臣下而敢有作福、作威、玉食,则坏法乱纪,下陵上替,大乱之道,自此而生……夫以下干上,其害遂至于此。”[8]223即若君道不振,以致下臣干上政,则法纪坏而治道乱。
如果说修德立身是个人层面的“治道”准则,那么为政用刚则是张居正执政思想的直接体现。所谓“《书》以道政事”[1]322,“道政事”指向“治道”,张居正恰是以诠释《尚书》义理为基础,以期构建统治者“治体用刚”的政治伦理。
四、解经佐政,辅助改革
“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包括了两部分的内容,即实用性的知识层面和思想主张层面”[15]4,具而言之,“既包括探讨性命、天理等道德话题,也包括处理实际政治事务的各类知识”[15]81。《书经直解》经世思想确非拘囿于学术思想和执政理念层面,它还为小皇帝讲明政治制度,并借助经讲达臻佐助改革之目的。
首先,张居正在解经时,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于解经中申明国之政体,如解释《周官》:
设官治政,固有国之大体,而为官择贤,尤用人之要务。若官不得人,徒取备员,则非唯无益而为多害矣。君天下者,不可不知也……这是冢宰之职,后世之吏部尚书即此官也……这是司徒之职,后之户部尚书即此官也……这是宗伯之职,后之礼部尚书即此官也……这是司马之职,后之兵部尚书即此官也……这是司寇之职,后之刑部尚书即此官也……这是司空之职,后之工部尚书即此官也……[8]367-370
张居正先明治官得贤于治体之重要性,进而又将周代官职与其时之六部官制结合以作论述,既便于小皇帝对经义的理解,又能帮助其更加形象地了解当前国家的官僚体制及其职能,可谓一举两得,其通经致用之意显豁可见。又如其解《禹贡》“导河积石……入于海”时,联想到黄河水患问题,故明示以君曰:“洪水之患,惟河最甚,故大禹疏凿之功,惟河独多,然当时但顺水之性,以除民之害而已。今之黄河,乃漕运所必经之道,而淤塞冲决之患,时时有之,既欲资其利,又欲去其害,故今之治河尤难,经国者所当加意也。”[8]86《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6]264,黄河每年汛期时,不仅影响正常的水利工作运转,更给两岸居民造成严重生命财产威胁,张居正通过解经,向万历皇帝言明水患之害,以在黄河治理问题上多加留意。由此可见,《直解》将社会实况与经义内容绾合于一体,达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其次,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期间为除积弊,力主改革,主张政治上施行“考成法”、经济上实施“一条鞭”法、文化教育上禁毁书院等。而其改革措施能否施行之关键则在于万历皇帝之态度,故其借解《书》拉拢帝心,明君改革之必要。如释《酒诰》篇云:“盖人欲为不善,最患其党与众多,则为害必大,而酒食乃聚党合众之资,故群饮者必诛,所以遏乱萌也。”[8]278此说与张居正禁毁书院之由实出一辙。又如解“禹曰……敷同日奏罔功”言:“夫既修德以致贤,而又能考成以核实,则精神所感,人皆化之……”[8]54再如《皋陶谟》篇所论“人君欲知臣下之贤否,但验之行事之间,看他偏与不偏。初时说好的,到后来看他变与不变,则下无遁情,而知人之哲得矣”[8]44之语,皆指任官用人层面综合名实、考成其绩,当为敷陈张居正政治改革中“考成”之法。
再者,时以张居正为首的政治改革,引起保守党强烈反对,他们攻讦其乃是于主少国疑之时,揽权行私。张居正则说:“汝谓人君安于所止,审于几康,而尤必赖辅弼之臣,直言规正。”[8]51又以周公辅佐成王之事明于万历,曰:
武王既丧,成王尚幼,周公乃摄位行事。是时,周公之兄管叔,方监殷武庚谋为不轨,乃与群弟蔡叔、霍叔等,造为无根之言……所以危惧成王而动摇周公也。盖主少国疑之时,奸人之所窥伺,托孤寄命之地,大臣之所难居。故虽以周公之圣,犹不免于流言如此。[8]242
张居正将自己辅国之事揆诸周公辅佐成王,而将攻讦自己的政治保守派划归武庚及蔡、霍之徒,以使皇帝信服保守派之言论皆类“危惧成王而动摇周公”。张居正受托孤之命辅弼万历皇帝,甚明此之“所难居”,故又借“以周公之圣,犹不免于流言如此”之言为自己“开脱”。张居正既阐明己之立身不易,进而又明己之忠心于帝,其曰:“保民之责,虽任于我,而保民之本,实系于王,故我将大责难之义,以启迪王心,裨益新政,此我所以仰承文武,而忠于吾王之本心也,王其念哉!”[8]304
“牵合实际,通经致用”是《直解》一书最鲜明的特点。面对年幼的万历皇帝,张居正一方面讲明国家基本政治体制和处理政务之方法,另一方面又试图为自己的政治改革拉拢帝心,在经解中言明改革之必要性。张居正借解经切入具体现实,正是其对经世为用治经理念的社会实践。
五、结论
程颐说:“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17]539-540首先,张居正担任经筵讲官,能够秉持陶冶君德、启沃君心的用世之道,充分把握并发挥《尚书》义理中切于治道之术,有益于统治者参稽先贤、敬修己身,从而助益统治。其次,张居正授讲经筵《直解》,能申明《尚书》篇章要旨而发明经文要义,对经筵《尚书》的内容与义旨阐释,于《尚书》学的深入研究有极大帮助。正所谓“儒者之学,务于经世”,张居正由“入世”为政而兼涉治道与治法两个方面,正是与文学家解经偏重字词训诂、寻章摘句的不同之处。张居正在万历二年(1574年)给皇帝的奏疏中直接指出经筵讲章之特殊性:“盖帝王之学,与韦布不同,惟在融会其意义,体贴于身心,固不在区区章句间也。”[5]43就明隆、万时期政局而言,较之纯粹的学术辨析,强调《尚书》经世大义,于裨补现实或许更为切要。从此一层面来看,说《书经直解》是张居正应对时局、匡济天下的理论武器实不为过。而透过对史料的爬梳,这一“理论武器”确乎于实践中发挥出了它的现实功效。
总而言之,通过对《书经直解》经世思想的梳理论析,可窥见张居正作为政治家“通经致用”的解经倾向,以及《尚书》作为经筵讲章的现实指导价值,其学术意义颇为重大。同时,对是书之研究有利于深度把握张居正的政治、学术、教育等思想并可窥见帝王讲师借解经立言,从而影响帝王思想的为政理路。
注释:
(1)此句所引乃是济南市图书馆藏,民国十七年(1928年)济阳道慈印刷局石印本《书经直解》序言。该书卷一次行题“济阳张尔岐稷若氏手著”,然江曦《张尔岐〈书经直解〉辨伪》一文已辨明此书与张居正《书经直解》实为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