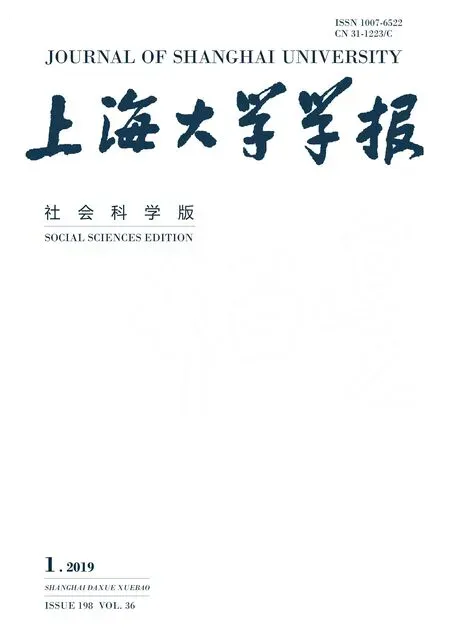再论李贽《答耿司寇》的文献问题
2019-02-12邬国平
邬 国 平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433)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论文(《李贽〈答耿司寇〉是一封“集束型”书信》,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2期),探讨李贽此信构成的复杂情况,以及这一文献现象含有的研究价值。关于这封书信构成的复杂情况,论文的主要结论是:第一,《答耿司寇》由李贽在不同时候写给耿定向的七封书信组合而成,而并非人们通常说的写于同一时间的“一封”书信。第二,第六封信是李贽在极其郁怒之下,对耿定向数恶揭短,它也是导致李贽与耿定向关系彻底破裂的催化剂。第三,恰恰是招致二人关系极度恶化的关键的第六封信,李贽写好后出于某种考虑,很可能没有寄给耿定向,而是等到与耿定向关系趋恶难以挽回時,才将它与别的六封书信合在一起,编成一封长信,以《答耿司寇》为题,于四年后刊行的《焚书》首次公开,耿定向也是在这时候才首次读到这部分内容,深为震惊,怒称《焚书》是一部诽谤他的书。
在后来刊刻和排印的李贽著作中,这封《答耿司寇》的文本又发生过变化。现在,以其文本在后来的再变化为考察对象,对这封书信的文献问题作补充论证。
一、《李温陵集》和《焚书》所载此信不同
《答耿司寇》既刊于《焚书》,又刊于《李温陵集》。然而,《焚书》的《答耿司寇》比文集的同题书信减少了约2400字,占原先篇幅的三分之一左右。管玉林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整理《焚书》,通过与《李温陵集》校对,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对二书与初刻《焚书》,以及二书所载《答耿司寇》的关系提出推想。他在整理本《焚书》的《点校说明》中指出:
这次整理《焚书》,系用清末《国粹丛书》本为底本。该书是依据一种明刻本排印的(见黄节跋)。从焦竑序看,这个刻本是李贽已死,《焚书》遭到禁毁以后重刻的。现存其他各本《焚书》,和这个刊本出入很少。只有明人顾大韶编订和校刻的《李温陵集》所收《焚书》(按,《李温陵集》共二十卷,除收录《焚书》、《道古录》两书外,还从李贽的《藏书》、《初潭集》各摘录了一部分,并选入了李贽其他著作的自序,重加编次)《书答》部分,比单行本《焚书》多出了十一篇,另有若干篇比单行本多出了整段的文字,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李温陵集》卷三所载《答耿司寇》一封长信,从“何其相马於牝牡骊黄之间也”以下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在单行本《焚书》中被删去。此外,多出一句、几句或几个字的地方及其他个别文字上的出入亦不少。由此可以推想,《李温陵集》虽也是在李贽死后编刻的,但所收《焚书》,是根据或接近於李贽生前的刻本,而现存单行本则是经过删节和改动的。[1]1-2
管先生认为,《李温陵集》所载篇幅长的《答耿司寇》符合原貌,后来重刻的流传本《焚书》所载篇幅短的《答耿司寇》则“是经过删节和改动的”。这结论完全可信。他整理《焚书》,处理这封差异甚大的书信的办法是,一方面保持重刻本《焚书》所载该信的原状,另一方面,又从《李温陵集》辑录二千数百字,列入《增补二》,附录于《焚书》全书之末。他欲用这种方法让读者既能够掌握书信《答耿司寇》的文本在《李温陵集》和《焚书》的变异情况,同时又保留流传本《焚书》的真实面貌。不过,由于该书体例方面的原因,辑录《答耿司寇》所删文字不是紧连此信,而是被置于《焚书》之末的“附录”(第270页-274页),与此信所在的实际位置(卷一,第29页-35页)遥遥相隔。而整理者在卷一信的标题或结尾处对此又没有任何提示,仅在全书最前面的《点校说明》中谈到所采取的处理办法,“单行本各《焚书》卷一《答耿司寇》一篇被删去的部分补录在后面,列入《增补二》”,欲以这种方式让读者意识到《焚书》正文所收《答耿司寇》只是一部分内容,不是全文,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读者容易误会整理本《焚书》所载《答耿司寇》正文即是此信刊于初刻《焚书》中的全部内容,这不免辜负了整理者一片苦心。这是管玉林先生整理本留下的一点遗憾。注管玉林先生《点校说明》云:“校勘方面,曾用《李温陵集》以及几种单行的《焚书》的刻本和排印本来校正底本(《国粹丛书》本)的误字。《李温陵集》比单行本《焚书》多出的字句,只选择较有参考意义的作了校记,会列在卷一之末。”(中华书局1961年版《焚书·点校说明》第2页)其校记共11条,包括《答周若庄》4条,《答焦漪园》2条,《复周南士》2条,《复京中友朋》1条,《复周柳塘》2条。这些校勘最主要的内容,是根据《李温陵集》补上被删掉的一些句子。而《答耿司寇》被删掉的约三分之一文字,却作为《增补二》置于全书最末,同一书而校勘体例不一致。又按,以上11条校记,在197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焚书 续焚书》合订本中,均已吸收为正文,然而对此未作具体标记和说明。
可能正是认识到这一遗憾而欲予弥补, 1975年中华书局将管玉林先生整理本《焚书》和中华书局编辑部整理本《续焚书》(1959年出版)合在一起出版(下称“合并本”)时,其《焚书》部分,对《答耿司寇》文献的处理出现了很大变化。合并本将原载于《焚书》的《答耿司寇》所缺少的二千数百字,从《李温陵集》所载的同题书信中移取来,直接续在它后面,使该书信内容重新完整化了,这是《焚书》版本史上一个新的变异本。如果采用适当的方式对此做出具体说明,这种整理方法本来也未尝不可。确实,我们读到了《焚书 续焚书·再版说明》对此所作的一定交代,“这次用中华书局整理本修订重印,其中《焚书》有少数地方根据明人顾大韶编的《李温陵集》作了校改和增补”。[2]4-5然而,像这样的“校改和增补”不是采用校勘记,或是在原文中加注说明的方式,而是直接改变原文,却对哪里做了“校改”,哪里做了“增补”,不作具体明确指示,这很难引起读者有效关注文本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具体改变,很容易发生误会。比如,以为后来重刻的流传本《焚书》所载《答耿司寇》的篇幅本来就是这么长,而这样的印象离开事实是很远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合订本的做法没有到位。另外,此整理本处理类似问题,体例方面也不一致。比如文字篇幅差别较大的《复焦弱侯》,整理者在《焚书》卷二保留其经过删节的文本,而将载于《李温陵集》未经删节的文本作为《附录二》载于《焚书》末,这与处理《答耿司寇》的方法不同。一书而体例有歧,让人犯惑。比起1961年版《焚书》,1975年的版本流传广,影响也大,读者了解的《焚书·答耿司寇》,大多是1975年版所提供的文本。
同样情况也存在于张建业先生主编、刘幼生先生副主编《李贽文集》第一卷(包括《焚书》《续焚书》)。其《焚书》之《答耿司寇》也是取自《李温陵集》,用以取代重刻的流传本《焚书》所刊的这一篇书信,整理者对发生的这种改变同样未做具体说明,沿用了中华书局1975年整理本的做法。张建业先生在全集的《前言》说:“《焚书》《续焚书》由刘幼生副编审依据明刻本进行整理标点,并参照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和岳麓书社、北京燕山出版社近年出版的点校本作了一些校改和增补。”[3]可见《全集》本与中华书局1975年合并本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这样,已经被管玉林先生发现的《答耿司寇》一部分文献的变异问题,又在某种程度上被掩盖起来,更甚者,由于整理者改变了这一书信的部分内容而未作具体、有效指示,更加容易导致读者对现存明刻本《焚书》所载此书信的实际情况产生误会,以为其所载之《答耿司寇》一文本来就是这么长,而谁会想到此排印本《焚书》之《答耿司寇》其实非彼现存明刻本《焚书》之《答耿司寇》呢?
二、《答耿司寇》并非由两封书信构成
初刻本《焚书》所载《答耿司寇》(即《李温陵集》所载的同题书信)被一截为二,它前面的大部分内容被用相同的题目保留在现存明刻本《焚书》中,后面的少部分内容则被削去。这容易致人猜想:初刻《焚书》所载之《答耿司寇》原本可能由两封书信构成,而当《焚书》刊刻新本子时,编刻者出于某种考虑,将两封书信分开,保留一封,删去另一封。若如此,《答耿司寇》就不是七封,而是两封书信的“集束”形式。
那么,《答耿司寇》究竟有没有原本由两封书信合成的可能性?不妨让我们先看一下《答耿司寇》被删去部分的开头一段文字:
展转千百言,略不识忌讳,又家贫无代书者,执笔草草,绝不成句。又不敢纵笔作大字,恐重取怒于公。书完,遂封上。极知当重病数十日矣,盖贱体尚未甚平,此劳遂难当。但得公一二相信,即刻死填沟壑,亦甚甘愿。公思仆此等何心也?仆佛学也,岂欲与公争名乎,抑争官乎?皆无之矣。公傥不信仆,试以仆此意质之五台,以爲何如?以五台公所信也。若以五台亦佛学,试以问之近谿老何如?
很显然,这段话绝不类书信的开头语,假如被删去的内容是集束型书信《答耿司寇》的第二封信的话,就非常难以理解作者怎么会用这样的一段文字作为书信开头,让人读了之后仿佛坠落云雾。而从“书完,遂封上”这一句子来看,又可以肯定这段话一定是书信的收结语。据此,我们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删者将《答耿司寇》从这里割落,并不是因为在它前面是一封书信,在它后面又是另一封书信,割落处恰好是两封书信的分界所在。
再看现存明刻本《焚书》之《答耿司寇》书信最后一段内容:
名乃锢身之锁,闻近老一路无一人相知信者。柳塘初在家时,读其书便十分相信,到南昌则七分,至建昌又减二分,则得五分耳,及乎到南京,虽求一分相信亦无有矣。柳塘之徒曾子,虽有一二分相信,大概亦多惊讶。焦弱侯自谓聪明特达,方子及亦以豪杰自负,皆弃置大法师不理会之矣。乃知真具只眼者,举世绝少,而坐令近老受遁世不见知之妙用也。至矣,近老之善藏其用也。曾子回,对我言曰:“近老无知者,唯先生一人知之。”吁,我若不知近老,则近老有何用乎?惟我一人知之足矣,何用多知乎。近老于生,岂同调乎,正尔似公举动耳,乃生深信之何也?五台与生稍相似,公又谓五台公心热,仆心太冷。吁,何其相马于牝牡骊黄之间也。
这段话是说明,耿定向其实并不了解李贽,因而对李贽的非议也不符合事实。李贽在信里提到的“近老”是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学者称近溪先生,江西南城人,官至右参政。他传承王艮学说,是泰州学派代表。“五台”是陆光祖(1521-1597),字与绳,号五台居士,浙江平湖人,官至吏部尚书。他刚正练达,政绩卓著,信仰佛教,有护法尚书之称。对于这两个人,李贽在《答周二鲁》有具体的介绍和称赞:“ 五台先生骨刚胆烈,更历已久,练熟世故,明解朝典,不假言矣。至其出世之学,心领神解,又已多年,而绝口不谈,逢人但说因说果,令人鄙笑。遇真正儒者,如痴如梦,翻令见疑。则此老欺人太甚,自谓海内无人故耳。亦又以见此老之善藏其用,非人可及也。”“近老今年七十四矣,少而学道,盖真正英雄,真正侠客,而能回光敛焰,专精般若之门者,老而糟粕尽弃,秽恶聚躬,盖和光同尘之极,俗儒不知,尽道是实如此不肖。……盖大之极则何所不有,其以为不肖也固宜。人尽以此老为不肖,则知此老者自希,知此老者既希,则此老益以贵矣,又何疑乎。”“仆实知此二老者,今天下之第一流也,后世之第一流也,用世处世,经世出世,俱已至到。”[4]卷4这道出了李贽对罗汝芳、陆光祖两人的认识,以及对他们的推崇。然而李贽又认为,就他本人与两人的思想、性习的关系而言,他与陆光祖“稍相近”,与罗汝芳则并非“同调”。然而,耿定向对李贽与两人关系的看法适反,认为李贽与罗汝芳相近,与陆光祖则有“心热”“心冷”之绝大反差。耿定向这么说,大概是利用当时士流对罗汝芳的学说存在很大争议性,而陆光祖普遍享有口碑,借此加重对李贽的贬斥和否定。李贽在《答耿司寇》中对此加以反驳,这一方面是形容出真实的自己。如他在《答周二鲁》称自己是一个“心肠太热”的人,就与《答耿司寇》所述耿氏称李贽“心太冷”针锋相对,也正好说明他对耿定向这么形容自己,向世人散布一个不真实的“李贽”,感到非常不满,而作挽回的努力。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李贽当时在社会上处境不佳,受到主流社会排挤,他要努力消除包括耿定向在内的人群加给他的一些负面议论。
以上这段内容具有鲜明的辩驳色彩,末句“吁,何其相马于牝牡骊黄之间也”,更可感到作者愤激之情外溢。如果将此作为书信的结尾,有一种岩巉崖断、意尽而言未尽之感,行文既不够完整,语气也有欠自然。当然,刊行的书信即使是存在中间截断的现象也属正常,因为书信在刊刻時往往会被删去一些内容,书信的行文不完整、语气不自然处很可能就是它经过删削之后留下的痕迹,它被删削之前,当不至于如此。既然从初刻本《焚书》所载《答耿司寇》截下的第一段是一封书信的结束语,而保留在重刻的流传本《焚书》的这封书信又缺少了结束语,那么只能得出结论,书信被截去部分的第一段,其实就是被保留下来的那封书信的结束语。
由此可见,后来刻于《焚书》的《答耿司寇》,其保留部分为一封书信,被删去部分为另一封书信,原本为两封书信之合成,这种可能是完全没有的。
三、《答耿司寇》被删去的内容
《答耿司寇》不是同一时间写的“一封”书信,因为假如它是“一封”书信,其中诸多疑点无法解释(具体见拙文《李贽〈答耿司寇〉是一封“集束型”书信》)。上面又证明,假如根据经过删节的《答耿司寇》逆推它由两封书信合成,则其分隔处前后两部分内容的起结语又不符合书信体的通常格式,也无法合理解释,因而这种假设也不能成立。我先前提出《答耿司寇》由七封书信“集束”而成,能有效解决文本留下来的困惑。下面在此基础上,再来求究后来流传本《焚书》删落《答耿司寇》一部分内容而导致文本再次变异的相关问题。
这里先谈《焚书》重刻時,删节者是依照什么思路将《答耿司寇》一些内容割弃的。
从现象上看,这个问题似乎相当简单,删者将《答耿司寇》从三分之二处截开,分作前后两个部分,保留前面,删掉后面。这似乎完全是根据书信的自然顺序实施操作,没有别的什么深意。
其实,绝非如此简单。
《答耿司寇》由七封书信组成,一至五封,以及第七封,主要内容是李贽与耿定向辩论学问,也即李贽自己所称“与中丞……辩学诸书”的一部分,[4]卷4答周二鲁而第七封信则又带有作者调节论辩节奏,缓和阅读情绪的策略性考虑(见后面分析)。第六封书信,则主要是针对耿定向的个人品行及关系其家人之事情,进行揭露和批判,虽然其中也包含思想学术之争,但是很明显此书信的内容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结果高度激化了李贽与耿定向本已趋向尖锐的矛盾,对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后来重刻《焚书》,《答耿司寇》被删去的内容依此是,(一)第五封信的最后一段,(二)第六封信,(三)第七封信。
第五封信的最后一段文字已见前面引用(“展转千百言”云云),此处从略。这是李贽写了第五封信(从集束型书信“且东廓先生非公所得而拟也”开始)的主要内容之后,在结束处流露他写此信時经历的高度紧张和痛苦的心理。他在第五封信里,批评耿定向的声音,有些已经相当刺耳,如说耿定向“名心太重也,回护太多也。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人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又说:“公之取善亦太狭矣。”这是李贽在意识到自己与耿定向之间的矛盾很难缓解,不愿迁就的情况之下,提高了对耿定向贬责之力,同时也意识到,这么做会招致耿定向更加强烈的反击,信末流露出的情绪反映了他的担忧。其实对于书信所表达的见解而言,这一段文字并没有补充新内容,后来刊刻的《焚书》将这一段话删去,也属合适。更主要是这段话删去后,原书信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显得平和了一点,因为直接流露剧烈心理感受的文字,本身会强化作者见诸作品的情绪。
第六封书信(从“公又云前者《二鸟赋》原为子礼而发”至“愿公加意培植之也”)在七封信中最长,言辞也最激烈。李贽在信里对耿定向作了严厉抨击,如说他是伪君子:“分明贪高官厚禄之足以尊显也,三品二品之足以褒宠父祖二亲也,此公之真不容已处也,是正念也,却回护之曰:‘我为尧舜君民而出也,吾以先知先觉自任而出也。’是又欲盖覆此欲也,非公不容已之真本心也。”类似的直指耿定向个人品格的刺话在信里不少,而且还牵涉到耿定向的家族亲人,如说:“分明憾克明好超脱,不肯注意生孙,却回护之曰:‘吾家子侄好超脱,不以嗣续为念。’乃又错怪李卓老曰:‘因他超脱,不以嗣续为重,故儿效之矣。’”耿克明是耿定向侄子。像这类涉及耿定向家人的刺话在信里也不少。从李贽一方面讲,他说这些话很可能并非无端,而这类话集中出现在一封信里,火药味显得非常浓郁,效果可想而知。将这一封信从集束型书信中删去之后,整封集束型书信的火气自然降下来许多。这与上述删去第五封信最后一段的涵义和作用是一致的,而且效果尤为突出。
第七封书信(从“闻麻城新选邑侯初到,柳塘因之欲议立会,请父母为会主”至结束)的內容,是李贽对耿定向陈述自己为何不同意周柳塘关于立麻城新任县令为讲学会主持的倡议,李贽在这件事情上对周柳塘提出批评。周柳塘与耿定向相熟,也是李贽朋友,李贽迁至麻城以后,周柳塘请他居住在自己的一座佛寺,两人关系密切,然而意见时有不同。从此信来看,李贽是陈述者,反映周柳塘的情况及自己的意见,耿定向是倾听者。信中没有直接牵涉李贽与耿定向之间的矛盾,这与集束型书信的其他六封书信都不同,比较特殊。李贽初刻《焚书》之所以将这封信编入集束型书信,且置于最末,或许是想借助其内容无涉与耿定向直接冲突,使集束型书信论争的甚至挑战的气氛得到某种舒缓,使刺激性有所弱化,起到某种淡化冲突的作用。一般来说,一篇论争性文章(特别是长文),往往开头部分和最后部分的醒目程度高于中间部分,阅读感受也是如此。李贽将七封书信组合为一,将较激烈和最激烈的两封信分别作为第五、第六封,放在靠后的位置上,再以一封内容无涉他与耿定向直接冲突的信作为结束,这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安排。后来刊刻的《焚书》既然删去了第六封信,则预设第七封信的这种舒缓效果似已经没有必要,加之此信所陈述的事情本身与耿定向并无直接的关系,所以将它删去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
在这三个部分的删削中,最重要也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删去充满火药味,高度激化李贽与耿定向二人矛盾,因而内容十分敏感的第六封书信。相比于其他两个部分的删削,第六封信的删落应该更加能够体现删者的用意所在。虽然这封书信在集束型《答耿司寇》中恰好处于比较后面的位置,但是,它的被删是无法用留前删后这一理由作解释的。比如,删削的内容为什么一定要按照书信的先后顺序进行呢?如果李贽在开始组合书信时心思不够周密,第六封信恰好被放在集束型书信前面而不是后面的位置上,难道就能保证它不被删去?所以,第六封书信是因为它的内容,而不是因为它所处的位置被删掉的。也就是说,只要对这封集束型书信进行删削,在三个部分中,其他两个部分尚有删、存之两种可能,唯第六封书信因其内容特殊而无法保留,一定会被删掉。
四、删者及删节之原因
重刻的流传本《焚书》所载《答耿司寇》,可能的删者究竟会是谁?
对于这个问题,管玉林先生虽然没有直接予以回答,其实他的看法还是有较明确的倾向性。他在1961年中华书局版《焚书》的《点校说明》中指出,“据一般考证,《焚书》一五九〇年初刻于湖北麻城,这年李贽六十四岁。”“一六〇〇年李贽重刻了《焚书》。这年他七十四岁。通行本所见著者六十四岁以后的作品,很可能是这次重刻時增入的。”虽然一六〇〇年李贽是否重刻了《焚书》,目前尚不清楚,不过,李贽后来对初刻《焚书》曾做增补,添入了一部分新的作品,这是可信的。管先生又说,他据以整理的这部《焚书》“是李贽已死,《焚书》遭到禁毁以后重刻的”,“是经过删节和改动的”。简而言之,管先生认为,李贽生前重刻《焚书》(一六〇〇年)的变化是“增入”作品,李贽死后重刻《焚书》的变化是对作品作“删节和改动”。由于《答耿司寇》是属于“删节和改动”,不属于“增入”的作品,则能使文本发生这种改变的自然是其他人,而不会是李贽本人。这么解释管先生的说明,应该是符合他意思的。
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焚书》和《续焚书》合订本,将这层意思就说得更加直接了。该书《再版说明》指出:“《焚书》在李贽生前刊行不止一次,但后来遭到禁毁。现在流传的《焚书》是李贽死后由别人重编刊行的,有些地方被人删改过。”[2]4明确肯定“删改”是别人的行为,与李贽无关。
然而,只认为李贽给初刻本《焚书》增加了一部分作品,排除他自己删节、改动《答耿司寇》等作品的可能性,这种思路对于弄清楚《焚书》文本变化,包括《答耿司寇》书信的删削究竟如何发生,其实是有迷惑或妨碍的。
李贽希望重刻一部经过修订的《焚书》,这是他暮年一桩很大的心愿。他对《焚书》曾作“批判”,《与焦弱侯》说:
《焚书》五册,《说书》二册,共七册,附友山奉览。乃弟所自览者,故有批判,亦愿兄之同览之也,是以附去者也。外《坡仙集》四册,批点《孟子》一册,并往请教。幸细披阅,仍附友山还我。盖念我老人抄写之难,纸笔之难,观看之难,念此三难,是以须记心复付友山还我也,且无别本矣。[5]卷1
所谓“批判”,是李贽将自己对《焚书》所收作品的看法写成评语、判断,或用符号表达看法,录在《焚书》纸页隙间。这反映李贽后来对《焚书》持续地思考、检验,以及再度斟酌,录下产生的新感受和认识。焦竑撰有《李氏焚书序》,是为李贽死后他人重刻《焚书》而作,序里谈到:“宏甫(李贽)曾以是刻商之于余,其语具载此中。”[6]卷首李贽与焦竑谈及《焚书》的书信,现存两封。一封是《答焦漪园》,写于万历十六年,信说:“更有一种,专与朋辈往来谈佛乘者,名曰《李氏焚书》,……今姑未暇录上。”[6]卷1这些话谈不上是与焦竑商量刊刻《焚书》。另一封即上引《与焦弱侯》,然而李贽在信里只是表示让焦竑“同览”有他“批判”的《焚书》等,而且特别关照他阅后必须将书归还给自己,这口吻也不像是在与焦竑商量刊刻之事。所以焦竑云“商之于余”,很可能是他对后来刻行的《焚书》与李贽“批判”语之间存在某种内在关系的一种理解。或许后来刻的《焚书》吸收了一部分“批判”语的内容。比如李贽《复焦弱侯》,初刻《焚书》所收完整,后来流传本《焚书》所收简略。李贽对这封书信所作的修改主要是删减内容,但是也偶有增加,如在“以学起名,以名起官”后,添入“循环相生,而卒归重于官”句,[6]卷2添入的内容很可能本来是李贽的“批判”语。或许在“批判”中,还有一些话是李贽对删节《焚书》的某种提示,其后转化成为对《焚书》具体的删改。若是这样,焦竑将李贽让他“同览”其“批判”的事情理解为是与他相商刊刻《焚书》,勉强也是可以成立的。
李贽还与人谈到要重刻《焚书》:
雪松昨过此,已付《焚书》《说书》二种去,可如法抄校,付陈家梓行。如不愿,勿強之。[5]卷1与方伯雨
发去《焚书》二本,付陈子刻。恐场事毕,有好汉要看我《说书》以作圣贤者,未可知也。如无人刻,便是无人要为圣贤,不刻亦罢,不要强刻。若《焚书》自是人人同好,速刻之。但须十分对过不差落乃好,慎勿草草。[5]卷1与汪鼎甫
“《焚书》二本”与“《焚书》《说书》二种”,两句话的意思相同。由此两信可知,李贽曾将手定的《焚书》新的稿本和《说书》先后托付给两人谋求刻行,这恰好说明他暮年为重刻《焚书》所作的不懈努力。值得注意的是,信所云“如法抄校”,“但须十分对过不差落乃好,慎勿草草”,可谓郑重其事,叮嘱谆谆,以示他对改动的部分十分重视。而合两封信观之,李贽叮嘱须仔细校对的书稿显然是指《焚书》,不是指《说书》。李贽重刻《焚书》增入了一部分新的内容,如后来流传的《焚书》包含一部分万历十八年以后写的书信即是。但是,对于增加的新作,留心抄写、校对都是很平常的作业,似不必用如此郑重的语气特意地加以关照。而若是他在书稿上作了较多修改,且其修改时,存(保留的内容)、删(删去的文字,删去的段落)、增(增添的文字)并见,改动情况比较复杂,那就需要特别提示抄校者,在编刻时要格外仔细和谨慎,否则很容易出现差错,而一出差错,或者违背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或者出现诸如书的目录与正文不尽一致之类技术性错讹。“如法抄校”,“但须十分对过不差落乃好”云云,如果是李贽出于这种考虑而提出的特别的关照,就很容易理解。李贽没有对重刻《说书》做类似的关照(上引第一封信“如法抄校”似包括《说书》,其实只是顺文提及,所引第二封信的叮嘱已将《说书》排除在外,即是明证),这应该是他对重刻的《说书》并没有做复杂的修改。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李贽提交重刻的《焚书》书稿经过了他本人复杂的改动。管玉林先生在《点校说明》中提到一个例子,《李温陵集》多出的“《答周柳塘》一篇,单行本(引者按指后来流传的《焚书》)目录上仍然保留着题目(卷二《寄答京友》篇后面),这正是删掉了正文但忘记从目录中删去篇目的一种痕迹”。[1]2这也可见李贽对人如此谆谆叮嘱并非多虑。
由上可知,李贽暮年对欲予重刻的《焚书》,不仅增入了作品,而且还进行了较为复杂的删改。我们将这一点确定下来,则《焚书》文本的一些变异现象,包括《答耿司寇》的删节,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下面,再说李贽删削《答耿司寇》的原因。
从万历十八年(1590年)《焚书》首次刊刻,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耿定向去世,在这七年里,我们需要注意一种新发生的情况,即李贽与耿定向之间的关系由高度紧张朝缓和的方面出现改变,而这正是导致他暮年修改《焚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焚书》初刻刚刚问世,耿定向立即以“闻谤”形容他读到此书后的感受,[7]卷8观生记心情愤怒,而“谤书”一词也成为他对《焚书》的严厉判断。[8]卷6求儆书附语这成为湖北麻城等地的乡绅及一方执政者驱逐、讨伐李贽的重要理由,使李贽的处境异常窘迫,以至滞留武昌难以返回麻城。他《与周友山书》说:“不肖株守黄、麻一十二年矣,近日方得一览黄鹤之胜,尚未眺晴川,游九峯也,即蒙忧世者有左道惑众之逐。”[6]卷2即说此事。这时,也有李贽一些好友,在李贽和耿定向之间调停解纷,以图改善李贽境况。李贽虽个性倔强,“铁石作肝”,[6]卷2与庄纯夫然而作为一个弱势者、老龄人,他走到这一步以后,事到逼迫,其实也是心存和解之念,希望平息风波。如他《寄焦弱侯》说:“夫耿老何如人哉,身系天下万世之重,虽万世后之人有未得所者,心且怜之,况如弟者,其钟爱尤笃至,乃眼前一失所物耳,安得不恻然相攻击,以务反于经常之路乎?谓我不知痛痒则可,若谓耿老乌药太峻,则谬甚矣。”[5]卷1《答来书》又称耿定向为“君子”,否定他会“落井下石害我”。[5]卷1《与友山》更是直接说:“我于初八夜,梦见与侗老聚,颜甚欢悦,我亦全然忘记近事,只觉如初时一般,谈说终日。……我想日月定有复圆之日,圆日即不见有蚀時迹矣。果如此,即老汉有福,大是幸事,自当复回龙湖,约兄同至天台无疑也。若此老终始执拗,未能脱然,我亦不管,我只有尽我道理而已。谚曰:‘冤仇可解不可结。’渠纵不解,我当自有以解之。”[5]卷2他这么谈论耿定向未必全可当真,可能有出于礼貌或无奈,甚至出于生存策略的考虑,不过他流露出来希望在友人调解下与耿定向达成和解的愿望确实是存在的,这也是当时李贽较为现实的一种选择。
开始,李贽对于是否能与耿定向达成和解比较悲观,他《与周友山书》说:“然事势难料,情理不常,若守其禁约,不肯轻恕,务欲穷之于其所往,则大地皆其禁域,又安所逃死乎?”[6]卷2三年后,经过一定曲折,情况发生改变。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李贽重新回麻城龙湖芝佛院居住,这应当是经过友人斡旋,注李贽与耿定向在一定程度上归好,以周友山所起之作用最为重要,《李氏续焚书·答梅琼宇》说:“乃今以友山故,幸得与天台(引者按,耿定向)合并。”他与耿定向的矛盾明显得到缓解的结果。次年李贽前往耿定向家乡黄安,两人见面,关系进一步解冻。李贽《耿楚倥先生传》说:“今幸天诱我衷,使余舍去‘未发之中’,而天台亦遂顿忘‘人伦之至’。乃知学问之道,两相舍则两相从,两相守则两相病,势固然也。两舍则两忘,两忘则浑然一体,无复事矣。余是以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黄安会天台于山中。天台闻余至,亦遂喜之若狂。志同道合,岂偶然耶?”[6]卷4根据李贽《耿楚倥先生传》的说明,两人达成和解前似乎都在思想上做了一定退让,原先李贽尊重人的自然禀性,耿定向强调人伦完美,相互对抗,而为了改善关系,营造安和相处的气氛,两人都似乎做出改变,收起锋芒不挑战对方。当然,两人关系之和解与思想差殊之弥合在李贽以上的记述中都不免被夸大,尽管如此,两人紧张对峙关系出现了明显舒缓的迹象则没有疑问。由于李贽与耿定向的关系有所回暖,他与别的一些人相处自然也会随之而调整。李贽对《焚书》的修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行的。
《答耿司寇》是李贽批判耿定向的一篇重要文章,锋芒毕露,文中潜含着李贽对自己与耿定向关系的痛苦思考,凝聚了作者丰富、剧烈、周密的心绪活动。书信除了从思想上辩驳论敌之外,还释放出对手负面的生活信息,作为思想论辩的一种辅助。耿定向读到《焚书》,特别是书中的这封长信后,激愤难平,蔽之以“谤书”二字,与李贽的关系彻底恶化。可见此信有关内容是二人关系中的一个“结”。既然后来李贽与耿定向的关系得到了一定改善,解除这个“结”也就有了必要和可能,对于耿定向来说,这自然会是他对李贽的一种要求,而对于李贽来说,接受这种要求也并不困难。在这种情境之下,李贽删削《答耿司寇》就很好解释了。
综合本文要点,李贽、耿定向的关系在暮年出现某种缓和,于是,先前因二人关系对峙而留在初刻《焚书》的一部分内容,特别是一些意气用事的文字,或者时过境迁,可以不再提及的一些事情,有了修改、调整的需要和可能。李贽通过修改,保留集束型书信《答耿司寇》根本的思想内涵,删去其中措辞最为激烈,旁及耿定向个人品格及其家族人事内容的第六封书信等,体现了李贽既保持自己一贯主要的思想,又认可与耿定向达成和解的意愿。这也是他对初刻《焚书》作出的最重要的修订之一。《答耿司寇》先后经过两次大的修改,第一次,李贽将七封书信合并为一封书信,改变了它们本来的书信状态,第二次,将合并的七封书信删去三分之一,保留其中五封书信,仍然保持集束型书信的形式。第二次是对《答耿司寇》修改的修改,使书信离开原貌更远(比如删去了集束型书信中第五封信末段)。这些修改的痕迹都是珍贵资料,我们通过研究其修改的全过程,可以窥探李贽、耿定向关系动态的、复杂的变化,从而对晚明发生的这场著名的耿、李之争获得更多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