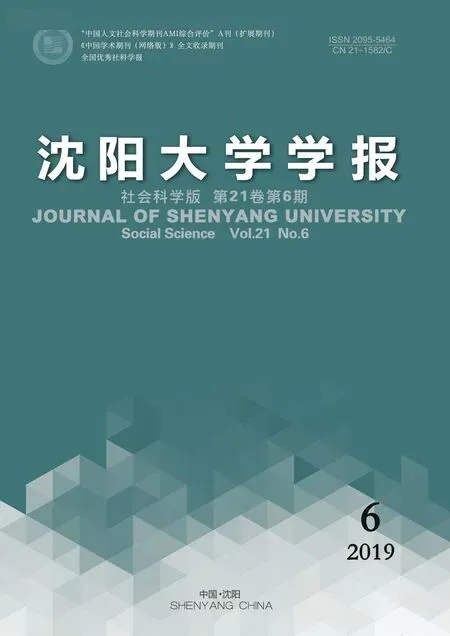从《尤利西斯》主人公的精神流浪看乔伊斯的身份意识
2019-02-09王振平师梦琪
王振平, 师梦琪
(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222)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空前发展。文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出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也给人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变化和心理焦虑。各种发达交通工具的出现使人们有了游走世界各地的便利,而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带来的精神危机却很难让人找到合适的发泄出口。于是,为了排遣情绪,有人酗酒,有人犯罪,有人在家冥思苦想,有人外出寻找出路。因此,流浪也成了一种社会现象。有些人流浪是为了糊口;有些人流浪则是因为深陷精神困境,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社会问题、种族问题充满疑惑,心灵空虚,前途迷茫。他们走出去更多的是想排遣心中的郁闷,发泄心中的不满,寻找心灵的寄托。他们的流浪除身体的游走外,更多体现为精神的流浪,情感的追寻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精神流浪主要指人的精神上的失落感、漂泊感、彷徨感、迷惘感、虚无感、荒诞感,以及心灵的无可归依感,是在精神上寻找出路中的迷惘,是对人存活的理由、现状及未来的怀疑与困惑[1]。
现代主义小说大师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擅长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他的意识流代表作《尤利西斯》以广告推销员利奥波尔德·布卢姆和青年诗人斯蒂汾·代达勒斯在都柏林一整天的游走为主线,描写了他们在1904年6月16日及第二天凌晨的经历。他们在这一天游走的所见、所闻、所想表现的情感缺失、迷惘无助、漂泊无依正是一种“精神流浪”,更反映了乔伊斯的一种复杂的身份意识。身份的形成不仅取决于自我, 还更多地受到自我与他者所处环境和互动进程的影响。它既是行为体自我认知的表征, 也是社会的产物, 是自我认知和社会文化语境中与他人互动交流的结果[2]。那么,《尤利西斯》中主人公的这种“精神流浪”是如何通过主人公自我及对环境的描写表现出来的?这种描写又体现了乔伊斯怎样的思想?
一、 “父与子”的精神流浪----亲情的缺失感
《尤利西斯》中的精神流浪首先体现在布卢姆和斯蒂汾父子亲情的缺失上。
布卢姆父亲去世,儿子夭折,他对他们充满思念。读着女儿米莉的信的时候,他不自觉想起夭折的儿子小茹迪,“要是活着,现在该十一岁了”[3]90;参加狄格南的葬礼,又想到了自己墓地里的亲人,“我的就在那边,靠近芬葛拉斯的那头,我买的那一块墓地。”[3]145;沿着小树林踽踽独行,惦记着父亲的忌辰,“二十七号我去给他(父亲)扫墓”[3]148。每当遇到相关的情景,布卢姆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的父亲和儿子,他们的离开是布卢姆内心无尽的悲痛。在生活中他体会不到任何父子亲情,享受不到作为父亲的快乐。
父亲和儿子的去世让布卢姆受尽他人的奚落。在巴尼·基尔南酒店,“公民”嘲笑他生儿子前的姿态,“布卢姆在他那夭折的儿子出生以前,那样子才妙呢。”[3]435布卢姆的性无能也遭到讥讽,“他就是那类不三不四的角色”[3]436。布卢姆先是用言语反抗,但随即逃跑了。亲人的离去本来就是布卢姆心中无法消除的伤痛,“公民”的无端诋毁更使他感到孤独痛苦。
与布卢姆相对的是在都柏林游荡的斯蒂汾。他的精神如身体一样无所归依。他需要一个让他的精神有所依托的“父亲”,即一个“精神之父”。渴求精神之父是因为他厌恶自己的亲生父亲,“父亲的粗俗可鄙和平庸无能都让他(斯蒂汾)迫不及待的想逃离”[4]。乔伊斯在形容斯蒂汾的父亲赛门的时候使用了“governor”一词,这说明赛门在家是独裁者、统治者,而父亲的不负责任又导致全家生活贫困。经济拮据,精神压抑,斯蒂汾感到无所适从。妹妹称他们的父亲是“不在天上的父亲”,讽刺父亲赛门虽然活着,却形同虚设。
斯蒂汾对父亲心怀不满,使他常对“父亲”这个概念陷入思考,在潜意识里不断追寻。马利根对斯蒂汾说:“唷,肯奇老爹的幽灵!杰菲特寻父!”[3]24,嘲笑斯蒂汾就像小说《杰菲特寻父》里的孤儿杰菲特一样寻父成狂;“Pater(拉丁语的父亲)!自由了!”[3]664这是斯蒂汾对自己理想父亲的呼唤,是神话中巧匠代达勒斯的儿子伊卡洛斯随父亲飞行时,翅膀被太阳烧毁而坠海时的呐喊,他向往的是精神的解脱,是一个象征自由的父亲。这个父亲可以帮他解决难题、脱离困境,是他心灵的依靠。
布卢姆在都柏林的街头不时追念已故的父亲,回忆早夭的儿子;斯蒂汾的母亲已逝,专制、不负责任的父亲使他感受不到父爱,父子亲情对于他只是一种虚无的感受。布卢姆渴望父亲身份,斯蒂汾需要一个精神之父,于是就有了他们的相互追寻和偶遇。
艾尔曼认为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的父亲就是赛门。乔伊斯是依照他父亲的形象来塑造赛门·代达勒斯这个人物的。乔伊斯的父亲和《尤利西斯》中的赛门一样,固执己见、常年酗酒,对孩子不负责任。家庭生活的困难和他有很大的关系。乔伊斯少年时对父亲的感受和斯蒂汾一样,他的知心人是他的母亲,而不是他的父亲----父亲是个不可能谈心的人[5]332。随着年纪的增长,乔伊斯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他的第三个孩子还未出世就流产了。对此,乔伊斯感到十分难过和惋惜,这次流产促成了《尤利西斯》中布卢姆的主要忧伤----儿子茹迪出生不久就夭亡[5]304。
文本读起来有时似乎是人物自己在书写,似乎是乔伊斯借笔给他们。布卢姆因失去儿子而产生的孤独感和斯蒂汾因对父亲赛门不满而产生的虚无感,正体现了他们父子亲情的缺失感,表达了乔伊斯对作为儿子和父亲身份时的意识与感受。在精神上,他需要来自父亲和儿子的爱。
二、 反英雄的精神流浪现代社会的迷惘感
《尤利西斯》中的精神流浪也表现为一种对于现代社会的迷惘感。小说的叙事结构是对荷马史诗《奥德赛》的戏仿,通过与《奥德赛》中英雄的对照描写,表现了反英雄式人物的现代困境与迷惘。
1. 神话英雄反衬的现代凡人
《尤利西斯》的题目源自《荷马史诗》中古希腊神话英雄奥德修斯(尤利西斯是奥德修斯的拉丁语名字)。《奥德赛》中,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奥德修斯攻破了特洛伊城,凯旋时却遇到海神波塞冬的万般阻挠。从特洛伊回归伊塔卡,奥德修斯经历了多重磨砺与考验,是英雄的流浪与回归。作为归乡英雄,奥德修斯是英勇无畏和敢作敢当的典型。人们崇拜这种历经艰难险阻、百折不挠、智慧出众的英雄。这样的故事对于鼓舞人心,激发斗志,培养人的优秀品格具有积极的作用。
《尤利西斯》的叙事结构与《奥德赛》极为相似,这是乔伊斯的有意戏仿,他就是要以古喻今,以古讽今。从内容上看,两者都涉及到流浪与回归,《奥德赛》述说的是奥德修斯历经十年终返故乡的故事,而《尤利西斯》主人公布卢姆的游历则仅为一天,地点也局限于都柏林市内,主人公的形象谈不上伟大,经历算不上艰辛,既没有离奇曲折的奋斗故事,更没有激动人心的励志经历。布卢姆只是因为妻子出轨而离家,在都柏林的街上游荡一天,经历了诸多闲事琐事,然后回家睡觉而已。
2. 现代流浪者的精神追寻
20世纪,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空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大,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显然,宏大的斗争主题、勇猛的仗剑英雄已经成为人们心中遥远的回忆,人们更加关注的是眼前的现实,看到的是生活的贫困,是人的自私、贪婪、冷漠。人们固有的观念开始动摇,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对现实社会充满恐惧。人们忍气吞声,精神空虚,甚至只是蝇营狗苟地生活着。
乔伊斯小说没有关注那些彰显民族精神的传统凯尔特人和民族英雄,而是聚焦于现代社会中的小人物[6]。现实生活中没有英雄,没有英雄主义,满眼皆是像布卢姆这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布卢姆只是一个普通的广告推销员,生意不好,事业毫无起色,在家中没有地位。他没有直面出轨的妻子及其情人去揭露奸情,却选择屈辱地、窝囊地离开家门,躲避妻子与其情人的幽会。《尤利西斯》以借古讽今的手法所要表现的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全部历史:布卢姆的庸人主义、斯蒂汾的虚无主义和莫莉的肉欲主义正是现代西方社会道德和精神文明的深刻写照[7]。在奥德修斯英雄光环的映衬下,布卢姆这个现代社会的小人物显得平庸、卑微。他没有使命感,没有凯旋的骄傲,也没有成为伟大英雄的目标,他所想的只是庸人所想,所为的只是凡人所为。
布卢姆在都柏林一天的经历,表面上反映的是他为了生存而奔波,实质上反映的是他内心的无所寄托。与斯蒂汾的交往是他在冥冥中追寻心灵寄托和精神家园。这不是英雄主义的追求,只是凡俗小民的情感需求,而这正是现实的反映,他的流浪行为和他的精神追寻正是都柏林现代社会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的真实写照。
乔伊斯把尤利西斯描绘成一个和平主义者、父亲、漂泊者、音乐家、艺术家,把这位英雄的一生紧紧地和自己联系起来[5]475。布卢姆的流浪行为和精神空虚的心理状态,正是乔伊斯本人的精神写照。乔伊斯曾说:他(乔伊斯)是一个外国人,身无分文,脆弱不堪[8]。置身于现代社会的变革洪流中,乔伊斯感受到的是恐惧和无奈,他能做的只有逃避,和小说主人公情形相似,他就是在无奈与无助当中逃离都柏林的。他的选择不是面对,不是抗争,而是逃避、退缩。他恰好用《奥德赛》中的英雄壮举来反衬小人物的庸俗窝囊。
三、 殖民统治下的精神流浪民族的漂泊感
《尤利西斯》中的精神流浪还表现为一种爱尔兰人的漂泊无依感。内忧外患的爱尔兰,民生凋敝,人民苦不堪言,身在爱尔兰的犹太人更屡遭歧视与迫害。爱尔兰人民在精神上迷茫无助,而爱尔兰的犹太人更难以体会到民族身份的归依感。
1. 殖民统治的国家
爱尔兰从12世纪初开始遭到英国侵略,于1801年并入英国版图,成为大英帝国的第一个殖民地。1922年,爱尔兰南部26个郡获得自治权,1949年,这些郡才建立了完全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爱尔兰对英国重要是因为它是英国的廉价食物来源:在过去150年里,无论以什么形式剥削,这一直是其本质[9]。在乔伊斯写《尤利西斯》的时候,爱尔兰还在英国统治之下,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虽然在殖民者的镇压下爱尔兰人也在反抗,但他们并不团结,甚至还在进行民族内部的斗争,致使多次民族解放运动均以失败告终。
《尤利西斯》第一章写到,斯蒂汾他们吃早饭的时候进来一个送奶的老妇人,“一个四处奔波的老妪,侍候着征服她的人和寻欢作乐出卖她的人,他们都占有她而又随意背弃她,这个来自神秘的清晨的使者。是来侍候人还是来谴责人,他说不清,但他也不屑于求她的恩惠。”[3]18有学者认为:“一个四处奔波的老妪”指英国殖民者和天主教会联合统治下的爱尔兰社会的卫道士,他们以爱尔兰复兴运动参与者的身份出现,也象征着爱尔兰;“征服她的人”暗指英国人海因斯,代表爱尔兰的征服者----英国殖民者;“寻欢作乐出卖她的人”暗指满足于现状的马利根,象征20世纪初甘心作异族奴隶的人[10]。许多爱尔兰人同“送奶的老妇人”一样,不过是在为殖民者服务。此外,像海因斯这样的“殖民者”,一边张扬自己的英国人身份,一边又显示尊重,告诉老妇人“在爱尔兰就应该说爱尔兰语”[3]19,结账的时候却又找马利根,这些都不过是在塑造自己完美、强大的统治者的身份。乔伊斯对于他们的态度与斯蒂汾一致----不屑于爱尔兰人的复兴运动。他眼中的爱尔兰是一个精神世界疲软的爱尔兰。爱尔兰的独立,需要爱尔兰人在精神上洗心革面。
乔伊斯在青年时期曾经这样评价爱尔兰和都柏林:政府在那里(爱尔兰)种下了饥饿、梅毒、迷信和酗酒;清教徒、耶稣会会士和宗教偏执狂迅速蔓延。“都柏林人是我所见到过的全岛或整个大陆上最无望、最无用、最反复无常的一群冒充内行的骗子。”[5]244乔伊斯不喜欢爱尔兰,他觉得爱尔兰也不喜欢自己。乔伊斯塑造的爱尔兰恰恰塑造了一种展示爱尔兰人民族性的风景。风景对于民族性的塑造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甚至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因素[11]816。当时爱尔兰的人们有一种被殖民的疏离感,心灵无所寄托,前途渺茫。布卢姆所代表的犹太人更是因民族身份受尽排斥。他们的精神流浪是对国家独立的渴望,也是对民族身份的追寻。乔伊斯呈现给读者一个在殖民压迫下,在天主教的精神控制下和在民族主义的蛊惑下的灵魂麻木、不知亡国之恨的爱尔兰民族的生存状态,从而表达他自己对爱尔兰民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切情怀[12]。
2. 无所归依的身份
犹太民族是流浪民族的典型代表。犹太人遍布世界各地,他们不仅没有因为散居的流浪生活而消亡,反而凭着坚强的民族精神更为壮大。在布卢姆生活的爱尔兰,爱尔兰人并没有因为有共同的祖国、共同的生活际遇而团结一致,抵抗侵略,反而嘲笑、歧视犹太人,更加深了人们心中犹太人的流浪者形象。布卢姆就是乔伊斯笔下一个典型的犹太人,他的流浪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的是整个犹太民族的流浪,他们身体居无定所,精神无所寄托,对于安定生活和美好家园,对于民族身份和自由意志更是充满了渴望。
布卢姆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和根深蒂固的民族思想。他善良友好、乐于助人、不酗酒、有教养,甚至还有艺术家的气质。他的性格是犹太人性格的缩影。但也正因此,他不合群而受到排挤。除性格的不合群外,犹太民族传宗接代的传统也让他感到自卑。犹太人认为婴儿如果健康,根源在于母亲,不健康的话,根源在男人[3]125。布卢姆失去了心爱的儿子,还没有继续繁衍后代的能力,这都成为他迷茫彷徨、无奈无助的原因。布卢姆对国家和民族深深的爱与国家所处的境遇、民族受到的迫害形成鲜明对比,他找不到归属感,找不到自己的根。民族传统对子嗣的重视和自己失子无后的现实使他深感愧疚,因此,他感到有家难归,后继无人,身体无所归依,精神无所寄托,流浪成为不得已的选择。乔伊斯以利奥波尔德·布卢姆为主人公,重申他常常直接谈到的一点,就是他对犹太人这一流离失所、备受迫害的民族有认同感。他本人的许多经历都变成了布卢姆的经历[5]428-429。
四、 结 语
《尤利西斯》中,布卢姆和斯蒂汾在都柏林的游荡、亲近和依赖反映了两人的精神需求。生活艰难,亲情缺失,社会冷漠,种族遭受凌侮,国家前途渺茫,让布卢姆有家难归,让斯蒂汾无家可归,而他们身体的流浪反映的正是他们心灵的空虚和对精神家园的渴望。他们的这种流浪正是所谓的“精神流浪”。斯蒂汾和布卢姆在流浪中遇到了对方,两人互相成全,得以相聚,都在对方身上找到了安慰、寄托和归属感。
1904年,爱尔兰仍然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中,爱尔兰人在政治、文化上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同感,在精神上缺乏应有的归属感。而浪迹在都柏林的布卢姆和斯蒂汾就是部分爱尔兰人的代表,作为父亲和儿子,他们感受不到生活的幸福;作为爱尔兰人,他们没有应有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而作为反抗者,他们有的只是愤怒和无力。这就是当时乔伊斯心目中的爱尔兰和爱尔兰人。流浪的、没有着落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身体,还有他们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