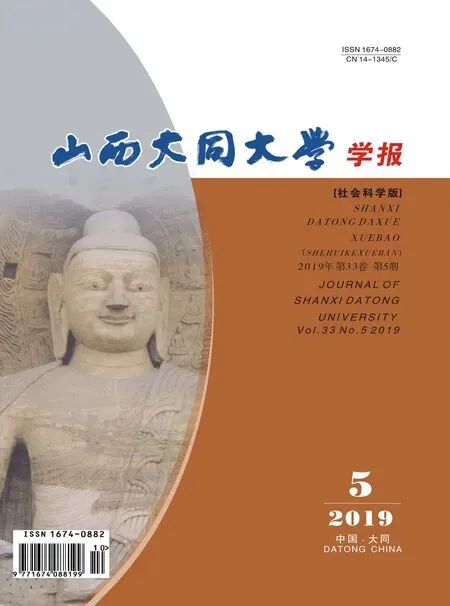唐武宗会昌毁佛的文学记忆
——兼论晚唐文人集体失声的原因
2019-02-09方胜
方 胜
(安徽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唐人对时事格外敏感,在他们饱和深情的笔墨里记述了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历史事件;但对于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会昌毁佛”运动,绝大部分文人都选择了沉默。会昌毁佛影响不大吗?显然不是,它是中国古代“三武一宗”灭佛运动中唯一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毁佛运动,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昌毁佛与文人关系不密切吗?拆毁寺院、勒令僧尼还俗、毁去佛教器物等似乎与文人无关,但众多晚唐文人与佛僧交游,在寺院读书习业,甚至信仰佛教,与佛教关系颇为密切。那么,晚唐文人对如此重大的社会事件集体失声的原因究竟何在?笔者不揣谫陋,试作分析,并求教于方家。
一、晚唐知名文人与会昌毁佛
先来看看会昌时期文坛的概况和较为著名文人的经历,为了便于叙述,根据会昌文人与毁佛运动的关系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一)会昌毁佛的决策者——以李德裕为代表 唐武宗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即位,“七月,召德裕于淮南;九月,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1](卷174,P5421)李德裕成为武宗朝首辅。会昌年间对内平叛藩镇、削弱宦官权力、整顿吏治和科举、打击佛教,对外坚决抗击回鹘入侵,这些重大举措都与李德裕密不可分。李德裕在毁佛中所起的作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有人认为他起到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也有人认为他积极参与毁佛;还有人认为他并非一贯反佛,在会昌毁佛中的作用也非常有限;[2]甚至有人说他是无关紧要的角色,没起多大作用。[3]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其所著《梁武论》《祈祭西岳文》来看,李德裕反佛的思想由来已久;并且在浙西、剑南任职时已经开始拆毁浮屠私庐,着手打击佛教;执政以后,又多次奏请,先后沙汰了部分僧尼,对僧尼的一些活动,也进行了种种限制。由此可见,李德裕在毁佛运动中无疑是起到了决策的作用。他在此期间政务极为繁忙,绝大多数文章都是政治文书,因此涉及佛教事宜,也仅在政治文书中提及,并没有专门的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作品是《贺废毁诸寺德音表》。
(二)会昌毁佛的执行者——以杜牧为代表 杜牧(803-约852)会昌元年任比部员外郎,二年外放为黄州刺史,四年(844)九月迁池州刺史。从他留存的《池州废林泉寺》《还俗老僧》和《斫竹》等诗来看,杜牧在池州坚决执行了朝廷毁佛命令。此外,在宣宗恢复佛教时,杜牧还写下了《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表达了自己反佛的心声。[5]其他在地方任职的文人,如令狐绹、许浑等,以及牛僧儒、李宗闵等“牛党”成员多被贬在外,均未见到有相关作品。
(三)会昌毁佛的旁观者——以白居易、李商隐为代表 白居易于会昌三年以刑部尚书致仕,时年72 岁,会昌六年八月卒。白居易晚年坚持创作,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读过白居易全部作品的人看到的,却是一个在晚年不断重复自己的诗人”。[6](P392)他这段时期作品最主要的内容是朋友相聚、怀念旧游、把酒言欢、自叹长寿等,基本不涉及时事。李商隐在会昌二年(842年)春,应书判拔萃科后授秘书省正字,该年冬其母去世,之后为姊、侄女等家人的葬事曾奔走他处,直至会昌五年十月,母丧期满后回京复为秘书省正字。这期间李商隐与知(智)玄、僧徹(澈)等僧徒有较为深入的接触,交往密切、互动频繁;但他与白居易一样,没有只言片语提及毁佛事件。温庭筠此时尚在为科举而奔走于权贵之间,段成式会昌三年任秘书省校书郎,姚合会昌年间先后任右谏议大夫、秘书监,均未对毁佛事件发表任何言论。
(四)会昌毁佛的受害者——以僧人为代表 《景德传灯录》卷九《福州龟山智真禅师》中记述了龟山智真在会昌毁佛中被迫还俗,有偈二首,[7](P608)其一:“明月分形处处新,白衣宁坠解空人。谁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为长者身。”意思是说禅无处不在,即便还俗也不妨碍修道,传说维摩本是金粟如来现身,他虽然是身着白衣,但道行远超佛的声闻弟子和众菩萨。其二:“忍仙林下坐禅时,曾被歌王割截支。况我圣朝无此事,只令休道亦何悲。”借用哥利王为验证仙人是否还有贪著而割其耳鼻削其手的典故,表明自己坚定不移的修道决心。武宗毁佛并没有如此残忍血腥,“只令休道”而已,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
《景德传灯录》卷二三《泉州龟洋慧忠禅师》中记载了慧忠三首偈[7](P1819):其一:“雪后始谙松桂别,云收方见济河分。不因世主教还俗,那辨鸡群与鹤群?”以比兴的手法来说明,正是因为毁佛,才能检验出修道的真伪。其二:“多年尘事谩勝腾,虽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满头留发候然灯。”以前虽然身在佛寺,但并没有悟道;现在虽然还俗蓄发了,但才是真正的修行。其三:“形容虽变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更读善财巡礼偈,当时何处作沙门?”以善财童子作比,表明自己求道之心。
写类似的诗偈的人都是毁佛运动的直接受害者,在“法难”之中或之后,以偈明志,表达对毁佛的不满和自己坚定修行的决心。但有意思的是,会昌时期较为著名的诗僧如无可等,并没有在作品中诉说自己的遭遇,表达对毁佛的态度。
通过以上概述可以看到,会昌时期的文坛呈现了新旧交接的局面,刘禹锡、贾岛、李翱等人已去世,白居易、李绅、姚合等人年寿已长,“咸通十哲”等诗人还未成气候,多位牛党成员被贬的远在天边,多位李党成员掌权的忙着政务。晚唐“三大家”杜牧、李商隐、温庭筠在会昌年间也步履艰难,温庭筠游荡无所依,还在为科举苦苦奋斗;李商隐辗转藩镇,徘徊在牛李两党之间,刚刚谋得京城小官,又逢母丧丁忧;只有杜牧在偏远小州遥望朝阙,不懈努力。
二、与会昌毁佛有关的文学作品
经过仔细翻检晚唐时期的各种诗文集,发现与会昌毁佛有关的文学作品实在有限。为了便于后文分析时人对待毁佛的态度,以武宗去世、宣宗即位为界,以创作的时间将反映会昌毁佛的文学作品分为两部分。
试验组生猪出栏总体重为3 302 kg,成活头数为29头,头均增重为103.48 kg;对照组生猪出栏总体重为2 843 kg,成活头数为27头,头均增重为97.65 kg。试验组生猪的头均增重较对照组增加5.83 kg,增加5.97%,差异显著(P<0.05)。
(一)武宗毁佛期间的作品 首先要提及的是李德裕《贺废毁诸寺德音表》,该表作于会昌五年八月七日,开篇直接说明毁佛之功,然后再论毁佛之理,最后阐明毁佛之意义。这篇政治文书可谓是一篇文辞优美、说理有力的文学作品。
杜牧有三首诗较为明确地反映了毁佛后寺院、僧人的情况。《池州废林泉寺》云:“废寺碧溪上,颓垣倚乱峰。看栖归树鸟,犹想过山钟。石路寻僧去,此生应不逢。”[8](P214)诗中描写的是一座因会昌毁佛而被拆毁的寺庙。寺废,墙塌,僧人离去,一派荒凉之景。《斫竹》云:“寺废竹色死,官家宁尔留。霜根渐随斧,风玉尚敲秋。江南苦吟客,何处寄悠悠。”[8](P243)借废寺之死竹,表达无所依托的苦闷之情。《还俗老僧》云:“雪发不长寸,秋寒力更微。独寻一径叶,犹挈衲残衣。日暮千峰里,不知何处归。”[8](P242)陆游认为此诗“盖会昌时废佛寺所作也。……词意凄怆,盖怜之也”。[9]的确如此,老僧还俗后蓄起了头发,短发尽白,年老力衰,无家可归。张祜《毁浮图年逢东林寺旧》云:“可惜东林寺,空门失所依。翻经谢灵运,画壁陆探微。隙地泉声在,荒途马迹稀。殷勤话僧辈,未敢保儒衣。”[10](卷510)所写与之类似。在以上诗歌中看不到诗人对待毁佛的态度,只是在描述毁佛以后的寺院和僧人情况,尽管有惋惜、同情之意,但不能据此认为诗人是在反对毁佛。
刘蜕《移史馆书》云:“伏以释氏之疾生民也,比虞禹时,曷尝在洪水下;比汤与武王时,曷尝在夏政商王下;比孔子孟轲时,曷尝在礼崩乐坏杨墨邪道下。然而圣主贤臣,欲利民而务除民害,如此其勤也。今释氏夷其体而外其身,反天维而乱中正。……今天子聪明,以为中正衣冠之所弃,则刑政教化亦无所取。故绝其法,不使污中土。未半年,父母得隶子,夫妇有家室,是以复出一天下也。仆故谓其功业出禹、汤、武王、孔子、孟轲之上。”[11](卷789,P8257)从文中“圣主贤臣”可知,此书作于会昌末年。刘蜕先言佛教之弊害,再畅想僧尼还俗后成家之乐,赞武宗之功德。
除上述以外,会昌年间直接讨论毁佛事件、表达自己见解的文学作品几无所见。
(二)宣宗朝及其后的作品 第一类是赞同毁佛。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云:“武宗皇帝始即位,独奋怒曰,穷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台野邑四万所,冠其徒几至十万人,后至会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东京二寺。天下所谓节度观察,同、华、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数,其他剌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缕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万五百,奴婢十五万,良人枝附为使令者,倍笄冠之数,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口率与百亩编入农籍,其余贱取民直,归于有司,寺材州县得以恣新其公署传舍。”[12](P154)此文作于宣宗即位后,杜牧对其恢复佛教表示担忧,列数佛教之危害,记述了武宗会昌毁佛的经过和成果,从字里行间不难读出杜牧对毁佛是持赞同态度的。
孙樵《武皇遗剑录》所云与杜牧的见解相似:“浮屠之流,其来绵绵。根盘蔓滋,日炽而昌。蛊于民心,蚕于民生。力屈财殚,民恬不知。武皇始议除之,女泣于闺,男号于途。廷臣辩之于朝,亵臣争之于旁。群疑胶牢,万口一辞。武皇曾不持疑,卒诏有司,驱群髡而发之,毁其居而田之。其徒既微,其教仅存。民瘼其瘳,国用其加。风雨以时,灾沴不生。非武皇四用其剑耶?”[11](卷795,P8333)孙樵(约 825 一约885),字可之,又字隐之,唐宣宗大中时进士,官中书舍人,后迁职方郎中、上柱国,是唐末古文运动的代表作家。孙樵在文中列举了武宗的四大功绩:讨回鹘、定太原叛卒、平泽潞、会昌毁佛。
第二类是反对毁佛。最具代表性的是李节《饯潭州疏言禅师诣太原求藏经诗序》,文曰:“会昌季年,武宗大翦释氏,巾其徒且数万之民,隶具其居,容貌于土木者沉诸水,言词于纸素者烈诸火。分命御史,乘驿走天下,察敢隐匿者罪之。由是天下名祠珍宇,毁撤如扫。”[11](卷788,P8249)李节,生卒年、籍贯皆不详,宣宗大中时登进士第。毁佛之后,潭州道林寺僧疏言前来太原搜求经卷,返回湖南之际,李节写此诗相赠。李节崇佛,反对毁佛。有学者说:“这里的见解,代表着一部分经历了唐武宗毁佛到唐宣宗兴佛这一历史转变过程的士大夫对佛教的认识。”[13](P251)
第三类是描述毁废佛寺。郑隅《津阳门诗并序》长达100 韵共1400 字,“为三唐歌行中第一长幅,可与《连昌宫词》、《长恨歌》参观”[14](凡例)。郑嵎,字宾光(一作“宾先”),生卒年不详,大中五年(851)进士及第。津阳门是华清宫北门,郑隅及第之前曾在华清宫东面的石瓮寺读书习业。此诗以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为线索讲述了盛唐由盛而衰的历史经过,其中一段描写了会昌毁佛之后华清宫遭遇的陵谷变迁:“会昌御宇斥内典,去留二教分黄缁。庆山污潴石瓮毁,红楼绿阁皆支离。奇松怪柏为樵苏,童山眢谷亡嶮巇。烟中壁碎摩诘画,云间字失玄宗诗。”这段记述“大有昔盛今衰的感慨,历史的‘豪盛’与眼前的凄凉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有不胜唏嘘之叹”[15]。
刘沧有两首诗描述了经过毁佛运动后寺院的凄凉景象,《经龙门废寺》云:“山色不移楼殿尽,石台依旧水云空。唯余芳草滴春露,时有残花落晚风。”[10](卷586)《题古寺》云:“古寺萧条偶宿期,更深霜压竹枝低。长天月影高窗过,疏树寒鸦半夜啼。池水竭来龙已去,老松枯处鹤犹栖。伤心可惜从前事,寥落朱廊堕粉泥。”[10](卷586)寺院已毁,高僧已去,昔日的繁华从寥落的朱廊中依稀可见。刘沧屡举进士不第,宣宗大中八年(854)及第时已是白发苍苍,其生活的年代正是会昌至大中年间。
李洞《题新安国寺》云:“佛亦遇艰难,重兴叠废坛。偃松枝旧折,画竹粉新干。开讲宫娃听,抛生禁鸟餐。钟声入帝梦,天竺化长安。”[10](卷721)描写了毁废的寺院重新恢复后的情景。李洞是唐末昭宗时人。类似的作品还有一些,但无法确定所咏佛寺是否因为会昌毁佛而废,故不再一一列举。
另有一些笔记小说中记载了毁佛时的故事,如李绰《尚书故实》中记载会昌毁寺时苏监察偷偷拿走银佛,有官员找白居易索要本是他添补的银佛[16](第862册),皇甫枚《三水小牍》记载毁佛时僧徒四处逃窜的情景,等等。
三、晚唐文人对会昌毁佛集体失声的原因
虽然白居易、李绅、李商隐等很多著名文人都亲身经历了会昌毁佛事件,但他们对此似乎漠不关心,几乎没有就此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会昌文坛并非不关心时事政局,会昌三年大破回鹘乌介部,迎回太和公主,多位文人赋诗歌咏此事。为什么对于朝廷轰轰烈烈开展的毁佛行动却异乎寻常地一致沉默呢?
(一)理智与情感的矛盾 从情感上来说,晚唐文人多与佛教徒交游,甚至信佛,还有不少人曾经在寺院读书习业,与佛教徒关系较为亲近;从理智上来说,他们意识到佛教发展过于迅速给社会带来了较大的危害。因此,面对毁佛运动,他们内心难免会产生矛盾。
唐代很多文人对待佛教的态度是矛盾的。白居易早年写过《策林·议释教》:“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臣窃思之,晋、宋、齐、梁以来,天下凋弊未必不由此矣。”[17](P3545)以及新乐府《两朱阁》:“忆昨平阳宅初置,吞并平人几家地。仙去双双作梵宫,渐恐人间尽为寺。”[18](P364)从这一文一诗来看,白居易反佛是毫无疑问的。但事实上,白居易自云“栖心释梵”[18](P2627),“通学小中大乘法”,[17](P3782)熟读佛经,其《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中统计了《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维摩经》等八种佛经的字数,用简洁的语言归纳了各经的主旨,可见他对佛经颇有研究。白居易还办理了入教手续,成为在家佛教徒。这是文人们对待佛教态度上理智与情感相矛盾的典型表现。
毁佛运动中大量寺院被拆废,许多精美的壁画、佛像和佛器被毁坏,着实令人感到惋惜;但晚唐时期不少人为了逃避徭役和赋税入寺院为僧为尼,寺院占据了大量田地,拥有众多奴婢,既不利国,也不利民。思想敏锐的文人们洞悉这一切,难以公开反对毁佛,也难以赞同毁佛。赞同毁佛,有违自己内心对佛教的那一份依恋;反对毁佛,亦有违自己内心的那一份清醒认识和朝廷严厉的政令。
(二)全身远祸的思想 “恐怖的历史事件往往会扭曲文人的心态。如甘露之变,就使得文人产生全身远祸的心理,文坛走向由反映社会转为表达自己的感情世界,文人由社会的参与者转化为社会的旁观者”。[19](P534)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发生的“甘露之变”,导致四位宰相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被杀,其他遇难的公卿及被株连之人多达一千余人,从此以后,“两省官应入直者,皆与其家人辞绝”。[20](卷245,P7921)朝廷要员生命朝不保夕,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这种情况下还有多少文人敢开口议论朝政呢?有不少文人经历永贞革新而被贬官,常常会在作品中流露出政治失意之感;但毕竟只是宦海沉浮,没有危及性命,而且随时还有被召回的可能和希望。刘禹锡被贬23年,回朝时还是乐观地高歌“前度刘郎今又来”;但面对甘露之变,刘禹锡基本上选择了沉默,心有不甘地写下了格外隐晦的《有感》,这是来自内心的恐惧。
会昌毁佛距离“甘露之变”不到十年时间,血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此时牛李党争日趋激烈,随着李德裕担任宰辅,李党大获全胜,李宗闵、牛僧孺、杨嗣复、李迁等牛党人士全部外贬,甚至被流放。会昌文人们多与牛李二党有着某些瓜葛,白居易、李商隐是典型的代表。
李商隐徘徊于两党之间,情感上与牛党关系亲近,政治上却肯定会昌之政。毁佛期间,李商隐在长安为秘书省正字,但从他的诗文中看不到任何相关记述,陈引驰先生曾注意到这个问题:“考查李商隐与当时佛教的交涉,不能不想到他亲身经历的会昌毁佛这一佛教史上的大劫难,然面我们在义山的诗文中完全看不到他的反感,这一事件于义山似乎了无影响。其实沉默也可以是一种态度。”[21](P129)陈先生进一步分析:“他反在诗中一再讽武宗之求仙,如《昭肃皇帝挽歌辞三首》《汉宫词》《汉宫》《茂陵》《华岳下题西王母庙》《华山题王母庙》《瑶池》《海上》等,都是意旨明确的讽喻诗,其意甚可玩味。”[21](P129)李商隐是不是认为武宗因求仙而毁佛呢?是不是因不满武宗毁佛而沉默呢?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包括李德裕在内的不少士人都反对武宗过度迷信道教、宠幸赵归真求仙,作品也相当常见。也就是说,反对求仙并不是武宗和李德裕等人的“逆鳞”;但省并佛寺、沙汰僧尼是国家意志,反对毁佛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很难说了。
白居易的情况其实也有类似之处。从家庭和个人情感因素来看,白居易倾向牛党是无疑的。元和二年,白居易娶牛党骨干杨汝士、杨虞卿从妹为妻,白居易与杨氏兄弟诗文唱和,关系融洽。从个人经历来看,白居易与牛僧孺的关系也很亲密。早在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因科举对策中批评时政而得罪宰相李吉甫,三人均未按常例授官,出为幕职。时任左拾遗并参与覆策的白居易向宪宗上《论制科人状》,力论牛僧孺等不当贬黜。白居易与牛僧孺赠酬之作有近30 首,关系非同寻常。从政治见解方面来说,白居易又不赞同牛僧孺的保守思想,主张有所作为,倾向于李党。白居易与李德裕交往不多,但他们其实在很多政见上是有一致之处的,如打击藩镇割据、不满宦官专权等,而且李德裕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在文宗朝牛李斗争激烈之际白居易主动请求出居洛阳,从此过着“中隐”的生活,优游卒岁,不问世事。身处党争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不测之祸,这可能是白居易、李商隐等著名文人不愿意对毁佛事件发表言论、创作诗文的重要原因。
诚如胡可先所言:“甘露之变后的晚唐文人,对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深感忧虑,中唐时期那种积极用世、改革社会的革新精神,被全身远祸、冷眼旁观的漠然心态所代替。”[19](P492)经过永贞革新和甘露之变以后,会昌时期的文人们或多或少都会卷入牛李党争,在此背景下,文人们对李德裕主导的毁佛运动不愿意轻易开口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置身事外的态度 不同于“永贞革新”和“甘露之变”,会昌时期的文人们并没有直接置身毁佛事件之中,自身也没有遭遇特别的痛苦与打击,面对朝廷的高压政策自然也就没有以身犯险的必要了,因此他们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愿意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会昌毁佛是“精准打击”,针对性极强,有着较为充分的历史准备,而且相对温和,基本上没有发生流血冲突[22]。自唐初开始,就发生过多次反佛事件,傅奕是唐代反佛的先驱,狄仁杰、李峤、桓彦范、韦嗣立、薛谦光、慕容珣、辛替否、姚崇、杨炎、张镐、高郢、常衮、李叔明、彭偃、裴伯言、韩愈、李翱等都曾反对佛教,或者反对统治者过度迷信佛教。在武宗即位之前,文宗意识到:“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11](卷10,P154)并且下诏《条流僧尼敕》:“丁壮苟避于征徭,孤穷实困于诱夺。……京兆府委功德使,外州府委所在长安吏,严加捉搦,不得度人为僧尼。”[10](卷74,P778)武宗会昌三年已经开始勒令部分僧尼还俗,拆并佛寺。 经过长时间准备,无论僧尼还是包括文人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在心理上已经不同程度接受了这个事实,因此毁佛过程中没有出现过激反应。尽管有些文人出于同情心,暗中对僧人伸出援手,但也仅限于提供不违背朝廷禁令的便利和物质上的资助,并没有在舆论上反对毁佛。
文人多习禅宗,不重庙宇,可能也是他们保持沉默的一个原因。晚唐时期,禅宗逐渐盛行,由于禅宗主张见性成佛,不重佛典,不重佛像寺院,而且在伦理道德方面有很多地方与儒家有一致之处,因此深受文人喜好。陈垣先生认为:“会昌五年毁佛,教家大受挫折,惟禅宗明心见性,毁其外不能毁其内,故依旧流行。”[23](卷2)确实如此,在会昌毁佛之后,禅宗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由于具有简捷方便、直指人心的特点,便以其‘一花开五叶’的势头得以迅速发展,进而无比兴盛。”[24](P209)由于文人与禅宗关系更密切,在毁佛中更是置身事外,保持沉默。
综上所述,会昌时期的文坛呈现出新旧交接的局面,永贞革新和甘露之变等政治事件给文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面对武宗和李德裕大力推行的毁佛运动,无论是运动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还是旁观者和受害者,他们都很少发表自己的看法,也很少表明自己的态度,更不愿意在文学作品中记录、讨论和反思毁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