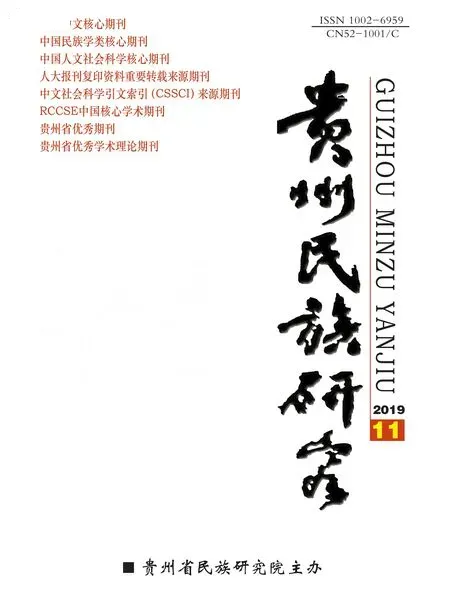嘉靖、隆庆年间的“石州之变”
2019-02-09崔广哲
崔广哲
(吕梁学院 历史文化系,山西·离石 033001;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在明代,石州归太原府管辖,其辖区相当于今天山西离石、方山、柳林。对于此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评论说:“州重山合抱,大川四通,控带疆索,锁钥汾、晋,诚要区也”,“州西踰黄河即延、绥边地,北边偏、老,最属要冲”,然而“嘉、隆之间敌往往入寇,州境被其蹂躏”[1],当地百姓深受其害。这里的“敌”即以俺答为首的蒙古军队。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地区,蒙古军队却能多次深入而不受重创?明朝军队和官员如何应敌以及事后明朝又是如何整顿边防的?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试图以明蒙关系为背景来探讨以俺答为首的蒙古军队对石州等地骚扰及其影响。
一
俺答(1507-1582年),蒙文史籍为阿勒坦,蒙古右翼首领巴尔斯博罗特次子,是明代蒙古靼鞑部的首领。俺答自嘉靖八年(1529年)叩关至隆庆五年(1571年)和议,持续了40余年。在这40余年间,蒙古兵数次深入内地,更甚者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深入京师,史称“庚戌之变”。明代边境有九座重镇,山西的大同、山西(今偏关)为其中之二。蒙古兵多次越过山西二镇进入山西内地,给当地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其中有三次到达石州,而以二三次危害最大。
嘉靖十九年(1540年)八月,俺答率部由大同进入山西内地,“流劫岢岚、兴、岚、石州、静乐等处。”[2]这是史书中第一次提到嘉靖年间俺答兵至石州。俺答这次重在掠夺财物,以迫使明朝通贡,逗留时间较短。
得知俺答兵自朔州进入山西后,巡抚山西都御史陈讲乞兵策应。嘉靖帝派大同、延绥兵3000前往救援,援军未至,俺答已退兵。但明朝官兵的反应,大大出乎人们的遇料,如山西副总兵魏庆不敢战,仅尾虏后,“有二虏直贯其营,庆惧不敢出”[3];巡抚大同史道、总兵王升、宣府总兵白爵调赴应援,亦观望不战。更甚者,俺答率诸部入晋后,大同镇卒阴遣人与约,“勿掠我人畜,我亦不拦汝”[4],与俺答诸部折箭而去。这次俺答基本没受到明朝官兵的抵御,可以说礼送出境。大同之变,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诸部,“俺答择其黠桀者,多与牛羊帐幕,令为僧道丐人侦诸边,或入京师,凡中国虚实,尽走告俺答”[4]。由此可知,俺答是利用“叛逃的戍军在明防线的后方当间谍和向导”[5]。正是由于明军腐败与汉奸诱导,俺答才能多次进入山西内地骚扰。
二
嘉靖二十年(1541年)七月,俺答派“石天爵、肯切款大同阳和塞求贡”,提出和平友好的主张:“果许贡,当趣令一人归报伊,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饮血为盟誓”。实际上,俺答这次派使通贡是诚心的。一方面是“近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因人畜多灾,卜之神官谓入贡吉”,[6]俺答想通过互市满足其民众的基本需求。另方面严格约束部众,“虏众有势掠哨卒劫其衣粮者,俺酋闻则痛惩之,遣夷使送哨卒,给衣粮还。”[6]明朝不仅拒绝通贡,且扣留使臣肯切,并发布诏令“悬赏购谙达、阿布噶首以振国威”[7]。这种绝贡扣使的做法激怒了俺答,“遂大举内犯,边患始棘”[3]。
嘉靖二十年(1541年)八月,俺答率部大举内犯,突破石岭关,进攻太原等处。九月,“虏犯山西者,由岚县赤壁岭深入至石州”[8]。这是俺答兵第二次深入石州。领兵者为吉囊,“吉囊之众,复自大同、平虏卫而入……遂长驱入宁武关,而兴、岚、纷(汾)、石之间再遭屠剥”[9]。得知蒙古兵再深入山西内地,嘉靖帝命总督尚书樊继祖、宣大三关兵都御史翟鹏、总兵官赵卿督所部兵前往抵御,“将领有畏缩者即以名闻,如戴升例赴京重罪之”[8]。嘉靖帝虽下严令,但军官仍是畏葸不前,如“吉囊之入寇也,正继祖阅兵大边之日,将师云集发纵甚易”[9],却纵其入关。应战不利的樊继祖未罚反赏,可知明廷腐败。
俺答的这次掳掠给山西造成了重大损失,“去岁虏深入山西大掠岢岚、石州、忻、平、寿阳、榆次、阳曲、太原等州县,宗室被掳者四人,仪宾一人,军民被掳者五万一千七百余人,诸所焚掠无算”[10]。这次也给石州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是时杀掠甚惨,石州为亲死者十一人,而张承相、于博、张永安尤著”[11]。嘉靖二十年(1541年)九月,石州义民杨时芳闻俺答兵将至,“私自预造虎尾炮五百余杆,置合火药千余斤,买粟五百石,愿输于官以备兵。本月十六日,驮载军火粟石来州,行至中途为寇所劫,遂遇害。”[12]知州王朗感其义节、恸其暴死,申请朝廷旌表杨时芳义举。
在蒙古兵蹂躏后,明政府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首先,抚慰山西受灾百姓。明政府“以灾伤、虏患免山西税粮有差”[13],“复徭役二年,仍发帑银六万两”[9],并派户部侍郎张汉往赈之。
其次,惩罚了一些作战不力的官员。总督樊继祖革职回籍,总兵官王升、白爵,副总兵云冒等或革职或降级或逮治[10]。
最后,军事布防的变化。为了防止俺答军队的再次进入山西内地,明朝对山西的军事布防做了调整。第一,重修石州城。嘉靖二十年(1541年),石州被掠之后,州守杨润“增修周围九里三步,高三丈五尺,壕深一丈二尺,东南北三门”[14]。
第二,设岢岚石隰参将。嘉靖十八年(1539年),山西巡抚陈讲指出“岢岚州地当要冲,累遭虏患,而隰州等处稍缓,宜改石隰兵备为岢岚石隰等处兵备,即于岢岚驻扎,且与雁门兵备画地分守,自八角迤北属雁门兵备,自三岔迤南属岢岚”[15]。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前后,俺答军队数次经此进入山西内地。为加强防御,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廷在岢岚石隰设参将一员,驻扎岢岚。
第三,设山西镇总兵官。在此之前,山西镇有副总兵官一人,驻守偏关,同年,设山西镇总兵官一人,“驻宁武关,防秋驻阳方口,防冬驻偏关”[16],“升山西副总兵戴廉为总兵官镇守山西地方”[17]。
第四,促进宣大总督设置的变化。由于俺答的掳掠,宣大总督樊继祖应对不力被革职,嘉靖帝派翟鹏担任此职。“二十年八月,俺答入山西内地。兵部请遣大臣督军储,因荐鹏。乃起故官,整饬畿辅、山西、河南军务兼督饷。鹏驰至,俺答已饱去,而吉囊军复寇汾、石诸州。鹏往来驰驱,不能有所挫。寇退,乃召还。明年三月,宣大总督樊继祖罢,除鹏兵部右侍郎代之……会有降人言寇且大入,鹏连乞兵饷。帝怒,令革职闲住,因罢总督不设。”[18]从中可知,宣大总督的设置属临时应对措施,“虏遁而总督辄罢,虏至而总督增设”[19]。这种措施不利于事变的应对,“然一遇有警,因地方兵马单弱,而各分彼此,不肯应援,纵有应援,亦多观望,未有斗志,往往坐失机宜”[20],以致“虏大入则大利,小入则小利”[21]。尤其是嘉靖二十年(1541年)、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军队的数次进入山西,明兵大多失利。
三
隆庆元年(1567年)九月,蒙古兵从山西、蓟镇、宣府三路进攻明朝。俺答部攻山西,为主攻方向,其子黄台吉攻宣府与土蛮部攻蓟镇进行声援。汉奸赵全为俺答分析了当时形势说:“蓟门台垣甚固,所征卒常选攻之,卒未易入,而晋中兵弱,亭障希,石隰间多肥羊、良铁可致也。”[22]九月初,俺答率兵六万从井坪、朔州、老营、偏头分道入。俺答兵皆悍勇,明兵望风而逃。老营副将田世威婴城自守,宣大总督王之诰率游兵六千抵雁门、云中延绥骑二万亦至皆相望不敢前。初八到岚县。“岚山道阻狭,诸将莫敢据险纵兵”,致使俺答兵如入无人之境。同时,明廷得知“黄酋窥上谷、土蛮逼滦河”,急调王之诰还怀来,派兵护陵寝,“尽力东捍,无暇西矣”[23]。
岢岚兵备道王学谟得知敌情后,缓报石州知州王亮采。直到初九晚,才收到檄报,王亮采匿檄于袖曰:“此常例耳。”[22]初十,俺答兵由石门墕进入石州。十一日辰时,驻扎至峪口(今山西方山县峪口镇),并派人向城内传话:“吾以牛之虻视平阳,而虮虱视尔城也。尔必贿我,我毋尔破,否则移其祸平阳者,祸尔城矣。”[23]守城士兵吓得面无人色,不敢出战。十二日黎明,至石州城下,扬言“我明日往汾州,不抢石州”,石州官员信以为真。十三日卯时,“喊声振天,马蹄震地,四面密围”石州城,俺答兵“矢石加身不动”,致使石州城万分危急。这时俺答提出“金一万两,缎三千匹”,可以免攻城。王亮采召城内富民商议,“以资啗虏”[24],被拒,最终城破。知州王亮采,同知宁晋封,学正郝纶,训导郝珊、田成、杜本翰,驿丞刘静,生员张中路、孙光裕、车成,州民张邦化、李正秋、崔桂、刘朝瑚殉难[12],“守节之妇蹈水火而殒者,不可胜纪,士罹锋镝百三十人”[25]“男女死者数万”[22]。“城陷,自投井者、庙宇井坎皆满,尸横遍野。”[26]石州被破时,山西总兵申维岳率兵数万驻扎于离石州北40里的大武镇,逗留不前。城破后,申维岳并没有追击,而是率兵退入文水。
攻陷石州后,俺答派兵由向阳峡(位于今山西汾阳市西35里,)掠孝义、介休、平遥、太谷、交城、文水、隰州等处,“所杀虏男妇以数万计,刍粮头畜无算,所过萧然一空,死者相藉”[27],同时,“遣间入汾州,分守冀南道宋岳获之,遂移兵州城下,攻八昼夜不克,乃引去”[28]。俺答进入山西内地,20余日,基本没遇到明军抵抗,饱掠撤退时,已人困马乏,依然没遇到阻拦,这是俺答兵第三次至石州,这一次受到损失最为严重,史称“石州之变”,或“汾石之祸”。
明军的腐败无能,致使发生了石州之变。为严肃军纪,整顿军备,提高战斗力,明廷处罚了一批应对不力的将官,山西总兵申维岳、老营副将田世威、参将刘宝斩,巡抚王继洛、岢岚兵备道副使王学谟戍边,太原府同知李春芳、岢岚州知州王下贤降三级,宣大总督王之诰降二级听用,大同总兵孙吴落职充为事官管事,参将黑云龙、隰州知州魏宗方、守备杨时隆等及各分守管操等下巡按御史按问[27]。
石州之变后,明政府对百姓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一是免正官朝觐,就地抚慰百姓。“免北直隶、山西虏所残破州县昌黎、卢龙、抚宁、乐亭、文水、交城、清源、郊、霍、石、汾州、孝义、介休、平遥,虏入所经县榆次、太谷……等县各正官朝觐。”[29]二是调太原府同知李春芳署石州事。李春芳,井陉人,隆庆元年至五年(1567-1571年)署州事。他加意抚绥,“恤死慰生,不遗余力”[30],“整理残疆,修城缮池”[31],将石州改为永宁州,“以石失二字,叶声不吉,请更名为永宁”[32]。三是旌表石州乔应光妻女。隆庆元年(1567年)九月十三日,石州城破后,乔应光妻苏氏“义不受辱”,携女入井,同死者10余人[33]。四是在石州城北建忠烈祠,表彰殉难知州王亮采等人,以抚慰民心。五是山西巡抚杨巍以驿递站粮银蠲免石州税粮[34]与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王友贤向明廷申请免石州徭役三年[29]。
修筑城池,加强防御。总督陈其学奏请“留山西巡抚应觧赃罚银十分之四修石州城”[27]。山西巡抚杨巍以石州城广人稀,难以据守,令截去东南半壁而新筑之。由于石州城墙原为土筑,不足恃,地方官请求将土筑改为砖筑,“非环土之筑可保,宜易之以砖。天子曰:‘可’。”[26]新筑石州城“高四丈八尺,长一千二十丈,基厚三丈二尺,顶厚一丈五尺,东南北外三面俱浚深濠,西面城下泉不须濠”。万历四年,“用砖石包甃东北两门,设甕城,竖城楼三座,角楼五座,悬楼一十五座,敌台一十七座,垛口一千二百二十八个”。汾州府设立后,万历二十六年,州守夏惟勤“重修改南门,于东南隅亦设甕城,添城楼五间,垛口房三十间。西南角筑高台一处,造楼一十五间以料敌”[32]。一是从城墙的材质看,明初山西的城墙大多由土筑,随着明中期烧制技术的发展和明蒙冲突的加剧,在嘉、隆年间城墙逐渐转为砖甃。石州之变后,经明廷批准,永宁州城的材质由土筑转为砖甃,使州城更加巩固。二是从城墙的高度看,原城墙高三丈五尺,新修高四丈八尺,高出一丈三尺,这增加攻城的难度。三是设甕城、浚深濠、添城楼、增垛口等,这些措施使新筑的永宁州城防御功能大大增强。石州之变后,受到影响的其他州县城亦得到修筑,如隆庆三年知州宁策修汾州城,“增其高厚崇凡四丈八尺,下厚四丈二尺,上厚丈八尺,又筑北城郭堡,周二里有奇,崇三丈二尺,门四”[35];隆庆三年知县岳维华修平遥城“增台楼新旧共九十四,甃以砖石,浚濠加深广”;隆庆元年知县刘旁重修介休城“增高丈二尺,厚增八尺,城台百一十有奇”[35],隆庆年间修筑的县城还有孝义、临县、宁乡等。总之,石州之变使山西出现了筑城的高潮。
石州之变促进了汾州府的设立。为了防止俺答再次进入汾、石,明廷对汾州军事布防进行调整,设汾州营,“抽(汾)州卫军千名,调平阳卫军千名,取汾州民壮千名,统以参将……(隆庆)四年罢参将设守备”[36]。汾州守备平时驻守汾州,“有警移住永宁”。永宁州隶属于冀宁道、太原府,而汾州隶属于冀南道,“两地故多盗,事发相诿”[25],这不利于对永宁州的管理和防御。为加强对永宁州的管理,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五月,经山西巡抚魏允贞奏请,汾州府设立。
嘉、隆年间,俺答兵数次进入山西内地,三至石州,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明朝对俺答采取的绝贡政策有关。俺答自嘉靖八年(1529年)叩关,多次派遣使臣,要求通贡。民族偏见甚深的嘉靖帝及一些朝臣不加分析地拒绝通贡,杀死使臣,激怒俺答。俺答采取武力逼贡的方式,入边掳掠,给北部边界人民带了深重灾难,严重影响到了明蒙关系的正常发展。俺答三至石州亦反映了明朝边防空虚、军队战斗力低下。嘉靖中参政胡松对明军的战斗力有所表述说:“边境近年侵盗驱略,虏大入则大利,小入则小利。竟不闻有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与之一角于疆场者。虽朝廷之上,严令剿杀,要不过息鼓偃旗。徐尾其后。贼如东向,我则西驰。俟其志欲充满,整暇而归,其所略老羸孱弱,行不能逮。彼乃视为弃核,委以啖我;而我则因之以为利,邀之以为功。以巧于张皇,奏功以阙下,而不知悉皆我之编氓,与其老耄婴孺也。岂不重伤天地之和,而远遗丑虏之笑哉!”[21]明朝不仅军队战斗力低下,而且对边防设施重视不够,“皇上锐意边防,凡申饬之令警戒之论盖数下也,乃边臣鲜闻以实应者,如蓟镇尝谓能修边矣,而虏近从罗汉洞入,山西石州尝议修筑城池矣,而院委之道,道委之一县,官上下相蒙,遂成陷没”。[29]石州之变的发生既反映了隆庆初年明蒙关系的紧张又暴露了亟待整治的北部边防形势。石州之变后,隆庆帝加强了对北部边防整顿[37],为俺答封贡的实现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