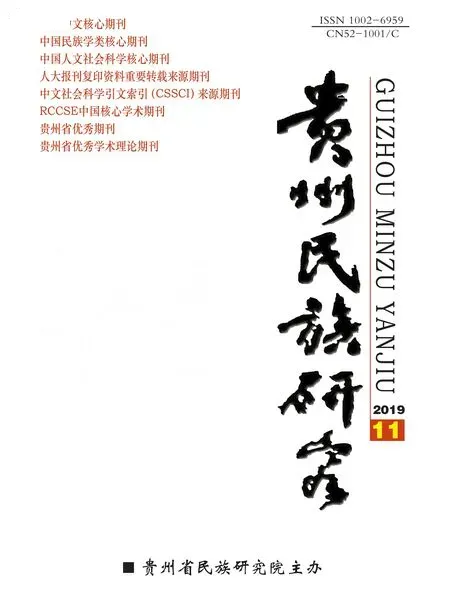电影媒介中民族文化的表达与认同研究
——基于城市意象理论的视角
2019-02-09肖艳华
肖艳华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文化是人类最为普遍的精神活动与社会现象。不同的民族群体都有着自身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要素,这些文化要素之间的传承、转化、融合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系统。而电影从其诞生开始,就以其独特的视听符号表现形式,记录与承载着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变迁,城市的空间展现也往往成为电影媒介中极其重要的民族文化书写与象征。凯文·林奇认为一个城市空间的“城市意象”塑造与传播,是源于该城市文化特质的传播与认可。即城市意象是个体文化、群体文化、民族文化、社会文化的交织作用,这些文化因其不同的国家、民族与群体而产生了不同的城市意象:“即在单个物质实体,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一种基本生活特征三者的互相作用过程中,希望可以达成一致的领域。”[1]这一论述阐明了城市意象塑造的关键是民族文化的显现与认同。在此基础上,可将电影文本中城市意象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内涵进行界定,城市意象在电影影像中首先是一种民族文化物化与外化的存在。其次是民族情感的承载,是人思想表达的主要场域。人们对于一个城市的意象认同,是缘由对城市中民族文化的认同,这两者是一个相互生成的关系。最后则是电影在借助民族文化塑造城市意象的反思,这种反思是电影表象符号下异质文化对于民族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适应机制,“文化适应机制是指在社会转型中影响一个民族吸收异质文化成分来丰富自身民族文化内容或改变其文化结构所具有的全部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2]文化适应机制是民族文化区隔的结果,不同的民族文化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下,会弱化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或丰富本民族文化的内涵,这是现代生活下城市意象塑造中民族群体精神状态的现实折射。
在王小帅导演的“三线”三部曲《青红》(2005年)、 《我11》(2012年)、 《闯入者》(2015年)中,“贵州”这一城市意象是贵州民族文化在外化与内化空间的双重叠现。影片中,导演通过三个层次的民族文化影像建构起来了历史中“贵州”城市意象:第一个层次是独有的贵州民族生活环境表述,如地形、气候、语言、饮食习惯等。第二个层次是特殊的历史时空中,异质文化冲突下不同民族间人物的命运与情感表述,如三线建设背景下异质文化群体的生存状态。第三个层次是在前面两个层次的民族文化阐释下,贵州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表达与城市意象的嬗变,这是一种从物化到精神的引领。这三个层次的民族文化在互为表意的影像叙事过程中,完成了历史中“贵州”城市意象的建构和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输出。
一、民族自然环境文化建构城市意象的外化形象
(一)民族自然环境的外化影像表现
民族文化包括民族自然环境与民族社会环境,其中自然环境指的是气候条件、地理位置、生物面貌等外化的要素。在王小帅的三线故事的影像表述中,贵州是故事的承载空间,影片中的贵州与“西部贫瘠的山区”是互文的。关于贵州城市的俗语,有一句民间谚语由来已久:“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这一固有的自然环境也在影片众多的影像中有了极致的描绘。
《青红》中极少见到阳光明媚的天气,不是灰蒙蒙就是阴雨绵绵,在许多镜头画面里,道路总是潮湿的,青红穿上小根送的红色皮鞋走在水泥地面上时,路面湿漉漉的,远处的山亦是雾气笼罩。青红与小珍偷偷参加跳舞晚会回家的路上,昏暗的路灯下,湿滑的路面与斑驳的屋墙令观者宛如触感到了夜凉如水的寒意。影片中人物经常随身携带的伞,看似不经意,却将贵阳阴霾的天气作了强烈的暗示。在《我11》中,也是缺乏阳光影像的,父亲载着王憨骑自行车从长长的坡下来,这个镜头在影片中出现了多次,但是整个画面是极其黯淡的光线,早上光景却如傍晚,虽然父子俩穿的都是单薄的衬衣,却透着阴冷的意味。在《闯入者》中,虽然绝大多数的影像篇幅都是在描述北京,但是和北京阳光灿烂的天气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老邓记忆中贵州的工厂破旧的秋千下荒芜衰败的工厂厂房,破旧不堪的工厂环境在没有阳光的照射下,更显落寞。
“地无三里平”这一自然环境镜像在青红与父亲的几个镜头中表现得异常明显,父亲与青红走在上学放学的山路上,由山上拾阶而下,满目不见任何城市的楼房;吕军被吕父追打的过程中,吕军在逃窜时不断地在不同的石梯中蹿上蹿下;小珍私奔前与青红在山坡上谈心时,远景的镜头里灰暗的房屋在山与山之间坐落。在最后青红一家坐上汽车偷偷离开的画面中,汽车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中穿梭前行,镜头越来越远,连绵不断的低矮山峰在雾气笼罩之下仿佛看不到远处的山了。《我11》中开篇的镜头中从窗户望过去,没有高楼只有山和树。去王憨的学校,爸爸骑着自行车要下一个长长的坡,在学校的门口,学生们还要走完长长的上坡路才能进入校门,在整个学校的环境镜头中,学校远处除了树就只有灰蒙蒙的天空,营造了学校在山上的空间感。在警察搜寻谢觉红哥哥的场面中,年代久远的石桥两旁看不穿的茂密的山林,都在映衬着贵州的山区环境。即使在疏隔几十年后,《闯入者》的老邓在回到贵州时,火车外的风光是满眼山峰与突然漆黑一片的隧道,这与北京影像中阳光灿烂车水马龙的城市写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二)独有民族饮食文化的展现与沿袭
每一个民族的饮食文化都是在特定文化条件下发展而来的,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与他们赖以生存的民族环境息息相关的。不同的城市意象的影像表达,借助饮食文化的展现有着极佳的民族文化区隔作用。在众多影片中,饮食文化是中西方民族文化差异呈现的重要影像。如李安的《推手》中父亲与美国媳妇生活上的无法融合,通过各自吃早餐的方式可以窥见一斑。电影媒介借助影像从许多侧面勾勒了贵州民族的饮食文化:《青红》中家门口外墙上一直挂着的是长长的风干了的红辣椒,这是贵州喜食辣习俗的表现。低矮屋檐上晾着的红皮萝卜(贵州地区酸萝卜的泡制原料)与一家人吃饭时桌上碗盘中的折耳根,都是典型的贵州民族饮食中嗜酸吃折耳根的习惯。《闯入者》中老邓虽然离开贵州数十年,但是却将食辣的这一饮食习惯带回了北京,老邓在北京的家里,吃辣椒酱成了她极其自然的一种饮食方式。
独有的习俗与该生活空间的天气与地理是相映衬的。贵州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又处于云贵高原的山区,因而其饮食文化也有着与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独特性,这也造就了贵州显著的民族饮食文化。在西部有这样一句俗语“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下雨像过冬”。再加之“天无三日晴”,在如此湿寒的天气里,吃辣椒、喝酸汤、食折耳根成了驱寒祛湿的一种日常饮食习惯。除此之外,有学者也从历史的角度认为贵州处于云贵高原之中,山路崎岖,交通不便,物资极度缺乏,造成这一地区的缺油少盐的饮食窘状,为解决这一难题,贵州人用辣与酸来调味。
折耳根是中草药鱼腥草的别名,因云贵地区只食用鱼腥草的根部才将其称呼为折耳根,贵州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地种植折耳根,影片中全家在吃饭时,讨论的是对于回到上海的渴望,而镜头的左下角却是折耳根作为菜肴的画面。关于折耳根为何会在贵州如此盛行,不少学者给出了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历史上的贵州由于地处山区,灾难频发,灾荒不断、土匪横行。人们为抵抗饥饿,挖而食之。其次由于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土壤肥沃度极其缺乏。但是折耳根生命力顽强,适应贫瘠土地的生长,这也是折耳根能在贵州地区普遍栽种的原因。从吃饱到不可或缺的饮食素材,折耳根是血泪历史的见证,也是这一地区的民族因适应环境而衍生的民族饮食习惯。
《我11》中还有几个看似不经意的镜头也体现了贵州湿冷天气下的生活习惯,王憨与几个小伙伴在冬日里,用细细的铁线拎着圆形的小火桶取暖,这种独特的取暖方式是贵州作为山地冬季户外寒冷的取暖方式,诚然,这一取暖方式有着经济因素也有着避寒的现实需要。直到现在,贵州的许多农村中,不少孩子还在用着此类“火桶”进行御寒。这也从另一侧面对贵州的山区外化城市形象做了点睛的影像描述。
二、异质文化与民族文化交织下城市意象的内在建构
(一)“三线”背景下异质文化的涌入
人类文化系统是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外来文化)两大类别组成的。异质文化的涌入必然导致本民族文化呈现出不同的反应:即民族文化接纳异质文化的程度与异质文化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度。三部影片里,被建构起来的“贵州”是知青群体这一外部异质文化介入下的“集体记忆”的想象。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其著作《记忆的社会性结构》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3]
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最明显的特征是其社会性,即使是个人的记忆,也是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的。个体的记忆是个人文化的体现,群体文化与社会文化中民族文化是主要的组成部分,或可以这样理解:城市意象的形成不仅有着本民族个体、群体文化,也有着异质文化融合的社会文化影响。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过程中,知青个体这一异质文化是与社会文化连接在一起的,两者文化的勾连营造了“贵州”城市意象文化的形成。
影片三线“三部曲”是对贵州特殊历史时期——三线支援城市的记忆演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经济运动,是以工业交通和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大后方建设,是涉及到全中国的一次经济战略大调整。整个过程历时16年,三线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几百万人从上海、北京来到偏僻的山区,支援三线建设,而贵州就是当时三线建设中重要的支援地区。作为特殊时代里的特殊地区,贵州这一历史空间是承载着当时无数三线人的共同记忆的。
《青红》与《我11》两部影片将“贵州”作为在场地的叙事,镜头开篇就用字幕将故事的背景——贵州这一发生地进行了特殊背景的界定。《青红》里写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无数个家庭随着自己的工厂离开故土来到西部贫瘠的山区,开始了三线建设。《我11》也以王憨的第一视角打出字幕:“谨以此片献给我的父母和所有像他们一样的三线职工。”然后下一个画面的镜头里显现的字幕是“中国西南三线建设某兵工厂1975年”,以此来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地——贵州。虽然在《闯入者》中,影片大量的影像篇幅是拍摄于北京,但是故事的主人公老邓心理挥之不去的沉重记忆指向的仍然是三线中的贵州区域。
(二)城市空间里民族文化与异质文化的意识形态交融
1.民族文化吸纳异质文化的体现。异质文化群体——知青的融入,在进入本土城市空间后,本民族文化的适应机制在接纳异质文化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产生了社会影响。首先是传统的民族经济状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三线建设是在新中国物质较为缺乏的年代开展的经济运动,在这一时期下,许多人赶赴三线城市的建设最初是抱着热血的爱国情怀,渴望英雄精神气质的心态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三线的建设是一种集体荣誉外来的异质文化情感的抉择,那一时期的热血情怀是全民族体验式的。青红就读的新兴光学仪器厂技工学校正是响应三线建设的人才需要而建设的培养基地,《我11》中王憨一帮小孩子欢呼雀跃地追赶着插满鲜红旗帜的运输车,车上的标语“大干快上”,两旁房屋的灰墙上刷着白色的标语“团结争取更大的胜利。”虽然《闯入者》中并没有用影像去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的贵州,但是,在老邓进入到曾经生活十几年的厂区时,背景音乐中激昂的军号响起,《山楂树》歌曲里的老邓泪光婆娑,仿佛一晃回到40年前的三线时光。
其次是异质文化的带动下,传统民族文化吸收流行文化丰富自身文化。三部曲中有几个极其明显的影像都明示或暗喻了当时八十年代的文化潮流。首先是《青红》开篇与《我11》中的校园操场上的第六套广播体操,从1981年起开始全国推广,这一时期的广播体操工作也被认为是最严肃的,不少地区都会进行体操的评比工作。王憨在获得领操的资格之后,对于这一任务的光荣性与他珍惜白衬衫之间形成了强烈的互衬。其次是服饰、电影、音乐等文化观念的外来影响,《青红》里技校的小青年们穿着喇叭裤、烫起了时髦的卷发,即使面对老师锋利的剪刀也无法阻止他们追逐时尚的步伐;在吕军与珍珍骑着自行车经过的广场旁,正放映着日本1981年上映的电影《阿西门的街》,这一部影片与另外两部影片《华丽家庭》和《野麦岭》被称为是日本社会发展的三部曲,里面反映了许多工业社会发展背景下,日本工人的生存艰难与辛酸;王小帅对于音乐的叙事也是非常娴熟的,《青红》中的邓丽君歌曲、《我11》中《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闯入者》的《山楂树》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主流歌曲,尤其是邓丽君的歌曲,是亚洲现代流行歌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异质文化融入民族文化的不适应性。民族文化在面对异质文化会出现不同的环境适应与改变。同样地,异质文化在融入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本民族群体的生活环境与文化规范对他者的行为与情感控制也具有强烈的文化冲击影响,这种冲击影响体现在异质文化对本土城市空间的怀疑与否定。《青红》里父母、《我11》里的谢觉红的父亲、《闯入者》里的老邓都认为来到贵州工作是一种牺牲,国家许诺支援者的涨工资和宣扬支援边远地区的光荣造就了这些异质文化涌进贵州的动力。但随着改革开放浪潮,东部城市,尤其是上海、广州等城市打破大锅饭的形式,多劳多得的工资分配制度使得更多部分人富裕起来成了现实。而这时的贵州与经济浪潮发展中的上海、北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性,这种落差率先体现在他们对于“贵州”的经济补偿失望上,因为他们并没有实现几年涨几级工资的美好愿望,甚至连吃穿住行的基本环境与生存条件都无法得到更好的改善,这种经济的落差在青红家清贫的家庭环境中、王憨想买件白色的衬衣的欲望中、老邓回忆的破败的厂房中都有着体现。
这种充溢在本土城市空间的否决意识催生了内心的绝望。父辈们在感叹外面世界的变化之快时,认为这个自己当下所处的城市空间是无法看到未来,期望自己的后代能脱离此空间场所。所以父亲才会从内心深处担忧青红的恋爱与学习,告诉她要好好学习,否则回到上海是会被人瞧不起的。《我11》中,王憨父亲的一句“大人在哪里上班不是大人说了算”是透露了在自己当初来到这里的无奈之举;老谢因他回上海的愿望而导致女儿谢觉红被玷污,儿子变成了杀人犯,这一切导致了他对本土环境与文化的彻底决绝。《闯入者》中老邓隐藏心中的告发秘史、老赵孙子的死亡,这是老邓无法救赎的绝望发酵。
除了异质文化群体中父辈们的绝望,还有在本土民族文化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辈的绝望产生。父亲阻挠青红与小根的恋爱,他对小根的不认可是对于小根所处的民族环境与文化的排斥表现。父亲丢掉了小根送给青红的红色高跟鞋,这也是意味着父辈对青红融入与认可小根所属民族文化的拒绝。父辈们用否定、拒绝、逃离本土文化与人的融入来限制青年一辈的当地融入。《闯入者》中的老赵的孙子从贵州空间出走“闯入”到北京,犯下盗窃、杀人等罪行后最终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这些年轻一辈的身上,是异质文化对民族文化抗拒之下,心理无法获得文化适应的悲剧行为体现。
3.对民族文化消极适应下异质文化的逃离。异质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互动交融过程中,如果民族文化的文化模式与功能不能满足异质文化现实与心理的需要,那么异质文化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就会被极大削弱,甚至会产生对民族文化消极意识的融入。三部曲里,外来者对于贵州空间出逃渴望并非是绝对的同一性,而是存在差异性的。这种逃离在父辈们的想法里是最为渴望的。《青红》里父亲跟母亲说,“我就是要我的孩子,不能再跟我们一样,又一个同样的十几年,所以我才像条狗一样,天天跟在领导的后面,求这个,求那个,我就是要他们回家回上海。我们是上海来的,我的孩子就要回上海去”。这里的父母穷尽自己的力量,就希望他们的子女将来能够体体面面地离开自己眼中这个毫无希望的城市空间。
父辈们对异质文化的逃离义无反顾,但是他们惶恐曾经的“上海”,自己认同的文化环境是否还能接受自己的回归。《青红》里工友们在说到上海时是不自信的,有着羞愧感的。他们认为自己对于上海而言,已然成了乡下人的角色,连一年回一次上海都是一种经济的奢侈,因为这会花掉他们一个月的工资!青红兄妹俩也会说,上海的亲戚并不会欢迎他们回去。青红父亲即使在收音机噪音干扰异常明显时,仍不放弃收听,因为在他看来,如果连这个都不听,他就真的回不到自己向往的上海环境了。这是一种不甘心被本土民族文化同化的恐慌,因而他们无奈地选择只有逃的方式。青红对于贵州空间的逃离是从被动到主动的一种转变,且裹挟着悲剧意味的。
在逃离意识的压迫下,异质文化群体本土民族文化之外的民族群体坚守着自己的民族文化模式,如坚守本民族语言的使用。不同语言的使用是各民族文化情感的归属体现。“语言反映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隐喻是人类思维的特征,人类通过语言隐喻认识世界,呈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4]在影片中,知青群体用语言的地域性来不断提醒自己上海的文化身份,来区隔与贵州民族语言文化的距离。《青红》里父辈们围坐一起,聊天使用的是上海话。《我11》中,集体的小院坝里,大家用上海话闲话家常,老董唱起了沪剧《燕燕做媒》,王憨母亲在生活的集体宅院里,和旁边的邻居们都是用上海话来进行日常交流。《闯入者》的老邓在离开贵州多年后,怀着救赎的心态回到贵州,她心灵的忏悔与她回到这里使用本土语言也有着相互的隐喻,在她购买水果和摊贩老板交流时,老邓说着贵州本地的方言,这也暗示着老邓在贵州城市空间由异质对抗转向接纳的心态。
三、城市意象中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与文化认同的表达
在上述影片的影像符号中,贵州城市意象所传递出来的民族文化是带有晦涩与暗淡色彩的。在影像的传播过程中,贵州城市意象被偏远、落后、闭塞、欠发达等标签牢牢地贴在了贵州的形象上。而这种标签认知是基于电影媒介所传递出来的民族文化影像理解,以及产生的民族文化心理认同。通过剖析影像视听符号的运用,电影媒介中一个城市意象的认可有着电影制作者、传播者、受众等多方面接纳该民族文化程度的影响力。
影片内容中的民族文化认同虽然能指的是贵州的地域性,但所指的却是三线建设中城市空间中外来者对于贵州人身份与贵州民族文化的认同,贵州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研究的就是民族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互动与接受。在这里我们先要理解贵州民族文化身份与贵州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差异性:身份与文化认同是存在两方面的差异性,“一是指某个个体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特定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等。在这种意义上是表示身份的意思。在另一方面,当某个个体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identity’可以叫做‘认同’。”[5]斯图亚特·霍尔也认为:“‘身份’与其说是一个完成的事物,不如将其看作是‘认同’,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5]。从这一意义上出发,他阐述了民族文化的最终认同是产生身份的点,这种认同是在历史的时空变化中,结合语言等社会环境出现的,并非是一种本质上的认同。
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从两种立场去界定了文化身份的定义:“第一种立场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第二种立场认为除了许多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些重要和深刻的差异点,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或者说由于历史的介入——构成‘真正的过去的我们’。”[6]
这两种立场其实也蕴含了斯图亚特·霍尔关于身份的两种文化实践观念:发现身份与生产身份。发现身份归属于第一种立场之中,这是一种传统性的身份,也是一种传统的民族文化认同观念,如世居的贵州人对于贵州的认同是因为贵州人身份的延续、民族文化的同一性而产生的认同,这种认同是传统的、与生俱来的、难以改变的。而生产身份则不然,在现代性、工业性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各种社会关系都在发生变化,社会观念的稳定性、传统性在不断地发生新的内涵演变,不同民族的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都在历史的时空中因为某些现实的因素而被不同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动态性是后现代性赋予其与文化身份最根本的区别。
电影是一种人为艺术的再现手段,“影像文本的开放性、符号表意的多义性,也形成了不同人们心中多元化的城市形象,赋予城市形象以多角度、立体感。”[7]因而在三部曲的贵州城市外化建构与人物情绪的倾诉下,置身于历史时空的贵州这一在地性的认同建构是复杂多变的,它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民族身份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身份与文化认同,这种民族文化身份的出现是属于生产身份的内涵。
(一)电影中贵州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形式
三部曲影片中的贵州民族文化认同建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是霍尔的生产身份的建构。对于所有的个体或者群体来说,群体意识或集体身份并不是后天产生的,而是群体通过具体交往和互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一种相关联的特性,可以通过它反观社会结构的性质和特征。在文化研究视野里,文化的认同随着现代性的演变,主要形成了三种文化身份认同模式,第一是以民族主体为中心的文化身份建构,这一模式是对于民族主体本质化的认知。第二是社会为主体的文化身份建构,是对社会作用于不同民族主体的强调。第三种是后现代主体文化身份的建构,指的是在社会的多变性与复杂性中,文化认同不再是确定的时刻,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透过三部曲,我们可以看到,贵州文化的身份的建构是有着这三个模式的共同作用的。
1.本质的、主体性的贵州文化身份建构。这里的本质是属于民族本身的地理环境、语言等文化,是已经内化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是不具备迁移性的。在王小帅的三部曲影片中,贵州的地理文化是一种本质化的呈现,在前文的外化空间展现中,地理环境与天气等因素构成了贵州的本质意象中重要的因素。因为这一地理环境的影像建构中也对贵阳人的主体身份建构进行了显现,边缘的环境形象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一环境中人的与生俱来的文化属性。地理环境与人的关系性在很多西方的启蒙思想家都被重视与论述过。康德在其著作《自然地理》中就特别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不同的族群的文化形成的影响。马克思也认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8]也就是说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是形成不同民族文化的重要原因,这与中国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是有着共通性的理解的。正是源于这一环境之于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于不同的环境中形成的民族是有着“刻板成见”的印象的,就如沿海地区的环境由于它位置的开放性,人们会普遍地认为这里的民族群体在思想上也会传递出现代性、民主性与开放性的特点,而偏处内陆地区的城市与人由于被限制的地理环境,他们在意象表达上呈现出封闭性与保守性的特点。
影片中除了用地理环境影像符号建构民族主体的外化形象,导演还在人物的外化影像上来加深这一民族环境的认知,如《我11》中王憨母亲花费一年的布票给孩子做了一件白衬衣,吃肉对于全家来说是难得的一次,而且需要肉票供应才能购得;《闯入者》中老邓时隔多年回到贵州时,当她敲开老赵家的房门时,老赵的爱人身上的不修边幅、室内环境的脏乱不堪与老邓身上的干净整齐、北京儿子的宽敞明亮时尚的居住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这些自然的、人物的外化的民族文化影像符号,在观众认知的基础上,形成了对贵州——是偏远的、封闭的、落后的山区之地的城市意象。这一种自然地理环境下发生的城市意象体现的是霍尔理论中本质主体性的身份观念,“个人具有一个本质的身份,这个身份与个人所属集团的本质特征相契合。所属群体的成员资格的建立需要个体经历长时间的自省,但是个人无法逃离自己的身份。它被更为本质性的东西固定下来——即人的天性。”[5]这里的民族个体属性的本质与群体相对应的是城市的本质实体化。这一民族身份的建构在时空视野中很少被讨论与思考,是因为民族个体与群体所处的稳定性形成的城市内涵也是固化的。
2.生产身份作用下贵州人物的意象建构。在电影影像内容里,主体与本质建构起来的贵州身份是确定的,本民族自然环境与社会历史观肯定了这一层身份的确定性。但是在生产身份的建构观里,“贵州”这一意象是有着重建色彩的。这种重建色彩可以理解为创作者对于贵州文化认同的再造。“认同不是对某种本质之物的机械的归附,而是一直人为的建构行为。即为什么认同、认同什么和如何认同都包含了一种人为的主观选择和策略抉择。”[9]在影片中,贵州的民族文化意象在社会色彩与人物的形象建构传达出了自带晦涩的性质,令受众在接受影片的思想意识时,对“贵州”意象产生了跟随创作者的单一认同,认为在固有的地理劣势之下,这一空间的人物也有着被潜移默化的消极。
自然环境与人物的交互烘托形成了贵州民族文化的主要建构途径。在《青红》中,技校的学生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向往着外来的流行文化,男生穿着喇叭裤、女生烫着波浪卷,一个个追赶着中国改革开放后涌进来的时尚流行文化。但是,影片中的老师在教室门口拿起剪刀挨个检查学生的着装与发型,有悖以往传统穿着者则要被剪刀“修整”。学生们想方设法地逃离老师的检查,这也暗示了贵州在流行文化的开放时代中,依然固守传统意识,不愿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人物被环境影响而流露出的消极意识对贵州民族文化滋生了异化的情绪。《青红》里的小根可以看作是导演对于当地本土文化的想象,青红与父辈们作为异质文化的闯入并没有认可小根,尤其是青红的父亲对小根充满了抗拒。小根的痴心苦恋在感受到失落与绝望时,他最终选择了用最偏激的方式来完成他对青红感情的最后终结。在《我11》中,王憨作为异质文化的载体,他在民族文化区域环境中萌发了青春意识,而青春意识的萌动对象谢觉红却是一个绝对悲剧性的人物。老邓在《闯入者》中无法救赎的过往,是她作为异质文化生活的环境中人生最为暗化的历史。
通过三部曲里的贵州文化身份建构梳理,可表明,在传统的民族文化观念与他者对于民族文化的意识形态表露中,“贵州”的城市意象是一种固化视野下偏远、贫苦、落后、未开放的形象。这一意象的建构随着影视作品在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让受众对“贵州”的城市意象产生了与作品内容相似的认同感,但这种民族文化认同感是存在主观性、而并非客观性的认知。
(二)“贵州”城市意象中文化认同的思考
文化生产身份的建构主义,对于本土民族文化的身份必然是一种解构与消解,对于传统的民族文化认同是具有颠覆性的,它颠覆了固有的民族文化身份中的同一性,而带来了主观性、多变性的异质文化认同内涵。这一新的文化认同观里,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不断变动不断重组形成的过程,既有异质文化的介入,也有本土文化的迁移与流离。这种认同的建构是具有后现代性的,不再单一地依靠原有的民族文化本质属性与在地性的中心场域化作为建构的依据,而是引入了外来异质文化多重视角的重新阐释。
结合三部曲电影中的影像文本,“贵州”这一城市意象中的民族文化认同是在四个认同的维度来传播文化认可意识的。
首先是个体的认同,从异质文化的参与角度来理解,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个体认同是在整体社会环境的作用下积极或消极地参加社会活动。如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三线的时代背景让位于商业经济快速发展起来的沿海城市,在这样的社会潮涌中,父辈们对扎根了多年的三线建设产生不再怀有当初的热血干劲,而是渴望融入改革开放中发展的大都市经济中去。
其次是集体的认同,在当今的文化认同趋势下,这种认同被指认是主体在两个不同民族文化的选择,如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集体选择。在三部曲的影像中,上海、北京相较于贵州而言是一种强势文化的存在,这也是贵州作为弱势文化的一种被拒绝。
再次是外来异质文化个体的认同,这是启蒙哲学的认同层面,如《我11》中王憨的青春生理启蒙、《青红》中青红与珍珍的爱情启蒙、《闯入者》中老邓若干年后的灵魂启蒙与反思,这是从个体的自我内心体验上对于贵州文化认同的表现。
最后是民族文化的社会认同,这种认同是归属于社会属性的认同,意即当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在进入社会领域中,能否获得他者主体、文化的认同,而片面性与排斥性的意识影响,对贵州民族文化认同程度有着关键性作用。这也是在不同文化中“贵州”城市意象的形成没有获得客观理解与良好接受的根本缘由。
电影作为大众媒介中重要的艺术形式,对社会的发展与大众的意识有着巨大影响力,尤其是在与城市结合上能对城市软文化的展现与提升起到助推的作用。当然,电影媒介不能完全舍弃艺术渲染的需要,而纯粹客观性地再现的城市意象,这种绝对的客观性任何一种类型形式的影片都不可能获得。所以,影片的创作者与受众在不同文化意识的作用下,基于传递出源自于影片又区别于影片的合理城市意象目标,进行合理的民族文化认同差异性创作与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我们也可从两个方面去思考借助电影媒介如何更好地进行民族文化与城市意象的传播与互动。
1.不同文化阅读思维方式的运用。对文化认同变化复杂性的忽略,会失衡不同民族文化的判断与城市意象的认知。在当代社会环境中,民族文化认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强调的认同是一个开放、发展变动的过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中的共同体》中所表明的现代民族身份的想象性特征,折射出后现代主义身份观的影响。身份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5]。这要求我们用变化的观点来分析影片中“贵州”影像,而不是被固化的“贵州”意象。这种固化体现在:《青红》《我11》中,父辈们渴望离开贵州空间是因为在这里工作十几年,工资并没有上涨、生活环境没有改善。《闯入者》中老邓时隔多年的回归,并未令时空环境发生变化,旧日的工厂青苔满地,老赵一家的环境仍然贫困,这是一种时空相对静态的观点。
在静止的认同视野下,我们更需要的是发展的文化认同观。从发展变化的思维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借鉴赛义德的对位阅读与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的两种文化阅读理解方式。对位阅读理解方法要求创作者与观看者要将影像文本所排斥在外的民族文化意识也要统一起来理解。而症候式阅读理解则是要求对影像文本浅层解析下进行民族文化的深度挖掘,并针对影像文本中存在的误解、空白、扭曲作出阐释与佐证的理解,这是对电影表意与潜在意义认知。任何一种民族文化认同从来不应该是先验性的,也不可能是已完成的认识产物,它永远都是一个借助不同外来想象力与实践性共同形成的民族文化认同观。
2.不同民族主体间性思维的介入。王小帅曾说过:“自从开始自己拍电影以后,心理就一直怀着一个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要碰触到“三线”这个题材,于是拿起摄像机去揭开那段尘封的历史,为观众展示大时代浪潮里个体生命的坚守与挣扎。”[10]而这三部曲的创作背后正是源于他年少时,跟随父母因支援三线建设而来到贵州生活的那段难忘时光。王小帅在他的自传《薄薄的故乡》中,提到了他的人生经历,他出生在上海,几个月大便跟随父母来到了贵州,直到13岁才离开贵州去了武汉,毕业后去了福建,迄今为止他落户河北,因而故乡的概念于他是极其模糊不清的。因而“贵州”意象是王小帅作为外来异质文化的艺术性呈现,是一种客体性的思维。
随着现代性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识模式已被主体间性的认识意识所影响。在社会文化的认识与思考上,完全主观意识或彻底客体意识都容易导致片面的民族文化理解,形成表面、单一的城市意象感受。主体间性的意识缺乏是造成影片“贵州”意象争议性的原因之一。在传播民族文化、建构城市意象时,我们不妨介入主体间性的思维,这是创作和认识影像文本中的民族文化与城市意象是一种相对合理的途径。主体间性从哲学上来说是将本民族之外的文化也当作是不同的主体,哈贝马斯认为主体间性是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交往。这种基于现实交往的认识主体间性要求在进行民族文化认知与城市意象建构时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首先是面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平等性观念,这样演绎出来的城市意象才是一种相对客观的意象阐述。其次是超越性,是作为自身认识本土民族文化时,要超越“刻板印象”的印象,做合理的城市文化意象建构者。再次是实践性,交流与对话是认识不同民族文化的主要途径,只有在充分践行了民族文化之后,才能由表及里地认识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最后是用发展的历史观点来阐释民族文化,承认它的变化性,并将这种变化性赋予城市意象新的文化内涵。
四、结语
不同的民族文化是不同城市意象的重要内涵,在城市视觉形象的基础上,“城市精神是城市居民的价值观念、社会形态和行为方式的综合”[7]。这表明民族文化精神内核的传递与认同才是电影媒介中城市意象建构起来的最终目的性。在电影“三线”三部曲中,通过集体记忆、异质文化影响等方式将贵州民族文化得到了展现,而民族文化的展现与传播影响最终形成了较为固化保守的“贵州”城市意象认知。结合本文研究可知,在电影传播的过程中,电影创作者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认同程度,会潜意识地引导着受众对于该民族文化的认识与认同:民族文化在电影媒介中的传播,能塑造这一民族所属的城市意象空间,并对受众产生深远之影响。在当下,不同城市着力提升民族文化影响力已然成为了城市软文化提升与城市意象建构的重心,因而在日新月异的媒介时代,如何适度地传播民族文化、再现民族城市意象是现代影像传播行为中一个不断被重复而重视的命题,这也对丰富民族文化的研究路径有着极其现实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