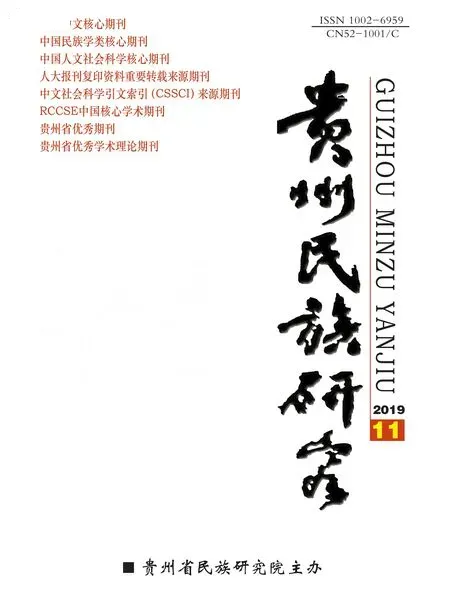苗族史诗《亚鲁王》场地名重名现象研究
2019-02-09张进一封孝伦
张进一 封孝伦
(贵州大学,贵州·贵阳 550025)
一、贵州省场地名重名情况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1]。地名因其具有标识的作用,不仅体现一个地区民族文化的审美取向,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作为集市的地名在“贵州为‘场’、云南为‘街’、广西为‘墟’”[2],场地名不仅是一个居住上的物理空间,更是一个地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换的重要场所。在贵州,以龙场、马场、羊场、牛场、猴场、鸡场、狗场、猪场、猫场等十二生肖命名的场地名构成了贵州独具民族特色的地名体系,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根据侯绍庄的统计,全省共有259个十二生肖场地名,有的在乡镇级,有的在村级,其中鼠场9个、牛场32个、虎场20个、兔场4个、龙场36个、蛇场4个、马场39个、羊场29个、猴场8个、鸡场29个、狗场20个、猪场19个[3],与邻近的云南省87个十二生肖专属街相比明显较多[4]。刘洪瑞、吴大华2016年对259个场地名的地区分布进行了统计,其中贵阳市7个,六盘水市35个,遵义市6个,安顺市49个,黔西南州24个,毕节市72个,黔南州50个,黔东南州12个,铜仁市4个,以县级行政区划看,全省88个县(市、区)51个有十二生肖命名的镇[5]。可见场地名在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分布,如果算上含有十二生肖单字或者变音的地名,其覆盖范围更广。
大量场地名的存在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地名重名现象。通过以乡镇为口径进行统计,全省含有十二生肖字或者类似字的乡镇(街道)有187个,其中含有龙字的有48个县70个乡镇,含有马字的有28 个县34个乡镇,含有羊字的有12个县12个乡镇,含有牛字的有11个县11个乡镇,含有鸡字的有10 个县11个乡镇,含有猪(或其变称珠)字的有9 个县、10个乡镇,含有猴场的有5个县5个乡镇,含有狗场地名的乡镇有4个县4个乡镇,含有猫字的乡镇有4个县4个乡镇,含有蛇(也叫顺)字或者与蛇有关的乡镇有3个县3个乡镇,含有兔街的乡镇有1个,涵盖了除鼠场外的所有场名,涉及全省绝大多数县份。从场名也可以看出,在十二生肖中最受欢迎的是龙,较受欢迎的是马、羊、牛、鸡、猪等。其中以龙场、牛场、马场、羊场、鸡场和猪场的重名最多,有以龙场(或龙场的变名龙昌)命名的乡镇10个,分别是凯里市、织金县、修文县、纳雍县、威宁县、贞丰县的龙场镇,水城县的龙场苗族白族彝族乡,七星关区的龙场营镇,福泉市龙昌镇,兴仁市的新龙场镇。有以牛场(或其变名流长、长流)命名的乡镇9个,分别是织金县、福泉市的牛场镇,施秉县的牛大场镇,六枝特区、大方县的牛场苗族彝族乡,白云区的牛场布依族乡,清镇市的流长苗族乡,息烽县的流长镇,晴隆县的长流乡。有以鸡场(或雉街)命名的乡镇8个,水城县、晴隆县的鸡场镇,盘州市的鸡场坪镇,普定县的鸡场坡镇,西秀区鸡场布依族苗族乡,织金县的鸡场苗族彝族布依族乡,七星关区的小吉场镇和赫章县的雉街彝族苗族乡。有以猪场(朱昌或者珠藏或者珠市)命名的乡镇有7个,纳雍县猪场苗族彝族乡,兴义市猪场坪乡,观山湖区、七星关区朱昌镇,织金县、瓮安县珠藏镇,赫章县的珠市彝族乡。以羊场(羊昌)为名的乡镇有6个,大方县、镇远县的羊场镇,盘州市羊场布依族白族苗族乡,纳雍县羊场苗族彝族乡,乌当区羊昌镇,平坝区羊昌布依族苗族乡,威宁县的羊街镇。以马场命名的乡镇6个,平坝区、普定县、大方县、织金县的马场镇,福泉市的马场坪街道,罗甸县的木引镇(位于马场村,也叫赶马场)。以猴场为名的乡镇5个,瓮安县、紫云县、威宁县的猴场镇,普定县的猴场苗族仡佬族乡,水城县的猴场苗族布依族乡。含有猫场或者有猫字的场坝有4个,大方县、织金县的猫场镇,普定县的猫洞苗族仡佬族乡,紫云县的猫营镇。含有或者以前叫狗场的乡镇有3个,观山湖区的金华镇(场坝地叫狗场),紫云县的大营镇(场坝狗场),修文县的久长镇(以前叫狗场)。以顺场为名或者与其相关的街道有3个,有水城县的顺场苗族彝族乡,七星关区的青场镇,大方县的顺德街道。以兔场命名的乡镇是威宁县兔街镇,虽然没有鼠场命名的乡镇,但不少地方也包含有鼠场的地名,如紫云县的宗地乡就有鼠场村。除此之外还要一些新场、老场的称呼及其变种,如乌当区的新场镇,六枝特区的新场乡,西秀区的新场布依族苗族乡,水城县的新街彝族苗族布依族乡,盘州市老厂(场)镇(现在更名为竹海镇),也有一些与特殊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场坝乡镇,如赫章县的铁匠苗族乡、威宁县的盐仓镇、威宁县的威宁县的麻乍镇,万山区的鱼塘侗族乡。还有一些与苗族生产娱乐有关的场名,如金沙县的鼓场街道、石场苗族彝族乡,印江县的罗场乡,沿河县的板场镇,三穗县的款场乡。有一些是场的变种,如金沙县、思南县的长坝镇,思南县的大坝场镇,松桃县的世昌街道,松桃县的大坪场镇,松桃县的长坪乡,晴隆县的大厂(场)及贞丰县的平街乡。
截至2019年9月,在全省1438个乡镇地名中,含有十二生肖场地名乡镇的有62个,占总数的4.3%,加上其他含有场字的场名及变种场名占到76个,占总数5.3%。在62个十二生肖场名乡镇中有38 个是少数民族乡或者在少数民族县或州,占到场地名乡镇总数的61.3%,其中有36个乡镇是苗族聚居区,占总数的58.1%,苗族聚居区占少数民族聚居区的95%。由此可以看出,以场命名的乡镇和苗族有很大的关系,可以看成是苗族文化的标签,场分布的地方不仅指示是苗族居住的地方,同时也代表了苗族迁徙的分布,从62个场地名的分布看,毕节市最多23个,主要分布在织金(6)、大方(4)、威宁(4)、七星关(4)等地;安顺市10个,主要分布在普定(4)、紫云(3)、平坝(2);贵阳市8个,主要分布在观山湖(2)、修文(2);六盘水市7个,主要分布在水城(4)、盘州(2);黔南州6个,主要分布在福泉(3)、瓮安(2);黔西南州5个,主要分布在晴隆(2),黔东南州有3个,与遵义、铜仁分布比较少的地区相比,这些区域不仅是苗族迁徙经过的重要地区也是当下苗族聚居和活动的地区,这些区域与苗族西部方言区传颂《亚鲁王》的在贵州分布的区域相重叠。如此看来,场的分布必然与苗族生活和史诗《亚鲁王》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关联,场分布的背后必然是某种文化性的因素导致的,而不是因为经济发展到了使用干支难以表达过多赶场次数的原因[6]。
二、《亚鲁王》史诗与场地名重名
《亚鲁王》史诗是苗族古老的史诗,它的发现被文化部列为2009年中国文化的重大发现之一,它的发现、记录与出版被认为是改写了“已有的苗族文学史乃至我国多民族文学史”,是“原始农耕文明时代的文化佳作,为中国文化多元化增添了新元素,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个新家族”[7],是“口述的、诗化的民族史”[8],是苗族传统文化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口述文化经典型作品,《亚鲁王》的叙述是“以数千年的历史征战、逃亡、迁徙、开拓为经,以几千名古代苗族人物、四百余个苗语地名、二十余个古战场的壮烈场景为纬,展开了极其波澜壮阔的英雄历史画面,将一个民族及其先祖的创世史、征战史、迁徙史融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诗篇”[9],对于研究苗族古代社会思想文化、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和生命生态观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对于揭示《亚鲁王》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传统文化传承保护、促进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能。具有文学、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神话学、地名学、艺术学、语言学、生命美学、生态民族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史诗对苗族场地名文化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
史诗中记载了许多关于苗族在迁徙过程中按照十二生肖来构建场地名的内容。苗族的祖先原本是居住在天外的空间,在史诗的开头,哈珈是最早的先祖,“哈珈生哈泽,哈泽生哈翟,哈翟生迦甾,迦甾生迦臧,迦臧生弘翁,弘翁生翁碟,翁碟生了火布冷”,火布冷生了火布碟,火布碟吃完了勒咚牛集市、兔集市的大田坝,面临粮食危机,于是迁徙到戈云定都,火布碟的儿子火布当在新的居住地按照十二生肖的方式开始建立十二个场坝,作为苗族的物理生存空间,十二个场坝是早期苗族生活的世界边界,代表着十二片领地。
火布当来造十二个集市,
火布当在天外的中央建龙集市,
火布当到十二集市中间造蛇集市,
火布当在大路上的卜朵建马集市,
火布当到鸿琼造羊集市,
火布当在鸿莱建猴集市,
火布当到斡列造鸡集市,
火布当在榕瓤建狗集市,
火布当到榕喀造猪集市,
火布当在艾芭建鼠集市,
火布当到天外的中央造牛集市,
火布当在盎哝建虎集市,
火布当到榕盎造兔集市。
火布当扶十二个太阳到十二个集市转动,
火布当抬十二个太阳在十二个集市轮回[10]。
在十二集市中,每个场中都有自身特定的位置,龙场、牛场位于整个世界的中央,马场位于交通要道上。地处中央和道路上的场,因聚集了较多的人流和物流,往往比较容易兴旺不容易衰弱,因此龙场、牛场和马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较大的规模,往往成为苗族居住的中心地带或者定都的首选地,这从我省当下的各场的数量都可以看出,以龙场(或龙场的变名龙昌)命名的乡镇10 个,含有龙字的乡镇有70个,是所有场名出现频率最高的。亚鲁王出生后,按照苗族的生命规则,“树高分枝丫,鸟大飞出窝。树种长出多多树木,竹根发出蓬蓬竹子。十二棵树木共一个根桩,十二蓬竹子是一个根篼,十二只鸟从一个窝分飞。你们去寻找自己的疆域,你们要建立各自的领地”[11],亚鲁王的五个兄弟按照父亲的指示,分别迁徙到不同的地方去开疆拓土,“赛鲁去远方开垦荒地,赛鲁到远方开辟集市”。而亚鲁王和母亲则定都在天清气朗的龙集市诃锦甾,母亲博布能荡赛姑带领亚鲁王学会开辟和建造场坝,他们按照十二生肖来排列场期,定期开辟集市,在新的居住地建造生活的空间。
龙轮回到龙,
亚鲁母亲带亚鲁开辟嵩当龙集市。
蛇轮回到蛇,
亚鲁母亲领亚鲁建造脦珰蛇集市。
马轮回到马,
亚鲁母亲带亚鲁开辟埠庆马集市。
羊轮回到羊,
亚鲁母亲领亚鲁建造埠章哲羊集市。
猴轮回到猴,
亚鲁母亲带亚鲁开辟哈琼猴集市。
鸡轮回到鸡,
亚鲁母亲领亚鲁建造布鲁几鸡集市。
狗轮回到狗,
亚鲁母亲带亚鲁开辟建造果朔狗集市。
猪轮回到猪,
亚鲁母亲领亚鲁来建造果侬猪集市。
鼠轮回到鼠,
亚鲁母亲带亚鲁开辟建造憋哝鼠集市。
牛轮回到牛,
亚鲁母亲领亚鲁建造沙讼牛集市。
虎轮回到虎,
亚鲁母亲带亚鲁开辟鳖盎虎集市。
兔轮回到兔,
亚鲁母亲领亚鲁建造丐若兔集市。
龙回到龙,是指苗族按照十二生肖的方式来记日,形成了特定了日历计算周期,龙日的这一天在苗族地区也叫龙场,这就实现了场意识在时间维度和空间温度的统一,当龙场的这一天到来,人们按照龙日的安排开辟建造龙场。赶集是一种地方文化的时空存储体,作为空间的本质,时间在集市中处处绽放着自己的身影[12]。赶龙场,人们按照场期安排自身的生产作息,从龙的认知到龙场的记忆,再到龙场的商品贸易,构成一套完整的场文化体系。当“龙心”失去后,亚鲁王失去了庇护,战败后被迫迁徙到岜炯阴的地方,失去了鱼米之乡的田园故土,只能靠刀耕火种种植小米为生,然而在场文化的作用下,亚鲁王依然没有忘记建立自己的场域空间,他们再一次开辟场坝、从事贸易。
龙轮回到龙,
亚鲁王走马嵩当开辟龙集市。
蛇轮回到蛇,
亚鲁王骑马去脦珰建蛇集市。
马轮回到马,
亚鲁王走马埠庆开辟马集市。
羊轮回到羊,
亚鲁王骑马去章哲建羊集市。
猴轮回到猴,
亚鲁王走马哈琼开辟猴集市。
鸡轮回到鸡,
亚鲁王骑马去布鲁几建鸡集市。
狗轮回到狗,
亚鲁王走马果朔开辟狗集市。
猪轮回到猪,
亚鲁王骑马去果侬建猪集市。
鼠轮回到了鼠,
亚鲁王走马憋哝开辟鼠集市。
牛轮回到牛,
亚鲁王骑马去沙讼建牛集市。
虎轮回到虎,
亚鲁王走马鳖盎开辟虎集市。
兔轮回到兔,
亚鲁王骑马去建丐若兔集市。
亚鲁王在诃锦甾、岜炯阴所建立的集市所使用的名字是相同的,如龙场都是建在嵩当的,蛇集市建在脦珰的地方。在战争的威胁下,亚鲁王带领族人经历了漫长的迁徙,从岜炯阴(Blak Jongt Yind)开始,先后经历16个平原地带:哈榕冉农(Had Rongl Raeb Nongh)、哈榕冉利(Had Rongl Raeb Lim)、哈榕呐英 (Had Rongl Nab Yinb)、哈榕呐丽(Had Rongl Nab Lih)、哈榕呗珀 (Had Rongl Bied Bongx)、哈榕呗坝 (Had Rongl Bied Bak)、哈榕丫语 (Had Rongl Yab Yut)、哈榕牂沃(Had Rongl Nzangl Wod)、哈榕卜稻(Had Rongl Buf Daod)、哈榕梭洛(Had Rongl Soab Lod)、哈榕饶涛 (Had Rongl Raob Taox)、哈榕饶诺(Had Rongl Raob Njof)、哈榕咋唷 (Had Rongl Zab Yob)、哈榕咋噪 (Had Rongl Zab Nzaot)、哈榕比卡(Had Rongl Bid Kad)、哈榕比力(Had Rongl Bid Lil)。
经过平原地带,亚鲁王带领族人来到山区,走过6个山区地带:哈榕玛嵩(Had Rongl Mas Songd)、哈榕玛森(Had Rongl Mas Sengl)、哈榕甲炯(Had Rongl Jab Njongd)、哈榕哈占(Had Rongl Had Nzaed)、哈榕泽莱(Had Rongl Nzwl Laeb)、哈榕泽邦 (Had Rongl Nzwl Bangx)。继续迁徙,走过3个平坝地带:哈榕呛且(Had Rongl Qangf Qiel)、哈榕甬农(Had Rongl Yongb Nongh)、哈榕嘿旦 (Had Rongl Heb Ndaeh),穿过5 个高山峡谷地带:哈榕崩索让(Had Rongl Bongb Soab Rangf)、哈榕岜索久(Had Rongl Blad Soab Njout)哈榕麻阳(Had Rongl Max Yangs)、哈榕哈嶂 (Had Rongl Had Zangx)、哈榕呐岜(Had Rongl Nab Nblab),最终来到了既能保护族人又能养育子女的理想居住地——盆地荷布朵疆域(Heid Buf Dok),在夺取这片土地后,亚鲁王在哈叠(一说是现在的安顺一带)(Hat Ndef)定都后,他吩咐自己的十二个孩子前往十二个不同的地方去开辟集市建立场坝做生意,后来亚鲁王交托大业时,亚鲁王说“娃哩娃,你们已经做成生意,你们快回转,你们已去建好集市,你们快赶回。”
从以上史诗的内容可以看出,苗族是一个富含迁徙基因的民族,不仅在战争年代被迫迁徙,寻找既安全又富足的居住地,而且在和平年代,苗族按照树大分桠、鸟大分窝的自然扩展规律,主动迁徙到新领地,开辟新场坝,在迁徙中,苗族每到一个新地方定居,都按照十二生肖的规则建立场坝、开辟集市、从事贸易,拓展族群的居住空间,这构建了苗族的场文化体系,由于场文化的原因导致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场地名的重名现象,在所有的场中,龙场是第一个开辟的集市,因此龙集市的重名现象最为严重。在古代信息不通、交通闭塞的时代,人们之间的交流范围狭小,往往局限于县内或者县际附近之间的几个乡镇,跨市州的交流较为少见,因此重名问题不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干扰,反而成为一种民族迁徙的标识,对于死后回归东方故土的亡灵而言,场地名往往具有一定指路作用,因此场地名文化在广大苗族聚居区得到很大的推广。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的旅游、出行不断增多,地名重名现象导致严重的地名混淆和辨识的模糊性,地名重名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难题。从以上的统计来看,在省会贵阳等地区,场地名为了提高自身的辨识度,降低它的重名性,开始采用异字同音、异字近音甚至是颠倒名字顺序和增加压减等方式来解决场地名重名的问题,如龙场有的保留龙字,将场字换为昌字,取名龙昌,羊场改为羊昌。有的则只保留字的读音,如猪场改为朱昌、珠藏,牛场改为流长。有的在原有地名前后或者中间加字,如新龙场、鸡场坪、牛大场。有的则是又改名又加字但保留部分读音,如小吉场。苗族的场文化在迁徙中不断应用不断扩展是造成贵州场地名重名的重要原因。从场地名的分布来看,无论是经济较为发达的贵阳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的麻山深处,都广泛地分布着场地名,只是在发达地区场地名的更名时间更早,由此可以看出场地名重名的存在首先是民族文化的原因而不是经济发展程度导致的原因,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我们才能透析到场地名重名的内在本质,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人们为了提高地名的辨识度,对场名作了更改,但是场名的文字读音相似或者相近的痕迹依然保存,这体现了场文化的影响的深远性。
三、场地名存在的文化意义
场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苗族聚居区生产生活和娱乐的中心场所。场地名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名体系,不仅是苗族迁徙的结果也是促进苗族进行迁徙的重要文化因子,对于苗族迁徙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1.地理标识
地名最基本的功能和意义在于指定一定的地理方位,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发挥标识的作用,从而构建起共同认可的外界活动空间和地理边界。赋予一个地理环境一个地名,不仅是将自然纳入人的管理体系,同时也是人对自然认识和相互适应的结果,有的地名带山、带水、带塘、带坪,无不是与地形水文结合的结果,带有更好的地理意义上的指向作用。根据史诗中场地名的建立情况,可以看出每一个场名对应一个实体地名,如龙集市对应嵩当、蛇集市对应脦珰、马集市对应埠庆、羊集市对应章哲、猴集市对应哈琼、鸡集市对应布鲁几、狗集市对应果朔、猪集市对应果侬、鼠集市对应憋哝、牛集市对应沙讼、虎集市对应鳖盎、兔集市对应丐若。随着时间的变化,场地名慢慢保存下来,而实体地名则逐渐消失,但在少数乡镇这种传统得到了保护,如紫云县的宗地镇,镇名为宗地(中地),但镇上政府驻地的集市贸易则名为龙场(建在中央的场坝)。
每一个场的构建都有其特定地理位置,如像龙场一般建立在整个领地的中央,而且牛场与兔场一般靠近龙场,都位于中央,兔场在苗族的场名体系里更是与龙场位置十分接近,几乎可以相互代指,如亚鲁王定居的诃锦甾既是龙集市也是兔集市。而马集市位于交通枢纽的位置,如贵州很多马场镇都位于主要的交通要道上。在贵州的场地名体系中,往往以龙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以十二生肖组成的农村商贸体系,如以紫云县宗地乡的龙场集市为中心,附近分布着鸡场(今罗甸县木引乡的摆落村)、马场(罗甸县木引乡的政府驻地)、鼠场(紫云县宗地乡的鼠场村)、猴场(紫云县猴场镇政府驻地的集市贸易)、猫场(紫云县猴场镇的猫场村)、牛场(紫云县四大寨乡的牛场)、猪场(紫云县大营乡三合村的猪场)、羊场(紫云县格凸河村的羊场集市)、狗场(紫云县大营乡的狗场集市)、兔场(紫云县宗地乡的红岩村境内)、蛇场(紫云县宗地乡火石关村境内,罗甸县交砚乡的集市也称蛇场),类似的情形在很多以龙场命名的地方都存在。场地名通过其特殊的指代意义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构建起自身的标识体系,为苗族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发展中,苗族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亡的思想,即使是人死后,人的亡灵依然存在,为了让亡灵能够回到苗族的东方故土,回到祖奶奶的家园,苗族人通过在葬礼上吟诵《亚鲁王》史诗,并通过砍鸡、砍马等丧葬仪式程序按照苗族人的古老地名返回到祖奶奶的地方,不至于飘零四方。场地名的建立往往是以各个中心地带展开的,龙场往往是国都的所在地,作为一个地区的中心场所,有利于指引本地区周边的苗族亡灵回归到中心的位置,继而开始沿着场地名和祖先迁徙的轨迹进行东迁,最终回到祖奶奶的住地。因此通过场地名体系,亡灵能够找到回归故土的路线和方位,实现了苗族群众生扩死归的圆满闭合。
2.商品贸易
场在广大农村承担着商品贸易的功能,赶场是一个集体性的经济活动及民族文化的展现。从产品交换的背后可以发现一个地区的语言文化、节日文化、服饰文化和民族风俗特征,这是一场地区的农村集体买卖活动,也是一场热闹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可以称之为农村文化盛宴。每遇场期,各村寨的家家户户都要穿着干净整齐,带上粮食、水果、蔬菜、牲畜、中草药等各种农村土特产品到场上去卖,同时从场上买回自身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生产用具等,在赶场天可以看到在通往集市的各条路上,人员来来往往,车辆川流不息,而场上则是挤满了成百上千形形色色的人,既有小摊小贩,也有从外地来搭棚卖衣服及日常百货,平日里安静的街道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不仅是乡镇内部的群众参加,邻近的乡镇也会成群结队地来赶场。有一些做生意的人根据各地场期的安排,在不同的乡镇轮回赶场买卖商品,被称为赶“转转场”,他们是本地的专业生意人。这种赶场的冲动也许是人们内心深处追求热闹和集体接近的需要。大家共同在场的情境,提供了比间接交流形式更丰富的关于他人的思想、感觉和真诚度的信息[13]。通过场上讨价还价的交易过程中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人们在语言上、思想上、心理上和价值取向上进行交流,实现了民族间文化的交融和传播,拓宽了人们的社会圈、生计圈、经济圈和文化圈。在很多少数民族乡镇,场还代表了一定时间概念,每一个月对应一个生肖,一年十二个月代表十二个生肖场,每一天对应一个场,村民赶集的活动不仅是贸易,更多的追求一种对赶场生活状态的体验,一种绵延着的时间感受[14]。既然含有贸易之外的因素,因此“不需要天天做买卖,所以这类集市隔几天才有一次”[15],按照十三天进行轮回推算,有些地方按照“空五赶六”的方法来赶甲子场,如花溪高坡赶亥巳日,即赶猪场蛇场,而烂泥沟则赶猫场猴场。场成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文化因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指引人们的行为活动。
苗族所建立的十二集市是苗族地区开展商品贸易的重要手段,通过十二场的分布可以将不同地区的产品传播销售到家家户户,根据苗族十二场的场期的设定,几乎每天都有赶场,一个轮回需要十三天,如此高频率和深入的场期安排体现了苗族对商业贸易的重视。史诗中记载了吒牧在说服雷公时讲述了十二生肖场的贸易过程:
你姑娘波妮冈孃到远处做买卖。
十二个集市,
她要去十二天。
十二个场坝,
她要走十二夜。
…………
她要去一个对场十三天才回,
她得走一个对场十三夜才转。
按照一天赶一场长期规定,十二个场赶一个轮回需要十三天。苗族的十二生肖场名体系充分揭示了在没有史书记载的苗族居住区,在很长的历史时空中维持着自身发达的商贸文化。场文化可以看作是隐藏在苗族文化深处的一种宝贵的文化,这是《亚鲁王》史诗带给我们的又一重大发现,史诗中讲述了亚鲁王及其先祖如何建造场坝、如何赶场、如何在场上做生意,如何开展贸易,如何通过贸易打探军情的有关信息。在亚鲁王年轻的时候,史诗记录了亚鲁王随着母亲开辟场坝、建造场坝的经历,记录了亚鲁王在场上卖牛、买战马的经历,亚鲁王收复失地后,带领士兵继续建造场坝赶场做生意,发现盐井之后,记录了亚鲁王如何在场坝上卖盐做生意的过程,即使是在亚鲁王逃难到荷布朵疆域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时,依然吩咐自己的十二个孩子去开辟场坝做生意,以上的种种事迹表明,在远古亚鲁王居住的贵州大地上,已经孕育了以十二场坝为主的苗族商业文明,这种商业文明时间至少可推测到秦汉时期甚至更早。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可见早在公元前135年的汉武帝时期,夜郎地区的苗族就已经与蜀地和南越建立起经济贸易关系,这种枸酱的商贸转运很可能是通过苗区的十二生肖场文化体系实现的,因为在四川和贵州等地的苗族同属西部方言区苗族,都是场文化的覆盖区,也是《亚鲁王》传颂的地区。
3.文化交流
施坚雅认为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不是村庄,而是基层社区[16]。苗族地区的场坝是苗族地区与外族共同做生意的场所,通过十二场苗族人将外来的先进的技术和物质文化产品转送到本居住区,弥补了小农经济时代物质产品上的不足和匮乏,维持了各类人群的生计。场文化的长期存在也带动了后来者不断的加入,大量的汉民、彝民等非苗族群众的加入,通过在商品买卖和交易中,促进了不同地区不同族别实现了在语言、风俗和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这体现了苗族文化具有开放性向外学习的一面。首先是语言上的交流。在赶场中,很多地区汉语还是通行的语言,学会了汉语才会克服语言上的障碍,才会在讨价还价中具有语言上的优势,因此在现实中很多苗族人在赶场时对汉人使用汉语,对苗人使用苗语。其次是巫文化上的学习,苗族是一个巫术文化十分发达的民族,这种巫术也通过市场的方式传播到汉族地区,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居住区在巫术文化上与苗族有很大的类似性。再次是服饰文化的交融。在场坝上,为了迎合苗族客户的需求,很多商贩开始研究学习苗族的服饰文化特征,有目的性地制作销售带有苗族条纹的衣服,同时促进了本民族对苗文化的认同和理解,在贵州西部很多乡村地区,用于背小孩的背带上绣有各种具有苗族迁徙条纹和蝴蝶图案,在广大汉族聚居区也广受欢迎。
4.管理体系
十二生肖场名体系对苗族的日常生活而言还是苗族人对地理环境、时间资源、信息资源和农事安排的管理的象征,不同地方代表不同的场名,需要在不同的时间才能赶场,从事不同的贸易。每一个场都有一个特定的地理方位,对应一个特定的时间周期和贸易行为,这种场文化体系已经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特征的不可磨灭的组成部分。场因为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群和商品,每一种人群和商品背后都有其特定的信息关系和行为追求,因此通过对场上人们的买卖行为和物品的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地区的资源分布状况和人员聚集状况,有的时候场作为信息集散的中心枢纽,还是打探军情的重要场合。如诺赛钦、赛钦讲通过与波丽莎、波丽露做绸缎生意,使用计策骗取了护佑亚鲁王的龙心。赛阳赛霸通过对集市贸易的观察,发现亚鲁王三年没有来赶集买盐,推断亚鲁王得到盐井。赛阳赛霸说:“我们幺弟亚鲁啊,三年没来做生意,三年不来赶集市。他没有去买生盐,他不再来要盐巴。也许他有了生盐井?莫非他得到盐井了?”当赛阳赛霸未来争夺盐井兴兵拉攻打亚鲁王时,在场坝上做生意的亚鲁王士兵提前知道了赛阳赛霸入侵的消息,让亚鲁王提前得知情况。场因为作为信息中转的重要场所,体现了苗族人对外界管理和自我管理的特征。
四、保护十二生肖场地名体系的建议
十二生肖场名体系的存在尽管导致了大量的场地名重名现象,但是就文化意义上而言,十二生肖场名文化体现了苗族古老的商业文明思想和迁徙文化,对于研究早期苗族经济特征及其倾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新的时期,场地名需要在重名上进行调整,要按照稳定存量、控制增量的原则继续优化对场地名的管理,不断加大对场地名的历史文化背景、集市形成规则及集市行为过程的研究,合理地引导各级政府有意识地做好场地名的保护,防止对场地名进行任意的破坏,在场地名比较集中且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地方,可以加大乡镇地名演变及其来源的研究,做好地名历史及文化的整理和收集,探讨场地名变迁背后更多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地名文化的民间故事和人文知识,通过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场地名文化体系进行保护和开发,加大对场地名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更多有历史意义的资料,进一步丰富苗族的场地名文化体系,把其打造成为与《亚鲁王》文化和苗族迁徙文化研究相互印证的重要组成部分。